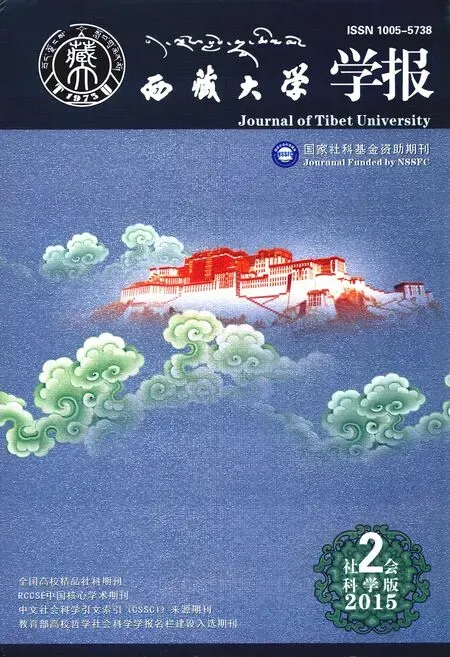清代布达拉宫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摘要:清代布达拉宫的历史是一部清代西藏的历史。五世达赖喇嘛修建布达拉宫时追叙吐蕃时期松赞干布在红山之顶修建宫殿的历史,寓意其所修建的布达拉宫是对吐蕃历史的继承。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受清廷册封后移住布达拉宫,开启了布达拉宫作为清天下秩序中西藏地方政、教权力中心的历史。五世达赖喇嘛之后,布达拉宫作为历辈达赖喇嘛坐床、驻锡、修行、执政、圆寂以及各种宗教活动的举行地,见证了清代西藏地方历史的发展。在晚清布达拉宫的历史书写中,无论其作为古代西藏建筑的集大成者地位,还是其在清代西藏地方历史创造中重要的政教地位,都成为史家笔下彪炳史册的书写。
DOI:10.16249/j.cnki.1005-5738.2015.02.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738(2015)02-099-09
收稿日期:2015-02-23
作者简介:陈鹏辉,男,汉族,陕西岐山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西藏历史文化。
清代布达拉宫的历史是一部清代西藏的历史。清初,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接受格鲁派上层林麦仲夏等人的建议,在红山之顶主持修建了布达拉宫白宫。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受清廷册封后移入布达拉宫,由此开启了布达拉宫作为清天下秩序中西藏地方政教权力中心的历史。此后,布达拉宫在外在的建筑规模上成为西藏古代建筑的集大成者,在政治、文化、宗教、艺术等诸多领域浓缩了清代西藏历史。历史记载中非常有趣的是,清初与晚清的诸文献展现了布达拉宫的两种场景,前者是充满神话色彩的历史记忆,后者是对客观存在的书写;前者源于对松赞干布在红山之顶修建宫殿的历史想象,后者源于五世达赖喇嘛继承这一历史想象修建布达拉宫。在布达拉宫从历史想象到历史存在的创造过程中,有诸多相关重要问题值得探讨,以下就清初文本中的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修建布达拉宫、清天下秩序中的布达拉宫以及晚清布达拉宫历史的书写等几个重要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一、历史记忆:清初文本中的布达拉宫
清初,红山之顶仅存“法王洞”和“观音堂”等处遗迹,然而历史文本中保存了松赞干布在红山之顶所建的宏伟宫殿的历史记忆。五世达赖喇嘛于1643年前后写成的《西藏王臣记》载:“(松赞干布)王又思维,若与布达拉山顶修建宫室居之,则四邻邦主,仰慕于我,必油然来归”,“乃于此处修建王宫。其宫如帝释天堂移来人间,华丽悦目;如天庭玉阶,高俊威严”。宫殿落成后,“四邻邦主莫不心生畏惧” [1]。此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的诸藏史中或多或少均有记叙。被认为松赞干布本人所著的《柱间史——松赞干布的遗训》记载,松赞干布到拉萨后,寻思“究竟在何方成利益众生大业为宜?”“忽然想起先祖拉托托日年赞曾在红山上居住过”,“于是决意在红山上兴建宫殿”。 [2]成书于14世纪的《西藏王统记》两次提及此事。一次是松赞干布因“先祖曾居”而决定往此居住,“修习佛法,做利益众生之事”,不过未载明具体时间,且此次当没有大规模的修建。一次明确记载于木阴羊年,即公元635年,在赤尊公主建议下,修建了“内有红色宫室九百间,连同顶上国王的寝室共计一千间。一切宫室屋檐,装饰着珍宝,游廊台阁,都有铃铛摇曳发声,显得堂皇富丽”,“和大自在天的圣妙宫殿相同,使人观尝无厌”的宫殿,后又在宫殿的南面为赤尊公主修建了高大宽敞、美妙壮丽的寝室,与国王的寝室之间有铁桥相连。 [3]该书还记载了宫殿落成后,从尼泊尔迎请秘密化身佛像——世自在观音像的详细迎请经过 [4]。作者意在强调,此次修建成了规模宏大、气象威严的宫殿,成了赞普权威的象征。成书于15世纪的《汉藏史集》与成书于16世纪的《贤者喜宴》,较之《西藏王统记》对红山历史的追叙更远,而对兴建原因以及宫殿宏伟规模的记载,与《西藏王统记》一致 [5]。
上引诸书记载最早的是《柱间史》,其后诸书明显可见后者援引前者,且成书越晚,记叙越夸张。五世达赖喇嘛在修习过程中博览群书,上引诸书都在他的涉猎范围之内。此外,在《西藏王臣记》写作中,他还常常参考引用《玛尼全集》、《拔协》、《青史》、《红史》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著作。尽管上引诸书是在浓郁的宗教语境中记人记事,但其浓墨重彩的记叙勾勒出了几个重要的历史线索:第一,松赞干布在红山顶兴建宫殿的时间与原因。《西藏王臣记》及此前诸书记兴建时间是木阴羊年(635年),这点基本一致,此后成书的藏族史大都沿用此说,如成书于1748年的《如意宝树史》。关于兴建原因,“王妃建议”当仅仅是个直接原因,根本原因是松赞干布当时的政治需要。第二,松赞干布所建宫殿毁损的时间与原因。《西藏王臣记》载:“(芒松芒赞时)唐军果至,纵火烧布达拉宫”,又记:“(赤松德赞时)以此触怒藏地鬼神,雷击红山宫以及年岁饥馑”。 [6]《青史》亦载赤松德赞时,雷击红山王宫 [7]。五世达赖喇嘛说他曾仔细阅读过 [8]《青史》,《西藏王臣记》所记的“雷击说”当属引自《青史》。《青史》记雷击原因,是大臣玛香毁灭佛法所致,这符合当时情况。两书记载说明赤松德赞未亲政前,红山宫殿遭雷击,毁损过一次。至于《西藏王臣记》所记芒松芒赞时期遭唐军纵火烧毁一说,遍查《西藏王臣记》成书前的诸汉藏文诸史,均无记载,当属杜撰。《白史》也说诸史书“无汉兵进藏之记载” [9],对此说提出了质疑。但此说影响到以后,18世纪中叶成书的《如意宝树》就予以引用说:“芒松赞时期与汉人交战,汉兵来藏时,大臣噶尔(禄东赞)战死疆场,布达拉宫被烧毁”。比《如意宝树》稍晚成书的汉文史书《卫藏通志》记载:“后因藏王莽松(芒松芒赞)作乱,官兵拆毁布达拉,仅存观音佛堂一所” [10],此书作者一度在藏任职,有过亲身考察,记载当属谨慎。由此,松赞干布在红山所建宫殿,后世多次遭毁,其中芒松芒赞时遭毁是因为吐蕃内乱,毁于吐蕃兵燹,与唐军无关,遭毁的根本原因是佛教社会秩序的失控。
清初历史文本中力图把松赞干布在红山顶修建宫殿,与其修习佛法联系起来的记叙有不攻自破之处。虽然松赞干布本人倡导佛教,但当时苯教的势力仍然很大,顽强抵抗佛教,强调松赞干布在红山修宫殿的目的是弘扬佛法显系佛教徒的臆造。后世松赞干布的“法王”形象系佛教壮大后佛教徒对其倡导佛教开创之功的追奉,上引诸书是在佛教所创造的赞普神话系统语境下追溯松赞干布的“法王”形象,主观意象超于历史真实之处的明显指向是,把赞普居住地的威严性转化为“法王”居地的神圣性。
二、历史创造:五世达赖喇嘛修建布达拉宫
清代布达拉宫的初建是应蒙藏上层联合掌政西藏地方的甘丹颇章政权的建立而建的,清初历史文本中松赞干布在红山之顶所建宫殿为五世达赖喇嘛主持修建布达拉宫提供了蓝本。五世达赖喇嘛原来的驻锡地哲蚌寺的“甘丹颇章” [11],是其处理格鲁派宗教事务的中心。1642年,蒙藏上层联合掌政西藏地方的权力格局一经确立,格鲁派成为统领全藏宗教事务的教派,格鲁派领袖五世达赖喇嘛成为全藏的宗教领袖,哲蚌寺的甘丹颇章实际上从格鲁派宗教领袖驻锡地转变成了新生的蒙藏上层联合掌政西藏地方的权力中心,而此时新生的甘丹颇章政权面临急需巩固的严峻形势,营建权力中心成为当务之急。一年后(水羊年),格鲁派掌权人物之一林麦夏仲向五世达赖喇嘛提议修建布达拉宫,五世达赖喇嘛以“对于城堡之类没有什么贪图之心”,予以拒绝。不过紧接着说:“(林麦夏仲)在教法方面与文殊菩萨没有两样,在世俗方面将他喻为大梵天王也当之无愧,他虽没有圣贤之称,但具有关心教法众生的大圣人的性状,长期坚持闭关修习总摄三身之法”。 [12]可见,尽管五世达赖喇嘛回绝了林麦夏仲的建议,但对其的高度评价说明,林麦夏仲的建议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经过一番酝酿,1645年,五世达赖喇嘛最终采纳了林麦夏仲等人的建议,决定修建。《五世达赖喇嘛传》载:“(木鸡年)以上师林麦夏仲为首的许多高低贵贱为首的各阶层人士向我提出,如果当今没有一个按地方首领的规则修建的城堡作为政权中心,从长远来看有失体面,从眼前来看也不甚吉利。再者,贡嘎庄园离色拉和哲蚌寺等寺院又很远,因此需要在布达拉山进行修建。根据他们的建议,请求我去举行合乎福田施主心意的净地仪轨。于是,我就按照林麦夏仲的请求,于三月二十五日前往布达拉。” [13]
为构建布达拉宫的权威形象,五世达赖喇嘛颇费心思。其一,阐述选址的继承性与重要性。文成公主曾把吐蕃境域比作仰卧的岩女魔,红山处于岩女魔的心骨位置,即吐蕃的中心地位。在修建布达拉宫之时,五世达赖喇嘛详细重提为众佛教著述中津津乐道的“文成公主堪舆一事” [14],无疑是借用文成公主堪舆传说表达布达拉宫地位的重要性。再者,尽管当时宗教语境中松赞干布所建红山宫殿的壮观景象无存,但吐蕃以后尚有一些修复和新建。《白史》载:“布达拉宫,后时似为寺院之形相” [15],即其性质转变为为寺院或为宗教服务,规模远比原来的宫殿或以后的布达拉宫小 [16]。展现在五世达赖喇嘛眼前的仅有“法王洞”、“观音堂”等佛教性质的建筑,以及“白房子”一带僧人生活用房等建筑物。然而,五世达赖喇嘛执政时拉萨客观上已经成了重要的宗教中心,红山地处拉萨河谷中心,位于大昭寺西侧不远,地理位置十分显要,加上松赞干布此时已被佛教徒神话,其所修建的红山宫殿自然受到重视。“达赖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选择在这样的地址上大兴建筑,完全出于一个巧妙的构思。西藏既有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的传说,达赖五世也自称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这暗示他在西藏的地位应该与历史上的松赞干布相比。选择在松赞干布的宫室旧址上,在所谓观音菩萨居住的地方(布达拉)重建宫室,这就把自己制伏后藏迦玛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前藏、后藏和阿里的理想同吐蕃王朝的缔造者松赞干布的不朽事业联系在一起,给人们以‘一体相同’的印象。” [17]
第二,高度重视工程进展。五世达赖喇嘛联合顾实汗等蒙藏僧俗上层对工程的设计、施工以及殿内壁画绘制等各个环节予以高度重视。宫殿图由朗日却赞设计,五世达赖喇嘛亲自审定,并委派管家索朗绕登主持施工。藏历十一甲子之木鸡年(1645)三月二十五日亲自参加奠基典礼,以宗教仪式隆重举行了安放诸神灵位的各种净土仪轨,并特意安排由顾实汗的王妃将流落到青海的,据传为从吐蕃时期就曾供奉在红山上的松赞干布本尊神像——洛格夏拉像(世自在观音像)寻回供奉。四月初一日动工,大昭寺为迎请洛格夏拉像举行了隆重仪式,五世达赖喇嘛和顾实汗亲自带领大队蒙藏官兵护送神像至布达拉山安放,沿路拉萨的男女老少盛装打扮,僧人各持伞盖、法幢、旗幡、花束、神馐、熏香等各种贡品夹道迎送。神像安放到位后,顾实汗在像前大张喜筵,讲论此像历史;五世达赖喇嘛主持安放仪式,并举行了埋藏宝瓶、祭祀等仪式,祈求修建布达拉宫能庇佑西藏僧俗百姓。举行完各种仪式,由僧人破土动工,施工过程中,五世达赖喇嘛不时上山视察。 [18]藏历十一甲子之火猪年(1647)七月主殿基本建成。五世达赖喇嘛所建布达拉宫,包括以白宫为主体的山顶宫区、山前的宫城区和山后的湖区三个部分。 [19]
综上,五世达赖喇嘛修建布达拉宫的这一历史创造活动中,近千年的历史记忆发挥了重要作用。五世达赖喇嘛以宗教语境追叙历史,强调松赞干布兴建红山宫殿的目的以及所建宫殿的宏伟景象,意在强调此次修建布达拉宫是对吐蕃历史的继承;而对布达拉宫外观景象和殿内神像安放、壁画绘制等内外庄严实体景象的塑造,旨在把布达拉宫建构成甘丹颇章政权的中心和其政教地位的精神象征。
三、多重构建:清天下秩序中的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是清天下秩序中的重要一环。顺治十年(1653)四月,清廷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20],颁给金册金印。始自五世达赖喇嘛移入布达拉宫,西藏地方的宗教与政治权力在布达拉宫交融汇聚。在清廷主导下,西藏地方的权力网络以布达拉宫为中心得以逐步建构,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的权力象征。迄代表皇权威严的万岁牌位与乾隆肖像供入布达拉宫,是皇权进入布达拉宫的隐喻,亦是清天下秩序之于西藏加强的象征。
(一)西藏地方纳入清天下秩序
早在明亡清兴的历史演进中,后金政权与西藏地方上层的战略眼光就汇聚到了一起,双方相互遣使往来,为五世达赖喇嘛觐见顺治帝奠定了基础。1653年,清廷册封五世达赖喇嘛的同时,册封顾实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 [21]。这次册封,标志着五世达赖喇嘛作为藏传佛教领袖的地位,得到了清廷的正式承认和确立,表明西藏地方政、教首领与清入关前就已建立的关系转变成了西藏地方隶属于清朝中央的主权归属关系,清廷正式把蒙藏上层联合掌权的西藏地方纳入了清天下秩序之中;同时,这次册封开创了以后历辈达赖必须由中央政府册封的制度。
顺治帝后,清朝历代皇帝顺应西藏地方的情势变化,通过调整、完善治藏政策,主导西藏地方事务,不断提高巩固中央在藏权威。不管是西藏地方内乱,还是西藏地方遇到外部袭扰,清朝皇帝积极应对,适时调整西藏的行政体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治藏法规。特别是1792年的《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明确加强驻藏大臣的职权与地位,并且针对寻访认定转世灵童的流弊制订了“金瓶掣签”制度。《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是清朝全面的、系统的治藏方案,把对西藏的治理提到了法制化的高度,是西藏地方之于清天下秩序的制度化体现。
(二)布达拉宫成为西藏地方的权力中心
五世达赖喇嘛受清廷册封后移入布达拉宫,是布达拉宫成为清代西藏地方权力中心的开端。1653年,五世达赖喇嘛受封返藏后,其宗教影响和社会威望大为提高,哲蚌寺的甘丹颇章作为号令地,来“兴隆佛化”显系局限。此时,布达拉宫白宫内外工程告竣,五世达赖喇嘛遂以清廷册封的宗教首领身份移入并将其作为驻锡地。由于他兼具一定的政治地位,特别是代其行使权力的第巴就在此掌印办事,从此布达拉宫逐步成为甘丹颇章政权的中心,初具权力机构之雏形。
为保证政、教权力运行,白宫内设有作为政教使用的大殿、地方政府机构用房、摄政住所、达赖寝宫、达赖经师用房、达赖侍从用房、厨师以及各种用途的库房等。 [22]据1681年第巴桑结嘉措制定的《各级官员办事条例二十一则》,布达拉宫内达赖拉章初建时的机构为:①达赖内侍僧官系统有索本、僧本、却本,分别管理达赖喇嘛的饮食、起居和宗教活动;达赖座前办事者有桌尼管接待宾客,仲译为秘书,管达赖印章文件,强佐管理达赖商上财务总司出纳。②达赖内侍俗官系统有第巴,是在拉萨的高级官员。第巴属下有:文武官员和孜本(审计财产收支)、协尔邦(审理刑事案件)及拉萨和宗谿一级的行政官员。 [23]五世达赖喇嘛之后,“经过格鲁派多年的经营和努力,使得布达拉宫和和硕特汗王的联系比达赖喇嘛要松散得多,达赖喇嘛和布达拉宫一起成为藏区和蒙古各地格鲁派信徒崇拜和朝礼的中心。” [24]
布达拉宫的不断扩建以及在清廷主导下达赖喇嘛权力的提升,使布达拉宫作为西藏地方权力中心的地位随之加强。康熙二十一年(1682),五世达赖喇嘛圆寂,为安放五世达赖灵塔,第巴桑结嘉措亲自设计并主持修建了红宫。工程于1690年举行奠基仪式,1693年竣工,完工后举行了塔、殿开光仪式。修建期间,康熙帝高度重视,选派数百内地工匠予以支援。五世达赖以后,历辈达赖喇嘛的坐床、驻锡、修行、执政、圆寂以及各种宗教活动都在布达拉宫举行。迄清廷主导建立噶厦、设置驻藏大臣制度,对达赖权力做出明确规定后,除达赖内侍机构系统外,噶厦在布达拉宫内设有常驻机构,驻藏大臣在其内“叩谒圣容”、“传宣圣旨”、“唔见达赖”。如乾隆五十八年,福康安等制定“藏内善后事宜二十九条”后,“赴布达拉宫叩谒圣容,达赖喇嘛相见”,“将章程翻出唐古特字,与达赖喇嘛逐条详细讲论,并传集各呼图克图、大喇嘛等,及噶布伦以下番目,将藏内一切章程详细训示”,达赖喇嘛等感激圣恩,“几至堕泪”,表示所议各条,“实可垂之永久”,“从此谨守章程,事事与驻藏大人会上办理” [25]。综上,随着清廷对达赖权力的明确,布达拉宫内的权力系统随之完善,趋于系统化规范化,其作为西藏地方的政教中心地位加强,成为清代西藏地方权力的象征。
(三)皇权通过礼制进入布达拉宫
清代布达拉宫是皇权的隐喻。皇权至上的封建礼制在清代发展到了极致,当皇权通过封建礼制包容佛法进入布达拉宫,是皇权凌驾于布达拉宫世俗、宗教权力之上的象征。
第一,布达拉宫内权力运转以清朝皇帝颁赐的封印为依据。封官赐爵,印信为凭,封印是权力的象征。西藏地方僧俗首领以清朝皇帝所赐封印执印掌事,封印是以布达拉宫为中心的西藏地方权力运行的主要依凭。五世达赖以所封“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之印”,发布各类文书。此后,历辈达赖均以清朝皇帝颁赐的金册金印行使权利。清帝在西藏册封世俗爵位的台吉、贝子、贝勒、国公、郡王时都一并赐给印信。其中亦有请封以巩固自身地位者,如康熙三十二年,第巴桑结嘉措假借达赖名义上奏:“乞皇上给印封之,以为光宠”,并“愿缴玉印,乞给金印” [26],清廷认为“此事颇大”,酝酿之后赐给“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教弘宣佛法王布忒达阿白迪之印” [27]。西藏宗教、世俗首领在发布命令、文告等时,文末钤清帝所赐印章,表明是在清帝授予的职权范围内办事,尊清帝为天下共主,权力高于自己,印章文化体现西藏地方在制度层面接受认同清天下秩序。
第二,西藏政教首领尊称清帝为“文殊菩萨”。及至清代,西藏佛法社会秩序的理念已经根深蒂固,松赞干布被佛教徒追奉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达赖继享这一尊荣,亦被视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五世达赖喇嘛受封回藏后,在奏谢表文中,首次对顺治帝使用“一统天下文殊菩萨圣主陛下” [28]称号。“给在世的统治者冠以佛菩萨名号,这在西藏政教观念的发展中可称一件创举”,以后西藏地方凡上奏都尊清帝为文殊菩萨。特别是六世班禅朝觐乾隆帝时,以“文殊菩萨”尊称后,清帝在西藏地方政教首领心目中的“文殊菩萨”地位更加巩固。“用此称名表示达赖以宗教领袖的身份承认清主的政治权力,并将清朝整合入了西方蒙藏民族的宗教/政治世界,在此世界中的权力赋予方式除了军事和政治力量的强大外,还多了层属于宗教、跨越民族畛域的神秘面纱。” [29]
第三,皇权通过礼制进入布达拉宫突出体现在七世达赖喇嘛之后,历辈达赖都是在清廷主导下,在布达拉宫的乾隆皇帝肖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隆重的坐床典礼仪式。康熙三十六年(1697),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坐床典礼在布达拉宫举行,康熙帝专门派二世章嘉活佛阿旺却丹从北京前往参加,这是清帝第一次派人参加坐床典礼。康熙五十九年(1720),平朔将军延信率部护送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由西宁至拉萨,于九月十五日在布达拉宫主持其坐床典礼 [30]。七世达赖喇嘛坐床前后 [31],康熙帝派人送去汉、藏、满、蒙四种文字书写的“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金字牌位。七世达赖喇嘛把此牌位供奉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寝殿——萨松朗杰中,每年正月初一,率僧俗官员向此牌位叩拜,以后成为定制。乾隆退位后,派人专程给西藏送去他穿着僧装的画像。“乾隆朝对‘文殊菩萨’的尊称逐渐由‘名义’上的称呼转向‘落实化’于图像和文字赞颂,一方面除了如美国学者H.Kahn所指出,乾隆帝爱好各式的‘异国奇珍’,擅长使用‘宏伟’的政治美学去激发或驱使人们对他的敬畏和忠诚之外,由于乾隆/文殊的唐卡画或挂轴画出现的地方是在拉萨的布达拉宫和北京的雍和宫等政教地位显著之处,使得我们相信,如此意像之‘清帝=文殊’的具体化和实有化,证明清朝在逐步统治蒙藏民族的过程中,其权力根基在乾隆中期曾在仪式和艺术中有西藏化,政教合一化的倾向,在当时清人的想法中,如此当有助于清朝在蒙藏社会建立威望,令蒙藏人士在敬佛的心态下易于归心。” [32]1798年,八世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三界殊胜寝殿内特设殿堂供奉乾隆皇帝肖像。并作指示:“此大皇帝是众佛之父至尊文殊菩萨,为统治者所依赖者,是神和世间众人之顶礼对象。……我们对他的任何画像都须圆满崇敬供奉。” [33]1799年,乾隆帝驾崩,八世达赖喇嘛即“莅临肖像前叩拜” [34]。此后凡皇帝驾崩,达赖都要叩拜乾隆肖像,敬献哈达。由于此前乾隆帝制定了“金瓶掣签”制度,凡达赖和班禅转世灵童的金瓶掣签,均在“萨松朗杰”乾隆肖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从掣签仪式可见清朝握定呼毕勒罕之大权。” [35]不仅西藏地方僧俗首领朝拜乾隆肖像和“万岁牌位”,驻藏大臣到藏后首先要到布达拉宫“叩谒圣容”,一直到清末联豫、张荫棠驻藏时概莫能外。
综上,达赖、班禅等的坐床在布达拉宫内乾隆肖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是清代皇权通过礼制进入布达拉宫的隐喻。驻藏大臣“叩谒圣容”,对西藏僧俗尊奉皇权起到了宣示作用。此外,布达拉宫内,乾隆帝御赐的“涌莲初地”金字匾额、同治帝御赐的“福田妙果”匾额等在宗教蕴义之外,亦有时时宣示皇权的政治作用。
四、晚清布达拉宫历史的书写
历史书写基于历史创造。晚清时期布达拉宫在清天下秩序中的政、教中心地位已经确立,除作为佛教信徒的朝圣地外,布达拉宫亦是驻藏大臣、达赖和噶厦举行诸如重大会议、重要庆典及各类政治、宗教、社会等重要活动的历史场域。沿这一定制布达拉宫的历史创造与传承实现了双向并进,创造越丰富,传承越多;传承越多,创造越丰富。缘此,更加凸显了布达拉宫的历史地位,在晚清知识精英的历史书写中她势必成为彪炳史册的叙述。
(一)历史书写:文本中的布达拉宫
晚清时期,布达拉宫历史的书写者不仅只是藏族学者,还有驻藏系统的官员以及进入拉萨的各色西方人,他们出于各自的目的、立场和视角,多方位地呈现了布达拉宫的气象。
1.藏族学者的书写。晚清时期,藏族史学已步入成熟期,出现了一大批史学著作,其中大量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记载,无不与布达拉宫密切相关。比如记达赖在布达拉宫坐床、学经、接受佛教徒朝拜、举行宗教活动、政治活动以及圆寂等等。布达拉宫作为重要历史人物活动地、重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其中对布达拉宫的总体性记叙并不多,这当与此时布达拉宫的政教地位早已确立,成为僧俗百姓朝拜的圣地,作者们在熟悉的文化场域中,对此已经成为一种“文化自觉”,所以在历史书写时觉得乏善可陈。比如《如意宝树》对此一时期的布达拉宫的记载惜墨如宝。对当时情况泼墨较多的当属19世纪中叶成书的《卫藏道场胜迹志》,书中对布达拉宫内外情形均有记载。 [36]
2.驻藏系统官员的书写。清代驻藏系统官员的著作是其与清廷往来公文之外最珍贵的资料,晚清以来其著述中关于布达拉宫的记载比较丰富。《西藏志》记布达拉宫是“西藏第一胜区”。 [37]《卫藏通志》特别提及“金殿内供奉御容” [38],《西藏图考》记布达拉宫是“卫地之首庙”,并记乾隆二十五年,御赐“涌莲初地”庙额之事 [39]。《康輶纪行》 [40]、《西藏纪游》 [41]等均有记叙。此外,驻藏大臣的奏稿中常常亦有详记。驻藏系统的官员,均有在藏履职经历,他们处于当时西藏的文化圈中,亲眼目睹过布达拉宫;且他们除为政之外,为学也均颇有建树,其所书当属真实可信。他们所言既有对历史的钩沉,又有对当时情形的记载,全方位地展现了布达拉宫的宏伟壮观气象。
3.西方人的书写。晚清以来,各有目的的西方人通过种种渠道进入西藏,其笔下自然少不了布达拉宫。第二次侵藏英军头目荣赫鹏在其《英国侵略西藏史》中说,拉萨“惟布达拉宫气象森严”。在选择“拉萨条约”的签字地点时,他有意坚持要在布达拉宫举行 [42]。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埃德蒙·坎德勒(Edwund Candler)在其《拉萨真面目》中记:“这座居住着佛教领袖、菩萨化身的宫殿比起欧洲血债最多的中世纪城堡来说,它目睹的杀人场面和怂恿人去犯罪的情景更多。” [43]日本人青文木教在其《西藏游记》专辟“布达拉宫城拜观记”一章,分别从“观音菩萨的宫殿”、“系舟普陀(即布达拉)”、“庄严无比的红王宫”等几个方面详加考察布达拉宫的历史与现状,赞赏其是“世界无比的宫殿”,“是别开生面的建筑物”。 [44]来自异文化圈的西方人的记叙,有作为他者身份所能体会到的诸多新鲜感。荣赫鹏坚持在布达拉宫举行签字仪式,是因为他深知布达拉宫是西藏的权力中心。埃德蒙·坎德勒所言,是汉藏文诸史所未有的,很大原因在于著史者身在大清帝制藩篱之中,有的本身就是此种历史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对此种另面的历史视若平常。青文木教的兴趣较多的在于“布达拉宫”与佛教“普陀洛迦”的传说之间的联系。
(二)历史传承:晚清的布达拉宫
历史创造是历史传承的前提。清代西藏历史创造了布达拉宫的实体景象及其闻名于世的名称,亦在宗教、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为人类珍藏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
1.名称的传承。藏语“布达拉(po-ta-la)”系梵语“普陀洛迦”的音译,普陀山与洛迦山隔海相望,佛教经典中说观世音菩萨先在洛迦山修行得道,后在普陀山开辟道场,而在流传中,普陀洛迦常常连在一起。藏族史记载松赞干布曾在红山(藏语“玛波日”,清末汉文文献中时有出现)之顶修建宫殿居住,后世佛教徒追认松赞干布为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五世达赖喇嘛修建白宫时,发挥这一历史,在其笔下“红山(dmar-po-ri)”被改为饱含宗教色彩的“布达拉山”,并把所建宫殿命名为“布达拉宫”。“布达拉宫”藏语意为“孜布达拉”(孜,意为最高、顶尖、至尊)、“颇章布达拉”或“孜颇章”(颇章意为宫殿)等。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康熙帝以“布达拉”指称布达拉宫所在的山,这是目前文献所见清帝最早提及“布达拉”这一名称的记载。其后的《嘉庆一统志》称布达拉宫为“布达拉庙”。可见,自清初五世达赖修建布达拉宫至晚清时期二百多年的流传中,“布达拉宫”作为一个富有宗教内涵的名称成为集体记忆;同时,“布达拉山”已成为一个固定的名称,指布达拉宫所在的山,其普陀山的宗教寓意也得到了广泛认同,原“红山”这一名称的历史记忆越来越模糊,其中佛教“普陀山”的传说是“红山”转变为“布达拉山”的根本原因。
2.文化遗产传承。及至清末,布达拉宫已是西藏规模最大、体量最为宏传的建筑群,体现了西藏古代建筑思想和风格的最高成就,其建筑特点被一些著名的寺院广泛借鉴 [45]。布达拉宫内汇集的赐品、壁画、塑像、灵塔等无数珍宝,“堪称文化之宫和艺术宝库”。被誉为“百科全书”的壁画,除体现宗教世界观的宗教画之外,“大量的具有明显的世俗化倾向” [46],展现出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和重要的历史场面,诸如,“林卡节图”、“猴子变人的故事图”、“文成公主进藏图”、“金城公主与赤德祖赞联姻的故事图”、“五世达赖朝见顺治皇帝图”、“十三世达赖入京觐见图”等等。大量以历史事件、人物传记、宗教故事、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为题材的壁画,内容贯通历史,蕴含着珍贵的文化遗产信息。
结语
布达拉宫是西藏佛教文明系统发展的产物。松赞干布在红山之顶修建宫殿时溯源于其“祖先曾居”,五世达赖喇嘛借松赞干布的观世音菩萨形象,寓意其所建布达拉宫是佛教神话系统中观世音菩萨的居地——普陀山。实际上,二人通过追叙历史,构建了观世音菩萨—松赞干布/法王/观世音菩萨—五世达赖/观世音菩萨这一传承系统,这一系统塑造了布达拉宫的普陀山意象,巩固了西藏佛法社会秩序,而“祖先曾居”则与吐蕃王系自天而降于山顶的祖先起源神话密切相关。
布达拉宫是清天下秩序的一个象征。清帝高度关注布达拉宫体现在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如上论及皇权通过礼制进入布达拉宫;第二层次是构建包容佛法的皇权体系,以此驾驭蒙藏地区的佛法社会。如康、乾二帝不仅先后在谕旨中大加论及“普陀有三”;而且扩建北京的雍和宫,营建经营承德的“小布达拉宫”。清帝西藏以外塑造布达拉宫的意象,实是构建皇权包容佛法的象征,这是清天下秩序的根本思想中融入了佛教社会秩序理念的体现,对实现世俗皇权驾驭广大蒙藏地区的佛教社会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清代布达拉宫的历史经由历史记忆,到历史创造,再到历史书写的过程,融汇贯通了西藏历史,她是西藏佛法社会秩序的产物,是清天下秩序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