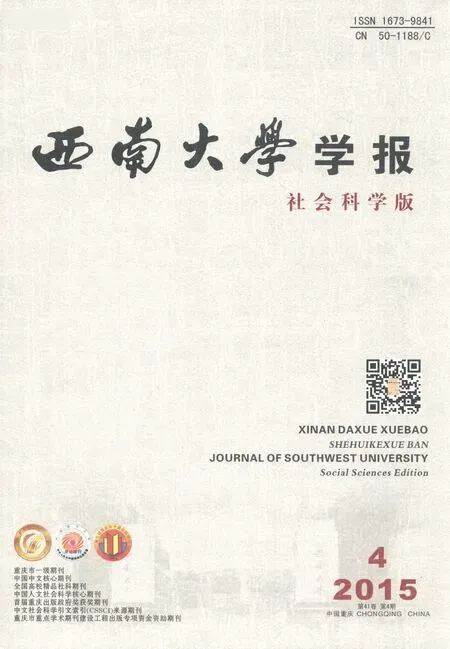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论雅可比的康德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
罗 久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哲学系,江西 南昌330031)
当人们谈起德国古典哲学时,首先总是习惯性地用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样一条逻辑进程来描绘它,似乎整个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对康德所开创的先验观念论哲学的发展和完善,而那些康德哲学最初的批评者和所谓的反理性主义者却很少能够以积极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1]。不可否认,康德的批判哲学的确具有一种世界历史的意义,通过他的理性批判,康德力图化解存在于理性与信仰、知识与道德、自然与自由之间业已尖锐的矛盾,将科学、道德、政治、法律、艺术和宗教等诸多领域的根基奠定在理性自身的统一性之下,这无疑开启了一种影响深远的思想范式。正如莱因霍尔德(Karl Leonhard Reinhold)在他的《论康德哲学书简》(Briefeüber die Kantische Philosophie,1786-1787)中所揭示的那样,康德哲学首先就不是作为一种新的知识理论,甚至不是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批判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相反,它被视为是一种为了捍卫自由、道德和宗教所做的精妙论证:实践理性公设作为一种“理性信仰”,一方面证明了自由的实在性,另一方面又能够承认现代科学世界观的有限的合法性[2]139。批判哲学的目的正是希望通过对人类理性能力的区分与限定,在自然科学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为纯粹出于理性自身的绝对法则、为人类的自由和道德重新奠基。然而,就在康德哲学稳步获得它在学院中的统治地位,并作为一种新的哲学范式被人们接受时,却有人看到了隐藏于其中的虚无主义后果,这是所有的主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哲学都试图避免却又难以逃离的深渊。这位欧洲虚无主义的最早的宣告者就是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可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1743-1819)。
虽然对雅可比哲学的研究在国内学界几乎完全缺失,但这种不重视并不能否认这位思想家的重要性。雅可比可以算得上是他的那个时代的一只牛虻,他不但挑起或加入了当时思想界最重要的三次争论(即莱辛的斯宾诺莎主义之争、费希特的无神论之争和谢林的泛神论之争),而且首次将一元论的体系性问题带入到哲学论辩的中心,并且营造了德国观念论者对康德哲学进行诠释的基本语境[2]95-96。就像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著名学者霍斯特曼(Rolf-Peter Horstmann)指出的那样,对于那些以康德为指向的观念论哲学家来说,雅可比的思考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不仅仅是康德最早的批评者之一,也不只是一种体系性立场的代表,他更是启蒙的理性观念和哲学基础的最具代表性的批判者[3]。正是雅可比对启蒙理性和康德哲学的批判,使后康德的观念论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了理性的本性,以及理性、信仰与绝对的关系,并且注意到康德的精神和他的字面之间的区分,这对于德国观念论的发展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在雅可比的两部主要哲学著作①即《关于斯宾诺莎的学说致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信》(Über die Lehre des Spinoza in Briefen an Herrn Moses Mendelssohn,1785)和《大卫·休谟论信仰,或观念论与实在论,一个对话》(David Humeüber den Glauben,oder Idealismus und Realismus.Ein Gespräch,1787)这两部著作。出版30年之后(1817年),黑格尔仍然在《海德堡年鉴》(Heidelberger Jahrbüchern)为其新版的著作集撰写了书评[4];而在后来的《哲学全书·逻辑学》的绪论部分和他在柏林大学所开设的关于哲学史的讲座中,雅可比始终都是黑格尔十分重视的一个批评对象,这在其耶拿早期的“信仰与知识”(Glauben und Wissen,1802)[5]一文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黑格尔看来,雅可比延续了康德希望通过理性批判来解决的问题,即通过对启蒙理性的区分和限制来论证“绝对”(Absolute)。但是雅可比认为,康德的观念论和所有理性主义哲学一样,当他们通过理性的演证,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主观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的后果,将一切本然之理和事物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定统统消解,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因此,要想真正把握绝对,就不能依靠理性的反思和推论,而只能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来通达上帝在他的启示中向我们揭示出来的绝对真理。
一、理性与虚无
尽管常常被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学者当作是“非理性主义者”,但如果从雅可比本人的哲学意图出发,他对理性主义者的批判实际上是为了从理性主义那里把理性拯救出来[6]96。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理性(Reason)是一种寻找理由的论理(reasoning)活动,这种理性认识必须遵循充足理由律(principle of sufficient reason):“凡存在皆有理由,凡结果皆有原因。”(There is nothing without a reason,or no effect without a cause.)[7]任何事物的存在都是有理由的,而构成此一事物存在理由的那个理由本身又是有另一个理由的,因此,在每个存在的事物背后都可以延伸出一个解释性的理由的序列。当我们这样来理解理性的本性之时一定想知道,这样一个理由序列会在哪里终结呢。这是一个永无休止之处的无限序列,还是一个我们能够最终完全把握存在的有限序列?如果是前者,那么在一个无穷无尽的理由序列中,所有在其自身的存在都被取消了,对理由的追问将使存在变成虚无。但是,根据莱布尼茨严格表述的理性主义的立场,理性要求有一个作为自因的无限的智性(infinite intelligibility)[6]96,即一个自足的、自我解释的理由,来充当整个条件序列的第一因,而这个第一因就是上帝。上帝依其概念就是本质与实存同一的至高存在,一切受造物的本质规定或实体作为上帝的造物都是自明的、不再需要以自身之外的其他任何东西为根据。因此,对理由的追问并不是没有终点的,确定的理性认识是可以达到的。
可是,在雅可比看来,把最终的根据归于一个无限智性的理念并不比虚无本身来得更好[2]97,它只是世界的虚无化之后不得不采取的一个补救措施而已。由于现实世界中一切事物都被取消了在其自身的存在,这个措施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规定,所以雅可比把充足理由律又叫做“从虚无而来的虚无”(nihilo nihil fit)[8]187。而且这样一种对上帝的援引和证明是没有合法性的,它只是独断地设定了上帝作为最高的实体,这一独断的设定与充足理由律的原则自相矛盾。如果要将理性主义的原则贯彻到底,那么上帝本身的存在也是需要理由的,所以,一种彻底的理性主义必然表现为斯宾诺莎主义。根据雅可比的看法,斯宾诺莎主义的核心主张是,作为第一因的上帝不能是一个超越的和合乎理性的存在物,相反,它必须与存在或自然本身相等同:上帝是理由序列的无限的总体性,而所有实体都是这个总体的样态或部分。因为:(1)如果第一因超越于条件序列的总体之外(在时间上先于创世而存在,在模态上能够不依靠创世而存在),两者对创世而言都会成为在先的理由,也就是说,在绝对的“有”之前还有条件,那么,第一因也就不再是第一因,或者变成以“无”为条件了,这与充足理由律是矛盾的[8]217,因此上帝只能与存在或创世同一;(2)合理性包含了表象和意志,其中,表象包含了与某个客体的关系,而意志包含了一种与自身的关系,但第一因是不能具有关系性的,有了这种关系性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表象和意志关系得以获得规定的理由,第一因就又变成有条件的和被决定的了[2]205-207。因此,第一因必须是条件序列的总体,即被认为是一个先于它的有限部分的无限的全体。无限的智性要求所有有限的存在物成为一个无限的实体的样态,也就是说,充足理由律需要将实在表达成一个“一元论”的体系。
这种始终一贯的理性主义是“无神论”,并不是因为它们不能将无限的实体称为“上帝”,而是因为对于雅可比来说,只有对一个超越的、神圣位格(有思维和意志)的信仰才是有神论的[2]363-364,但对于一个一元论体系来说,超越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与此相关,理性主义又必然导致“宿命论”,因为在这个条件序列的总体中,排除了无限人格与有限人格的一切目的和自由行动,只承认命运和机械因果律的盲目操纵;人至多被允许作为运动的观察者,而不是自由的行动者[2]193-194。因而,理性主义的最终后果就是“虚无主义”,因为存在是需要理由的,所以理性主义者把现实存在的事物都看作是有条件的,它否认一切自在的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除了条件序列的总体之外没有什么是无条件的,没有什么就其内在的本性而言是其所是,所以随着现实的虚无化,这个总体本身也不可能是真正有内容的、以自身为根据的根据,而只不过是一个混沌的、无根据的深渊(Ab-grund)[6]99,充足理由律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一切即一、一切即无[8]572-579。
根据他对斯宾诺莎主义的诠释,雅可比认为,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也只是另一种形态的理性主义,它将原本被归于上帝的那种无限智性重新赋予理性主体,从而完成了理性主义的自我神化。这样一来,理解某物就意味着给出使它得以是其所是的条件,我们所能够理解和认识的只是那些我们能够凭借理性的先天形式建构出来的东西,而不是事物自身的存在,所以先验观念论同样是一种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知识或真理被当作是“彻底的主观形式根据彻底的主观规则作用于彻底的主观直观”(um durchaus subjectiven Anschauung,nach durchaus subjectiven Regeln,durchaus subjective Formen zu verschaffen)的结果[5]351。因此,对理由的反思和对无限智性的追求导致对现实的、外部事物的取消,而代之以我们自己主观的观念性的构造[8]372-375。但是这种以逆推的方式达到的自明的先验自我和与之对立的物自体,就像传统理性主义对上帝的援引一样是独断的。在《大卫·休谟论信仰》一书的附录“论先验观念论”中,雅可比对康德哲学的内在不连贯性做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没有(物自体)这个预设我无法进入(康德的)体系,但是有了这个预设后我又无法停留在其中。”[2]336康德关于物自体存在,以及感性是不同于自发的知性和理性的一种被动的、接受性的能力的断言,实际上是一个未经证明的预设。因为,如果我们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而不是事物本身,我们又如何能够知道物自体是存在的以及感性是接受性的呢?一方面,康德认为,“存在”的范畴只能用于直观表象,而不能用于物自体;可另一方面,康德的体系又必须建立在物自身存在这个基础之上。如果物自体的存在只是一个调节性的理念,而不是实际存在着,那么一切知识都将缺乏与事物本身的相关性而成为纯粹主观的构造,可如果物自体真的“存在”,这就意味着它可以通过范畴来规定,那么物自体就是可以被认识的。所以,雅可比指出,如果康德的体系想要保持连贯,他就必须彻底抛弃物自体的概念而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观念论或主观唯心论,将整个世界看作是心灵的构造;要么就变成彻底的理性主义,即斯宾诺莎主义,认为世界就是一个遵循因果必然性的整体,其中一切都是被决定的,没有目的和自由可言。
二、从怀疑到信仰
正如黑格尔指出的那样,雅可比对现实事物的客观规定应当被否定并认为其中什么也没有的看法感到非常震惊和厌恶,因为理性探究的结果是主体的有限性、自我成为反思性的感觉和思维主体,而我的整个世界应当只是一个关于自在之物的空洞幻象。雅可比对虚无化所感到的厌恶伴随着他对现存之物的绝对确定性的信仰,这种厌恶将处处表明这就是雅可比哲学的基本特征[5]351。雅可比认为,如果知性规则或范畴只是根源于思维主体自发性的、经验的先天条件,而不是事物本身的性质,那么康德事实上并没有驳倒休谟的怀疑,因为概念的联结只是主观理性的逻辑功能,根本不同于事实的联结。因此,在雅可比看来,主体的知性概念必须同时完全存在于一切经验事实之中,时间、连续性、因果关系和广延、实体、数量等等所有这些范畴都是独立于思维的、在物自体中的客观关联[5]349,而这种不依赖于认识主体的客观性是世界向我们揭示出来的它自身的规定,而这种自明性就是“启示”(Offenbarung)。在此基础上,雅可比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与观念论相对的、一种广义的或普通的实在论(Realismus)。黑格尔借用科彭(Friedrich Koeppen,1775-1858)的话来概括雅可比的知识观念:我们人是通过感官以及关于看、知觉和感受的超自然的启示来得到作为事实的事物的;从经验所获得的东西都总是已经被综合了的,无需通过我们而首先被综合,它也确实不可能被综合,因为我们的活动作为直接指向这种综合性的所与,是一种综合活动的倒转,它是对所与的分析,我们在对象中发现的这种分析性的统一,已不再是一个综合了。相反,在一个对杂多的联结中,杂多(经验材料)被分析性的统一撕碎了[5]371,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是一种前反思的、事物在其自身的综合性。
因此,对怀疑论的真正回应不能依靠理性的分析和推理,而只能通过“向信仰的腾跃”(salto mortale,致命的翻腾)[8]189这样一种方式来直接达到。因为理性的根据是第二手的或间接的确定性,它始终是有条件的、不充分的,而信仰才是第一手的确定性,是对自明的客观性的直接认识。在关于莱辛的斯宾诺莎主义之争中,门德尔松等人认为雅可比是通过借助基督教的信仰来对抗理性[2]250-251,但雅可比自己却指出,他所说的信仰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我们出生在一个社会中就会分享这个社会所共同信奉的一些关于事物的认识,它不是那种有着特定历史、要求归于某种宗教才会有的信仰[2]230。尽管雅可比在论述时使用了一些基督教的语言,但是他的信仰观念(Glauben)却是来自于休谟(David Hume)和里德(Thomas Reid)等人的自然信念(natural belief)和常识(common sense)学说。
实际上,休谟所谓的自然信念并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那种作为物理事实之附现象的意识状态,他强调的不是这种信念的或然性或者不确定性,相反,这种自然信念本身是某种具有历史性的、社会性的权威的体现,因而是一种非反思或者前反思的知识[9]。所以休谟对洛克的心理主义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因为在他看来,在洛克那里,经验是一种人为造作的和理智反思的产物,很多日常信念和直觉其实并不是像白板一样描绘上去的,这样一些包含着意义和理解的自然信念是各种历史经验和社会经验的成果,而不是主体反思的产物。尽管在康德看来,休谟将信念等同于主观的心理联想,这不仅损害了知识的确定性也损害了人的自由和尊严,可是,如果不从康德的观点反过来看休谟的话,我们会发现在休谟那里,主观自由或者理性主体的自律不是最重要的,他的怀疑主义恰恰是想提醒人们注意,理性主义所寻求的确定性实际上可能比他们自己认为的更加主观,这也是为什么黑格尔会对这种意义上的怀疑论和经验主义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的原因。休谟对理性主体建构的知识所具有的必然性的怀疑,使人类的信念更加有机会返回到一种前反思的状态,能够与人的历史经验或者说与事情本身固有的合理性的展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通过反思将知识限定在主体的自我意识的确定性中。因为理性的反思是对事实的分解,通过空洞的同一性将普遍从特殊那里分裂出去,如果任何一种哲学建立了普遍与特殊的绝对同一性,那么这种同一性立马就会转变为一种与特殊割裂开来的普遍性[10]375,这反而是对现实的一种分割和裁剪,将一些僵死的片断当作整体。
比如,休谟在讨论正义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convention的作用。这个词常常被翻译为“协议”或“同意”。可是如果我们对休谟的学说稍有了解的话就会知道,休谟恰恰是反对洛克意义上的同意或者通过理性主体相互达成契约的方式来实现正义的方式。相反,convention应该理解为“共识”,它只是一般的共同利益的感觉。这种对共同意义的感觉(common sense)是社会全体成员相互表示出来的,并且诱导他们以某种规则来调整他们的行为,它作为历史和社会经验的产物体现了超越个人意见的权威性,但又是与个体的自我认同相一致的。因此,休谟特别强调,只有那些长久生活在共识中、被这些共识所浸染的人才知道什么是共识。共识不是主观的、心理主义意义上的信念,不是理性反思的结果。没有足够的历史和社会经验根本不可能人为地设定这些共识。对此,休谟还举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他说,所谓的共识实际上就像两个水手在一起划船,并不需要事先有什么特别的商量和约定,两个人自然而然地就能够彼此协调一致,这就是一种共识[10]。而正义是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的,绝不是洛克所说的理性主体在知道什么有利什么有害的基础上,经过反思和协商达成的社会契约,也不是康德式的完全与个体的感性存在相对立的理性自律。
当雅可比说“法是为人而制的,非人为法而制”(das Gesetz um des Menschen willen gemacht ist,nicht der Mensch um des Gesetzes willen)[8]516时,正是希望表明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自然信念、直觉和情感对于纯粹形式立法的优先性,康德的实践理性在其与自然的不可消除的对立中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所能产生的无非是理性法则对人之自然的统治体系,这是对伦理生活和美的割裂[5]380,而自然的伦理之美应该包含两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一方面,它必须具有个体的精神活力,拒绝服从僵死的概念;另一方面,它必须具有概念和法的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形式。康德的定言命令是将绝对的形式当作唯一,完全使个体的精神活力服从于绝对的形式而扼杀了它,而雅可比试图恢复精神活力和伦理自由的方面[5]381。其实,通过对休谟的怀疑论和苏格兰常识哲学的引用,雅可比在一定程度上从他们那里承接了古代实践智慧(phronesis,明智)的传统①与雅可比交情甚笃的另一位启蒙运动的批评者哈曼(Johann Georg Hamman)就曾直接将自己与康德之间的关系比作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康德哲学的最大问题就在于通过理性的纯化来追求纯粹的同一性(柏拉图的纯粹理念),因而导致了唯我论。在哈曼看来,理性应当是展现在我们的语言、书写以及生活当中的理性,是多中之一(亚里士多德的存在于殊相之中的共相),而不是主体的纯粹理性。参见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8.,将理性视为体现于传统、风俗、历史和社会生活实践这些具体情境中的合理性,使抽象的形式规范(Norm)转化为具体而又客观的准则(Maxime),对启蒙的理性主义的确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这一点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影响也不容小觑。
所以,尽管被人们称作非理性主义者,但雅可比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与理性相对立的,而是“理性的自然信仰”(natural faith of reason)[8]552。雅可比认为,理性主义所宣称的“理性”只是知性(Verstand)能力的一种抽象,它是从属于真正的理性(Vernunft)的。首先,知性(作为把握事物的条件的能力)只是达到思维的真正目的的一个手段,而思维并不是为了说明事物的条件,而是“为了揭示存在(Dasein),让存在显示出来”[2]194。其次,知性并不是自足的,因为每个解释都包含了一个未经解释的预设[2]234,而信仰恰恰构成了理性反思的前提。确切地说,真正的理性并不是说明事物的条件的一种能力,而是把握无限的能力[2]230,对于知性来说,这种能力不可避免地会是某种神秘的东西[2]376。理性所把握的只是那些知性说明止步的地方,而理性主义对无限智性的探究侵蚀了使说明得以可能的根基,这个根基我们只能通过信仰、直觉和情感来通达,而不能通过知性的说明来解释。我们知道,康德也曾在知性和理性之间做出过区分:知性是统一感性直观的规则能力,而理性是统一知性判断的原则能力。但雅可比对二者的界定却与康德完全不同,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彻底放弃这样一种理性观念,即把理性看作是解释性的条件或理由,把人的理性看作是理解事物为何存在或者事物是其所是的能力[6]97。就像雅可比一部著作的书名所描述的那样,批判哲学的任务是将理性带向知性(die Vernunft zu Verstand zu bringen),而他的信仰学说则是让理性在对绝对和无限的直接把握中重新成为理性[5]373-374。雅可比为知性和理性概念所做出的这一重新界定对黑格尔理性观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1]。
三、信仰主义的悖谬
然而,在黑格尔看来,雅可比的信仰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纠偏效果,但是对理性主义和观念论哲学的厌恶却让雅可比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因为这些哲学都意在表明,在有限和时间性当中没有真理存在,现存之物之“是”并不是天然合理的,相反,它们的合理性必须通过概念来加以把握和证明,所以,对理由的追问和理性演证的工作对于真理的探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5]377。可是,雅可比却只看到了充足理由律的否定的方面,而忽视了它的积极意义。他对有限之物的取消感到震惊和愤怒,因而将绝对和真理限制在时间性和物质性的东西上。就像黑格尔指出的那样,雅可比认为理性的客观规定属于物自体的预设与康德范畴演绎的结果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根据康德,感觉不向我们提供任何形式,合理性的根据在概念和思维当中,所以,因果和连续性概念等等都必须严格限制于表象,所有关于它们的认识都不是事情本身的规定,因此,自在存在和理性完全超越于有限性的形式,并将有限清除出自在和理性的领域,这给予康德以不朽的价值,因为这是哲学的开始;相反,在虚无的有限之物当中,雅可比却看到了绝对的自在存在。在康德哲学中主体性有一种客观形式,即概念的形式,相反,雅可比哲学使主体性完全成为主观的,将其转变为个体性;康德的知性及其形式虽然是主观的,但仍是积极的,在其中仍有绝对[5]350,而雅可比由于把有限提升为在其自身的存在而径直导向了一种绝对的经验主义或者经验主义的独断论。在单纯信仰中,与永恒和绝对的关系是直接的确定性,还没有成为客观的和通过思维达到的概念形式[5]379,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同一关系并没有通过概念的中介作用证明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而只是依靠一种独断的设定,所以,这种通过信仰达到的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同一并不是真实的同一,它仍然受制于一种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合理性的内容还是由理性自身之外的因素决定的[5]347-348,而不是在其自身中有其根据。信仰的确定性远没有雅可比期望的那样绝对。
虽然呈现在我们的日常信念之中的事物是直接的和自明的,但这种现成存在并不必然合乎本然之理,而雅可比对有限之物的绝对化必然导致一种最坏意义上的“凡是现存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敏锐地指出:“倘若理性为了取消有限性和悬置主体性而从反思逃入信仰,那么,信仰自身就受制于它与反思和主体性的这一对立。因为它现在将否定作为自身意义的一部分,信仰在对反思的取消中保存了反思,在对主体性的取消中保存了主观意识。由此,主体性在其自身的取消中保住了自身。”[5]379
雅可比其实还是在以一种反思的方式来寻找最初的根据和确定的起点,只不过是将观念论哲学赋予主体的确定性重新拉回到客体上,但这一转变并没有阐明起点本身的合理性,而径直将合理性的形式赋予缺乏理性必然性的经验内容。当雅可比为了拒斥理性的反思而把意识中直接确定的日常信念当作天然合理的时候,他并没有像休谟在他的《英国史》中那样去阐释存在于传统、习俗和常识当中的活生生的理性,反而是把一些历史形成的、特殊的经验认识从它的历史传统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抽离出来,将反思哲学所产生的那些僵化固定之物保留了下来,当作理性自身的普遍必然的规定,从而彻底阻断了理性通过人类的历史和社会生活进行自我修正的可能性。这一点恰恰是与那个充满历史感的、积极的怀疑主义背道而驰的。
随着思维一起被取消的还有真正自在的、自我同一的概念,我们也因此失去了终极的合理性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个体主观的意愿和情感。在雅可比的实践哲学中,这种新教的主体性原则得到了更为鲜明的体现。尽管康德的道德学说和法权学说用最不光彩的证据玷污了伦理自然,但是,雅可比对康德哲学的敌意却导致他鄙视客观伦理形式中的概念,鄙视纯粹法则,即道德的形式原则[5]380,把这种客观性等同于个体当下的善良意愿和美好的情感,而没有就这种客观性本身来展开它的内在必然性。另外,雅可比还将宗教、国家、民族和法视为现成之物,将这些活生生的东西转变为人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他不是将它们当作神圣的存在,而是当作人们所熟悉的日常物,从而将理性的东西当作经验性的东西[5]382,这就进一步削弱了绝对理性之法自身的客观性和有效性。当主体的情感和意愿取代客观的伦理法则成为绝对,必然会导致一种道德和政治上的狂热与自负,从而对理性主义的危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雅可比那里,主体与客体、信仰与知识仍然是对立的:“绝对”如果不在主体之中,那就只能在客体之中;如果不能通过理性来认识,那就只能通过直接的信仰来把握。这种反思的、以对立为前提来设定同一性的做法,使得雅可比的信念学说继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之后成为了主观性的形而上学的第二个阶段。与理性主义对自然的祛魅相反,雅可比的信仰主义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当理性的探究削弱了一切意义、价值和规范的客观根据,使人们赖以生存的那些基本的存在论的信念变得不再确定之时,直接的信仰就逐渐取代理性的论证而成为规范性和客观性的来源。这种反理性的信仰主义广泛地表现在现代政治、宗教、道德、文化和艺术领域当中,而雅可比的哲学实际上为这一思潮提供了形而上学的原则。黑格尔后来在《法哲学原理》中给予过严厉批评的浪漫主义者诸如小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弗里斯(Jakob Friedrich Fries)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等人都与雅可比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或者希望通过神话和艺术关于万物一体的想象与直观来完成对自然的复魅(re-enchantment of nature)[9],重新在自然中建立合理性的客观根据,或者通过诉诸内心对于绝对法则的直接信念和对绝对者的强烈情感来促成政治和宗教上的革命,而这些主张其实正是以雅可比的主观性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发展出来的[12]。
雅可比虽然试图通过直接信仰和个体的良知来克服理性反思所导致的虚无主义和客观伦理法则的形式性,但却有些矫枉过正。在他的哲学中,理性只是被理解为直觉和情感;伦理行为只在经验偶然性的情境中发生,依赖于由经验、偏好和心灵的方式所给予的事物,而知识只不过是对内在或外在的特殊性的意识[5]385。理性可能确实体现在自然和人类精神中、体现在我们赖以共同生活的常识和信念中,但是这种主观确信的自然态度本身并不能用来证明原则的普遍必然性,直接呈现于主观意识中的思有同一其实是经过思维的中介的。因此,雅可比仍然没有脱离主观性反思哲学的窠臼,他的信仰哲学以及他所影响的浪漫主义思潮,与现代性的主观主义精神是契合的[13]。单单通过直觉、情感和信仰不仅不能克服主观主义和虚无主义,反而会产生更加恶劣的后果。要想真正把握绝对,就必须通过对雅可比哲学的扬弃来寻找新的路径,这也正是经过了新一轮怀疑主义洗礼的德国观念论者们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四、结 语
尽管并没有最终逃脱主观主义的窠臼,但是雅可比的康德批判及其信仰哲学对于德国观念论的发展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不仅仅阐明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内在矛盾,以及反思性论理的局限,更进一步揭示了所有以知性为理性的理性主义和以理性主体的先验构造来消解物自身的主体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后果。雅可比让人们不再能够在康德的二元论体系中安之若素,因为在实然与应然、必然与自由的对立中,规范性的一面被归于主体的自我立法,那么,当被问及应当何以为应当时,理性的主体就会因为孤立无援而采取一种与自身的原则相背离的非理性的独断论立场。由此,所有二元论的哲学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怀疑主义的攻击,使他们对合理性的终极根据的奠基变得摇摇欲坠。而雅可比自己则以直接信仰重申了思有同一这一根本性的原则以对抗二元论所产生的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一努力虽然有着种种问题,却为后康德的观念论哲学家在新的高度来理解和发展康德哲学提供了重要的契机。
[1]杨祖陶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2]Daniel Breazeale.Fichte and Schelling:the Jena period,The Age of German Idealism[M].ed.Robert C.Solomon and Kathleen M.Higgi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gde,1993:139.
[3]Rolf-Peter Horstmann.Die Grenzen der Vernunft:Eine Untersuchung zu Zielen und Motiven des Deutschen Idealismus[M].Frankfurt am Main:Klostermann Vittorio GmbH,2004.
[4]Georg Whilhelm Friedrich 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15:Schriften und Entwürfe I(1817-1825).[M]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1990,S.7
[5]Georg Whilhelm Friedrich Hegel.Gesammelte Werke,Band 4:Jenaer kritische Schriften[M].Hamburg,Felix Meiner Verlag 1968.
[6]Paul Franks.All or nothing.systematicity and nihilism in Jacobi,Reinhold,and Maimon[C]//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erman Idealism,ed.Karl Amerik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7]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M].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Leroy E.Loemker(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9),p.268.
[8]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The Main Philosophical Writings and the Novel Allwill[M].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4).
[9]Terry Pinkard,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95.
[10]休谟 .人性论(下册)[M].关文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530-531.
[11]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2]Georg Lukács,The Young Hegel[M].London,Merlin Press 1975:296-298.
[13]Jürgen Habermas,The Philosophical Discourse of Modernity[M].Cambridge,Polity Press 198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