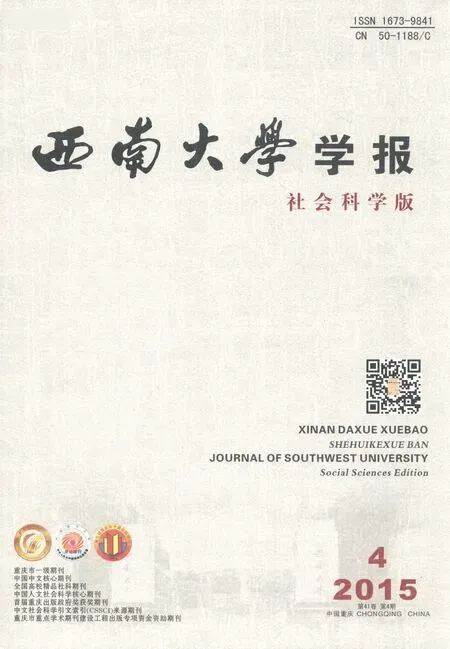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摘 要:古希腊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城邦国家的兴起与衰退推动了公民政治生活向市民私人生活的转变,使得人类社会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公共生活中发展出了一种“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城市公社的复兴和发展则打开了中世纪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为近代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城邦国家和城市公社不仅构造了二者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而且奠定了近代市民社会的公民品格和市民精神的历史基础.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G9841(2015)04G0005G10
DOI:10.13718/j.cnki.xdsk.2015.04.001
收稿日期:2015G04G12
作者简介:刘荣军,哲学博士,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期刊社,编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现代社会的发展主题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12AZX003),项目负责人:刘荣军;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现代社会的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规律研究”(NCETG12G0933),项目负责人:刘荣军;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市民社会:从哲学批判到社会建构”(10YJA720019),项目负责人:刘荣军;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市民社会:从哲学批判到社会建构”(2010YBZX01),项目负责人:刘荣军.
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时代,正是“欧洲中心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所以恩格斯只描述了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三个民族国家的起源问题.事实上,当古希腊、罗马接受西亚、北非文明的影响,从原始氏族社会进入阶级文明社会之前,国家就已经在埃及、波斯、印度、中国等东方文明国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所不同的是,与东方国家的“神权国家”或“政教国家”性质不同,古希腊罗马国家一开始就表现出“城邦国家”或“政治国家”性质.这种国家采取的是公民政治与私人生活合二为一的形式,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政治都处在相对于私人生活来说的绝对优势地位,但它毕竟为市民社会留下了一定的活动空间.正是这种活动空间,使得西方社会结构在经历了中世纪初期的社会分化、裂变与重组后,能够在中世纪欧洲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相互斗争的社会缝隙中产生出“城市公社”、“城市社会”或“城市共和国”这样的新的市民社会形式.由此,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和中世纪欧洲的“城市公社”,实际上构成了近代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
一、“城邦国家”中的公民生活与私人生活
谈及希腊城邦,人们首先会联想到亚里士多德“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1] 7的经典论述.因为它揭示了希腊城邦生活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方面,城邦作为一种国家实体,关涉到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另一方面,个人作为城邦的组成部分,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正因此,亚里士多德从公民与城邦相统一的角度对两者进行了定义:“(一)凡有权参加议事和审判职能的人,我们就可说他是那一城邦的公民;(二)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团.” [1] 116G117亚里士多德的定义说明,“什么是‘城邦’”和“什么是‘公民’”这两个问题其实是“城邦政制”的两个不同面相.希腊的“城邦国家”这种政制问题,本质重要地涉及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城邦的国家生活,二是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人们为了满足其自然需要,建立了三种不同层次的社会组织,首先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即“家庭”,其次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初级形式的社会团体即“村坊”.然而,一旦由若干村坊组合而为“城邦(城市)”的时候,社会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正是看到了城邦具有相对于个人来说的“高级而完备”的“社会团体”优势,亚里士多德特别看重希腊公民个人对于希腊城邦的高度依赖性.他说:“我们确认自然生成的城邦先于个人,就因为[个人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 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其生活,必须共同集合于城邦这个整体[才能让大家满足其需要].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弃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弃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祗.” [1] 9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个人要想成为不被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就要努力地参加到城邦的政治生活中,通过政治参与实现希腊人特有的道德观念.这种对城邦和个人同时有用、能够为人们带来荣誉的道德品性,就是希腊人称之为“幸福”的东西.
可是,在希腊城邦中,只有公民才有资格参加城邦政治生活.这样,城邦的政治生活问题自然转化成了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问题.事实上,按照其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希腊城邦的人口通常被划分成三个主要阶级:一是奴隶阶级,他们处于社会最底层,毫无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被亚里士多德称为“有生命的工具”、“有生命的财产”;二是非公民阶级的自由人,包括妇女、儿童,以及定居本邦的外邦人(外邦人作为非公民的自由人,虽然适应了城邦经济的商业化发展需要,但是除非作出特殊贡献,否则很难取得公民权,因而同样没有参加城邦政治生活的权利);三是公民阶级,他们是出身于本邦公民家庭的成年男性,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参加本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显然,奴隶阶级的毫无地位、非公民阶级自由人的无权地位和公民阶级的特权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加强化了城邦作为公民团体的性质. [2] 11这样,在希腊城邦国家中,尽管存在着雅典民主政治与斯巴达寡头政治这两种城邦政制的区别,但它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城邦的最高治权都寄托于公民集体身上. [2] 8以此为基础,希腊城邦普遍实行的是一种主权在民的政制原则,“公民大会”与“轮番为治”就是这种主权在民原则的贯彻和落实.以雅典为例,公民不仅可以出席公民大会,参与公民大会的辩论和投票,而且可以轮流参加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处理国家事务,审理案件,调解纠纷.即就是在“不那么民主”的斯巴达,其国王也由两人担任,且其权力平等;其长老会和监察官也都由多人出任,轮流执政. [2] 8不难想象,正是在这种城邦政制中,孕育出了古希腊民主、平等、自由、法治与理性的精神传统.
那么,城邦公民在政治生活之外又是如何生活的?亚里士多德从城邦与家庭的区别出发,认为公民除了基于城邦的“政治生活”或“公共生活”之外,还存在另一种生活方式,即基于家庭的“家务生活”或“私人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完全的家庭是由身份和地位不同的奴隶和自由人(包括家主、妇女和儿童)组成的.家主具有公民权,奴隶、妇女和儿童则没有公民权.在家庭中,奴隶处于依附地位,妇女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的存在似乎天生就是为那些处于家主地位的公民创造生活资料,提供生产性、生活性、服务性的活动资料而已.亚里士多德就是从这种整体论和目的论出发理解公民即家主的私人生活的.在他看来,一个完全的家庭除了“主奴关系”、“配偶关系”和“亲嗣关系”这三项要素以外,还有另一项更为主要的要素即“致富技术”.亚里士多德说:“财产既然是家庭的一个部分,获得财产也应该是家务的一个部分;人如果不具备必需的条件,他简直没法生活,更说不上优良的生活.” [1] 10G11亚里士多德不仅区分了两种“获得财产的技术”,即“为生活而从事于觅取有限的物资”的“自然的”“家务管理”和“专以聚敛财富(金钱)为能事”的“不合乎自然的”“货殖”,而且认为作为“家主和政治家”的公民应该熟悉家务管理这种获得财产的自然技术,因为这种致富方式和技术“不但有益于家庭团体,也有益于城邦团体” [1] 21G29.一方面,对于城邦公民来说,自外于城邦的公共生活而过一种彻底的私人生活,“首先意味着被剥夺了对真正的人的生活具有本质意义的东西:被剥夺了来自于被他人看见和听见的现实性,被剥夺了与他人的‘客观’关系,被剥夺了达到比生命本身更加永恒的境界的可能性” [3] 90.所以,无论对于那些想通过参与城邦政治而保持与公民集体或公共生活联系的普通公民,还是对于那些想作为有闲阶级而从事修养德性、担任公职的行政人员以及议事和审判人员等著名人物,都必须拥有一定的财产作为政治保障.正如阿伦特所说:“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财富还是财产都比其他的私人事情或私人关怀对公共领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两者至少在形式上或多或少起着相同的作用,成为一个人进入公共领域、具备充分的公民资格的主要条件.” [3] 92另一方面,对于作为城邦公民的家主来说,无论是对“无生命工具”还是对“有生命工具”(奴隶)的管理,都是对其“家有财产”的管理.由于“家务和政务,以及主人的治理奴隶同政治家和君王统治人民完全相同”,所以,家务管理即家有财产管理这种致富技术,在更高的意义上其实是对公民政治能力的训练与培养.以这种观点审视希腊人对于家务管理与公民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关系可以发现,他们虽然在家务生活或私人生活方面保有充分的活动空间因而保有一定的个人自由,但最终还是将其消弭到了公民的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这种城邦自由之中去了.正如阿伦特所说:“‘私人的’一词,就其原初的剥夺涵义而言,只有与公共领域的多元性联系起来才有意义.” [3] 89G90“古代人必须每天穿越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那条鸿沟,越过狭窄的家庭领域,‘升入’政治领域.” [3] 66
遗憾的是,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他们对城邦国家的论述都只是一种历史想象.一方面,希腊人对城邦的公民身份(公民资格)的认同本身受到荷马理想的巨大影响,存在着贵族主义的文化倾向,体现出非常明显的排他性与不平等性.其最大特点是,与物质财富的功利性追求不同,希腊人更加注重精神世界的非功利性追求,因而对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极其鄙视,往往将人划分成高贵者和低贱者、贵族和平民两类,认为他们在外貌、体格、能力、德性等所有方面都是不平等的. [2] 69不仅如此,就是公民阶级,其参政的范围与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在有闲阶级人数不可能比现在一个与之同等规模城市的有闲阶级人数还多的希腊城邦,绝大多数公民都还只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来维持生活的商人、工匠或农民(他们除了人身自由等基本权利能够得到保障外,其他权利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蛰伏”状态)的情况下,“只有那些能够担任公职、出任元老的人能经常行使他们作为公民的权力” [2] 35,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充分的时间全面了解有关国家的事务,也只有他们有足够的财力接受必要的演说训练” [2] 16.显然,这种实际情况是和希腊城邦所主张的主权在民的政制原则背道而驰的.至少它为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古希腊的城邦政制实行的是包含着不同程度的民主因素、但远非真正民主的政体形式.另一方面,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够实行主权在民、轮番为治的政制,那也是由希腊城邦在基本上都是“小国寡民”的社会状态所决定的.在这里,“城邦的大小(人口的多寡)”成了希腊城邦政制实行主权在民、轮番为治这种直接民主政治的决定性因素.比如,柏拉图理想中的城邦国家的公民人数仅有五千多人,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其理想国家的公民人数,但是却对“城邦的大小(人口的多寡)”进行了原则上的规划.他说:“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这该是足以达成自给生活所需要而又是观察所能遍及的最大数额.” [1] 361G362总之,希腊城邦由于其范围相对狭小、公民人数相对较少的“小国寡民”状态,使它能够实行主权在民的直接民主制度.这既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局限所在.空间狭小、人口较少的“小国寡民”状态,使希腊人能够有条件实行公民直接参政的民主政治,但也容易滋生城邦本位主义——希腊城邦不仅拒外邦人于公民权之外,而且对相邻城邦的情况漠不关心,这必然导致城邦之间各自为政的发展格局.这种情况能够适应氏族社会向政治社会的转变,但却无法适应城邦政制向大一统式帝国政制的转变.
学术界普遍认为,在经历了雅典和斯巴达为争夺希腊霸权而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之后,希腊城邦政制即开始走下坡路.依此标准,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前347 年)生当希腊城邦的危机时代,而到亚里士多德时(公元前384-前322年),希腊城邦已经分崩离析了.显然,在一个城邦基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瓦解、形态已经不再是城邦的国家中,亚里士多德还希望用城邦的政治手段恢复城邦的政制体系,显然是脱离历史发展实际的一种“历史想象”,而罗马共和国时期对包括了高级官职(包括执政官、副执政官和监察官)与低级官职、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于一体的共和政治的实践,充其量也只是希腊“城邦政制”临死前的一种“回光返照”.正因此,学术界普遍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去世,乃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如萨拜因所说:“在政治哲学史中,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22年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正如他那位比他早去世一年的伟大学生的一生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学时代的开始以及欧洲文明史的开始.城邦的失败乃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条十分明确的分界线.” [4] 183事实也说明,在经历了最初亚历山大的征服及其继承者的分割,以及后来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对希腊化国家的征服之后,古典时期的希腊城邦再也无法作为自足的政治单元而独立存在了,城邦不仅让位给了军事化的帝国这种更加强大的政治单元,而且日益丧失了其独立性.到公元前1世纪的时候,不管是雅典式的民主政治、斯巴达式的寡头政治,还是罗马式的共和政治,都先后退出了实际的政治生活.
然而,城邦政制退出了历史舞台,对城邦政制特别是城邦与公民关系的观念反思与思想反拨却伴随着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对希腊世界的先后征服而在希腊化时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伴随着长期征服带来的战争、动乱以及生活贫困和颠沛流离,那些失去城邦保护的个人在庞大帝国的战争机器面前既失落又无助,开始从关注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转而寻求个人内心深处的灵魂安宁和伦理修养,由此产生出以伊壁鸠鲁学派和斯多葛学派为主要代表的哲学流派.伊壁鸠鲁不仅以偶然性的形式分析了人的自由意志,而且从社会契约角度论述了个人与社会正义的问题.斯多葛学派则分别在马其顿和罗马统治的不同时期形成了早期斯多葛学派和晚期斯多葛学派.早期斯多葛学派站在“众生平等”的立场上,提出了自然法思想的最初萌芽.他们提倡不分种族的大同世界和抽象普遍的世界公民,主张根据个体的人的实际处境把他们划分为道德和政治两个不同的序列,从而对政治与伦理进行了截然二分的态度,提出了“人的双重忠诚”的社会思想,即作为普遍的人类中的一员,作为世界公民,人应该忠诚于源于人性的自然法;作为某一国家的一位公民,作为某一种族中的一员,人应该忠诚于该国家的人为法或习惯习俗.可以发现,这种思想已经在悄无声息间实现着社会政治哲学的一种历史跃迁:将城邦政制中城邦与公民、城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推进到了帝国政制中个人与人类、个人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这种思想到了罗马统治时期虽然被顺应自然、不问政治、服从整体的主流思想所改变,但对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思考则成了此后的思想常识.在这里,无论是伊壁鸠鲁学派对个人与社会问题的关注,还是期多葛学派对个人与人类关系的理解,都本质重要地标志着一种新的、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思想的产生.正如塔恩所说:“作为一种政治动物(亦即作为一种polis或自治城邦之一分子)的人,已经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去世而终结了;作为一个个人的人,则始于亚历山大.这种个人既需要考虑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又需要考虑他与其他个人的关系(他同这些个人构成了‘人们居住的世界’);为了满足前一需要,产生了种种研究行为的哲学,而为了满足后一需要,则产生了某些新的有关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 [4] 183G184总之,伴随着城邦的衰落、失败和帝国的征服、统治,当人们不得不学会作为一个个人去生活和思想的时候,“个人”概念终于出现在了欧洲文明史的地平上.从“作为一种政治动物的人”的政治生活与公共生活出发竟然发展出了一种与其相对而立的“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自由意志与私人生活,难怪萨拜因将这一根本性变化调侃为亚里士多德之后“最为戏剧性的对照” [4] 183.
对于亚里士多德之后城邦政制的这种发展趋势,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有着非常独特的历史感悟,这从他将在希腊语πολιζ(polis)基础上形成的politikekoinonia翻译成societascivilis就可看出.在希腊语中,“政治”、“城邦”、“公民”等词语,全都出自同一个词根πολιζ(polis),意指同“乡郊”相对的“堡垒”或“卫城”,后来人们就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πολιζ(polis),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城邦”或“国家”的意义. [1] 113在这里,πολιζ(polis)既指城市又指国家或同时指两者,但它首先指的是相互依赖的个人与城市组织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共同体及其中的社会政治生活.正因此,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首先提出了politikekoinonia的概念,用它指称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即“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 [5].而西塞罗在公元1世纪将politikekoinonia翻译成拉丁文的societascivilis时则赋予了其更为宽泛的意义,不仅意指“单一国家,而且也指业已发达到出现城市的文明政治共同体的生活状况.这些共同体有自己的法典(民法),有一定程度的礼仪和都市特性(野蛮人和前城市文化不属于市民社会)、市民合作及依据民法生活并受其调整、以及‘城市生活’和‘商业艺术’的优雅情致” [6].显然,西塞罗对societascivilis从而对politikekoinonia因而也是对πολιζ(polis)的意义界定,恰恰反映了罗马法观念从市民法向万民法再向统一法转变的社会现实,因而是从野蛮与文明、国家与社会、公民与市民的多重视野出发对城市共同体的理论界定.正因此,当西塞罗对societascivilis的意义规定在14世纪为欧洲人广为接受并将其翻译成英文civilsociety的时候,它就同时具有了文明社会、公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三层含义,尽管它们在本质上都是城市社会的不同译法.
总之,从希腊时期规模有限的城邦社会发展到罗马时期疆域辽阔的帝国体系,从城邦公民的政治生活和公共生活发展到帝国居民的商业生活和私人生活,从特别注重公民的政治生活发展到更加重视市民的私人生活,这就是城邦国家的兴起及其衰退带给我们的历史遗产.它说明,随着“作为一个个人的人”的概念的提出,市民社会在公民社会的母体中已经发育出了它的胚芽.
二、“城市社会”中的市民等级与市民社会
罗马政制、罗马军队和罗马法,像三驾马车一样,使罗马帝国从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大帝登位到公元180年奥勒留皇帝去世的两百多年里空前强盛.然而,盛极而衰.395年狄奥多西一世死后,罗马帝国就被分成了东西两半.此后,随着5世纪时北方日耳曼蛮族开始的对罗马帝国的入侵而在西部帝国原来地盘上建立起诸多王国以及这些王国特别是法兰克王国在后来的分裂组合,终将西罗马帝国楔成了碎片化的社会格局.然而,7世纪中叶开始的阿拉伯人对欧洲的侵略性进军,尽管因为拜占庭帝国和法兰克王国的英勇抵抗而粉碎了它对基督教欧洲两翼实行包抄合围的强大攻势,但却对西部欧洲后来的社会秩序与发展轨迹产生了巨大影响.一方面,阿拉伯人入侵的直接后果是封锁了地中海,基本上中断了自古希腊以来的海上贸易与商业活动.这种断裂是重要的,因为它让商业凋敝,让城市衰落,让城邦时期积聚起来的个人力量和市民社会的胚芽在经历了妊娠的剧烈反应期并沉寂了几个世纪之后才重新释放出来.另一方面,阿拉伯人入侵的间接后果是成就了法兰克王国的内陆国家优势,确定了其为欧洲中世纪奠基者的历史地位.由于阿拉伯人的入侵封闭了地中海,西部欧洲的重心从以前的地中海沿岸“北移”了,这就为“在西部仅起第二流历史作用的法兰克王国将要成为西部命运的主宰”创造了条件.由于法兰克王国“基本上是一个内陆国家,它对外再无交往,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一个没有出口的国家,生活在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之中”,因而法兰克王国尽管也实现了“以推翻传统的世界秩序作为基本条件”从而“为中世纪欧洲奠基”的历史使命,但是其实现这种历史使命的经济基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却是由它作为内陆国家和农业国家的特性决定的. [7] 17G19正因此,皮雷纳认为,无论查理大帝时代在其他方面的成就看起来是多么辉煌,但“从经济观点来看,它是一个倒退的朝代” [7] 27.
法兰克王国及其后来的分裂为中世纪欧洲奠基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综合吸收罗马社会、日耳曼传统和基督教精神的基础上创建的中世纪主义秩序,它包括了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社会这两个重要方面:(1)封建制度.汤普逊说:“罗马贡献了财产的关系,日耳曼人贡献了人身的关系,它们的结合形成了封建制度的主要性质.” [8] 325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是一种以土地分封、军事采邑、领主政治、庄园经济、人身依附为特征的等级社会和特权社会,它既是一种国家管理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社会制度下,等级森严,界限分明,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等级系统中.尤其是在军事采邑的封建庄园中,庄园居民不仅是庄园主即领主的佃农,而且直接就是他的臣民,领主以其无上权力决定着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封建制度的确立产生了一个显然十分重要的变化,“它改变了人口在地面上的分布”.这个变化对于欧洲文明的性质和进程发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居社会优势的成分、社会的管理突然从城市转到乡间;私有财产渐渐变得比公共财产更为重要;私人生活比公共生活更为重要.” [9] 63G64(2)基督教社会.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后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现象是,日耳曼人用武力征服了罗马帝国,而罗马帝国则用宗教征服了日耳曼人,侵入罗马帝国后建立的日耳曼王国最终都皈依了基督教.随着基督教对法兰克人的征服以及法兰克军队的四处扩张,基督教神权和日耳曼政权就已经在逐渐地彼此融合并且重合了,最终在罗马帝国的中心建起了一个独立而日益强大的基督教国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汤普逊认为:“中世纪的历史基本上是中世纪教会的历史”;“教会在一个惊人的程度上把宗教活动和世俗事务、理想观念和实践行为联在一起.如果说它的头是在天堂上,它的脚则一向是立在地面上的”. [8] 262
总之,一方面是城市商业的衰落,另一方面是封建制度和基督教社会的确立,这两个方面此“消”彼“长”,共同构成了中世纪后期商业复兴和城市发展的社会背景,为市民社会的最终生成奠定了隐蔽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商业的沉沦和城市的沉寂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封建制度一旦彻底建立,人人各就各位,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停止了流动的生活.这样过了一些时候,市镇又获得一点重要性,再次显出活力.ƻƻ只要人们瞥见秩序与和平的一丝光亮,就产生希望,随着希望又工作起来.市镇也是这样.封建制度的大局甫定,采邑领主就有了新的需求,又想有所进取和改善.为了满足这需求,商业和工业重又在领地上的市镇里出现.” [9] 121G12210-11世纪开始的商业复兴改变了一切.随着日耳曼人的归化和阿拉伯人侵略的消退,西欧人民终于能够在大陆腹地的封建庄园中集中精力发展他们的农业经济了.自1050年左右起,西欧出现了农业革命和人口增长这样两个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历史现象.有了人口和财富的增加,就为以农业和土地为基础的西欧经济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商业复兴奠定了稳固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1096年开始的十字军东征也标志着地中海重新回到了欧洲的怀抱,标志着东西方商路被重新打通了.这样,从11世纪起,欧洲商业进入了复兴时期.这种复兴是从南欧地中海沿岸(主要是意大利)和北欧波罗的海与北海沿岸(主要是尼德兰和德意志)这两个策源地逐渐向欧洲大陆腹地推进并展开的.
商业的复兴必然带来城市的兴起,它所引起的变化首先就是西欧城市结构的改变.“中世纪城市的起源与ƻƻ商业复兴直接相关,前者是果后者是因,这是毋庸置疑的.” [7] 85简单地说,以商业为生的商人最初必然聚居在城镇或城堡等设防地点之内以供应它们的生活必需品.然而,由于“城堡只是四周用城墙围起、面积狭窄有限的堡垒”,所以结果只能是“由于缺少地方,商人们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定居在城堡之外”.他们在城堡旁边建起一个“外堡”(forisburgus)或“郊区”(suburbium),并且以“新堡”(novusburgus)相称,以区别于与之相连的封建城堡即“旧堡”(vetusburgus). [7] 91这里最关本质的就是,功能上的相互区别以及现实中的相互融合,使得新型城市诞生了:“较老的一个是堡垒,另外较新的一个是商业地点.正是通过这两种成分的逐渐融合,第一个一点一点被第二个所吸收,城市诞生了.” [7] 93“中世纪城市,是从某个城堡前面或附近的‘堡’的一个地方化的商人集团兴起来的.我们必须区别两个中心:一个老的和军事的——城堡,另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堡’.最后,后者并吞了前者,因而两者合成为一个社会了.” [8] 418城市最先是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及其附近地区为数有限的地方发展起来的,然而从11世纪到15世纪,在欧洲大约诞生了5000个左右的城市和市镇,一些地区甚至有一半以上人口从农业转向了商业.
“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 [8] 424城市兴起的最大的革命性成果就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改变和市民社会雏形的出现.
首先,商业的复兴和城市的兴起产生了以经商为职业的商人群体以及商人阶级,而商人的出现反过来又刺激了商业繁荣与城市扩张,这种相互作用必然把城乡重新联为一体.在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文明中,在一个人民依附于土地、每个人隶属于一个领主的社会组织中,商人能够周游各地而不属于任何人,这本身就显示了商人“不仅是自由人而且是享有特权的人”的特殊性,显示了他们“摆脱了仍然压在农民身上的领地权力和领主权力”的自由性. [7] 83按照皮雷纳的说法,商业适应着人类“追求冒险”与“喜爱谋利”的本性,因此在本质上具有“传染性”和“渗透性”. [10] 24商业活动的这种传染性和渗透性使它成为了一种开放的外向型活动,在12世纪时就使西部欧洲开始摆脱传统农业活动那种静止的封闭状态.慢慢地,商业和工业不再仅仅处在“从属于农业”的地位,而是反过来支配农业;农业产品不再只是供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交换品或原料被卷入到“总的商品流通系统”中.这样,禁锢着经济活动的领地制度的框框被打破了,乡村重新趋向于城市.日益紧密的利害关系使得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相互依赖显著增强.
其次,城市的发展壮大和城市生活的强化,培育了城市市民等级与市民阶级.随着商业和商人的出现,一个全新的市民阶层在城市生活中崭露头角.虽然说市民并不都是商人,但在最初的时候,市民指的就是那些与商业活动有着直接联系的人,正如皮雷纳所说:“商人聚居地称为新堡,以别于原来的旧堡.从而新堡的居民最迟从11世纪初期起得到市民这个名称.” [9] 97但是慢慢地,市民的概念就由最初的商人阶级扩大到了所有的城市居民身上,并且形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特性的合法的阶级.“市民阶级本身就是商业复兴的产物,而最初商人与市民两个名词就是同义语.不过当它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阶级时,市民阶级就变成了一个具有高度特性的合法的阶级.” [10] 45城市使市民获得了人身自由,市民的人身自由则成了城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城市与市民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同生共死、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从此,市民等级或市民阶级成了封建城市中继教士和贵族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力量,“市民阶级在他们旁边取得了自己的位置,从而使社会得以补全,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之臻于完善.ƻƻ社会具备了它的一切构成元素” [7] 134.发展所致,在14世纪法国的三级会议中,市民阶级“虽然在地位方面居第三,但在重要性方面不久即成第一” [7] 144.
再次,随着市民阶级人身自由的获得与强化,以司法自治和行政自治为核心的城市制度就确立起来了.市民的人身自由不仅是城市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础,而且也是市民阶级的最基本的经济权利、社会权利与政治权利的重要保障.然而,由于中世纪的城市是在封建主或教会的领地上兴起来的,在物质上掌握着土地所有的封建主掌握着城市的权力,他们把城市作为额外财源,任意向城市居民勒索赋税,摊派徭役,甚至肆意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市民为了取得各种权利,逐渐展开了反对领主的沉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从11世纪开始,城市市民或者“通过赎买”、或者“通过武力”、或者“利用贵族的弱点或者他们之间一心只顾争吵的机会”等方式 [11],迫使封建国王或教俗领主以颁布“特许状”的形式建立了自由城市、城市公社、城市共和国等独立的、自治的社会实体,取得了城市的自治权,不仅免除了许多封建劳役和赋税,明确了市民人身与工商经营活动等基本权利和义务,而且确认了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所获得的不同程度的自治主权和经商特权.11世纪后期起,“执政官”的大量出现就反映了城市自治的基本特点.
第四,市民阶级的自由性以及城市生活的自治性,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打开了传统封建社会和等级社会的缺口,将人们从封闭的身份共同体中引领出来.城市市民的人身自由,说到底其实是劳动的自由,是奴役性劳动向自由性劳动转变的结果:“在城市出现以前,劳动是奴役性的;随着城市的出现,劳动成为自由的.” [7] 66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以劳动自由为载体的市民的人身自由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城市生活的自治性以及市民生活所展示出来的那种较为舒适、讲究的生活方式,无疑具有非常强烈的示范效应,成为失去土地的农民和不堪压迫的农奴从封建庄园向城市逃亡的一个有力激励.德意志的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成了适合于所有地方的真理.尽管市民阶级本身也是一个特权特级,但是这种市民社会的等级与传统社会的等级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它不再以人的身份状况而是以人的居住地域或财产状况来划分等级的!由此,市民社会打开了传统等级社会的缺口,将人们从封闭的身份共同体中引领出来.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没有市民社会从等级世界中的突围而出,政治生活将永远都只是身份精英们的权力游戏.” [12]在这种意义上,城市的兴起与市民阶级的诞生,本身就是一个“去身份化”、“去等级化”的过程,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过程.
最后,随着市民阶级的形成以及城市制度的确立及其发展壮大,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就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农奴等级制的城市等级制.“中世纪的城市本身是一个个体,但是一个集体的个体,即一个法人.” [7] 115作为一个集体,市民阶级本身也是一个特权等级,也需要他们的等级象征,这就是行会和同业公会.正如汤普逊所说:无论中世纪行会的根源是什么,有两个事实是清楚的:一是“它们与市民阶级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同时发生”;二是在它们萌芽时“就是组织起来的自由商人或手艺人团体,以保护他们摆脱不自由的竞争和同等团体的竞争”. [13] 559在行会中,行会成员是“师傅”,师傅之下是“帮工”和“学徒”.然而,随着行会逐渐富裕和强大,行会中就出现了大行会与小行会、大师傅与小师傅的分化,大行会中的大师傅便在形式上和实质上“贵族化了”,“一个贵族阶级在城市中成长起来” [13] 562.他们不仅狡猾地篡改了行会的规章,以便排斥较低等级的工人或商人,保证他们自己对行会控制权的垄断,而且很自然地同城市政权结合了起来,有意无意地谋求政治地位. 到14世纪时,行会不仅成为“剥削和垄断的团体”,而且“在城市里产生了一种和农村等级制相似的等级制”——“同业公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 [14] 70G71
总之,商业的复兴、城市的兴起、市民阶级的产生和城市制度的确立,为市民社会的诞生提供了一切必须的物质的和精神的社会要素.随着这些社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市民社会已经走到了近代社会的门槛上.
三、市民社会两种历史传统的分析与比较
当我们分别考察了市民社会的两种历史传统后,对它们之间的相同和差异进行一番分析和比较,就是一个很有理论意义的事情了.这种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客观地看待近代市民社会两种历史传统的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
从总体上说,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国家与中世纪的城市社会,最大的区别就是政治与经济的差异,正如皮雷纳所指出的:“如果说城市在政治组织方面的作用在古典时代比在中世纪为大,那么城市的经济影响在中世纪则远远超过古典时代.” [7] 66表现在城市生活中,按照韦伯的说法,二者存在着“性格”上的差异:“中世纪市民的政治状态使他们走上经济人的道路,反之,古代的城邦,在其繁荣时期,保持着就技术观点而言最先进的军事团体的性格:古代市民是政治人.” [15]古典时代的城市生活是一种以身份为手段、以德性为目的的政治生活.作为一种“政治人”,城邦公民在行为中几乎没有掺杂任何经济上的考虑.如果说城邦中存在着经济行为,那也是服务于其政治目的的.与此相反,中世纪的城市生活则是一种以经商为手段、以谋利为目的的经济生活.作为一个“经济人”,中世纪城市市民的任何行为都是出于经济目的,市民可能会在某些问题(如反对贵族与领主的勒索、摊派甚至抢劫等)上采取政治行动,但这种政治行动完全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16]就经济影响来说,中世纪虽然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但人们却普遍受到了重商逐利的市场取向与利益驱动的推动与影响,“追求利润的思想指导着他的一切行动” [7] 76.就此来说,商业、商人、城市、市民,这些概念至少在中世纪的历史语境中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因而是具有同等程度的概念.
城市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性格差异,在城市生活中明显地表现为公民与市民的差别.在古典时期,城市的政治生活不限于城镇的城垣之内.城镇本身是为整个部落建立起来的,部落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居住在城墙之内还是城墙之外,都可以成为城镇的公民.而在中世纪,市民的概念却大大地强于公民的概念.在中世纪城市诞生之后存在着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随着城市的兴起,出现了“市民”这个概念,但这个概念在一开始却没有得到普遍使用,人们仍旧根据老的传统使用“公民(civis)”这个词.正因此,在当时的文献中用来指城镇居民的civis(公民)一词,仅仅是一个“地形学”上的名称,并不具有“法律上的意义” [7] 43G44.“在最初的市民阶级的思想中,没有任何人权和公民权的观念.他们要求人身的自由,也并非把自由当作天赋的权利.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他们才寻求人身的自由.” [7] 108相反,无论是对传统概念的借用,如“civis(市民;公民)”,还是对新概念的创造,如“poorter(市民)”、“poortmannus(市民)”、“burgensis(市民)”等,市民都特指城市中的主体,即主要是商人以及与商业活动有关的手工业者、行会师傅和劳工阶级.在这里,“市民”不是相对于“公民”的概念,而是相对于“臣民”的概念.市民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他的自由性.正如范迪尔门所说:“一个市民比一个农民更能决定他自己的一生.” [17]作为“自由人”,市民对人身自由的争取和对城市自治的争取是一致的.
然而,相对于中世纪的封建领地制度,中世纪的城市制度并不是主要的,城市社会并不是社会生活的主流.中世纪欧洲从整体上仍然是在物质上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在精神上由对商业极端仇视的教会控制的封建社会.正如皮雷纳反复强调的那样:“从各种观点看来,九世纪以后,西欧在本质上是一个农业社会.” [10] 11“从社会统计学的观点说来,中世纪社会,本质上是农业社会,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10] 53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古代的起点是城市及其狭小的领域,中世纪的起点则是乡村.” [14] 70明白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它说明中世纪兴起的新型城市文明,是在社会性质从总体上来说是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封建制度与基督教会的夹缝中生长并发育起来的,这种情况直接导致了中世纪晚期城市发展由兴盛到危机的历史转变.
事实上,在封建社会的土壤上兴起的中世纪城市,自产生之日起就深深地打上了封建的烙印:一方面它受领和扩散着源自乡村的一些封建因素,另一方面它又创造了具有封建内容的特定事物.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以手工业行会制为特征的城市等级制.在行会制度中,产生了帮工、学徒对师傅、个人对行会之间一定的人身依附关系;(2)城市贵族阶级的出现.随着行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由富有的、有显赫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上层市民构成的城市贵族阶层,面对下层民众表现出的盲目、放肆、凶猛的民主精神和原有领主重建权威的压力和威胁,城市贵族往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表现出畏首畏尾、固守本份、过于迁就、适可而止的态度,从而在城市贵族和下层劳动阶级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3)城市发展的分隔性、孤立性与封闭性.无论是面对内部城市贵族的压迫,还是面对外部其他国家的侵占,城市都没有采取一致行动进行对付,各个自治城市被分割成了许多心胸狭窄的社会共同体,权力和土地小块割据的局面蕴藏着的脆弱性使多数自治城市不能联合御敌;(4)城市和乡村貌合神离的社会现实.城市市民阶级的出现,在一方面看促进了城乡融合,在另一方面看则引致了城乡分化,因为它把“一”分成了“二”,使得中世纪欧洲在封建社会基础上出现了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区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ƻ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 [14] 104
城市自身的封建特性在其兴起之初有力地保护了它的成长与壮大,保证了城市工商业的顺利发展.但是,随着城市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封建因素必然演变成城市发展的严重桎梏,因为城市自身的封建性质越来越不适应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所培育出的新生的商品市场经济关系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了,而城市的旧的封建性躯壳却依然大大地禁锢着这些新生事物的成长.这种新与旧的矛盾冲突及其日益激烈,在14世纪的大饥荒与黑死病所引发的农业危机的强烈冲击下,最终导致了中世纪晚期欧洲普遍性的社会危机与城市危机,城市生产萎缩,经济萧条,市场荒芜.对于中世纪晚期城市危机的封建性质与根源,有学者给予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所谓城市危机的实质是封建危机,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城市及其整个社会的封建性质引发了城市危机,是封建制度引起了城市的危机,这是城市危机的基本根源.ƻƻ但在同时,城市危机又加深了封建主义制度的危机,使封建生产关系又一次面临崩溃瓦解的边缘.” [18]
城市的出现引起了欧洲社会结构的改变,社会结构的改变又引发了封建社会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和阶级斗争.不仅原有的教权与王权的斗争、贵族与王权的斗争、农民(农奴)与封建的斗争没有停息,而且在新增加的市民与封建的斗争(包括市民与王权的斗争、市民与贵族的斗争、行会师傅与帮工学徒的斗争、城市平民与富商大贾或城市上层分子的斗争等)的推动下更趋尖锐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从12世纪到15世纪,欧洲社会拥有了包括“国王、世俗贵族、教士、市民、劳动平民、宗教和世俗的权力”在内的“众多的独特力量”,形成了“组成国家和政府的一切必要因素”. [9] 134G135就城市社会而言,城市成了王权、贵族、教会与市民四种力量的角力场.在这四种力量的斗争与角力中,王权因面临着教会与贵族两种力量的挤压(特别是因贵族拥土自重而表现出的王权相对衰弱)而希望重建公共权威,市民也因面临着教会与贵族两种势力的盘剥而要求获得权利保障,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天然的同盟关系:在国王与贵族之间,市民扮演着一种中间力量;在贵族与市民之间,国王又扮演着一种中间力量.四种力量斗争并整合的结果是,到15—16世纪中世纪行将结束的时候,教会势力和贵族势力逐渐衰落下去了.这样,在历史舞台上就只剩下了封建王权和城市市民这两种主要力量.然而,这两种力量同样因为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要求社会结构获得一种新的质性改变,这就是为着适应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需要,一方面是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孕育,另一方面是独立的市民社会的培育.当然,这两种力量在能够分化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前,首先必须从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为一个高度重合的政治共同体,就如同双胞胎婴儿在诞生前必须共处于一个母体中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