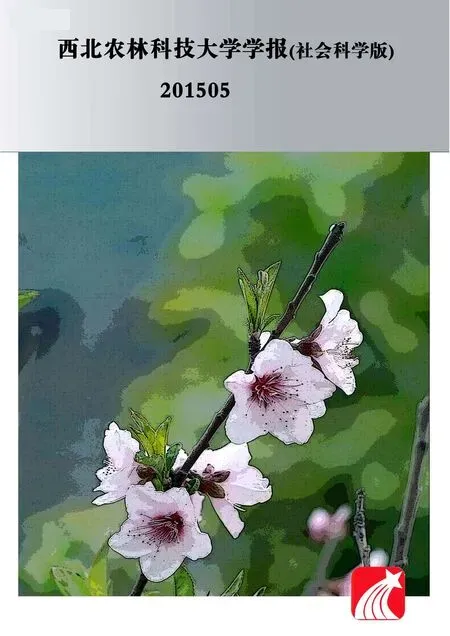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私法逻辑
刘 征 峰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私法逻辑
刘 征 峰
(中国政法大学 民商经济法学院,北京 100088)
“三权分置”土地改革的理论动因来自于经济学界,而非法学界。对“三权”法律关系的厘清不能僭越现有大陆法系私法的概念和逻辑体系。应当将对绝对所有权概念的坚持作为基础,拒绝借用普通法系的地产权和保有概念。“双重物的用益”和“物的用益—权利的用益”体系框架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不宜采纳。“物的用益—用益权的行使”和“成员权—物的用益”框架各具利弊。“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本质是通过债权实现物权和资本的结合。放宽物权性流转限制是当前改革的主要方向。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是土地权利私法化改革的基础。
三权分置;土地所有权;保有;用益物权;物的用益;权利的用益;用益权的行使;成员权;私权谱系
引 论
土地改革成为现阶段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早在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目标是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201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农村土地改革的目标和原则。2014年9月2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5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和《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方案》两份有关于农村改革的文件,“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经营权流转”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改革方向基本确定[1]。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11月20日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对三权分置的改革方向进行了细化。作为配套,2014年12月30日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规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该意见的一项重要目标。2015年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土地改革的内容,提出了 “将户籍与承包经营权脱钩”“坚持农民家庭经营主体地位,引导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抓紧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方面的法律,明确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界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农户承包权、土地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关系”等几方面的农村土地改革意见。这一系列的改革文件,奠定了现阶段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改革方向。
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来看,由于“集体所有权糅合了公法层面的治理功能、生存保障功能以及私法层面的市场化私权功能”[2],对集体所有权及其相关权利谱系的改革既会涉及到公法层面的探讨,也会涉及到私法层面的争论。从私法的角度来看,“三权分置”土地改革的核心在于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否突破了现行物权法的框架,是否存在对大陆法系财产权概念体系的背离。本文对这两个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存在两项前提:首先,由于“三权分置”主要针对“四荒土地”之外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而本文的分析也限定在该范围内;其次,本文仅对“三权分置”改革进行私法层面的法教义学分析,而不涉及对这一改革的利弊进行价值判断。
一、“三权”关系的法律梳理
(一)现行法律中只存在“两权”的概念
在现行法律中并没有单独的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只有统一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8条使用了“承包经营”这一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土地管理法》)第1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条均使用了这一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实际上并没有对《农村土地承包法》所规定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进行实质调整,在概念仍然沿用了统一的“承包经营”以及“承包经营权”的概念。在涉及流转问题时,无论是《农村土地承包法》还是《物权法》均使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而非单独的经营权的流转*参见《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2至43条,《物权法》第128、129和第133条。。 现行法律中只存在集体土地所有权和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两权概念。而此次土地改革所谓的三权分置,实际上是对土地承包权和经营权的分置,而不涉及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调整。
(二)大陆法系财产权体系下的“三权”关系
1.对绝对的土地所有权概念的坚持。“普通法系对于利益的现行分类最为清晰的形式反映在了与土地相关的利益中,被称为地产权(estate)”[3]。有学者分析认为,“英国法中的财产所有权客体不是有体物,而是利益”[4]。而大陆法系以所有权为基础的财产权体系是建立在对有形物(rem)基础之上的。在《德国民法典》中,所有权只能存在于有体物之上,并且与无形的权利相对应[5]。正是由于两大法系财产权体系的基础不同,无论是两大法系的法官、律师还是学者都对对方的财产权概念体系感到陌生和困惑。由于大陆法系所有权的客体是“物”,在逻辑上不可能形成英美法系那种双重(或者多重)的所有权结构。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是绝对的,完全的。正如英国学者F. H. Lawson 和Bernard Rudden所分析的那样,“完全所有权(dominium)是罗马大陆法体系中最引人注目的概念…完全所有权之负担种类屈指可数,这些负担与对于某物的完全所有权的概念之间存在细致的区别,后者被认为包含对某物普遍的,未分化权利的特征。”“一旦这些负担消失,它就能恢复到最初的状态”[6]。美国学者John Henry Merryman对大陆法系中所有权概念和普通法系中土地产权概念的比较更为形象。大陆法系中,“罗马式的所有权概念可以被比喻为一个标记了所有权的盒子,拥有盒子的人就是所有权人。在所有权处于完整、无负担的状态下,盒子中包含了特定的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所有权人可以打开盒子,转移其中一项或者一些权能给其他人。然而,只要他仍然拥有盒子,那么他就仍然拥有所有权,即使盒子中空无一物。与此相对,英美法的相关规则是极其简单的。不存在盒子的概念,只存在一系列法律利益的概念[7]”。
由此可见,在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下,土地所有权的形态是单一而绝对的,他物权(如担保物权、用益物权)只是土地所有权项下权能的有期限让渡,而土地所有权本身则被假定为永续存在。回顾两大法系土地财产制度的这些基本性区分的意义在于如果我们将“三权分置”的概念置于大陆法系的框架下进行解释,那么解释的框架就应当是罗马式的,而非英美式的。亦即,我们不能以利益束为基础解释三权分置的改革架构。因而,对“三权分置”进行解释的前提是对单独所有权及其派生权能的坚持。三权分置改革并不是要建立类似于英国封建时代的双层所有权结构,虽然有学者经常将社会主义制度中的集体所有和私人用益制度与英国的土地保有制度进行类比。如John Henry Merryman教授所言:“与欧洲大陆的传统相比较,苏联财产法的概念体系与英国更为相似”。他形象地将这种体系称为社会主义保有(socialist tenure)。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联合报告《中国: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城镇化》的报告中,亦将我国现在的土地制度称为双层的地权制度(dual-track tenure system)[8]。但从规范层面来看,我国物权法沿袭了大陆法系民法传统,是建构在有体物而非无形利益的基础上的。从现有的改革文件来看,“三权分置”改革并没有超越传统大陆法系的土地所有权概念,对绝对土地所有权的承认是三权分置的基础和前提。承包权、经营权不是与所有权并列的权利。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它是绝对的。土地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
从最新发布的《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第22条来看,现阶段农村产权改革的目标首先是要探索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而非在所有制上进行私有化改革。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全面的、绝对的归属权(umfassende absolute zuordnungsrecht)这一性质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土地上的他物权只是将“对物直接控制的个别权能置于权利人之下”[9],而不是与之相并列的权利。无论是所有权还是限定物权,它们原则上都指向有形物*德国法中例外情形包含第1 068条规定的权利上的用益权和质权。同上注,第7页。在陈卫佐先生所译注的《德国民法典》中,其认为权利上的用益物权所指向的权利主要是可转让的债权或有价证券。参见德国民法典[S]. 陈卫佐,译注.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65。, 而非抽象的利益。那种认为“农地产权是一个权利束,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子权利,且每一项子权利的内容还可以再细分为由一个人或多个人享有的相应的权益”的观点实际上是对大陆法系绝对所有权概念的背离[10]。
2.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关系。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是以对承包经营地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权利的用益物权。既然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性质上为用益物权,那么在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的情况下,承包权和经营权是否均是用益物权呢?要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首先需要对现有改革文件的描述进行归纳梳理。就承包权的法律性质而言,按照高圣平教授的解读,“三权分置”实际上是将“土地承包权利理解为农民(农户)的成员权性质或身份权性质的权利”[11]。如果将承包权作此理解,那么经营权明显不属于承包权的派生。从农业部部长韩长斌的政策解读来看,三权分置是顺应农民“保留承包权,流转经营权”的创新[12]。这里所保留的承包权实际上仍然是物权法中的承包经营权,在性质上仍然是用益物权。我国法律采用承包经营权这一术语在很大程度是上路径依赖的结果,其既表明了此项用益物权的原因行为(承包经营合同),也表明了其权利的内容和性质(农业经营)。从《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的内容来看,“稳定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包含了两部分的内容:一是“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二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这两项内容似乎进一步印证了“三权分置”中的承包权实际上就是现行法律中的承包经营权,而并不是指取得作为取得用益物权基础的身份权。如果只是一项单纯的成员权,其并不属于物权法的范畴,自然无进行登记和进行物权保护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3月1日即将开始实施的《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仍然使用的是“承包经营权”登记,而不是承包权或者经营权登记。。
就经营权的法律性质以及其与承包权的关系而言,《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并没有界定经营权和承包权的法律关系,而是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需要研究探索。不过该意见使用了“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这一用语。《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采用了“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这一用语,并且认为,该经营权可以采取出租、入股等方式流转。《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在“交易品种”一项中使用了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概念,并且认为该经营权可以采取出租、入股等方式交易流转。该文件使用了“产权”这一经济术语,并且认为经营权乃产权的下位概念。在强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时,却又使用了土地承包经营权这一术语。统观这些改革文件,我们不难发现,改革文件的制定者在术语使用上缺乏清晰统一。更为根本的问题是,迄今为止改革者对承包权和经营权二者的法律关系仍然缺乏清晰的认识,认为此问题仍然有待探讨。
从民法的角度来看,对经营权这一概念法律性质的正确理解是确立其与土地承包权、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关键。从逻辑上来看,如前文所述,我国物权体系建立在大陆法系传统之上,因而不可能存在两个所有权。故而,经营权的性质必然不为所有权。比较有争论的两种判断是用益物权说和债权说。持用益物权说的学者认为,在承包权为身份权的情况下,经营权应当为用益物权,承包权只是获得经营权的原因[14]。也有观点认为,应当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同时认定为用益物权,二者均受物权保护[10]。持债权说的学者认为,承包权的性质应当为用益物权,同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相互冲突的用益物权,因而经营权的性质应当为债权[14]。分析这些观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双重物的用益。所谓双重物的用益,是指承包权和经营权在法律性质上均为用益物权,且二者均为对土地的用益。对于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此种理解源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土地是权利束的集合。这种理解本质上是普通法式的。正如Anna di Robilant 教授所言:“在美国,每一个法学院的新生都会了解到财产是 ‘一捆树枝’(bundle of sticks)”“这一概念由霍菲尔德引入,并在其他法律实证主义者那里得到了发展…在大陆法系,大体上来说,律师们仍然认为财产为所有权,而对于法学家来说,财产仍然是对某物的一致而带有整体性的权能集合”。Anna di Robilant教授形象地将大陆法系的财产权概念比作一颗树。树干就是所有权这一核心概念[15]。如果将承包权和经营权均理解为用益物权,实际上是在相近的所有权权能上设定了相类似的物权。这与大陆法系一物一权原则严重相违背。这种架构之下,承包权和经营权作为指向所有权的同样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在逻辑上与用益物权的内涵不相协调。并且,这一理解将导致所有权——用益权体系的复杂化,模糊了权利之间的界限,与现代法律的概念清晰性要求相背离。
第二,物的用益和权利的用益。这一种理解实际上是将承包权仍然理解为承包经营权,而将经营权理解为承包经营权的用益,亦即经营权是用益权的再用益。作这样的理解避免了对一物一权原则的背离,因为承包权所指向的用益物为土地,而经营权所指向的用益物为承包权。但是,对权利的用益(Nie brauch an Rechten)在大陆法系是作为例外情形存在的。权利用益的范围通常并不包含用益物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将经营权理解为权利的用益与改革文件的精神并不相符合,因为取得经营权的权利人并不是在使用权利,相反,他是在占有、使用土地并获取收益。从域外立法例来看,德国法上的权利用益权是“通过对本体权利的占有而获得本体权利的孳息”,主要包含债权用益权、有价证券用益权、抵押权用益权和继承权用益权,并不包含用益权的用益权这一类型[16]。故而,将经营权理解为权利的用益既难以获得法律上的逻辑自洽性,也缺少实证法上的证据。
第三,物的用益和用益的行使。与前两种理解相似的地方是,将承包权理解为用益物权。与前两种观点不同的是,此种观点将经营权理解为用益物权的行使。在德国法中,虽然用益权不能转让,但是用益权的行使权可以转让*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 059条。德国法上用益物权的不可转让性实际上是继承了罗马法的传统。参见屈茂辉.用益权的源流及其在我国民法上的借鉴意义[J].法律科学,2002(3):77。但囿于工商企业发展之需要,德国民法作了一些修正,增订了第1 059a条作为例外,亦即“法人或有权利能力的合伙的情形下的可转让性”。。 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让限制的理由与德国并不一致。德国法上对用益物权转让的限制更多是来自理论上的,亦即用益权的性质决定了用益权的不可让与性[17]。而我国对用益物权转让进行限制的理由则大多来自政策层面,例如对失地农民生活保障的担忧[18]。《瑞士民法典》中亦有用益物权行使权转让的规定。根据该法典地758条的规定,除非用益物权是专属于个人行使的权利,否则用益物权人可将其转让给第三人。在此情况下,所有权人可以直接对抗受让人。类似的规定出现在《法国民法典》第595条中,用益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自己享有权利,也可以将权利出租给他人。
从现阶段的改革文件来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仍然是受到限制的。如果将承包权理解为受流转限制的用益物权,那么经营权作为行使用益物权的权利可作债权性流转。这种债权性流转的本质是用益物权的出租,而非转让。这里需要区分的是行使用益物权的权利的流转和由此产生的债权的流转。比如承包权人将经营权转让给第三人后,承包权人获得了收益权。如果承包权人将此收益权进行流转(如权利的质押),本质上并非是对经营权的流转。对这种区分有清晰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经营权的流转所指向的客体是用益物权的行使,而非流转所产生的收益权。但是此种理解,可能会与前文《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所使用的“经营权的抵押、担保”描述相悖。因为能成为抵押权客体的只能是土地的用益物权,而不可能是一项债权。当然,该意见并没有直接使用“抵押担保”这样的描述,而是使用了并列的“抵押”“担保”,为将来的学术讨论预留了空间。另外,需要特别澄清的是,按照德国法的观点,能够设立权利物权的权利,必须是能够转让的权利,适用于关于权利转让的规定,并且必须移交权利文书的占有[16]。如果作此理解,那么所谓经营权的担保流转实际上是经营权收益的担保流转。因为经营权的流转本质上是用益物权的出租,而非用益物权的转让。因而能够满足前述三项要求的只能是用益权出租的收益权,亦即收益权的质押。如果用益物权人没有将用益物权的行使权利转让给其他人,此时他并没有获得相应的收益权,此时他是没办法将收益权进行用于担保的。故而,在此种观点是按照这种逻辑展开的:
土地所有权—土地用益物权(承包权)—用益物权的出租(经营权的流转)—经营权出租的收益—收益的流转(转让、入股、质押等等)
对承包权和经营权作这样的理解是相对保守的,也基本建立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不需要对现行法律进行大幅度的调整。
第四,成员权和物的用益。相对于前一种理解的保守性,这种理解则需要大幅度调整现行法律。这种理解首先将承包权视为一种成员权,而将经营权界定为对集体所有土地的用益物权。亦即承包权是一种集体组织成员进行承包的资格,通过承包经营合同获得经营权。与此相关的是集体资产的股份化改造。这种改造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即企业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分离。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代表国家成为国有企业股东,行使出资人权利,从而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明晰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集体成员的权利的股份化改造是避免集体土地等集体资产所有权主体虚置化的一个重要改革方向。这种改造与“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的改革目标相吻合。《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所提出的“确权确股不确地”正是这种改革思路的集中反映*最新发布的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对于确权确股不确地采取了保守的态度,认为应当从严掌握着一种试点的范围。现有的改革文件将农村集体产权区分为三类:土地等资源型,非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资产。对于最后一种才能进行完全的股份量化,因为这种资产的流转通常限制较少,不会触及土地的公有制性质。。亦即,在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意的情况下,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不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而向集体经济组织外的成员发包。发包的收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以其股东身份获得分红。当然这种改造不可能以绝对法人化的方式进行。因为集体土地所有权并非公司的出资形式。完全的法人化改造会危及集体所有权的性质。因而“确权确股不确地”实质上是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资格换取集体经济组织中的股权。正如学者郭晓明所言,很多地方试点的土地股份合作,农民以承包权而非经营权成为股东[1]。但是,从农业部部长韩长斌的政策解读来看,农民入股的并非承包权而是承包经营权[19]。从《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第八条规定的内容来看,现阶段流转形式最为狭窄的为农户承包土地经营权,方式局限于出租、入股等。这里所使用的用语为经营权。并且,该意见着重区分了家庭承包方式取得和非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经营权。因而,在该意见中,经营权的范畴大致与现在承包经营权的范畴相一致。承包权是作为获得经营权的一种方式存在的。
如前文所述,将承包权确定为成员权或者股权的最大问题在于,成员权和股权并非物权,不属于物权保护的范围,这就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大范围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不动产物权登记的只能是经营权。并且,法律将面临如何界定成员权的困境。
综上,界定承包权和经营权法律性质是确定二者关系的前提。以上四种学说中,前三种学说都将承包权界定为物的用益,在范畴上大致与现行法律中的承包经营权相重合。对于经营权则存在物的用益、权利的用益和用益权的行使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通过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前两种观点与大陆法系的所有权——用益物权理论之间存在严重的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与此相对,物的用益和用益的行使这一解释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就成员权和物的用益这一学说而言,与现行改革文件的精神最为契合,但是此种理解的问题在于:如果存在“通过承包方式所取得的集体土地用益物权应当受到限制”这样的理论假设,这种框架除了产生额外的物权登记改革外,并不具有实际意义。
二、经营权流转的私法内涵
(一)“三权分置”和经营权流转的关系
“三权分置”是服务于“经营权流转”这一目标的。从私法的角度来看,“三权分置”的目标是确立私权的归属,“而经营权流转”则更多涉及私权之下物的高效利用。“物尽其用”是当代物权法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而物尽其用的前提在于物权的自由性。正如日本著名法学家我妻荣先生所言,所有权的解放是其与契约结合的第一步[20]。资本主义革命不仅解放了人,也解放了所有权[20]。梅因爵士在分析“身份向契约的社会运动”时同样涉及到了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化问题[21]。封建时代土地所有权缺乏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双重所有权的存在。我们不妨将梅因和我妻荣所讨论的对象从“所有权”扩展到“其他物权”。实际上,无论是何种物权,其在内容和法律性质上的清晰化均是其与债权结合的前提。当代市场经济中的“流转”在法律规范层面是通过契约这样的工具实现的。正如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所言,在动态的法律生活时代,债权不复是旨在物权或物之享益的手段,而本身就是法律生活的目的[22]。也就是说,在法律生活层面,权利的谱系和结构是不再是契约法的目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们是服务于契约法的。
现在人称“此物是我的”在更大意义上是为物及其之上权利的流转创造基础。故而改革文件首先强调了确立清晰土地物权的重要性,并意在完善土地物权的登记。在坚持集体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的目的在于完善一套最有利于土地物尽其用和规模化生产的私权谱系。“三权分置”正是要发展出一套适宜于土地高效利用的私权谱系。当然,如前文所述,这套私权谱系应当建立在大陆法系财产权概念体系之上,而不是从普通法系中借鉴个别孤立的概念。我们不能因为经济上考虑,就抛弃已经形成的法律传统,借用双重所有或者土地保有这样的法律概念。因而,虽然物的高效利用是决定“三权分置”的目标,但对于“三权分置”的规范解释仍然应当受制于大陆法系私权体系和逻辑。
(二)债权性流转和物权性流转
“三权分置”改革的动因在于原“二权分置”状态下农户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处分是受到严格限制的。以未经发包方同意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为例,受让方不仅无法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这项用益物权,其转让合同亦属无效合同*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3条。。相对于物权性流转而言,现行法律对于债权性流转的限制则要宽松许多。以最为常见的租赁而言,并不存在转让流转情况下出让人需要具有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收入来源要求*参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第35条。。这是由于租赁不会导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转移或者被设定权利的负担,而只是会产生债权性质的利用[23],这种债权性质的利用在方式上较为便利,且符合所有权人或者用益物权人强化其支配地位的愿望[20]。相对于物权处分而言,其在数量上实际上占据绝对优势*我妻荣先生在考察日本的状况后认为,日本的土地利用关系实际上很少设定用益物权,大部分是设定租赁契约[20]。。但债权性流转的弊病在于妨碍了土地实际利用人对土地的投资。在缺少物权保护的情况下,单纯的债权债务关系会导致对土地的短期过度利用和长期改良投入的减少。我国过去工商资本一直徘徊于农业经营边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对于缺乏物权保护的担心。
“三权分置”的大背景正是要建立现代化的农业,鼓励工商资本的进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将入股区分两类:一是以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联合从事农业合作生产经营而发生入股行为;二是以其他承包方式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股份公司或合作社。这明显不利于工商资本参与前一类土地的经营。《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提出了现阶段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两种方式:出租和入股。出租属于债权性处分而入股则属于物权性处分。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相比,该意见认为经营权流转的受让方原则上不受限制*参见《关于引导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展的意见》第九条。。即,出租和入股的对象可以是法人企业。在《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尽快制定工商资本租赁土地的准入和监管办法的意见,仍然将债权性用益作为工商资本进入的主要方式。该意见确认了土地经营权入股的两种对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并没有明确排除入股法人企业的可能。之前重庆市在获批“国家统筹城乡发展综合试验区”后,开展了股田公司改革,但中央调研后叫停了股田公司试验,对通过家庭承包方式获得的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法人方式流转持否定态度[24]。在“三权分置”改革后,流转的对象是经营权而非过去的承包经营权。但现有改革文件仍然将其局限在“出租”和“入股”。实际上,如果认可经营权的入股法人这一物权性处分,对于其他物权性处分已经无限制的必要。经营权入股法人企业会导致经营权的实际转移。
如前文所述,对“三权分置”的理解构成对“经营权流转”法律理解的基础。如果我们将承包权理解为用益权,而将经营权理解为用益权的行使,那么经营权的流转实际上是“用益物权行使权”的流转。用债法的术语来描述,流转受让人取得的是债法上的用益(承租权)。根据民法原理,流转受让人可以取得占有保护(Besitzschutz),对抗用益权人和所有权人。如果流转受让人再将经营权进行流转,则必须受到债法规则的调整。例如,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40条的规定,转租必须要经过出租人的同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方有学者指出“从租赁关系中拟制出的对实物财产的经营权高度依附于出租人,不具有可转让性”[25]。在德国,承租人地位依据法律而非法律行为进行转让只存在于例外的情形(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 568a条规定了夫妻双方离婚后承租地位依据法律(kraft Gesetzes)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中,其他情况下承租权的转让均需要取得出租人的同意。如前文所述,在设定担保等物权性流转情形中,能够设定权利质押的只能是出租收益权,而非用益权的行使。并且,法律将这种用益权的行使进行证券化从而创设可高度流转的权利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将承包权理解为成员权而将承包经营权理解为用益物权,从现行改革文件来看,稳定和确定成员权是改革的基础,而用益物权的流转是改革的第二步。这种理解之下的经营权流转同样包含物权性流转和债权性流转。现有的改革文件既允许经营权出租,也允许入股企业,实际上是取消了原来法律中对用益物权物权性流转的过度限制。现在,对于经营权流转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农业用途之上。
三、结论:私法框架与经济改革的冲突与协调
综上,要形成与“三权分置”土地改革相配套的私权体系,首先不应当突破传统大陆法系的私法框架,破坏私法体系上的自洽性,盲目借用普通法中诸如“保有”之类的概念。对“三权”的法律解释不应当以平行权利束为视角,而应当以大陆法系“树型”或者“盒子型”财产权谱系为基础。其次,由于“三权”均构建于集体土地所有权基础之上,大陆法系绝对所有权的概念是解释的前提。再次,“双重物的用益”和“物的用益—权利的用益”这两种解释框架存在法律逻辑上的矛盾,不宜采纳。而“物的用益—用益权的行使”这种框架面临“有因性”原则的制约,且不利于权利的再流转,但在法律逻辑上具备科学性。相比较而言,“成员权—物的用益”这种结构与现阶段改革文件的精神较为契合。不过在这种解释框架下,如何界定成员权的权利内容成为现阶段法律所面临的难题。最后,私权体系的建构与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套密不可分。在《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城乡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土地权利体系的完善密切相关。与之前进行的国企改革相类似,只有让土地经营权与社会保障、户籍脱钩,土地相关的权利才能真正回归其私权本质。扩大农民的财产权利必然会以土地相关权利的一定程度上的商品化和契约化为基础[26]。
构建与“三权分置”相适应的私权谱系应当以“经营权的流转”为目标。物权和资本相结合的最重要方式便是契约。科学而清晰的私权谱系是物权与债权结合的前提。从流转的方式来看,逐步放宽物权性流转是现阶段改革的主要方向。不同的解释框架决定了对“经营权流转”的不同解释。但值得注意的是,经营权的高效流转这一经济目标的实现不是创设私法权利的唯一理由,私法的秩序和科学性为私权体系的构建确立了边界。
[1] 李秀中.习近平定调农村土地改革[N]. 第一财经日报,2013-09-30(A03).
[2] 汪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三重功能属性:基于罗马氏族与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的比较分析[J]. 比较法研究,2014(2):12-25.
[3] 刘兵红.论英国土地保有关系对债作为财产所有权客体的影响[J].河北法学,2012(4):175-178.
[4] Thomas W,Merrill,Henry E. The Oxford Introductions to U.S. Law: Property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97.
[5] 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M].邵建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875.
[6] F H Lawson, Bernard Rudden. The Law of Property[M].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2:115.
[7] John Henry Merryman. Ownership and Estate: Variations on a Theme by Lawson [J] .Tu L Rev, 1974(48): 916-945.
[8] World Bank Group,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Urban China: Toward Efficient,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Urbanization[EB/OL].[2015-01-01].http://www.world bank.org/ content/dam/Worldbank/document/EAP/China/WEB-Urban-China.pdf:226.
[9] 曼弗雷德·沃尔夫.物权法[M].吴越,李大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6.
[10] 潘俊.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权利内容与风险防范[J]. 中州学刊,2014(11):67-73.
[11] 高圣平.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下农地产权结构的法律逻辑[J]. 法学研究,2014(4):76-91.
[12] 张玉洁.土改再推进,政策创新撬动农业现代化[N]. 中国证券报,2014-12-30(A03)
[13] 刘俊.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探讨[J]. 现代法学,2007(2):170-178.
[14] 陈小君.我国农村土地法律制度变革的思路与框架: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相关内容解读[J]. 法学研究,2014(4):4-25.
[15] Anna di Robilant. Property: A Bundle of Sticks or A Tree?[J] .Vand L Rev, 2013(66):869-932.
[16] 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50-351.
[17] 丁关良.国外农用土地流转法律制度对中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启示[J]. 世界农业,2010(8):39-44.
[18] 邓科.土地能保障农民什么[J]. 中外房地产导报,2001(19):22-23.
[19] 李慧.解读:《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J]. 黑农江粮食,2014(11):40.
[20] 我妻荣.债权在近代法中的优越地位[M]. 王书江,张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4.
[21] 梅因.古代法[M]. 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169-171.
[22] 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M]. 米健,朱林,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64.
[23] 杨光.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问题研究[D].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49.
[24] 郑钢,邓勇.重庆:“股田”转向“合作”[N]. 中国财经报,2008-10-14(1).
[25] 宋志红.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法律性质辨析[J]. 法学杂志,2010(5):9-13.
[26] 史卫民.我国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实践与发展趋势[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2):105-109.
Analysis of the Reform on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Contracted and Management Rights of Rural Land”: From Perspective of Private Law Logic
LIU Zheng-feng
(SchoolofCivil,CommercialandEconomicLaw,China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andLaw,Beijing100088,China)
The theoretical reasons of rural land reform stem from economics rather than jurisprudence.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wnership, contracted and management rights of rural land should be confined to the conception and logic system in civil law. It is the conception of ownership, instead of estate or tenure in common law system, which constitutes the premise of the analysis. There are some logical inconsistencies in “Double Usufructuary Rights in Rem”structure and “Usufructuary Rights in Rem-Usufructuary Rights in Right”structure. Both the “Usufructuary Rights in Rem-Exercise of Usufructuary Rights”and the “Membership Rights-Usufructuary Rights in Rem”have their virtues and faults. The legal essence of “Circulation of Management Rights” is the combination of real right and capital. Putting fewer restrictions on circulation based on real right is the trend line of current reform. Reforms on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re crucial to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to private law.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contracted and management rights of rural land”;ownership of land; tenure; usufruct; usufructuary rights in Rem; usufructuary rights in right; exercise of usufruct; membership right; private right system.
2015-02-11
中国—瑞典政府互换奖学金资助项目(Swedish Institute Reference No. 19118/2014)
刘征峰(1988-),男,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瑞典隆德大学法学院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法、人权法和公司法。
F302.2
A
1009-9107(2015)05-002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