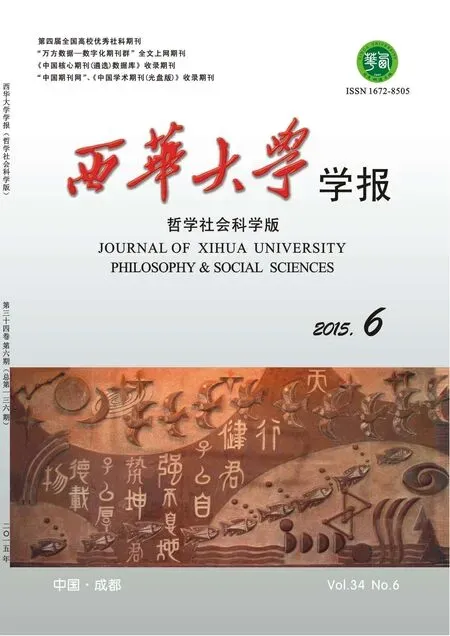蒯因的“初始翻译”及其“意义倾向”论
肖福平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翻译理论与实践·
蒯因的“初始翻译”及其“意义倾向”论
肖福平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蒯因的“初始翻译”为我们展示了翻译的相对性特征,这样的相对性特征既涉及译者自身的观察与理解,又涉及目标语言使用中的意义表现“倾向”。在蒯因那里,“初始翻译”并非完全意义上的翻译,译者总会在现实的和可能的语义世界中追求与言者之语义的同一,当然,这样的“同一”追求在外延主义的要求下又总是难以实现的,除非我们回到译者与言者所处的主体性地位的认识上来。不论“初始翻译”如何体现意义确立的“倾向”决定,译者与言者的主体性地位总是为我们提供语言行为发生的普遍性基础,即作为理性存在的纯粹语义基础,翻译的“不确定”只是我们走向“确定”的过程与环节,人类社会语言行为的发生及表现形式遵循着共同性的理性规定与认知模式。
翻译;语言;倾向;不确定性
在语言哲学的分析传统里,关于语言的概念问题和语言的意义赋予问题讨论总是发生在一种外延性要求的范围之内,其过程的展开总是要体现外延主义的逻辑要求。语言是基于现实世界的经验现象,其意义的赋予在于语言现象的陈述真实和经验事实的“指称”。在20世纪的分析哲学领域,许多哲学家围绕语言概念和语言意义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蒯因就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蒯因的研究里,他关注了作为现象存在的语言形式特征,并力求通过这种特征分析来展示出一种语言现象规律,就如自然世界中的其它规律一样,从而探讨一种关于语言驾驭和使用的理想方法。不论蒯因的理想方法是否会因为他的研究成果与实践而到来,但他的研究对于语言概念与意义问题的探讨确实反映了“语言转向”的辉煌成就。蒯因通过概念与语义问题的研究将语言的表达形式同意义源泉、形成条件联系起来,并在语词现象的意义和句子现象的意义方面加以凸显。
如果我们为语言概念的讨论选取一个恰当的提问方式,那它就是“语言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我们在此只局限于蒯因的现代语言哲学分析。在“语言是什么”的思考中,蒯因和戴维森等人一起在相同的领域和方向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在涉及具体内容的细节上,他们的研究又具备各自的特征。在以下的内容中,我们将围绕语言的翻译问题来探讨蒯因的语言概念观,以及关于这种观点的局限性问题。
一、语言与蒯因的“初始翻译”
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对于语言概念的思考总是要同一种经验性的目标存在联系,而非直接地聚焦于概念形式本身的存在。我们在进入语言概念时,尤其是在遵循外延性逻辑要求的情况下,我们是将“语言是什么”的答案视为自然存在的现象,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语言”。于是,我们才有了自己认知的语言,以及构成了这种语言的语词、句子等等。由于这些作为“自然语言”及其构成部分的语词和句子对于使用它们的人类而言无需任何的特别关注,它就像空气和阳光一样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在蒯因看来,正是这种对语言存在的习以为常,我们在思考“语言是什么”才会自然地滑向“语词现象是什么”的替换中,而对于语言存在的特征、语言意义的产生源泉和理解语言意义的原因和条件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如果我们要在语言概念思考的问题上获得新的认识,并重新确立“语言是什么”的探寻之路,我们就必须克服那种“习以为常”的状态所造成的对于语言特征和意义特征揭示的遮蔽,我们就必须从语词现象的存在原因中去获得新的定义方法。
为此,蒯因提出了自己的“初始翻译语言学家”与“初始翻译”等概念。根据蒯因的界定,初始翻译语言学家就是那些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如自己的母语,去翻译研究另一种未知语言的人,他们所要认知和翻译的这种语言应该属于一种陌生地方的人们所讲的陌生语言,这样的语言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外语。尽管他们可以凭借自己所熟知语言的特征,如语词特征、结构特征、表意特征等,去直观那些陌生语言所具有的相似性特征,但这样的相似性只能是一种表面的相似性,它根本就不能真正地代表两种语言在意义和语法规律表达上的相似或等同。蒯因的初始翻译所关注的就是对一种完全陌生语言的翻译,因此,这样的初始翻译没有任何预先存在的翻译方法和翻译手册可供利用。因此,从事这种翻译的语言学家们所面临的陌生语言其实就是一种初次接触并加以认知的陌生对象,一种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此,为了有别于自然世界中物质的对象,我们将这样的陌生语言称之为对象语言。蒯因认为,在认知这样的对象语言中,语言学家们所担当的就是作为科学家的角色,语言学家们必须采取一种严谨的科学态度,以对象语言的事实根据为观察和思考的出发点,力求达到语言分析的客观性,从客观的、经验实在的视角去确立对象语言的语词意义和句子意义。这种以自己的语言为基础来确立对象语言意义的方法被蒯因看成为一种初始性的翻译工作,通过这样的“翻译”工作,任何来自于对象语言的句子在理论上都可以在语言学家自己所熟悉的语言中找到相应的部分和意义说明,即对象语言的句子意义可以使用另一种语言来加以呈现。
考虑到初始翻译的实现条件,初始翻译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系统且完整的方法,因为在陌生的对象语言里,我们有可能遭遇句子构建的无限性问题,而且,无限多的句子构建将会使“翻译”变得困难。从事初始翻译的语言学家必须首先拥有自己的翻译手册或指南,然后再依据这样的手册将陌生语言中的句子转换成自己语言中的句子,即母语中的句子和意义。我们将这样的翻译称之为“初始翻译”。在蒯因看来,所谓“初始翻译”,就是将一种人们从未接触过的、完全陌生的语言,如一种与世隔绝的土著部落人使用的语言,译成母语,如英语。这样的翻译是第一次的和初始性的翻译,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翻译资料或翻译手册。从事这种“初始翻译”的唯一办法就是去观察土著人是怎样使用这种语言的,即从外部的语言行为刺激过程来分析刺激的意义、刺激的语言表现形式等等,进而对语言表现形式进行诸如场合句、观察句、同义句等的揭示。这样的理解或“翻译“没有借助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方法而完全地转向观察或语言行为来加以完成,“在心理学上,一个人可以是,也可以不是行为主义者,但在语言学中,人们没有选择”[1]5。通过观察并记录下结果,并将这样的结果放入母语的理解模式中,编写出相关的翻译手册,由此达到对陌生语言的理解和翻译。因为对于翻译的人而言,对象语言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完全是陌生的,这样的翻译完全是一种首创性尝试和意义解读。显然,蒯因所构想的这种翻译只能是一种初始意义上的翻译,它并不能涵盖全部的翻译行为,也不能算作理想的模式标准。因为初始翻译过程中所获得的翻译手册仅仅是语言学家们基于一种假设的归纳结果,它源自于母语的表达体系和意义赋予体系,这样的翻译手册其实更多地承载了母语的表现习惯和思维方式,陌生语言更多地被语言学家主观地赋予了“意义”。因此,对于陌生的对象语言而言,不同的语言学家在他们从事“初始翻译”中自然会形成各自不一样的翻译手册。“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编写出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手册,这些手册都符合全部的言语行为倾向,但彼此之间并不相一致。”[2]27从整体上来看,这些翻译手册都能起到翻译陌生语言或土著语的作用,但在两种语言的句子、语词的一一对应上,其翻译就是难以达到的。“在一个成分语句的翻译所出现的偏差,会在另一个成分语句的翻译中得到弥补。就此而言,没有任何根据去说,两个很不相同的个体语句的翻译中哪一个是正确的”[3]591。然而,在当今的哲学、语言学和翻译领域,蒯因的翻译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仍然不可低估,“有些哲学家把它当一条公认的数学定理一样看待”[4]vii。
在蒯因看来,从事初始翻译的活动所指向的“科学对象”就是作为语言的存在,一种作为理性的认知世界之内的对象的存在,而且,关于它的认知活动一定要发生在理性存在的语言经验世界之中。于是,我们在思考初始翻译的问题上不可绕开这样两个层面:一种是作为语言对象本身的存在,另一种是作为我们认知的语言对象;前者所示属于语言自身的对象地位或本质地位,后者所示属于我们的认知语言或作为知识的语言现象。依据蒯因的观点,在初始翻译的过程中,我们真正要从事的工作就是要创造出“翻译手册”,即“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编写出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手册,这些手册符合全部言语行为倾向,但彼此之间却不一致”[5]27。正如上文所言,这样的翻译手册一定是基于母语或自己所熟悉语言的应用过程的经验总结和模式,而且总是在不断克服歧义的过程中趋向全面和精确。实际上,我们依据这样的翻译手册而从事初始翻译的解读情形和理解方式并非仅仅表现在翻译外语的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使用相同母语或熟悉语言的交流过程中,所以,不论是处理完全陌生的初始翻译,还是使用相同语言的交流,我们在理解语言意义时都要面临一样的处理情形和方式。只不过使用母语交流过程的“翻译手册”早已被我们所熟知而无需建构。此外,如果我们对陌生语言的形式符号进行翻译,我们就要对这些语言形式符号进行语音、拼写、组合、定义等方面的确立,当然,它一定是基于“翻译手册”的确立过程并遵循了翻译者自己所熟知语言的意义赋予过程。显然,没有这样的发生过程,陌生语言的形式符号就只能是未知的东西,这样的未知的陌生形式或符号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母语中某些我们所不知晓的形式或符号。如果我们将这样的语言形式或符号限制为一种更为具体和熟悉的语言单位,那这样的语言单位就一定包括了语言学者们所乐见的语词部分。从语言存在的自然观来看,语词部分的内容应该是一种具备任意性特征的符号,这种符号本身是不具备任意意义的。
那么,从真正和恰当的意义上来说,每一人类语言中相传下来的每一个词都是任意的和规约的符号。之所以是任意的,是因为目前人们使用的上千个其它的词,或成千上万个人为造出来的词,都可能是同样学得的并用于这种具体的目的;之所以是规约的,是因为使用这个词而不使用那个词完全在于这样的事实:它已经在说话人所属的语言社团中使用了[6]19。
依据语词意义的“任意论”,语词就是符号本身,这样的语词本身不能为我们提供任何关于其意义的指称与赋予,蒯因的“初始翻译”清楚地体现了这种“任意论”下的语词存在特征。蒯因关于语词意义的“任意论”与洛克的语言自然观思想联系在一起。洛克认为,语词意义的获取不在于语词本身,它必须是建立在同言说者心灵观念存在的前提之下,而且在两者之间发生了某种联系的情况之下。于是,语词意义在于指称“观念”,语词作为符号只有在指称“观念”时才具有意义。洛克认为,人们在创造了词语符号时,也创造了符号与“观念”的对应关系,当然,这样的对应关系“并非自然的联系”[7]389,而是一种任意的关系。此外,洛克在将语词视为一种符号之外,他还将语词视为了一种声音,一种可以由人类自身能够发出来的声音,并且认为,只有当这样的声音被建立为一系列的关于观念的感性符号时才具有意义。比较而言,在蒯因的语言哲学思想里,语词的意义赋予和形成的“自然性”和“任意性”特征同样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蒯因不同于洛克的地方在于语词意义的来源,蒯因并不主张语词意义的源泉在于心灵的观念。在蒯因看来,人们关注语词的意义不能缺少一种言说者的可利用的“感觉证据”事实,这样的“事实”不同于“观念”的存在,同时,它也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指称的对象事实。
我们被告知,语言是用来传达观念的。当我们学习语言时,我们学习把它的词与其他说话者与之相联的同一观念相关联。我们如何知道这些观念是同一的?并且,就交际而言,谁在乎它?我们全都已学会把“红的”这个词用于血、西红柿、熟苹果和炸龙虾等。与之相联的观念、与之相联的感觉,是随情况不同而不同的。语言回避观念而以对象为家。对于语言研究来说,没有比观念更无用的东西了[8]35。
二、言语行为与意义“倾向”
在蒯因看来,语词的意义不可简单地等同于指称的物质对象,任何通过物质性对象来将意义确定为实体的做法都是不恰当的,而洛克观念论更是将内涵性的观念作为独立存在的对象,这样的观点更是不能被蒯因所接受。在意义的指称理论和观念理论之外,蒯因还将语言的意义考虑带向了句子的层面,带向了言说者与句子认同之间的关系分析。关于语言的“感觉证据”的事实在蒯因看来属于客观存在的基本事实,这样的基本事实集中体现在言说者对于语言句子的认可倾向,即对句子的赞同和反对。言说者的认可倾向会因为句子的不同而变化,例如,当一只猫被提及指明时,我们既不是在指明一条鱼,又不是在指明什么对象都没有,那么,我们倾向于同意这样的句子“那是一只猫”(句子被认为是真的)。在这里,我们的同意倾向与指明的(对象)环境有关,而且,我们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总是要期待那些使用相同语言的人们能够作出相同的反应,要么认可,要么反对。于是,对于具有明确对象环境的句子而言,“那是一只猫”在言语行为者那里所引起的反应倾向应该具有“共同性”,一种符合言语行为者期待的“应该反应”,尽管这样的“应该”也许不会是全部的经验现实。基于相同的倾向和期待,言语行为者认可态度的变化就应该取决于指明的环境,而不是取决于言说这类句子的人。除了这些同环境相关的句子之外,另外的一些句子却具有不同的特征。比如句子“观世音菩萨存在”,显然,不同的言说者对于它的认可态度是不相同的,一些人的认可倾向是坚定的,而另一些人的反对倾向却是不容置疑的。这里的认同“倾向”不是建立在环境的变化上,而是建立在言说者的变化上,所以,句子“观世音菩萨存在”在言说者的“倾向”上缺失“共同性”的反应期待,进而产生关于这类句子认知的差异。此外,语言中还有一类句子值得我们关注,即一种在所有环境中都被所有言语者认同或反对的句子,如句子“1+1=2”和“1大于2”等,对于前者而言,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而对于后者,我们又会毫不犹豫地拒绝。由此,如果我们在言语行为里依据言语行为者自身提供的倾向态度可以对语言句子的类型特征进行认知,我们就能取得关于这种语言的句子知识。从上文的分析中,这样的句子知识或者涉及言语行为者的经验内容,或者涉及信念内容,或者涉及先验的内容。不论这样的知识是否具有了统一的标准,它肯定地成为了回答“语言是什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它也成为了我们由自己的母语走向其它语言理解的必然过程,一种“初始翻译”发生所不可或缺的过程。
蒯因的“初始翻译”在方法论上看就是将一种言说者所熟悉的语言知识(如关于句子的知识)应用于其它语言之上,就句子而言,我们可以将一种熟悉的句子与认可“倾向”之间的关系移植到其它语言的理解认可之中,从而达到对陌生语言的翻译。因此,从事“初始翻译”的语言学者进入一种对象语言的过程就是使用已知的标记去标示未知语言的过程,它既有观察过程的言语行为,又有这种行为中的语言注释或形式,还有关于对其进行对比和“熟悉化”的显现过程。一旦“熟悉化”的过程完成,陌生的语言或句子就被进行了“初始翻译”,我们也就取得了陌生语言的部分知识。具体而言,在做“初始翻译”时,语言翻译学者必须观察对象语言的个体句子所涉及的“赞同”和“反对”情形,然后,将这样的情形同自己语言中的情形进行对照。比如,在只是一只猫而非其它东西在场时,陌生语言的使用者认可了一个句子,观察到这一现象的翻译者就会暂时性地将这样情形同自己语言中的“那是一只猫”对应起来;在老鼠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时,如果一个句子在言说者那里引起赞同,那翻译者就会将它同自己语言中的句子“那是一只耗子”对应起来;同样,当一只猫嘴里叼着一条鱼从屋子里出来时,翻译者在对象语言里观察到出现有涉及两个对象语言句子的表达式,而且使用对象语言的言说者对之表现出认可赞同的倾向,翻译者会立即想到自己语言的句子“那是一只猫和一条鱼”,而且,翻译者会意识到句子之间的关系存在,这样的关系使得翻译者立即想到自己熟悉的语言中的“关系”表达形式。于是,如果对象语言中的所有句子在言说者的“倾向”反应方面都是可观察的,那这样的句子都是可以理解和翻译的。
当然,在蒯因的研究里,通过观察和对应来处理对象语言的句子及其表达的内容就是一个翻译工作者所必须涉及的过程。这种过程所聚焦的就是言说者对于句子的反应“倾向”,而这种“倾向”在任何语言的使用者那里都会必然地发生,并且还要基于人类相同的认知模式,包括语言的认知模式,即人们的反应“倾向”总要在经验“猫”、“鱼”等物质对象时表现出赞成或不赞成的态度,而关于经验对象的无“倾向”则不可接受,因为无“倾向”联系的陌生语言除了作为某种神秘的符号之外并不能成为一种可供翻译或理解的外语。根据蒯因关于“初始翻译”的想象构建,只要我们能够观察到陌生语言的句子在被使用时所联系的环境事实的存在,我们就可以认为这样的句子同这样的环境事实的语言表达形式具有某种等同性,即使我们还不能对于这样的句子进行读音、拼写、组合规律等方面的认知。确切而言,当我们在发现外语言说者使用某种语言形式(句子)来表达某种经验事实时,我们也会在这样的时刻使用我们自己语言的某个句子来表达它,那么,两种语言之间的句子对应与比较就一定要产生(即使这样的结果还不是关于翻译的完美状态)结果,如此结果无疑要成为翻译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样的结果进行持续不断的观察,在不同语言的句子对应情形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句子的组成成分会出现在另一些句子中,成为被反复使用的东西。倘若我们将这种含有共同句子成分的句子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发现这些具有共同成分句子的句法规律,我们就可以将这样的句子群同我们自己语言中的相似的句子群对应起来,不仅如此,通过这些句子在对象语言中的不同组合方式,我们可以预测不同组合方式可能引起的不同反应方式。只要我们在两个句子群的对应比较中熟悉了对象语言的组合方式,我们甚至可以利用对象语言的句子成分来设计、构建关于对象语言的句子了。对于这些构建的句子,我们当然赋予了自己的期待,期待对象语言的使用者能够具有相同的“赞成”或“反对”,一旦我们的期待在他们那里没有实现,那就意味着这些句子在我们这里的“倾向”未能取得他们的认同。要想克服两种语言的句子在表达“倾向”上存在的差异,我们就必须重新审视两种语言中的句子及其构成成分的对应情况,并根据对象语言的使用者所反应出的“倾向”实际重新就我们的“认同”过程进行修正。从理论上看,这样的“修正”过程在达到两种句子意义匹配的完全等同时就会终止,但在翻译的实际中,完全的匹配却是一种“应该”的状态,“修正”的完成会成为一种无限的过程。由此,关于“初始翻译”的结果就会呈现出一种相对性、有限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
从事“初始翻译”的语言学者会在“修正”的进程中全力地去找寻恰当的方法,以便让自己从对象语言的言说者那里获得期待的“倾向”,进而取得进行翻译的正确通道。在这里,寻找恰当的方法或通道的最为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观察和推理,即翻译者必须基于应验的过程来面对陌生语言句子的言说行为,通过观察言说者的句子使用情形而推算句子使用的可能变化,当然,这样的言说变化不能脱离生活经验的条件,不能脱离言说的对象世界的可认知条件。为了辨明并进入对象语言的句子系统,为了搜罗更多的关于那些言说者的“倾向”实际,翻译者还会跟随那些言说者去习得关于这种陌生语言句子的读音、组合和刺激反应模式等方面的知识,并通过这样的习得过程揭示产生“倾向”差异的原因。只有取得了“倾向”差异的产生原因,对象语言和母语之间对应和解说规则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翻译者关于对象语言句子的建构和理解才会真正地符合这种句子在使用时所拥有的“倾向”,一种属于对象语言的原生态的“倾向”。在不断的“观察”和“修正”过程中,翻译者的目标不仅仅是要达到自己同那些言说者具有一样的“倾向”,而且更是要确立这种过程的“翻译手册”,将对象语言的翻译方法理论化,使之成为可以反复使用、经验查证、精确而科学的语言交流工具。对此,蒯因持有“一种同质语言观,认为语言应该是一种整齐划一的系统,其中的语形和语义是严格确定的,不允许任何含糊和歧义”[9]34。如果这种“翻译手册”的建构是可行的,那它的内容或规则一定要涉及两种语言的句子以及句子结构成分之间的配对与等同。在形成“翻译手册”的过程中,翻译者就是通过这样的“配对与等同”来达到解读对象语言的目的和翻译方法的形成。凭借一种理想的“翻译手册”,任何作为我们母语中的句子都会有来自对象语言的句子与之匹配,而且是具备相同的外界刺激反应情形,那么,理想的“翻译手册”就具备了融合不同语言的地位,当然,这样的翻译手册及其功能还仅仅是一种理想。不论我们是在理想的层面还是在实际的层面探讨“翻译手册”,我们都要求这样的“手册”必须是基于(不同语言的)言说者的相同“倾向”而建构,两种语言句子的配对和等同源于一样的可观察的“赞同”或“反对”。作为刺激环境变化在一种语言中所引起的“倾向”的不断变化同样存在于另一种语言之中,唯有如此,两种语言句子的真正“配对和等同”才是可能的,作为翻译的过程才可能体现: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表达式E是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表达式E*的翻译,当且仅当E与E*是意义相同的(同义的)。
总之,不论是关于翻译理论的形成,还是关于言说者“倾向”的观察与认同,翻译者都要试图从翻译的视角来面对“语言是什么”的问题。翻译的视角在此将语言聚焦为一种主体的语言和一种对象的语言,从事翻译的人不只是在用自己的语言去解释另一种语言,也不只是在用自己熟悉的语言系统去标记并重新编排另一种陌生的符号系统(因为这样的过程只会避开问题在对象语言那里的展开情形),他们所作的翻译不能离开两种语言的使用行为、行为环境,以及言语行为变换和言语意象的相互匹配发生,即不能离开关于语言意义的探讨。于是,“语言是什么”的问题就可以转变为“语言意义是什么”的问题。语言的意义世界通过翻译所涉及的对象语言可以被重新置于一种原始的、陌生化的存在状态,即一种假设在面对对象语言并且又完全地忘掉了自己母语的状态,那么,我们对于对象语言的观察结果就只能是陌生的符号、陌生的言说、陌生的环境、陌生的联系等等。而且,不同层面的陌生符号形式联系于不同的陌生表达方式,以及陌生的言说者态度和刺激环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可了这样的语言具有自身的存在功能,如果能够将它的功能具体地被展示为语言行为的发生过程和表现形式的应用过程,我们其实就在具体内容上体会了这种语言的意义。当然,翻译者无需这样的假设前提来体验语言意义的重新产生过程,因为他们会凭借自己的母语经验而熟悉这样的过程,语言的意义形成于这样的过程之中。
三、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与翻译确定性基础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蒯因的“初始翻译”及其言说者的意义“倾向”验证所强调的是关于两种语言之间的对比与等同,而确立这种等同结果的关键就在于观察一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在被使用时具有怎样“赞成”或“反对”情形,而且,这样情形同样地要出现在翻译所涉及的另一种语言之中。在蒯因看来,正是这样的“赞成”或“反对”普遍地存在于不同语言的语言行为中,语言意义的同一性情形才会出现于不同语言的表达之中,翻译的可能性无疑来自于这样的“同一性”。尽管不同语言在不同语言行为者那里具有意义表达的“共同性”特征,尽管不同语言的意义认同可以通过语言行为者所具有的一致“倾向”来加以完成,但蒯因在论及不同语言的意义之共同性、相通性和可翻译性时并未对言说主体(即语言行为者)加以特别关注,也并未因意义“倾向”出自言语行为者“判定”而凸显人的主体性地位。翻译者在自身的翻译进程里始终要体现这样的主体性地位,它不仅要体现主体语言(如母语)到对象语言的配对过程,而且要体现在预见和推断不同“倾向”的过程中,并且具有对“倾向”观察的自我判断能力和朝向“同一”情形的自我修正能力。实质上,翻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在翻译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建立,体现在语言差异和言语行为差异中的持续不断的、对于人类共同的语言认知模式的信赖。这样的“确定性”和“信赖”源于人类揭示世界的共同性基础,尽管生活于不同时空、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们会因为他们的特定环境条件而各自具有自身的特征。如果说翻译者的主体性地位仅仅是在于形成翻译的“手册”、在于观察言说者的“倾向”与语言形式使用的相关性,以及比对主体语言与对象语言的匹配情形,那这样的主体性地位就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程序化的操作与执行,更多地体现为具有实验性的自然科学进程,这样的结果应该更加符合蒯因的翻译观和语言观。在蒯因看来,任何关于语言翻译及其语言意义的表达不能因为翻译者主体性地位的强调而与观念决定、内涵赋予等东西联系起来。“由于蒯因的自然主义态度,他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能够得到自然的解释。在各专门自然科学中,为了系统化和解释的目的,都不需要像内涵实体这样的东西,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理由仅仅为了对我们世界的一个微小部分即人类的语言作出适当的分析,就允许引入这样一些新实体。”[10]84-94一旦翻译者的主体性地位被加以蒯因似的限制,翻译中的任意性就是不可避免的,翻译中意义的同一性确定就会成为一种奢望,即翻译具有不确定性特征。于是,这样的主体性地位将翻译者的作用几乎全部外在化,展示为使用语言的行为、世界的直观和关于语言描述的“倾向”,从而将翻译者自身内在的原因淡化或搁置起来。对此,翻译者作为主体存在的所具备的特征在蒯因那里被展示为世界、语言和言语行为事实层面上的观察和发现,即出于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发现。就如蒯因对“gavagai”[11]32-35的分析一样,即使我们通过观察、假设和验证过程得出了这一词项的翻译为“兔子”,我们还是不能确立“gavagai”就一定指“兔子”,它还可能指兔子的未分离部分或兔子的某种状态等等。翻译表达“gavagai”的词项总会有很多。
于是,在蒯因的“不确定性”翻译里,翻译者作为世界、语言和言语行为决定者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凸显,不仅如此,翻译中所涉及的“共同性语言认知模式”和“共同性意义产生基础”更是不可能在蒯因的外延主义理论中得以建立。不论蒯因如何强调“翻译手册”的多样性和翻译的不确定性,在世界与多种语言的关系中,我们可以将它缩减设定为一个对象与多种符号间的关系,其对应的事实就是现象世界与描述她的不同语言形式的关系。处于这样的关系中,现象世界成为显现的和描述的对象,不同的语言存在既是描述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描述语言自身的工具,前者呈现“世界是什么”的图景,后者呈现“语言是什么”的图景,显然,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而这样的统一性不能归属任何一方的规定或强加,作为对象的世界和语言自身并非自发地决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规定性,两者之间的统一性与一致性表现只能是基于语言行为者的结果存在,尽管这样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对于具体的现实经验过程而言总会是有限的、不确定的。因此,要取得真正的统一性原因并确立翻译的确定性之路,外延主义的经验之路必须要加以重新的审视,即我们必须要回到翻译者作为主体性存在的地位上来,翻译者自身作为理性存在者的地位存在,“语言应该是理性的语言”[12]121-125。当然,世界也应该是理性的世界,它们都在遵循“人是万物的尺度”而非思维-语言-逻辑的尺度。因此,在蒯因的“初始翻译”里,我们可以接受他的“不确定性”观点,但这样的接受必须是基于有限时空条件下的接受,它所反映的是关于译者的有限性认知的现实。显然,不管对象语言中的“gavagai”在土著人的使用中具有什么样的本体论承诺,也不管译者在阐释的过程中关注了什么样的承诺,关于“gavagai”的承诺或意义相关项可以在现实的经验中是有限的,也可以在译者的等同性认可中是片面的和不确定的,但在现实世界的语义中,只要译者和言者认可了他们所共同拥有的认知模式和共同拥有的对象世界,关于“gavagai”的对象及其相关项确立就应该是可能确定的,即土著人使用的语言形式和意义指称的相关项在译者那里的再现和翻译都是可能的。语言形式表现的陌生并非语义世界的陌生,这种“陌生”因为译者的理性主体地位及其所具有的共同行为意志和认知模式而将最终被消解。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可以想象无限多的“gavagai”相关项,关于不同语言中的表现形式的相关项和关于对象世界的相关项,但不管我们怎么延伸这样的相关项世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一个信念:“gavagai”的无限既是土著人的,也是译者的,如果译者可以穷尽可能世界的语义,那土著人的语言表达在译者的那里就会是透明的,就不会呈现“初始翻译”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阐释,所有土著人使用的语言表达之意都会存在于译者的整体性知识世界之内。当然,这样的情形对于外延主义的经验展示而言只能是一种可能和一种理想,即便如此,这样的“可能”和“理想”也同样是属于土著人和译者的,作为语言行为者的言说行为尽管涉及了不同形式的语言表达,但作为语言形式产生的主体性意志与心理图式根据却一定要是相同的,它既是人类相互理解现实存在的必然前提,也是我们领会意义“倾向”和判定“不确定性”翻译特征的共同性标准。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这种“共同性标准”总要体现为具体翻译中的“是”与“不是”的过程,体现为“确定”与“不确定”的过程,而在译者作为理性存在的主体性地位里,这种“共同性标准”又要体现为一种翻译得以进行的纯粹意志条件。“主体常常在实现自己主体性的同时,伴随一种主体以自己的意志、意向、目的为轴心的心理倾向……。”[13]52-53倘若我们将理性主体的意志、意向视为世界与语言存在的统一基础,那这样的基础就一定是言者和翻译者作为理性主体所必然拥有的先验条件。只要立于这样的先验条件,认知世界及其语言的共同性条件也就拥有纯粹性源泉,一切关于翻译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便可以被看成翻译者作为有限理性存在的必然结果,翻译者的翻译就是承载了这种结果的不断经验过程,并不断地呈现为语言表现困境、意义遮蔽困境和两者联系统一困境。只要局限于现象的经验世界,翻译者的观察与发现始终要体现出有限性的特征。
总之,实践经验中的翻译是一个包含了“学”与“术”[14]、理解与表达的动态过程,而这个过程的主体就是翻译者,尽管这里的“主体”远非那种决定世界与语言存在意义的主体。在蒯因看来,“语言只是一种具有社会性的技艺。在学习语言当中,要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完全依赖主体之间可以利用的线索。因此,只有知道那些使人们作出明显反应、可见的社会刺激,我们才能检验语言的意义”[5]ix。显然,语言行为主义的意义观成为了蒯因翻译理论建构的基本观点,他所推崇的翻译“倾向”关注,以及言语行为中的“赞成”和“反对”情形无不与这样的观点相联系。翻译过程的语言行为决定了不同语言间的并置、比对和匹配发生,也决定了翻译手册的多样性产生,而且,语言行为的不同结果在经验的世界中都具有自身产生的有效性根据。因此,在我们将翻译或翻译者的工作视为语言经验中的人的有限行为时,其翻译成果并非具有恒定而永真的地位存在,除非翻译者作为主体性的存在已经超越了自身经验的有限性特征而绝对性地拥有了无限性存在的地位,即拥有了绝对完美的翻译能力存在。显然,蒯因不可能认同这样的完美翻译,他会认为这样完美翻译所依据的共同性“先验模式”完全离开了可观察的、可经验的和可认知的现实世界而变得神秘、不具备科学性。然而,不论翻译领域的外延主义如何通过经验现实来加以贯彻实现,那都只是关于认知结果的对象语言及其意义表达的重现,翻译或重现的过程只能是基于译者主体性地位存在的发生,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所决定的是关于外延主义的现象真实,但又不仅仅是关于外延主义世界的真实。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最终所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对于观察中“不确定性”的确定和判断中意义“倾向”的确定。我们没有理由漠视译者主体性地位的存在,一旦这样的主体性地位得以凸显,一种导致了翻译发生的主体性原因也就存在了,这样的原因就是翻译存在的理性根据。
[1] Quine.Indeterminacy of Translation Again[J].JournalofPhilosophy,1987,84 (1).
[2] 奎因.语词与对象[M]. 陈启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 Quine W..OntologicalRelativityandOtherEssay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4] Quine W..TheRootsofReference[M]. Chicago: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5] Quine W..WordandObject[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60.
[6] Whitney W. D..TheLifeandGrowthofLanguage:AnOutlineofLinguisticScience[M].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1875.
[7] Locke J..AnEssayConcerningHumanUnderstanding[M].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9.
[8] Kirk R..TranslationDetermined[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9] 陈波.蒯因的语言哲学 [J]. 北京社会科学,1996 (4).
[10] 陈波.蒯因的“两个教条”批判及其影响[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0 (3).
[11] 洪汉鼎,陈治国. 知识论读本[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12] 肖福平. 理性主体的地位特征与语言存在形式的确立[J].广西社会科学, 2011(10).
[13]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14] 龚小萍,陈达. 关于实现翻译教学中“学”与“术”有机统一的思考[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
[责任编辑 肖 晗]
Quine’s “Radical Translation” and “Meaning Inclination”
XIAO Fu-ping
(SchoolofForeignLanguagesandCultures,Xihua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39,China)
The problem of Quine’s radical translation and its uncertainty represents the relative characteristics in achieving ideal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ing of this relative characteristics involves functioning of the translator and translator’s own language, it also involves observ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object language. In the case of the radical translation, the understanding and translation of object language of a translator must be based on the stimulus response pattern in language behavior process, and only relying on the repeated 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words and the specific context, can the translator enter the meaning world of language. In Quine’s view, the radical translation is not the full sense of th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is always in reality and the possible world pursuing “the sameness” betwee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speaker, it is always difficult to pursue “the sameness” in the requirement of extensionalism, unless we go back to the analysis of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 and the speaker. No matter how to embody the “uncertainty” of radical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and the speaker may always provide universal basic for language behavior from their subjective position, as the pure language basis of rational existence, the translation’s “uncertainty” is the process and procedure to “certainty”, and the language behavior of human society manifestation observes the common transcendental regulation and cognitive model.
translation; language; inclination; uncertainty
2015-06-25
肖福平(1962—),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语言哲学的研究。
H315.9
A
1672-8505(2015)06-007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