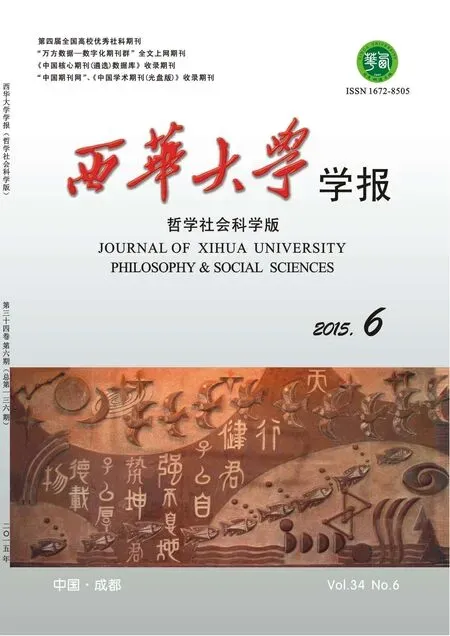《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句新解
亓 晴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文学研究·
《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句新解
亓 晴
(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对《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句的解读历来众说纷纭,至今未有定论。文章综合分析各家观点,适当取舍,并结合殷商甲骨文等史学、文字学研究成果,认为“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指的是启急切希望自己将来能升天宾于天帝,于是以表演《九辩》《九歌》这样的乐舞来彰显自己功德,祭祀取悦上帝。
《天问》;启;棘;宾帝;九辩;九歌;祭祀;娱乐
屈原一篇《天问》,博大精深、古奥难懂,给后世研究者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句之解便至今仍是众说纷纭、未有定论。笔者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于“宾”,以及“九辩九歌”等关键字词的解释还有待完善,本文希望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能够推陈出新,尽力试为之解。
一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句最为难解之处在于“棘”、“宾”、“商”等关键字词。历代学者对这些关键字词解释各异,争论不休,但前人观点也不乏真知灼见。
前代注家首重王逸、洪兴祖、朱熹,其后诸家多是在此三家基础上,或有所承继,或有所突破。王逸曰:
棘,陈也。宾,列也。《九辩》、《九歌》,启所作乐也。言启能修明禹业,陈列宫商之音,备其礼乐也。[1]98-99
洪兴祖曰:
《史记》: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兴于唐、虞、大禹之际。此言宾商者,疑谓待商以宾客之礼。棘,急也,言急于宾商也。《九辩》、《九歌》,享宾之乐也。[1]99
朱熹曰:
窃疑棘当作梦,商当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误也。盖其意本谓启梦上宾于天,而得帝乐以归。[2]189
观此三家之言,可总结如下:王逸认为“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启修明禹业,陈列宫商之音”,洪兴祖认为是“启急于以《九辩》《九歌》礼待契商”,朱熹认为是“启梦见到天上作客而得到天帝之乐”。
关于王逸的说法,后世继承者较少,贺宽曰:“启亟于敷陈大禹之业,《九辩》《九歌》之乐,灿然明备。”另有林云铭曰:“启缵禹绪,急于陈列商度禹功,以为《九辩》《九歌》之乐。”[3]204-205然而,贺、林二人只是取王逸“启修明禹业”之意,对具体字词的解释又各有见解,如林云铭曰:“棘,急;宾,列;商,度也”。
关于洪兴祖“启急于以《九辩》《九歌》礼待契商”的说法,后世注家多有取其“以《九辩》《九歌》礼待(宾客)”之意者,只是各家对于“礼待”的对象,也即“商”之所指与洪氏见解不同。徐文靖曰:“经言启上三宾于天者,启以黄帝尧舜之后为三宾,上告于天而飨之;其所奏《九辩》《九歌》,则于禹宾商均而得之,……今以理度之,宾为虞宾,商为商均,正有无烦改字者。”刘梦鹏曰:“宾谓以客礼之而不臣。商,商均。”曹耀湘曰:“商,谓舜之子商均也。宾商者,商均作宾于夏,犹丹朱为虞宾也。”[3]205-210沈祖绵曰:“予谓启之所急,在以商均作宾。”[4]67诸人皆以“商”为舜子商均,以“宾商”为“以宾客之礼对待商均”,此见不同于洪兴祖以“商”为“契商”。
朱熹认为“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启梦见到天上作客而得到天帝之乐”,汪瑗、蒋骥等径从朱说。聂石樵:“启梦中在天帝那里做客,取得《九辩》《九歌》两支乐曲回来。”[5]65姜亮夫:“盖其意本谓启梦上宾于天而得帝乐以归……”[6]302-303皆持此见。但是,更多注者虽然认为“商”指“天帝”,也认为《九辩》《九歌》是启从天帝那里得到的乐曲,却不认同朱熹将“棘”解为“梦”的观点。王闿运曰:“棘,戟也。商,盖帝之误,启列戟傧于上帝……得《九辩》《九歌》之乐于帝。”[3]210林庚曰:“夏后启带着戟到天上作客,如何便取得了《九辩》《九歌》以国于下”[7]35。此外更多注家将“棘”解为“急”或“亟”,其中有人认为“启棘宾商”是启急于上天作客,如褚斌杰:“启急急忙忙去天帝那里作客,窃得《九辩》、《九歌》两部天乐供自己享受。”[8]249另外一些注家虽然也将“棘”解为“急”或“亟”,但却根据郭璞对《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夏后开(启)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两句所作的注“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来解释“启棘宾商”。如陈子展:“夏后启赶忙上献三美人给上帝,得到了天上的音乐《九辩》和《九歌》。”[9]135然而,郝懿行早对郭注有所驳斥:“《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宾嫔古字通,棘与亟同。盖谓启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故《归藏·郑母经》云:‘夏后启筮御飞龙于天,吉。’正谓此事。《周书·王子晋》篇云:‘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亦其证也。郭注大误。”[3]208-209郝氏认为“宾”“嫔”古字通,所以“上三嫔于天”应该是“上三宾于天”,此说以“嫔”为“宾”,并取其“作客”之意。游国恩《天问纂义》对于各家说法进行了综合,并取“启急欲宾于天帝”与“启上三嫔于天”之意,又有“三度宾天或嫔天”之说,并无确论。[3]211
总结以上所列关于“启棘宾商,九辩九歌”的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一、启急于陈列彰显禹的功业,《九辩》《九歌》是彰显德业的乐曲(王逸、贺宽、林云铭等持此见);二、启急于以《九辩》《九歌》为礼乐来礼待宾客商(契商或商均)(洪兴祖、徐文靖、刘梦鹏、曹耀湘等人持此见);三、启梦见到天帝那里作客,得到了天乐《九辩》《九歌》(朱熹、蒋骥、聂石樵、姜亮夫等持此见);四、启列戟(持戟)上天作客,得到天乐《九辩》《九歌》(王闿运、林庚等持此见);五、启三次到天帝那里作客,得到天乐《九辩》《九歌》(郝懿行等持此见);六、启献给天帝三个美女,得到了天乐《九辩》《九歌》(陈子展等持此见);七、启急于到天帝那里作客,以得到天乐《九辩》《九歌》(褚斌杰等持此见)。此七种观点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此外,近来也出现了一些超出传统观点范畴的创新之见。如吉家林的《<天问>“启棘宾商”新解》就认为“棘”是“棘乐”,“宾”是“宾祭”,“商”为“帝”,是“女祖”,特指“启母涂山女”,而“综合新解‘棘宾商(帝)’的联贯之意为‘用棘乐宾祭女祖’”[10]。众说纷纭中,到底哪些说法是正确的呢?接下来,我们就对这些观点加以分析比较,以进行合理取舍。
二
上文所列几种观点中,王逸以“棘宾商”为“陈列宫商之曲”,对于“棘,陈也”“宾,列也”之解释并无确据,而将“陈列宫商之曲”引申为“陈列彰显禹的功业”虽是由《九辩》《九歌》而来,但就上下文看,即使是彰显也当是启之功业而不会是禹之功业。贺宽、林云铭更于“陈列”前加一“急”字,若“棘”为“陈”,则“急”意无从得来,若以“棘”为“急”,则只能将“陈列”之意归于“宾”,而这又是无据之说。总之,以“棘宾商”为“陈列宫商之曲”之说不足取。至于《九辩》《九歌》是否是彰显德业的乐曲,则可留待后考。对于“启急于以《九辩》《九歌》为礼乐来礼待宾客商(契商或商均)”,单从字面理解可以讲通,但将“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放诸《天问》原文,则觉此说太过突兀。“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之前是“启代益作后,卒然离蠥……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这几句讲的是启与益争夺权位的事情,并未涉及上代恩怨,而商均是舜之子,即使要礼待也当是继承了舜位的禹来做,为何启会在自己即位之后急着去礼待商均?而且下文“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之问也与礼待商均没有关系。故所谓礼待之说乃是完全就字面生解,并不足取。

至于王闿运、林庚等持的“启列戟(持戟)上天作客,得到天乐《九辩》《九歌》”的观点,最主要的问题就在于“棘”能否解为“戟”。林庚《天问论笺》曰:“棘:戟。《礼记·明堂位》:‘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越乃夏之后裔。说明戟(棘)可能乃是夏民族所首创的。”[7]34按,无论越棘是否是越国之戟,都是“天子之戎器”,戎器,武备也,启上天宾帝,岂能带戎器去耀武扬威?故此说不能通。
那么“启三次到天帝那里作客”的说法又如何呢?以前文所引郝懿行的说法为例来看,郝懿行说:“《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宾嫔古字通,棘与亟同。盖谓启三度宾于天帝,而得九奏之乐也。故《归藏·郑母经》云:‘夏后启筮御飞龙于天,吉。’正谓此事。《周书·王子晋》篇云:‘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亦其证也。”[3]208-209按郝氏之说,“棘”通“亟”,而此“亟”被解释为“三度”。《左传·成公十六年》:“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杜预注:“亟,数也。亟,去吏反。”[11]1918《汉书·刑法志》:“师旅亟动,百姓罷敝。”颜师古注:“亟,屡也,音丘吏反。”[12]1084-1085“亟”之“数”“屡”之意当是郝氏将“亟”解为“三度”的根据。然而,“亟”为“数”“屡”之意时为“去吏反”或“丘吏反”。《诗·豳风·七月》“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笺》曰:“亟,急。”《疏》曰:“亟,纪力反。”[13]505可见,亟音“纪力反”时意为“急”。“棘”据段注《说文解字》为“己力切”,与“纪力反”之“亟”音同,故两字可同音假借。《诗经·小雅·出车》“王事多难,维其棘矣”,《笺》曰:“棘,急也。”[13]597亦为一证。由此可知,“棘”通“亟”时意为“急”而非“数”“屡”,故而不能解释为“三度”。郝懿行引《周书·王子晋》(按,即《逸周书·太子晋》)“吾后三年上宾于帝所”作为“启三度宾于天帝”的旁证,然而除提供了“三”这样一个数字,《周书·王子晋》并不能提供其它有力证据,而且这“三”是“三年”,能否作“三次”讲也难确定。故而,“启三次到天帝那里作客”的说法并不足取。至于“启献给天帝三个美女,得到了天乐《九辩》《九歌》”的说法,主要依据是《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九歌》以下”以及郭注:“嫔,妇也。言献美女于天帝。”郭说之非,前文已述,《山经》之说亦不得为解释《天问》之确据,况上文已说,“棘”于此并无“数”“屡”之意,“三个美女”之数实在无从谈起。所以,“启献给天帝三个美女,得到了天乐《九辩》《九歌》”的说法也是于理无据的。
以上观点之外,今人也颇有新说,如吉家林:“‘棘’为‘棘乐’,是几种打击乐器和丝弦乐器的合奏乐;‘棘乐’原系上古作战时所用的一种‘武象乐’,但自虞舜时起就已转化为宗庙祭祀‘韶乐’中的‘堂上乐’了,故夏启时仍用‘棘乐’为‘宗庙祭祀乐’。”他承袭其曾祖吉城的观点,认为《尚书》中的“戛击鸣球”即“棘击鸣球”,且“戛”和“棘”都通“戟”,“故作音乐名词而用的‘戛’和‘棘’都源自古代兵器戟,这也说明了‘棘乐’原为‘武象乐’”[10]。然而笔者对此有不同见解,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句注:“马融曰:‘戛,栎也。’郑康成曰:‘戛,栎也。戛击鸣球三者,皆总下乐,栎击此四器也。’”[14]122-123“栎”有“打击,搏击”之意。《文选·潘岳〈射雉赋〉》:“栎雌妬异,倏来忽往。”徐爰注:“栎,击搏也。闻他雄鸣,击搏其雌。”[15]419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中“戛击鸣球”“搏拊琴瑟”当都是动宾结构,“戛击”“搏拊”应当皆是动词。由此看来,以“戛”为“棘”,并以“棘”为“棘乐”的说法并没有足够证据。吉家林先生还认为“‘启’句中的‘商(帝)’字应释为‘女祖’,特指‘启母涂山女’”,又说:“关于‘帝’的原始初义……许多学者认为‘帝’的初义为女阴。尽管此说不被学术界普遍接受,但‘帝’具有生殖或化生万物之义,则是很少有异议的。”[10]“帝”或许确实与万物化生有关,也可能与原始生殖崇拜有关,但并不能以此证明“帝”是女性,更不能证明此“帝”特指“启母涂山女”。《诗·大雅·生民》讲到周族始祖后稷出生时说:“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后稷母亲姜嫄履上帝足迹而生后稷,此说当然是神化周族,但也由此可见,帝是作为父存在的,并不为女性。周之始祖与夏之始祖几乎兴起于同时①,周部族之传说很可能是世代相传的,大约可以反映部族初生时的信仰情况,所以也大约可以反映夏初的信仰情况。总之,就目前所有资料情况看,将“商(帝)”释为“女祖”且特指“启母涂山女”的证据并不充足。故,吉家林先生之说也不足取。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大多数注家对“棘”的解释是“急”,对“宾商”的解释是“上天作宾于帝”。那么“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是否为“启急于到天帝那里作客,以得到天乐《九辩》《九歌》”呢?启急于宾帝,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得到天乐《九辩》《九歌》?或许,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对“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加以解读。
三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棘”,游国恩《天问纂义》:“盖棘者,《诗·素冠》‘棘人乐乐兮’,《毛传》云,棘,急也。又《采薇》‘玁狁孔棘’,《出车》‘维其棘矣’,《郑笺》并同。”[3]211以此看,“棘”训“急”有据可循。以“商”为“帝”之讹字,说者众多,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曰:“‘商’为帝之误字。《天问》启棘宾商,按当作帝,天也。”[16]但是朱说只是大略,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证:“朱骏声、王闿运谓‘商’当作‘帝’,甚确。游同志(按,国恩)谓‘商’或为‘帝’、或为‘高’、或借为‘上’,令人无所适从。‘帝’之讹为‘商’者,金文晚期‘帝’字也作‘啻’(见陈侯因资敦)。‘啻’及从‘啻’之字隶书多写作‘啇’,因字形近故易讹。”又说:
如果认为这一说明还有不够,那末,请验之以契文。今择录《殷虚文字丙编》图版叁陆·三段于下:


于省吾以甲骨卜辞中关于“宾帝”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启棘宾商”为“启棘宾帝”。同时,于省吾认为:“卜辞贞问的先臣、先王之宾帝与否,都就已死者言之,而启之宾天,得《九辩》与《九歌》,则就生时言之。”考其意,是启活着时就宾于天帝,得到《九辩》与《九歌》。于氏将“宾”解为“宾主之宾”,并用作动词,而对于“宾于上帝”又将“宾”解作“宾相或宾辅”,这与启上天作天帝之宾客从而得到《九辩》与《九歌》意义似乎有所不同。虽然仍旧不能明确“启棘宾商”所指,但于省吾之说却表明“宾”并不能想当然地解为“作客”,而且于省吾也为我们开拓了一条到甲骨卜辞中寻求“宾”字确解的道路。
刘桓《甲骨集史》中有一篇文章《殷墟卜辞“大宾”之祭及“乍邑”、“宅邑”问题》,文中解释了殷墟卜辞中的“大宾”之祭。文曰:
在殷墟卜辞中,有一片记有大宾之祭的武丁卜辞十分引人注意。其中有:
癸丑卜,争,贞:我宅兹邑,大宾,帝若。
癸丑卜,争,贞:帝弗若。(《合集》14206正)
所谓“大宾”,应指大型的“宾”祭……自夏代以来,人们对于至高无上的上帝神的信奉所形成的神秘观念是,只有统治者死后可以升天,因而能宾于上帝之所,在上帝之左右。……殷人认为商先王死后可以升天,宾于上帝左右,因此当商王举行“大宾”之祭时,往往要反复贞问数位先王能否宾于上帝,希望祭祀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宾”祭的目的是要祭祀上帝,借以求得保佑,维护统治秩序,使得心想事成。……“宾”祭实际上是祭天的重要环节。[18]1-2
刘桓此说有一点与于省吾相合,即“只有统治者死后可以升天,因而能宾于上帝之所,在上帝之左右”,两人都认同“宾帝”是死后伴随在天帝左右,不同在于,刘桓认为殷商时期存在一种“宾祭”,这是与祖先有关系的重要祭祀活动,是祭天的重要环节。那么,“宾祭”与“启棘宾商”是否有关系呢?笔者认为,存在这种可能性。
虽然殷墟卜辞中的“宾”祭是殷商时期的事情,但是对“上帝”的崇拜却是自远古时期就有,认为自己的先人死后上宾于天并且希望自己死后能够上宾于天是各先公先王的共同认识。甲骨文之前没有明确文字记载,我们难以确切知道夏代及以前的事情,但前已列过殷商甲骨文中关于先王宾于帝的占卜文字。此外,《尚书·召诰》:“兹殷多先哲王在天。”《诗·大雅·文王》:“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大雅·下武》:“三后在天,王配于京。”这些都说明“宾于帝”这种观念当是在商、周两代一直延续的。直接文字记载之外,也还有许多流传下来的传说,比如轩辕黄帝即乘龙升天。可见,上古时期,“乘龙飞天”“上宾于帝”是比较普遍的观念。同时由以上所述也可看出,并非所有去世的君主都可以上宾于天,只有具备大功德者才可配宾于天。至此,我们还可以明确一点:所有关于“宾天”的甲骨卜辞或者诗文作品提到“宾天”时都是就死人而言的,也就是只有死人才有可能“宾天”。由此可以推断,所谓“乘龙飞天”当是对“死”的委婉说法,后代帝王去世便通用“龙御上宾”或“殡天(宾天)”的说法。此说也进一步证明“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不能解为“启三次到上帝那里作客,得到天帝之乐而归”之类。商、周两代都有较为明确的“上宾于帝”的观念,而《归藏·郑母经》曰:“夏后启筮御飞龙于天,吉。”可见占卜祖先是否“宾”于上帝,或者占卜自己能否“宾”于上帝是夏代君主也会做的。《归藏》相传是《周易》之前的古易,此说虽然还有争议,但《归藏》是战国之前的古书则基本可以确定。这样,先秦著作中有关启“宾天”的记载就有了三个版本:《归藏·郑母经》:“夏后启筮御飞龙于天,吉”;《山海经·大荒西经》:“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三者之中,《山海经》创作时间尚有争议,近代以来的学者一般认为《山海经》中的《山经》与《海经》是战国时作品,而《海内经》和《大荒经》则为西汉初年作品。无论此说正确与否,可以肯定的是《山海经》成书时间与屈原创作《天问》的时间前后不会相差太多。而《归藏》则基本可以确定比《山海经》和《天问》都要早。因而,《山海经》与《天问》同受《归藏》相关记载影响的可能性较大。《归藏》既然说“夏后启筮御飞龙于天,吉”,那么就说明启希望知道自己是否德配于天,能否乘龙飞天以“宾于帝”,并为此而筮,占卜的结果又是“吉”,后世因此有“启上宾于天”的说法也属正常。既有《归藏》之说,“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与“宾”祭或是卜筮有关系就可以说是有根据的。如此,“启棘宾商”就可以这样理解:启强烈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上天宾于上帝左右。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启可能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制定礼乐、占卜、祭祀上帝等,以达到彰显功德、取悦上帝的目的。笔者认为启用来彰显功德并祭祀上帝的乐曲就是《九辩》《九歌》。

《九辩》《九歌》既非天乐,那么其制定或许与后代开国之后的制礼作乐一样,目的是既要娱乐又要彰显功德,如虞舜之《韶》、周之《武》、唐之《功成庆善乐》《秦王破阵乐》之类。那么该如何解决“九辩九歌”无动词之疑呢?笔者以为,《九辩》《九歌》作为乐曲之名是名词,但若将之理解为名动用法,也无不可,毕竟名词用作动词在古代文献中是极为常见的。这样“《九辩》《九歌》”就可以理解为“演奏(表演)《九辩》《九歌》”。而“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就可以解释为“启急切希望自己将来能够上天宾于上帝左右,因此表演《九辩》《九歌》这样的乐曲来祭祀上帝”。同样,《离骚》之“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也可以如此理解:启演奏《九辩》与《九歌》,开了夏代享乐自纵的风气。演奏《九辩》与《九歌》既可以祭祀天帝,达到娱神的目的,也可以自己享乐。上古时期,娱神与娱人在有些时候并不矛盾。同时,启既然希望自己能德配于天,那么祭祀上帝时表演《九辩》《九歌》这样的乐舞本身就是彰显自己功德的行为,也可以达到取悦上帝的目的。
“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两句试解如上所述,然而对此两句之解读在联系“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两句之后还能否成立?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历代对“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两句的解读亦是众说纷纭,综合分析各家观点,我们暂取袁珂先生之说:“启……为何却去殷勤其子,屠剥其母,以至死后五子内讧、而使境地为之分崩。”[19]如此,“启棘宾商,九辩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乃是感慨:“启既然急切希望自己德可配天能上宾于帝,并以《九辩》《九歌》的乐舞来彰显功德,取悦上帝,又怎么会有殷勤其子,屠剥其母,并导致死后五子内讧,国家境地分裂的事呢?”马其昶曰:“此再申言启德之不终,虽有生时瑞异,而身殁祸作,盖思忧则能达,荒乐则鲜终。《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不顾难以图后。正是此谓。”[3]210此言可谓得之。此外,《离骚》“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衖”几句谓启德不能终,放纵享乐,导致五子内讧、国家分裂,亦可为一证。总之,“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几句意在感慨启功德圆满之愿望与身殁祸作之现实间的差距,而这也正符合屈原以史为鉴之意旨。
所以,无论是结合“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还是联系《离骚》相关诗句,《天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句解为“启急切希望自己将来能升天以宾于天帝,于是演奏《九辩》《九歌》来彰显自己的功德,祭祀取悦上帝”是可通的。
注释:
① 《史记·夏本纪》曰:“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9页)《史记·殷本纪》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于唐、虞、大禹之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页)《史记·周本纪》曰:“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嫄。姜嫄为帝喾元妃。……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1—112页)《史记·五帝本纪》曰:“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于颛顼为族子。”(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页)契、稷二人之生虽有吞卵履迹之传说,然而两人事实上当为同父异母兄弟。总之,依太史公所考,夏商周三代始祖为同族同宗,且几乎兴起于同期。本文暂取此说。
[1] 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 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 游国恩.天问纂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 沈祖绵.屈原赋证辨[M].北京:中华书局,1960.
[5] 聂石樵.楚辞新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6] 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7] 林庚.天问论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8] 褚斌杰.楚辞要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9] 陈子展.楚辞直解[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10] 吉家林.《天问》“启棘宾商”新解[J].盐城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11]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
[12]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3] 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14] 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5] 萧统.文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清光绪八年(1882)临啸阁刻本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
[17] 于省吾.泽螺居楚辞新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8] 刘桓.甲骨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 袁珂.《楚辞与神话》读后——兼论《天问》“启棘宾商”四语的正诂[J].思想战线,1988(6).
[责任编辑 李秀燕]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Sentence “Qi Ji Bin Shang, Jiubian Jiuge” inTianwen
QI Qing
(TheResearchCenterofChinesePoetry,CapitalNormalUniversity,Beijing, 100089,China)
As interpretations of the sentence “Qi ji bin shang ,Jiubian Jiuge” inTianwenvary,no unanimous conclusion has been reached so far. Having analyzed the interpretations comprehensively so as to examine and select appropriately, the thesis, and referred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historiography and philology of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in Shang Dynasty, comes to a conclusion that the meaning of the sentence is: Qi, the king in Xia Dynasty, put on the song-and-dance performance, Jiubian and Jiuge, to show his feats to please the God, because he desperately wanted to be an immortal.
Tianwen; qi; ji; beside the God; Jiubian; Jiuge; offer sacrifice; amusement
2015-07-13
亓晴(1989—),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歌研究。
I207.223
A
1672-8505(2015)06-00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