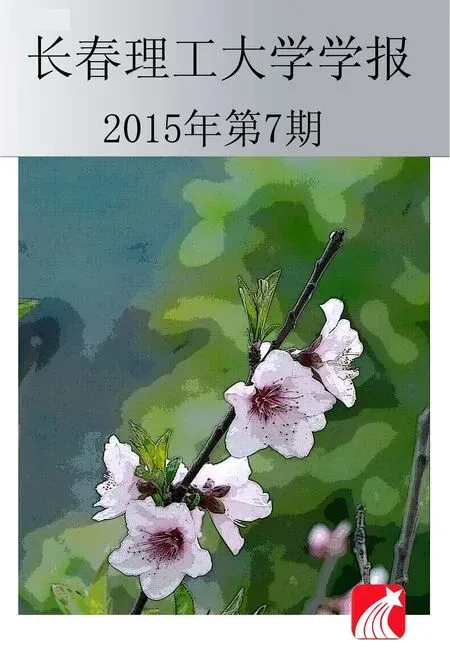论鲁迅的时间表达及其文化含蕴——从《阿Q正传》说开去
和 磊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济南,250014)
吉列维奇在《时间:文化史的一个课题》一文的开篇写道:“时间的表象是社会意识的基本组成部分,它的结构反映出标志社会和文化的韵律和节奏。时间的感觉和知觉方式揭示了社会以及组成社会的阶级、群体和个人的许多根本趋向。”[1]313这就明确指出了时间对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杨义在《中国叙事学·时间篇》中也指出,时间的表述形态实则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密码。那么,对中国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时间表述形态?而这样的时间表述,又蕴涵着中国怎样的文化密码?我们通过对《阿Q正传》的时间分析,也许能了解到一点。
一、阿Q的时间意识
阿Q初一登场所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什么东西!”而他临终前说的最后一句话(如果不算他喊的那句“救命,……”的话)是:“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前一句话指向的是过去,后一句话则指向未来,但这过去与未来对阿Q来说,都是虚无的:过去他并不阔,而未来也注定不可能是一条好汉。或者说,阿Q根本就没有值得骄傲的过去,也绝不可能有什么理想的未来。那么,没有过去与未来的阿Q,又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现在”呢?在鲁迅的笔下,阿Q的“现在”的确不值得炫耀,无论是他的生计、恋爱还是革命,都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也就是说,阿Q的“现在”是一个不断被否定的“现在”。这样,既没有过去,也不可能有未来,又被否定了现在的阿Q,便注定只能成为一个时间的“多余者”,而“被遗弃”也就成了他必然的结局。
在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了阿Q的时间意识:在现在被否定中,把时间极力地向过去和未来延伸,而现在愈被否定,过去与未来就会被延伸得愈远愈美。这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起到了心理平衡的作用,消解了因现实被否定而带来的失落感。但这又显然是阿Q精神胜利法的一种体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几千年的苦难现实使得处于现实存在中的我们都不愿意去正视它,不愿意停留在它上面,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去否定它、规避它,如此,把时间向前或向后延伸便成了一种可以聊以自慰的方式。因为人人都可以借着过去与未来的不可知性而任意地去虚构它,从而尽可能地遮蔽现在。
二、鲁迅的时间表达
鲁迅在《阿Q正传》中的时间表述,经过了一个由疏到密的过程。除去第一章序,第二章“优胜记略”及第三章“续优胜记略”前半部分,几乎是无时间性标志的,这也可以说是永远的“现在时”的时间表达,叙述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从第二章中部开始,鲁迅用“有一年的春天”引入较具体的时间,依次叙述了阿Q所遭受的一次一次的“屈辱”:先是春天的“恋爱的悲剧”,接下去是夏天的生计困境,然后是秋天的末路及革命的失败,而其被杀则大约是在冬季。在最后一章“大团圆”中,鲁迅的时间表达趋向紧密:正午——下半天——第二天的上午——这一夜——明天的上午。
那么,鲁迅的这种时间表达有什么寓意呢?首先,永远的现在时的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消了行为的时间意义,或者说,人物的行动并不具有特别强的时间意义,而这也就使得所叙述的事件普遍化。鲁迅用这种时态叙述阿Q的精神胜利法,显然有这种目的。其次,鲁迅用从春到冬的季节顺序来叙述阿Q的悲剧一生,如果用弗莱的四季叙述结构理论,我们会发现其中所蕴涵的讽刺效果。弗莱的四季所对应的叙述类型依次为:春天的喜剧(或传奇),夏天的浪漫,秋天的悲剧,冬天的反讽或讽刺。对阿Q来说,他春天的恋爱似乎可以看作他的传奇或喜剧,但其悲剧性的结局,却与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讽刺:阿Q是不配有爱情的。夏天的浪漫对阿Q来说是偷窃与由此带来的中兴,这显然是可笑的。而秋天阿Q革命的失败,则在本应严肃中,被阿Q的想法撕得支离破碎。在这一季节里,鲁迅似乎有些异乎寻常地用了一个具体的时间:“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其用意显然是要人们记住“革命”这一具有极其严肃性的时间,但结局的可笑却与之形成了强烈的反讽,从而消解了这一具体时间的意义与价值。阿Q的冬天是死亡,但这死亡所带来的反讽却是全面的:人就这样在无知无智中糊里糊涂地被取消了生存权,这是社会的悲剧,还是个人的悲剧?也许兼而有之吧。
也是在这一章中,鲁迅又用近乎琐碎的时间,详细记录下了阿Q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刑场的,这里面显然渗透着鲁迅对阿Q之死的深切关注,但阿Q死的可笑,却使这一时间记录变得毫无意义。正如冯铁先生所说的:“时间的单位变得越来越小,具有象征的意味,它会走向对时间的超越,当鲁迅写下‘七月二十九,或三十,随便’时,有意义的时间变得没有了意义。或者说对时间相当在意的鲁迅,突然宣布对时间漠不关心了。”[2]而之所以如此,正在于所有的时间记录都因所记录的事件的荒唐可笑而失去了意义。鲁迅的沉痛于此可见一斑。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对时间的运用与表达是有其深刻含义的。鲁迅其实一直都很关注时间的表达,并以此去关注时间旅行中的国民的生存状态。鲁迅曾说过,《彷徨》比《呐喊》的技巧要圆熟一些。如果从时间的运用与表达上来分析的话,我们也许能发现这种圆熟的一个方面。在此只以《在酒楼上》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在这部小说中,吕纬甫所讲的那两个故事,具有一定的隐喻作用。为弟弟迁坟,可除了弟弟的点滴遗留物外,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显示了过去的无从拾起。或者说,当现实把过去埋葬并使之腐烂后,即使扒开现实,也无法再寻觅到那早已失去了的曾经美好的过去。而给顺姑买花的故事,则显示了对美好过去的失落感。过去再美好,到现在也只能是一声无奈的叹息。如果说过去已找不到了,那么现在呢?在小说中,我们能分明感受到吕纬甫那种在现实中的“生疏”感。而对于未来,吕纬甫说:“以后?——我不知道。”这样,过去找不到了,现在生疏了,将来又不可知,最终只剩下了一个孤单单的根本无法支撑起来的“现在”。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似乎有意识地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流程中思考人的处境。
总之,时间是我们理解鲁迅笔下人物的一个重要视角,尤其是人物的“非现在性”的存在方式,对于我们理解国人的生存状态具有重要意义。鲁迅笔下的人物,如阿Q的无时间意义的存在与鲁迅的清醒的时间表达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透露出鲁迅内心的沉重、痛苦乃至无奈。
三、时间中的文化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鲁迅所揭示出的中国人的这种时间意识或存在状态呢?帕塔罗在《基督教的时间观》中指出,基督教的礼拜仪式实际上是一种“仪式时间”,它通过回忆以复活过去,从而使自己与基督的时间联系起来。[1]251对我们来说,儒家所规定的一系列的繁文缛节其实也具有这种“仪式时间”的性质,即儒家通过这些仪式以复活过去,复活礼崩乐坏以前的礼仪,从而归正现在。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在似乎并不重要,并不是被看作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是一个不断被过去归正的时间。这也许正显示了儒家向后看的保守的一面。孔子的名言:“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所体现出的时间观念,我想并不是,至少并不完全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线形时间观,更多的应是指向过去,是对过去一去不复返的感叹。
对于未来,儒家通过反省,而道家、禅宗则通过顿悟来实现。两者实际上是相通的,即都通过对现在的超越或否定以趋向无时间性的无限,或者说从俗性时间中解脱出来,走进无限的圣性时间。儒家的“立功、立德、立言”与道家的成“圣”、成“真”实则都是这种追求时间无限化的体现。这对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显得尤为重要而普遍。王孝廉在对中国神话时间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古代人的时间信仰,“是借着通过死亡以及原来形体的解消而结束一个俗性时间(现实时间),然后经过变形而回归到原始永恒的圣性时间(神话时间)里去,在神话的主题上,死亡与再生所代表的,正是这种由俗到圣所必经的‘通过仪礼’(Rites of Passage)。”[3]
这在中国的艺术中也体现的非常明显。中国艺术具有“时间率领空间”,空间时间化的倾向[4],而这种时间化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时间,也就是与“道”相合。因为“道”从时间上讲,是一个无时间性的概念,也可以说是全时间性的概念。我们所推崇的王维的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正包含了这一特质:“水穷”是一个现实的空间,而“云起”则把这空间的“水穷”引向了无时间性的时间,并在这种引向中与“道”合在了一起。禅宗所追寻的三个人生境界:“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则在一种回归中实现了与“道”的相合。
在这里,我们当然不能否定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的独有的价值与地位,但我们也应当从中看到,过分追求道的无限性,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现在”的关注,这与西方艺术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指出:“希腊人知道并且感受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为了能够活下去,他们必须在它前面安排奥林匹斯众神的光辉梦境之诞生。”这样,奥林匹斯神的世界便成了希腊人和生存的恐惧之间的一个“艺术中间世界”,从而“不断地重新加以克服,至少加以掩盖,从眼前移开了”那生存的恐惧,这也就保护我们不受自然界巨大毁灭力量的摧残。[5]
这样,中国人便通过复活过去与把时间无限化的方式,获得了对苦难“现在”的遮蔽,从而达到了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却因对现在的回避甚至否定而带有较强的虚幻性,从而使我们缺少了前进的生机与动力。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文化的五大病症,其中之一是“不落实”。梁说:“西洋文化从身体出发,很合于现实。中国文化有些从心发出来,便不免理想多过事实,有不落实之病。……西洋是从现实(利与力)中发展出理性来的,而中国人却讳言力,耻言利,利与力均不得其发展。离现实而逞理想。”[6]299我想这是很切合实际的。我们中国人一直存在着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正显示了这一点:因为现实的苦难,我们有了理想;但理想的脱离现实,却使这理想有了太多的虚幻性,由此,返回现实,斤斤计较于眼前的既得利益,便成了虚幻理想的另一极端。李炳海则进一步指出,孔子的时间意识和人生哲学从形式上看,“要求人的进取必须不间断,从内容上看,他所说的进取,有时指的是停顿;他所说的恒久,实际是间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以中断为持续,以停顿为进取。……孔子自以为是在不间断地前进,实际却是走走停停,时断时续,这和他欲速而缓、高耗低效的人生悲剧一样,都是他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7]
至此,我们似乎在时间的历程中寻找到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节。可我们为什么总难以突破传统获得长足进展呢?这也许与我们所特有的时间观念——圆形时间观念有关。关于此点,古人与今人都有详细的阐释与论述,而且很多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甚至把它看作是一种生命时间,使我们“在往来推脱中别故致新,尽情宣畅宇宙雄奇创意,将生命不断提升到新的高度”[8],从而达到“生生”而“新新”的人生发展目标。如果真是如此,我们中国岂不早已突破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而成为世界一号强国了吗?因此,中国的圆形时间中一定存在一定问题。再回到阿Q,当他把时间极力地向过去和未来延伸后,现在几乎被压缩成了一个非实存的点,这样未来与过去便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圆。圆从结构上看,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的,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当下性的现在,因为现在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应当看作是开始,或者说,现在本身就是一个既是过去也是未来的时间概念。钱钟书在《管锥编·圆喻之多义》中指出了圆的流变性与停滞性。流变性是一种圆滑,它在一种无始无终、首尾相咬中让人无法攻破它。钱钟书在《谈艺录》中引用帕斯卡的话说:“譬若圆然,其中心无所不在,其外缘不止所在。”[9]“中心无所不在”是一种无原则的圆滑,而“外缘不止所在”则让人无从琢磨。中国人在这一方面体现的尤其明显。停滞显然是一种保守,钱钟书说:“体动而处未移,重复自落蹊径,固又圆转之事也。守故蹈常,依样照例,陈陈相袭,沉沉欲死,心生厌怠,摆脱无从。圆之可恶,本缘善于变易,此反恶其不可变易焉。”[10]在此,不管是流变还是停滞,圆的这种惰性显然都不利于人的心性与社会的发展。
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来看,中国的圆形时间结构中充满着的是“天”,是“天道”,而不是“人”、“人道”。对于此点,刘骁纯在《绘画意境论》中指出:“中西宇宙观的差别不在‘天人合一’,而在‘天人合一’是以人为本还是以天为本。……西方宇宙观的轴心是依照自然规律去征服自然,即依天道以治天,也就是以人为本的‘天人合一’。中国宇宙观的轴心则是顺应自然的‘天人合一’。”[11]这就明确指出了“天人合一”观念中“以人从天”的思想,而这显然会导致对人,对“我”的忽视。梁漱溟说:“中国文化最大之偏狭,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6]259正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指明了,只有充分发挥个体性的潜能,实现天人之分,在正视现实中脚踏实地地去克服现实,才能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更高程度的、真正的“合一”。
阿Q的时间意识给我们的启示也许不止这些,但他却让我们看清了唯有正视现实,从我做起,顺着时间之轴向前走,我们才有真正的未来,同样也才会拥有真正的过去。
[1] 路易·加迪,等.文化与时间[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 冯铁.略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时间运用——以鲁迅等作家为例[J].鲁迅研究月刊,1998(11).
[3] 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121.
[4] 林同华.宗白华全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440.
[5] 尼采.悲剧的诞生[M].北京:三联书店,1986:11.
[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
[7] 李炳海.孔子的时间意识及人生哲学[J].传统文化,1991(1).
[8] 朱良志.中国艺术的生命精神[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82.
[9] 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111.
[10] 钱钟书.管锥编(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928.
[11] 刘骁纯.绘画意境论[J].文艺研究,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