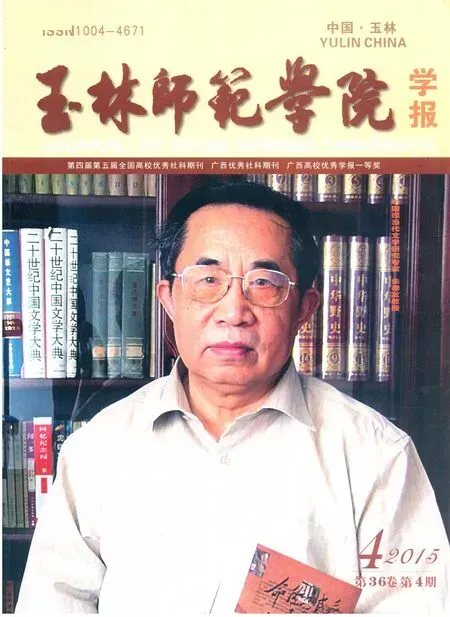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双人物”
□梁惠梅
(玉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双人物”
□梁惠梅
(玉林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西 玉林 537000)
“双人物”指文学作品中所具有较高关联性的一对人物形象。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双人物”手法是纳博科夫小说中常见的创作技巧。随着创作时间的推移和技巧的成熟,纳博科夫所塑造双人物形象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早期双人物形象同质性强,晚期双人物形象在内容和表现技巧上都体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作为一种“制谜”的策略,“双人物”不仅是纳博科夫独特的文学观和艺术现实观的表达,更是他对“追寻自我”的人生命题之思考。
双人物;制谜;追寻自我
“双人物”(doppelgangers)是德国文学中的一个传统文学术语,指文学作品中具有较高关联性的一对人物形象,包括一个“活着的人”和其“虚构的影子”。“人”与“影子”之间,相互映照,如影随形,构成一种镜像关系或对立关系,呈现不同的关联状态—同质关联和异质关联。在同质性双人物中,影子是此人的精确复制品, 具有与其外貌、着装,举止相似的特点,形成一种互为镜像的关系;在异质性双人物中,“活着的人”和“虚构的影子”在举止、性格和外形等方面相互迥异,形成一种相互对立的关系。
作为一种小说创作手法,“双人物”起源于18世纪晚期的浪漫主义文学,在19世纪后期达到鼎盛期,并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在文学作品中,“双人物”具有无可替代的文学作用。它能够帮助作者表述难以直接加附于某人物之上的内容, 表现文学作品复杂主题和营造作品的神秘气氛。[1]因此,“双人物”成为了许多中外作家青睐的小说创作手法。如《红楼梦》中晴雯和黛玉、《简爱》中的简爱和贝莎梅森,《蝴蝶梦》中的丽贝卡和我,《简萨默斯的日记》中的理查德和弗雷迪等都是典型的双人物形象。
尽管纳博科夫在接受小阿佩尔的采访时,曾流露出对“双人物”小说的不屑。然而,正如纳博科夫研究专家肖谊教授所说的那样,“否认一件事通常暗示其存在的可能性……大师否认任何文学的影响就几乎跟承认一样意义深远。”[2]不可否认,在纳博科夫的作品中,“双人物”手法应用广泛,几乎每部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捕捉到“双人物”的影子,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眼睛》、《绝望》、《塞·奈特的真实生活》、《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等。那么,我们就以这些小说为基础,分析其中的双人物形象,从而揭露纳氏小说中“双人物”手法的创作特征、根源及文学功能。
一、创作特征
首先,从创作时间的跨度看,“双人物”主题一直是纳博科夫小说创作的关注点,无论是早期发表的俄文小说还是晚期创作的英文小说,均体现了文体学家的纳博科夫对“双人物”创作手法的青睐和重视。“我”与斯穆洛夫,这一对双人物出现于纳博科夫写于1930 年的俄文小说《眼睛》一书中;赫尔曼与费利克斯,这一组双人物出现在其1936 年的俄文小说《绝望》中;“我”与塞·奈特,这一对双人物出现于1941年创作的英文小说《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中;亨伯特与奎尔蒂,这一对形象则出现在1955 年出版的《洛丽塔》中;在1957年出版的《普宁》中,甚至还出现了两对双人物形象,普宁与“我”、普宁与考克瑞尔教授(一个以模仿普宁为乐的人);不过,后一对因在小说中着墨不多,在此,就不赘述。在1962 年出版的小说《微暗的火》中,也出现了一对双人物──金波特与谢德。在英文中,谢德(Shade)是“影子”的意思,名字本身其实已经暗示谢德就是金波特的“影子”。可以说,从早期的俄文小说《眼睛》到晚期的英文小说《微暗的火》,“双人物”手法都贯穿在纳博科夫一生的小说创作中。
其次,从双人物形象的特质看,不同时期的作品体现出不同特性的双人物形象。在稍早期的作品中,双人物形象的同质性强。“我”与斯穆洛夫、赫尔曼与菲利克斯、“我”与塞·奈特都属于具有高相似度的同质性双人物形象。《眼睛》中“我”与斯穆洛夫形象是前后延续的,“我”自杀之后斯穆洛夫其实就是“我”的替身,且最后这两个形象合二为一;《塞·奈特的真实生活》中“我”本与塞·奈特是兄弟两人,在随着“我”对兄长生平的不断探寻,“我”竟然发现自己其实就是塞·奈特;在《绝望》中,赫尔曼更是疯狂地坚信费利克斯就是自己的复制品,是另一个我,即使在别人看来他们之间没有丝毫相似之处,赫尔曼也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这些都体现了这几组双人物形象明显的同质性。但随着纳博科夫创作手法的成熟,在其晚期的作品中,这种同质性逐渐淡去,更多呈现的是异质性,主人公与影子人互为反忖,体现更多的差异性和对立性。在1953的《普宁》中,尽管我和普宁都是教俄语的大学教授。但两人却是情敌,境遇大不相同,“我”踌躇满志,春风得意,在美国文化语境中混得如鱼得水;而普宁却是一个不善言辞,温顺善良,最后还由于无法适应新环境而被迫远走他乡的一个苦恼人。如果说这对双人物形象仅仅是纳博科夫尝试转变双人物表现风格的开始,那么,到了1957的《洛丽塔》这种风格的转变就更加明显了。亨伯特与奎尔蒂是势不两立的情敌,为了洛丽塔,最后两人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两人的性格迥异,前者痴情专一,对洛丽塔一往情深;而后者卑鄙无赖,对洛丽塔欺骗玩弄。同样,《微暗的火》中的金波特与谢德也是一组迥异对立的人物形象,前者是评论家,后者是诗人;前者高大挺拔、须眉浓密、身手敏捷且是左撇子;后者矮小瘦弱、眉清目秀、动作迟缓且是右撇子;思想上,前者是个基督徒、素食主义者、同性恋者,爱好音乐;而后者是个无神论者、异性恋者,无特殊饮食偏好,厌恶音乐。[3]由此可见,随着时间的迁移,纳博科夫在文学创作上的技法日臻成熟,双人物形象在表现手法和内容上体现也更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二、创作根源
纳博科夫如此热衷于“双人物”手法,这他对蝴蝶的钟爱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学观密不可分。纳博科夫一生对蝴蝶情有独钟,并“与蝴蝶结下不解之缘,他无法在潜意识中、情感中、文学创作中排除蝴蝶的身影,甚至他的创作冲动、小说语言、人物形象和美学观念等无不打下了蝴蝶的烙印。”[4]
蝴蝶对纳博科夫文学艺术观的最大影响,当属“摹拟之谜”。蝴蝶有着超强的模仿技能,不仅可以模仿枯叶的形状,甚至能模仿枯叶上被虫蛀过的小洞;利用翅膀上闪亮的斑点模仿被阳光折射过的露珠。种种自然界生物的模仿奇景无疑使纳博科夫着迷,并醉心于探究其中的奥妙,纳博科夫正是透过蝴蝶的这一习性得出了模仿与真实之间的领悟,看出了艺术与自然之间通贯的秘密:“两者都是魔法的一种形式,两者都是一个奥妙的巫术与欺骗的游戏。”[5]在纳博科夫看来,大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伟大的魔法师,越是伟大的作品越有高超的欺骗性。因为“所有的小说都是虚构,所有的艺术都是欺骗”[6],在这种文学艺术观的指引下,纳博科夫变身为文学世界中的制谜高手,通过使用纷繁、缠绕的模式,制造一个个如像蝴蝶般充满迷惑性的文学迷宫,虚实相映,平行错出。如果说蝴蝶是自然界中的制谜高手,那么纳博科夫便是文学世界里的那只调皮的蝴蝶,借助纷繁复杂的艺术手段,凸现“制谜”的魅力,实现其文学“欺骗”的狂欢。
自然而然,“双人物”手法成为纳博科夫表达其文学艺术观的必然选择。毕竟在纳博科夫看来,人物角色的相似度越高,迷惑性越大;迷惑性越大,文学性就越强。在小说里,纳博科夫刻画出众多双人物形象,往来穿梭于不同的叙事层,令人眼花缭乱,真假难辨。《普宁》中“我”与普宁的关系,在小说叙事视角从第一人称装换成第三人称后,这个“我”就像影子一样,若隐若现地陪伴在普宁的身边,默默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分享着他的喜怒哀乐,直至最后接替了普宁教职职位,以与普宁相仿的身份走到了台前。“我”既是被叙述者的形象,又是构成普宁形象的角色之一。随着“我”的丰富性发展,普宁更加走向虚幻。《绝望》中,诗人谢德创作出了金波特这个人物,并把自己死后的生命想象性地投射到了虚构人物金波特的身上。在诗歌的一开始,谢德就将自己一笔勾销,他( Shade)把自己的影子(shadow)投射到外面的镜像世界,继续生活,飞翔。如果说谢德的诗歌是一面镜子,那么金波特看到的镜中之像则是自己的人生命运和心灵哀曲,是赞巴拉国的一段隐秘历史。但是,所有赞巴拉国的历史都是金波特叙述出来的,是谢德诗歌的镜中之像,其真实和虚假都无法得到证实,增加了小说的虚构性和迷惑性。
三、文学功能
(一)表达找寻自我的主题
“双人物”具有独特的文学功能,如主题揭露,人物刻画等。在主题揭露方面,纳博科夫通过设置“虚构的影子”,把“活着的人”性格中被压抑的部分显现出来,以此表达出找寻自我的文学主题。因此, 在纳氏小说中,“双人物”往往被设置成一对自我分裂、时而矛盾对立、时而模糊混淆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作者关于“自我”的思考和困惑。
《眼睛》这部小说正是以“我”对自身形象的调查和追寻为主线展开的,直接表达了纳博科夫对“自我”的探索。“斯穆洛夫”是谁?斯穆洛夫是个怎样的人?小说中“我”热切地盼望知道他人对“我”的化身--斯穆洛夫的看法,但随着探求的深入,“我”发现,“遇到的所有这些人都不是活着的生灵而仅仅是折射斯穆洛夫的镜子,同时,在所在的镜子当中,即使那面被我认为是最重要、最明亮的镜子,也未能向我展示真正的斯穆洛夫形象”[7],真相似乎离“我”越来越远,“我”迷失在众多的斯穆洛夫的形象之中。最后,小说以那对原本分裂的双人物形象重合--斯穆洛夫就是“我”,“我”就是斯穆洛夫,结束了侦察斯穆洛夫身份之旅。如果说《眼睛》表达纳博科夫对“自我”的思考和探索,那么,小说《绝望》则更多流露了作者对“自我”的迷惘和困惑。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赫尔曼是一名巧克力商人,同时也是文学爱好者,深受身份和意识分裂的困扰。他起意谋杀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菲利克斯,与其说是由于赫尔曼遭遇经济上的窘迫,不如说是其身份和意识的分裂所致,他希望能够把自己的一部分分裂的身份和意识转嫁到菲利克斯那里,视菲利克斯是赫尔曼身份分裂和意识分裂的转嫁对象,最终造成了谋杀这一悲剧。
而在《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中,“自我”变得更加难以确定。亨伯特与奎尔蒂、“我”与普宁、金波特与谢德这些双人物形象之间界线就不再那么分明了。谁能否定奎尔蒂就不是亨伯特人性中被压抑的另一面,“我”就不是那个适应了美国生活的“普宁”呢?金波特不正是谢德死后生命的投射吗?在这,“活着的人”和“虚构的影子”时而对峙分裂,时而交错渗透,让读者难以分辨谁是谁,“自我”在此更加扑朔迷离。
尽管找寻“自我”之途艰难曲折,纳博科夫却没有让小说中的人物停止追寻的脚步。纳博科夫为什么如此热衷于表达探寻“自我”的主题呢?这与纳博科夫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文化身份是放不开的。“作为一只漂洋过海的蝴蝶,纳博科夫是一名文化流浪者和一名俄罗斯文化的热爱者和坚守者,纳博科夫同样和他笔下的主人公一样,在文化的分裂之中,体验到意识分裂和身份分裂的痛苦。”[8]纳博科夫一生中的前四分之一时间是在俄国度过,宁静而幸福,而后的四分之三的时间则漂泊于异国他乡,怀着对祖国传统文化无限的依恋和向往,却又不得不在异质文化中艰难生存,饱受文化冲突和跌宕生活所带来的迷茫和痛苦。在内心深处,他有一种强烈的“确立自我”的欲望,并把这种欲望写进了小说中,与读者一起探索“找寻自我”的人生命题。身份认证因而成为了纳博科夫反复书写的重要主题,所以,我们才会在他的小说中看到充满文本的那些身份和意识分裂的双人物形象,看斯穆罗夫、赫尔曼、金波特等人追寻自我的历程。
(二)抹平艺术与现实的界限
如前面所述,双人物包括双重人物角色── 一个“活着的人”和“虚构的影子”。考察纳博科夫小说中的双人物形象,我们会发现这些双人物角色并非从一而终的,而是在一定的时空下,发生转换。在《眼睛》中,一开始,读者认为“我”就是那个“活着的人”,而斯穆洛夫则是“虚构的影子”,但是,到小说后面,斯穆洛夫却走到台前,与我重合,成了那个“活着的人”。同样在小说《绝望》中,读者开始会认定叙事者赫尔曼就是谋杀的实施者,也是那个“活着的人”,而费利克斯则是那个“虚构的影子”。但在小说的结尾,赫尔曼被警察包围的时候,赫尔曼对外面的围观群众发表一番演说,声称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电影拍摄的场面,自己是出演主犯的著名演员。原先那个“活着的人”通过叙事者赫尔曼之口,又变成了“虚构的影子”。在后期作品《普宁》中,双人物的这种身份的相互转换就更明显了。小说的前六章全部是围绕那个“活着的人”--普宁的故事展开,“我”只是他若隐若现的影子。但在第七章,即小说的最后一章,“我”突然高调现身,成了整章的聚焦,原先的“影子”摇身一变成了那个“活着的人”;而普宁则黯然离开温代尔学院,化身为远去的影子。显然,双人物的身份角色切换是纳博科夫的故意而为之。那么他的用意何在呢?
1972年朱丽亚·巴德在《水晶地:纳博科夫英语小说中的技巧》说道,“映像、孪生、学究的乡愁、揶揄的认真、疯狂与堕落、死亡与永恒,所有这些虽然不能为艺术主题所涵盖,但都涉及这个主题”[9],“这个主题”指的就是关于艺术与现实的关系。艺术与现实是怎样一种关系?纳博科夫不止一次强调这样的观点:艺术是欺骗,是虚构;客观现实只存在于人的头脑中。如果说现实对应的是那个“活着的人”,那么,艺术就是那个“虚构的影子”。在这里,“双人物”具有一种深刻象征意义的隐喻作用。双人物角色之间的可切换性暗示艺术和现实也是同质的,可转换的。这与纳博科夫的艺术现实观是一致的。纳博科夫认为,“艺术与现实世界具有原初同一的性质。”传统的主客对立的二元艺术观在‘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凿开了一条很深的鸿沟,“艺术真实”追求对“生活真实”的逼真摹仿, 也就是说,作品中的内容靠“现实生活”越近,作品的‘生活气息’越浓厚,就越成功。而纳博科夫的观点却是,现实世界本来就充满了欺骗和假象, 本身就是充满了艺术味的潜在小说,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在构成性质上是一致的,因此, 它们之间没有界限。”[10]纳博科夫撒费苦心地让双人物在两种身份角色间往返穿梭,其用意就在于颠覆二元对立的传统艺术观,打破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截然界限,进而表达其“物我一元”的艺术现实观。
至此,“双人物”原本是一种小说创作手法,但在纳博科夫的笔下,它成了更高层面的文学主题,发挥着双重文学功能,实现了对“自我”人生命题的追寻和对艺术与现实之间对立关系的解构。 ■
[1]郭曼,王丽丽.灵魂的影子[J].山东外语教学,2006(4):98.
[2]肖谊. 莎士比亚“戏中戏”对纳博科夫英语小说叙事的影响[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6(4):47.
[3]王霞.纳博科夫小说中人物的孪生现象探析[J].作家杂志,2009(12):81.
[4]何岳球.纳博科夫的蝴蝶情结与美学意蕴[J].当代外国文学,2009(12):105.
[5]纳博科夫.说吧,记忆[M].陈东飙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113.
[6]纳博科夫.文学讲稿[M].申慧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1:128.
[7]纳博科夫.眼睛[M].张玉夺译.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321.
[8]梁惠梅.“镜子的反照”和自我认证的分裂[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6):134.
[9]汪小玲.《绝望》对纳博科夫的艺术创作观的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8(1):55.
[10]赵君.探寻“现实”的本真内涵[J].外国文学评论,2008(4):76.
【责任编辑 吴庆丰】
Doubles in Nabokov’s Novels
LIANG Hui-mei
(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Yulin Normal University, Yulin, Guangxi 537000)
Doubles is a common creation technique in Nabokov’s novels.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and creation techniques getting mature, Nabokov’ doubles theme reflect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in his early novels, the images of doubles show more homogeneity; in his later novels, the images of doubles demonstrate more complexity. Doubles is a strategy of Nabokov’s "making mystery", is the expression of his unique literature and art view, and also is his thinking about the "pursue self" life proposition.
doubles;making mystery;pursue self
I106.4
A
1004-4671(2015)04-0114-04
2015-05-19
2012年度广西教育厅科研项目《“镜子的反照”与自我认证的分裂-纳博科夫小说中的镜像写作研究》(项目编号:201204LX340)。
梁惠梅(1975~),女,广西贵港人,玉林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和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