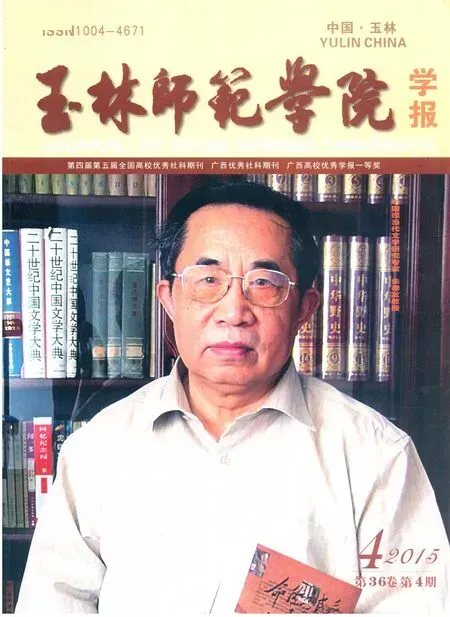学校文化建设若干问题思考
□韦丽银
(广西民族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6000)
学校文化建设若干问题思考
□韦丽银
(广西民族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西 南宁 536000)
审视当前学校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虽呈现“繁荣”景象,但仍有一些基本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一是 “学校文化”界定问题,须辨明“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实质区别,阐明学校文化的本质所指;二是“学校文化资源”的定位问题,须正确认知学校文化资源特质;三是学校文化价值问题,须把握学校文化价值的根本在于育人;四是当前学校文化缺失问题,审视现代学校文化,其最大缺失即是逐渐脱离了“教育本质”;五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逻辑问题,须明确学生与教师的共生发展既是逻辑起点也是逻辑归宿,学校文化问题与学校文化历史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基础,学校文化建设主体是学校主体而非其他。
学校文化;教育资源;文化缺失;育人;校长
一、“学校文化”本质问题
自美国学者华勒(Waller)于1932年提出“学校文化”概念以来,学校文化就成了教育学者所热衷的一个基本命题或基本对象。在我国,“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交织出现于教育研究领域,生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研究进程,其中,关于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的概念辨析问题是我国学者长期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近年来,随着我国教育研究领域“文化热”的沸起,学校文化应用研究开始涌现,凸现了学校文化建设、学校文化特色构建等热点命题,然而关于学校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仍并未停滞而愈加强烈,随着学校文化研究的深入与拓展,一些基础理论问题显得更加复杂、难以把握,比如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概念界定问题,学校文化内涵、外延、分类框架等问题。即便如此,对基础概念的厘定与把握仍然是价值性、策略性研究的逻辑前提之一,因而对“学校文化作为教育资源”命题的讨论同样需要对“学校文化”概念有所把握、有所定位。
众所周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诸多基本概念的界定、定义、解释等都难以普遍化或共同化,其原因首先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具有的主体价值参与性与研究价值对象性特征,研究者价值观、方法与过程、研究视角、学科背景等因素加上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多元化、模糊性等特点共同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惯常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学校文化”概念自产生之日起就陷入了这样的惯常现象之中,尤其是后来“校园文化”概念的出现所制造的“混乱”。学校文化概念始于西方,校园文化概念产自我国,可以说“校园文化”是基于“学校文化”的继承创新,也可以说“校园文化”是我国文化语境的产物,但从根本上看,这两者则存在必然差异。
从“学校文化”发源的西方语境来看,华勒认为学校文化是学校文化中形成的特别的文化[1],班克斯(Banks)认为一个学校群体成员的价值取向、信仰、态度和行为为学校文化;加里·菲利普斯(Gray Philips)提出学校文化就是“一个学校的行为、态度和信仰”;瓦格勒(Wagner)认为经验、团队感、归属感和集体意识为学校文化。[2]大卫·斯图法特(Daive Stewart)把学校文化描述为学校成员一般所认同的价值和信念。[3]由此看,西方学者普遍趋向于从“文化”的内部向度定位“学校文化”。我们知道,关于“文化”的定义当前已经不下260种,然总的说来,“文化”定义不外乎为综合文化论、文化物质论与文化精神论三种,从“学校文化”的定义来看,西方学者趋向于文化精神论,即普遍将学校文化视为精神性存在,比如价值、信念、信仰、归属感等。
纵观我国相关研究,虽有人认为“大约从80年代后期开始,有研究者较早开始使用‘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开始取代校园文化成为理论研究者更认同的说法”[4]。然而历史实践中,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的交织状态并未厘清,学校文化概念模糊难辨,对进一步的应用研究制造了诸多困难。作为两个已然存在的名词性概念,从文辞发演规律来讲,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都有其特定所指,由所指的范围、对象来确定两者所应有的价值;从尊重起源这角度来讲,学校文化的内涵应传承西方语义,校园文化则应保持中国文化语义。由此出发,就产生了“学校文化就是学校文化,校园文化就是校园文化”的基本逻辑,两者实然不应混淆使用,更不应相互取而代之。
概念具有发展的属性,这是因为概念本身是作为“研究对象”而存在的,伴随历史文化演进、地域变迁、知识更新与学者换代的客观现象,概念(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外延会逐渐拓宽或变窄、丰富或萎缩,而本质或内涵亦不会变化,除非“唯心主义”者掌控了历史。从这个角度上说,“学校文化”由于穿越了时空则必然产生变化,这种变化就是外延的变化。在我国研究领域,这种变化普遍表现为“丰富化与延展化”,比如诸多学者在基于原初意义的基础上将“学校文化”进一步解释为“学校文化是指一所学校内部形成的为其成员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价值观体系、行为准则和共同的作风的总和。它表明一所学校的独特的风格和精神,是联系和协调一所学校所有成员行为的纽带,是学校的灵魂所在”[5];“学校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组织成员共享的基本假设和信念以及稳定的生存方式,它们表现为学校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6];“学校中全体成员或部分成员习得且共同具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等”[7]。等等。这些都符合必要的基础理论研究逻辑,并没有“自以为是”或盲目自大的歪曲、扭曲概念的原初意义。
如果说“学校文化”的内涵真的发生了变化,那将不能继续称之为“学校文化”。内涵的变化意味着概念符号已经变化,比如“人”的所指不再是“人”,那么指示或象征人的那个符号就必然发生变化,即不能再用“人”这个符号。“学校文化”内涵发生变化之后成了“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所指的就不再是原来的“学校文化”本义,于是如同上面所说“学校文化是学校文化,校园文化是校园文化”。对于这种“变化”,其原因可以归纳为几点:一是基于“文化”的内涵而得出不同解释,二是受制造“变化”的主体所要达成的目标所规定,三是受历史文化语境、言语差异的影响。比如“学校”与“校园”两个词,实际上前者指的是独立于社会其他系统而存在的教育系统,而后者指的是学校作为教育系统在空间意义上保持的状态,学校象征“教育的存在”,而“校园”则指“教育要素所存在的空间”。正因如此,诸多学者在定义“校园文化”之时往往将其纳入“时空”框架,进而以文化整体论为基础定义“校园文化”,同时,混淆“学校文化”与“校园文化”概念的情况同样趋于文化整体论。此时的“校园文化”或“学校文化”的内涵都大于、超越了原有的“学校文化”本义被认为是:“是经过长期发展历史积淀而形成的全校师生(包括员工,下同)的教育实践活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这里面同样包含了物质层面(校园建设)、制度层面(各种规章制度)、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师生的行为举止)”[8];“是学校师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创造和形成的精神财富、文化氛围以及承载它的活动形式和物质形态”[9];包括“教师文化、行政人员文化、学生文化、社区文化、学校物质文化、学校制度文化”[10]等等。
当使用“学校文化”概念之时,它指的就是学校文化而非校园文化。很多学者认为校园文化归属于学校文化,“校园文化可能只是学校文化的一部分或具体表现”[11]。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两者的根本旨趣不同。学校文化专指学校作为“教育”的象征,是承载教育真谛与丰富内涵的文化实体。如华南师大刘良华教授就认为学校文化的核心在于精神,这种精神是自由与平等,他说“好的教育不只是让儿童自由生长和自由发展,而且为儿童的自由生长和自由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坏的教育常常为儿童的生长与发展制造不平等的竞争环境。……,让自由与平等成为学校文化的核心精神,这是一个美好的想象。这个想象若不兑现为具体的课题文化与班级文化,所谓‘学校文化的核心精神’,依然只是一张没有印章的空头的支票”。“自由是学校文化的立足点,平等是学校文化的底线”。[12]“校园文化”与“学校文化”这两个概念本不应混淆而应分别独立存在、各有所指。研究者完全可以根据研究目标、价值取向等采用相应概念,而在指导实践的意义上,它们各自的内涵与象征将为实践者指明方向、做出严格的规定。学术研究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正在于此,即对核心概念不能模棱两可、含含糊糊。一直以来,学者们无不广泛承认这两个概念的模糊与混淆状态,然而在他们的研究中,结论却往往不约而同的相似,都是含糊而“中庸”式的给出一个“无所不包”的界定,要么校园文化包含学校文化,要么学校文化从属校园文化,这就导致在实践操作中普遍混淆使用,找不到明确方向。
二、学校文化资源特质问题
学校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从“资源”的角度审视学校文化,即是从“用”或“价值”的取向来定位学校文化。其所要探讨的基本问题是“学校文化凭什么是教育资源,而且重要”。这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解答,第一,学校文化具有促进教育发生、发展的属性,这里的“教育”是体现教育本真的教育;第二,学校文化的这种促进作用或价值属性比一般的“资源”更大。同时,还需要以对“资源”本身内涵的准确把握为前提。
首先来看“资源”的含义。不同领域关于“资源”的定义存在一定差异。一般而言,经济学领域对“资源”概念的界定具有普遍意义,当然,这与“资源”概念本身产生于经济学有很大关系,“资源本质上就是生产要素的代名词”[13]。赵卓元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大辞典》将“资源”解释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广义上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学技术、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等,狭义上一般指自然资源”[14]。“人口、环境、资源和发展”专题讨论会专家组对资源的定义是:“资源一词包括人力资源、资本货物和自然资源,后者是能用于生产过程中的自然的组成部分”[15]。以上两者实际上都没有解释出“资源”的本质内涵,都意在说明资源的种类,或说资源由什么组成。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解释,“资源”实质产生于劳动,与劳动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劳动和土地,是财富两个原始的形成要素。”恩格斯的定义是:“其实,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它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转变为财富。”[16]从而,“资源”实质即指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的财富。或者说,资源就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种可以用以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具有一定量的积累的客观存在形态。从定义上讲,“资源”的所属范围是整个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这主要是由于“资源”本身没有添加任何限定性前缀。“教育资源”是“资源”的具体化,这赋予了“资源”特定指向与载体。教育资源指的就是可用以促进教育发生、发展的一切可被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的总称,即可开发、可利用价值。
学校文化是一种重要的教育资源,强调学校文化是一种对教育具有重要价值或意义的文化存在,是一种促进教育发生发展的正能量,而这种正能量即“学校”所象征的精神、信念、信仰、价值观等。就学校教育而言,学校是教育发生的场域,学校文化体现学校教育精神和整体性的文化景观。不同的学校文化体现不同的教育理念、教育信仰和教育价值取向,这是学校文化的核心所在。比如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就以“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精神为学校文化的核心要义,对学校教育运转、教育功能的发挥起到了“灵魂支撑”的作用,这就是学校文化。又比如一所小学,它以“生命教育”为教育信仰,那么它的学校文化将以此为特质,展现该学校的教育本质。一旦特定的学校文化得以形成,它对学校教育的发生、发展将产生巨大作用。如若学校文化是正向的、反映教育真谛的文化,那它的“教育作用”就是积极的,反之则是消极的,而只有发挥积极作用的学校文化才能称之为教育资源,并且毫无疑问是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
学校文化作为重要的教育资源,其重要的“价值属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学校文化是学校各种“主体”所自觉尊重、自由信仰的精神或理念,学校文化将内化为主体(管理层、教师、学生)的心理与情感,潜移默化或直接的影响主体态度与行为,比如外化为管理制度与方法、教学理念与方式、学习态度与行为等。其次,“学校文化以学校全体成员为主体,是他们在教育教学和管理实践中逐渐共同创造生成的体现时代特征和社会进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规范及其活动结果”[17],它们将凝聚为人类进步的能量,成为指导人类实践的方法论。第三,学校文化是一个区域、社区文化中的文化体,从泛教育意义上讲,特定学校文化所代表的理念与精神将辐射影响区域发展,甚至成为某区域的核心文化对人们的道德、行为产生重要积极作用,提升民族、民众的素质素养,甚至升华为区域性的文明形态。
三、学校文化育人价值问题
根据学校的影响范围与所属范围,可推知学校文化的第一承载体是学校实体,第二承载体是区域或社区,第三承载体是国家。第一承载体指特定的学校所形成的学校文化,这样的学校可以是一个或多个。第二承载体是指学校文化所辐射的区域,它将成为学校文化生存、延续、发展的“栖息地”,因为学校文化依托特定的区域文化、人文特征与自然环境。国家作为学校文化的第三承载体,强调的是学校是传承与发扬民族传统文化、社会核心价值观、民族精神与情感的基本场域,学校文化之中必然包含国家情怀、民族立场和社会使命感。所以,学校文化的育人功能是无处不在的,它是社会发展、人类进化的基本教育资源。从根本上说,学校文化的承载体是“人”,因为它是人的创造物,人是符号的动物,学校“人”是学校文化的主体、传承体。特定的学校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校文化将会被时代汲取、被人类传承而得以发展,成为跨越时空的教育资源,对人类与社会发展产生持久的作用;消极的学校文化将被历史淘汰,成为永久的印迹。
学校文化的育人功能从本质上讲即是文化的育人功能。所谓“育人”,强调的就是文化对人的直接与间接的作用关系。学校文化的育人功能其主旨为学校文化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思维、理念等构成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濡染与教化。濡染是文化对人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人生长在特定的文化环境或文化模式之中,在参与创造文化的同时也在接受着文化的熏染。教化更加注重“人为性”即人为的教化,从我国优良传统教育的立场来看,学校文化的教化功能是体现教育本真的重要组成。“教化指那些积极促进人性的优秀和卓越的活动。”[18]“教化是精神的引导和创造的结合,是启迪与自我建构的结合。教化所面对的是在追求真、善、美的过程中精神的自由创造,理性和德性是精神创造的根本条件。教化对理性和德性的培养,使我们获得一种经验的穿透力以及判断、质疑的勇气,从而可以克服任何的盲信和盲从,克服冲动和盲动,既制服外在的霸权和暴力,又形成内在的自制和自治,从而自由的追求人格精神的构建”。[19]
四、学校文化缺失问题
当前学校文化缺失是我国教育所需亟待解决的大问题,正因如此,21世纪以来我国持续兴起“学校文化建设”的热潮,尤其在我国“文化强国建设”与“人文理性呼唤”的当下,这种学校文化建设更成为重要课题。实际上,学校文化缺失指的就是以人文价值、人文精神为文化核心的学校文化的缺失。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兴起的学校文化特色建设实践并没有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学校文化精神的构建,诸多所谓学校文化特色构建仍停留于校园文化建设层面,主要致力于搞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校园特色”,校园中各种“文化活动”、“文化形式”异彩纷呈,类似在“学校文化建设”的口号下进行的文化建设行为一方面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还在于没有尊重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忽略了文化演进机制的“循序性”,而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
学校本身作为文化体是由学校各种文化要素组成的,或者说学校作为一种文化系统由学校内各文化体系共同构成,比如很多有关“学校文化”构成框架就根据不同维度得出了学校文化的多种分类,有精神文化、规范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物质文化,或者教师文化、学生文化,抑或是课程文化、管理文化等等。从这个角度讲,学校并不缺少“文化”。我们说学校文化缺失指的是一种代表学校教育精神、正确教育理念或教育信仰的文化的缺失。当前,我国学校教育普遍受功利主义、工具理性和“知识规训”的支配,丧失的正是一种极具人文精神、人文价值、生命关怀的学校文化。同时,由于个人主义文化泛滥与道德文化滑坡,学校文化中普遍缺失了社会责任感与民族立场,致使其“育人”功能萎缩,并不能发挥学校文化作为重要教育资源的最大价值。
以民族地区学校为例,总结当前我国民族地区学校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个显著问题就是:在大力实行民族教育的进程中,过于注重形式化的“特色课程”建设,而忽视了课程文化本质的建构,并没有发展出以民族教育为支撑及以民族课程文化为核心的学校文化,其间的突出问题就是没能深度挖掘民族文化基因,并使之与现代课程进行有效融合,进而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教育及通过课程文化而实现民族文化传承发展。此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民族教育并没有与现代学校教育发生融合,从而使得学校文化缺乏鲜活性。从文化的角度上,民族教育与现代学校教育的深度融合所生发的应是一种以民族文化基因为根本的学校文化形态。所谓民族文化基因,根据人类学观点,即指民族文化的基本单位,是根本存在于民族生活与实践当中并起着支配作用的文化存在,它是“游荡在文化基础结构中最活跃的成份”,“文化现象背后的运动机能”,[20]如民族思维、观念、常规、价值观、世界观等。以民族教育为支撑的学校文化首先是基于民族文化基因的课程文化建构,核心任务就是将民族文化基因植入现代课程体系,实现对学生的无形教化,是一种民族思维与精神世界的传承,而非是表现上风风火火的民族特色课程,也不是热火朝天的学校文化活动。
五、学校文化建设的逻辑问题
学校文化建设的出发点首先是学生成长,这是根本,其次是教师发展,这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逻辑起点也是逻辑归宿。反过来,学生不成长、教师不能发展,则难以实现文化建设与文化构建。胡贵勇认为学校文化建设可以从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文化形成和文化构建宗旨几个方面思考[21]。学校文化建设实质是育人文化环境的营造,甚至是学校育人文化模式的构建,这是一个系统、动态、长期的过程。所以,学校文化建设必须有历史依据、现实依托与未来展望,也就是说学校文化建设是文化传承与文化发展共同进行的过程,由此而论,学校文化建设至少要立足于三个基本点:一是学校历史文化积淀;二是学校所处人文环境的历史与特征;三是诊断学校文化问题或文化缺失。保持二个出发点:一是无论如何建设学校文化,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育人”;二是学校文化建设是为了传承与发展学校文化。总的就学校文化建设本身这个“建设”活动而言,它必须“一方面是基于文化自身中所拥有的历史文化价值理念,另一方面则是针对自身文化中所缺少的,吸纳异质文化以更新和丰富自身的文化传统。两种机制的互动与交融共同构成了学校文化建设过程中的行动逻辑与实践导向”[22]。
学校文化建设要充分发挥学校各类主体的作用。传统认为学校文化建设是学校管理层的事情,而很多学校管理者也认为管理是“上层”的特权,“下层”则属于被管的地位。校长是学校文化建设的指导者、引路人,然而学校文化的建设的主体则须是师生共同体,这是由学校教育的本质规定的。校长必须清晰的认识到,师生才是学校的主人,只有充分的发挥了师生的能动性、主体性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学校文化建设,也只有让全体师生充分认识到其所应承担的学校文化建设的责任与使命,他们才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学校文化建设之中。校长是学校文化建设的发起者、引路人,其首先要秉持一种能体现学生成长、教师发展与学校进步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将会直接转化为学校文化的内核,对塑型学校文化起到核心支撑作用。在这样的基础上,校长需养成特有的文化自觉性,这是学校文化建设实践的逻辑前提。所谓“文化自觉”,就是要求校长要对学校的文化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有充分认知与认同,对学校文化的内涵、形成因素、影响因素有必要的认知,对学校文化与其他文化系统的差异性有充分把握。同时,还需认识到学校文化对师生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对国家民族发展的意义,“意识到学校的文化精神和学校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文化发展中的历史使命。这既是由学校文化建设与社会大文化复杂生态直接关联所决定的,也是由学校在文化继承和创新中的独特地位与功能所决定的”[23]。
具体来讲,学校文化建设要从三个基本路径出发:“一是在学校变革进程中感受文化的力量。二是在课程开发中发现文化资源。三是在教学研讨中体悟文化的意蕴”。把握学校文化建设的两大来源:“一是学校自身发展历史所积淀,二是学校所处地域的丰富文化资源”。[24]而学校文化建设“最主要的是学校文化管理,即从文化的视角管理学校。学校文化管理要侧重于体察师生内心,最大限度地调动每个人的激情,让学校成为师生的精神家园”[25]。这也就是赋予师生更大的精神自由,使其真正意义上成为文化创造的主体。教师作为学生的指导者,教师的精神自由很大程度决定了学生精神自由的程度,因为教师文化在学校文化系统中对学生文化的形成、变化与发展有直接作用,还因为“没有教师精神的解放,就很难有学生精神的解放;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没有教师的教育创造,就很难有学生的创造精
神。”[26] ■
[1]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590.
[2]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3-24.
[3]Davie Stewart,D,J.Tomorrow’sprincipals today [M].Palmerstom North:Kanuka Grove Press,Massey University,2000:49.
[4]张连生.学校文化的现实批判[J].教学与管理,2013(7):6.
[5]朱颜杰.学校管理论[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
[6]马延伟,马云鹏.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重建——一所学校的个案研究[J].教育研究,2004,(3).
[7]郑金洲.教育文化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40.
[8]顾明远.论学校文化建设[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9]李莺歌.校园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关于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考[J].教师,2013,(3).
[10]林清江.教育社会学新论[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1.
[11]张连生.学校文化的现实批判[J].教学与管理,2013,(7).
[12]刘良华.学校文化的精神图景与核心使命[J].新课程,2013(1).
[13]http://baike.baidu.com/link?url=ZL3NvEWUxzxcFXeqn WE4aBvu5xsMRGw4yb3AqEIldoripHJ0_NHo1qL1b3fa0 mhKfZgk7cmTcK2ybIRb9RDpPa[EB/OL].
[1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张卓元.政治经济学大辞典[M].科学出版社,1998:299-301.
[15]向洪,邓明.人口管理实用辞典[M].成都科学大学出版社,1990:275-277.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373.
[17]李金初,牛玉发.试论现代学校文化建设[J].中国教育学刊,2003,(7).
[18]金生鋐著.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2
[19]金生鋐.规训与教化[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4.
[20]吴秋林.原始文化基因论[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4).
[21]胡贵勇.学校文化应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J].中小学校长,2013,(6).
[22]杨小微,张良.学校文化建设的思与行[J].人民教育,2013,(3-4).
[23]卞恩鸿.学校文化管理的实践与思考[J].基础教育参考,2008,(9).
[24]杨小微,张良.学校文化建设的思与行[J].人民教育,2013,(3-4).
[25]王定华.试论新形势下学校文化建设[J].教育研究,2012,(1).
[26]叶澜.教师角色与教师发展新探[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89.
【责任编辑 吴庆丰】
Thinking on some problems of school culture construction
WEI Li-yin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Nanning 536000)
Although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 culture is "prosperity", there are still some basic issues to be thought-provoking. The first is about the definition of "school culture", we must discern substa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school culture" and "campus culture", and clarify the nature of school culture; The second issue is the positioning of school cultural resources, we must be correct in the school cultural resources characteristic; Third, something about the problem of school culture value, we should grasp the fundamental value of school culture, which is to educate people; Fourth, it is about the problem of current school culture, the biggest flaw of modern school culture is out of "the nature of Education". Fifth,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logic of school culture, we need to clea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are not only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but also the logical destination. School culture and school culture history are the foundation of school culture construction, school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the main body of the school and not the other.
school cultu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cultural loss, educating people, principal
G40-055
A
1004-4671(2015)04-0150-07
2015-03-12
韦丽银(1990~),女,壮族,广西柳州人,广西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民族高等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