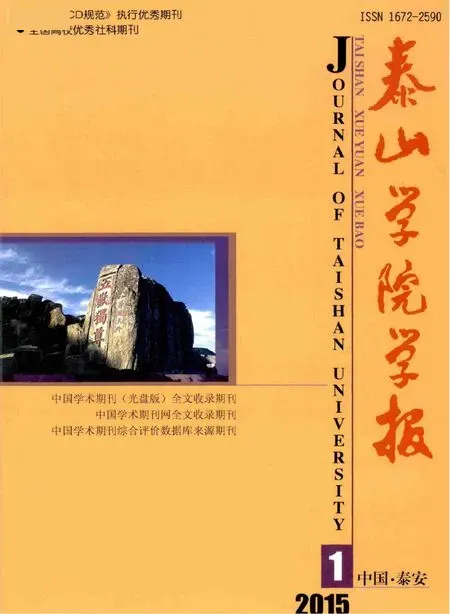新发现的顾随呈“药堂翁”诗六首
顾之京,石蓬勃
(1.河北大学文学院;2.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药堂”是周作人的别号,顾随称老师周作人为“药堂翁”。
顾随与周作人的师生情分始于就读北京大学英文系时,1929年受聘到燕京大学执教后,方与周作人有了较为密切的交往。弟子向老师述说创作体验,曲作、诗作呈交老师,又向老师汇报剧曲创作的“五年计划”;老师亦有“读书录”等交弟子阅读。大约是周作人做人处事一贯平易随和,“不似鲁迅先生之泼辣”(顾随致卢伯屏函,1929.12.3),顾随从周作人受教,尊敬之外,相处亦较为随意,是师似友。
顾随所书有关周作人的文字,近二十年来已辑得致周作人函八通,论周作人诗《跋知堂师〈往昔〉及〈杂诗〉后》一篇,论周作人散文一段。近时,又发现了顾随呈“药堂翁”之诗稿六首:前五首系七绝,乃弟子和“药堂翁”所示之“游僧诗”;最后一首为七律,乃弟子因“有感”而“呈药堂翁”者。七律有诗题标明写于“廿八年元日”,据此可推知,前五首七绝写作时间当是1938年冬日。
六首诗作之产生因由,盖源于周作人所得之“游僧诗”。当是时,周作人先是得到一首据说是“游僧诗”的七绝,拿给弟子看,弟子于是和作两首,诗题为“药堂翁以一绝见示,谓是游僧诗,戏和二首”。从诗题中的“戏和”二字,可以推想那首游僧诗定是写得相当诙谐;也可以想见当年师生二人读诗时,那气氛可能是相当轻松。弟子的戏和二首曰:
南来北去充行脚,东疃西村侭化缘。
输与牵风青荇里,小鱼跳出浪痕圆。
坐卧不曾修胜业,奔波枉是结尘缘。
禅心欲问天边月,何似遮头箬笠圆。
药堂师所示“游僧诗”现无可查考,且就和诗而说之。
前首先以游僧“南来北去”、“东疃西村”的“行脚”、“化缘”比况自己往来于各校任课的教书生活。继之化用杜甫诗“水荇牵风翠带长”(《曲江对雨》)、张炎词“鱼没浪痕圆”(《南浦·春水》),而冠以“输与”二字,意在言明:教书是自己的事业,它关系于后辈成长与文化流传,故而自身终不能如游僧之萧然物外,容身于杜诗张词中悠闲、恬适、俊雅的自然风光中;更深一层之蕴意则在于:自己终不能忘怀于国事民情。
次首承前,首二句言教书生活乃为生计而奔忙,此乃“尘缘”,因而无暇于修治禅家之“胜业”。“胜业”,本佛家语,指胜妙之事业。“胜业”二字,后来顾随在致弟子周汝昌、叶嘉莹的书札中,也用以代指创作与著述等有价值的文字。“禅心欲问天边月,何似遮头箬笠圆”二句,月,在佛典中用以为涵盖一切、包容一切的圆满浑融境界,《五灯会元》言:“山河与大地,都是一轮月。”“禅心”二句意谓自己欲以修禅之心追求这种极高之境地,但身处尘世,终不能如头顶遮阳箬笠之游僧可以超然物外。另“天边月”是否又可理解为用《楞严经》“第二月”之典?《楞严经》有注曰:“人以手捏目望月遂成二轮,取其捏出者为第二月。……第二月虽非真月,然离真月,亦无第二月之可见。”所谓“禅心欲问”,是否可用顾随九年后《揣龠录》第三章结尾所用佛典中之几句问答为解:
僧问法眼:“如何是第二月?”
眼曰:“森罗万象。”
问:“如何是第一月?”
眼曰:“万象森罗。”
若此臆解尚可暂为一说,那么此首之后二句,仍是呼应着前首之后二句,所欲言者仍是:自己终不能忘怀于“森罗万象”、“万象森罗”之世事民情,哪里比得了头顶遮阳箬笠的游僧之消闲自在?
未几,周作人又得到三首游僧诗,再次拿给弟子看,于是弟子又以“药堂翁继得游僧诗三首,因再和”为题,再赋三绝:
归来不觉暮寒生,旋拨地炉活火明。
煨得山芋熟初透,甜香缕缕引乡情。
此日城西行脚去,却逢云暗雪霏天。
情怀正自淡如水,一任长空乱撒盐。
黑月白月无休时,说青说黄枉费词。
篓斗桥边偶然过,一湾流水绕荒祠。
这三首绝句,仍是依游僧诗之原韵而抒自我情怀。
第一首,极富生活情趣,写冬日课罢归寓,在书房守着炉火以煨烤白薯的独特方式来舒缓课后的疲倦。顾随的童年是在穷乡僻壤的清河县农村里度过的,在那里,夏日自有不乏孩子们喜食的生鲜瓜果,到了冬天,恐怕就只有烤白薯这一种美味作零食了。(“烤白薯”至今在清河县仍被尊为“清河名小吃”。)顾随自幼爱吃烤白薯,如今,刚刚烤熟的白薯散发的缕缕甜香,怎能不引动他浓浓的乡情?
和诗的第二首,抒写自己在漫天飞雪之际去西郊燕园授课时平静而又黯然的情怀。此处以僧人之“行脚”代指自己之教书谋生。燕园,在当时已陷于敌手的古都,尚可算作一方净土,使顾随得以在内心的一角保留片时的安宁,但毕竟是羁身北地,毕竟是身同楚囚,他的内心怎能不笼罩在黯淡之中?所以长空飘舞的雪花虽然妆点着京郊的美景,也还是任随它如“乱撒盐”般的自飞自落吧,无法改变我“云暗雪霏”的黯淡情怀。
第三首,延续着前首的黯淡情怀。诗中“黑月白月”言时光,出自佛教类书《法苑珠言》注:“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为白月;十六日以去至于月尽名为黑月。”古印度历法即以阴历上半月为“白月”,下半月为“黑月”。“说青说黄”之“青”、“黄”,犹言是非、善恶。孔尚任《桃花扇·却奁》中有句:“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顾随以“说青说黄”借指自己的讲书,绝句以“黑月白月”、“说青说黄”言自己的讲堂生活,随着岁月流逝而延长,“枉费词”则是谦言自身事业无成就,是以“戏言”对教书生涯的自嘲。后二句景语其境界更为萧疏而荒漠。1930年代,篓斗桥尚存于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西门之西南方,桥长120米,宽3米,旧时文人又称之为西沟桥,今桥已不存。篓斗桥实为一处古迹,明代画家米万钟曾绘桥景,清时附近建有蔚秀园,之后桥东又建勺园,桥西有茶楼、酒肆、小市场。此际,诗人燕大课后返城,偶过“篓斗桥边”,已是繁华不再,只见“一湾流水绕荒祠”。诗以荒漠之景致写萧寂之意态,实是暗写身处沦陷之古都的凄凉况味。
五首和游僧诗之作,除几处佛典而外,几乎不干游僧何事,诗人只是“借游僧之酒杯”,以戏言之名,“浇自己之垒块”。
及至进入1939年,古都北平已是沦陷了一年有半,而展望前景,天暗如铅,新年伊始,顾随感触良多,遂书七律一首——“二十八年元日有感呈药堂翁”:
二十年来隐旧京,幽斋小院拥书城。
万言难补国治乱,举世谁知身重轻。
纵使飞空看圆月,可堪忍已到无生。
世尊不作冤亲别,翘首人间一动情。
诗之首联概言自己在古都近于隐居的书斋生活,“二十年”当是自大学毕业走入社会算起,乃是一个概数。颔联直言国土沦丧已年余,身处乱世,一介书生无力纾国难、济时艰。颈联仍用佛书看月之典,下句“忍”,佛家语,言自身遇苦而不动心,证悟真理,安住于“理”。“无生”亦佛家语,言无生灭、不生不灭之境界。二句曲言即使心灵超脱到能飞空看到庄严美满的圆月,现实的严酷早已让人忍受到忍无可忍的地步。尾联再借佛典,言即使是放下世间一切恩怨区别的“世尊”(佛祖释迦牟尼)对世事民情也仍是不能不动心的,用以喻自身不能忘却现实家国之苦难,民生之多艰。诗中饱含着忧时念乱的爱国之情与报国无力的悲慨,读之使人心情沉重。此时,药堂翁尚未任伪职,弟子引师为知己,以沉痛语向老师吐露心曲,故以此“有感”一诗呈上。
“元日有感”一诗之前不久,顾随填过一首《鹧鸪天》:
不是新来怯凭栏,小红楼外万重山。
自添沉水烧新篆,一任罗衣透体寒。
凝泪眼,画眉弯。更翻旧谱待君看。
黄河尚有澄清日,不信相逢尔许难。
他以词所独有的婉约要眇的特质,把家国伤痛与坚贞心志抒写得既幽微又明澈。再如与这首“元日有感”几乎同时的一首《临江仙》之下片:
极目江湖满地,遥天一发青山。春风何日约重还。好将双翠袖,倚竹耐天寒。
词中化用苏轼词句、杜甫诗句,抒写期盼收复失地、河山一统的心志。这些词作,都可说是对这首七律题中“有感”二字的注脚。
从以上六首诗可知,顾随与周作人这一对师生,到1939年初仍然保持着亲密的交往。顾随自1934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兼课,止于“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但他与老师周作人的交往并不是止于1937年末,而是直到1939年9月,周作人开始执掌日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的教务及其他伪职,而顾随坚持民族操守,拒绝到伪北大任课的聘书,师生二人的交往方日渐疏远以至几乎极少再有直接的往还。由此似可视此六首呈“药堂翁”之作是现今所见周、顾二人亲近交往的最后记录。
新发现的顾随佚诗六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自有其意义,故此笔者不避浅薄甚至疏误,作了如上的解读,只期引起学界对顾随佚诗的关注,且就正于方家与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