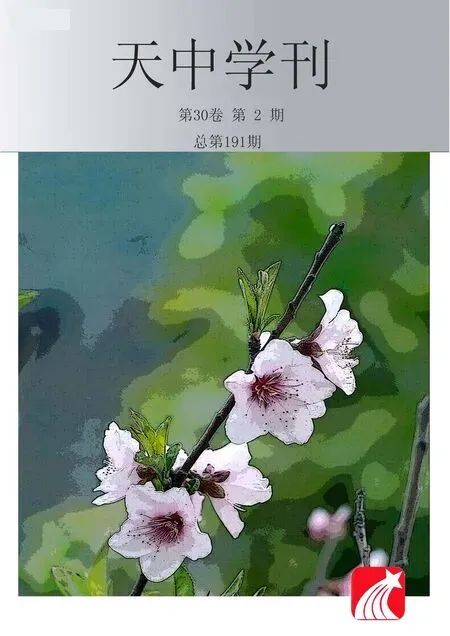笛卡尔哲学难题的种种求解方案及现代启示
朱荣英
笛卡尔哲学难题的种种求解方案及现代启示
朱荣英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开封 475001)
为破解笛卡尔身心两离又内在统一的哲学难题,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曾做了种种试解,但最终倒向了唯心主义而只在主观观念中实现了身心统一。现代经验论对这一求解感到失望,而试图将精神的因素归结为物质的因素予以求解,即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来消除形而上学弊病,但因语言的固定界限而窒息了思想的内在活力。因此,现代存在论主张通过实现语言学转向以突破语言的逻辑限制,在生存命义中找到一条破解笛卡尔难题的可能路径。然而,将“此在”视作语言性的诗意存在,仅为求解这一难题找到一种虚幻可能而非可行之策。在语言学范围内,笛卡尔哲学难题是无解的,只有诉诸马克思实践观,这一难题才有望得到科学解决。
笛卡尔;哲学难题;求解方案;理性启示
在近代西方哲学中,认识论问题是最基本的问题,也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不仅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而且曾经长时段地占据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地位,是近代哲人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它追求世界的内在统一性、致思世界本源的背后,深藏着为人类一切知识体系奠基的理性奢望与思想动机,这是因为它与人类的终极关怀内在相关,是与人的存在意义性命攸关的难题。致思世界本体获得统一的认识论依据,具有丰富的内涵、广阔的疆域、抽象的思辨和宏阔的玄想,是其他任何哲学问题所不能比拟的,构成了近代西方哲学思维中最复杂、最令人困惑、也最具有理性魅力的哲学难题。本文不避浅拙,愿从近、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主题的多重变奏入手,以历史与现实视界交融的方式,采取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从古今中西历史大视域出发,尽可能系统地展现笛卡尔哲学难题及其种种求解方案带给我们的理性启示,以期能够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与深入思考。
一、近代哲学转向与笛卡尔哲学难题的生成 本体论曾经是古代西方哲学的核心,作为最亮的动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视作一切科学体系和文化门类的最终基础和内在根据。它通常是关于宇宙万物最普遍、最一般、最根本、最高的根据和基础的知识体系,在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中,形成了一道十分奇特的文化景观。只是在受到了怀疑主义的挑战、质疑和诘难后,哲学界才开启了它的认识论转向。本体论问题虽然历史悠久、难以克服,但它的基本概念却不够清晰,始终未能达到一般的确定性,哲人们在世界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以及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研究它的问题上,始终没有达成最起码的共识。本体论问题显然不是孤零零的一个问题,而是一组或者一系列的问题,它构成了一个有内在联系的问题域,比如:万物流变的基础是什么,究竟有没有永恒不变的存在本质,宇宙万物统一的根据或者基础是什么,整个世界统一的规律和秩序是什么,人类有没有能力认识它又该怎样去认识它,等等。古代本体论关心的核心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世界存在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从巴门尼德对“在”与“在者”的划分到苏格拉底对“概念”问题的追问,从柏拉图对“理念”及其等级的把握到亚里士多德对“实体”性质的分析,他们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一致的,这就是通过思想来把握存在,试图通过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来把握世界万物的本质。但在如何把握存在的本质和世界的本源这一问题上,他们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致思方式的进一步转换,在古代哲人那里,从以存在为对象的存在论研究逐渐演变成了以存在的意义为对象的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主客二分、形上致思的研究方式与方法,成为古代西方哲学史的主流导向。蒋春猪高兴得叫起来,皇上起用元帅,嫂子又有喜了,元帅,你这是双喜临门!跟着,他说,我要把双拐扔了,随元帅杀敌去! 诚然,在古代哲学的本体论中,囿于其主客二分思维方式的局限,在某种程度上,尚没有将思维与存在严格区别开来,哲人们相信事物就像我们所思想的那样。此时,认识论是不发达的,知识的可能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是直接呈现在思想中的,主客体的统一也是无须论证的,但是这种统一不是经过认识论论证后的自觉统一,而是在思想中实现的自然的混一。“他们大多是武断地宣称本原是什么,至于知识的可能性等问题则尚未进入他们的视野。”[1]142但是,即便如此,它仍然遭遇到了怀疑主义对它的挑战、质疑和诘难。在怀疑主义者看来,古代本体论在未考察人类的认识能力之前,就武断地宣称事物的本质就像它所直接呈现的那样或者不像它所呈现的那样,并武断地宣称人们能够获得关于外在世界之本质的确定性的知识,而且认定人们的知识是具有绝对真理性的最高知识。怀疑主义者的挑战、质疑和诘难,显然击中了古代本体论的致命缺陷,犹如一种思想的“清醒剂”,要求后来的哲学家必须为本体论提供认识论的理性支持,必须具备敢于面对问题的勇气和探索的精神,以便为重建形而上学的基础做出重新思考。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不断深化和发展,近代哲学家们逐步意识到了我们所认识到的事物和事物自身可能是不一样的,从而开始了深入分析知识的内在根据和我们的认识能力,并把认识主体确立为认识的逻辑前提。可见,本体论必须以认识论为基础,世界本质的规定及其最高基础的描述必须依赖于人们的认识活动和理论建构,以便从认识上说明其选定的认识对象是能够为我们所认识的,我们的确具有相应的认识能力以通达这种对象,当然也需要从逻辑学的角度形成关于外部世界及其本质的知识体系。应该说,笛卡尔哲学就是基于这种思想变革的实际需要而产生的,他响应理性发展所需并挺立时代潮头,在经院哲学的废墟上试图为人类重建理性根据。 作为近代哲学奠基者和唯理论创始人的笛卡尔,对二元实体进行了缜密思考,认为哲学作为一切知识体系的基础必须是从一个清楚明白、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推演出来的严密的科学体系。它从普遍怀疑的立场出发,要求对一切知识采取怀疑的态度,只接受那种被理性明确认定是真实的东西,将一切可疑的东西暂时搁置起来,为形而上学寻求那种无可置疑的基本原则。在笛卡尔看来,当我们对一切知识实施普遍怀疑的时候,唯一不能怀疑的就是“我在怀疑”这一活动本身,即“我思故我在”。以“我思”而非“存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基础,这的确开启了认识论上的一场革命,将蕴含于本体论背后的主体性因素凸现出来,为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奠定了统一的理性基础。笛卡尔的心灵观彰显了人类理性的至上性,高扬了人类的主体性原则,他认为人类理性能够摆脱一切偏见与传统束缚而给我们提供绝对可靠的方法,进而为一切知识体系奠基。 然而,笛卡尔哲学又是一种典型的二元论哲学,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包含着不可靠的理性缺失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面临诸多的理论困境[2]。他一方面认为,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和变化,都严格服从于机械运动的规律,自然界完全是一个必然的领域;另一方面又认为,在此之外,还存在一个自由自觉的领域,即人类的灵魂、心灵或者意识。他裂世界为二,一是自由的精神世界,一是必然的自然世界。这样,必然和自由就处于彼此悖反之中,身心也处于二元对立之中。身心本质上是不同的,但实际上又是内在统一的。本质不同的东西如何获得内在统一,这就是笛卡尔哲学的难题。对此,笛卡尔做出了如下几方面的论证:他提出了“自然信念”理论,借无限完满的上帝之手试图实现身心的统一;他提出了“重力比喻”理论,重力与物体的结合是整体性的,重力的这些特征能够为我们解释身心一致提供一个恰当的类比,表明身心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犹如重力和物体是密不可分的一样;他又提出了“神经网”理论,认为神经如同一张网,散布全身,它是身心统一的媒介,身心正是通过它而实现相互作用和内在统一的;另外他还提出“松果腺”理论,认为身心的结合来自于大脑最深处的松果腺,它位于大脑实体中间的某个非常细小的腺体,它把悬在身体上的某种元气从前腔流到后腔,从而实现了身心交感。可见,笛卡尔对身心统一的论证不仅是牵强附会的,而且是毫无根据的,身心关系问题成为笛卡尔哲学中不可解决的一个难题。为了加深对英语词汇的理解,必须了解其所对应的文化背景,而许多单词正是经由希腊罗马神话才进入英语词汇库。神话所引申出来的词汇可分为普通词汇与专业术语,前者多与神、英雄、鬼怪等名称有关,可利用其隐喻特征引申并拓展词义。例如含义为长期艰辛的旅途odessay,这一单词就是由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奥德修斯Oldysseus衍生而来,并且1月(January)和3月(March)也来自于神话故事中的两面神janus和战神mars。专业术语与自然科学有关,例如在天文学中许多星体的名称都是由神话故事而来,故事中的战神和爱与美之神分别对应的是火星Mars和金Venus。
二、笛卡尔哲学难题的近代求解方案及其理论缺陷 笛卡尔身后的近代哲学家,不论是经验论者抑或唯理论者,为消解他的身心二元的哲学难题,都曾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近代的唯理论者如斯宾诺莎,认为笛卡尔曾经将“实体”归结为并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事物的存在就能自己独立存在的东西。但是,斯宾诺莎所说的上帝、心灵和物体,没有一个不是与实体的定义自相矛盾的。为消解这种二元对立,他曾经提出实体一元论来取缔笛卡尔的二元论。由于他的一元性的实体中又保留着两个相互对立的属性(思维与广延),实际上并没有克服二元论,而是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身心平行论,或者是身心两面论[3]。斯宾诺莎的“实体自因”理论认为,实体是在自身内并通过自身而被认识的东西,实体独立自存,自己生成自己,自己说明自己。这种实体就是“神”,宇宙间只有“神”这一个实体,一切事物都存在于“神”之内,都依赖于“神”而存在,凭借着“神”而显现意义。“神”是万物的内因,万物都预先为“神”的绝对本性与无限力量所决定,“神”的意志或者力量造就了万事万物的存在法则及发展规律。显而易见,斯宾诺莎试图通过将笛卡尔的思想与广延降低为同一个实体的两种基本属性的方式,来化解他的身心二元矛盾。思维与广延是实体的本质属性,二者在思想上是同一的,“观念里的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与联系”是相同的。凡是在知性中把握的实体的本质属性都隶属于实体自身,思想的实体与广延的实体都隶属于同一个实体,不仅思维与广延完全等同,而且实体的属性与实体自身也完全等同。思维与广延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是同一个实体的两个不同属性,它们都内在地表现了实体的本质,只是表现方式不同罢了,思维中的东西与广延中的东西内在一致。这样,表面上精神实体的一元论就取缔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但是,思维与广延毕竟性质不同,既互相对立又互相限制。又由于斯宾诺莎坚持不同性质的东西不能相互影响,思维与广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不能调和。虽然他把这种身心二元称为身心平行或者身心同时发生,但是仍然存在二元论的思想残余。图4示出冷源放热温度TL随负荷增加而单调增大,热源吸热温度TH随负荷增加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冷源放热温度TL为46~73℃,平均值为59.2℃。热源吸热温度TH为267~543 ℃,平均值为379.2 ℃。 再如另一位唯理论者莱布尼茨,在他看来,实体作为万事万物的本质,必须具有不可分的单纯性和内在的统一性,绝不可能是二元对立的;必须是在其自身之内就具有能动性和自因性,是自己保证自己的统一,而绝不可能依靠外在的原因而实现统一。这样的实体就是精神性的“单子”,它是客观存在的、无限多的、非物质的、能动的精神因子,构成了万事万物的灵魂与内在目的。这种单纯的精神实体具有知觉和表象的能力,由于各种“单子”的知觉力与表象力不同,“单子”间存在着质的差别,这构成了“单子”的等级系列。整个宇宙就在“单子”中,世界就是各种“单子”相互联系的总体,从无意识的植物“单子”到人的理性的灵魂“单子”,又到全能全善的上帝的“太上单子”。他认为,上帝是最完满的“单子”,一切事物皆为之所造。上帝在创造每一个“单子”时就预见到了它们的全部发展状况,预先安排好了各种不同“单子”的和谐一致与内在联系,就如美妙的交响乐,整个宇宙就是“单子”们的和谐演奏。由此出发,莱布尼茨批判了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或者平行论,认为上帝造就了身心“单子”的前定的和谐。灵魂与身体虽然各自都遵守着自己的独特规律而行事,但是它们并不是彼此两离的,它们在上帝的召唤中又会合在一起,上帝使一切“单子”保持和谐一致,一切“单子”也自然是对同一个上帝的表象。精神性的“单子”一元论,实际上并没有克服笛卡尔的二元论,因为这种“单子”理论认为自然从来不飞跃,物质是一片死物,身心、心物仍然是对立的,只不过一切灵动都来自上帝,一切变化与同一都是上帝预定的,上帝使得万物存在又保持同一,这又背离了实体自因的基本规定。 与唯理论者在方法上有别,近代的经验论者洛克认为,人们得到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都是外部事物在心灵上留下的痕迹,即观念。所谓上帝及其天赋观念等说法,只是心灵的虚构,根本不是真实可靠的。心灵在自身中知觉到的东西就是观念,那种在我们心灵中产生观念的能力就是主体性。事物的性质与在心灵中产生的观念,既是互相区别的又是互相对应的。事物的第一性质如运动、体积、形象等,不论为我们知觉与否,它都为事物本身所固有,是事物的原始性质。事物的第二性质如色、香、声、味,并非真实存在,而是第一性质的变形。这两种性质都能在心灵中产生观念,第一性质的观念是真实的,而第二性质的观念纯粹是主观反映,并不存在与之对应的客观原像。这样,受笛卡尔影响,洛克认为存在着三种实体观念:“感觉”使我们相信有广延的物质实体,“反省”使我们相信有能思的心灵实体,“追求完满”使我们相信有神明的上帝实体。然而与笛卡尔不同,洛克认为这些实体不过是主观的产物,不过是心灵的组合而已,并非真实地存在于人的心灵之外。对此,另一位唯心主义经验论者巴克莱说得就更明确、更彻底。在巴克莱看来,观念只能与观念相似,本质不同的东西是不能相互结合的,观念不可能与存在于心外的物质交感,物之所以被感知,是因为它原本就是观念。笛卡尔的身心、心物二分的做法是错误的,洛克的两种性质的区分也没有道理,因为对象与感觉原本是一个东西,一个观念与感知到另一个观念其实也是一回事。观念的存在就在于被感知,一切实体存在与否及如何存在,都依赖于感知它的某种心灵实体,在心灵实体之外根本不存在所谓的物质实体。物纯粹是观念的复合,在观念中不存在身心二元、心物二分,唯物主义所说的“物质”纯粹是一种虚假意识,物质实体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是最抽象、最不可思议的东西。这样,他就以观念的一元论克服了身心二元论,主客体在主观观念内部实现了统一。这种唯灵论与唯我论的主张,其实也不能克服笛卡尔的哲学难题。中西哲学属于两种不同的心灵哲学,“同样重视心灵,同样讲心灵哲学,但是中西方着眼点不同,发展趋向也不同”[4]69,中国心灵哲学中的主客交感实现得很自然,而西方哲学就显得牵强附会。因为,西方哲学的心灵向度是自相矛盾的,既然本质不同的身心、心物不可能交互作用,它又如何在人的心灵中引发观念呢,只能感知观念而不能感知事物,那观念又来自何处呢,感知不到的东西就真的不存在吗,观念复合出来的东西就一定不是虚妄的吗?可见,在纯粹经验论内部,由于其自身的缺陷,笛卡尔的哲学难题仍得不到解决。
三、现代经验论者对笛卡尔哲学难题的求解及其理性困惑 现代经验论者对近代哲学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种种求解方案感到失望,不满足于在主观观念中实现身心统一、心物不二。他们认为,在纯粹的精神领域特别是借助上帝所实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根本不能解决笛卡尔的哲学疑难;解决问题的路径,不是将物质的东西归结为精神的或者观念的东西,把物等同于观念,让主观心灵吞噬一切,而是将精神因素归结为物质因素,从而获得主客体的统一。易言之,不是把物质实体归结为精神,用心灵吞没一切外在事物,使一切都依赖于主体的心灵而存在,而是把心灵、意识归结为物质的属性或者功能,把人的心灵的各种活动直接混同于人的身体的机械运动。这实际上是以身体的机械活动吞没了主观的心灵活动,身心矛盾在机械唯物论的立场上获得了统一。现代经验主义哲学的分析学派自始至终都坚持着这种解决方法,“出现了形形色色的理论,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了‘唯物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倾向,即把精神现象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现象,以此来消解笛卡尔的二元论问题”[5]103思潮。为消解笛卡尔身心二元的哲学难题,他们更是把精神现象直接视作一种特殊的物质现象,试图把精神实体消融于物质实体中,以物质实体吞没精神实体,对心灵及其功能作机械唯物主义的理解。这看似唯物性很强,实际上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求解方案,几乎在整个现代经验论的分析哲学论坛上一度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经验论者尤其是分析学派的哲学家们,对笛卡尔哲学难题的求解不再诉诸纯粹的理性抑或经验,不再探讨身心究竟谁是真的存在及如何存在的问题,也不再考虑能不能认识及如何去认识身心关系的问题,而是关心语言能不能及如何描述二者关系的问题,身心及其关系抑或只是语言的构造,语言所描述的存在就是我们认识的界限,一切存在及其意义都依赖于语言的表征,在语言中根本不是二元的而是内在统一的,这就是“所谓的‘语言学的转向’”,它“把语言问题放在首要地位,甚至把全部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把哲学的全部方法归结为语义分析[6]241−242。 比如,卡尔纳普认为,笛卡尔哲学之所以会导致二元论谬误,关键的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在经验上抑或在理性上是如何断定认识对象的,也不在于我们有没有及有什么样的认识能力去通达对象,而在于我们的语言对世界对象的描述出了问题。笛卡尔的身心二元或者心物两离,完全是用语错误导致的,如果使用一种清晰明白的、统一的科学语言去表述对象,就不会出现二元论的谬误。在他看来,如果用物理主义及其方法,就能够对认识对象做出绝对完全的科学描述,因为物理语言是一种普遍性的科学语言,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件、身心经历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用物理语言来描述,心灵中闪现的每一个观念、每一个心理学的命题,也都可以转译为仅仅包含物理语言的科学表述。物理语言的客观性、主体间性和普遍性,确保了我们在运用它描述一切事件时避免二元论错误。一切心理事件都可以翻译成用时空坐标来表示的物理事件,一切生理的抑或心理的活动都可以归结为身体中发生的物理现象,人的一切心理情绪与表情都可以翻译成用物理语言来表达的、可观察的物理行为。这样,心理的东西、主观的观念就都变成了物理的东西,笛卡尔的心物二元对立就不存在了,其哲学难题也就自然消解了。 又如,日常语言学派的赖尔认为,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身心不一的错误,完全是一种语言学上的弊病,纯粹是一种范畴错误,即他把主观的观念摆放在了不包括它的逻辑类型中去了。真正发生的一切,只有物理现象、物理事件与物理过程,一切表面上关于精神的、心灵的活动的叙述,其实都是关于身体行为的叙述,根本不存在只有本人才能感知的隐秘的内心世界,一切精神现象都可以归属为物理现象。笛卡尔二元论的错误就在于在身体的活动之外去寻找精神的活动,把精神及其活动看成是不同于身体及其活动的东西,认为精神是存在的、唯一真实的活动。其实,只有身体的物理活动和生理行为,若把心、心灵、精神放置在并不包括它的物理范畴中,自然就会出现二元论的谬论了。可见,并不存在精神的东西,人们用于表达精神行为的那些概念只是指精神活动,而这种活动完全可以转译成身体的物理事件。正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才使我们认识到人们具有某种心理属性,心灵的精神活动绝不是什么神秘的私人性活动,而是可以观察的物理行为。笛卡尔二元论的错误就在于将精神的概念视作精神的实体,将精神性的活动和物理的活动看作并行不悖的两种活动,将精神与物质看作世界共同的本源,其实世界只是物质的一元性世界,行为只是物理的一种行为,语言也只是统一而科学的物理语言而已。在笔者看来,这种语言学上的分析看似科学,其实其缺陷是明显的,它否定了人的内部经验、心理感受,根本否认精神活动的私人性、本己性,不承认有精神现象的存在,不承认人的意识经验的实在性,将精神活动作机械化的物理性处理,抹杀了人与物的本质区别。The parameters of the instrument can be set up uniformly, and the number of teachers that need are reduced. 再如,澳大利亚的哲人阿姆斯特朗认为,人的心理状态就是大脑的生理状态,每一种心理状态、精神现象和心理活动过程,就其实质看来,其实完全等同于一种大脑神经系统中的生理状态、生理现象和生理活动过程。一切精神的现象、心理的活动与心灵的感知,都可以还原为身体的生理行为、物理事件与物质现象。在大脑的神经中枢系统的工作原理上,身心与心物都是大同的。他分析说,心、精神、心理状态完全等同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大脑神经系统的活动纯粹是一种物质性的活动,一切心理行为完全可以根据这一神经系统中的事件来表达。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神性的对象,在大脑的神经中枢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物理学的事件,没有非物质的东西,一切心灵活动及其精神事件的唯一性质就是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所承认的那些物质性的东西。心灵不过是物质性的大脑功能之有机形式的一种特殊排列罢了,精神不是一种非物质的东西而是物质的大脑及其派生物,心灵状态等于脑神经中枢的运转状态,心理状态及其运动过程其实就是物质性的大脑的工作原理,二者在生理机理上完全是同一的,二者在物质性的实质上也是完全等同的。在阿姆斯特朗看来,神经中枢上的统一性消解了二元性悖论,身心问题被消解成为一个科学的细节问题,神经生理学完全可以对笛卡尔哲学难题的求解提供正确的方案,心物一体、身心合一就都得到了论证,笛卡尔的二元论的哲学难题就不攻自破了。对此,在笔者看来,笛卡尔的二元论是消除了,但是精神领域里一切奇妙的思维之花却被机械性的生理学一笔勾销了,神经系统的同质性解释将五彩斑斓的精神世界化为乌有了,以此实现的心物一体与身心合一,在哲学上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倒退[7]。
四、现代语言哲学对笛卡尔哲学难题的破解及其内在局限 总的看来,现代分析哲学所开辟的语言学转向,毕竟探求了哲学研究的新途径,但是通过语言分析来消除笛卡尔难题又的确具有多种局限性:将理性认识的界限转化为语言学的界限,窒息了语言的内在活力。语言的确可以有不同的功用,能够表达不同的对象和问题,但由于哲学领域与生活领域毕竟存在本质的差别,适用于生活领域的语言究竟能否成功地运用于哲学领域就成了一个问题。如果用同一种语言同时表述本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中的问题,就会造成语义混乱,产生像传统笛卡尔哲学难题那样的理性悖论。从笛卡尔哲学难题诞生之日起,就有人不断质疑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再三追问形上理性究竟能否使用日常语言来通达哲学的对象。其实,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形而上学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常语言能否通达对象的问题,更重要的在于,形而上学的对象究竟是真的存在抑或仅仅是语言的产物。“语言使人与世界相通相融,语言开启了世界,建构了世界,或者说,世界由语言而敞开、而有意义。”[8]194换言之,哲学所把握的世界并非真的存在,而只是语言的一种特殊构造。在西方语言的形成过程中,由于其特殊的颠倒功能,原本没有任何意义的“存在”本身却成了哲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存在”究竟是独立存在的对象抑或只是一种语言的现象?在一些人看来,以“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不过是哲学语言的误用罢了。因为“存在”只是联结概念之间的系词,它本身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以之为对象进行哲学思考,纯粹是“乌托邦”的虚假营造。“存在”概念在语言中的产生是一回事,我们用它来表征某种对象的存在完全是另一回事,无论“存在”概念产生时具有多么明显的语言学因素,都不妨碍我们运用这一概念去表达另外的一种意义。所以,“存在”的语言学悖论,并不能证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无意义性。在康德看来,思维与存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存在并不表述事物的任何属性,当我们说某物存在时,并不能由此说明确实有某物存在[9]。“存在”仅仅是在语句中起连接作用的系词,它并不实际指称某种事物,把“存在”加诸事物上并对之进行言说,丝毫不能为它添加任何新的属性或内容。要断定一种事物具有某种属性,必须有经验上的依据,而与语言上的表述方式无缘。他的这一思想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将“存在”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并将它看作是语言的构造,的确可以消除形上理性的虚幻性。这虽说是一种最方便快捷的方法,然而却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说我们生活在语言之中,并被语言所包围,那就意味着任何语言现象都有可能被我们赋予新的意义,从而成为我们认识或者考察的对象。 通过语言分析来消除笛卡尔难题的确具有多种局限性,然而它毕竟开辟了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新途径。在古代和近代哲学那里,表述某种对象的语言与语言所表述的对象之间似乎是没有区别的,至少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区别。就此而论,现代分析哲学所开辟的语言学转向,的确功莫大焉。现代分析哲学学者将理性批判转化为语言批判,将理性认识的界限转化为语言学的界限,旨在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来说明哲学所把握的世界实际上是语言所及的世界。因而,人的语言就是世界的界限,世界就存在于语言之中,在这个界限之内,一切都是可以言说的,说出来人们也能够听得懂;而超出这个界限,一切都不可言说,人们只能保持沉默。哲学家从普遍关注本体的存在和关注通达这一本体认识能力,转化成了普遍关注人们的语言及其误用的问题,语义分析成为哲学研究的唯一主题。分析哲学认为,形而上学的错误乃在于对语言的误用,当它诉诸语言去表达存在的时候,实际上谈不上真假对错,因为它根本没有实际意义,它所言及的存在实际上只是一种主观虚构,根本没有实际的对应物。当然,在分析哲学家内部也有细微的差别,其中逻辑学派认为日常语言是有缺陷的,它经常掩盖了语言本质的逻辑形式,形而上学这种乌托邦的东西就是由此而来的;而日常分析学派则认为,日常语言并没有缺陷,在日常语言中意义得到了直接呈现,不会造成误解,形而上学问题的产生恰恰是由于人们使用日常语言的错误方式造成的。尽管它们有差别,但拒斥形而上学的立场是一致的,正如维特根施坦所说,能够说的就要说清楚,不能说的就要保持沉默,语言是银,沉默是金。可见,分析学派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不在于通过调适哲学的把握方式而拯救或者重建形而上学,也不在于为通达世界本体探寻认识通道,而在于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而为思想划定界限,以此来求解笛卡尔难题。在它看来,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换言之,世界只在语言所及的范围之内,整个世界都停留在语言之中,语言所及之外的东西根本没有任何意义。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我们弄清了语言的界限,知道了什么是可说的、什么是不可说的,我们只能说可说的,说不可说是做不到的。笛卡尔难题的产生就在于哲人们总是僭越语言界限,试图言说那种不可说的东西。有的哲学家对此虽采取宽容立场,认为形而上学不过是一种纯粹的本体论承诺,但它所言及的存在,只是在哲学中得到了一种言谈,而并非实有此物,只不过是在理论上一种有用的假设罢了。 现代分析哲学试图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消除笛卡尔哲学的错误,的确是有意义的探索,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一定说服力,有助于我们澄清形而上学命题中所蕴含的许多逻辑错误。但它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消解形而上学的所有问题,更不可能彻底颠覆形而上学的把握方式。他们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确让我们看到了语言自有语言的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能设想语言界限之外仍然有物存在,而且这种设想也并不像分析哲学所说的那样根本无足轻重,实际上它很可能比分析哲学本身更重要。对分析哲学而言,只有一种存在,那就是语言所及的存在,语言的界限就是存在的界限,一切事物只能存在于语言中,语言之外的东西根本无法想象。这就导致了“语言的唯我论”,“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界限”[10]130,反过来也一样。但是分析哲学也有它内在的局限,其错误在于把语言和存在混同,语言的界限只是表明了总有语言所不能企及的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语言不能企及的东西就真的不存在。由于分析哲学学者过于强调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的重要性,试图通过对语言弊病的克服来消除形而上学,但实际上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特别是他们过于强调语言的纯洁性,不但缩小了语言的范围,而且缩小了思想的范围。如果我们把语言仅仅理解为如此纯洁的科学语言,那么形而上学也完全有理由认为思想的领域比语言的范围更宽泛,乌托邦性的本体论仍然可以找到它的栖身之地。可见,分析哲学对笛卡尔难题的批判也有过于偏颇之嫌,在对语言进行逻辑净化的同时,也缩小了语言使用的合法范围,从语言逻辑形式的角度限制或者窒息了人类语言自身的内在活力,从而也缩小了人类认识的思想领域,将自己局限在逻辑分析这一狭小天地,使得语言学转向陷入作茧自缚。(1) 因建筑物本身对信号的屏蔽和吸收作用,导致无线电波较大的传输衰耗,从而产生移动通信信号的弱场强区和盲区。通过室内覆盖系统,实现室内信号的准确覆盖。
五、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对笛卡尔哲学难题的破解及其弊病 与现代分析哲学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根治语言弊病并以此破除笛卡尔难题的目的不同,现代存在论学派所实现的语言学转向的根本目的,不在于把哲学的全部工作仅仅局限在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这一狭小的天地,而恰恰在于试图突破语言的逻辑工具性的限制,发现语言在成为逻辑工具之前就已经与人的存在及其本质保持着一种原发性的相属关系,弄清语言与存在的这一原始关联,旨在找到一条揭示身心合一及世界和人的存在意义的可能路径。在现代存在论者看来,通过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证明了形而上学作为科学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形而上学问题本身的无价值性,实际上正是因为妄图实现形而上学的科学化才导致它陷入歧途。与分析学派通过逻辑清扫以破解笛卡尔难题的道路不同,存在论学派试图通过深入挖掘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原始关联”,使哲学的运思重归早已被传统形而上学遗忘了的存在视域,以此实现身心融合[11]。在存在论者看来,现代语言分析学派的失误并不在于它的问题和对象没有意义,而在于它试图利用某种科学方法达到对存在的言谈。当它从本体论上承诺有物存在的时候,由于它忽略了“在”与“在者”的区别,因而自始至终就处在对“在”的遗忘之中,其哲学史就是“在”的遗忘史,所以有必要重提存在哲学问题,真正将语言与存在的关系提升到本体论的高度予以把握,以便能够深入人的基础存在领域实现对人的意义的领会。“在”和“在者”是有差别的,一切“在者”皆因存在而在,而“在”总是“在者”的在。如果我们试图追问存在的意义问题,那就必须找到这样一个“在者”,它能够对它的存在发问并与它的存在保持某种内在的相属关系,即通过言谈、解释和领会来直接展示存在的意义。这种“在者”就是我们向来所肯定的“此在”,其根本用意在于表明人是通过生存活动来展现自己的人生意义的。简言之,意义是人自己“在”出来的,是自我的生存活动开拓出来的。“此在”的生存活动是存在得以开展出来的基础领域,是人的本质和意义的展露口,“此在”的存在就是通过人的生存活动而奋力开拓出来的。由于人对自己存在的理解内在地规定着他的存在样态,因此,人的存在与人的语言就处在原发性的相属关系中,语言与存在结下了不解之缘,语言也就成了人的存在的本质。对于存在论者来说,语言在本质上不仅仅是人与人相互交流的工具,而是与人的存在本质具有内在关联的一种东西,因而语言就具有了基础本体论的意义。 “此在”对人生意义的开拓和对存在本质的展示,分为三个相互渗透的环节:情绪、理解、言说。“此在”作为“可能之在”,由于面对诸多存在的可能性,所以它自始至终都承载着生存的重负。在作为现身情态的情绪中,“此在”之“在”就处于被抛状态,即人生在世,就被抛入多种存在的可能性之中。既然“此在”是“可能之在”,“此在”对它的存在意义和本质就总有理解和筹划。它如何理解自己的存在,它就怎样存在,“此在”对存在的理解,实际上就规定着它的真实存在。解释就是对理解的展开,也是对生存情态的一种展现。“人的存在基于语言”,而且“语言的真正本质,即它实际上规定了我们存在的可能性”[12]379。语言在“此在”的展开状态中,有其内在根源,从存在论的意义上来说,语言根源于言说,而言说乃是存在论意义上的语言,是对多种可能性的存在的一种谋划,言说内在地牵连出人的存在本质和意义。所以,语言并不是附加在人身上的外在功能,而是作为“此在”的人展开自身、生成自身、成就自身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可见,语言与存在具有内在的关联,它意味着“此在”这种存在者是以解释世界意义、人的本质的方式存在的。这样,语言在存在论哲学那里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为了真切地把握语言的存在本质,就必须从现代分析学派的逻辑桎梏中解放出来。当从生存论入手揭示“此在”的存在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从根本上颠覆了语言分析学派关于“在”与“在者”的划分。对于生存论者来说,所有一切存在着的东西实际上原本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它们是以潜在的方式存在着,即“可能之在”。这里的“此在”是一种动词,即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展示自己的存在本质。已经定型的存在并不是“在”而只是“在者”,存在之为存在就在于它的自我显现,就在于它能够“去存在”。唯有“此在”作为一种非现成性的、永无定型的、开放性的存在,才能对自己的本质进行筹划。所以,现代存在论学派实现语言学转向的目的,就在于使“此在”摆脱自己已经凝固化为现成存在这种非本真的生存状态,而本真地开拓出自己的在世状态,义无反顾地去开展自己的存在可能性。“此在”与语言处于原发构成的相属关系中,“此在”因存在而存在,而“此在”在生存中显现本真的存在,故“此在”就担负着使人获得本真生存、显现自我真意的使命。简言之,只有“此在”才能以可能之在的本真方式存在着,无论它如何生存,都是对存在意义的一种显现。 在现代生存论者中,海德格尔放弃了通过“此在”来破解笛卡尔难题的道路,而试图直接通过语言的揭示作用来开启哲学新图。在其本体论上,语言对本质的开启作用就得到了特别的发挥,以至于他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人必须首先聆听然后才能言谈,语言不是人的发明,不是人说话,而是语言自己说话,唯有当存在言说时,人才真正成为其人。语言是人的存在的栖身之地,人栖居在语言所构筑的家园之中,哲人们就是通过自己的言说而使存在的本质得以开敞,人的生存真意就保存在自己的语言中,哲人们的看守实际上是对人的存在本质的敞亮。语言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揭示和敞亮,因此,语言便与存在保持着一种特殊的始源关系。“语言不仅是‘存在之家’”,也是存在的庇护所,“在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没有语言,存在无从开敞,语言将人带入是其所是之地,“语言是有生命的,它蕴涵着存在与生存的深层缘构”[13]288−289。那么什么样的语言才是真正具有原发意义的语言呢?在海德格尔看来,是一种诗性的语言。人诗意地栖居,诗人由语言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丰富性所牵引,聆听应和这种本然所思的语言,就存在着的本然所是将存在者的本质由晦暗带进险要之地,让世界万物向我们展示它的意义。 在某种意义上说,分析学派强调划清语言的界限,试图运用逻辑分析消除形而上学,而存在学派则致力于突破科学语言的逻辑界限,实现对人的生存本质的敞亮。二者同样把人的存在看作是一种语言性的存在,人的世界也就是语言所及的世界,但是他们对语言世界的理解是不相同的。语言不仅仅是思想交流的手段和工具,而是人的存在真意的自我显现的展露平台,所以,人因为拥有语言而成为本真的存在者。这种分析对以后的哲学走向影响深远,其意义无论怎么样估计都不会过分。但是,在我们看来,本体论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仅仅归结为语言学问题,因为语言学虽然是研究本体论的基本方面,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或前提,但是如果我们把本体论问题完全限制在语言学范围之内,那就完全本末倒置,也就丧失了人类理性追问形而上学的根本目的和意义。尽管语言学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澄清笛卡尔哲学难题,甚至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一难题的基本维度,但它毕竟不是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解决,在语言学范围之内,这个难题始终是无解的,只有诉诸马克思的科学实践观,这个问题才有望得到科学的解决。孢子悬浮液制备:将摇培获得的悬浮液用纱布过滤去除菌丝后,镜检测定孢子液浓度,并采用无菌水将孢子悬浮液浓度调节至试验所需即可。
六、笛卡尔哲学难题的种种求解方案带给我们的理性启示 西方哲学在学理上所揭示的笛卡尔哲学难题及其求解方法,能给我们带来很深刻的理性启示。 在西方近代哲学中,作为唯理论与理性至上主义的开创者,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普遍怀疑方法,开辟了近代哲学推崇人的主体性原则的新视域,引导了哲学由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将理性的至上性与主体的能动性第一次凸显出来,其理论意义的重要性和实际影响的久远性是不言而喻的[14]。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精神的“我思”给予能动性的解释,为人们提供了第一个通达世界本体的认识通道与理性支点,而且他提出的哲学难题也构成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交汇点、近代思维与现代思维的会通处。他对认识对象的二元划分、主客两离以及他的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引起了哲学史上诸多哲学家的竞相研讨,使得各个哲学派别对这个问题都必须首先做出回答,对这个问题的求解内在地构成了近、现代哲学的全部意义。尤其是他对心身二元关系问题及其理性困惑的分析,以表象论为基础的认识难题的追问,更是成为他身后的哲学派别无法绕开的理论怪圈,以至于成为把握西方哲学史研究主题多次转换的一条总线索,成就了一个个以唯心主义方法研究认识论、语言学、存在论的哲学体系。他把世界万物统一于主体性的精神内部,以主体性的“我思”统摄一切自然本体,通过消除本体的这种外在形式而赋予心灵以无限的能动性,从而揭示了在灵魂中人如何借助上帝的召唤而将心物与身心内在统一起来,将思维作为自我的本质,进而又将自我变成了精神实体,这一切的确开了西方哲学以唯心主义研究身心关系问题之先河。这表明,笛卡尔对人的理性和主体性的彰显,既顺应了时代潮流,体现了人类思维发展的规律,又凸显了他追求思想解放、向往意志自由的人文情怀。 笛卡尔哲学难题是最富挑战性、最具活力的问题之一,在近现代心灵哲学、心智哲学的研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开。虽然随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它已经发生了偏转,但是并没有失去作为理论源头和始作俑者的理性魅力。即使是当今西方心智哲学所讨论的许多身心关系、心物关系问题,仍然在原则上没有超出笛卡尔哲学难题的原初视阈,因为笛卡尔哲学难题触到了在世界及人自身之外除了物质的东西外究竟还有没有精神元素的存在这一根本问题。笛卡尔在证明身心区别与心物对立时,从思维的反向规定上显然触到了心灵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但是,他仅仅表明了身心的差别、心物的对立,说明了心灵不是什么,并没有进一步揭示出心灵究竟是什么,心灵的本质是如何规定的。他的后继者正是沿着这一难题所开辟的理论道路而展开研究的,或者以一种精神实体吞噬物质客体,认为是上帝的精神力量预定了一切事物的和谐,或者把心灵中的意识现象、心理活动过程看作是物质及其活动的一种特殊形态,以此来消解二元论的哲学迷思,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并发展了我们对于心智本质的理解。但是,正如上述所分析的那样,心物关系、身心关系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很复杂的哲学问题,仅在机械唯物主义者内部或者仅仅在唯心主义、唯灵主义内部,都不能得到正确的求解。笛卡尔身后的哲学家们对破解哲学难题做了种种努力,但他们的分析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心智本质理论的一个个片面的理解,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心智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全部内涵,离开实践观和辩证法对它做任何求解都只能徒劳。 笛卡尔哲学难题开启了近代认识论的转向,使得认识论的问题成为近代哲学研究的中心,其试图在基础主义和表象论的研究框架中寻求知识合法性和确实性的努力,在现代哲学中的确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哲学家的挑战与质疑。为了破解笛卡尔哲学疑难而奠定认识论的稳固基础,一些哲学家曾经设想从客观实在的确定性来保证认识的确实性,为认识论找到一个外在赋予性的理性根基,在受到怀疑主义的批判后,这一立场自然就被颠覆了。相反,另外有些人按照笛卡尔思路,主张为认识论找到一个内在赋予性的基础,这一思想在现代哲学家那里,得到了不同形式的弘扬。他们普遍认为,认识论的确实性基础,不是外在赋予的而是心灵赋予的,是心灵不得不为自身确立的,知识的基础最终是在人自己的心灵中发现的,这种基础虽然不是来自于心灵中不证自明的天赋观念,但是的的确确又是来自于主观心灵的内在构造。诚然,也有一些现代哲学家对笛卡尔哲学难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反思,认为笛卡尔奠基的所谓内在赋予性的认识论基础,虽然一定程度凸显了主体性,在人类认识史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但是随着对近代主体性哲学及其理性主义路线的过多张扬,以至于它又反过来成了窒息人类认识能力、限制人类认识视阈的思想桎梏。过度膨胀的主体性哲学及其理性至上、理性万能的思维模式,又发展成为一种内在压抑人类认识的新的绝对、一种僵化的思维方式,曾经长期滥施淫威于认识论领域,造成思想的独断化和极权化,并扼杀人类的认识能力与思想活力。这逼迫现代哲学又开启新的一轮研究主题的转换。 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哲学家,反对以主体为中心的心智哲学路线,主张从以主体性哲学为核心向以交互主体性(或者主体间性)哲学为核心的转换,从个人中心的认识论转向社会化的认识论,从心灵赋予的认识论基础转向社会交往赋予的重叠共识,从个别主体对客体的镜像反映转换成认识共同体,在问答逻辑中生成交往互惠。因而解构主体性哲学及其理性至上主义路线,反对基础主义和表象论,批判主客两离与身心二元的思维方式,就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基本导向。现代哲学的另一个基本导向是语言学转向,具体又有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一种是现代经验分析学派,主张对哲学的语言进行逻辑分析,试图通过医治哲学语句的弊病来破解笛卡尔哲学难题,但是又以语言的界限窒息了思维的灵性;另一种是存在主义的语言学转向,这种尝试唤醒了思的自觉与人的解放,但是以非理性的主体体验代替社会实践,仍然存在致命缺陷。现代哲学从逻辑与语言关系的角度对笛卡尔难题的求解,虽然无果而终,但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今天“也是哲学在当代演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15]176。在现代语言学转向之后所开启的后现代转向,以激进的方式试图完全取缔近现代思维方式,取缔认识论和主体性哲学,试图破解结构、击碎整体,颠覆一切带有主体性踪迹的任何认识论,这又使近、现代认识论哲学的一切努力陷入一场崩溃性的逻辑中,通过理性的自残与自杀而走向了自我消解。可见,破解身心二元、心物两离如何实现统一的笛卡尔哲学难题,似乎成了近、现代哲学乃至后现代哲学研究的共同主题。至今坚信二元论立场的人可谓已经凤毛麟角,但是笛卡尔哲学难题的阴影仍然没有散去,它又以更加多样化的方式吸引着当代哲学家对之进行深入拷问。笛卡尔自己曾经说,身心二元如何统一的问题,其实并非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是一个科学的问题,只有期待科学事业的巨大进步才有望解决。马克思则认为,破解这类思想迷思以及其他哲学怪论“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16]503。只有在实践中而不是在心灵中,才能确立认识论的真实基础,才能验证主体性认识能力及其认识成果的科学性。离开实践的思维,纯粹是经院哲学的病态思维。消解身心二元对立只能借助于实践,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凡是把哲学论争引入神秘主义邪路上去的奇谈怪论,都只能在对实践的合理理解中得到真正解决,舍此并无它途。 参考文献: [1]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 曾裕华.知识与价值之间的内在一致——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批判性考察[J].学术月刊,2013(10). [3] 韩秋红,等.“思”与“在”的世界——笛卡尔哲学二元论新解[J].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10(5). [4] 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两组患者术前PO2及PCO2比较均具有可比性(p>0.05);术后2 d及5 d,实验组较常规组均有明显改善(较p<0.05或p<0.01),见表1,2。 [5] 张志伟.西方哲学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 刘大椿.科学哲学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是我国第一个苏维埃县级回民自治政权,开创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先河,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中,沿着民族区域自治这条道路不断地进行探索,总结经验教训,完善政策制度,建立了一批少数民族自治政权,先后在淮南、山东、晋察冀解放区分别建立了二龙回民自治区、鲁中回民自治区、枣庄回民自治镇、孟村回民自治镇、宣化二区回民自治区等一批县级民族自治地方。1947年5月,建立了第一个省级自治政权——内蒙古自治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自治和区域自治政策进入了成熟阶段,也是我国正式确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开端。 [7] 朱荣英.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及其生存意境[J].河南大学学报,2003(1). [8] 张世英.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政府应该放宽出租车行业的准入机制,不仅要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到出租车行业的运营当中,将出租车数量的控制权交给市场进行管制,还可以通过更多的法律制度规范来约束整个出租车行业,更多地实施监管的责任,保证乘客的安全,提高人们对出租车的选择率。 [9] 高秉江.“思”与思维着的“我”——笛卡尔和康德自我观的异同[J].哲学研究,2011(6). [10] 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发展的历史,有着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人物。通过对这些历史、人物的了解,不仅可以令学生对数学的兴趣和认同感逐步提高,同时也能够令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点的时候,感受该知识发现者的数学理念与数学思维,吃饭还能够扩展学生知识面,提升学生的数学人文素养,从而强化学生的核心素养。 [11] 王新生.试论海德格尔“存在—神—逻辑学”批判的神学维度——兼论其对卡尔·拉纳的启发[J].哲学研究,2010(3). [12] 张汝伦.思考与批判[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13] 邹诗鹏.生存论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4] 高新民,等.笛卡尔二元论的重新解读与最新发展——从现代心灵哲学的视域看[J].哲学动态,2011(12).结合上述法律的规定,继续盘问制度是指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对于当场不能够解除或确认其违法犯罪嫌疑的人员,按照法律规定将其带至公安机关进一步盘问、检查,以最终确定相对人是否违法或犯罪的法律制度。 [15] 张祥龙.现代哲学观念[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 叶厚隽〕
The Solutions of Descartes’ Philosophy Problem and Its Rational Enlightenments
ZHU Rong-yi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For solving Descartes’ philosophy problem--- the separation and unity of body and mind, modern Empiricism and Rationalism has made efforts to solve, which results to the unification of body and mind in the subjective concept. Modern experience theory was disappointed with this solution, and in contrast, tried to get the spiritual factors due to material factors to give solution, that is to say,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logic of language analysis to eliminate the metaphysics. But due to the fixed boundary of language, the inner vitality of thoughts is choked. Modern ontology was advocated by implementing the linguistic turn in breaking through any limits from the logic of language in living life just find a possible path for deciphering the problems. However, Paradox will be regarded as the existence of linguistic just found a possibility for solving this problem rather than the exact solution, only resort to Marx’s practice viewpoint to obtain positive solutions.
Descartes; Philosophy problem; solution; rational enlightenment
B1
A
1006−5261(2015)02−0041−10
2014-05-25
河南省人文社科开放性研究中心资助课题(YH:2010-12)
朱荣英(1963―),男,河南尉氏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