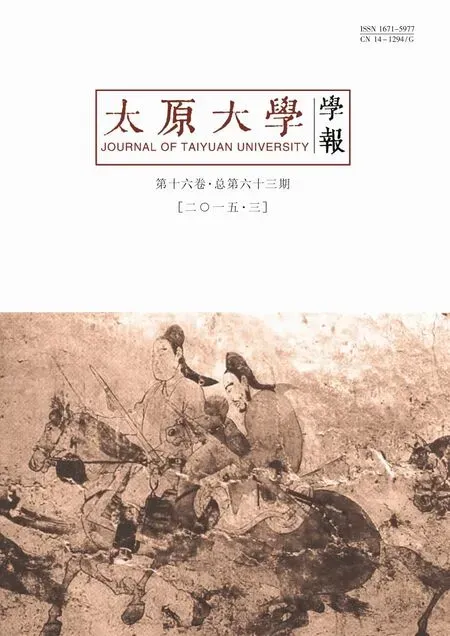论福克纳与莫言的酒神精神
朱 峥 琳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论福克纳与莫言的酒神精神
朱 峥 琳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福克纳与莫言的比较研究历来备受学者关注,他们的创作带有强烈的酒神精神,这与他们的生命历程密不可分。在写作上,他们注重叙述的狂欢之美,在人物的塑造上充分体现人性的自然之美。酒神精神在他们的小说《喧哗与骚动》与《红高粱家族》中有着深刻的体现,彰显了福克纳与莫言在生命与艺术上的狂欢。
福克纳;莫言;酒神精神;《喧哗与骚动》;《红高粱家族》
尼采说:“我是哲学家狄奥尼索斯的最后一个弟子。”[1]101狄奥尼索斯(Dionysus)即酒神,是古希腊神话中酿酒及酿酒植物的保护神。19世纪70年代初期,尼采最早提出了“酒神”的概念,认为“酒神狄奥尼索斯象征主观情感的放纵,酒神精神是人类自古有之的大创造,大破坏的精神”。80年代之后,尼采的思想渐趋成熟,在多部著作中论述“酒神精神”这一概念——“肯定生命,哪怕是在它最异样最艰难的问题上,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中,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1]101这样一种肯定生命的酒神精神,正是贯穿福克纳与莫言的生命历程以及文学作品的核心精神。福克纳与莫言分别是1949年和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虽相隔半个世纪,但无论是从影响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平行研究的角度,这两位擅长写故事的作家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自改革开放以来,译介福克纳的作品便成为热潮,其小说包括《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等,都是中国文艺界的宠儿。近几十年来,我国对福克纳的研究早已形成体系,并具有专门的研究组织。对于莫言的文学作品,众多学者也早已展开学习与研究,成果颇丰。随着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莫言更是名声大振,《丰乳肥臀》、《红高粱家族》、《蛙》等诸多作品一时之间销售一空,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
一、生命的狂欢——福克纳与莫言的酒神精神
酒神,是宙斯与忒拜国王卡德摩斯的女儿塞墨勒所生之子。塞墨勒因受天后赫拉的诱骗而被雷电烧死后,宙斯从其腹中取出胎儿缝入自己的大腿中,因而走起路来像瘸子一样。后来宙斯将其取出,取名为狄奥尼索斯,意思就是指“瘸腿的宙斯”。古希腊悲剧起源于酒神祭祀,在祭祀礼仪之前人们常常会喝得酩酊大醉,他们载歌载舞,情绪亢奋,冲破了平时的禁忌,在无意识之中追求精神的解放。在狂欢的氛围中创作的歌谣充满生命感与力感,痛苦仿佛成为了艺术的兴奋剂。由此可见,酒神精神就是整个情绪系统亢奋的状态,在这样狂欢与迷醉的状态下,人的原始生命力得到充分扩张,理性逐渐隐退,而人的本能欲望、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得以释放。因此概括来说,酒神精神在于“提倡一种特殊的人生态度,即积极肯定人生,尤其是肯定生命的非理性方面”。[2]
福克纳与莫言肯定生命意志、追求人性自由、歌颂原始生命活力,他们在“大醉”之中,寻找着渴求已久的酒神精神,这种精神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着深刻的联系。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年出生在美国密西西比州新奥尔巴尼的一个没落庄园主家庭,其曾祖父是个有名的历史人物,一直被福克纳视作自己的人生向标,他就像一个在大地上仰望着曾祖父的小孩,“像我曾祖父那样”是他的口头禅。福克纳身材矮小,而且气质上也有些女性倾向,与母亲更为相像,常被认为是“母亲的儿子”。他自认为不够男子汉,因而在心中隐藏着自卑的种子,当自己心爱的女孩艾斯黛尔跳舞时,他只是一声不吭地、静静观看她与别的男孩子跳舞。福克纳的童年生活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关爱,他在父亲和母亲的势不两立中长大,母亲莫德不满意丈夫的软弱无能,而父亲则待人冷漠、不易相处,这样的环境对幼年福克纳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在他的很多小说中,我们几乎看不到温馨和谐的亲情,家庭关系是阴冷的、异化的。福克纳的一生有太多的角色:讲故事的孤僻少年、版本多样的传奇老兵、流浪汉、酒鬼、邮政局局长、好莱坞写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等等,然而他本质上始终是一个作家,这些不同寻常的经历都成了福克纳文学创作的不竭源泉,“他写了一些书,然后死了”——这是他理想中的墓志铭。
福克纳始终对自己的母亲有着深深的敬意。在母亲的指导下福克纳看了很多书,从初级的童话故事到狄更斯之类的经典作品,母亲用这样的方法把“对文学执著的爱”传播给自己的孩子。莫德是一个非常坚强的母亲,虽然个子矮小但个性极强,她在厨房里用木板挂上自己的信条“不抱怨,不解释”,这种顽强对待生活的精神对福克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很多作品中的白人老太太身上都有着莫德的影子,这些人物在小说中像是沉闷暗夜里闪现的一道亮光,照亮了读者沉闷压抑的眼睛与心灵。福克纳是一个酒鬼,一生浸泡在酒精中,他甚至在准备去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前还喝得酩酊大醉。无论福克纳是为了庆祝喜事或借酒浇愁,还是他能够在酒精麻醉下的“大醉”状态中寻找更多的创作灵感,他都让自己在“醉”的境界中探寻人生、对待生命,“由于福克纳经常生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里,可能他自己有时都分不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他想象的产物。”[3]20曾经有记者采访他的家庭情况时,福克纳“神情认真”地回答道:“我于1826年由一个黑奴和一只鳄鱼所生——他们的名字都叫高兴的石头。”相信这样匪夷所思的答案只有这位会编故事的福克纳才能信口说来吧。1921年12月,福克纳开始担任密西西比大学邮电所所长,从此以后邮电所再也没有确定的开门时间,他有时候很久都不分发信件报刊,有时候又迅速的把信件加急发送,碰到一些有趣的杂志,他就自己拿过来看上好些天,遭到投诉后依然我行我素,做了差不多三年“世界上有史以来最糟糕的邮电所所长”。*转引自Minter,William Faulkner,p.42.由此可见,福克纳无疑是一个自由散漫的怪人,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蓄上胡子,光着脚在街上或者是在树林里漫无目的地走,有时候甚至在广场上站几个小时,呆呆地对人视而不见,他就像是不断在思索着困扰他的问题的流浪汉,在面无表情的平静中进行着思想的大狂欢。
莫言曾说过:“一个作家读另一个作家的书,实际上是一次对话,甚至是一次恋爱,如果谈得成功,很可能成为终身伴侣,如果话不投机,大家就各奔前程。”[4]由此看来,莫言与福克纳的谈话很成功。莫言在《自述》中写道:“我一边读一边欢喜,对这个美国老头许多不合时宜的行为感到十分理解,并且感到很亲切。”1955年生于山东高密的莫言有着与福克纳相似的童年生活,他们从小在民间的口头故事中长大,自己也是讲故事的能手,福克纳甚至以讲故事作为交换,让小伙伴们替他干活。其次,莫言与福克纳都有着丰富的文学储备。尽管莫言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作,但是他还是读了很多书,为了得到阅读别人家书的权利,他常常去给人家干活。相比较而言,福克纳则具有更为便利的条件,受过大学教育的母亲莫德在福克纳很小的时候就指定文学作品让他阅读,“10岁时就开始读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扎克和康拉德”。[3]16他们如海绵一般努力吸收,为以后的写作生涯打下了良好基础。再次,他们的童年生活并不美好。莫言曾坦言“我的童年是黑暗的,恐怖、饥饿伴随着我成长”,莫言的家庭成员很多,因而很容易成为被忽略的孩子,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被遗忘、被侮辱的黑孩儿一般,这种充满爱与伤痛的成长经历为莫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题材。而福克纳的童年是在对自己身高、性格等各方面的自卑以及家庭关系的貌合神离中度过。最后,他们都有着惊人相似的创作动机:实现自身愿望。福克纳以自己的曾祖父为榜样,而他的曾祖父曾经发表过小说,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因而福克纳上三年级时就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另外,福克纳还希望通过写作满足心理要求,“他很希望做一件既使他显得与众不同又令人羡慕、崇敬的事情,来弥补自己的先天不足,获得一种心理上的优势。”[5]23莫言最初决心当一个作家是因为听到别人说只要当了作家,就可以每天吃三顿饺子。另外,莫言在《小说的气味》中说:“其实,鼓舞我写作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石匠家那个睡眼朦胧的姑娘。”怀着对饥饿的恐惧和对美好爱情的向往,莫言创作了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文学作品,他从卡夫卡、福克纳、马尔克斯等作家身上学习到魔幻现实主义,结合自身对家乡、对中国真实历史的了解,将“乡土”的推向全世界。
虽然经历过痛苦和饥饿,但是福克纳与莫言的生活也并不缺乏关爱,他们在家乡的土地上成长,遭受打击和批评,但是他们始终离不开这片热土,就像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一样,围绕着酒神狄奥尼索斯且歌且舞,在半梦半醒中编织着他们的文字王国。
二、艺术的狂欢——文学作品中的酒神精神
“狂欢化”是美学范畴的命题,由巴赫金提出。狂欢化的叙事追求沉醉和热烈,并将一切狂欢节式的随心所欲渗透在文学创作中。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一种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
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通过四个人的不同视角讲述了康普生家族的兴衰:故事的中心人物是康普生家的女儿凯蒂,凯蒂因失身怀孕不得不与另一男子结婚,被丈夫发现后抛弃了她,便将私生女小昆丁寄养在母亲家。哥哥昆丁因凯蒂失去贞操而失去精神平衡,在凯蒂结婚后不久投河自尽。大弟弟杰生是一个实利主义者,他将自己没有得到银行里的职位归罪于凯蒂,因而他恨凯蒂,也恨小昆丁,在他的虐待下,小昆丁终于在1928年复活节那天取走杰生的不义之财,同一名流浪艺人私奔。班吉是凯蒂的小弟弟,1928年的时候他三十三岁,但是却有着三岁孩童的智力,他没有思维能力,分不清大脑中事情的先后顺序。《喧哗与骚动》的书名取自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中的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正如这句话,先天性的白痴班吉是第一个叙述视角。通过班吉颠倒时序的叙述,虽不能够全面地了解具体情节,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凯蒂是一个自然、勇敢并富有同情心的女孩。莫言的小说《红高粱家族》也是围绕一个女性“我奶奶”戴凤莲逐步展开,她敢爱敢恨,遵循自己的生命意志,蔑视道德规范,与“我爷爷”在茂盛的高粱地里谱写了最原始粗野又最自然纯真的爱情交响乐。“我爷爷”是一个“最美丽最丑陋、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的人物,他撒在酒篓子里的一泡尿奇迹般地酿制了奇香的“十八里红”。他一生杀人无数,打死过土匪头“花脖子”、袭击过日本鬼子,是红高粱养育的北方硬汉,在“我爷爷”身上有着中华民族压抑已久的蓬勃生命力,他彻底摆脱了传统礼教的奴性,敢作敢为。罗汉大爷是一个坚毅的汉子,他被日军拴在马柱上剥皮零割示众,“刘面无惧色,骂不绝口,至死方休”,[6]11这些震撼的场景描写,让读者在心惊肉跳之余大呼过瘾。
(一)叙述的狂欢之美
福克纳与莫言在小说创作上有着共同的地方,他们都力求新变却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首先,他们都追求独特的小说结构。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通过班吉、昆丁、杰生和迪尔西四个不同视角,使事件不断清晰呈现,四个小部分就像是四个乐章,并且结构也并非按照时间顺序,而是跳跃穿梭的,先写的是1928年4月7日,将我们带入白痴的视角,混乱而毫无逻辑,接着跳转到1910年昆丁自杀那天,然后又跳回到1928年4月6日,通过这一天杰生的心理活动展现出康普生家族的颓败,最后是1928年的4月8日,通过黑人女仆迪尔西的眼睛展现出康普生家庭扭曲的人际关系。而《红高粱家族》的结构虽说并没有清楚的分为四个时间段,但它是由五个部分组成的,“采用即兴说书的的叙述方式,在时间上跳跃反复,而不是采取直线进行的因果叙述”,[5]185整部小说有两条主线,一条是“我爷爷”余占鳌的战斗生活,是按照时间的顺序,从冷水伏击战开始,到加入铁板会,再到抗击日本军。另一条线索是围绕余占鳌、戴凤莲以及我“二奶奶”恋儿的情感纠葛展开,莫言采用闪回的方法,不着痕迹地进行着零散的片断回溯,使整个故事有条不紊地呈现,由此可见莫言炉火纯青的叙事能力。
其次,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具有明显的“狂欢化”倾向。巴赫金指出:狂欢化人物的精神原型具有某些佯狂化的人物特性,如傻、癫狂、滑稽、疯子等等,“他们不与世界上任何一种相应的人生处境发生联系,他们看出了每一种处境的反面和虚伪。”[7]231福克纳与莫言的小说中,多采用小孩或者是痴傻人的视角,借助儿童或者痴傻人的眼光或口吻进行叙述。批评家李乔说过:“以‘幼稚观点’叙述,可以让人领悟成人世界的愚昧可笑;以‘痴呆病态观点’叙述,可以暗示所谓健康正常人间的可怜病态来。”[8]124《喧哗与骚动》中的白痴班吉就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虽然很多事情他不懂也无法理解,但是他的感官非常敏锐,“我已经一点也不觉得铁门冷了,不过我还是能闻到耀眼的冷的气味”,[9]41921年他父亲去世那晚班吉闻得到死亡的气味。对他来说凯蒂身上有树的香味,当凯蒂长大喷香水时,班吉就大吵大闹把凯蒂往卫生间推。凯蒂失去贞操的那天,班吉更是疯了一样把凯蒂往卫生间推,然而这次却永远没有树的香味了。昆丁也是一个处于癫狂状态下的人物形象,小说中他所叙述的那一部分发生在他要自杀的当天,因而精神处于极度癫狂之中,他在那天砸碎了折磨着自己的祖传手表、打包自己的行李衣物、帮一个迷路的外邦小女孩回家、在回忆和现实的恍惚中与别人打架……他有板有眼地做着这些对于一个濒死之人无关紧要的事情,从容不迫、安心等待着死亡。昆丁不断回忆着妹妹失身后他们之间的对话,他无法接受凯蒂失去贞操的事实,一心想要说是自己与妹妹乱伦,从而能够和妹妹两个人坠入地狱,“纯洁的火焰会使我们两人超越死亡,到那时我们两人将处在纯洁的火焰之外的火舌与恐怖当中”,这种在世俗礼教压抑下形成的病态心理导致了昆丁的悲剧。《八月之光》中的痴情女子莉娜,带着“一种内心澄明的安详与平静,一种不带理智的超脱”踏上寻找情人的路,她仿佛有一颗婴儿般的心,无所惧怕、毫不担忧,具有坚韧的生命力和超然的人格,这样一个光辉的形象,正是福克纳所赞美的“心灵深处的亘古至今的真情感受、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10]254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采用了“我父亲”豆官的视角,当时豆官还是一个半大小子,跟着余司令四处打仗。“我父亲”在小说中是一个全知视角,他像是整个事件的目睹者,见证了小说中每个人物的一生。在“我奶奶”出嫁的路上,轿夫们拼了命的颠晃新娘,不把她颠得呕吐不罢休,这竟然是一种高密乡的风俗。像这样匪夷所思的类似于狂欢节一般的风俗还出现在《丰乳肥臀》中,上官金童被选为“雪公子”,在“雪集”上负责抚摸村子上女性的乳房,并寄托美好的祝福,并且在“雪集”上买卖不可以说话,整条街寂静无声。另外,“我奶奶”和“我爷爷”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这种粗鲁而原始的欲望,本身就带有强烈的狂欢色彩,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当头一棒。我“二奶奶”恋儿的奇死也是让读者看得冷汗淋漓,她莫名其妙的灵魂出窍以及被神怪附体的可怖描述,让人身临其境。他们小说中这些癫狂的、独特的、非理性化的人物形象,无论美丑,都真实得让人落泪。
最后,他们的叙述风格别具特色。第一,在文学创作上有着不羁的想象力。中国古代就有刘勰“神与物游”之说,没有想象力便不会有成功的文学创作,而从小就是编故事能手的福克纳和莫言自然以想象力见长。福克纳曾说过,一个作家需要的三件工具就是经验、观察和想象力,而莫言也认为想象力是一个作家最宝贵、最重要的素质。他们在自己家乡的基础上构建了“邮票般大小”的艺术世界,在这个超级王国中讲述着一代代家族的历史兴衰,描绘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福克纳侧重于人物心理活动的内部想象,在《喧哗与骚动》中,他塑造了班吉这个白痴的形象,通过想象他为我们呈现了傻瓜的思维方式:他会因为听见的声音或是闻到的气味而联想到大脑中过往的印象。福克纳采用意识流的手法,恰到好处地将读者引领到一个傻子的混乱思维中。相比较而言,莫言则比较善于外部的想象。在他的笔下,红狗、绿狗、黑狗齐聚一堂,拉帮结伙啃食人尸;高粱酒因为“我爷爷”的一泡尿变得香醇无比,成了酒坊的酿酒秘方;战斗中牺牲的哑巴双眼圆睁,大口洞开,像是要吼叫……莫言的语言并不精炼,他铺张浪费地使用着天马行空的字眼,展现出“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东北高密乡。第二,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自成一格。福克纳擅长角度多元化的叙述,如《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等小说都是由若干个人物的独立讲述逐步呈现的。在福克纳的小说中很少出现“他想”、“他说”这样的字眼,很多对话以及想法像是从人物头脑中直接涌出来的,从一个思绪跳到另一个思绪。尤其是在昆丁部分,一些反复出现的文字片段如“忍冬的香味”、“你有姐妹么”等等在正常的叙述中不断闪现,体现了昆丁极度亢奋的精神状态。在《喧哗与骚动》中有一个打秋千的描写,班吉的大脑里出现二十年前凯蒂赶走情人来安抚自己的场景,然而回到此刻却是对着自己破口大骂的凯蒂的女儿小昆丁,这种蒙太奇的手法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对比,也极大地深化了家族道德沦丧的主题。而在莫言的小说中,大部分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或第一人称叙事。全知视角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够随心所欲地叙述,极大地促进了小说叙述的狂欢。另外莫言重视民间文化,独特的语言词汇使他的小说别具特色。例如为了凸显罗汉大爷的高大形象,他被打之后,“民夫们看着他血泥模糊的头,吃惊的眼珠乱颤”,这样的语言不仅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冲突,让人想象出“眼珠乱颤”的画面,更能够从侧面表现出罗汉大爷的汉子气魄。他还在作品中使用很多粗俗的比喻和词汇,在第三章《狗道》的最后,豆官看到一个老头子,小说中用了一句话来描述:“那老头子浑浊的眼睛像两摊鼻涕一样粘在眼眶里”,就这么一句话,却能够形成强烈的画面感,难怪会有人说莫言的小说不是电影更胜电影!莫言喜用色彩词,通过色彩的变化表现人物情感,给人物的主观感觉赋予色彩。《红高粱家族》中有一段描写战斗时的场景,负责吹号的刘大号,“一条腿跪着,举起大喇叭,仰天吹起来,喇叭里飘出暗红色的声音”,这种陌生化的效果给读者带来独特的阅读体验,神经不断抽跳着,让人印象深刻。福克纳与莫言不受理性控制的叙述方式,正是在酒神精神影响下的自然体现,这种叙述的狂欢之美,也正是对酒神精神最好的诠释。
(二)人性的自然之美
佛斯特说过:“我们可以对人性不喜欢,但如果我们把它从小说中祛除或涤净,小说立刻枯萎而死;剩下的只是一堆废字。”[11]18由此可见,文学即人学。福克纳与莫言都十分注重对人物的塑造,无论是英雄、恶棍还是少女、妇女,在他们笔下都被刻画得深入人心,在文学的长河上熠熠闪光。
福克纳善于揭示人性的弱点。在小说《喧哗与骚动》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有着局限性,福克纳透过细腻的描写展现出来。康普生家庭笼罩在灰蒙蒙的压抑气氛中,康普生先生醉醺醺地消极处事、康普生太太自私冷酷又爱无病呻吟、昆丁懦弱消极又神经质、杰生怀着仇视的目光看待一切、白痴班吉整天哼哼唧唧、就连逐渐长大的小昆丁也对着偏袒自己的女佣迪尔西骂骂咧咧……这些被现代社会的金钱、虚荣、安逸所异化了的一群人,在福克纳笔下栩栩如生。因为妹妹凯蒂的不贞洁,昆丁的精神陷入了挣扎之中,福克纳运用大量的意识流和闪回的手法,将读者带入昆丁混乱的精神世界。身为长子,昆丁自认为身负维护家族声誉和旧传统的重任,他将妹妹的贞洁与之相联系,然而他是如此的软弱,在与达尔顿·艾密司决斗时,在对方根本没有打自己的情况下“像一个女孩子那样的晕了过去”!然而在这样一个沉闷阴暗的环境中,凯蒂像是一抹亮色,深为福克纳心爱,福克纳甚至说:“我爱上了我的人物中的凯蒂。”*转引自M.E. Coindereau,The Time of William Faulkner(Univ.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17),p.41.凯蒂和兄弟们在水边玩耍,弄脏了内裤,这时候昆丁就在一边数落她,这个细节十分重要,为以后的故事埋下了伏笔。内裤脏了,暗含着凯蒂的失身,而儿童时期的昆丁对妹妹的数落也隐喻昆丁对妹妹贞洁的重视。大姆娣去世的时候,孩子们被禁止呆在家里,只有凯蒂爬上了树偷看。她像一个假小子,大嗓门、喜欢当国王让别人听自己的命令、像妈妈一样照顾自己的白痴弟弟班吉。可以说凯蒂给了班吉如母亲般的关爱,她为了班吉抛弃香水、离开情人,这些都体现了凯蒂的自然和善良。她像普通女孩子一样向往爱情,并为之奋不顾身终不后悔。小说中有一段昆丁与凯蒂的对话,昆丁询问凯蒂是否爱达尔顿·艾密司,“她瞧着我接着一切神采从她眼睛里消失了这双眼睛成了石像的眼睛一片空白视而不见静若止水”,[9]196凯蒂把昆丁的手放在自己的咽喉上,让昆丁说达尔顿的名字,“我感到一股热血涌上她的喉头猛烈地加速度怦怦搏动着”。这段文字让人动容,显而易见凯蒂是爱着达尔顿的,她毫不避讳自己的喜欢,坦然地面对家人的非难。尽管在小说中凯蒂是堕落的,她最终为了家族的名誉而流落在外,成了纳粹军官的情妇。但是福克纳依然对凯蒂有着特殊的情感,凯蒂曾对自己的哥哥昆丁说过“我反正是个坏姑娘你拦也拦不住我”,而小昆丁也对自己的舅舅杰生说“我很坏,我反正是要下地狱的,我不在乎。”但是凯蒂是一个身上有着树的香味的自然之女,她的身上闪现着人性光辉,尽管凯蒂最终是悲剧收场,但是她对爱情的追逐、对人性自由的追求是颇受肯定的。
相比较而言莫言的《红高粱家族》的色彩就比较浓烈,人物形象也更加具有狂欢之美。如果说在《喧哗与骚动》中,大部分的人性是被压抑着的,那么在《红高粱家族》里,人性的自然之美被渲染到了极致。“河滩上的狗蛋子草发疯一样生长,红得发紫的野茄子花在水草的夹缝里愤怒的开放”,[6]226这种疯狂怒放的状态,正是东北高密乡最自然原始的生存状态。小说中有一段对“我奶奶”哭声的描写,尤为动人:“哭声婉转,感情饱满,水分充沛,屋里盛不下,溢到屋外面,飞散到田野里去,与夏末的已受精的高粱的綷縩声响融洽在一起”,[6]80将“我奶奶”的哭声与大自然相结合,可见“我奶奶”是大自然孕育的女儿,她在高粱地里初尝爱情之果、在高粱的庇护下风生水起地经营酒坊、在殷红的高粱地中如蝴蝶般翩然死去……无疑“我奶奶”不仅是抗日女英雄,也是个性解放的先驱、妇女自立的典范。她剪的梅花鹿的窗花,在背上生出一枝红梅花,以一种自由独立的姿态,昂首挺胸地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我奶奶”活得自然,想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就笑,她敢爱敢恨,当“我爷爷”为了“二奶奶”恋儿搬到别的村上时,“我奶奶”毫不示弱地跟了铁板会的头子黑眼,“我爷爷”和黑眼为了她争斗,她“头发溜溜的亮,脸颊艳艳的红,眼睛灼灼的明,模样实实的可爱又可恨”。“我奶奶”爱得疯狂、恨得洒脱,她蔑视人世间的堂皇说教和道德,当子弹穿透她挺拔的乳房时,“我奶奶”的英魂也在这片茂盛的高粱地里翩然纷飞,天地间充斥着异常壮丽的色彩!
福克纳在1949年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说:“我拒绝接受世界末日的观点……我不认输。我认为人类不仅会延续,还会胜利。”莫言也曾在《红高粱家族》的卷首写道:“仅以此书召唤那些流浪在我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梁地里的英魂和冤魂。”他们的小说都有着强大的生命力,热切肯定生命。福克纳的作品中,无论是黑人小厮还是南方淑女,都力求拥有鲜活的生命,勒斯特渴望去看戏、迪尔西用自己的钱给班吉买生日蛋糕、凯蒂从不否认自己内心对自然人性的渴望。而莫言更是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具有张力的形象,英雄身上充满血性和匪气、母亲有着宽厚博大的内心、女性身上充满了自由和独立……福克纳与莫言都肯定生命中非理性的方面,呼唤原始的生命强力,同时他们也深刻地意识到了民族“种”的倒退。他们似乎都对“过去”有着强烈的崇敬,推崇过去,认为今不如昔,着眼于当下的情形以衬托出昔日的辉煌。《喧哗与骚动》中,康普生家族由胜转衰,不仅仅是往日的辉煌不在,更是“种”的衰落。这也与福克纳自己家族的发展有关,在他曾祖父时代如此辉煌,然而到了他父亲的时代便光辉不再。康普生先生身上有着福克纳父亲的影子,他们都嗜酒、都没有胜任壮大家族的历史使命。《红高粱家族》更是热烈地歌颂原始生命力,小说处处透露着如纯种红高粱般强韧、茂盛、壮丽的色彩。“如果秋水泛滥,高粱地成了一片汪洋,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的向苍天呼吁”,这样高昂着头颅的生命力,正为莫言所歌颂:“这就是我向往的,永远会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6]361
无论是在叙述上,还是在对人物的塑造、对人性的描写上,福克纳与莫言都处处体现酒神精神。福克纳的人物有着挣扎狂欢的内心世界和自然原始的人性之美,莫言笔下的人物有着强烈的生命意志和原始的欲望追求,他们运用异曲同工的方法,将人性的扭曲和耸动的野性美展现在读者面前,在酒神精神指引下进行着艺术的狂欢。
三、酒神的欢歌——福克纳与莫言酒神精神的美学价值
20世纪时期的欧美现代文学,重视对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摒弃理性,作家如庞德、艾略特、乔伊斯、沃尔夫、福克纳等人,无论从作品内容还是从他们的创作手法来看,都深受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影响。福克纳小说中充满了非理性的叙述,“他的独白就是他本人的非理性,他把它放入他所写人物的心灵。人物的独白和作为讲述者自己的独白合而为一,也来回于往昔之间。”[10]120福克纳坦言《喧哗与骚动》是自己花费最多心血的作品,一共写了五遍,用足了功夫。他通过对人物命运的创设,通过让人难以理解的晦涩语言以及毫无过渡机制的意识流手法,为读者展现了康普生家族的悲剧历史、美国南方的受难史。福克纳对酒神精神的表现是压抑着的,他从反面来描写,通过对人物内心的细致描述,表现压抑酒神精神所导致的悲剧:凯蒂最终听从命运的安排,嫁作他人妇,不再为了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抗争,她没有像自己之前说的那样“你拦也拦不住我”,而是顺从地放弃了抗争,最终她无家可归沦落风尘;昆丁是清教主义的维护者,然而他懦弱的肩膀承担不起维护家族荣誉的重任,凯蒂的失身使他失去精神平衡,他否定凯蒂的真爱,一味地渴望妹妹是被迫的,他蒙蔽自己,生活在过去与现实的虚幻中,最终自杀;杰生在金钱利益下迷失自我抛弃亲情,在铜臭的钱眼里扼住自己的欲望,甚至对自己的情人也防之又防,他不懂什么是爱,只有悲哀的活着,正如小说中的描述“他那无形的生命有如一只破袜子,线头正在一点点松开来”[9]342;班吉的可悲在于他本是个白痴,他的母亲认为班吉是上帝给她的惩罚,因而整天无病呻吟,凯蒂因为他抛弃过自然的原始情感,因为追逐放学的女学生,班吉毫无概念地接受了非人道的阉割手术,最终在1933年被送进精神病院……虽然福克纳对自己创造的人物有着特殊的情感,但是并不代表他赞同人物在过去的做法,《喧哗与骚动》中,金钱取代了家庭内部的感情:杰生想尽办法占有凯蒂寄给小昆丁的生活费;小昆丁不在乎母亲说了什么,只关心寄来了多少钱;康普生太太愚昧地以为烧掉凯蒂的支票就可以证明自己与女儿毫无关系……小说中每当听到哭声,班吉就会说听到有人在唱歌,这是一曲资本主义金钱世界的哀歌,是资产阶级道德沦丧的哀歌。在尼采的哲学阐述中,古希腊悲剧源于酒神祭祀,而希腊悲剧的人文主义就是酒神精神,当人与人之间的裂痕极为强烈时,酒神精神引导人们回归大自然、复归原始生命,此时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卑贱之分,在酒神精神的支配下,人的每个细胞都充满着狂喜与幸福,一切原始冲动都得到释放。而福克纳的小说正是充满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对种族问题和女性问题的关注,成为对酒神精神最好的诠释。
莫言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发表演讲时,曾坦言“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使他明白了在文学创作中,作家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然而莫言也意识到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为了保有自我,莫言很快逃离了他们,构建有着自己独特味道的文字王国。相比较而言,莫言对酒神精神的表现是热烈的,他的作品让读者深刻感受到酒神迷狂、沉醉,不受世俗束缚、追求自在生命原欲的特点。莫言笔下的语言文字达到了狂欢的极致,它们随心所欲地组合堆砌,使自己拥有了空前的自由和解放。莫言也深爱着自己笔下那些有着强大生命力和自然原始的人性欲望的男女,他们敢爱敢恨、敢作敢为,他们抗争、奔走、哭号、豪饮、野合……这些肯定生命本能的活脱脱的生灵,在满是殷红血泪的大地上顽强生长,如同一茬又一茬的红高粱,茂盛地欢唱!《红高粱家族》中洋溢着一种精神,一种能够洗净“可怜的、孱弱的、猜忌的、偏执的、被毒酒迷幻了灵魂的”孩子们的肉体和魂魄的“纯种红高粱精神”,莫言以尼采式的呐喊呼唤人性的复归,使他的人物永远充满着不死的生命力。他敏锐地意识到现代人“种”的退化,指出这种退化体现在民族性格、心理素质以及民族生命活力上,“面对生命世界的大法则,那些世俗世界的小伦理显得那样虚弱不堪;面对酒神那英雄的迷狂和汹涌的诗意,日神统治下的理性、道德、一切功利化的价值判断,则显得那样渺小卑俗;面对‘既杀人放火又精忠报国’的爷爷奶奶壮丽的人生,‘我’‘深切地感到种的退化’”。[12]而酒神引领着我们不惜一切努力寻找到那株生长在白马山之阳、墨水河之阴的纯种红高粱,“高举着它去闯荡荆棘丛生、虎狼横行的世界”。[6]362小说中的“纯种红高粱”就是自然生命的象征,它燃烧着生命之火、欲望之火,而“高粱酒”则是酒神精神的象征,莫言在西方文化的启发下,创作出《红高粱家族》这样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狄奥尼索斯式”的经典,开辟了一条独具莫言特色的文学道路。
酒神精神带有砸碎一切道德束缚、释放生命原欲的狂欢壮阔之美,酒神式的作品则具有狂放不羁,充满野性、激情和感性等特点。福克纳与莫言的作品中洋溢着酒神精神,他们在各自的文学王国里大显身手,尽管叙述手法和对人物的塑造各有特色,但是都追求狂欢的叙述之美和自然原始的人性之美。他们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人物内心、敏锐地注意到现代人“种”的倒退、关怀人类命运、关注种族与妇女问题,渴望人性平等、歌颂健康的原始生命活力……正是在这种酒神精神的引领下,福克纳与莫言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更为深邃、更加生机勃勃的世界,用酒神狄奥尼索斯的欢唱,唤醒人类最为原始、最为美好的灵魂。
[1]尼采.偶像的黄昏[M].周国平,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2]王晋生.论尼采的酒神精神[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
[3]肖明翰.威廉·福克纳——骚动的灵魂[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4]莫言.童年的读书梦[J].新一代,2011(5).
[5]朱宾忠.跨越时空的对话——福克纳与莫言比较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莫言.红高粱家族[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7]刘康.对话的喧声——巴赫金的文化转型理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8]李乔.小说入门[M].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
[9]威廉·福克纳.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0]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11]E.M.佛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1.
[12]张清华.叙述的极限——论莫言[J].当代作家评论,2003(2).
[责任编辑:姚晓黎]
On William Faulkner and Mo Yan’s Dionysian Spirit
ZHU Zheng-lin
(School of Literal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Comparative study of William Faulkner and Mo Yan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of the scholars. Their creation has strong Dionysian spirit, which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ir life course. In writing, they pay attention to the beauty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carnival. Their image shaping is full of natural beauty of human. Dionysian spirit has profoundly been reflected in the novels “The Sound and the Fury” and “Red Sorghum Family”, which shows the carnival in William Faulkner and Mo Yan’s life and art.
Faulkner;Mo Yan;Dionysian spirit;“The Sound and the Fury”;“Red Sorghum Family”
2015-06-23 作者简介: 朱峥琳(1991-),女,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1671-5977(2015)03-0102-07
I106.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