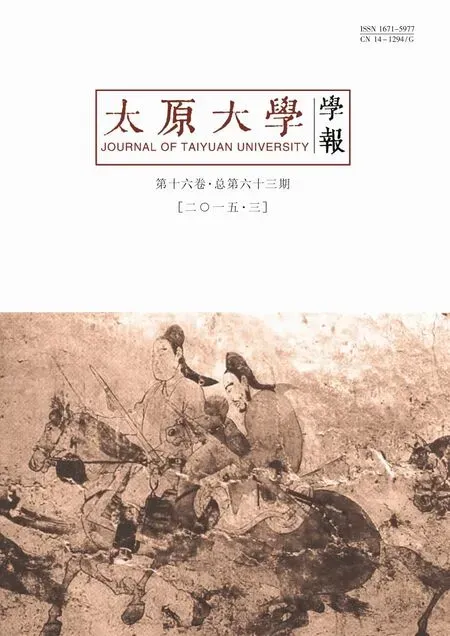论基本权利的限制及其审查原则
马 瑞 辰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论基本权利的限制及其审查原则
马 瑞 辰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权利的内在机理与外在要求的统一,然二者均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方面,内部限制理论过于保守,难以将新兴的权利涵盖在保护范围之内;另一方面,以“公共利益”为核心的外在限制又难以描绘其外延,故通过“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对“限制的限制”进行规制是重中之重。具言之,前者的适用规则为“个案法律之禁止”、“指明条款要求”以及“根本内容之保障”;后者则通过规制“立法裁量”与“行政裁量”来实现。基本权利的限制与保障在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层面实则是“殊途同归”,以“限制”的手段来实现权利之间的平等,在运行中保障公民权利的享有。
基本权利的限制;限制的限制;法律保留原则;比例原则
一、基本权利的限制的正当性依据
“人民基本权利的肯定及维护,是任何一个崇尚民主法治且实行宪政的国家所责无旁贷的任务,现代国家率皆在宪法内明文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价值”。[1]387但是,公民基本权利地位的至上性,也并不意味着其不受任何的制约,“宪政实践亦表明,基本权利的受制约性与基本权利的不受侵犯性相伴而生”,[2]因此,各国宪法也或多或少同时规定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问题。当然,实践中的限制做法并非“一意孤行”,我们亦可在应然层面找到相应的依据。
韩大元教授认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基于以下三点:第一,防止妨害他人的权利;第二,保证国家功能的实现和国家的生存;第三,维护公共利益。[3]这种宏大的视野为我们的论述指明了方向,但此处更希冀通过“解剖麻雀”式的挖掘来验证限制基本权利的理论基础。正如林来梵教授所言:“从规范意义上来说,基本权利本身就有两种界限,一种叫作内在界限,另一种叫作外在界限。因为存在内在界限,因此它就可以受到内在限制;而因为存在外在界限,因此就相应可以受到外在限制。”[4]学界有关“基本权利双重制约”论,即“内在制约”与“外在制约”的观点与此说法不谋而合。同样类似于德国宪政法院认为的对基本人权的“规定”与“限制”的区别。[5]
(一)内在制约
“内在制约说”,指任何权利按照其社会属性都有一个“固定范围”,所谓“权利的限制”不过是在此固定范围的边界之外的东西。[6]具言之,每一项基本权利都有其一定的构成要件,通过这些构成要件,可以对某种行为是否属于该项基本权利的行使作出判断。也就是说,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本身就是对基本权利的范围的框定,从这种意义上讲,基本权利的构成本身就是基本权利的限制。[3]158由于是从界定基本权利的内涵的角度去界定基本权利的限制,所以这种限制是基本权利的自我限制,体现了基本权利在本质上的有限性。似乎可以这样理解——“权利的限制”甚至谈不上是什么限制,而是权利按照其本性,本来就不应该达到的地方。
学界对“内在制约说”还存在另外一种看法,乃是将内在制约认为是基本权利相互之间的制约,即一种基本权利对另一种基本权利的制约,某一主体的基本权利对另一主体基本权利的制约。[7]487这种观点是建立在“权利体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某项权利与其他权利、某个人的权利与其他人的权利之间存在关联性与互动性”的预设之上的。不得不说,由于我们无法否认这种预设性前提的正确性,故而,也不能对上述观点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两种“内在限制说”的区别根源于对基本权利的范围在认识上的差异,第一种观点将单独的基本权利视为一个整体;后一种观点是将多个基本权利放在同一框架内进行讨论,更恰当的说法是,这种做法倾向于在多个基本权利之间互相冲突、对抗的范畴内讨论。以“言论自由”为例,前者认为,言论自由本身的构成要件造成了其走不出自身的局限,犹如给自己画了一个圈;后者以为,言论自由权的行使可能会侵犯他人的人格尊严、隐私权等权利,这种对其他权利产生的不利影响是基于言论作为权利本身难以消除的制约性因素。上述两种思考的不同角度到底哪个更合理,此处我们暂且不议,因为不妨碍得出这样的结论——基本权利本身总是有界的。
(二)外在制约
所谓外在制约,是指为实现秩序、福利及公序良俗而对基本权利所必需设定的且为宪法价值目标所容许的制约。此处的“秩序、福利及公序良俗”可统称为“公共利益”。[2]可见,“外在制约说”认为“公共福利”乃是基于基本权利之外的对基本权利的制约。[8]86根据这种理解,宪法所保护的利益除了私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外,还包括公共利益,二者是不相同的法益。基于这样的预设,利用公共利益的公共价值对抗基本权利的个人价值,从外部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这种观点在“限制基本权利”正当性的领域中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几乎没有哪篇文章在论证本课题之时不涉及公共利益问题,足以说明这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我国宪法中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有如《宪法》第10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第3款:“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37条第2款,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公安机关可以对公民进行逮捕。第40条,为了刑事侦查的需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可以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等等。可见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无边界的,不受任何管束的。对此,“存在即合理”的断言并不能使我们“避而不究”,因为任何对基本权利的无正当理由的限制都是“权力的专制与暴政”。

表1 对日本学界关于限制基本权利的各种学说的归整*本部分根据芦部书整理,参见 [日]芦部信喜.宪法[M]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5-91.
备注:日本国《宪法》第12条中规定,国民对基本人权负有“为公共福利”而利用的责任;第13条则就国民的权利,规定:“在不违反公共福利的限度内”,有必要在国政上予以最大程度的尊重。此外,还针对经济自由(职业的自由、财产权),特别规定了可根据“公共福利”加以限制的意旨(《宪法》第22条、第29条)。
可见,无论是我国还是日本的各个阶段的学说,都将“公共利益”(公共福利)作为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似乎具有“不证自明”的正当性。有如陈新民教授所言:“宪法对人民基本权利,以在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前提下,许可国家以订立法律之方式来限制之。”[1]388-389
(三)对两种学说的合理怀疑
在探讨之前,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宪法一方面肯定基本权利的存在及保有和行使这个权利所赋予私人之利益,另一方面也承认这个私益可能会对公共利益产生威胁,所以这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隐秘的紧张关系。[1]389“外在制约说”显然是看到了这一点,并向前“勇敢一跃”:公共利益是外在于基本权利的,而且构成限制个人利益的理由。基于二者互相对立的看法,如若对二者进行取舍,则必然采取“利益衡量”的方法——表面上将“基本权利”和“公共利益”分别置于天平的两端以区分“孰轻孰重”,进而“舍次而取重者也”。然而,现实情境是——以公共利益作为基本权利外在限制的观念,它相对于基本权利而享有的优先级似乎有着准公理的属性——不证自明的必然性与合理性。[6]此外,“公共利益”长着一张“普罗米修斯之面”,其本身极为抽象,为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除了具有利益内容的不确定性及受益对象的不确定性外,更随着国家任务范围扩充甚至政策的转变而发生变化,如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必然会引发相关领域公益的变更,进而言之,这种抽象性使得“公共利益”与《刑法》上“罪恶滔天”的“流氓罪”有着剪不断的“暧昧关系”。
在“公益优先”及“公益”本身高度抽象的阴霾之下,以下的担忧便不是“杞人忧天”了:公权力机关可能以公益为借口去随意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甚至直接掏空基本权利的内涵。现实中,部分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强拆屋舍、征用土地显得那么随意,不就是鲜活的例子吗?
基本权利的“内在制约说”又如何呢?“内在制约说”确实可以避免“外在制约说”中由于公益泛滥导致的危险。因为“公共利益”与“基本权利”在宪法上并非“分封而治”的关系,公共利益不是外在于基本权利的法益,而是基本权利的构成要件自身。也就是说,“公共利益”并不是与“基本权利”对立的,更不是要实现对基本权利的统治。这里强调的是,基本权利不破坏其自身赖以存在的社会秩序就是“公益”的实现,为达致此目的,基本权利就需要自我限缩。[6]正因为如此,“内在制约说”可以与“公益优先”道别,也不必有基本权利被彻底否定的担忧。
那么,“内在制约说”是不是就能够为基本权利的限制提供足够的正当性证明了呢?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权利应在何种范围内被保障”是其关注之核心,而“权利的限制”不过是在解决了“权利的保障范围”问题后自然被解决的第二层次的问题。[6]看似完美的“内在制约说”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出了大麻烦。因为“内在制约说”很可能会在基本权利构成之初,预先排除某一部分的内容,而该部分的内容本是正当的、合理的。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可以预见某些基本权利的内涵极易被掏空,成为一种“徒有其表”的宣扬,当公民受到侵害请求国家救济时,却发现该项合理主张本就不属于基本权利的范畴。可见,“内在限制说”不利于基本权利保障范围的扩大,更有限制权利生成的威胁,这与人权发展的趋势是不符的。[6]
综上所述,“外在限制”的最大问题在于我们无法捉摸“公共利益”的真实面貌,这可能会带来公益对基本权利的“专制与独裁”,压缩基本权利的生存空间;“内在限制”虽然内容确定,“一览无遗”,可以排除“外在限制”的危险,却又内在地、本质地限缩基本权利的内涵、外延,使之几乎不可能突破自身的牢笼,更不可能扩大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这与不断涌现的新兴权利呼唤扩大宪法保护范围的发展趋势不相融合甚至相悖。如果将存在“公益优先”危险的“外在限制”比作对基本权利的“直接暴力”的话,那么,畏首畏尾的“内在限制”就是对基本权利施加的“冷暴力”。有鉴于此,我们宁可接受可以施加控制的“外在限制”,也不愿承认对不断涌现的新兴的基本权利“不闻不问”的“内在制约”的主体地位,因为保守、僵化更难以忍受。从这个方面来看,限制基本权利并非完全基于公益的考量,亦是实现基本权利的必要的牺牲,是迂回的“曲线救国”式的选择。
二、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有学者将其称为"基本权利的限制的合宪性审查",参见许育典著:《宪法》,元照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47页;有学者将其称之为"基本权利限制违宪的阻却事由",参见张翔:《基本权利限制问题的思考框架》,载《法学家》,2008年第1期。
正如上文已经论及的那样,我们接受基本权利的“外在限制”的主要地位(即认可“公共利益”成为衡量是否限制基本权利的理由)是基于“公共利益”的可控制性,即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或者方式将其“圈养”于宪法的视野之内。因此,在广袤的法律的原野上挖掘一道道田垄便是接下来的首要任务。
许育典教授将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分为两个层面,即先就形式的规范面,判断是否存在宪法保留、法律保留或基本权利内在限制;再就实质的限制手段面,检验其限制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即判断其限制目的是否正当及其手段是否必要。[9]147这两个层面可以构建出一种立体的合宪性审查模式。进而,我们认为,就每个层面而言,亦不能对每个原则“等而视之”,必须有所侧重,或以某个原则为主,辅之以其他原则。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带来的困惑,如果只对“作为形式规范面审查的法律保留原则”以及“作为实质限制手段之比例原则”作具体考察,相信能对解题有所益助,并且也能获得谅解。
(一)基本权利的以法律限制——法律保留的原则
之所以选择“法律保留原则”作为形式规范面审查的代表性原则,是因为其与公益条款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公益条款是以宪法本身对一个涉及基本权利的限制方面,就目的上的许可性问题所作之规定,而法律保留原则则是涉及执行这个目的的许可性方面的执行工具之制度——即必须由法律来限制。
所谓“法律保留原则”是指如果宪法已将限制基本权的事项,保留给立法者,容许立法机关透过法律加以限制,而且“行政机关”的行为,也取得此形式上的法律限制依据,这里的基本权限制,就是合宪的法律限制。可见,该制度强调任何情况下对基本权利的限制都必须以代议机关(国会)通过的法律为准,与之相适应的是,涉及一个(限制人权)的解释时,应该采取最有利公民权之方式。[10]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法律保留和宪法授权*“宪法授权”原则渊源于《法国人权宣言》第4条,是指涉及限制公民基本权利时,只能由宪法授权国家最高立法机关通过(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来实现,否则须承担违宪的后果。参见汪进元著:《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55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说宪法授权讨论的是法律保留的依据问题,而法律保留则是宪法授权的具体化,宪法授权主要是一项拘束立法机关的权利限制原则,而法律保留则是用来约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一项限制原则。法律保留原则源于分权结构模式下的法治理念,即对民意机关的信任和对行政权力的恐惧。[11]56
1.立法模式
那么,如何看清“法律保留”的脸庞呢?一般而言,宪法言明“依/通过/根据法律”或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如前述我国《宪法》第13条第3款有关征收或征用公民私有财产的规定;又如第34条规定的“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只能依靠法律”等等。在法律制度发达的国家对于法律保留的规定则更为精细,如德国根据规范限定的繁简程度,德国学者将基本权利条款中的法律保留区分为简单法律保留、特别法律保留与无法律保留。在简单法律保留中,立法者所获授权的弹性最大;在特别法律保留中,立法者进行利益衡量的权限,因为宪法的周延规定被大大限缩;而对于那些根本不受法律保留限制的基本权利,立法者的这种权力则被彻底排除了。[12]
2.重大性理论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审理一连串有关教育法中,提出“重大性理论”,意指任何涉及人权的事项,诚然是立法者的立法范围,同时也是立法者的专属权力,不得任意授权给行政机关或其他组织,对于牵涉人权之重大部分则必须保留予立法者为之,是权力与责任、权力与义务的统一。这一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关切:现代国家的职能不断扩大,如果一切涉及基本权利的事项都必须由国家立法规定,就会造成立法的过重负担和国家效能的低下,因此,现代国家普遍将大量的立法事项转而授权行政机关为之,这其中也包括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权。可见,这一理论不仅是要求立法者对涉及人权之事项要不要立法的问题,也是如何立法的问题。其致力于遏制立法者的滥行授权行政机关为立法之行为,督促立法者在处理有关人民权利时,须如履薄冰地做仔细的考虑,而不可推向行政机关代为决定,[1]406-408这对于充分地、实质性地保障人权而言,有极重大的意义。
3.法律保留原则在具体适用中的规则
德国《基本法》第19条的内容*德国《基本法》第19条(1)只要依《基本法》之规定,可以依法律或经法律授权来限制基本人权者,该法律必须是广泛的,而非只对个案适用之法律。此外,该法律必须指明该(被限制)基本权利的条款号数;(2)在任何情况之下,基本权利的根本内容皆不可侵犯。可以分为三个规则:个案法律之禁止、指明条款要求以及根本内容之保障。所谓“个案法律之禁止”即要求限制人权的法律必须具有普遍性、抽象性与延续性,使得适用该法律的当事人及案件具有对象上的一般性、数量上的不确定性以及效力上的持续性。可以看出,此规则,主要是基于宪法上平等权的考虑,以保证某些人民不会额外享受法律所赋予的特别利益或者不会遭到由法律所加诸的特别不利益之待遇。所谓“指明条款要求”指立法者对人权的限制应明确无疑,以避免在日后的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争议——被任意地扩大或缩小法律的本来意图。如果违反此规则,则会导致法律违宪之后果。“根本内容之保障”规则是指任何人权之根本内容(即核心)不得侵犯,否则法律将被宣布违宪。正如黑塞所言“当某项措施使受到限制的基本权在共同体生活中再也无法发挥其功效时,那么则完全是无视上述(基本权,笔者注)内容了”。[5]267但究竟如何寻找基本权利的核心成为我们新面临的问题。也许T. Maunz的办法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启示:每个人权的规定,至少须保留起码的内容,作为人类尊严的内容之表征。而且,立法者在立法时,也要受到比例原则的拘束,不立不必要之法律限制人权。[1]451
(二)基本权利限制的比例原则
如上文所提及,台湾学者许育典教授认为,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的合宪性审查之第二方面乃是“从实质手段面看限制的合宪性”,概括为三点:特定公益目的的检验*具体包括“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和“增进公共利益”。、必要性的检验*具体包括适合性检验、必要性检验。以及合比例性原则。可以看出,许教授所言之“实质手段面”即为一般意义上的“比例原则”内容之详尽化。我们认可许教授的观点,即比例原则构成对基本权利的“限制的限制”之实质审查标准。*需要说明的是,对"限制的限制"之实质审查标准,除以德国"比例原则"为代表的一元标准外,还有以美国"双重基准论"为代表的多元标准。后者认为各种基本权利的地位并不相同,某些具有"基础性"和"优先性"的权利应该受到更严格的保障,而对其他的一些权利的立法限制则只是受到较为宽松的审查,从而形成了以基本权利分类为基础的审查限制基本权利的立法的一系列、多层次的标准。本文限于主题对此且不予展开。
所谓宪法的比例原则,就是审视一个涉及人权的公权力主体的主观目的与其采行的手段之间有一定的比例,即是否满足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的比例原则三个要件。“妥当性原则”即“目的符合性”及“目的切合性”。需要指出的是,根据联邦德国宪法法院的见解,即使只有部分能达成目的,也算是符合这个原则的要求。[1]416“必要性原则”即“尽可能最小侵害原则”;“狭义比例原则”即指手段与目的符合必要性原则的同时,应当将对人民权利的侵害风险降至最低。比例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标准,主要体现为对立法裁量及行政裁量之限制。
1.立法裁量之维——目的性之审查
由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假想式的因果关系。为了达成目的,才采取手段。于此相关的问题是,一个立法者所预期的目的能否在客观上达成目的?如上文论述的那样,“法律保留”原则是基于人民对立法机关的信任,那么,立法机关是如何表明对人民的“忠心”的呢?方法是——制定良法。根据传统分权理论,立法机关针对社会发展状况,拥有决定预期目的的权限,法院似乎应当肯定立法者拥有相当程度的政策决定权。正如学者所言,“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尊重立法的选择,符合现代宪政的权力分立和民主诸原则,但这又确实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一种不确定性的后果。”[13]224那么法院如何适用比例原则审查立法机关的立法裁量行为,以避免将一个法律的合宪性问题转换成法院对该法律合宪性的确信问题呢?*联邦德国宪法法院早期的见解认为,只要立法者在立法时,认为这个目的有经由所采取的手段可以达成的确信存在时,即使以后到宪法法院裁判时,该立法目的仍无法由其采纳之方式达成时,或只一部分达成时,该法律并不当然违宪。这种审查态度的出发点,是偏向肯定立法者主管的立场,承认立法者对将来事件发展的预估可以容有错误之余地,显然是过度维护立法裁量权,实际上是将一个法律的合宪性问题转换成法院对该法律合宪性的确信问题。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432-433页。“立法者不当预期”标准乃值得采纳的标准。此标准有两重含义:第一是在立法时,就是明显错误的考虑,如基于错误的数据、认识等,即预期错误。法院对此种立法可以直接宣布无效,或是命令立法者予以改善;另一种不当的预期是立法者当时的考虑完全无误,只不过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使得立法者非可预料的后果产生,使法律已不符合当初之立法要求,可以称之为“不良预期。对于此种立法,宪法法院只能要求改进,无直接宣告违宪之权限。正如德国R. Stettner教授所称,这种区分法,主要是着眼于避免对立法者作太大的钳制,以免立法者丧失立法勇气,而且,任何立法总不免有瑕疵,可由政治的方式予以改进,不必完全由法院来矫正。[1]434
2.行政裁量之度——对行政裁量行为的必要性及比例性审查
“宪法是静态的行政法,行政法是动态的宪法”,比例原则在行政领域的出现频率远高于宪法领域。一般认为,行政主体依据法律作出行政行为之时,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包括不得违反授权之目的及限度等。“在选择裁量之情况下,一个行政措施,虽然在法律所许可(授权行政机关选择)之范围内,原则上,其妥当性较不致发生问题(否则立法者不会制定该法条),但是,对于必要性(有无绝对必要)或是比例性(不成比例的负担)的原则,则非可非可由行政机关自由裁决。”[1]437易言之,对于行政裁量的必要性及比例性的审查任务自然落在了法院的手中,成为法院审查行政裁量行为有无侵犯基本权利的法宝——同能达成目标之手段是否较为温和?是否采取了“杀鸡取卵”式的粗暴行为?
三、代结语:权利保障与权利限制殊途同归
现代社会的治理方式正在由传统的“压制—服从型”向“服务—协商”型转变,这种转变暗示着深刻的社会变革,其核心理念便是强调权力与权利的良性互动。在权利与权力之间,权利是目的和灵魂,权力是手段和工具。不论是权力对权利的积极保护,还是权力对权利的消极限制,皆以人权保障为终极价值取向;如果说权力对权利的保障是权力对权利“无处不在”的眷爱,那么权力对权利的限制则是权力对权利“于无声处”的关怀;权利限制与权利保障也正是在人权光辉的普遍照耀下实现了二者的趋同归一。立法,作为国家权力行使之重要领域,在法治、宪政已成历史主旋律的当代,其势必得以人权保障为权力运行之基线,以权利实现为权力前行之航标;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立法也只有在人权明灯的指引下,才能始终沿着宪政轨道有序行驶,并不断促进人类福址之增长。[2]
个人权利不加限制地行使势必会引发其与公共利益或其他人权利之间的冲突。解决权利冲突的关键所在,就是通过一种方式尽量清晰地明确权利权能,从而有效地确定权利界限。因此,协调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及个人权利之间的冲突是宪法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基础。[14]虽然“内在限制”与“外在制约”理论均存在难以克服的障碍,但对基本权利的限制是权利本身内在与外在的共同要求,因此,更重要的是如何对“限制”进行“限制”。因此,归结到我国的宪法,不应当对限制权利的规定“三缄其口”,遮遮掩掩,反而应当明需要对权利进行限制,同时确定对各权利进行限制的适用情形,以保证权利领域“霸王条款”的逐渐消逝。在具体规定上,虽然我国宪法已经表明“基于公共利益”可以限制财产权,但这样的规定显然过于简单,在现实中带来的弊端可能远远大于收益,因此,有必要将“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的精神贯彻到文本之中,从而增强法律与操作的统一性,才能真正推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向前迈进。
[1]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胡肖华,徐靖.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正当性与限制原则[J]. 法学评论,2005(6).
[3]韩大元.宪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林来梵.宪法学讲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黑塞.德国联邦宪法纲要[M].李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6]张翔.公共利益限制基本权利的逻辑[J]. 法学论坛,2005(1).
[7]张千帆.宪法学导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8]芦部信喜.宪法[M].林来梵,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9]许育典.宪法[M].台北:元照出版公司,2006.
[10]秦前红.论我国宪法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规定[J]. 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11]汪进元.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构成、限制及其合宪性[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
[12]赵宏.限制的限制:德国基本权利限制模式的内在机理[J]. 法学家,2011(2).
[13]徐继强.加拿大最高法院之“奥克斯标准”:基本权利的限制与反限制[J]. 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8(2).
[14]毛俊响.国际人权公约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政治与法律,2010(9).
[责任编辑:岳林海]
On Restrictions of Basic Rights and Their Review Principles
MA Rui-chen
(Wang Jian Law school, Suzhou University, Suzhou 215006, China)
The restrictions of basic rights are the unity of the inner mechanism and the extrinsic demand of rights. However, they both have some abuses. On one hand, the inner restriction theory is too prudent to restrict new rights in the scope of protection. On the other hand, the outside restriction taking “public interests” as its core is hard to depict its epitaxial.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regulate the “Restriction’s restriction” by “the principle of legal reservation” and “the proportion principle”. Specifically, the principles of the former are “the forbid of the law for a case”, “the specified term claims” and “the insurance of essential elements”; while the latter is realized by “the legislative discre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ve discretion”. The restriction and the guarantee of basic rights are the same thing on the level of basic right protection. That is: we can realize the equality of different practical rights by “restriction” and guarantee the citizens to enjoy their rights in operation.
restriction of basic right;restriction’s restriction;principle of legal reservation;proportion principle
2015-06-02 作者简介: 马瑞辰(1991-),女,江苏扬中人,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1671-5977(2015)03-0041-06
D921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