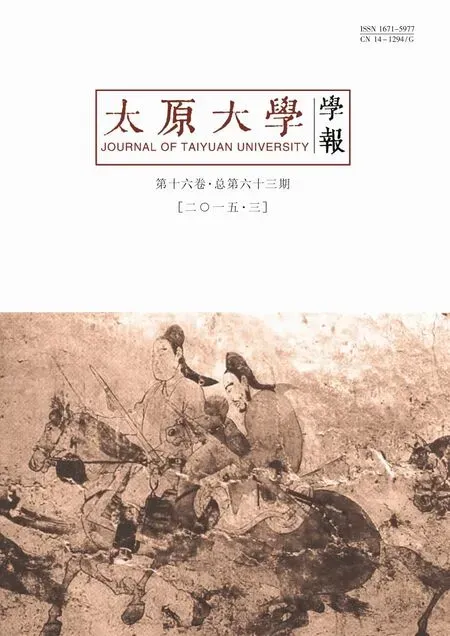无处安放的生命
——试析《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身份认同问题
吴 潇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无处安放的生命
——试析《野草在歌唱》中玛丽的身份认同问题
吴 潇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关注种族、阶级等其他社会规范与性别的交叉影响,是当下性别研究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将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身份认同”问题作为切入点,以文本细读的方式梳理小说《野草在歌唱》中主人公玛丽在婚前婚后经历的种种身份认同困境,并结合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深刻揭示出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
《野草在歌唱》;玛丽;性政治;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兴起的课题,它关注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作为个体的人如何通过建立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认同关系,来获取合理的自我认知,从而在不同的社会秩序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1]37。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表征,我们每一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会拥有多种身份,它们有的归属于性别或是血缘关系,也有的来自不同种族、阶级的划分,如果这些按照不同标准分类的身份在某个严酷的环境中产生了尖锐的冲突,就很有可能对一个人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英国著名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的成名作——《野草在歌唱》就讲述了这样一个由于身份认同错位而招致不幸的故事:南非的城市姑娘玛丽与农场主迪克缔结了一桩错误的婚姻,从此她陷入了女性、白人、穷苦白人这三重身份的挣扎之中,最终在几度精神崩溃之后被黑人摩西杀害。我们可以透过她短暂而悲苦的一生去追溯自我身份认同的失败是怎样酿成个人悲剧的。
一、从单一到多样的身份认同
倘以结婚为界来划分玛丽的一生,婚前她以性别为主导身份,婚后则混同了多重身份。但是,她在各种身份的转换和碰撞之中常常感到茫然无措,无法认同,所以无论处于哪一个阶段都没能享受到真正的幸福。我们只能看到一个面对外部环境的压力时,内心自我被不断地撕扯、挤压,永远无法摆正自己的位置,永远浸泡在孤独与恐惧的苦海里的女性形象。
(一)婚前
玛丽在婚前一度扮演的是一个类似于单身贵族的角色,她在职场生涯中已经做到了经理秘书的位置,拥有稳定的收入,她沉稳矜持的性格赢得了女性朋友的尊敬和男性朋友的信任,然而好景不长,性别身份的束缚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来明显。当她无意中听到友人对自己婚恋经验的议论后,她的内心头一次出现了自我怀疑。
实际上,这时候的玛丽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根本没有任何了解,她的生活水平也没有困难到需要依附婚姻来实现个人价值的地步,只是她的自信建立在别人的目光之上,她害怕那些言语中含有的道德审判的意味,于是她只能开始按照社会传统道德给女性指明的道路去走,去寻找一个丈夫。
(二)婚后
对于玛丽敏感脆弱的神经来说,仅仅是女性身份就已经叫她备受折磨。而当她跟随丈夫到农场定居后,就陷入了更大的精神牢笼里。她首先没办法接受的是自己瞬间从一个都市白领变为了乡村农妇,被限制在狭小的家庭空间里,隔绝在一切现代文明之外。她不想承认自己的贫困处境,甚至为了延续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而疯狂地操持家务,一旦无事可干就会陷入绝望的情绪里。
至于丈夫,随着了解的加深,她像母亲怜悯孩子一般同情他的软弱无能,同时又憎恶他身上男性力量的萎缩,这两种感情都与妻子的身份无关。这时候出现的帮佣摩西,强健有力且细心体贴,成为了她内心苦闷的唯一出口。但不幸的是,他是一个黑人,一个在南部非洲被认为是“野兽”、“畜生”一样的东西。即使她的生活可能比黑人更精光赤贫,但她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白人,她属于上层统治阶级的阵营。因此,玛丽独自承受着三重身份带来的巨大的煎熬。
二、基于两性关系的身份认同
小说中有两句关于他人对玛丽的评价非常有意思,这也是让玛丽本人念念不忘的魔咒。一句是因为她早年单身时被朋友在私底下议论“不是那么回事”[2]36;另一句则是嫁到迪克的农场之后,其行事方法被说成“不像那样”[2]201。玛丽并没有意识到这两句话给自己造成困扰的真正原因——性别身份、种族与阶级身份的要求在无形中规范和控制人们的行为,并且后两者建立在前者之上,它们借助语言的形式来暗示玛丽,她没有按照自己身处的群体认可的方式活着,就必定要背负上孤僻怪异之名。那么,玛丽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作为女性的弱势心理
1.缺乏自主意识
小说中,初次出场的玛丽可算是个了不起的“现代新女性”了,她拥有能够充分展现自己才能的工作,住在满是朋友的女子单身公寓,更重要的是她有足够的薪水来保证她的娱乐消费,做一个有尊严的体面的城里姑娘。可是,她却并不是一个清楚自己需要什么的人。她的精神世界非常荒凉,只装得下时髦电影和通俗小说。她的先天条件十分平庸,后天又没有树立清醒的目标来指引自己的行动,所以很容易安于现状,被别人有意无意的评论左右。所以,她会无条件地接受社会传统道德观念,将婚恋上的成功作为女性自我成就的首要衡量标准,而不管自己是否真的需要一个伴侣。
这样一来,当玛丽意识到自己的情感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尊敬和满足的时候,就很容易陷入惊慌失措中,最后只能不顾一切地抓紧自己根本就不了解的迪克。玛丽的闪婚是她屈从于性别身份规范的结果,并非出于本心,所以她不会得到真正的心理认同感,反而在寻找救命稻草的过程中承受了不小的精神折磨。与其说是那时候所有人都在逼着她结婚,倒不如说是她自己内心想要借助婚姻关系来逃避现实的尴尬,只是当她意识到这次逃避是个彻底的错误时,她已经把自己成为自由人的唯一机会给弄丢了。
2.来自家庭的影响
玛丽的童年家境凋零,这种成长经历不但消灭了她对幸福婚姻的所有期待,也让她暗暗发誓绝对不能成为母亲那样歇斯底里的穷人。可是她没有察觉的是,母亲的女奴思想已经潜移默化到了她的骨子里,即女性天生就扮演着悲惨、顺从的角色,总需要依附他人才能立足。
就是因为这个致命的心理暗示,尽管“她觉得自己好像在演戏一样,本来她演的是一出她所了解的戏,扮演的角色也是她适合的,可是现在却突然要她改扮一个陌生的角色。…她感到自己所演的角色和自己的身份不相称”[2]100,她依然想尽各种办法麻痹自己,依靠幻想在陌生环境里苦熬着;她明明比丈夫更精明果敢,可是为了不伤害迪克的男性尊严,也为了逃避自己不喜欢的农场生活,玛丽固守着男女分工的界限,任丈夫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她从来都将摆脱困境的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甚至临死之前还幻想新来的农场助理能救她。就这样,她软弱的天性决定了她一定会被性别身份紧紧地束缚住,最后如宿命轮回一般走上了母亲的老路。
(二)多重身份认知的捆绑
嫁给农场主迪克之后的玛丽,落入了社会精心编制的一张权力大网之中,她一下子拥有了三种身份:生理上的女性,阶级结构上的穷人和种族意义上的统治者白人。一方面,这三种身份的实质都是支配与从属的权力关系,但是另一方面,正如米切尔在《性政治》中揭示的那样,“我们这个社会,一切通往权力的途径都完全掌握在男人手里”[3],因此,当三组关系相互交织在一起,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生发出来的身份碰撞就极为激烈。
1.富裕白人与穷苦白人
白人与穷苦白人本来是同一个种族群体,可是,在经济层面他们的社会地位又是各有高低的。富裕白人对穷苦白人的心态很复杂,一方面这些人的窘迫让他们看不起,另一方面又会尽力帮助他们,这不仅仅出于亲近同胞的情谊,还隐含着一种为了维系白人高于黑人的社会结构而不得不做的努力。
玛丽生活在一个濒临破产、勉强支撑的白人家庭里,她的邻居查理夫妇虽然时刻觊觎着他们家的农场,但是出于白人的种族立场又愿意主动前来交往。这对夫妇的态度唤醒了玛丽身上属于穷人的敏感和自尊,她受不了哪怕一个异样的眼神,便拒绝了一切善意的邀约。而草原上地广人稀,农场主们的住所大多隔得很远,这样就把仅有的社交可能都切断了。所以,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她不合群的生活方式使得她不仅没能融入自己同族的圈子,获得某种身份上的归属感,还被同胞们视作骄傲自大,到死都没有得到大家的同情。
2.白人与黑人
玛丽第一次真正接触到种族歧视文化的时候,在现代文明都市中浸淫多年的公平意识还未退去,她对迪克称呼土著佣人为“老畜生”一度感到非常不习惯,也会反省自己对佣人的粗暴态度。然而,父母自幼的教育毕竟给予了她身为白人的优越感,她很快就能熟练使用自己手上唯一的特权——在黑人身上发泄对生活的不满。于是,她用近乎体罚一般苛刻的方法逼走了一个又一个佣人,从一个被剥夺了所有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欺凌他人,甚至是黑人女同胞的白人独裁者。她从这种权力关系中获得快感,将之视为唯一的尊严。
但是,当玛丽代替生病的丈夫去矿工院监工时,她身体里作为屈从者的女性部分又颤抖了,她的行动变得犹豫,黑人土著们大胆的讥笑让她羞愤难当,接连想到使用家犬、皮鞭、言语威胁等等手段来为自己壮胆。尽管玛丽面对的是一群比自己“低等”的土著黑人,但他们毕竟是男性,她本能地意识到自己的虚弱,所以只能凭借外力来达到威慑的目的。也就是说,玛丽自小接受的种族隔离教育与善良顺从的传统女性身份产生了冲突,使得她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白人统治者。
3.男人与女人
这一层关系相对复杂,因为两性关系在男权社会里可以成为一切权利关系的起源。而女主人公玛丽尽管在对待不同男性时有不同的表现,其性别身份发生不同程度的错位,但最终还是以屈从告终。
首先,玛丽与迪克。从表面上看,这是一对性别气质被倒置的夫妻。迪克善良温顺,是个被贫穷摧毁了坚强意志的人,终日为自己的无能感到自卑与愧疚;而玛丽身上则时常表现出传统认知里偏向男性的性格:她使用一系列铁腕政策来惩罚偷懒的黑奴时显得凶狠决绝;她计划要逃脱家庭桎梏时始终保持着冷静果敢的态度;当她决定改变家里的经济条件,就不顾丈夫的情感逼其种植烟草,不惜破坏农场生态环境,表现出冷酷激进的一面。并且,夫妻两人之间的斗争乍看之下也好像总是以玛丽取胜,迪克妥协告终。然而,这并不代表迪克就完全丧失了其家庭权威的地位。
所谓男性气质或女性气质“属于社会性别范畴,与男性中心社会的性别控制和规范有关”[4],对人们形成后天的自我认知有重要影响。在整个父权制文明笼罩下的社会里,迪克再平庸卑琐,仍然是一家之主,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支柱。而玛丽尽管有着成为一个积极行动者的潜力,但她必将因为无法调和自身“男性气质”与女性角色定位的矛盾而最终退缩。小说中玛丽唯一一次大胆的抗争,是私自跑回城里,以为回到过去生活的地方一切就能重来,可是社会对一个已界中年的已婚妇女同样是冷酷的,职场的大门永远向她关闭了。于是,当她走投无路之际,她只能等待迪克来拯救自己。作为一个妻子,虽然她从来都看不起自己的丈夫,也不屑于谅解对方的情感,但她仍然不得不依附于男性权威之下。
其次,玛丽与摩西。暂且不论种族问题,玛丽与摩西之间的关系也是男女角力的一场战斗。本来在白人眼里,作为奴隶的摩西应该是一个非人类的存在,更别说有什么足以吸引人的男性特征了。可是,玛丽竟然发现了摩西身上充溢着健康强壮的阳刚魅力,这一超越了玛丽自身种族和阶级身份的发现让玛丽的内心充满了罪恶感。她曾经鼓起勇气抽了摩西一鞭子,被吓破胆的却是自己,摩西的鲜血让其真切感受到自己是在“对男性施以暴力,这让一贯对于男性权威习以为常的玛丽内心感到不安”[5]260。
而另一方的摩西,作者在书中很少对其进行正面描述,但是饶有意味地提到了两次他的“惊讶”表情:一次是玛丽因为摩西的请辞而崩溃大哭,另一次是玛丽在噩梦后向其表露暖昧。这两次事件打破了白人与黑人不可逾越的目光和肢体接触禁忌,前一次让摩西从此获得了与主人平等的权利,后一次则让他在女主人面前恢复了男性的身份,他们之间的权力天平由此发生了倾斜,“在玛丽的乖张与无常中,摩西第一次窥视到了男性对女性的性别优势,在玛丽逃避直视的目光里,她看到了男性的权威,直至服伺玛丽穿衣,并开始对玛丽有了隐形的支配权”[5]260摩西由一个被奴役的对象成为了情感上被人依赖的男人,他为此而得意。也正因如此,玛丽最后选择重拾白人的身份来对待摩西,伤害了他刚刚觉醒了的男性尊严,于是,他在一种复杂的仇恨情绪驱使下杀害了玛丽。
其实,从小说字里行间的暗示来看,白人女性与土著黑人之间由于各自身份造成的尴尬事件,玛丽并非个例,甚至许多白人男性与黑人妇女还育有后代。但是在南部非洲的社会氛围里,对待这样的事情具有双重标准,我们从查理与警长的谈话就可以听出来轻蔑的意味,他们认为“在这个国家里,女人在这方面通常都很差劲的…他们完全不懂得怎样对付黑人”[2]18。这样说其实是因为,本来白人男性对于自己生理上弱于黑人就感到自卑,如果白人女性竟然被黑种人所征服,那就会从根基上挫伤白人的父权中心制,从而动摇白人的统治地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约而同地对玛丽的死因持冷漠和掩盖的态度。相应地,女性之所以更容易与土人关系紧张,正是由于在两性互动中附加在她们身上的身份意义要比男性要更加复杂,她们越过障碍的可能性更小,因此受到的内心谴责就越沉重。
(三)作家本人经历的投射
跟之前的英国女作家相比,多丽丝·莱辛的作品明显拥有更为广阔的文学视野和更为独特的文学题材,这得益于她早年多国背景的生活经历以及20世纪以来逐渐扩大的女性自由空间。多丽丝·莱辛的父母皆是英国人,受一战的影响举家搬至伊朗西部,后又迁移至德黑兰,多丽丝·莱辛5岁之前的生活都是在这里度过的;之后他们又迁居南非的南罗德西亚(现津巴布韦),她在这里成长、学习、工作、结婚,度过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直到三十岁才重返伦敦。
在国外的岁月里,由于母亲严格的教育和种族观念,她不能跟当地人完全融合在一起,好不容易重归故乡却又被当做海外殖民地的流亡者,受困于经济原因只能住在贫民窟里,甚至被打上非洲作家的标签。在她身上交融着多种文化因子,但又自觉与其中的每一种保持一份疏离,因为她觉得自己“在哪里都不适合”[6]。《野草在歌唱》发表于作家回英国的第二年,她多少将自己骨子里缺少的身份认同感投射在了女主人公玛丽身上,写一个同样在众多身份标签中无所适从的女人,看她怎样渴望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却总是遭遇生活无情的碾压。从这个层面上说,《野草在歌唱》中玛丽面临的身份认同障碍实际是作者本人心结在小说中的复现。
三、身份焦虑的艺术表现
小说的书名《野草在歌唱》取自著名诗人T.S.艾略特的诗作《荒原》,而作者笔下的南部非洲也确实呈现出带有末日气息的荒原景象。作者用神秘恐怖的自然意象和冷峻而细腻的笔调,烘托出主人公在多重压力集结下的现实处境,并深刻剖析了玛丽因为身份认同障碍导致的心理焦虑。
(一)不同意象的象征意义
1.人物情绪的外化
南部非洲郊野的天气酷热难忍,尤其令玛丽烦心的是,由于贫穷他们家一直只能使用一个波纹状的“铁皮屋顶”,它“泻下来那一股损人精力、耗人元气的热浪,真使她受不了”[2]69。这屋顶的身影在文中反复出现,仿佛时时提醒着玛丽家贫四壁的凄凉现状,使她死气沉沉,遁入消极。
然而,当她为自己找到一点生活目标,比如开始为种烟草致富的梦想努力时,她内心的焦灼因为有所依托而变得平静,甚至连炎热也变得不那么可怕了,当她满怀希望时她对迪克说“今年热得不怎么厉害,迪克回答她说,从来没有哪一年比今年热得更厉害了”[2]18。所以,小说中外部环境的“热”恰好反映着人物内心的郁积之“热”,这种“热”是一种自我认知陷入混乱后寻求解脱的渴求,是原始生命力得不到满足的焦躁之感。这种自然气候与人物心理节奏的同步也表现在非洲草原的冬季,当天气开始凉爽的时候,玛丽也正沉浸在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之中,她憔悴不堪的身心暂时得到平静与休息,与丈夫的关系也相对缓和。
2.精神压迫的变异
疯狂呜叫的昆虫、低矮的灌木丛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自然物象,它们常常以一种敌对的态度与代表着人类文明的住宅处于对峙状态,仿佛随时要侵占和挤压人类的生存空间。在女主人公玛丽的想象中,蚁冢、灌木丛、幽暗的小树林以及昆虫的呜叫都在找机会吞噬掉自己的屋子,把一切变成废墟。这其实是变相地反映出现实环境对女主人公玛丽的心灵倾轧:他们的房屋建在人烟稀少的小山坡上,环绕四周的树木就像一座没有缝隙的监狱,正如玛丽多年来失去了群体的庇护,孤独禁闭在狭小空间里的生活现状。而这些被拟人化的动植物,在结尾一章里更是与风雨雷电一起,作为大自然强大摧毁力量的代表,照亮了玛丽临死前的忧惧,预示着人物将要迎接的悲剧命运。
3.内心欲望的投射。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不是荒谬的;它们也不意味着我们一部分观念正在休眠而另一部分开始苏醒。相反,它们是完全有效的精神现象——愿望的满足。它们与可理解的清醒时的心理活动是互相接续的,由高度复杂的精神活动构成”[7],也就是说,梦境可以通过潜意识实现内心深处压抑的愿望,它是人类深层欲望最真实的表达。小说中玛丽一直强行压抑着自己对摩西的暖昧情愫,然而她在自己的梦境中却看见了父亲和摩西巨人般的身躯。父亲的形象可以看做是原始情结和绝对权威的象征,他与摩西的形象一同出现在女主人公的梦里则暗示着摩西强健有力的男性形象唤醒了玛丽对于正常情感的渴望。所以玛丽在醒来的时候感到恐惧,她意识到在自己的身份地位与自己实际上对摩西产生的依赖感之间有着互不相容的矛盾。
(二)冷峻细腻的叙事风格
1.第三人称叙述的反讽效果
首先,小说开篇之时谋杀案已经发生,作者透过初到南非的英国青年托尼的眼睛去看眼前发生的一切,警察们讳莫如深的处事态度在托尼的心里引发了现代文明与后殖民地文化的激烈碰撞,他与观众一同疑惑着:为何作为事件最大的受害者——玛丽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甚至她的死亡原因成为了一个禁忌。这样的描述已经营造出了一个扭曲怪异的社会氛围,从侧面衬托出女主人公生前所受内心折磨之剧烈。如果说这件凶杀案的始末就是一出悲剧,那么这个压抑畸形的社会就是舞台背景,这样的故事只能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也只有这样的环境中才能酝酿出这样的惨剧。
接着,作者便一直将小说主人公置于被观察的位置,在她理性的凝视下,女主人公玛丽一步步步被重重身份关系束缚住,滑向了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双重贫瘠。在作者对玛丽一生轨迹的平静叙述下,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女主人公这种被多重力量贬抑和迫害的处境是那个时代南部非洲贫苦白人女性的写照,她们是哲学意义上的“绝对的他者”[8],在任何一种双方关系里都是偏弱的,是丧失了主体性的那一方。一个人生活在世上需要找到符合自身期望的角色认同,如果他一直处于混沌状态就容易对自我的存在产生怀疑,成为被支配的对象,因而也就无法赢得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对于玛丽这个个体来说,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尽管是大环境下身份认同错位造成的,但多少也得归咎到玛丽自身“怒其不争”的个性上,尤其通过其婚前婚后生活的对比,作者将其性格上的缺憾如实地暴露了出来。
2.重视精神状态的细节刻画
多丽丝·莱辛拥有女性作家独有的细腻笔触,她关注心理细节,将一个极度压抑,憔悴不堪的女性形象写得入木三分。玛丽在小说中的后半部分,已经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精神错乱,作者写她常常控制不住地自言自语和莫名其妙的哭泣,这表明她对于自我的消耗已经到达了顶点。而玛丽默许摩西一些僭越主仆关系的行为,并不是因为她想要借此挑战种族制度,而是身份认同的错位给主人公的心灵留下巨大创伤之后的消极表现。“可怜的玛丽只有在失去理性的状态下才能逃脱殖民主义的束缚,实现真正的自我,感受自然的人性”[9],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即使她不被杀害,也已经完全丧失了维护自我尊严的力气。
四、结语
总之,多丽丝莱辛通过描写小说女主人公玛丽的艰难处境既触及了普遍的人性问题,又诠释出了广义上的“身份认同”概念,即“某一文化主体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选择,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1],与此同时,也让我们深思:如今我们有幸身处于一个更为文明和开放的时代,当全球化的汹涌浪潮带来更多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时,我们应该怎样更好地处理不同身份认同间的矛盾,从而避免小说中的悲剧再次重演。
[1]陶家俊.身份认同导论[J].外国文学,2004 (2).
[2]多丽丝·莱辛.野草在歌唱[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凯特·米利特.性政治[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34.
[4]魏天真,梅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导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49.
[5]王丽丽.多丽丝·莱辛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6] Doris Lessing. Under My Skin[M].London: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1994:39.
[7]弗洛伊德.梦的解析[M].北京:中华书局,2013:123.
[8]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64.
[9] Roberta Rubenstein. The Novelistic Vision of Doris Lessing:Breaking the Form of cousciousness[M].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79:26.
[责任编辑:姚晓黎]
Life Nowhere to Settle——Analysis of Mary’s Identity Problem in The Grass is Singing
WU Xiao
(Humanity Culture College,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 510006,China)
The heroine of the novel the grass is singing, Mary had three identities; a physiological woman, a white in the sense of class, and an economically deprived person. Her triple identity brought her serious dislocation in the harsh environment of South Africa, made her bear the heavy mental stress which exceed the average women, and led her to the final tragedy life.
The Grass is Singing;Mary;sexual politics;identity certification
2015-06-10 作者简介: 吴潇(1990-),女,湖南宜章人,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20世纪欧美小说、戏剧。
1671-5977(2015)03-0114-06
I561.47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