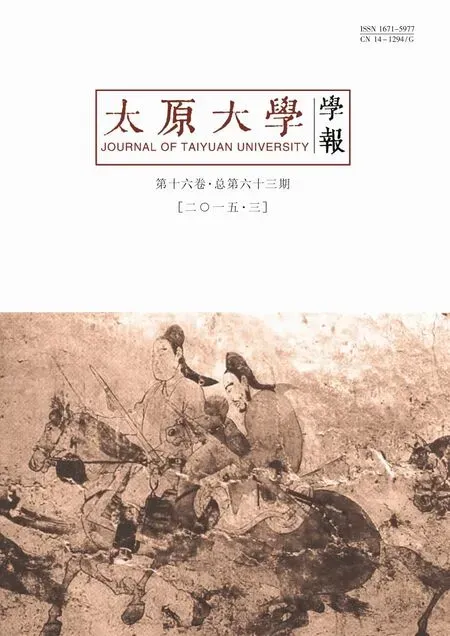“缺席”与“召唤”
——倪瓒“亭下无人”的美学诠释
孙 伟 伟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缺席”与“召唤”
——倪瓒“亭下无人”的美学诠释
孙 伟 伟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人物作为中国山水画的构成元素之一,对画面情节的补充和画家思想的揭示有着重要功能。而倪瓒在其画作里,有意将人的存在取消,从而使“空亭”这一意象符号成为一种哲学标志。“亭下无人”既是“在”的缺席,也是一种有所向往的“召唤”,其蕴含的美学意义和人文情怀有助于对倪瓒这位画家以及中国山水画所潜藏的思想性有更加深刻的探讨与分析。
倪瓒;缺席;召唤;“亭下无人”;美学
如果说现实社会是承载着主流抱负和生存之道的容身之地,那么山水幻境则为文人人格中另外一部分,即对心灵自由和灵魂独立的渴慕予以安妥的精神之乡。作为自然中能够和林泉烟霞对话的审美主体,山水画里的“或独坐平原,或支颐蓬户;或闲步于水边,或眺望于岩岫;或倚楼作沉吟之状,或凭槛为赏玩之容;或投携童策杖于汉溪挢,或拉友散步于丘壑;或振衣于高冈,或偃息于林麓”[1]214的点景人物,他们的参与给平静的画面加入了一定的生活情节,也成为创作主体“引情丘壑,往辙忘返”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在遍是山川林壑、人迹难至的世外高地,需要那么一立方米的空间,以便跋涉千里的旅者能够“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而为山水添加眉目,又为游人开辟落脚点的亭台轩榭便点缀在了青山绿水间,白云深处里。在这其中,因为虚空独立的形式,以及集“可行、可望、可游、可居”多功能于一体的亭子,成为山水画作中最常见的点景建筑。幽然独立于天地间的这座孤亭与亭中的存在者——人,以及亭外的广袤山水自成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世界区别于尘俗世界,却又衍生于它。在这个世界中,人对世界的领会与解释就于亭内展开。赵千里《荷亭销夏图》、刘松年《春亭对弈图》、刘松年《溪亭图》、蒋乾《抱琴独坐图》、唐寅《虚亭听竹图轴》等无一不填充人物活动的痕迹。正如舒尔茨认为:“人之所以对空间感兴趣,其根源在于存在。它是由于人抓住了在环境中生活的关系,要为充满事件和行为的世界提出意义或秩序的要求而产生的。”[2]1然而,这样的绘画逻辑在倪瓒的笔下得到了解构,人被从画里剔除,耐人玩味的是,有着“幽亭秀木”美誉的倪瓒画作,虽然杜绝了人的存在,却独留下和人有着剪不断联系的亭子,偏居于画面一隅,以低调却仍旧醒目的姿态聚焦着观赏者的视线。高居翰在《中国山水画的意义和功能》一文中说道:“在这样认读绘画的意义时,我们采用了一种可以被泛泛地称为符号学的方法:即我们把特定母题和构图特征视为含有意义的符号。符号学认为有一种表意系统,一种代码,是艺术家的同时代人无须细想或无须相互解释就能理解的。这种代码没有记载于当时的文本中,而是必须由我们去破译,必须由我们从绘画本身或者借助于绘画上的题款或其他文本所提供的线索去找出来。”无人空亭作为倪瓒在绘画创作中重复不断的一个意象符号,解开其背后的意义,便能通往画家最隐秘的内心世界。
一、拒绝沉沦,呼唤本真

图1 容膝斋图
有好奇者问过倪瓒亭中不著人物的缘由,他回答说:“天下无人也。”这个人正是象征着俗人以及俗人所代表的俗世的反面——真人。云林一生都在和俗作斗争。杨维祯在《霜柯竹石图》上题倪瓒:“懒瓒先生懒下楼,先生避俗如避仇。”现实生活中的云林也从来不和俗人交往,“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述怀》),不愿在尘世沉沦,“人以秋毫轩轾我,我心澹(淡)然如碧渊。何期失脚堕尘网,谈笑区中饱世缘”(《人我二首》)。这个俗人,海德格尔称之为“常人”,即以“非自立状态与非本真状态而存在”“庸庸碌碌的平均状态”[3]149的此在,而当时“纷攘千态,怪技百出”(《清閟阁全集》卷一《义兴异梦篇》)的社会,就好比此在的沉沦:“此在首先总以它自身脱落、即从本真的能自己存在脱落而沉沦于‘世界’。”“沉沦于‘世界’就意味着消散在共处之中。”[3]204所以,云林不想为这些俗人俗世动笔。而常人的消解让原本被遮蔽的世界呈现了本来的面目,这世界不同于烟火弥漫的现实人间,也不完全是文人墨客心心念念的山水自然,而是画家在涤荡了尘俗渣滓后,以一腔“逸气”还原的生命真实。这是一片荒寂的自在天地。荒,是荒寒。作为中国画历来的最高审美境界之一,而将人迹从画面中抹去的云林,他的荒寒,有着区别于其他画家的彻底性,是将现实的生活气息完全隔绝。因为无人,萧疏的林木与淡远的山水自成一派空灵的净地,仿佛亘古以来就存在的原初图景,所谓荒天古木,不过如此。难怪清朝画家布颜图赞绝:“高士倪瓒师法关仝,绵绵一派,虽无层峦叠嶂,茂树丛林,而冰痕雪影,一片空灵,剩山残水,全无烟火,足成一代逸品。”(《画学心法答》)这样荒寒无人的境界,便是恽寿平一直崇尚的“洗尽尘滓,独存孤迥”的生命至境。寂,是寂寞,是寂静,是空寂。“寂”,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释作“灭,涅槃之异名”。佛学中,寂灭常连用,指代一种无生的境界。寂不完全等同于静,更确切说,寂是通向生命的至静。佛家常说,“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然而云林的画境,已经静寂到一丝生命感也无。晚年的集大成之作《容膝斋图》(图1):天空没有飞鸟的痕迹,水面亦不见鱼群的跃鳞,永远空落的孤亭,也将地老天荒式的静默进行到底。这样近乎了无生机的画风,和六朝以来流行的气韵生动的主张似乎截然不同。
表面看来,云林笔下这个因人的缺席而“萧散历落,荒荒寂寂”的山川之境,是对所有在世存在的拒绝,创作者在自我织筑的梦境里独自玩赏着寂寞与孤独。然而,事实却不尽是如此。那静伫于岸边林下岑寂无人的孤亭,其四面敞开的姿态却隐隐暗示着一种期待的呼唤,呼唤本真存在的开显。海德格尔说:“在存在者整体中间有一个敞开的处所,一种澄明在焉。从存在者方面来思考,此种澄明比存在者更具存在者特性。”[4]37亭下无人,人是存在者,但这种无人的澄明之境其实是让本真的人进入到自由无蔽的公开场中。试看关于倪瓒空亭的几首题画诗:
松林亭子图
亭子长松下,幽人日暮归。
清晨重来此,沐发向阳稀。
雨后空林图
雨后空林生白烟,山中处处有流泉。
因寻陆羽幽栖去,独听钟声思惘然。
清溪亭子图
数里清溪带远堤,夕阳茅草乱莺啼。
欲将亭子都捶碎,多少离愁到此迷。
可以看到,作为对画中未能尽言的补充,诗中那个或沐阳而归或临泉听钟或于亭惜别的此在,正是从沉沦于世的非本真状态中超越出来,回归向本己的能在。何谓本己的能在?海德格尔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在我看来,这和佛家的“本来面目”以及道家的“返璞归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其本质都是将人被遮蔽的本性重现,使人恢复原本的纯真无染的状态。故而在倪瓒笔下那看似荒寂的世界里,恰是生命的冰点积蓄着无穷的张力。而那表面上看起来一片岑寂的空亭,实际上却是隐括掉所有有色世界的繁杂,借以等待生命原有的简真。
二、在者退场,览者参与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倪瓒最终呼唤的还是本真的存在,那为什么不在画中将其绘出,即使这世间有云林不屑动笔的俗人,然而也还是有像他自己一样高洁脱俗的存在,像清代王概在《芥子园画传》中形容的那样,“画山水之人物,须清如鹤,望如仙,不可带半点市井气,致为烟霞之玷”,这里的人物也就是很多画家借以明志托怀的此在。而云林有意让这样的人物“缺席”,则牵涉到“在场”和“不在场”的哲学命题。何谓“在场”?“通俗地说,在场就是现在正在这里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某物现在正在这里在。”[5]46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对“在场”的解释有三种含义:第一,它指现成的或者当下即在的状态;第二,指当前时间或者此时此刻的一个时间点;第三,指此时此刻的呈现。如果按照这样的定义,那么亭下无人的这样一种状态则是一种此在的“不在场”。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回到中国画学的语境中,发现“在场”与“不在场”的问题,便是传统绘画创作中“藏”与“露”的问题。“藏”在绘画中是笔墨清淡、景物疏散乃至空白无物处,“露”是画面中笔墨浓重,可以直观的物象处。二者之间的关系正如清沈宗骞在《芥舟学画编》第四卷说道:“或露其要处而隐其全;或借以点明而藏其迹。如写帘于林端,则知其有酒家;作僧于路口,则识其有禅舍。”[6]414这种藏中显露,以露隐藏的构图技巧和辩证美学在倪瓒的空亭意象中被运用的出神入化。有着固定图式的倪瓒,其画上显露出的只有远山、平岸、几株疏木以及树下孤零零的一座空亭,人在画面中并未现身,看似是一种“不在场”,然而,无论是画面中锁住观者视线的孤亭,还是题跋中都有明显人为活动的场面,“溪声漱欲流寒玉,山色依依列翠屏。地僻人闲车马寂,疏林落日草玄亭”(《疏林亭子图》),“旷远苍苍天气清,空山人静昼螟螟。长风忽度枫林秒,时送秋声到野亭”(《枫林亭子图》),都暗示着人迹未远,所谓“山水无人人在兹”,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在场”。海德格尔说过“澄明乃是一切在场和不在场者的敞开之境”,故而他的真正意图是,在场是事物来到世界上的自我呈现,而人的在场就是此在的自我呈现,倪瓒的笔下的山川林木无一不自在显现,这是物的“在场”,是直观的“露”,而人则通过隐在山水空亭的背后,或者直接融入其中,从而展现了自己的存在,这也是“在场”,是间接的“藏”。
这种“不在场”的“在场”意义何在,唐志契在《绘事微言》中点出了迷解,“更能藏处多于露处,而趣味愈无尽矣”[6]413。这趣味便是观者的审美之趣。王伯敏谈及“藏”在绘画艺术上的特点,首先一条就是“使观者得到联想,‘形’不见而‘意’现”[7]20。故而,人物的“缺席”使空亭虚位以待,意在开启一个“召唤结构”。“召唤结构”是德国康斯坦茨学派重要代表沃尔夫冈·伊瑟尔在《文本的召唤结构》提出的:“作品的意义是不确定点和意义空白来激发接受主体对作品本身中的各个部分进行主观衔接,并联系现实生活进行想象,从而赋予接受主体本身参与作品构成的权利,也就是说,作品意义需要接受主体与创作本身来共同完成”。“召唤结构”最初用于讨论文本作品,指文章的意义只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才能产生,随后这一理论被运用到了艺术领域。绘画作品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但仍需要审美主体的参与才能构成完整的意义传达,尤其是虚实相间、拥有大片留白的中国山水画,更需要观赏者运用想象进行补充,和创作者来一场情感的邂逅与共鸣。摊开倪瓒一系列作品,无论是《雨后空林图》中沿石阶蜿蜒而上的稻草茅屋,还是《江岸望山图》里临着高山与汀渚的草亭,抑或《林亭远岫图》上那寥寥勾勒的亭子,都在召唤着观画者跃入画中,去沟通潜藏在作品深处的那个存在。于是张雨在《雨后空林图》里寻觅追踪:“望见龙山第几峰,一峰一面水如弓。苍林茅屋无人到,犹有前时镊履踪。”丹房生在《江岸望山图》中期待归程:“杳蔼钟声隔翠微,清泉白石映斜晖。道人定是知心者,结个茅屋待我归。”更多的文人画家不期而同地在《林亭远岫图》前思绪翻腾,俞允在闲亭中等候画中人的归来:“青山隔横塘,疏树蔽幽径。山中人未归,闲亭秋色暝。”俞贞木对云林的不能到来怅然若失:“栖神山下玄元馆,华表巍然鹤未归。寂寂小亭人不见,夕阳云影共依依。”而曾恒则一直深情守望:“故山何处最关心,亭外遥岑入望深。却恨浪游江海上,漫教猿鹤守空林。”
三、消解主我,等待无我

图2 王蒙《西郊草堂图》局部
和倪瓒同为“元四大家”的另外两位,吴镇和王蒙,则以善著人物而有名。其中吴镇毕生以画渔父为痴。他的《秋江渔隐》《清江春晓》《洞庭渔隐图》《渔父图轴》等,表现了一幅幅渔父与自然亲和不弃的性灵之景,可以得知,画中的那个渔父就是画家的化身。而另一位画家王蒙,画风则是四大家中最具生活气息的一位。他的画如《破窗风雨图》、《谷口春耕图》、《西郊草堂图》(图2)等无一不有人物点缀其中,而画家更是借在山林书斋悠闲恬适生活的画中人,表现自我的隐居情怀。故而,这种“借景中人自喻”的方式充分揭示了绘画中的那个人物通常是主体的投影,就是意识的集合体——“我”。“我”的消失,意味着主体情感的消融,营造了一种主客悬搁的“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这是王国维的境界说。以我观物,我来认识物,我来决定物,这世界是以我的存在为中心,在这里,我是主体,物是客体,主客之间是割裂的,反映在画中,亭下的那个个体,当他或独坐或眺望或负手而立地观看着对面的山川江渚时,他与世界就注定了“相隔两岸”,正如朱良志先生在《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一文说道:“人是世界的一分子,但在知识系统中,人总喜欢站在世界的对岸看世界,世界在我的对面,是被我感知的存在物(科学的)、消费的客体(功利的),或者是被我欣赏的对象(审美的),人用这样的态度看世界时,好像不在这世界中,人成了世界的控制者、决定者。”[8]96这也是海德格尔一直所反对的主客二分的认识方式:“‘只要认识世界’一被把握,它就被赋予一种‘浅表的’、形式化的解释。这种情况的证据是:在(今天仍然惯常的)主张认识是‘主客体关系’的做法中,‘真理’却空空如也。”[9]11相对而言,无我旨在消解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意识,让世界自在涌现,人退回到世界之中,与世界一同展开,就此“无我之境”开启。在云林的山水中,山永远是和缓淡缈的,极少有高耸入云的压迫,水面永远是波澜不惊的平静,稀疏而立的几株树木,还有一座低矮的、沉默不语的空亭。这是画家创造的世界,看起来是如此寡淡,难怪清代阮元对倪瓒山水颇有微词:“予尝谓他人画山水,使真有其地,皆可游赏。倪画则枯树一二株,矮屋一二楹,残山剩水,写入纸幅,固极萧疏淡远之致,设身入其境,则索然意尽矣。”[10]48
然而就是这个残山剩水的世界,在涤荡了感官刺激和欲望起伏的干扰后,在拆除了思维逻辑和情感意念的壁障后,你会发现这远山近水幽亭秀木自成姿态,在这个完整的世界里,它们自给自足地安放,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也就是海德格尔一直提倡的“澄明之境”。“唯进入澄明之敞开领域中万物才能显现,才能显现为现实事物之所是”[11]1252,在这敞开着的无蔽境界中,人与万物是其所是且不分彼此。这样的境界,等待的是作为存在的守护者的,也就是海德格尔称之为牧者,看护者的人的进入。“人不是在者的主人。人是在的看护者。”[9]13作为主体的人,他是占有、支配这个世界的,但是在这样的行为中,他最终失去了世界,也迷失了自身。而当人放弃自己的主体身份,不再执着于以自我为标准干预世界,而是“让”世界成为世界时,人反而得到了本质和真实。云林的《秋林亭子图》题诗:“云开见山高,木落知风劲。亭下不逢人,夕阳淡秋影。”映照出了一个自在空灵的世界,作为存在者的人任它“风吹叶落,云卷云舒”,不惊扰,不打断,只是以一种“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沉默”来守护。就像郭熙描述的人应该这样观摩自然:“学画花者,以一株花置深坑中,临其上而瞰之,则花之四面得矣。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林泉高致·山水训》)艺术是一场生命和生命的交流,一朵花中绽放一个般若,一枝竹里隐藏一具法身,人需低下那高高昂起的头颅,放下困顿已久的分别心,与万物共舞,同世界共在。
四、厌倦漂泊,渴望安居

图3 水竹居图
观察倪瓒的诗画会发现,他经常以居所来命名亭子,如“容膝斋”就取自陶渊明的辞赋《归园田序》中的“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居家情怀一目了然。还有《紫芝山房图》,里面就简简单单的一座茅亭。而他的《松亭山色图》、《雨后空林图》中的亭子实际上就是房屋一所,和《水竹居图》(图3)、《安处斋图》中的房屋亦如出一辙,《安处斋图》上有题画诗句:“幽居不作红尘客,遮没寒江卷浪花。”这样有意的模糊亭与居的概念,不禁让人联想到倪瓒后半生的漂泊生涯。倪瓒的早期时代,家中是富户,在其兄长倪昭奎的经营下更是闻名当地,早年的倪瓒过着悠闲富裕的生活,结交高士,不与俗人俗世处,“白眼视俗物,清言屈时英”(《述怀诗》)。而当中年后,伴随着兄长嫡母的逝世,以及随之而来的家事牵绊、政治欺压和时局变动,为逃避官租,也为实现心中的隐逸情怀,最终决定散弃田产,举家搬迁到船上,余生都在江河水面上度过,这样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地触动这个敏感艺术家的心房,其羁旅思乡的哀切之感都倾泻在笔下:“畏途岂有新知乐,老境空思故里归”(《寄卢士行》),“阶下樱桃已著花,窗前野客独思家”(《喜谢仲野见过》),“春风夜月无踪迹,化鹤谁教返故乡”(《柯丹邱梅竹》),时间一长,这思念愈发浓烈,渗透在梦中,“忽起故园想,冷然归梦长”(《桂花》)”、“黄云堆径无行迹,幽思迢迢梦故乡”(《题周逊学天香深处卷》)试看他的这阙《江城子·感旧》:
窗前翠影湿芭蕉,雨潇潇,思无聊。梦入故园,山水碧迢迢。依旧当年行乐地,香径杳,绿苔绕。
沉香火底坐吹箫,忆妖烧,想风标。同步芙蓉,花畔赤阑桥。渔唱一声惊梦觉,无觅处,不堪招。
午夜萦回,魂牵梦绕的故园依旧是当年的景象,然而当沉眠被惊醒,现实的孤独却让人无可奈何。正如弗洛伊德所说,梦和艺术都是人愿望的满足,二者结合更是将人内心的呼喊和盘托出。所以,云林的亭中是无人的,漂泊仿佛是他的宿命,终其余生,他都不得回归故土,“春多风雨少曾晴,愁眼看花泪欲倾。乱离漂泊竟终老,去往彼此难为情”(《清閟阁集》卷三)。
然而,对于任一尾扁舟漂荡太湖二十多年的倪瓒来说,亭子仍旧象征着彼岸的渡口,是一直静待羁旅游子的安顿之处——“举世何人到彼岸,独君知我是虚舟”(《次韵奉谢併期面别》,纵然归程遥遥无期,亭子却指引着回归的方向,正如他在《孤亭秋色》上的题跋:“七月一日风雨集,桐里湖边吟夕凉。柳叶肇烟笼翡翠,荷花溅泪湿鸳鸯。却疑身在潇湘诸,且著舟停云锦乡。顾我自非徐孺子,烦君下榻更衔筋。”这梦寐以求的“云锦乡”不仅仅是他现实中家乡,更是生命的最终归宿。西方哲学家诺瓦利斯说“哲学原是怀着一种乡愁的冲动到处寻找家园”,而这家园更深层次的意义上是人的终极栖居,海德格尔认为“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9]87。而在中国的哲学中,这个本源便是人与天地宇宙契合无间的生命形态,所谓“天人合一”,是所有艺术都执着追求的至高之境。亭子则毫无意外承担了这个沟通的使命,张宣题倪画《溪亭山色图》诗云:“石滑岩前雨,泉香树林风,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苏东坡《涵虚亭》诗云:“惟有此亭无一物,坐观万里得天全”。这个和苍莽天地比不过微渺一存在的凉亭,却有着将整个乾坤收入囊中的魄力,它屹立于荒天迥地间,为奔波疲惫的灵魂开辟出一安抚之地,让有限的人生突破到无限的宇宙中。正如倪瓒在晚年悟道时写下的一篇《蘧庐诗并序》:
天地一蘧庐,生死犹旦暮。奈何世中人,逐逐不返顾。此身非我有,易稀等朝露。世短谋则长,噬哉劳调度。彼云财斯聚,我以道为富。坐知天下旷,视我不出户。荣公且行歌,带索何必恶。
“乾坤一草亭”正是“天地一蘧庐”,此在在这里方才真正诗意地栖居。
“此翁老去云林在,枯树荒亭几夕阳”,这是明人沈明臣为云林所写的纪念诗,清代遗民画家弘仁亦留下一幅《幽亭秀木图》,云林的空亭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成为一个哲学标志。文人墨客在对其师法的过程中亦对“亭下无人”做了自己的诠释,所谓“寂寞云林”是普遍的一个解读,联系云林的自身性情和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是重要的原因。然而,从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来看,人不仅是独一无二的“此在”,而且也是相互交流与对话的生命“共在”。人的“缺席”诉说着倪瓒寂寞而无可奈何的心境,空亭的遗留却又暗示这位高逸孤洁的山水画大师的隐秘渴望,这些在他的诗作里已有充分的反映。这也是为何许多画家想要模仿倪瓒,却难以深入的原因。正可谓:“无人空亭成绝笔,人间难觅倪云林”!
[1]俞建华.中国古代画论精读[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2]诺伯格·舒尔茨.存在·空间·建筑[M].尹培桐,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
[3]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4]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5]彭锋.重回在场——兼论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J].学术月刊,2006(12).
[6]周积寅.中国画论辑要[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5.
[7]王伯敏.中国画的构图[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8]朱良志.生命的态度——关于中国美学中的第四种态度的问题[J].天津社会科学,2011(2).
[9]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语要[M].郜元宝,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1.
[10]阮元.丛书集成初编·石渠随笔卷四[M].上海:中华书局,1991.
[11]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责任编辑:王丽平]
“Absence” and “Summon”——Aesthetic Interpretation of Ni Zan’s “No One under the Pavilion”
SUN Wei-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s one of elements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characters have an important function for replenishing the picture plot and revealing the painter’s thought. But in Ni Zan’s paintings, he deliberately cancels man’s existence, in order to make the image of empty pavilion into a philosophy mark. “No One under the Pavilion” is not only the “absence” of “existence”, but also a yearning “summon”, of which aesthetic significance and humanity are beneficial for the deeper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Ni Zan and the ideological level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s.
Ni Zan; absence; summon; empty pavilion; aesthetics
2015-07-11 作者简介: 孙伟伟(1990-),女,安徽马鞍山人,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 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批评。
1671-5977(2015)03-01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