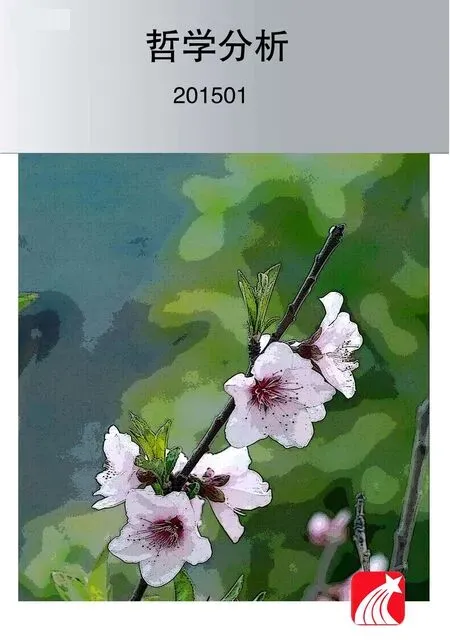基于缺乏之上的另类动力论
——论笛卡尔上帝观念的发生
黄作
哲学传统研究
基于缺乏之上的另类动力论
——论笛卡尔上帝观念的发生
黄作
笛卡尔摒弃经验主义道路,否认无限来自有限之物的不断添加,而认为无限观念(上帝观念)验前地先于一切有限观念。在上帝是自我思维本身的条件这个意义上说,笛卡尔的上帝观念说可谓是后来超绝哲学的理论先驱。结合精神分析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可见,人类精神总是处于缺乏(受到缺乏的诱惑)与欲望(总是要去认识更多东西)的张力之中,而正是其中的动力性促成了上帝观念的发生。
笛卡尔;上帝观念;缺乏;动力性
在笛卡尔上帝观念问题上,一般研究都用因果律的动力论来解释上帝观念的产生;本文从人类精神本身出发,从思本身具有的张力出发,运用另一种动力论,试图来解释上帝观念的发生。
一
在如何把握上帝的无限性问题上,我们知道,笛卡尔采取的理论立场与圣·托马斯刚好相反。鉴于人类的有限性和上帝的无限性,后者认为我们实际上无法直接把握这种无限性,而只有通过否定的方法或道路才能达到这点,“尽管在上帝之中没有某种缺失(privatio),可是,依据我们的觉识方式(modum apprehensionis),除非通过去除和排除的模式(permodum privationis et remotionis),否则他不被我们所认识。因而,没有东西能够禁止我们去宣称关于上帝的、带有否定性前缀的某些言说,例如,他是非有形的(incorporeus),他是无限的(infinitus)”①S.Thomas d’Aquin,Summa Theologiae I,q.11 a.3:Et licet in Deo non sit aliqua privatio,tamen,secundum modum apprehensionis nostrae,non cognoscitur a nobis nisi permodum privationis et remotionis.Et sic nihil prohibet aliqua privative dicta de Deo praedicari;sicut quod est incorporeus,infinitus.参见http://www.corpusthomisticum.org/ iopera.html(网上圣·托马斯拉丁文献库)。;在另一处谈及对于石头和上帝的认识之差异时,托氏更是直接使用了“否定之方式”(modum negationis)一词来明确表达这种迂回的认识之路,“相反,从神的众结果出发,依据它在自身中所是以至于我们从中知道其所是,我们无法认识神性本性(ex effectibus divinis);而是通过卓越之方式、因果性之方式和否定之方式才能认识它,就如在前面已经说过”②Ibid.,q.13 a.8 ad2:Sed ex effectibus divinis divinam naturam non possumus cognoscere secundum quod in se est, ut sciamus de ea quid est;sed permodum eminentiae et causalitatis et negationis,ut supra dictum est.。
托氏的这种无限观源自亚里士多德。在面对“我们的理智能够认识无限吗?”这一问题时,托氏直接借用亚氏在《物理学》中的一句名言“作为无限的无限是不可知的”③Aristote,Physique,livre I,chap.4,187b8,cf.Aristote,Physique d'Aristote ou Leçons sur les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nature,traduite en français pour la première fois,et accompagnée d’une paraphrase et de notes perpétuelles, par J.Barthélemy-Saint-Hilaire,Paris:Ladrange:A.Durand,2 volumes,1862;cf.Aristote,La physique d'Aristote, Traduction HenriCarteron,Les Belles lettres,Paris,1966.(参见http://docteurangelique.free.fr)来做回答,这说明他认同亚氏在《物理学》中对无限所做的定义,即“无限就是人们总是能够对之进行添加的那个东西”④Ibid.,livre III,chap.6,207a6-7;cf.Traduction J.Barthélemy-Saint-Hilaire et Traduction Henri Carteron;cf.la traduction de S.Thomas de Aquino,in Summa Theologiae I,q.86 a.2:est enim infinitum cuius quantitatem accipientibus semper est aliquid extra accipere.圣·托马斯的该拉丁文很拗口:“无限实际上是那个东西,它的接受性的量就是总是去接受另一个额外的东西。”(《神学大全》中译本翻译为“无限乃是‘任取其量者,常有所余供取’”。参见圣多玛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三册),周克勤总编,刘俊余译,台南:碧岳学社、高雄:中华道明会2008年版,第187页。)本文中译按该拉丁文的法译文(L’infiniest ceàquoi on peut toujours ajouter)译出。,认为“除非它部分接着部分地得到接纳,否则无限不能被智识”⑤S.Thomas d’Aquin,Summa Theologiae I,q.86 a.2:non potest intelliginisi accipiendo partem post partem.;“部分接着部分地”意味着,“除非它的所有部分都得到列举,否则无限不能实现了地(actu)被认识⑥Ibid.:infinitum cognoscinon posset actu,nisiomnes partes eius numerarentur.”,而要列举出无限的所有部分,“这是不可能的事”⑦Ibid.:quod est impossibile.。总之,“总是能够对之进行添加”,意味着我们能够对之进行添加直至无限,而直至无限,在亚氏和托氏看来,只能是一种“潜在的”可能状态,而非“实现了的”现实状态,故我们的理智只能认识“潜在的”无限,而非“实现了的”无限。⑧cf.Aristote,Physique,206a16-18.S.Thomas d’Aquin,Summa Theologiae I,q.86 a.2:ita nec actu nec habitu intellectus noster potest cognoscere infinita,sed in potentia tantum.
笛卡尔明确反对托氏从否定前缀角度出发把无限理解为有限之否定,在他看来,恰好相反,任何有限都是对于无限之否定,“通过对于有限或限制之否定,无限得到智识,这不是真的,而是相反,每一种限制都包含对于无限之否定”①RénéDescartes,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Œuvres de Descartes par C.Adam et P.Tannery,nouvelle présentation par Rochot et P.Costabel,Paris,1964-1974(简称AT本),Tome VII,p.365,ll.6-8:Nec verum est intelligi infinitum per finis sive limitationis negationem,cum e contra omnis linitaio negationem infiniti contineant.Traduction française,cf.RénéDescartes,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3 vol.,Éditions Carnier Frères, 1963-1973,Tome II,p.808.中译文参见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6页。,进一步说,“‘通过对于限制之否定,我们无法智识无限’,这是最真的;‘限制包含对于无限之否定’,由之推论出,‘对于限制之否定包含对于无限之认识’,则是错误的”②RénéDescartes,Contra Hyperaspistem,août 1641,Corresp.CCL,AT III,pp.426,l.7-427,l.3:Verissimum est, non a nobis in finitum intelligi per lim itationis negationem;&ex eo quod limitatio contineat negationem infiniti, perperam infertur negationem lim itationis continere cognitionem infiniti.Traduction française,cf.RénéDescartes, 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364-365.需要指出的是,斜体拉丁文是笛卡尔本人的文本,黑体拉丁文则是之前写信给笛卡尔(1641年7月,AT本收录为第246封信)且笛卡尔在此对之进行回信的那位匿名斗士(伽桑狄的一个朋友)的文本,具体可参见AT本卷III第403页第17-21行。我们在中文翻译中把黑体拉丁文用单引号引起。。有意思的是,笛卡尔本人有时也会说“除非通过否定性方式(modo negativo),否则无法智识它[无限性]”③RénéDescartes,Réponses aux premières objections,AT VII,p.113,ll.12-13:non...nisi negativo quodam modo intelligimus.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9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7页。本文中所有中括号“[]”都为本文作者所加,或为必要的补充,或为必要的说明。这一类的话,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认同托氏的否定性道路,从该句话的拉丁文的后一句[中文翻译的时候实则是前一句]“根据以下这个事实,即我们显然无法在[无限性这一]实在之中(in re)标出任何限制”④Ibid.,p.113,ll.13-14:ex hoc scilicet quod in re nullam limitationem advertamus.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9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7页。中不难看出,笛卡尔显然首先从无限本身出发,从无限本身不包含任何限制或任何否定这一事实出发来谈论问题,接着谈到,论说无限的方式是否定性的即“无法……标出任何限制”,故所谓的“否定性方式”,既不是对无限之否定,也不是说无限是有限之否定;而在托氏理论中,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他所说的“否定之方式”其实就是对有限之否定,“通过去除和排除的模式”,排除或否定有限,就像“非有形的”就是对“有形的”的排除或否定一样,简言之,托氏走的是一种否定道路。
与托氏的否定道路不同,笛卡尔走的完全是一种肯定道路,他完全从肯定的角度出发来论述无限问题,如他所说,“当我留住无限这一名字时——如果我们意愿每一个名字符合每一事物的性质,它本可以比较直截了当地被称为最大存在,[我]同样[尽最大可能遵循已经得到检验的说话方式]”⑤Contra Hyperaspistem,août 1641,AT III,p.427,ll.11-14:ut etiam cum retinui nomen infiniti,quod rectius vocari posset ens amplissimum,sinomina omnia naturis rerum vellemus esse conformia.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365.,换言之,我们本可以用完全肯定的名字即“最大存在”或“最大者”(maximum①笛卡尔在《第五组答辩》中说“没有东西比无限更大”(infinito nihilmajus esse ptest),参见Réponses aux cinquième objections,AT VII,p.365,ll.20-21。盖鲁(Gueroult)则直接称之为“最大者”(maximum)。(Martial Gueroult,Descartes selon l’ordre des raisons I,Aubier,1975,p.207.)我们知道,关于“最大者”,安瑟尔谟(Saint Anselme)已经表述为“就是那种东西,比之更大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被思”(ce quiest tel que rien de plus grand ne peutêtre pensé)。(cf.Fédéric De Buzon et Denis Kambouchner:Le vocabulaire de Descartes,Ellipses,2002,p.36.))来称呼无限,后来之所以选择了至少在字面意义上多少带有点“否定”意思的“无限”一词,完全是由于我们不得不遵循日常说话方式的缘故。笛卡尔在另一封信中又明确说道:“应该指出,我绝对没有利用词无限去仅仅指没有尽头——这是否定性的东西,且我把词‘没有做出限定’(indefini)运用于它,而是去指一种实在的东西(une chose réelle),后者相比较于所有那些有某种尽头的东西而言是无与伦比地更为伟大”②A Clerselier,23 avril 1649,Corresp.DLVII,ATV,p.356,ll.1-7.原文是法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笛卡尔创造性地区分了“无限”与“没有做出限定”,他把前者只赋予上帝,“只有上帝是无限的”③Réponses aux premières objections,AT VII,p.113,ll.3-4:solus Deus est infinitus.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89.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6页。,而把想象的空间的广延(extensio spatii imaginarii)、数的多(multitudo numerorum)、量的众部分的可分性(divisibilitas partium quantitatis)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称为‘众没有做出限定’”④Ibid.,AT VII,p.113,l.7.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9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6页。,“因为它们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尽头(fine carent)”⑤Ibid.,AT VII,p.113,l.8:quia non omni ex parte fine carent.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9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6-117页。。
从这样的无限观出发,笛卡尔无疑同样反对圣·托马斯关于“部分接着部分”逐渐“添加”接近无限的观点。针对伽桑狄在反驳第三沉思中上帝观念时所持有的类似于托氏的上述观点,笛卡尔明确表示:“实际上,您不要认识为,‘由于众造物得到增长了的众完满,我们连续地形成上帝观念’,而是,通过精神我们触及到无限存在(它无法进行任何增长),依据无限存在这种东西,上帝观念整个且同时得以形成。”⑥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371,ll.23-26:Neque enim,ut scias,idea Dei formatur a nobis successive ex perfectionibus creaturarum ampliatis,sed tota simul ex hoc quod ens infinitum omnisque ampliationis incapxmente attingamus.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817.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72页。具体来说,其一,上帝观念或无限观念是一下子形成的,这就涉及笛卡尔哲学中所谓的“时间的非连续性”问题;其二,上帝观念或无限观念是整个形成的,所有的完满性早就已经包含在观念之中,不存在逐步增长或扩大的问题,为此笛卡尔还特意举了三角形观念的例子⑦Ibid.,cf.ATVII,p.371,ll.21-23.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817.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72页。来做说明。
从上面不难看出,在笛卡尔的理论体系中,有限与“没有做出限定”,并非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有限与无限这样一组对立概念。可以这么说,无限其实是超越了有限与“没有做出限定”之间二元对立的一个“元”概念。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种“元”概念的性质,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点来进一步说明:其一,无限观念属于笛卡尔称之为“天生”(innatae①Méditation III,AT VII,p.37,l.29.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29.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7页。)观念的那一类,“就如自我观念本身对我而言也是天生的一样,它[上帝观念]是天生的”②Ibid.,AT VII,p.51,l.13-14:quemadmodum etiam mihi est innata ideameǐipsius.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41.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53页。需要指出的是,在AT本卷IX第一版法译文中,添加上去“dès lors que j’aiétécrée(我一被创造出来)”这样一句从句,中译文按第一版法译文译出,故也有这一从句。。其二,笛卡尔用“隐含地”(implicite)一词形容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而用“显明地”(explicite)一词来形容我们对于我们的众非完满之认识,“既然在朝向上帝之前,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朝向我们,而且我们实际上能够在得出他是无限的以前就得出我们是有限的,那么,实际上我们能够在认识上帝的完满之前显明地认识我们的不完满。然而,隐含地,对于上帝及其众完满的认识总是先于对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众不完满之认识:既然我们的非完满是神性完满的一种缺省或否定,而且任何缺省或否定都预设缺省由之丧失的东西,否定要否定的东西,那么,实际上,在众事物的实在中,上帝的无限完满总是先于我们的不完满”③RénéDescartes,L’entretien avec Burman,edition,traduction et annotation par Jean-Marie Beyssade,PUF,1981, pp.44-45.Le texte latin cf.aussi AT V,p.153.按照吉尔森的说法,说完满先于不完满,其实是圣·奥古斯丁的传统,但在怀疑中瞥见上帝的直观能力则为笛卡尔独有。(Étienne Gilson,Descartes.Discours de laméthode, texte et commentaire par E.Gilson,p.315.)。甚至可以这样说,“显明地,尽管[你以为]这并没有产生什么(quamuis hoc non fecerit④“fecerit”为动词“facere”(faire)的虚拟完成式第三人称单数,而“fecit”则为直陈完成式第三人称单数。),可是隐含地,它已经产生什么(fecit)”⑤RénéDescartes,L’entretien avec Burman,pp.44-45.Le texte latin cf.aussi AT V,p.153.。其三,从逻辑上说,作为“元”概念的无限观念必定先于任何有限观念,包括任何其他天生观念,包括自我观念,“从而,在自我中我以某种方式(quodanmodo⑥这里所说的“某种方式”(quodanmodo)显然指上述“隐含地”,而非“显明地”。)先具有对于无限的知觉,而非对于有限的知觉,这就是说,对于上帝的知觉,而非对于自我本身的知觉”⑦MéditationIII,ATVII,p.45,l l.27-29:acproindeprioremquodammodoinmeesseperceptioneminfinitiquàm finiti,hocestDeiquàmmeíipsius.Traductionfrançaise,cf.ATIX,p.36.注意法译文用“lanotion”(概念或观念)来翻译“perceptionem”(知觉)一词。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6页。阿尔盖在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在众肯定之秩序中,我思(lecogito)先于上帝。然而,在关于这些肯定本身的验前的(apriori)(借用钱捷先生的译法)众条件之秩序中,上帝先于我思。上帝是关于自我的思维本身的条件,因为我只能从最高者出发来认识最低者,只有通过在无限中切割有限才能认识有限。因此这里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是上帝,而不是我思,他现在将成为真正的中心和真正的认识之支撑”。(Alquié,Descartes.Œuvresphilosophiques,t.II,p.446,note1)不难看出,阿尔盖的解释明显带有后来所谓的“超绝”(transcendantal)(借用钱捷先生的译法)哲学的味道。需要指出的是,“apriori”一词在笛卡尔理论体系中并不对应于“验前的”的意思,而主要运用在论证之上,如“从原因到结果”的论证是“apriori”,与之对立的“aposteriori”则代表“从结果到原因”的论证。中世纪以来一直到17世纪一般都是这样来理解的。“apriori”似乎又对应于笛卡尔所说的分析法,而“aposteriori”则对应于综合法,但一旦我们看到笛卡尔在一个括号中说“综合法中的证明总是比分析法中的证明更多为‘apriori’”这句话时候,问题就变得异常复杂了。(cf.Alquié,Descartes.Œuvresphilosophiques,t.II,p.582,note1)。更具体地说,“不过,我说我所具有的无限概念在有限概念之前就处于自我之中,是由于以下唯一的这点,即我设想(conçois)存在或存在的那个东西(l’être ou ce quiest),而不去想是否它是有限的或无限的,我所设想的是无限存在(l’être infini);然而,要想我能够设想一种有限存在(l’être fini),我应该从关于存在的这一一般概念(它因此应该是在先的)中截去某种东西。”①A Clerselier,23 avril 1649,Corresp.DLVII,AT V,p.356,ll.8-14.原文是法文。这再次说明了,在与完全肯定性的无限的关系上,有限与“没有做出限定”都代表一种否定性东西,只不过各自否定性的内涵不同而已。
我首先思考“存在或存在的东西,而不去想是否它是有限的或无限的”,我首先思考的是“无限存在”,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笛卡尔把无限视为完全肯定的东西了。无限与一般存在有关,而一般存在是完全肯定的东西,正是在(一般)存在的意义上,笛卡尔道出了无限与有限的根本差别,“因为,由之把无限与有限区分开来的那个东西,是实在的和肯定的,相反,由之把有限与无限区分开来的那个限制,则是非存在(non ens)或存在之否定(negatio entis);不存在的那个东西并不能引导我们去认识存在的东西,而是相反,从一东西之认识出发,其否定才应该被觉知(percipi)”②Contra Hyperaspistem,août 1641,AT III,p.427,ll.3-8:quia id,quo infinitum differt a finito,est reale ac positiuum;contra autem limitatio.qua finitum differt ab infinito,est non ens,sive negatio entis;non autem potest id quod non est,nos adducere in cognitionem eius quod est;sed contra ex rei cognitione percipi debet eius negati.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365.在法译文该页的注释1上,阿尔盖进一步区分了肯定与否定之否定,“限制之否定只是对于一种否定之否定。然而,如果从逻辑上说,对于一种否定之否定等于一种肯定,那么,对于存在的任何一种认识都不能从这样的一些运作中被得出。存在总是应该从一开始就被把握”。古耶(Gouhier)则认为,无限的这种完全的肯定性和完全的在先性,不仅仅取决于与一般存在的紧密关系,而且更主要的还与笛卡尔独特的对象性实在(realitas objectiva)(哲学史上由笛卡尔所提出的第三类存在)理论有直接关系,“古典主张的这种倒转[即从无限出发去理解有限,而非相反]随着笛卡尔的观念和经院哲学的概念之间的差别而来。观念所表象的东西(la chose représentée)构成一种存在模式,这种存在模式显然不是事物本身(la chosemême)的存在模式,可是它补充到表象性主体(le sujet représentant)的存在模式之上;在这些条件中,既然在无限实体中比在有限实体中有更多的实在,那么,‘展示’(exhibant)第一者(la première)的对象性实在,相比于‘展示’第二者(la seconde)的对象性实在,拥有高级的存在程度(degréd’être);就如最高者(le plus)不可能来自最低者(lemoins),完全应该把最高者放在最低者之前”。(HenriGouhier,La pensée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Paris:Vrin,1969,p.127.)。我们可以用柯瓦雷先生(A.Koyré)的一段话来总结这种具有完全肯定性和完全在先性的无限,这种代表一般存在的最高的无限:“对笛卡尔而言,它并不简单地是无限的,而是无限地无限的(infiniment infini);它不是存在之无限(l’infini de l’Étre),不是处于其本质深处的、无限的和绝对的存在(l’Étre infini et absolu),而是可以说,一种最高程度的无限(l’infini d’un plus haute degré)。”①Alexandre Koyré,Essai sur l'idée de Dieu et les preuves de son existence chez Descartes,Paris:E.Leroux,1922, p.14.
二
尽管上帝观念的无限性代表完全肯定性的东西,不过,笛卡尔本人仍然设计了两条道路来通达该无限性,或者说来证明上帝的实存:“只有两条道路,通过它们上帝可以得到证明,即:一条当然地通过众结果,而另一条通过其本质或通过其本性。”②Réponses aux premières objections,AT VII,p.120,ll.9-12:duae tantum sunt viae per quas possit probari Deum esse,una nempe per effectus,&altera per ipsam eius essentiam sive naturam.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94.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22-123页。相较于后一条道路(笛卡尔事实上在第三沉思里讲得并不多)的直接性,前一条道路则是迂回的,无论是其中的第一种论证(“只有从以下事实——即其观念在我们之中——出发,上帝之实存通过其众结果得到论证”③Exposégéométrique,AT VII,p.167,ll.11-12:Dei existentia ex eo solo quod eius idea sit in nobis,a posteriori demonstratur.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129.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67页。),还是被笛卡尔本人称之为具有“更为容易领会的方式”(palpabilius④Réponses aux secondes objections,AT VII,p.136,l.7.Cf.Henri Gouhier,La pensée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 pp.132-141.)的其中第二个论证(“上帝之实存再次由以下事实得到论证,即拥有他的观念的我们自身实存”⑤Exposégéométrique,AT VII,p.168,ll.2-3:Dei existential demonstratur etiam ex eo quod nos ipsi habentes eius ideam existanmus.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129.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68页。),其实都是从人类理智的有限性出发间接地论证出上帝的实存。我们认为,正是这种人类理智的有限性及其与上帝的无限性之间的张力,引起了我们精神中上帝观念的发生。对此,我们准备在第三部分中详细加以论述。
人类理智在上帝的无限性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有限性,在笛卡尔哲学体系中集中体现在“不可囊括地把握的”(incomprehensibilis⑥笛卡尔另外还用了两个词汇来表示人类理智的这种有限性,分别是“inconceptibilis”(不可构想的)和“incogitabilis”(不可想象的)。笛卡尔曾经这样来解释:“当上帝被说成是‘不可想象的’时,这要从完全相当地具有‘囊括地把握性’的思维活动出发,而非从存在于我们之中的那个非完全相当的思维活动(它足以去认识他本身实存)出发来理解”(AT VII,p.140,ll.2-5:cum Deus dicitur esse incogitabilis,intelligitur de cogitatione ipsum adaequate comprehendente,non autem de illa inadaequata,quae in nobis est,&quae sufficit ad cognoscendum ipsum existere.)简言之,“完全相当地具有‘囊括地把握性’的思维活动”对我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由此可见,“不可想象的”,“不可构想的”和“不可囊括地把握的”意思都是相通的。)这个词之上。从1630年4月15日那封著名的《给麦尔赛纳的信》(“相反,尽管我们认识它,我们不能‘囊括地把握’上帝的伟大。然而,这一点同样意味着,我们判断它为‘不可囊括地把握的’,我们使它得到更多的重视”①A Mersenne,15 avril 1630,Corresp.XXI,AT I,p.1146.原文是法文。有意思的是,笛卡尔随后还专门举了国王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不可囊括地把握”与上帝的伟大之间的关系:“正如同,可是只要他们并没有为此想到国王不存在,且只要他们足够认识他以便不去质疑他,那么,当他的众臣民越不熟悉他,国王就越有威严。”(Ibid.)),到1641年《沉思集》的“前言”(“应该考虑我们的众精神就如已经得到了限定,而考虑上帝就如‘不可囊括地把握的’和无限的”②AT VII,p.9,ll.15-17:simusmentes nostras considerandas esse ut finitas,Deum autem ut incomprehensibilem& infinitum.法译文不在AT本卷IX,是克莱尔色列(Clerselier)在1661年第二版法译文中译出,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392.令人感到惊讶的是,中译文居然把这段话整个给漏了!),笛卡尔始终用“不可囊括地把握的”这一词汇来表示我们对于上帝既能智识(intelligere,entendre③笛卡尔拉丁文本中“intelligere”(智识)一词几乎都被翻译为法文“concevoir”(构想或设想)一词。阿尔盖为此批评克莱尔色列把《沉思集》及其众反驳与答辩中的拉丁动词“intelligere”(智识)几乎都错误地翻译为法语动词“concevoir”(cf.Alquié,Descartes.Œuvres philosophiques,t.II,p.369,note1 et p.371,note1)。卑萨德(Beyssade)则认为这是那一时代的习惯(cf.Jean-Marie Beyssade,Descartes.L’entretien avec Burman,edition,traduction et annotation par Jean-Marie Beyssade,PUF,1981,p.47,note2)。)却又不能“囊括地把握”(comprehendere,comprendre④需要指出的是,中译本《第一哲学沉思集》把“comprendre/comprehendere”一词译为“理解”或“懂得”,故到处出现“不可理解”或“不能懂得”却又可以“认识”无限这样根本无法理解的话。)的这种“奇怪”认识。为了更好地理解该词,我们需要从智识、“囊括地把握”,以及与这两种认识行为关系甚密的其他几种认识行为之间的关系说起。
其一,智识、构想(concipere)和想象之间的关系。《沉思三》中有两个所谓的表达式⑤按照马礼荣(Marion)的说法,这两个表达式其实包括通过众结果而得到上帝实存之证明,该证明在第一表达式之前开启,而在第二表达式样之后结束(J-LMarion,Sur le prisme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PUF,1986,p. 223)。在这两个表达式中也不难发现,其中既有通过智识上帝的本性直接证明上帝实存的相关内容,也有通过众后果(我们心中的上帝观念和拥有上帝观念的我们)来间接证明上帝实存的内容。是直接谈论上帝的,其中都用“智识”(intelligo,我智识)一词来指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我由之智识到某个至高的、永恒的、无限的、全知的、全能的、作为他之外所有事物的造物主的上帝之观念,相比众有限实体由之得到展示(exhibentur)的那些观念而言,它在自身中肯定拥有更多的对象性实在”⑥Méditation III,AT VII,p.40,ll.16-20:illa per quam summum aliquem Deum,aeternum,infinitum,omniscium, omnipotentem,rerumque omnium,quae praeter ipsum sunt,creatorem intelligo,plus profecto realitatis objectivae in se habet,quàm illae per quas finitae substantiae exhibentur.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32.“intelligo”(智识)一词在法译文中被翻译为“conçois”(设想);“exhibentur”(得到展示)在法译文中被翻译为“sont représentées”(得到表象)。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0页。,和“用上帝之名,我智识到某个无限的、独立的、至高智识性的、至高有能力的实体,而且,通过这一实体,时而自我本身,时而任何其他东西(如果,这个其他东西出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显然的)被创造出来”⑦Ibid.,ATVII,p.45,ll.11-14:Deinomine intelligo substantiam quandam infinitam,independentem,summe intelligentem,summe potentem,&a quâtum ego ipse,tum aliud omne,si quid aliud extat,quodcumque extat,est creatum.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p.35-36.其中“intelligo”(智识)一词在法译文中被正确地翻译为“entends”(智识)。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5-46页。。后来笛卡尔明确谈到智识与构想及想象的区别:“这里,大家应该细心地区分智识活动、构想活动和想象活动:这种区分有一种很大的用处。例如,上帝的众完满,我们既不能想象它们,也不能构想它们,但我们智识它们……假设我们构想它们[上帝的众完满或众属性],我们就把它们构想为‘没有做出限定的’(indefinita)。”①L’entretien avec Burman,edition,traduction et annotation par Beyssade,pp.46-47.Le texte latin cf.aussi AT V, p.154.笛卡尔在不少地方把“imaginari,imaginer”(想象)和“concipere,concevoir”(构想)等同起来,对立于“intelligere,entendre”(智识),如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AT X,p.416,ll.3-4中的“imaginari vel concipere”以区别“intelligere”;A Clerselier,12 janvier 1646,AT IX,p.212中的“concevoir ou imaginer”以区别“entendre”(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95页)。但非常有意思的是,笛卡尔本人在其法文文本中有时候也把“concevoir”(设想)一词运用到无限或无限的众属性之上,如“如果上帝不是通过想象而被设想的话,那么,或者当大家谈论上帝时大家什么也没有设想(那种东西会标出一种可怕的盲目),或者大家以另一种方式设想他;不过,既然当我们智识我们所说的东西时,只有从这点本身——即只有我们在我们之中拥有关于被我们众言语所指称的事物的观念,这才应该是确定的——出发,我们才能通过我们的众言语来表达,那么,大家以某种方式设想他,大家拥有他的观念”(AMersenne,juillet1641,AT III,p.393);以及前面已经引用过的“我所设想的是无限存在”(A Clerselier,23 avril 1649,AT V,p.356,ll.8-14)。对此,也有专家专门指出,笛卡尔时代的人习惯用“concevoir”来翻译“intelligere”(Beyssade,Descartes.L’entretien avec Burman,p.47,note2)。如果该解释成立的话,说明当时的法语“concevoir”就有“intelligere”(智识)的意思,故笛卡尔把“concevoir”一词运用到无限或无限的众属性之上也是无可厚非的。由此可见,法文“concevoir”一词的涵义并不等同于拉丁文动词“concipere”和名词“conceptio”,而是超出了两者的范围,有时候可与拉丁文动词“intelligere”(智识)相当,有时候甚至可与更为宽广意义上的拉丁文动词“percipere”(觉知)相当。我们把拉丁文动词“concipere”和名词“conceptio”都翻译为“构想”,而把法文“concevoir”一词有时翻译为“构想”(当它与拉丁文动词“concipere”相当时),有时翻译为“设想”(当它超出拉丁文动词“concipere”的范围时)。这些都说明我们只能依靠智识这种单独的“力”的作用——“最后它[这种力]单独起作用,它就是智识”②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AT X,p.416,l.4:si denique sola agat,dicitur intelligere.与“智识单独起作用”不同的是,这种“力”适用在创立诸新形象的想象之上的结果,就是“想象或构想”(cf.AT X,p.416,ll.2-4:si ad eandem ut novas fingat,dicitur imaginari vel concipere)。——来认识上帝以及其众属性或众完满。当然,智识这一认识行为的使用范围也是非常广泛的,并不仅仅用于上帝及其众属性或众完满。可以这样说,要想认识真实的、清楚的且分明的东西,都离不开智识这种“力”的作用,只不过在认识上帝及其众属性或众完满问题上,我们只能依靠这种单独的“力”去“纯粹地智识”(pure intelligere)③Principia philosophi I,AT VIII-I,p.17,l.23.。
其二,理智/智识与知觉(perceptio,perception)/觉知(percipere,percevoir)之间的关系。在笛卡尔体系中,相比智识,觉知是一个更为宽广的大概念,他称之为两大思维模式之一,并直接把它与理智的运作活动等同起来(“知觉或理智的运作活动”④Ibid.,ATVIII-I,p.17,l.21.),且认为“感觉、想象和纯粹智识只是觉知的不同模式”⑤Ibid.,AT VIII-I,p.17,ll.22-23.,所以当笛卡尔说我们能够觉知上帝或无限时,如“……在我所觉知的上帝观念中……”⑥Méditation III,AT VII,p.48,ll.19-20:…in ideâDei percipio…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38.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9页。,“我不应该估算如下,即我不是通过一种真实的观念,而只是通过对有限者的否定来觉知无限,正如我也不应该估算如下一样,即我通过对运动和光明的否定来觉知静止和黑暗”①Ibid.,ATVII,p.45,ll.23-26:Nec putare debeome non percipere infinitum per veram ideam,sed tantùm per negationem finiti,ut percipio quietem&tenebras per negationem motùs&lucis 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36.需要指出的是,法译文前半句用“concevoir”来翻译“percipere”,后半句则用“compredre”来翻译“percipere”。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6页。,他都是把觉知当作一种智识来使用。当然,即便觉知作为一种智识,其使用范围也是比较大的,我们既可以觉知上帝观念或无限观念,也可以觉知任何有限观念,“单独通过理智,我只能觉知我能够对之下判断的那些观念……”②Méditation IV,AT VII,p.56,ll.15-16:per solum intellectum percipio tantùm ideas de quibus judicium ferre possum.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49.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59页。,这跟我们在上述“其一”部分指出的智识情况是一样的。
其三,智识、“囊括地把握”、触及(attingere,toucher)和瞥见(apercevoir)之间的关系。笛卡尔这样说:“由于‘囊括地把握’一词指某种限定,故一个有限的精神无法‘囊括地把握’无限的上帝;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有限的精神瞥见他,正如虽然人们不能怀抱(embrasser)一座山,却能很好地触及它。”③A Clerselier,12 janvier 1646,AT IX,p.210.原文为法文。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93-394页。还有,“这并不妨碍以下事实,即,不存在被‘囊括地把握’的无限,或者④这里的“或者”关系对应于AT本卷VII第113页9-17行所说的“无限性”与“无限的东西”之间的区别关系。在上帝中有无数的另一些东西(我以任何方式既不能‘囊括地把握’它们,也不能通过思维活动有力地触及它们)”⑤Méditation III,AT VII,p.46,ll.18-21:Nec obstat quod non comprehendam infinitum,vel quod alia innumera in Deo sint,quae nec comprehendere,nec forte etiam attingere cogitatione,ullomodo possum.Traduction française,cf. AT IX,p.37.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7页。。从中可以看出,一方面,除了智识和觉知,笛卡尔还使用了两个并不怎么学术化的词汇(瞥见与触及)来表示我们对于上帝及其众属性的认识。需要注意的是,瞥见在此并不表示,“他们看上帝就如同远处看过去一样”⑥Réponses aux premières objections,ATVII,p.114,l.3:tanquam e longinquo respiciunt.Traduction française,cf. AT IX,p.9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7页。,并不是表示“混沌地(confuse⑦Ibid.,ATVII,p.113,l.22.第一组反驳作者卡特鲁斯(Caterus)引用圣·托马斯在《神学大全》第一册问题2条目1解答1中谈到“以某种普遍的方式(in aliquo communi)”和“在某种混沌情况下(sub quadam confusione)”来认识上帝的存在,认为我们对于无限的认识只能是“混沌地”或无限于我们是不可知的。在此问题上,笛卡尔显然并不认同圣·托马斯和卡特鲁斯,他之前举了大海和千边形的例子,认为要想认识到整个大海或整个千边形,那只能是“混沌地”认识,随后语锋一转,认为如果由此推断出对于上帝的认识也是“混沌地”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不能清楚分明地认识到上帝。由此可见,一方面,无限或上帝与大海及千边形具有某种相似性,即,我们既无法“囊括地把握”大海及千边形,也无法“囊括地把握”无限或上帝;另一方面,我们能够清楚分明地认识到整个无限,却只能“混沌地”认识整个大海或整个千边形。(cf.Summa Theologiae I,q.2 a.1 ad.1.ATVII,pp.96-97,pp.113-114)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笛卡尔在此问题上并不认同圣·托马斯和卡特鲁斯,但并不意味着他认为前两者认可对于上帝的认识是模糊的这样的观点。法译文中有这么一句话“comme sous une image obscure”(就如在一种模糊的像之下),是克莱尔色列后来添加上去的,拉丁文原文里并没有。)”看,而是整个一下子看到上帝,我们对他具有清楚的观念,而且是“最真实、最清楚且最分明的观念”①Méditation III,AT VII,p.46,l.28:maxime vera,&maxime clara&distincta.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 37.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7页。,简言之,瞥见在此其实就是一种智识。至于触及,熟悉哲学史的人都知道,它属于精神的看(intuitus②马礼荣从笛卡尔著作中找到大量论据来说明并不适宜用“intuition”(直观)(康德意义上或胡塞尔意义上)来翻译笛卡尔文本中拉丁文名词“intuitus”,并主张用法文名词和动词“regard/regarder”来翻译笛卡尔文本中拉丁文名词和动词“intuitus/intueri”。cf.Descartes,Règles utiles et claires pour la direction de l'esprit en la recherche de la vérité:Traduction selon le lexique cartésien,et annotation conceptuelle par Jean-Luc Marion avec des notes mathématiques de Pierre Costabel,Paris:Martinus Nijhoff,1977,pp.295-302:Annexe I,Traduction d’intuitus et utilisation de regard.我们把法文名词和动词“regard/regarder”翻译为“理智的看/智视”,且认为这属于希腊哲学精神的看的传统。)的传统,在此更多地是要表示前面所说的智识这种单独的“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囊括(地把握)”就如“怀抱”,上帝是最大者,所以我们无法“怀抱”上帝,无法“囊括”其全部属性,无法穷尽它们,“……自我无法‘囊括地把握’它们[所有那些完满],却能够通过思维活动以无论哪种方式来触及它们”③Ibid.,AT VII,p.52,ll.4-6:quas ego non comprehendere,sed quocunquemodo attingere cogitatione possum.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41:dont notre esprit peut bien avoir quelque idée sans pourtant les comprendre toutes.需要指出的是,第一版法译文并没有译出“attingere”(触及)这一重要词汇。中译文按照第一版法译文译出,自然也没有译出该词,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53页。,在此,“囊括地把握”与触及的区别清晰可见。
其四,关于“囊括地把握”、知觉和“concevoir”(构想或设想)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由于笛卡尔本人在相当宽泛的意义上使用“concevoir”(构想或设想)一词,以及它与拉丁动词“concipere”(构想)之间既同又异的关系,导致该认识行为与其他认识行为之间的关系难以被理解——尤其是“囊括地把握”与“concevoir”(构想或设想)之间的关系。二十世纪笛卡尔研究名家们甚至为此产生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譬如,卑萨德认为“‘concevoir’(构想)与‘囊括地把握’相近,而并不必然地与智识相像”④Beyssade,Descartes.L’entretien avec Burman,p.47,note2.;而阿尔盖则把“concevoir”(设想)与“囊括地把握”对立起来,认为上述形而上学观念如上帝观念,“不能被‘囊括地把握’,却能被设想(conçue)”⑤Alquié,Descartes.Œuvres philosophiques,t.II,p.345,note2.。我们怀疑,前者是在拉丁动词“concipere”(构想)意义上使用“concevoir”(构想)一词,而后者则是在觉知的宽广意义上使用“concevoir”(设想)一词。⑥当阿尔盖说“我们的意志只能基于我们所设想的东西”时(Alquié,Descartes.Œuvres philosophiques,t.II,p. 371,note1),我们知道他所说的“concevoir”(设想),其实就是笛卡尔所说的觉知——譬如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版法译文就曾经用“concevoir”来翻译“percipere”(觉知)。如果该解释成立的话,阿尔盖会陷入某种矛盾之中,譬如,一方面他批评克莱尔色列把笛卡尔文本中的“intelligere”(智识)错误地翻译为“concevoir”(我们可以推断,该错误的前提就是,阿尔盖把法语动词“concevoir”狭义地等同为拉丁动词“concipere”(构想),当然,如果大家都用法语动词“entendre”(智识)来翻译拉丁动词“intelligere”(智识)的话,那或许就没有那些歧义与纷争了);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在觉知的意义上使用“concevoir”一词来认识上帝及其属性,而觉知上帝及其属性其实就是“intelligere”(智识)上帝及其属性。
最后,我们可以这样简单地来小结:虽然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上帝及其众属性或众完满,我们无法构想他和它们,但我们却能智识和觉知他以及它们,却能以这样的方式瞥见和触及他以及它们。
笛卡尔最初把“囊括地把握”一词主要应用于无限的东西领域,后来则把“不可囊括地把握性”(incomprehensibilitas)上升至“无限的形式理性”的高度。在《第一组答辩》中,他这样说:“我在无限的形式理性或无限性与其乃无限的东西之间加以区分;因为,至于无限性,尽管我们智识它为多么地、尽可能大地肯定性的,可是,根据以下这个事实——我们显然无法在[无限性这一]实在之中(in re)标出任何限制——除非以某种否定的方式,否则我们无法智识它[无限性];至于其乃无限的东西本身,我们的确肯定性地智识它,而不是完全相当地智识它,这就是说,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在该东西之中可被智识的全部东西。”①Réponses aux premières objections,AT VII,p.113,ll.9-17:Praeterea distinguo inter rationem formalem infiniti, sive infinitatem,&rem quae est infinita;nam quantum ad infinitatem,etiamsi illam intelligamus esse quàm maxime positivam,non tamen nisinegativo quodam modo intelligimus,ex hoc scilicet quôd in re nullam limitationem advertamus;ipsam verôrem,quae est infinita,positive quidem intelligimus,sed non adaequate,hoc est non totum id,quod in eâintelligible est,comprehendimus.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9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7页。而到了回答伽桑狄反驳的《第五组答辩》中,笛卡尔则明确提出把“不可囊括地把握性”作为无限的形式理性:“我说,我将提请你注意,说我‘囊括地把握’某种东西,而且我所‘囊括地把握’的东西应该就是无限,这是令人厌恶的说法;因为,就‘不可囊括地把握性’本身包含在无限的形式理性之中而言(Ipsa incomprehensibilitas in ratione formali infinti continetur),要想有一种关于无限的真正观念,无限以任何方式都不应该‘被囊括地把握’(debet comprehendi)。”②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367,l.25-368,l.4:Moneo,inquam,e contra plane repugnare,si quid comprehendam,ut id quod comprehendo sit infinitum;idea enim infiniti,ut sit vera,nullomodo débet comprehendi,quoniam ipsa incomprehensibilitas in ratione formali infiniti continetur.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811.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38-369页。简言之,不但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其乃无限的众东西,即无限之众属性或众完满,而且更为根本地在于,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无限本身即无限性,因为“不可囊括地把握性”代表了无限的形式理性,代表了无限的本质。
具体来说,“不可囊括地把握性”可分以下三个层面:其一,由于上帝的众属性或众完满性是无限多的,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到它们;其二,即使是上帝的每一个属性或每一个完满性,由于它们各自所具有的无限性,我们也无法“囊括地把握”到它们;其三,至于无限本身或无限性,其本质就是“不可囊括地把握性”。与之相对的我们的智识情况,或许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其一,我们无法智识到上帝的所有属性或所有完满性,只能有限地智识到其部分属性,“可是,当我每一次说上帝能够清楚且分明地被认识时,除非从这种有限性和理智禀性之度量出发,否则我无法通过我们的适当思维活动进行智识”①Réponses aux premières objections,AT VII,p.114,ll.14-17:Ego autem,ubicumque dixi Deum clare&disctincte posse cognosici,non nisi de hac finita&ad modulum ingenii nostri accommodata cognitione intellexi.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9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18页。;其二,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到上帝的每一个属性或每一种完满性本身,却能够智识到它们;其三,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到无限本身,却能够智识它。其中两个“其一”情况并不难理解,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无限的众部分,只能有限地智识到其部分;难以理解的是两个“其二”和两个“其三”问题。然而,它们其实属于同一类问题。我们不能“囊括地把握”到无限的全部,却能智识到整个无限——“明显的是,从它应该被人类观念所表象(debet repraesentari)这一方式出发,我们拥有的无限观念不仅表象某一部分,而且是整个无限(totum infinitum)”②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p.368,ll.5-8:estmanifestum,ideam quam habemus infiniti,non repraesetare tantum aliquam eius partem,sed revera totum infinitum,eomodo quo debet repraesentari per humananm ideam.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p.811-812.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68-369页。。
这是为什么呢?笛卡尔随后用三角形观念的例子做出解释:“同样,尽管对于几何学家们而言这同一个三角形的许多其他东西能够被认识且在其观念中能够得到留意,对于那个人而言它们则是未知的,不过,当他把三角形智识为由三条线所构成的一个形象时,我们实际上无法怀疑,那个于几何学并不了解的人通过理性拥有整个三角形观念。”③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368,ll.11-16:Eadem ratione qua non dubitamus quin Geometriae imperitus totius trianguli ideam habent,cum figuram esse tribus lineis comprehensam intelligit,etsi a Geometris alia multa de eodem triangulo cognosci possint atque in eius edea animadverti,quae ab illo ignorantur.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812.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69页。坦白地说,这个三角形观念的例子并不能释疑上述“无限的全部”和“整个无限”之间的关系问题,原因很简单,由三条线所构成的整个三角形(观念)与整个无限(观念)根本不能等量观之。④cf.Alquié,Descartes.Œuvres philosophiques,t.II,p.816,note1.我们或许可以从笛卡尔随后的一句话中找到答案:“实际上,这就好比,去拥有整个三角形观念,去智识一个由三条线所包围的形象就足够了;因此,为了拥有关于整个无限的一个真实的和完整的观念,去智识一个不被任何限制所围绕的(comprehensam)东西就足够了。”⑤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368,ll.16-20:Ut enim sufficit intelligere figuram tribus lineis contentam,ad habendam ideam totius trianguli;sic quoque sufficit intelligere rem nullis limitibus comprehensam,ut vera&integra idea totius infiniti habeatur.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 812.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69页。笛卡尔认为三角形观念与上帝观念具有一定的可比性,关于上帝实存的论证与关于三角形实存的论证以及它们的方法“实际上都是相同的(enim est par)”,只不过关于上帝实存的论证比关于三角形实存的论证要“更加简单和清楚(multo simplicior&clarior)”,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可比性:“可能的实存在三角形观念中是一种完满,就像必然的实存在上帝观念中是一种完满一样(existentia possibilis sit perfectio in ideâtrianguli,ut existentia necessaria est perfectio in ideâDei)”;不过,“可能的实存”与“必然的实存”之间的差别,“只有必然的实存与上帝相匹配(illi soli competit)”,造就了两者在实存上的根本差异。(cf.AT VII,pp.383-384.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81-382页。)简言之,笛卡尔在此关心的是如何用最常用的话来说上帝或无限,且认为这已足够说明上帝观念或无限观念。①可参见Contra Hyperaspistem,août 1641(第250封)中笛卡尔提及上述《第五组反驳》那段话的一个文本:“Et cum dixi pag.522,sufficere quod intelligamus rem nuliis limitibus comprehensam,ad intelligendum infinitum,sequutus sum modum loquendi quàm maxime vsitatum.”(我在第522页说,为了智识无限,我们智识没有被任何限制所环绕的东西就足够了,我尽最大可能遵循已经得到检验的说话方式。)(AT III,p.427,ll.9-11)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365.我们之所以提出困扰我们的“无限的全部”和“整个无限”之间的关系问题,与我们在后面第三部分要阐述的上帝观念的发生说有着很大的关联。
三
前面已经指出,在笛卡尔哲学体系中,上帝观念属于天生观念一类,与自我一起诞生,凡是有理性的人,他一诞生就具有上帝观念。在关于上帝观念天生性②我们主张翻译为“天生性”,而非通常所译的“先天性”,正是取其“发生性”,而非“上帝赋予性”,详细论述见后文。的问题上,一方面,笛卡尔显然受到了柏拉图“回忆说”的影响,因为在他看来,不论你是否拥有具体的这一类天生观念,天生观念其实早已处在你的精神之中,你能够通过回忆得到它,譬如他在《第五沉思》开头谈到数、形象、运动以及诸如此类的天生观念时就说:“它们[众个别情况]的真理对于我的本性而言是开启的和相合的,以至于到了这种地步,即,当我第一次发现它们时,在此我看起来并没有另外学到新的某个东西,更多地是回忆起从前我已经知道的关于它们的那些东西,或者第一次把注意力朝向它们(它们不久以前确实存在于我之中,尽管从前我并没有把精神的目光转回到它们)”③Méditation V,AT VII,pp.63,l.25-64,l.5:quorum veritas adeo aperta est&naturaemeae consentanea,ut,dum illa primùm detego,non tam[mois que]videar aliquid novi addiscere,quàm eorum quae jam ante sciebam reminisci, sive ad ea primùm advertere,quae dudum quidem in me erant,licet non prius in illa obtutum mentis convertissem. 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51.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68页。,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曼奴的例子;另一方面,他总是把上帝观念与众数学观念(如数的观念、形象的观念等)进行比较,始终坚持上帝观念在真理性上高于众数学观念的一贯思想。在1630年5月6日《给麦尔赛纳的信》中笛卡尔写道:“这些真理[众数学真理]的必然性并没有超出我们的认识,它们是比这种‘不可囊括地把握’的能力更小点的且受后者支配的某种东西(quelque chose demoindre et de sujetà cette puissance incompréhensible)”④A Mersenne,6mai 1630,Corresp.XXII,AT I,p.150.原文是法文。——阿尔盖在该页的注释上为此解释道:“科学处于可囊括地把握的众观念的领域。形而上学则是关于不可囊括地把握的上帝观念的研究。在笛卡尔明确的学说中,众科学将屈从于形而上学,不需要一个其他理由”⑤Alquié,Descartes.Œuvres philosophiques,t.I,p.265,note2.。后来的《沉思五》则说:“然而,一旦我使精神的穿透力转离那个论证[三角形论证],尽管我仍然记得自身最清楚地认出它,可是,如果我确实不认识上帝,那么很容易就会发生以下情况,即我怀疑它是否真实。”①Méditation V,AT VII,p.70,l.1-4:sed statim atque mentis aciem ab illâdeflexi,quantumvis quamvis adhuc recorder me illam clarissime perspexisse,facile tamen potest accidere ut dubitem an sit vera,si quidem Deum ignorem.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55.(法译文并没有译出“mentis aciem”(精神的穿透力)这个有哲学传统含义的词汇,中译文按照第一版法译文译出,自然也没有译出该词,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72-73页。笛卡尔又觉得两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至少)同等性(in eodem gradu ad minimum②在上帝观念所具有的实在性问题上,笛卡尔也有讲到这种“至少同等(量)”(tantumdem ad minimum...quantum;au moins autant…que)的情况。(Méditation III,AT VII,p.40,ll.21-25;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32.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40页。),“在我之中,相比较众数学真理,仅就程度而言,上帝的实存至少应该是同等确定的”③Méditation V,AT VII,pp.65,l.28-66,l.1:in eodem ad minimum certitudinis gradu esse deberet apud me Deiexistentia,in quo fuerunt hactenus Mathematicae veritates.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52.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69页。,从而有可能借用数学论证的方式来论证上帝。④在数学真理和形而上学真理的关系问题上,盖鲁认为可以相似地对待形而上学论证如上帝实存论证和数学论证,而古耶则并不赞同这种说法。cf.Gouhier,La preuve ontologique de Descartes,(àpropos d’un livre récent), dans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n°29,1954,et La pensée 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p.177.Gueroult, Nouvelles réflexions sur la preuve ontologique,Paris:Vrin,1955 et Descartes selon l’ordre des raisons I,chap.8.然而,《哲学原理》第一册第五条的标题明确为“为什么我们同样能够怀疑数学论证”(Principia philosophiœI,AT VIII-I,p.6),相反,形而上学论证则被认为是不可怀疑的。
我们在这里想探讨的,不是上帝观念在笛卡尔整个形而上学体系中如何产生的问题——按照《沉思集》的逻辑理路,笛卡尔提出上帝观念,至少有摆脱唯我论困境的考量,而是上帝观念的天生性本身是如何发生的问题,也就是说,人类精神为什么必然会天生地被赋予这种观念,这是人类精神自身造成的吗?
在《沉思三》中,笛卡尔这样来谈论上帝观念的这种天生性:“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把这个观念分发给我,以便就像艺术创造者铭刻在其作品之上的众印记一样,当然这并不令人惊讶。”⑤Méditation III,AT VII,p.51,ll.15-17:Et sane non mirum est Deum,me creando,ideam illam mihi indidisse,ut esset tanquam nota artificis operi suo impressa.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41.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53页。到底该如何来理解这种表达呢?我们暂且把上帝造人⑥笛卡尔讲过三种创造或生产,即上帝造人及造物、自然生产和人工生产,前者和后两者是根本不同的,因为前者是以“依据存在”(secundum esse)的方式创造,后两者则以“依据产生”(secundum fieri)的方式创造。“依据存在”的创造就是笛卡尔讲的连续性创造,需要上帝来保存。(cf.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 AT VII,p.369.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70页。)这一西方传统思想放在一边,先从“(众)印记”(nota)一词出发,来看看它与天生性之间究竟有什么样的关联。那么,什么是“艺术创造者的(众)印记”呢?在回答伽桑狄“这个印记是什么形式的?”这一疑问时,笛卡尔明确表示:“这就如同,在某幅画之中如此多的技艺被发现,以至于我判断它只能由阿贝尔(Apelle)本人独自所画,且我会说,这种不可模仿的技艺就如阿贝尔以前铭刻在其所有的画之上以便与其他的画区别开来的一种印记”①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372,ll.3-8:idem est aliqua in tabella tantum artificii deprehendens ut ipsam a solo Apelle pingi potuisse judicarem,diceremque inimitalbile istud artificium esse veluti[just as] quondam notam,quam Apelles tabellis omnibus suis impressit ut ab aliis dignoscantur,tu vero quaereres.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817.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72页。,也就是说,“艺术创造者(众)印记”并不是像签名一样的东西,而是像画的风格之类的东西,它使画家马上被认出来且与其他画家区分开来,就如法国人经常说的,“这是莫奈的东西”,“这是塞尚的东西”,等等。那么,上帝观念代表哪种风格呢?我们不妨借用古耶的话来做个小结:“如果我们之中的上帝观念就如画家在其作品之上的印记的话,如果这一标记更多地与画的风格而不是与写有其签名的画的那一块相比拟的话,这就意味着,我们之中的这一观念就不像其他东西旁边的一个东西。”②Gouhier,La pensée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p.196.简言之,上帝观念其实并不仅仅是我们之中众多观念之一,而是充当了另一种更为重要的角色③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上帝观念与我们之中其他众观念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笛卡尔哲学意义上观念与众思维活动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上帝观念具有某种“元形式”的功能。,即,如果我们认可笛卡尔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那么,我们同时就得承认,上帝观念就是上帝铭刻在所有造物上面的他的印记,也是我们所有观念中必定带有的共同东西,可以说它代表了上帝创造之风格。
上帝观念的这种“风格”,一方面说明,虽然我们人类作为造物是有限的和不完满的,但有限的和不完满都是对无限和完满的一种截去或否定,这其实必然已经隐含着,无限和完满早已天生地、验前地、深深地烙印在我们的精神之中。换言之,我们有缺陷(defectus),我们有怀疑和欲望(dubitare et cupere),我们是有限的,但上帝在创造我们的同时也让我们智识到无限与完满的典范,即上帝本身,或许这正是上帝观念的天生性所隐藏的真正含义。另一方面,当我们说上帝观念是上帝创造人类世界的风格时,同时也意味着,这并不是其他理智体所拥有的上帝观念,因为,笛卡尔在回答伽桑狄关于无限观念的问题时确实谈到其他理智体可能拥有的上帝观念,“尽管毫无疑问,另一种远为完满的无限观念即更为确切和分明的无限观念能够被上帝或比人类本性更完满的另一种理智性本性所拥有”④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368,ll.8-11:etsi procul dubio aliamulto perfectior,hoc est accuratior&disctinctior,haberi posit a Deo,aliave natura intelligente,quae sit humana perfecior.Traduction française, 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812.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69页。,故上帝观念可以说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特有现象,即我们的有限性。
我们可以把上帝观念的天生性与我们有限理智的独特性联系起来。从静态角度看,人类理智是有限的、不完满的,而上帝是无限的和完满的,两者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一道鸿沟;而从动态角度看,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无限与有限并不是一种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张力关系:一边是我们永远不可能越过的极标即无限,另一边则是我们总是想超过自身界限,“总是要去认识更多东西”的一种“力”。熟悉笛卡尔哲学的人都知道,这种“力”就是意志的力量。在意志与理智的关系上,笛卡尔哲学有一个明显的“印记”,即他赋予人类理智一定的有限性,却没有给人类意志设定任何限制,“因为我确实体验到它[意志]并不为任何限制所环绕”①Méditation IV,AT VII,p.56,ll.29-30:nam sane nullis illam limitibus circumscribi experior.Traduction française,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45.法译文多加了“si vague et siétendue(如此含混和如此宽广的[意志])”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59页。。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当意志比理智伸展得更为宽广时,我并不把它包含在同样的众限制之中,而是,我仍然把它伸展到我智识不到的众东西处;它对于它们而言当然是不好不坏的(indifferens),它容易离开真和善,而且因此我弄错和做坏事。”②Méditation IV,AT VII,p.58,ll.21-25:cùm latius pateat voluntas quàm intellectus,illam non intra[+acc.]eosdem limites contineo,sed etiam ad illa quae non intelligo extendo;ad quae cùm sit indifferens,facile a vero&bono deflectit,atque ita&fallor&pecco.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46.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59页。简言之,意志总是想越过理智的界限,怂恿理智去囊括地把握无限,却总是不成功,这就是错误的来源。
我们在这里并不想讨论真理与错误的问题,而是对意志与理智的这种关系感兴趣,或者说,对这种张力关系下两者协同运作的内在机制感兴趣。笛卡尔在《第二组答辩》中曾经举了个数的例子来具体说明这种运作:“而且我断言,单从以下这个事实出发,即通过思维活动或理智活动我以某种方式触及位于自我之上的某种完满,您想想,单从以下事实出发,即我注意到我在数数中并不能够达到所有数的最大者且我因此认识到数数理性里有某种东西超出我的众力量,我必然得出结论,至少一个无限的数并不实存,如您所说,也不是为了包裹它(illum implicare),而是,构想可思的更大的数的这种力通过我有一天能够被认识,我并不是来自自我本身处,而是从另一个比我更完满的存在处接受它。”③Réponses aux cinquièmes objections,AT VII,p.139,ll.11-22:&contendo ex hoc solo quod attingam quomodolibet cogitatione sive intellectu perfectionem aliquam quae suprame est,puta ex hoc solo quod advertam inter numerandum me non posse admaximum ominium numerorum devenire,atque inde agnoscam esse aliquid in ratione numerandi quod viresmeas excedi,necessario conclude,non quidem numerum infinitum exister,ut neque etiam illum implicare,ut dicitis,sed me istam vim concipiendimajorem numerum esse cogitabilem quam a me unquam possit cogitari,non ameipso,sed ab aliquo ailo enteme perfectior accepisse.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p.109-110.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43页。令我们感兴趣的不是其中的最后一句话(即这种力并非来自自我本身而来自上帝),而是这种力所涉及的一种张力状态。古耶把它与无限观念的情况进行对照,并且形象地概括道:“因此,无限存在的观念被抛入‘没有做出限定地’去添加的能力之中——对于我们称之为‘观念’的东西而言,由此得出什么结论呢?在这里,观念的内容就是这一不可想象的数(ce nombre inimaginable),它被感觉为可想象的最大数(le plus grand nombre imaginable)的一种彼岸,而且,既然观念阻止精神停顿在这一最大的可想象的数上面,那么,这一不可想象的数因此就使观念成为根本上是动力性的东西。”①笛卡尔见伽桑狄不能理解上帝观念的整体性,就提请他注意众哲学家都认可的事,即“事物的众本质都是不可分的”(essentias rerum esse indivisibiles)。(AT VII,p.371,ll.10-11.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816.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371页。)
单就人类理智而言,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无限的全部,却能智识整个无限;而意志加入后的情形则是,我们可以想象“最大的可想象的东西”,可以欲求在它的彼岸总有一个“不可想象的东西”存在。为了更好地理解两者协同运作的情况,需要做进一步说明:其一,这个“不可想象的东西”,并不处于无限的全部之中,因为说到全部,还是就可数的或可想象的意义(尽管这是一种“无限可分或可数”的情形,就像自然数)而言。当然,作为意志欲求的对象,作为无限观念所要表示的东西,它就是整个无限。我们无法想象或构想的东西,却能用观念的形式来智识,于是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可以想象“最大的可想象的东西”,但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无限的全部;相反,我们无法想象“不可想象的东西”,无法想象整个无限,却能智识整个无限。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做解释:前者属于“无限可分或可数”的情形,仍然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但由于是“无限多的”,我们无法“囊括地把握”到无限的全部;后者超出了想象的范围,是意志想在想象范围之外欲求的一种东西,作为整个,我们却能智识,我们把它当作一种不可分的②De Buzon et Kambouchner:Le vocabulaire de Descartes,2002,p.36.本质来智识,它是“无限不可分的”,而且,只有在整个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智识到它。进一步说,“可分或可数的无限的全部”这一表达式其实并不是用来描述无限本身,而是完全相对于我们理智的有限性而言,因为,“尽管在我们之中是可分的东西,在它[无限]之中却是独一的”③Aristote,Physique,livre III,chap.4,206b34-207a30.,独一或整个才是无限本身。在此我们再次看到笛卡尔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在无限问题上的根本差异,因为后者恰恰把无限与整个(整体)对立起来。④我们知道,在笛卡尔哲学中,欲望(cupere)属于意志范围。(参见《哲学原理》第一册第32条,Principia philosophiœI,ATVIII-I,p.17,l.24-25)。
其二,那个“不可想象东西”本身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缺乏(un manque)。在缺乏问题上,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精神分析学研究成果,没有一门学科比精神分析学更加深入地探讨缺乏问题。如果说弗洛伊德还是比较间接地论及缺乏问题的话——譬如他认为愿望(欲望)总是找不到其真正对象,于是只得找一种替代性对象来暂时满足,对象总是另一个(un autre),那么,拉康就直接把缺乏本身视为欲望⑤参见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八章第一节。的对象,认为欲望是对缺乏的欲望。⑤缺乏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或吸引力,譬如《会饮》对话中美少年阿尔基比亚德所迷恋的,苏格拉底身上的那种无人拥有的“Agalma”就是一种典型的缺乏。同样,这一不可想象的东西作为缺乏,对人类精神也有一种致命的诱惑力,它引发意志怂恿理智“总是要去认识更多东西”。为什么在此要引入精神分析的缺乏概念呢?我们无非是想说明,在以往的解释中,对于意志的越矩性强调得比较多,譬如说我们的意志超出理智的范围,总是怂恿理智越界去“囊括地把握”上述“不可想象之物”等,而对于另一方面,即意志的这种特性是如何形成的那方面却谈论得比较少,我们在此就想在这一方面做点补充。可以简单地说,意志是被缺乏所引诱。当然,大家都不太赞同在“实在论”意义上来理解这种诱惑,而更愿意从相互作用,从思维活动本身的运作这一角度出发来理解上述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再次借用一下精神分析的另一个大概念即无意识,无意识所具有的自动装置式的自动运作或许可以解释上述思维这种运作情形。
其三,为什么会欲求处于彼岸的这一“不可想象的东西”呢?归根到底还是我们有缺陷,我们会怀疑。在笛卡尔哲学精神中,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会怀疑,能够推论出上帝存在。早在《指导精神的规则》一文中,基于上述“隐含地”(implicite)这种原理,笛卡尔就明确道出“我存在,故上帝存在”①Regulae ad directionem ingenii,AT X,p.421,l.29:sum,ergo Deus est.,且进一步解释道:“就如从我存在的事实必然推论出上帝存在,可是,从上帝存在的事实还是不可以去肯定我实存的事实。”②Ibid.,AT X,p.422,ll.3-6:ut quamvis ex eo quod sim,certo concludam Deum esse,non tamen ex eo quod Deus sit,me etiam existere licet affirmare.在《通过自然之光探索真理》一文中,笛卡尔又把“我思,因此我存在”与“我怀疑,因此我存在”等同起来③cf.AT X,p.523:dubito,ergo sum,vel,quod idem est:cogito,ergo sum.(“我怀疑,因此我存在”,或者,相同的表述:“我思,因此我存在”)Traduction française,cf.Œuvres philosophiques,éd.de F.Alquié,t.II,pp.1135-1136)。,这样一来,把上述几个表达式结合起来,就能推论出笛卡尔本人并没有明确表达过的另一个表达式,即“我怀疑,因此上帝存在”。《方法论》中的一个文本完全支持这一推论:“通过反思我怀疑的事实,因此,我的存在不是完全完满的。”④Discours de laméthode,texte et commentaire par E.Gilson,Vrin,19251,19876,p.33.ll.25-27:faisant réflexion sur ce que je doutois,et que par conséquentmonêtre n’étoit pas tout parfait.对此吉尔森就明确总结道:“《方法论》的文本因此看起来朴实地观察到(constater simplement),通过自它们出发着手进行一种演绎——其表达式可以为:‘我怀疑,因此上帝存在’——这些命题[本段文本中所述表达式]是相互牵连的。”⑤Étienne Gilson,Descartes.Discours de laméthode,texte et commentaire par E.Gilson,p.315.由此引出一个大的问题:如果说在Cogito(我思)[dubito(我怀疑)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之中我们的思维直接智识的是我们的实存(作为思维的实存),而不是上帝的实存的话,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通过反思的方式“间接地”智识到后者呢?或者说对于后者的知觉是一种反思呢?古耶通过区分上帝观念(l’idée de Dieu)与对于上帝观念的意识(la conscience de l’idée de Dieu)巧妙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上帝观念铭刻在我们思维实体之中;笛卡尔肯定其优先性的这种‘无限知觉’来自存在和可认识者(l’connaissanble)的次序,而非来自已知者(le connu)的次序;其优先性表示,它是已知者层面上任何‘有限知觉’的条件。换言之,关于无限的非当下意识到的‘知觉’使关于‘有限’的当下意识到的‘知觉’成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在一种反思——在使一种关于有限的‘知觉’成为当下意识到的过程中发现了它——之际,关于无限的‘知觉’使自身成为当下意识的。”①Gouhier,La pensée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1969,pp.190-191.古耶先生的这一说法其实在笛卡尔本人的表述中可以找到依据,譬如他对观念一词所下的定义:“Ideae nomine intelligo cujuslibet cogitationis formam illam,per cujus immediatam perceptionem ipsius ejusdem cogitationis conscius sum(用观念这一名称,我想指的是对于不管哪种思维活动而言的这种形式,通过对该形式的直接知觉,我对这同一种思维活动就有了意识)”。Exposégéométrique,AT VII,p.160,ll.14-16:Traduction française,cf.AT IX,p.124.需要指出的是,法译文用“connaissance”(认识)来翻译“conscius”(意识到)一词。中译文参见《第一哲学沉思集》,第160页。由此可见,对于观念的直接知觉或理智直观(智识)是一回事,对于该观念的意识又是另一回事。简言之,虽然我们对于上帝观念的意识是通过一种反思活动得到的,但上帝观念本身则只能是一种直接知觉或理智直观(智识)形式,而不会是一种反思。②吉尔森也支持上帝观念理智直观说,反对上帝观念反思说,不过他认为这是同一种直观:“一边通过怀疑本身(思维在其中领会其实存)发现完满观念——它暗含上帝的实存,思维在单一的直观中发现这种双重的实存。”(Gilson,Descartes.Discours de laméthode,texte et commentaire par E.Gilson,p.315.)同一种直观,两种并存的实存,这种观点非常有意思,不过他似乎忽略了反思活动在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故本文更愿意采纳上述古耶的观点。
其四,对缺乏的这种追求迫使我们的精神并不停留在“最大的可想象的东西”之上,而是在对于有限知觉的当下性意识同时,形成一种对于“不可想象之物”的直接领会(即上帝观念)的意识,以便通过上帝观念反过来(在逻辑上实际上是在先地)保存有限实存物的实存。正是通过这种反思,我们清楚地看到,我们的精神不但受到缺乏的诱惑,而且还受制于上帝观念的调节③如果只受到缺乏的诱惑,而没有上帝观念的调节,按照精神精神分析的理论,那就是自恋型的毁灭。;而恰恰由于这种调节,我们的精神活动才表现为既有限制又有欲求,既有对抗又有协同,才表现为一种复杂且丰富多彩的思维活动。简言之,上帝观念意味着调节,暗含着一种运作机制,所以我们说,上帝观念,而非缺乏,才是我们人类思维活动的真正的发条。古耶形象地总结道:“只有通过在去思者之上实施一种诱惑,或者更为确切地说,通过从去思者的存在本身出发形成一种对于去思者对之具有观念的那种东西之欲望,无限观念才能是我们之中的动力性生成点(principemoteur④我们主张称“上帝观念”为“动力性生成点”(principemoteur),以区分一般所说的上帝是“动力因”(cause efficiente)这种表达形式。另一考虑就是,我们可以把原因的角色赋予缺乏。)。”⑤Gouhier,La penséemétaphysique de Descartes,1969,p.197.
上述这样的阐释,在下面两个问题上会带来一些理论的困难:
(一)用基于缺乏之上的动力论来解释上帝观念的发生,我们不难看到,上帝观念的这种动力性只是一种功能,但问题在于,这很容易导致进一步的拷问——上帝观念的提出,是否也是功能性的,或者说是一种权宜之计?这同样会带来另一个更为基本的问题:笛卡尔提出上帝观念,其真正目的是不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实存呢?对于笛卡尔而言,上帝是一般的“实在论”意义上的,还是另一种“实在论”意义上的,譬如“关系实在论”或“功能实在论”等?至少有一个地方可以说明笛卡尔本人似乎也认可这种另类动力性上帝观念论,譬如他反对伽桑狄和那位匿名捍卫者(l’Hyperaspistes)不顾上帝观念来谈论“增长”问题。对此,古耶这样总结道:“伽桑狄和那位匿名捍卫者并没有援引思维活动的这种动力论[就是上述动力论]来解释上帝观念的发生,相反,倒是这一观念对于思维活动而言的天生性解释了动力论”①cf.Ibid.,我们都知道,后一种动力论就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动力论,它把上帝视为动力因。如果我们认可上面这种功能性的动力性上帝观念,那么,笛卡尔本人又是如何在动力因上帝说与功能性上帝观念论之间做出调整的呢?
(二)接纳精神分析的缺乏理论,会带来一种几乎是毁灭性的结果。当拉康说缺乏是一种比存在更基本的东西时(如他认为,古典知识理论讨论的是存在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弗洛伊德的学说则探讨了存在与缺乏的关系,而且,只有从存在与缺乏的关系角度出发,或者说,只有从缺乏的角度出发,才能看清楚存在的真面目,因为“存在是作为缺乏的一种功能而开始存在的”②参见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第219页。),他显然已经远离了笛卡尔的存在理论。对此,我们只想说,引入精神分析的缺乏理论,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即,趁着上述那种反思开启“缝隙”之际,我们功能性地引入缺乏理论,来完成上帝观念动力性运行机制的构建。
(责任编辑:韦海波)
B94
A
2095-0047(2015)01-0053-21
黄作,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