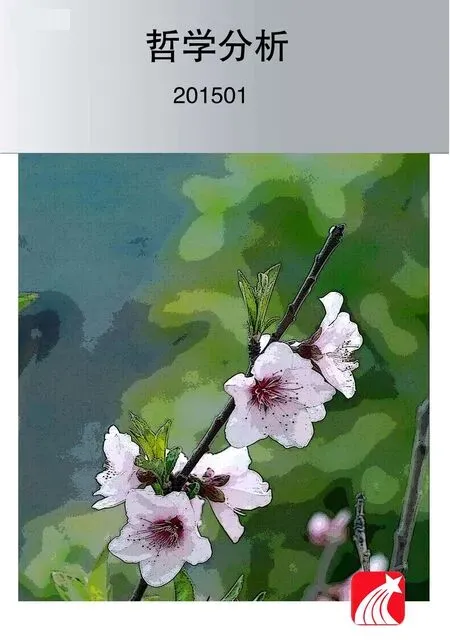论儒家传统幸福观的三个维度
王成峰
论儒家传统幸福观的三个维度
王成峰
幸福总是建立在“是”的基础上的,人们总是从他的生存状态出发得到与之相应的幸福观,因此必须立足中国人的生存状态考察幸福问题。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幸福观是一种圆满的幸福观,包括个人、家庭、国家三个维度,即注重内外兼蓄的个人修养、讲求家庭和睦的人伦秩序、倡导国泰民安的天下观念。这种“个人—家庭—国家”的幸福观不仅使得幸福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达到了统一,而且使得私人善与公共善之间实现了统一,更是一种“爱己—爱人—利天下”观念的有机结合。
幸福观;儒家;伦理思想
在现代中国社会语境中,幸福成了一个越来越流行的词语,而且幸福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幸”、“福”并用的情况很少见,而且所谓的“幸福”也和现代社会中讲的幸福有很大不同。古籍中出现的“幸福”多是祈望得福的意思——比如,《新唐书·李蔚等传赞》:“至宪宗世,遂迎佛骨於凤翔,内之宫中。韩愈指言其弊,帝怒,窜愈濒死,宪亦弗获天年。幸福而祸,无亦左乎”。又如,魏源《默觚下·治篇》:“不幸福,斯无祸;不患得,斯无失。”而在现代日常语言中,幸福则意味着人生的某种状态,是对“人应该如何生活”追问的结果。这其实是延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维,他将幸福当作人生的终极目的——“把自身当作目的而从未当作手段被选择”①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页。,于是“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变成了“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如果我们承认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将幸福当作人生的终极追求,那么幸福无疑也是中国传统伦理所关注的,但是中国传统伦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围绕“人应该如何生活”展开的,所以讨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幸福问题在本质上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对人应有的生存状态的回答,而儒家传统伦理对中国人应有的生存状态的回答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而且也的确对中国人的生活产生了最具实质性的影响。
一、幸福作为“是”的观念
亚里士多德只是将人生的最终目的规定是“幸福”,而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幸福具体的是指什么或者说我们如何得到幸福。这并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就像康德所说的,“幸福的概念是如此模糊,以致虽然人人都在想得到它,但是,却谁也不能对自己所决意追求或选择的东西,说得清楚明白、条理一贯”①转引自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66页。。
如果说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话,那么在一千个人那里就可能有一千种幸福观。纵观整个西方哲学史,我们会发现西方哲学家们对幸福的回答是各种各样的,每一种幸福观都与这些哲学家们所持有的世界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凡物在世皆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只有这些功能得到实现才算是善的,所以他持一种功能幸福论的观点,而且他认为理性是人特有的功能,所以从事理智活动的哲学家才可能是最幸福的人;而对于基督徒来说上帝才是一切,所以幸福就是要爱上帝,他们持一种注重来世的幸福观;经验论者重视感官世界,所以强调兼有情欲快乐的幸福观,而唯理论者则强调靠理性引导性情获得幸福;功利主义者则认为人生就是趋利避苦的,所以他们把如何实现一个人的最大快乐当作是幸福。
由此可见,关于幸福的内涵在西方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并没有达成一致,唯一可以算得上一致的地方的就是“幸福”作为人生最终追求的指称。根本上说,幸福就是一种“是”的观念,人们总是根据自己眼中的世界来构建他们的幸福观。一般的思路是,由某种关于世界的观念推导出某种重要的价值观念,而追求到这种价值就意味着获得幸福。有人认为快乐是重要的,幸福就意味着千方百计得到快乐;而有人认为德性才是重要的,所以幸福就是培养自身的德性。对幸福是什么和怎样得到幸福的追问就变成了这种重要的价值是什么以及如何达到这种价值。所有这些问题,就它们的提出而言具有一般性,就它们的回答而言却具有特殊性,但根本上还是“人应该如何生活”的问题。“什么是幸福”就是一个既有一般性又有特殊性的问题,一般性是指各种幸福观念都会牵涉到的关于幸福的构架,即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问题;而特殊性则是指和不同社会文化相联系的主观的或客观的幸福具体是什么样的。
关于幸福的一般性问题——幸福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在这里我不想做更多的说明,大致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幸福既有客观性又有主观性的观点。在这里我想再次强调——就像上文一直想要说明的——幸福是个生活问题而不是个概念问题,所谓回到西方幸福问题的源头,指的也是如此。幸福或许和德性、快乐有关系,但是并不是一种本质上的联系,快乐只可以说是幸福的伴随状态。而那种一谈到幸福就要联系到快乐和德性来谈的做法,其实是对西方思维的摹拟,是将幸福本质化的表现。这种做法不仅背离了幸福问题的源头指向,而且也远离了中国人的生活。本文更想讨论的是具体的幸福,特别是中国人认为的幸福是什么样的。而这个问题必须从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去揭示,我们必须明白中国人之“是”,才能知道我们所“应是”,这与中国社会文化传统相联系,因此考察中国传统伦理语境中关于幸福的讨论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因为儒家传统伦理在中国人传统生活中占据主流而且影响最深远,所以儒家对幸福的认识可以算作是中国人传统幸福观最实际的说明。儒家同一时代的不同思想家以及不同的时代思想家关于“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回答不尽然相同,但我认为这些不同的回答是他们根据对时代的观察以及自身关于社会构建的理想提出来的“补偏救弊的说话”(《传习录》),没有绝对正确或错误之分,只存在以偏概全之嫌,甚至在这些思想家那里也是心知肚明的——“此是古人不得已”(《传习录》)。因此本文将采取一种综合的方法,尝试归纳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社会主流的幸福观是什么样的。
二、注重内外兼蓄的个人修养
幸福说到底还是个人的事情,幸福与否最终有赖于当事人的感受,但是当事人感觉自己是否幸福并不是主观任意的结果,而是和他接受的观念有关。总体上而言,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伦理在个人幸福上既注重内在德性,又注重外在事功,坚持一种内外兼蓄、义利统一的幸福观。如果非要说德性与功利哪个更重要,总体而言,德性更具优先性。
中国传统哲学是一种真正的智慧之学,强调生命的自觉,以成圣贤为根本的追求,注重在日用常行中的个人修养。不论是儒家伦理、道家伦理还是佛教伦理都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对内在精神世界的关注,幸福在很大程度上也和个体的德性修养相关联。儒家伦理是一种真正的德性论,孔孟的学说都极力强调仁义道德,认为个人修养与其幸福关系紧密,讲求“修己安人”,看重精神内在的愉悦。孔子讲:“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种“孔颜乐处”成为后世儒家所努力追求的境界。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孟子·尽心上》)这也是对幸福内在性的强调。不仅是儒家,道家伦理也强调淡泊名利、崇尚自然,要“物物而不物于物”(《庄子·山木》),返璞归真,在对生命内在的关注中达到真正的自由解脱,而做到这样又和个人的修养相关。佛教伦理虽然关注的是来世,但十分强调现世的修行,通过“空”观否定万法实有,破除我执,最终实现生命的涅槃。
儒家传统伦理虽然强调内在的幸福,但也没有否认幸福的外在条件。而幸福首要的外部条件就是存身,如果没有一个“我”,也就无所谓“我”的幸福。《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子也说“父母唯其疾之忧”,这都是强调“存身”或者说健康地活着的重要。道家也重视存己存身,并发展出一套养生理论。事实上,不管是儒家的修养、道教的修炼,还是佛教的修行,在这背后都暗含了对德福一致的承认,内在德性的好往往有助于外在条件的改善,从而在更完满的程度上得到幸福。在传统观念中幸福本就具有完满性,在最早出现幸福观念的《尚书·洪范》中就有“五福”、“六极”之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幸福不仅是好的德性,而且和寿命、贫富、健康,生死联系在一起,贫穷、疾病、凶祸都是不幸福的表现。儒家思想本就含有强烈的入世情怀,也不可能不关注现实的功利,孔子就讲“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太平盛世,贫困本身就是一件令人耻辱的事情,又何谈幸福?道家和佛教思想,虽然一个强调出世,一个关注来世,但是老子推崇的“小国寡民”的社会,佛教讲的“西方乐土”都是讲求一定外部性的。另外,“义利之辨”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问题之一,“义”关注的是幸福的内部性,“利”则关注幸福的外部性。虽然“重义轻利”、“贵义贱利”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主流,但是每当道义之论在社会发展到极端的时候,总会有强调事功思想的出现,努力促使义利之间达到均衡。幸福的外部性问题从来都没有被否定掉——荀子在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他提出了“裕民养欲”的说法。汉代董仲舒也讲“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及至宋代,李觏、王安石、叶适、陈亮更是掀起一时的功利主义思潮,王安石讲“理财乃所谓义”,叶适也说“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及至明末清初,王夫之明确地提出了义利均衡的幸福观①贺汉魂:《论王船山义利均衡的幸福观》,载《船山学刊》,2001年第2期。。
三、讲求家庭和睦的人伦秩序
幸福虽然是个人的事情,但它绝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就像霍尔巴赫所说的“光是自己一个人,是谁也不可能成为幸福的”②冯俊科:《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2页。。我们既不可能在自身之外寻得幸福,也同样不可能独自一个人获得幸福。我们谈的是现实的幸福问题,也是现实的人生关怀,而现实的人生绝不是独自一个人的问题。我们总是处在某种家庭的或社会的关系当中,在这种生存状态中谈论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总是和他人的幸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亚里士多德在谈幸福时,就很注重个人幸福与他人的关系性,特别强调个人幸福与友谊的关系,他说:“朋友能提供你自己所无法提供者,因为他是另一个你(he is another yourself)。”“在给幸福的人以各种美好的东西时,不使他获得朋友似乎是荒唐的,因为拥有朋友是最大的外在的善(the greatest external good)。”③转引自杨国荣:《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6页。
对中国人来说,这种最大的外在的善无疑是家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扩大了的家庭。因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人际关系的“天然”形式④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血缘宗亲是我们必居其中的生存状态,我们总是在宗亲关系中谈论幸福,而且我们的个人修养也总是立足于这种家庭人伦关系之中的。在传统家庭中,没有一个绝对的“我”的存在,“我”总是表现在与之相应的人伦秩序当中,总是通过同时处在这种人伦秩序中的他人来表现“我”自己,因而“我”的幸福总是和这个家庭相关。孟子就指出了家庭对个人幸福重要,他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者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父母俱存,兄弟无故”都是令人感到快乐、幸福的事情,反之则人生幸福就不完满。
家庭的幸福最突出的表现是和睦,也即我们通常讲的家和万事兴。家庭和睦就是保持宗亲关系下的人伦关系的有序状态,传统的说法就是凡事要立足本宗,也就是孔子讲的“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论语·学而》),也就是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夫妻恩爱、和敬乡邻,就像孔子说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而在所有这些当中,对孝亲的强调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之一,孔子讲“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常言也道“百善孝为先”,“孝”作为传统伦理的三大德目(孝、忠、节)之一被纳入刑律而法制化。因而,孝亲也是家庭和睦的基石和起点,兄弟友爱、夫妻恩爱都在此基础上才成为可能,并且进一步促进了家庭关系的和谐,这些都是家庭幸福重要条件。
如果说个人修养讲的是“修己安人”,是爱己,那么立足家庭谈幸福就过渡到了“推己及人”,是爱人。但是这种爱人不是无条件的,在宗法制度下,中国传统伦理突出的是一种“亲亲有术,尊贤有等”的有差等的爱。这种“推己及人”的爱,首先是从爱自己父母开始的,然后扩展到宗族、乡邻中的人,而当这种爱超出宗亲关系之后,就有了天下国家的关怀。
四、倡导国泰民安的天下关怀
霍尔巴赫说:“社会对于人的幸福是有益的和必需的。”①转引自冯俊科:《西方幸福论:从梭伦到费尔巴哈》,第378页。个人不仅处在家庭人伦关系当中,而且处在社会关系当中,社会为个人人生目的实现提供着各种各样的手段,因此个人的幸福和整个社会的状况都有着紧密的关系。儒家伦理思想十分强调个人幸福与天下国家的紧密联系,而且即使是其他的伦理思想也不会否认天下太平对个人幸福的重要性。
高度分散的自然经济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并存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它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互相沟通,形成了中国传统伦理独特的“家—国同构”模式。“以父家长制为中心,以‘立子立嫡’为继承系统的宗法制度,即所谓‘宗统’,不仅是凝固一家一户自然经济的社会结构,而且还是维系君主‘家天下’统治系统,即‘君统’的‘天然’保障。”②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第10页。如果说“宗统”所决定的伦理要求孝亲爱家,那么“君统”所要求的无疑是忠君爱国,“忠”也是被纳入刑律而法制化的三大德目之一。当对“忠”的理解超出仅只是维护君主“家天下”的统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背后还有“利天下”的要求,而“利天下”的背后是对个体生存的深切关怀。
国家安定与兴旺不仅是个人幸福重要的外部条件,而且也是个人获得完满幸福不可或缺的心理诉求,中国传统伦理强调个人对天下国家的关怀。这种天下关怀与个人幸福的关系,首先是对治国者而言的。儒家的“外王”学说就是讲君主对治理好天下有很大的责任,而且所谓“忠君”也是和统治者要有天下关怀分不开的。治国者要仁政爱民,使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不受饥寒冻馁之苦。其次,天下关怀也是对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的。孟子说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大学》“三纲”、“八目”也直陈“治国”、“平天下”的要求,及至北宋张横渠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是彰显了后世儒者的理想和使命,他在《西铭》中阐发的“民胞物与”的精神饱含了儒家知识分子对生民的深刻关怀,将儒家知识分子的个人幸福同整个天下国家维系在一起。最后,天下国家关怀也和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幸福有关。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如果我们每天都面对着他人的悲苦而无能为力,我想多数人都会心有郁结的。顾炎武也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事实上来看,当天下太平的时候,我们或许未觉察到个人幸福和社会国家有什么关系,而在国家动荡的时候就会强烈地感觉到国家兴旺的重要。试想如果社会动荡不安,百姓因为战争和天灾而流离失所,又何来幸福可言?国家疲弱,饱受外敌侵侮,民族尊严扫地,又何谈个人的幸福?或许一家一人能避得一时的灾祸,但是此种幸福终也不能长久,不为圆满。纵观整个历史,我们会发现这种国家观念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都打下了深刻地烙印,尤其是在国家危难的关头,无数中华儿女会为国抛头颅、洒热血,为天下国家的危亡而舍小家为大家,在“忠”、“孝”冲突的时候,决然为国。
五、结语
由以上的说明可见,儒家伦理思想坚持了一种圆满的幸福观,我将之总结为“个人—家庭—国家”三位一体的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在个人层面上讲求内外兼蓄的个人修养,在家庭层面上讲求家庭和睦的人伦秩序,在国家层面上讲求国泰民安的天下关怀。这种幸福观不仅使得幸福在主观与客观之间达到了统一,而且使得个人善与公共善之间实现了统一,更是一种“爱己—爱人—利天下”观念的有机结合。
对家庭、社会国家向度的强调既可以算是个人幸福的外部条件,也使得个人善与公共善能更好地结合。个人的幸福不全然是自我的,而是和全部的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家庭的、社会国家的状况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个人的幸福感。因此,追求幸福不仅要利己,还要利他;不仅要有私德,而且要有公德;不仅要靠个人的努力,而且与社会国家的大环境紧密相关。不得不说的是,我们了解儒家传统伦理思想中关于幸福之“是”,最重要的不是要提供一种关于幸福的标准,而是要明白中国人的幸福是在个人、家庭、国家的场域中实现的。幸福退守到个人层面固然也可以实现——尤其是个人对家、国无力的时候,但它必定存在着向家、国扩张的诉求。
最后,我们在今天的社会谈论幸福的时候,当然要立足于我们的生存状态,而儒家传统幸福观则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我们自己,更重要的是在对这种观念的理解中寻找到“能近取譬”的幸福之路。在这个时代,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是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拜金思想弥漫,个人本位主义泛滥,很多人为了一己私利往往不择手段,以邻为壑,结果是人人自危,何以谈幸福?这就反衬出个人德性修养的重要,我们希望得到一切好,但是最重要的好是自己本身是好的,而“自己本身好”最基本的当然是“存己”,也就是人首先要活着,之所以强调活着,是因为自我伤害在今天已然成为问题;其次就是要存心养性,不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己,今天我们追求幸福应当更多关注自己的心灵。当然在这个离婚率攀升的时代,我们也要关心家庭伦理的发展,不仅是要养家,更重要的是爱家。虽然传统的“纲常”已然过时,夫妻关系成为现代家庭的核心和基石(传统家庭观念中父子关系是第一位的),但是孝亲的传统不能忘,人伦秩序不能乱。至于社会国家,这早已不是“家天下”的时代,虽然不用再“忠君”,但是热爱国家、奉公守法还是很必要的,尤其随着传统宗法制度的解体,我们与熟人社会渐行渐远,这个社会越来越是由一群孤立的个体组成,因而公共德性就愈发显得重要。只有国家富强,社会文明有序,家庭和个人才可能好。个人为社会国家奉献了,那社会国家也应该为个人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保障个人的合法利益,使长幼有所居,老能有所养,病能有所医,给个人以希望。
(责任编辑:韦海波)
B94
A
2095-0047(2015)01-0100-08
王成峰,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评《当代中国青年幸福观及其培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