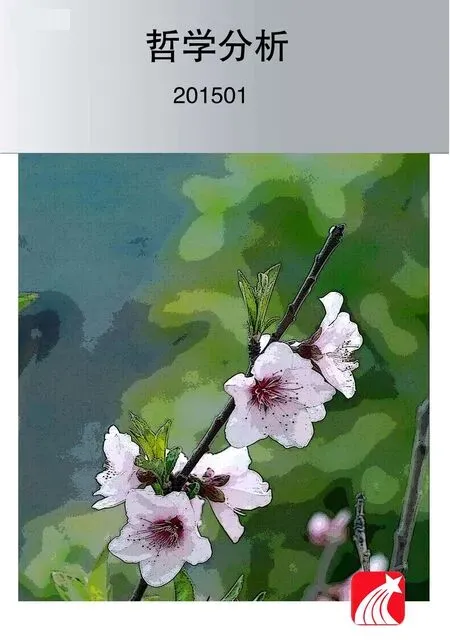志气相依与通达
——王阳明心志与气机关系略论
李洪卫
志气相依与通达
——王阳明心志与气机关系略论
李洪卫
西方哲学的身心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中是以心气关系呈现的,而心气关系在儒家则是“志”与“气”的关系。志与气的关系,由孟子较为系统提出,经王阳明充分发展与完善。阳明认为,持志即是养气,孟子的“守约”、“专心致志”说的是一个道理。持志首先要立志、定心,养气即在其中。阳明认为,立志既是涵养正气的功夫同时也抵御、辟出邪气,即克服杂念、清除习气、通理气机。阳明详细阐发了定气与定心的关系原理:他依据孟子学说用“主一”概念解释了通过持志而定心和“硬把捉此心”之间的分别,从而通过“意动气动”对“志公意私”的说法作出了准确的说明。王阳明认同程明道关于“生之谓性”的论述,认为气也是性,只要不执著一边,依良知行去即是,这样最终将性、心、气完全打通归并为一。这一论述将身心一体的哲学推向了高峰。
王阳明;持志;定气与定心;生之谓性
探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的身心关系,有一个重要的侧面就是心与气的关系。身与心的相互作用到精微处也就是心与气的关系。溯往来看,把心志与身体中的气机联系起来并产生了深入而广泛影响的是庄子和孟子,志气讨论则始于孟子。《庄子》中有:“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
(《庄子·人间世》)孟子关于“志至气次”的一段话则是后世儒家思考和践行的出发点。
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这一段话,前圣与时贤均有反复的引证,其主要意思有三:首先,心志是气之统领,志至而气次。所以在儒家看来,对心志和意识的修养是主要的方面,所谓“持其志,无暴其气”;其次,气壹也能动志,反动其心,所以还是要持其志,无暴其气,暴气也会动心移志,志壹与气壹都会牵动二者中的一方,所以最终的修养目标是“不动心”;复次,浩然之气是义气、道气,该气的根基在乎人的内心,人心之中若有不安,此气随之衰颓。自此也可看出人的心灵与身体之气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儒家才有格、致、诚、正的诸般功夫。养其内心的良知、正念、诚意等,心正、心安是气充的条件,由此修身则成为正心和养气合一的工夫,二者相资为用,以心灵修养为主。王阳明继承了原始儒家的这一基本思想,他在与其弟子交流过程中的论述大端都是从上述孟子及宋儒的思路展开的,同时在身心、心气的相互关系方面又有新的发展和更详尽的展开。
一、持志:养气与辟气
毋庸讳言,儒家中尤其是心学一系,相对比较看重养气的工夫,这一点是从孟子养浩然之气就开始了的,至宋儒在吸收佛老之学以后变得更加自觉和充分,连朱子也言“半日读书,半日静坐”,二程更是见人静坐“辄叹其善学”,象山则谓学者“常闭目亦佳”等不一而足,阳明授学初从静坐始。总之,儒家修养的学问中对静坐养气有着充分的理论和实践的储备。静坐在儒释道被理解为养心与养气并育的工夫,静坐必须调整呼吸、调理身体的形态而影响气机的运行,因此养气自然是其中的内容。当然,回过头来,儒家从开始践行静坐养气的工夫就没有将它看成是其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和归宿,这同时又构成儒家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即便是达到“尽心、知性、知天”的超迈境界,这样的个人仍然是有其先定的社会属性的,由此而与当时的道家和后来的佛家区别开来。由此,在修养的入手处(即理论的归结上)呈现为自始至终的以心为主、以正心诚意为目标的“有心”、“道心”和“大心”的境界而不是“无心”的境界。①陆九渊评《庄子》中“狎海上之鸥,游吕梁之水,可以谓之无心,不可以谓之道心”。参见《陆九渊年谱》,载陆九渊:《陆九渊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6页。尤其是儒家在着手处特别强调心志的主导性,这一特点最初就见于孟子与告子的争论之中。当弟子问到这段著名的争论时,阳明是这样解释的:
问志至气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气亦至焉’之谓,非极至次贰之谓。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无暴其气则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夹持说。”②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阳明试图在这里强调,心志与体气之间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心志所到,气也就随之而来了,并不是一个先、一个后。只要持守心志,养气也就自在其中。在这一点上,朱子没有阳明说得这么清楚、坚决,应该是他在这一点上缺乏足够体会的结果:
问“志至焉,气次焉”。曰:“志最紧,气亦不可缓。‘志至焉’,则气便在这里,是气亦至了。”
李问:“‘志至焉,气次焉’,此是说志气之大小,抑志气之先后?”曰:“也不是先后,也不是以大小,只是一个缓急底意思。志虽为至,然气亦次那志,所争亦不多。盖为告子将气忒放低说了,故说出此话。”
郑太锡问“志至焉,气次焉”。曰:“志最紧要,气亦不可缓,故曰:‘志至焉,气次焉。’‘持其志,无暴其气’,是两边做工夫。志,只是心之所向。而今欲做一件事,这便是志。持其志,便是养心,不是持志外别有个养心。”
或问:“‘志至焉,气次焉’,此是说养气次第。志是第一件,气是第二件。曰:“‘志至气次’,只是先后。志在此,气亦随之。公孙丑疑只就志理会,理会得志,气自随之,不必更问气也,故云。”③朱熹:《朱子语类》(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38-1239页。
朱子在这里向弟子作解释时,所说不尽一致,前面曾说“志至气次”不是大小、先后,而是缓急,有些教人不得要领,说先后尚可,说缓急就不是那么清楚;后面又明确说就是先后,这里的问题不是太大。阳明虽然认为,持志的同时就是养气,孟子的说法也不为错,但阳明明确的是,它们之间没有第一、第二的关系,而是一种依赖性的关系。朱子说“持其志,无暴其气”、“是两边做工夫”,这就与阳明不同了。因为阳明认为“无暴其气”,持志也在其中,这就是志与气的最紧密的依赖性和同一性。所以他认为,孟子那样说是为了补救告子的偏颇,不得已才“夹持”,把两个方面都说到。我们先来看一段孟子的原文以了解“持志”的内涵以及告子的“偏颇”所在。
公孙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曰:“若是,则夫子过孟贲远矣。”曰:“是不难,告子先我不动心。”曰:“不动心有道乎?”曰:“有。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桡,不目逃,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养勇也,曰:‘视不胜犹胜也;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孟施舍似曾子,北宫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曰:“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既曰,‘志至焉,气次焉。’又曰,持其志,无暴其气。’何也?”曰:“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孟子·公孙丑上》)
这一段也许是自《孟子》问世以来被认为最富于弹性和启迪同时又最具争议的文字之一。公孙丑请教“不动心”之道,孟子以“养勇”谓之,北宫黝之有“悍勇”可见一斑,孟施舍则以不计胜败而获勇,后者是“平心”之为,即不虑得失所以心有不惧。在孟子看来,孟施舍要胜北宫黝一筹,名之曰“守约”;但进一步,孟施舍“守约”还是“守气”,则又不如曾子的“守约”,曾子“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按照朱子的解释,曾子守约是“反身循理”,这是有道理的,也大概符合孟子的原意,但是恐怕还不完备。朱子说:“言孟施舍虽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气,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动心,其原盖出于此”。“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故二子之与曾子、子夏,虽非等伦,然论其气象,则各有所似。”“养气,则有以配夫道义,而于天下之事无所惧,此其所以当大任而不动心也。告子之学,与此正相反。其不动心,殆亦冥然无觉,悍然不顾而已尔。”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0-231页。考究孟子关于“不动心”、“养勇”、“养气”、“守约”与“持志”之间的相互关联,可以判断其“持志”既有“反身循理”的意思,同时又有心意专一不动的诉求,以达到心、理合二为一的效果,可以名之曰“持志”。孟子并没有停留于“守约”的概念上,而是随之提出了“持志”。而对于孟子的持志,我们还可以理解为“专心致志”一意,这一点可以参考他的另一段话:“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奕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奕,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孟子·告子上》)守约可以理解为“守义”、“主一”,而这个“一”既可以理解为“理”,同时也可以解为“心”,“持志”也需要按此理解才可以周全孟子的思想内涵。那么,孟子为什么还要接着谈“志至气次”的问题呢?盖源于告子的关于几个“不得”与“不求”的说法。孟子认为,这是他与告子比较重要的乃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定心要求之于心,这正是儒学的特色,否则就流入其他的学派了。孟子为了强调心志的重要性,才说出“志至气次”的话来,这也正是阳明的理解。阳明认为,孟子在这里论气是不得已,本来“持志”即气在其中了,不需要再说气了,说气只是为了校正告子不主心志的思想。可以说,阳明是志气同一论者,他不是不论气,而是认为持志已经内在地涵养了气机,至少在这里可以不必再提及此。这也成为阳明的一个基本思路,从早期教人静坐,到后期只提撕“致良知”一句大体都是贯彻这个思路。阳明晚期在其境界上可能已超出一部分儒家所认为的“法度”——譬如“四句教法”。但是“四句教法”第一句虽然讲“无善无恶”,但终究是境界之论,主要不是方法之论,因为这种“直下心源”的方式在日常并不得见,而他在方法上,确是始终坚持传统的儒家的“持志”、“正心”等可以把捉的方式。阳明把“立志”作为他教人入门乃至成就圣贤的终南捷径,始终强调如一。因为持志首先要立志,立志然后才能有持志之功,这是他强调志气一如的观念之表征。
在阳明,立志、持志、定心首先是调理气机的一种手段和方法:
崇一问:“寻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无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气机,元无一息之停;然有个主宰,故不先不后,不急不缓,虽千变万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时,与天运一般不息,虽酬酢万变,常是从容自在,所谓‘天君泰然,百体从令’,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②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30页。
问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①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1页。
阳明的讨论涉及中国哲学的两个最基本范畴(“意”与“志”)的厘定,这里只进行最简单的分析。在中国思想中,意念、思想或思虑也属于“心”的范畴,但是它与“志”有着明显的区别,按照张载的说法就是“意私而志公”。孔子要人立志、自己立志,但同时要去除“意、必、固、我”。张载之解是:“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则与天地为不相似。天理一贯,则无意、必、固、我之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诚也;四者尽去,则直养而无害矣。”“道以德者,运于物外,使自化也。故谕人者,先其意而孙其志可也。盖志意两言,则志公而意私尔。”②张载:《正蒙·中正篇第八》,载《张载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8、32页。朱子解“意”字为“私意”(《论语集注·子罕》)③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09页。而许慎的《说文解字》把“志”和“意”互解,以意解志,以志解意。④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17页。可见,“志”、“意”大体都可以解释为“心之所之”,但“所之”的对象是不同的,出发点或动机也是不同的。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孟子的说法:“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上》)如此,“志”的对象如张载所言就是确定的公义,而“意”则既可能是私意或私欲,也可能是闲思杂虑,这就是普通的意念和思想,就是所谓的“寻常意思”,就是动心起念、思虑纷飞。既然“志”能动气,那么“意”也能动气,它们同是心之所发。意念的形成实际上就是所谓的个人的一私的“意向性”的出现,就是孟子的“放心”,即心的放逸逐物,同时还是人体的血气的奔涌冲动,也就是没有主宰,“这气奔放,如何不忙”。如果它很猛烈的话,则如老子所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因此要“虚其心,实其腹”。孟子是要持志以“求放心”,老子是直接地虚化个人的心智和心志,其原因皆在于心意的冲动导致了气血的狂乱和不规则的运行,使人的行为失去控制,身体也可能受到伤害。王阳明上述这两段话正是要阐明这个道理,当然也就是孟子的持志定气养气的路径。在阳明看来,自然界同时也包括人体的气机的流行,气机周而复始,没有停息,寻常思虑不断,身心疲惫,这些都是源于个人的内心缺少一个定向,缺少一个主宰,缺少气流运行的指挥棒和中枢。有事固然心有负荷同时身体的气机运动剧烈,即便无事的时候,意念纷纷不断,其实在身体内里也是一个气机的不协调、不规则的运行状态,如阳明在肯定黄勉之时所说:“‘过思亦是暴气’,此语说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却是因噎而废食者也。来书谓‘思而外于良知,乃谓之过,若念念在良知上体认,即终日终夜以思,亦不为过。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虑’,此语甚得鄙意。”①王守仁:《与黄勉之》,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96页。过思正是不能持其志却暴其气了。而调理控制气机狂放的方法就是“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念念在良知上,终日终夜定在一个思想上,或者说,不外于一种思想,也就没有别的闲思杂虑了,这也就是持志主一了,这种方式在阳明看来也是养气。其成果之一就是精气的凝结、聚集如道家的所谓结“圣胎”。这很显然是一种养心养气合一的方式,最后到达美大圣神的境地——正如阳明所言,“持其志则养气在其中”。只有持志才不会造成义袭而取,阳明谓学者曰:“为学须得个头脑工夫,方有着落。纵未能无间,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虽从事于学,只做个义袭而取,只是行不着,习不察,非大本达道也。”②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30页。所谓“义袭”而取,是孟子的话。公孙丑“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子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集义所得,即通过持志得到的,而不是偶尔道义降临获得的,偶获的浩然之气不能时时保存,行为也不能时时符合道义,当个人心有不安的时候,这气也就衰颓了。在阳明看来,就像舟车航行需要有一个舵手时时操纵把持着航向一样,浩然正气也时时伴随,这就是立志与守志,也就是善养浩然之气。志与气是相互依存的,以持志为养气的头脑,最终才能达到本体和大道。
在阳明看来,立志持志不仅是养气的功夫,同时还是抵御邪气、克制邪气的法门。从本源上说,气无邪正,全在于人的心思之过与不及。但是由于先天的气稟不同、后天的社会环境不同,人的思想、心理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杂念,这也就是儒家常说的“习气”。习气有各种各样,但都是妨碍人的身心健康发展的东西。阳明认为,通过立志立心可以克制杂念和习气。志立则理明,理明则心定,心定则气和,其他的邪心杂念也就自行消失了:
夫恶念者,习气也;善念者,本性也;本性为习气所汩者,由于志之不立也。故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久则志亦渐立。志立而习气渐消。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此守仁迩来所新得者,愿毋轻掷。③王守仁:《与克彰太叔》,载《王阳明全集》(下),第983页。
夫志,气之帅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浚则流息,根不植则木枯,命不续则人死,志不立则气昏。是以君子之学,无时无处而不以立志为事。正目而视之,无他见也;倾耳而听之,无他闻也。如猫捕鼠,如鸡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结,而不复知有其他,然后此志常立,神气精明,义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觉,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责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听一毫客气之动,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或怠心生,责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责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责此志,即不懆;妒心生,责此志,即不妒;忿心生,责此志,即不忿;贪心生,责此志,即不贪;傲心生,责此志,即不傲;吝心生,责此志,即不吝。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故责志之功,其于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阳一出,而魍魉潜消也。①王守仁:《示弟立志说》,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60页。
以上论述已足见阳明对立志正心之功用的重视。如前所引,从其根本角度看,气也只是一气,所谓私欲、习气、客气等诸般,不过是心念的问题,心意昏昧不明或失之偏颇,则导致身体中气的运行偏差,气血奔涌,或喜或怒,表现为行为的乖戾不端正,身体气血运行的不协调。所以,“凡学者为习所移,气所胜,则惟务痛惩其志”“只责此志不立,即客气便消除。”正心正念而有正气,邪心杂念而有邪气,无志则气质昏昧,杂念丛生,所以时刻要立志责志。立志与责志只是持志的两个方面或两个阶段而已,立志还要守志即持志,而持志就是每遇事情就反复在自己的“志向”上琢磨,从而坚定意志和信念,不偏离方向。在阳明看来,能持志,则存心的功夫也就在其中了。
二、定气与定心:动静一如与心、性、气的贯通
孟子在阐述心志和体气的关系时曾经指出,志壹可以动气,气壹也可以动志。但是孟子所讲的志壹之动气不是后人说的“不动气”或不动心,而是持志、集义、养气的意思,因此志壹动气是集气养身,而气壹动志则是动心移志,是气的结集使心志动摇转移——显然这不是学者所期待的结果。结气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蹶者趋者,“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这是孟子概括的;一种是阳明根据孟子对告子所做的概括,阳明认为后者是“硬把捉着此心”,是人为的控制,实际上是制气而不是定心:
尚谦问孟子之“不动心”与告子异。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动;孟子欲是集义到自然不动。”又曰:“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
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①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4页。
“硬把捉着此心”实际上是定气、憋气而不是定心,是人为的不动,不是集义到“自然不动”,不是由心不动而过渡到气不动,不是以心为主导,而是气壹动志,没有将心志本体发明出来,只是在表层上定气,是心气关系的颠倒扭曲。②关于孟子与告子之争,是儒学史上的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宋儒如大程子明道在这个问题上与孟子当时的看法已经有所不同——尤其是对于告子的认识。下面我们在讨论“生之为性”时会进一步涉及这一问题。阳明在这里肯定孟子,主要在于强调:一要持志、主心、集义,这是儒家的最根本的看法和不二法门,二则是要突出心灵本体,以使其自然呈现,最后如如不动。他强调心灵本体的性与天道的特征,而否定意、必、固、我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从这个角度上说,阳明在这里“对告子的批评”是成立的,虽然他凭依的是孟子的文本。也许更应当从如下角度来理解阳明的意见,即他这里的批评主要是借解说原始儒家来对治当下学者可能的流弊,而在讨论性与气的关系时,他可能又超越了孟子和告子之间争论。这种状态在心理上表现为意、必、固、我,偏执于枝节问题的一边。下面一段对话表明了阳明的看法: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晳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者,故夫子亦皆许之。”③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4页。
“吾与点也”一章,历来是儒门之中理学与心学争论的焦点之一。朱子虽然在《集注》中也有称道,但保留的意味更重,阳明却对此段常有深得我心的感慨,其晚年境界更得与此沟通。这一段话,阳明主要是提撕学者不要执著于一边,以免陷于个人私意。陷于个人私意也会导致心意的凝结,从而造成体气不能畅通无碍,不能上下与天地同流,对这一点的强调与“持志”的工夫并不冲突。阳明对此也有说法:“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④同上书,第11页。“侃问:‘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语,管闲事?’先生曰:‘初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向。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⑤同上书,第26页。
持志与主一是同一的工夫,但持志不是死守着,主一也不是定在一事物上,那样就又诱发了感官欲望的狂热追求,没有达到境界,在过程中、在工夫上就又犯病了,所以孟子说,又要“勿忘勿助”。这些在不同层面上的说法,放到一起,难免有令人混淆、产生矛盾之感——既要持志集义,又要“勿忘勿助”,不执著于一边。实际上,阳明在这一点上是十分清楚的:持志主一,是专主于一个天理,世情万变在天理上去判明,依循于一个天理一切自明;意、必、固、我则是离开天理专主于个人的一点具体的私意。这两者应当是截然分开的,着了个人的一点私意,便会产生许多动气处。而如我们前面所说,“意私而志公”,循天理便不会动气。这是孟子的思想,也是阳明所反复强调的:
侃去花间草,因曰:“天地间何善难培,恶难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间,曰:“此等看善恶,皆从躯壳起念,便会错。”侃未达。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子欲观花,则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欲用草时,复以草为善矣。此等善恶,皆由汝心好恶所生,故知是错。”曰:“然则无善无恶乎?”曰:“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是谓至善。”曰:“佛氏亦无善无恶,何以异?”曰:“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不动于气。然遵王之道,会其有极,便自一循天理,便有个裁成辅相。”曰:“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见。草若有碍,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恶?”曰:“不作好恶,非是全无好恶,却是无知觉的人。谓之不作者,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恶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循于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心体便有贻累,便有许多动气处。”①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29-30页。
学者一般熟知阳明的“有善有恶意之动”,这里却说“有善有恶气之动”,这实际符合阳明思想的本旨。因为“意私志公”,所以循理持志是集义养气的功夫,私意萌动则是动心动气之所为。“意之动”和“气之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从而也就可以自然推出:无善无恶是不动于意,不动于气,但这种不动是自然不动,是循理持志之后的成果,不是强自把捉自己的思想强制不动。着一分私意就是动气,就是恶。人的良知本心原无善恶是非,私意动则气动,则善恶出现,这是个人的心之所为,是人为的后果,是心体不能廓然大公,被狭隘的私意笼罩束缚的结果。那么,人是不是就不能动心动气,或者说,得道之人就会不动心不动气呢?在阳明看来并非如此。人会动气动心,但不要着了意思,执著于它就会有错:
问有所忿懥一条。先生曰:“忿懥几件,人心怎能无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些意思,便怒得过当,非廓然大公之体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于凡忿懥等件,只是个物来顺应,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体廓然大公,得其本体之正了。且如出外见人相斗,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虽怒,此心廓然,不曾动些子气。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才是正。”①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99页。
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自家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②同上书,第19页。虽怒却不着一分意思,就不会产生过与不及的问题,就不会过当,自己的心仍然是气机畅通无碍,自然而然的,就不会为它所牵引束缚,这就达到了无善无恶的境界了。这一点在阳明主要是从境界上说的,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从工夫上说的,二者之汇合处是循理而不动心。循理是工夫,不动心是境界,不动心也就不动气。在这里依然可以看出,阳明在本质上已经是主张心与气为一的。但是,这个一是在境界上、在本体上说的,在工夫层面上,心与气不能达到一如时,要以心为主,因为心是主宰,气的动静出入来源于心的动静出入。如果达到本体境界,则没有动静出入之分了,持志集义养气等也就不必说了。这时候,主宰就是人的道德本心本体,在这种状态下,人已经纯是天理,再无私欲。心气一如,动静一如,成为一种境界目标,存心养气也就只是成了修养的一个阶段,而不是最终的目标和成就了。心与气的起伏动静循理而行,没有大的波折,随过随化,动静也就一如了。阳明说:“若论本体,元是无出入的。若论出入,则其思虑运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之有?既无所出,何人之有?程子所谓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虽终日应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里。若出天理,斯谓之放,斯谓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动静,动静无端,岂有乡邪?”③同上书,第18页。其实,这里阐发的是心的平和导致气的平和,导致动与静没有分别,这些都是程颢所说的“定”。
说到“定”还有一个问题,即“守静”。人的身心宁静可能有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是真正的循理之后的不动心、不动气,一种是静坐之下的气宁静但心不宁静的情形,是身心、心气相离的状态。后者容易被人错会为这就是“未发之中”的气象,它只是气定而心不定,还容易导致个人对“宁静”的喜好,喜静厌动。但是,由于缺乏定心的工夫,在社会中遇到事情依然不能依循天理正当地处置,还是会出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表面上“喜怒哀乐未发”,但不能“发而皆中节”,因而还要做循理持志主一的功夫,最终达到动静一如的境界。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喜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①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3-14页。
循理自然是心循理,而不是气循理,是气由心动。心循理则气自然循理并条顺,条顺之后则心气性就贯通为一,心理与体气互相融合,道德本体主宰人的身躯。这个时候从个人的身体的气机运行的角度看,体气是循理而行,不会产生凝结滞障使心体反受其乱的问题。大程子明道有云:“壹与一字同。一动气则动志,一动志则动气,为养气者而言也。若成德者,志已坚定,则气不能动志。”②程颢、程颐:《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页。明道讲的是“成德者”,阳明讲的是持志循理的成功者,其说一也。从批评对象看,明道讲的对应者是“养气者”,阳明说的是“养生者”,都是针对有的儒家学者不从心体上体认用功而言的。从心体上用功体认就做的是以心使气、体认天理的功夫。由心理而入,最后达到心气协调如一、动静常静常定的状态: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气言。理者气之条理,气者理之运用;无条理则不能运用,无运用则亦无以见其所谓条理者也。精则精,精则明,精则一,精则神,精则诚;一则精,一则明,一则神,一则诚:原非有二事也。后世儒者之说与养生之说各滞于一偏,是以不相为用。③王守仁:《答陆原静书》,载《王阳明全集》(上),第62页。
“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④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6页。
宋儒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的区分,气质之性夹杂着人生而有的先天杂质或偏颇,所以与天地之性是二分的。那么,到动静一如这个时候、这种状态下又究竟如何呢?阳明认为,从本源上看,性与气从本身来说也是一,两者并无二致。他还认为,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上看,人性本善之端绪也要从生命的气质层面来考察,无气则性无从体认,而从本质层面,性气本就不可分,性就是气,气就是性。这个观点虽然不能说是振聋发聩,但也是令人叹异的,在此之前,对此亮明态度的只有大程子明道。下面我们分别来看这两个人的论述:
王阳明说:“‘生之为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需从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①王守仁:《启问道通书》,载《王阳明全集》(上),第61页。
程明道说:“‘生之为性’,性即气,气即性,生之谓也。人生气禀,理有善恶,然不是性中元有此两物相对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恶,是气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亦不可不谓之性也。盖‘生之为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所谓‘继之者善’也者,犹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终无所污,此何凡人力之为也?有流而未远,固已渐浊;有出而甚远,方有所浊。有浊之多者,有浊之少者。清浊虽不同然不可以浊者不为水也。如此,则人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则疾清,用力缓怠则迟清,及其清也,则只是元初之水也。亦不是将清来换浊,亦不是取出浊来置于一隅也。水之清,则性善之谓也。故不是善与恶在性中为两物相对,各自出来。此理,天命也。顺而循之,则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则教也。自天命以至于教,我无加损焉,此舜有天下而不与焉者。”②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0-11页。
对勘二人的论说,虽然他们所处时代不同,但其论述却有惊人之相同处,可说是互补的阐发。由此,我们就有可能得到一个结论:所谓是非善恶是一种人为的“造就”而非先天之本源的东西。摒弃人的私意念头,任天机流行,则无所谓善恶是非了。再看阳明在另处与弟子的问答,这一点也就一目了然了:
问:“古人论性,各有异同,何者乃为定论?”先生曰:“性无定体,论亦无定体,有自本体上说者,有自发用上说者,有自源头上说者。有自流弊处说者。总而言之,只是一个性,但所见有浅深尔。若执定一边,便不是了。性之本体原是无善无恶的,发用上也原是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恶的。譬如眼有喜时的眼,有怒时的眼,直视就是看的眼,微视就是觑的眼。总而言之,只是这个眼,若见得怒时眼,就说未尝有喜的眼,见得看时眼,就说未尝有觑的眼,皆是执定,就知是错。①王守仁:《传习录》,载《王阳明全集》(上),第115页。
问:“先生尝谓‘善恶只是一物’。善恶两端,如冰炭相反,如何谓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体。本体上才过当些字,便是恶了。不是有一个善,却又有一个恶来相对也。故善恶只是一物。”②同上书,第97页。
阳明认为,性自不可说,要说就会触其不同侧面,从本体、从发用、从流弊,就会各有说法。孟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是从源头上说的,但不能说孟子就已经说得彻底了。荀子说的也是人的性,但他是从流弊上说的,在救治人的身心时不易把握究竟,但也不能说他说的就不是人的性了。善是本体,本体廓然大公,天机流行不息,气机畅通没有滞碍,而恶只是本体的偏移,这种偏移就是着了私意、动气,这就是恶。动心动气,为己意所束缚就不是天道,就是恶,就失了人的本性。很显然,阳明和明道都是从天道和气的层面上论说的,与儒家日常的见解甚至可能有大相径庭之处,但这是真正修养者的体道之言,这种对人性的说法对整个儒学史而言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是关键性、升华性的补充。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可能超出了原始儒家(包括孟子)的认识范围。如果对这一点我们还没有把握的话,那么至少可以说,阳明的思想表达超出了原始儒家的表述范围,因为在尽心、知性、知天的表达中应有此意,但孟子并没有申明,而且他对告子的批评中也有意识地否定了此意,这可能就是阳明说孟子也只是说个大概的根据。但是,阳明毕竟是儒家,他一方面要从本体上提撕学者修养境界的究竟,另一方面,鉴于学者多为初学之士,即有见道者也体悟有限,他又要提醒学者心、性、气本质为一。良知也不外于气,但是必须把握头脑,也就是首先要悟得良知在己,达到万物一体之境方可真正知晓它的含义,故而阳明又有一个阐释和提醒:
问:“‘生之为性’,告子亦说都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认得一边去了,不晓得头脑。若晓得头脑,如此说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这也是指气说。”又曰:“凡人信口说,任意行,皆说此是以我心性出来,此是所谓生之为性。然却要有过错。若晓得头脑,依我良知上说出来,行将去,便自是停当。然良知亦只是这口说,这身行,岂能外得气,别有个去行去说?故曰:‘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气亦性也,性以气也,但须认得头脑是当。”③同上书,第100-101页。
阳明认为,“生之为性”这句话本身是不错的,但是,它是就不同视角、不同条件来说的。譬如,孟子说善是性,是从人的本体来说;荀子说恶是性,是从人性的发用流行的过程尤其是流弊上说的;大程子和阳明本人说的则是善恶是一回事,只是从人的行为的过与恰当来看的,无过与不及就是性。而说气是性,也是说气是人的天性,但气的发用流行需要良知本体的调控,循天理而行然后自然而然,即天性的本原就是孟子所谓的性。
三、结束语
阳明上述论述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一个生命体,人的身体活动、各种行为举止,无论其是否得当,是否符合道德标准,都不可能是心灵的或道德理性的直接表现。身体的活动,首先是由人的心灵和身体之气共同协调的行动,因此,良知之在人身,无时无刻不与人体的气同在同行。良知作为行动的主体对身体的气的运行起到自觉发见、调整、理顺与整合的作用,它能引领正气,自觉抵御、辟出邪气,这是道德主体性功能表现,是儒家志气理论的第一个层面。同时,人体之中的气的运行就是“生之为性”,它本身无善无恶,气就是性。人的行动的不适当源于“憋气”或“暴气”,这又与人的“志”定向等问题联系在一起。因此,志、气之间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过程。气的和顺、协调与人的道德知觉的互动就是人的自我修养的进程,其最终的境界则是万物一体、心性气的合一,也就是复了人的本体。阳明在这一点上的突破为儒家的身心认识和修养理论构筑一个新的支撑点,即以心为原点,以气为中介,以心性气的合一达成了身心之间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乃至同一性,从而推动中国哲学的身心理论到达一个新的台阶。
(责任编辑:韦海波)
B94
A
2095-0047(2015)01-0085-15
李洪卫,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
本文得到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文化的认识基础和结构研究”(项目编号:10&ZD064)的资助。
——论阳明学派对告子思想的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