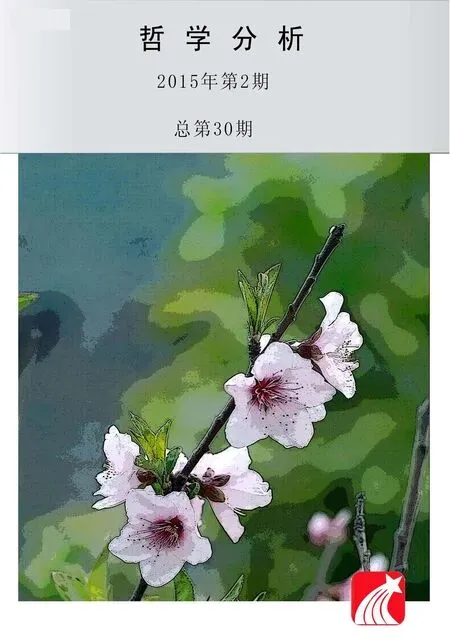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
吴国盛
科学技术的哲学理解
科学作为希腊的人文
吴国盛
希腊人以“自由”为理想人性,以“科学”为人文教化的手段。“科学”就是希腊人的“人文”。“自由”即成为“自己”,而“自己”只能通过“永恒”不变者才可达成。追求永恒的“确定性”知识于是成为一项自由的事业。作为自由的学术,希腊的理性科学具有非实用性和内在演绎两大特征。自由的科学为着“自身”而存在,缺乏外在的实用目的和功利目的。自由的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和展开“自身”。
科学;人文;希腊;自由;演绎科学
一、知识即自由
希腊是一个城邦民主制的奴隶社会,自由民享受充分的政治权利,是城邦的主人。希腊人多次自豪地说:“我们的国家没有统治者,每一个城邦公民都是统治者。”希腊人也多次为自己是自由的人民而自豪。对希腊人而言,奴隶是一种不幸的存在者,因为他们没有自由。尽管长得跟人一样,也会讲话,但奴隶不算真正的人,因为在希腊人看来,人的基本规定就是自由;在希腊人这里,“人”的反义词是“奴隶”。正像中国人骂某些无情无义之人为禽兽,希腊人乃至现代西方人骂某些不懂自由的人为奴隶,都是相当严厉的指责。
然而,要真正理解、领悟自由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中国人常常把自由简单理解成不守规矩、不受约束、任意胡来,这当然是对自由的大误解。实际上,在西方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由”也有不完全一样的内涵。西方的普通人也容易把自由简单理解成“为所欲为”,这跟中国普通人在理解“仁爱”时容易发生偏差(比如溺爱、愚忠、乡愿等)是一样的。高扬自由之大旗的希腊人,是如何理解“自由”的呢?
希腊人着眼于“知识”来理解“自由”。对我们来讲,这特别令人意外、令人不解。近代的斯宾诺莎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说的基本上是希腊人的意思,也是把“自由”落实到“知识”上。但是,我们通常是这样理解斯宾诺莎的:我们认识了必然,从而就获得了征服必然的力量,因此我们就自由了。比如波普尔也有这样的说法:“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基本上是这个意思。正因为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常常把斯宾诺莎的说法改成“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由被看成是一种征服的、“为所欲为”的能力,是一种“解放”。
这个理解并不是希腊人的,而是现代人的。现代人信奉“知识就是力量”,或者“知识服务于力量”,因此并不把“知识”本身看成是最高的目标,而只是达成“力量”、“解放”的手段。希腊人不一样。希腊人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最高的目标,获得知识就是获得自由。
如何理解获得知识即获得自由呢?这里涉及希腊人对“知识”的看法。在现代汉语里,“知识”一词已经很平庸了,对什么东西知道点什么的人都可以说(关于什么东西)是有知识的。但是,希腊人的“知识”(Episteme)包含了更多的独特的意思。总的来讲,希腊人所谓知识,是确定性知识、内在性知识,不是一般的经验知识。
我们从德尔斐神庙里一个著名的神谕“认识你自己”开始,探讨一下希腊人独特的知识论传统。在这个神谕里讲了两件事情,一个是“自己”,一个是“认识”。“自己”、“自身”其实就是“自由”,但希腊人对“自己”的把握是通过“认识”而获得的。不是通过“顿悟”,也不是通过实践,而是通过“认识”。这样一来,希腊的“认识”也被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即认识是追随知识“自己”、知识“自身”的,因而本质上是一种内在性认识。
历史上,德尔斐神庙的这个神谕被认为是苏格拉底提出来的,或者至少是他将之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一个大问题的。人们都说,苏格拉底在西方思想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孔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确实如此。苏格拉底的旷世贡献是把一种知识论传统确立为西方的正宗传统,也就是说,我们之前讲到的西方大传统的开山宗师就是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在把知识论塑造成西方的正宗方面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他始终不渝、坚定不移地把追求知识、追求真理作为最高的“善”,甚至,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对中国人而言,德性是一回事,知识是另一回事,德性总是高于知识,而苏格拉底却把知识与美德相等同,“有知即有德”、“无知即缺德”。由于知识是最高的善,因此实际上是任何道德的基础。
知识为什么是最高的善?知识何以能够充当一切道德的正当基础呢?秘密在于苏格拉底所说的“知识”不是一般知道点什么、懂得点什么、了解点什么,而是通往“永恒”的唯一途径。苏格拉底反复使用为他所特有的那些方法——辩证法、助产术、下定义等,只为了表明一件事情:知识并不只是接近“事实”,而是接近事实之中含有“永恒”要素的东西。这些个“永恒”的要素即使在事实消失之后仍然存在,比事实更坚硬。这才是知识之所以成为最高追求的根本原因。
苏格拉底的这个思想当然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由来有自。从泰勒斯开始的希腊思想家一直在把握世界的统一性上做文章,并且在做文章的过程中,突出了变化与不变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世界真的充满了变化,那么同一性如何保证?如果没有同一性,如何把握世界的统一性?巴门尼德突出了“变化”的不可理喻,从而断然否定了“变”,而声称世界是“一”、是永恒不变的。据此黑格尔甚至认为,巴门尼德才是开辟希腊理性主义的第一人,是希腊哲学的真正开端。但是,我们的经验世界的确充满了变化。在苏格拉底之前,在(经验的)“变”与(理性的)“不变”之间已经出现了好几种调和方案。一种是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一种是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说,再就是原子论。所有这些调和方案,都是把大千世界多样的变化,化解、还原为某种不变东西的少数几种样态变化。四根说中四根是不变的,但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进行结合;原子论中原子是不变的,但原子可以有多种排列和组合的可能。但是,追究变化背后不变化的东西,是希腊科学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
苏格拉底把这个“尊崇不变”的原则进一步深化,用定义的方法得出“一般本质”的概念。他的学生柏拉图又进一步把这个“一般本质”提升为“理念”。理念之为理念就在于它是永恒、不变、完整无缺的,它是事物的理想状态,是事物之所以被理解的根据。怀特海说过,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就是对柏拉图的注释史,是说整个后来的西方思想都一直活动在这个思想脉络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本质在于寻求不变性、确定性。知识、科学的本质在于确定性。
永恒不变的东西为什么这么值得追求呢?因为它独立不依、自主自足,它是“自由”的终极保证。只有永恒不变,才有“自己”。持守“自己”就是“自由”。“认识你自己”就是追求自由的最后根基。
中国文化缺乏一个明确的“自己”概念。对中国人而言,整个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人都是这个有机体中的一个部分,不能独自存在,只有在整个有机体中才能发挥它恰当的作用。进而言之,整个宇宙是一个生命之流,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只是这个生命之流溅起的一个浪花。任何事物之所“是”,不是因着事物的“自身”,而是生命之流的“势”“时”“史”共同造就的。因此,严格说来,事物并无一个“自己”,都是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对中国文化而言,“自己”不是一个原初的、基本的东西,而是派生的、可有可无的。强调“自己”往往是有害的,对社会对个人都是如此,因此“自己”往往是一个负面的词汇。许多带“自”的成语都是贬义的,比如“自私自利”、“自作自受”、“自取灭亡”、“自以为是”、“自暴自弃”、“自不量力”、“自高自大”、“自鸣得意”、“自命不凡”、“自欺欺人”,等等。中国人对究竟什么是“自己”其实并不太在意。
西方思想着眼于“自己”。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本性”(nature),“本性”是属于事物自己的。追求事物的“本质”、“本性”,就是追究事物的“自己”,这是理性的内在性原则,即从自身中为自身寻求根据。
为了理解“自己”,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中西方对于“身份”的规定。对中国人而言,所谓“身份”即社会地位,它处在变化之中。你出身贫民,但可以勤奋刻苦地读书,最终考取功名,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你是富贵人家子弟,但富不过三代;“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讲的也是这个意思。当我们讲“身份”的时候,并不是对个体的一种确定性的识别,而是对“当下”社会地位的一种认同。这就是中国网民们经常自嘲的,“你不要以为自己有身份证就是个有身份的人”。
西方人讲身份用的是Identity一词。这个词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认同、识别,一个是同一性、恒等性。这几个意思共同附着在同一个Identity身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西方人“身份”的含义:所谓“身份”,就是可以帮助识别一个人之为一个人的那些稳定同一的东西。不论是生物学意义上还是社会学意义上,人始终处在持续的变化之中。可是,当我们说一个人在变化的时候,我们预先设定了是“同一个”人在变化,如果不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就谈不上变化。因此,在我们谈论变化的时候,我们已经预设了“同一性”。西方人讲“身份”讲的就是这种被预设了的“同一性”。在现实中,这种同一性通常通过相貌来确认,因此,西方的ID一般是Photo ID,也就是身份证一般是有照片的。尽管人的相貌每天都有变化,但还是能够通过照片将他或她的“同一性”即“身份”辨认出来。
从西方人的身份概念可以看出,所谓“自己”、“自身”根植于“同一性”、“确定性”,因此,以确定性、内在性为根本特征的希腊科学(知识),是通往“自由”的必由之路。获得知识即获得自由的意思是,通达了永恒的理念,就通达了任何事物包括认识者本人的“自己”、“自身”,因而也就通达了“自由”。“自由—科学”构成了希腊人的“人—文”。在希腊人眼里,科学既非生产力也非智商,而是通往自由人性的基本教化方式。没有对科学的追求之心,你就不配做一个自由人。
二、自由学术的非实用性
科学之所以是希腊人的人文,原因还就在于,希腊人的科学本质上就是自由的学术。自由的学术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希腊科学纯粹为“自身”而存在,缺乏功利目的、实用目的;其二,希腊科学不借助外部经验,纯粹依靠内在演绎来发展“自身”。我们要深入理解希腊科学,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做更多的考察和分析。
亚里士多德①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中译文均取自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求知是人的本性”,把“知”的问题摆在了最为突出的地位。他在这部重要著作的第一卷区分了经验、技艺和科学(知识,episteme,在希腊文里,“知识”和“科学”是同一个词)。他认为,低等动物有感觉,高等动物除了感觉还有记忆。从记忆中可以生成经验,从经验中可以造就技艺(techne)。经验是关于个别事物的知识,技艺是关于普遍事物的知识。技艺高于经验,因为有经验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技艺者知其所以然,故技艺者比经验者更有智慧、懂得更多。但是技艺还不是最高的“知”,最高的“知”是“科学”(episteme)。技艺固然因为超越了经验而令人惊奇赞叹,但是由于多数技艺只是为了生活之必需,还不是最高的知,只有那些为了消磨时间,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日常必需为目的的技艺,才是科学。我们中国人常常把知识分成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两大类,亚里士多德却给出了知识的三个阶段。他的经验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经验知识,技艺这种追究原因、知其所以然的普遍知识,大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知识,但是我们的分类中却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科学”的位置。这件事情反映了希腊科学精神相当大程度上被我们忽视、被我们遗忘。
什么是“认识”?认识即是追求“科学”。什么是“科学”?为什么在“技艺”这种理论性知识之外还要增加“科学”这样一个纯粹知识的阶段?这是特别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的地方。亚里士多德说得很明白,“在各门科学中,那为着自身,为知识而求取的科学比那为后果而求取的科学,更加是智慧”(《形而上学》982A15-18)。“如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进行哲学思考,那么,很显然他们是为了知而追求知识,并不以某种实用为目的。”(《形而上学》982B21-23)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多次强调科学是一种自由的探求。他提到“既不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为目的的科学”(981b25),提到“为知识自身而求取知识”(982b1),最后他说:“显然,我们追求它并不是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们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他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仅是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纯粹的科学必须是为着求知本身的目的而不是任何其他目的而存在,这种指向“自己”的“知”,才是纯粹的科学。这样的科学,就是“自由”的科学。
这里所说的当然是哲学,亚里士多德也把它看成是一切科学(知识)中最高级的,是最理想的科学形态。这种科学理想,不只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能够找到,在他以前的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同样能够找到。这种科学理想,既体现在亚里士多德开创的第一哲学(形而上学)那里,也体现在希腊人特有的科学——数学——那里。在《理想国》里,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特别强调了数学的非功利性、它的纯粹性、它对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为算术和几何的学习不是为做买卖,而是“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这门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纯粹为了知识。希腊人开辟了演绎和推理的数学传统,这首先是由于他们把数学这门科学看成是培养“自由民”所必需的“自由”的学问,自由的学问是纯粹的为着自身而存在的学问,不受实利所制约。
希腊数学的集大成者是欧几里得的《原本》。《原本》成为西方思想最重要的经典(也许仅次于《圣经》),但其作者欧几里得的生平几乎不可考。流传下来仅有两则故事。第一则故事说,有国王师从欧几里得学习几何学,欲求捷径,欧氏回答说:“在几何学的王国里没有为国王单独铺就的康庄大道。”第二则故事则说的是,一位年轻人师从欧氏学几何,但问及几何学的用处,欧氏勃然大怒:“给他两个钱,赶紧给我走,居然想跟我学有用之学,谁不知道我的学问是完全无用的?”
为什么希腊学者强调自己知识的非实用性呢?因为任何知识若是仅仅为他者而存在、成为实现他者的手段和工具,那么这样的知识就不是为着“自己”的知识,因而就不是自由的知识;学习这样的知识,就不能起到教化自由人性的作用。希腊人强调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其背景在于,他们的学术本来就是自由的学术。
我们中国文化有很强大的“学以致用”传统,强调学术、知识本身并无内在价值,只有工具价值。“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读书的价值在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学问“本身”没有价值。学问是敲门砖、是进身之阶,“学而优则仕”。总的来讲,中国的读书人、学者、士人并未视学术有着自身独立的价值,因而士人阶层总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阶层,总是依属他人而存在。今天人们批评中国学者缺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其实这个局面的深层原因是,中国文化中缺乏“为学术而学术、为知识而知识”的精神,学以致用的传统太过强大。我们嘲笑无用的学问是“屠龙之术”,我们的学生总是问老师我们学习的东西有什么用,而我们的教师、学者也总是苦口婆心地向学生、向管理者、向科研经费的拨发者强调他们从事的学术是有用的。这个学以致用传统,严重妨碍了我们去理解科学精神的真谛。
三、自由学术的演绎特征
希腊人所高标特立的无用的知识如何可能成为知识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实践出真知”、“一切知识归根结底来源于人的生活实践、生产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一切生活实践中产出的知识都是为了优化、指导进一步的实践,因而肯定是有用的。无用的知识何以是知识呢?希腊人的回答更加特别:一切真知识都必定是出自自身的内在性知识,来自外部经验的不算真知识(episteme),只能算意见(doxa)。什么是真知识,什么是内在性知识?这就要说到希腊科学的演绎特征。
我们知道,人类几个最古老的文明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并且产生了专职守护并传承这些知识的社会阶层(比如祭司、僧侣、文官等)。这些知识,有的事关国计,有的事关民生,但均是有用的知识,均是祖先生活智慧的结晶,均是经验知识。唯有希腊人奇花独秀,提出知识的本质是非经验的,从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演绎科学。
演绎科学注重内在“推理”,不重解决具体应用问题。什么是“推理”?百科全书说:“推理是使用理智从某些前提产生结论。”人们通过经验学习都可以习得从某些前提得出结论的能力。看到天上风起云涌,我们得出结论“快要下雨了”;看到大街上的人都朝一个地方奔去,我们得出结论“那地方出事了”;房间里的灯突然熄灭了,我们得出结论“停电了”。这些都是经验推理。这些推理多半是正确的,但也不一定。风云突变,甚至电闪雷鸣,也有可能不下雨;人们都朝一个地方跑,也许是抢购什么东西;灯熄灭了,也可能是灯泡坏了。但是,有些推理却必然正确,比如,“单身汉是未婚的”,“屋子外面要么下雨要么不下雨”。如此看来,推理作为知识的重要表现形式有许多种。有些推理不是必然正确,有些推理必然正确。希腊人看重的推理是内在推理、演绎推理,必然正确的推理。
演绎推理的根本特征是保真推理,即只要前提正确,结论必定正确的一种推理形式。三段论是最基本的保真推理。它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希腊人最常说的三段论是:“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苏格拉底会死”。这个推理是由一般向个别过渡,结论所包含的断定不超出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此,我们中国人容易把它看成是“废话”。是的,它确实是废话,因为只有废话才“永恒正确”。希腊人为了寻求“永恒正确”,不惜投入巨大的精力来研究“废话”。
“废话”何以能够构成“知识”、发展“知识”?这是我们理解演绎科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我们熟悉“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中国人来说,不容易明白知识如何按照“自身”的逻辑“自行”展开。希腊人的知识构建是通过推理、证明、演绎来进行的,而所谓证明、演绎,只是顺从“自身”的内在逻辑而已。
我们可以举芝诺悖论为例,来考察一下希腊人的证明性知识如何独立于经验进行构建。芝诺是巴门尼德的学生。巴门尼德提出“存在者存在、不存在者不存在”(或可译成“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作为他的基本立论,基于这个立论,他认为变化不可能,一切变化根本上是假象。芝诺为其师的立论提出论证,他想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他一共提出了4个运动悖论,以此证明运动不可能存在。
第1个悖论叫做“二分法”。他认为,从A点到B点的运动是不可能的,因为,为了由A点到达B点,必先到达AB的中点C;为了达到C点,必先到达AC的中点D;为了达到D点,必先到达AD的中点E……,这样的中点有无穷多个,找不到最后一个,因此,从A点出发必须要迈出的第一步根本迈不出去。
第2个悖论叫做“阿基里斯追龟”。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的英勇战将,迅跑如飞,芝诺现在要论证他追不上乌龟。芝诺说,阿基里斯为了追上乌龟,必须将到达乌龟起跑时的位置;可是,等他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乌龟已经在前头了。他若继续追,总是要先到达龟先前所在的位置,而这个位置总是离龟现在的位置有一段距离。无论龟跑得多慢,阿基里斯跑得多快,他也只能逐步缩小这个距离,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一距离,因此,阿基里斯永远追不上龟。
第3个悖论叫做“飞矢不动”。他说飞着的箭在每一瞬间肯定在某一个空间位置上,而在一个空间位置上,意味着在这一瞬间它是静止的。既然在每一瞬间都是静止的,而时间又是由这些瞬间所构成,那么总的来看它是静止的。
第4个悖论叫做“运动场”,说的是三列物体的相对运动。一列物体相对于静止的一列物体运动了1个单元的空间,相对于运动的一列物体却运动了2个单元的空间。如果我们承认有一个最小的空间间隔的话,那么就会出现1个空间等于2个空间这样的悖论。
芝诺悖论采用的是证明的方法,但结论却与我们的经验常识相左。我们中国人很容易认为,芝诺悖论由于背离生活常识,只是一种廉价无聊的诡辩,不值得重视。但是,西方思想却没有轻易放过它。希腊人认为,结论是否荒谬并不要紧,关键是论证是否符合逻辑、符合理性的推理规则。如果他的论证不合逻辑、推理有漏洞,那自然应当放弃;如果他的论证没有问题,那就不能轻易放弃,相反,要以此追究我们的常识是否出了问题。事实上,芝诺悖论提出两千多年,一直没有被忽视、一直被讨论。由于涉及非常深刻的无限问题,对它的讨论实际上推动了无限数学的发展。
要深入理解芝诺悖论,需要考虑时间空间的连续性问题。在这四个悖论中,前两个是一组,后两个是另一组。前一组“预设”了时间空间是连续性的,因而可以无限分割;后一组“预设”了时间空间是不连续的,因而存在着最小单元。只有考虑到这两个预设,芝诺悖论才是合理的。他想说的是,时间空间要么是连续的,要么是不连续的,无论哪种情况,都显示出运动的荒谬性,因此,最好的结论就是,运动不存在。我们喜欢“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人会断然否定芝诺的论证,会认为我们只须起身在屋子里走几步,举起手在空中舞几下,就证明了芝诺是错误的。然而,希腊人不这么看。希腊人会认为,我们并不否认我们经验中的确存在着运动这回事,但是,正如芝诺所说的,它不合理、不合逻辑。因为不合理、不合逻辑,所以我们宁可相信它不存在,它是一个假象。要破解芝诺悖论,不能诉诸经验、常识,只能诉诸进一步的理性论证。
希腊人亚里士多德对芝诺悖论做了一个破解的尝试。针对“二分法”论证,他说,我们固然不能够在有限的时间里与数量上无限的事物相接触,但是,我们却可以以无限的时间点与数目无限的事物相接触。只要时间和空间都可以无限分割,那么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过无限数目的点是可以的。
我们暂且不论亚里士多德的论证是否正确——这个论证当然有其合理之处也有其局限——我们着重看一下理性知识的建构过程。很显然,在理性论证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会运用三段论,从前提推导出结论,另一方面,我们分析一个命题一个断言所包含的“预设”。前一方面是明面上的,是简单的,另一方面则是隐蔽的,是复杂的。正是后一方面,使我们见识到所谓“废话”是如何能够自我构建为知识体系的。
芝诺的论证和亚里士多德的质疑,都是在理性规则的指导下,拓宽一个问题领域的逻辑空间。这种拓宽有时候是顺着的,比如,芝诺说,两点之间总是有一个中点,于是在迈步者的前面就有无限多个中点需要经历;在有限时间内经历无限个点是不可能的;因此,由一点运动到另一点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的拓宽是逆着的:你说“两点之间总是有一个中点”,那就意味着你承认了空间的连续性;你承认了空间的连续性,最好也同时承认时间的连续性;你承认了时间的连续性,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无限多个时间点;以无限多个时间点去接触无限多个空间点,是可以的。亚里士多德的质疑的关键在第一步,即追究到芝诺论证中的预设。对预设的追究,是演绎科学之所以能够提供“新知”的关键。
演绎推理貌似重复一些废话,但希腊演绎科学的确提供了“新知”。希腊数学和希腊哲学的伟大成就就是明证。没有人敢说希腊哲学和希腊数学都只是一些人人皆知的废话。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向个别推进,因而展示了多样性,就此而言是提供新知的。但是,你可以说这些“新知”其实并不“新”,实际上是“旧知”。是的,从根本上说是“旧”知,但这些“旧”知因为被掩盖着、遮蔽着,并不为我们所“知”。
智者曾经讨论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学习悖论,意思是说,我们究竟对我们正在学习的东西是懂还是不懂呢?如果是懂的话,那么学习是不必要的;如果不懂的话,那么学习就是不可能的。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对此问题做了一个著名的回答。他说,我们的确只能学习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但是为什么还要学习呢?那是因为,那些我们本来就懂的东西后来给忘了,而学习不过就是把它们重新记起来,因此,学习就是回忆。为了证明“学习就是回忆”,苏格拉底还喊来一个奴隶小孩,现场让他计算二倍面积的正方形边长,结果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得出了正确的结果。柏拉图以此表明,奴隶小孩本来就懂得几何学,但他并不知道自己拥有这些知识,经过苏格拉底的启发,他回忆起来了。
这个学习悖论的柏拉图式解决听起来不可思议。当然,我们若是从经验心理学意义上来理解柏拉图的这个“学习即回忆”的理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个理论却可以非常好地帮助我们理解,演绎科学何以能够提供“新知”。“新知”本质上是“旧知”,但因为我们的“遗忘”、“遮蔽”,当它们被重新挖掘出来的时候,它就是“新知”。
希腊思想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秘密,那就是,我们生活在遗忘和遮蔽之中,遗忘和遮蔽是我们生活的本质。这个说法可能有些深奥。如果通俗地说就是,我们的存在是一种条件性存在,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的存在状态,决定了我们之所是,但通常我们对这些条件并无意识。然而,只有通过追溯这些条件,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及世界是怎么回事,因为世界的存在也是条件性的。
人们常说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经验一定也是有条件的。是什么让经验成为可能的?特定的经验基于何种特定的条件?我们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可是,我们的“看”并不是赤裸裸的、中性的。我们的“看”是条件性的,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先决因素。同样一个东西,不同的人或者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下,能“看成”不同的东西。因此,真正的理解经验,我们必须回到使经验成为可能的先验条件那里。正是这些先验条件使经验成为可能,使经验成为它所是的样子。
我们的经验中有这样的说法:脑袋像一个圆球那样,可是脑袋并不是一个真的圆球。这里有一个先决条件在起作用,那就是我们必须先有“圆球”的概念,我们才能说“脑袋像球”以及“脑袋不太圆”。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根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圆球。我们能够找到的都是像脑袋这样有点圆但又不绝对圆的东西。如果一切知识都来源于经验的话,那“圆球”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呢?柏拉图明确宣布,圆球的知识属于一个超验的领域,我们是通过概念的内在演绎获得圆球的知识的。何谓“圆”?“圆”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是被定义出来的:“圆是这样一条曲线,它上面的每一个点都与一个叫做圆心的点保持相同的距离。”我们在做这个定义的时候,根本不用实际上用圆规画一个圆来。事实上,圆规画出来的也不是真正的、绝对的“圆”。相反,圆规画出来的东西之所以被叫做“圆”,乃是因为“圆”这个概念事先已经被规定出来了。
不仅“圆”如此,我们经验世界中的一切东西无不如此。因此,要恰当理解我们的经验世界,我们需要进行先验追溯。在先验追溯之中,我们发展我们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科学。
作为先验追溯的演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之所以显得是“新”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向对于我们自身所拥有的知识没有觉察。这些知识深藏在我们的灵魂内部,是一向属于我们“自己”的。正是因为一向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正因为一向属于我们,学习这样的知识,也就是在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你自己,就是在追求自由。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①《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许良英、范岱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74页。当人们意识到现代科学出现在现代西方,是因为它们继承了希腊演绎科学的基因之后,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创造了演绎科学?”我想,没有把“自由”作为理想人性进行不懈追求的民族,很难对演绎科学情有独钟、孜孜以求。我们的祖先没有充分重视演绎科学——不关乎智力水平、不关乎文字形态、不关乎统治者的好恶,而关乎人性理想的设置。我们的“仁爱”精神,使我们走上了不同的人文发展道路。
(责任编辑:张琳)
B813
A
2095-0047(2015)02-0130-11
吴国盛,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