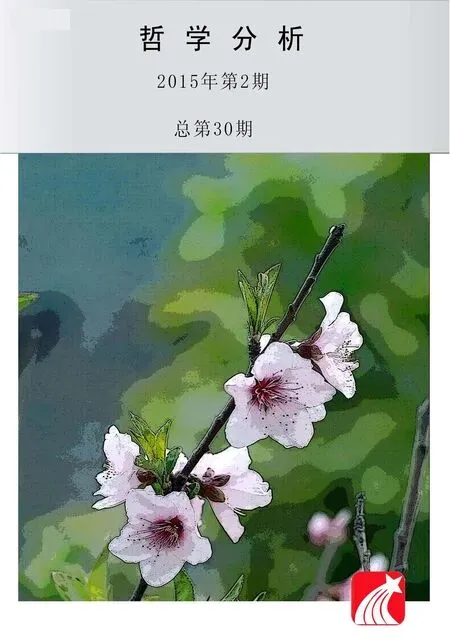人去哪了?!
——第九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会议综述
闫宏秀 张帆
人去哪了?!
——第九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会议综述
闫宏秀 张帆
当我们穿行在现代文明的社会生活中,我们不必餐风饮露、不必刀耕火种、不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离开手机、网络、微信我们却不能活。显然,我们变了!技术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那些正在使用技术的人——我们不单是生物意义上的“人”,我们更是被各种技术附着了的“技术人”。那么,技术是如何改造人的,经过技术的洗礼人变成了什么样?围绕“人去哪了?!——技术时代的主体与客体”这一主题,2014年12月18日,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主办的第九届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会议在上海交通大学闵行校区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401会议室召开。会议吸引了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对外贸易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校和学术机构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的参与。来自《上海大学学报》、《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分析》、《上海理工大学学报》杂志的编辑也到会并参与了讨论。
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成立于2009年4月,旨在形成一个立足上海、放眼国际的技术哲学学术交流平台。到2014年为止,论坛共召开了九届会议。在过去的五年中,论坛主要采取“校院联合接力”的机制,实现了讨论的可持续发展。在以往举办过程中,通过发挥中老年教授、专家的引领和指导作用,激发了青年学者的学术热情,有效地凝聚了上海各高校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中青年学者。论坛举办地包括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社联等。论坛主题涵盖技术哲学的经典论域、当下技术哲学的新思潮、对技术工作者身份的哲学反思、技术物的多视角剖析、技术与政策的关系、技术设计、技术创新等,论坛形式包括报告会、读书会、沙龙、论文交流,等等。
在本次论坛的开始,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李侠教授对论坛的宗旨、发展以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简要介绍。他指出,在论坛成立五周年之际,期望以学术交流为主旨而建立的“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学术共同体能够传承下去,发挥推动青年学者成长的功能。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书记关增建教授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与会学者的热烈欢迎,并希望通过“上海中青年技术哲学论坛”的平台加强与上海的兄弟单位的沟通、交流与合作,为繁荣上海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随后的主题报告共有五个,上半场的报告讨论了技术时代对“人之为人”的挑战,下半场的报告分别从人类学和技术哲学的视野对“人还是人”的观点进行了辩护。
一、人还是“人”?
论坛的上半场,上海交通大学的闫宏秀副教授以《技术时代的人如此多元?Human,Nonhuman,Transhuman,Posthuman》为题引出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她从人的本质、人与技术的关联性以及新技术发展的三重维度,以电影《Her》为例,抛出了“人未来去哪里?”的问题。在报告中,她首先阐述了技术对于人的意义,即从技术的角度看,人为什么是人。人类诞生之初因其生物性的缺陷使得人需要依靠技术才能生存,因此,从存在论的意义上讲,人的存在是基于技术的,即人与技术组成一个整体;在人的类本质的意义上,日本学者星野芳郎将人具有技术而动物不具有技术作为人类与动物的区别,即技术成为了人与他物的一个区别,成为人类(human)区别于非人类(nonhuman)的一个标准,人的类本质与技术有着紧密的关系。其次,人在技术中去哪了呢?当技术的维度成为人的存在的一个维度时,当技术与人组合在一起(即人—技术)时,我们却发现伴随技术的发展,人在技术中有种迷失的征兆,我们开始重新反思人的主体性这个话题。在现代性的视域中,主客体是二分的,并且人的主体性被大肆渲染,而技术则被视为客体。但是,当下的技术作为客体不仅仅表达主体的意愿,而且不断地模仿人的一些属性。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了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新特征,传统意义上的主体性渐行渐远,而作为技术的客体也不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主体的人的对立面而出现,此时,主体与客体的界限在何处?当曾被视为人的对立面的非人(如超声波检测等)被赋予伦理意义的时候,当人所特有的伦理属性被非人分享时,对人的类本质、类属性的界定已然变成了一个新的话题。特别是,当人类的身体经过技术改造而形成的转化人类(transhuaman)悄然问世时,当技术进一步对人类进行设计与改造后,在寿命、智力及情感等方面都超越目前人类的后人类(posthuman)出现时,关于人的哲学思考又再次凸显出来。最后,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看,人还是不是人?就像特修斯之船,一艘船坏了,修船、拆板,拆了很多板之后,却发现除了旗号,其余什么都不一样了。如瑞士苏黎世大学社会心理学家梅尔以他自己为蓝本制造了生化电子人,现在也有很多代替人类器官的技术物。若大胆假设,人类器官真的被技术物取代,即这个“人”除了名字,其他都被技术化了,此时的人该如何看待?到底什么是客体、什么是主体?
在上半场的第二场报告中,上海大学的周丽昀教授以《现代技术背景下的主体与客体——从身体的角度看》为题,围绕技术内化与身体的不确定性、身体转向与涉身自我、技术和身体的关系展开阐述。首先,周丽昀教授强调,技术改变了身体的传统认知观。现代技术和知识已经内化,开始侵犯并不断重建身体的内容。技术内化引发了人们对身体的不确定性的关注。以赛博格(cyborg)为例,赛博格是借助特定的机械或电子装置辅助完成或者控制生理过程的存在物,是一种受控体,是人、机器与动物的混合体。赛博格具有强烈的隐喻意义,它构建了一个多重主体,并且主体和客体的边界是模糊的;它的出现模糊了所有范畴,甚至对立的两极的界限,并对身体与意义的关系进行了重构,产生了身体的跨界。其次,周丽昀教授认为,在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身体成为一个新的话题和焦点。究其原因,是因为消费主义的兴盛导致了作为“符号的身体”的产生,性别关系的转换导致了“权力的身体”的产生,高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带来了作为主体的身体与作为客体的身体之间的张力。她特别指出,这里的身体的理论基础是“涉身自我”,它具有两个特征:其一,强调自我与躯体不可分,是一种肉身化的主体;其二,强调身体的含混性和可变性。这样的身体既具有物质性和普遍性,也具有文化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它已经不仅仅是传统的生物学意义上的事实,不仅仅是一副由生理组织构成的血肉之躯,而是呈现出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稳定性与流动性、普遍性与差异性的统一。这样的身体因此具有梅洛-庞蒂意义上的“身—心—世界”的三重蕴涵结构。再者,技术和身体之间有一个双向互动的关系。从身体之于技术来看,它表征为身体作为技术的来源与场域;从技术之于身体来看,表现为技术对身体的取代、技术对身体的扩展以及技术的政治变革功能。最后,周丽昀教授从身体的角度对当今技术时代的主客体的关系提出了几点思考:一是主客体有无边界的问题。随着技术对身体的入侵,主客体边界日益模糊,主客体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二是“一元”与“多元”的问题。技术时代的主体很多时候呈现为一种多重主体,能发挥主体作用的不一定是人,也可能是非人,体现出了“去中心化”和“非一元化”的特征。三是在场与缺席的问题。人去哪儿了?人一直都在。如赛博格空间中的身体,貌似缺席,实则在场,与其说赛博格空间是替代了身体的相遇,毋宁说是补充或者延伸了身体的相遇。以身体为视角,可以更好地理解技术时代的主客体关系。
二、人还是“人”!
在下半场的报告中,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王球博士首先做了题为《人之为人:人类学差异还是范畴差异?》的报告。王球博士基于人的本质是理性动物这一共识,指出:进化自然主义者相信,人类与其他动物物种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基因或文化基因(meme)的载体。尽管符合逻辑规则的推理能力是人类独有的,但是这种能力无非是通过一些动物所缺乏的某些认知机制——例如,托马塞洛主张的“因果/意图调解力”和“联合注意”,帕品纽所说的“读心机制”和“手段—目的推理机制”来实现的,这些认知机制的存在,使得我们超越了(surpass)动物。类似地,技术哲学家对“人是什么”或隐或显地持有一种标准型态(prototype)的预设,一旦由于技术上的或进化上的原因导致我们的智力、生理、心理水平在未来超越了现有的标准型态,“人去哪儿了”就成了一个迫切的哲学问题。王球博士指出,进化自然主义者和技术哲学家都把“人之为人”当作了一个“人类学差异”问题:前者试图寻找人与动物在哪些认知机制上有差异,后者的目标之一就是去探索在典型的自然人与后人类之间存在差别的标准和依据。然而,要认清楚人是什么,需要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本质”学说。根据哈佛大学波义尔(Matthew Boyle)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人在类别上(in kind)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不在于人类拥有某些动物所缺乏的那些额外的认知机制,正如动物与植物的区别不在于动物拥有植物所不具备的某些额外的生物学特征。在某种层面上你可以说一棵树是一个能动者(agent)——一棵老树被伐倒了,到了春天它又长出新的枝叶,它的确是主动在“做”生长枝叶这件事,而不是说这件事被动地在它身上发生。然而,对一棵树来说,它虽然具有目标导向,但是这种目标导向的行为截然有别于动物。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动物作为能动者拥有目标导向。这不仅仅意味着动物能够做一些植物所不能做的事,而且,我们是以全新的方式来谈论动物的“做事”。你可以说植物的根系把石头缠住,但是更贴切的说法是,它的根系是以缠住石头的方式生长着。一块石头此刻出现在这里,并没有对植物的根系生长添入新的内容。但是,动物的行为则与此时此刻的环境紧密关联,对当下环境的描述,能够构成动物行为的内容。同样,无理性的动物和有理性的人类都是能动者和认知者,但动物却是在一种不完善的意义上作为能动者和认知者,我们是唯一能够按照意图(intentionally)去行动的物种。在行动时,我们可以自主决定哪个目标值得追求以及如何追求,我们知道(knowingly)自己应该如何行事。因此,理性意味着“我们以一种极其不同的方式去规导和展现全部的心灵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康德所说的“‘我思’必须能够伴随着我的一切表象”。作为理性的实质的“我思”,就是人之为人的“范畴差异”。因此,只要一个主体符合康德的“我思”标准,无论他所依赖的技术条件多么复杂、多么离奇,这个主体仍然属于人类的范畴。
三、关于转化人类、后人类的几点说明
在下半场的第二场报告中,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计海庆副研究员以《转化人类主义的哲学应对》为题,展开了对“转化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和“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概念的梳理、辨析以及与此相关的几种立场。他指出:可以从技术哲学研究技术与人的进化的角度区分以下两组概念:(1)转化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转化人类(transhuman)、后人类(posthuman);(2)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非人类(nonhuman)。计海庆副研究员首先指出,后人类是在想象中借助于科技的成果影响自身演化的进程,是在未来的某种存在形式,是对未来的一种勾勒,后人类在智力、体力和心理等方面都远远超越现代人具有的能力水平。以现在的社会标准,后人类很难被归类为现在的人类。后人类技术,指那些可以用来改进和提升人类智力、体力和心理能力的科技研究。从范畴上来看,它是生物学意义上未来的人类进化,它不是试图超越人类的生物极限,而是使我们得以去除意识、理性、反省等形而上学封闭性领域的意义,用更大的开放性来描绘人和其他的交流活动。“posthumanism”这一近年来逐渐定型的英文“新”词应该对应中文里的“后人文主义”,意指20世纪末期西方对文艺复兴和启蒙传统所建立起来的对人类理性和人文精神之绝对信仰的质疑与反思。“后人类主义”与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后学”思潮在精神渊源和批判脉络上同宗同源,都是针对“Humanism”(人本主义)。其次,计海庆副研究员强调,“转化人类”是指人类在向后人类演化过程的一个中间状态,即在智力、体力、心理方面已经有了提升,但以现有观念而言还属于人类(名词:中间状态的人类,动词:把人类转化)。但“转化人类主义”是一种极端的进步主义的人类观,是相信并希望在科学技术的帮助下,人类将演化为某种新物种,现存的社会制度、观念、伦理等也将随之发生根本变化。但在价值判断上,转化人类主义认为技术是值得肯定的,是积极的,应该推进它。准确地说,转化人类主义是一个社会运动,是由一群社会学家正在推动的社会运动,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如福山2004年的一篇文章所指出,转化人类主义致力于把人类这个物种从生物性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它的目标就是利用生物技术使人变得更强壮、更聪明并且可以长生不老,它是21世纪最危险的观念。但后人类主义与转化人类主义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转化人类主义应该被视为是人本主义的强化,它直接来自对人类完美性的追求,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理性和主体性信仰的承继;后人类主义则恰恰是转化人类主义的反面。
下半场的第三场,来自上海大学的杨庆峰教授做了题为《图像中的“后人类形象”解读》的报告。他认为:传统图像主要是将相似性原则作为图像之所以为图像的基础,在图像对象上也多是呈现经验事物,如人物、动物、食物、城市,等等。当然有一类图像主要呈现的是非经验的事物,如宗教故事、神话角色,等等。在图像艺术家族中,有一类图像题材成为我们关注的对象,即“后人类形象”。所谓后人类形象,即所展示的对象是一种新的实体存在,其特征是人与机器的界限、人与动物的界限变得模糊。从图像史角度考察会得出如下主要结论:首先,“后人类”形象并非是随着当代技术发展出现的新现象,传统图像对此早已触及,所以后人类问题并非新的问题。其次,图像中的后人类形象表征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的形式:(1)传统艺术图像中“后人类形象”表现为想象行为所指的意向对象。从形象上看,后人类表现为人与动物、人与机器的物质性“结合”。在图像艺术中所呈现的后人类形象,主要是通过想象力完成的,这种形象并非是想象的机械结合,而是完整的存在。(2)在超现实主义图像中,“后人类形象”表现为批判意识行为的社会表达。从形象上看,后人类表现为人与机器、技术的“结合”(如本雅明所举的钟表脸)。这与上述想象所指的意向对象是相似的,但是“后人类”被用来作为哲学家批判异化的媒介,是非符号化的。比如,本雅明就批判了机械时代人的物化、人自身成为机器。(3)在当前的电影图像中,“后人类形象”表现为他者的自我反思。科幻电影所呈现的后人类主要是一些他者形象,如机器战警、弗兰肯斯坦等。这种解读不仅仅是批判式的,而是从他者角度开始让我们思索人类的情感和存在的意义。最后,上述图像中“后人类形象”主要是自然结合、想象结合与技术结合的结果。想象结合与其他两种结合形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想象结合是靠想象力把本来不相关的、不存在内在统一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比如人首与羊身的结合(潘神)、人首与蛇身的结合(女娲、美杜莎),等等。想象力消解了自然层面的内在统一性。“自然结合”是基于生命的结合,也可以说是基于统一性的结合。自然的结合就是内在统一性充分表达出来的结果。“技术结合”表现为人与自然物、人与机器的物质性结合。这种物质性的结合的实质需要从哲学上加以解释。
在讨论环节,来自科学史、科学技术哲学哲学和机械工程领域的各位专家针对技术时代的主客体问题展开激烈交锋。之后,大家就以下三种观点达成共识:(1)无论当代技术如何发展,人与动物、机器之间总有一条清晰的界线,人的主体性和理性使得人永远区别于他者,人永远是人;(2)当代技术可以模拟、增强或者改造人类的智力、情感、意识等,人可能会被技术替代,甚至身体可能会消解;(3)当代技术发展会对主体与客体的传统认知方式产生冲击,但是人一直是人,而对主体和客体的理解则会更加多元和丰富——主体表现为多元主体,主客体之间的分界是模糊的。
最后,华东师范大学的安维复教授进行了点评和总结。他对年轻人能不断追踪学术前沿给予了肯定和鼓励,与此同时,也语重心长地与年轻学者交流了自己做学问的体会、经验和教训。他希望大家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忽视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和梳理——毕竟这才是科学研究的生命之根。无论研究科学哲学还是技术哲学,都应当扎根于科学与技术思想史的经典文献,对相关的概念、范畴进行追本溯源的梳理和界定,以夯实研究基础,拓宽研究路径,不断做出扎实的成果,进而真正推动科学技术哲学学科的发展。
(责任编辑:韦海波)
闫宏秀,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张帆,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