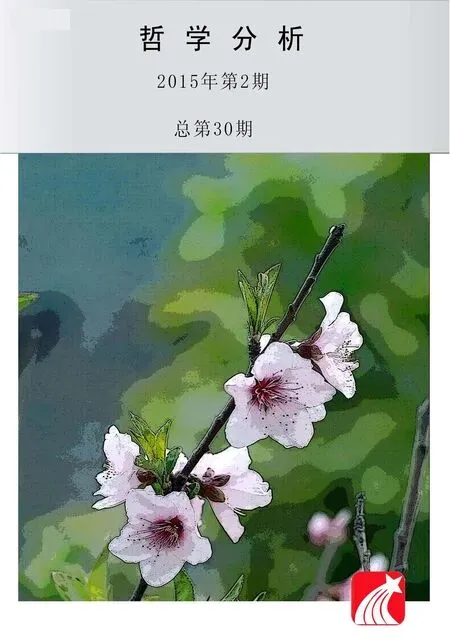信息本体论何以可能?
——关于邬焜信息哲学本体论观念的探讨
邓波
信息本体论何以可能?
——关于邬焜信息哲学本体论观念的探讨
邓波
信息本体论是邬焜信息哲学体系的基石,也是其用来判断信息哲学带来哲学“革命性”转向的最终依据。由于哲学“教科书体系”及日丹诺夫哲学史观念的长期影响,包括邬焜在内的众多学者往往把“本体论”误认为是关于世界存在的“本原论”,把西方哲学史简单化、公式化地曲解为物质—精神二元结构的演变史。通过对西方本体论传统基本观念的梳理,并以此为基准来对邬焜的信息本体论进行较为深入的讨论,可以发现,它不是严格意义的本体论,而是响应信息时代精神的自然哲学。以自然主义的哲学取代其信息本体论,邬焜的信息哲学体系仍然能够成立。
邬焜;西方本体论;信息本体论;哲学革命
信息本体论无疑是邬焜信息哲学最为重要、最为核心的基石。如他所说:“正是在这一新的本体论观念、新的世界存在图景的基础上,信息哲学的其他领域的开拓,如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信息社会论、信息思维论等的开拓,才可能有一个合理立论的根基,从而将信息哲学的众多学科、领域、观点和理论在本质上统一为一个有机联系和综合的整体构架。”①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34页。因而,任何欲对其思想进行认真严肃的研究、评价,乃至任何争议,都不能绕开他的信息本体论,都不得不追问这种信息本体论何以可能?
近些年来,邬先生侧重于与西方哲学进行对话,力图强调信息哲学给整个哲学发展带来了“全新的哲学革命”。他始终强调对话必须在本体论的层次上进行,才能真正显现出信息哲学转向的“革命”性质。然而,贯穿西方哲学史的本体论在形态上虽有多种变化,但其保持不变的基本精神究竟是什么?它与邬先生持有的“本体论”观念是否一致?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对话的有效性,当然也必然影响着他对其信息哲学转向带来了“人类哲学的发展从未实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性哲学革命”①邬焜:《存在领域的分割和信息哲学的“全新哲学革命”意义》,载《人文杂志》,2013年第5期。这一判断的有效性。
一、邬焜信息本体论产生与发展的境域
邬焜先生对我而言亦师亦友,他长我10岁,原是同一所高校的同事,也是使我决心放弃原来的专业踏上哲学之路的最早引路人。可以说,我应该算与邬先生信息哲学思想构造过程比较贴近的“知情者”之一。本打算从我与他交往的亲身经历来评说其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但由于篇幅限制,只好从略。概括地说,邬先生的信息哲学产生与发展于如下的境域:
首先,20世纪80年代,对科学精神的敬仰甚至崇拜,对技术进步的推崇乃至渴求,对现代物理学、“老三论”、“新三论”等讨论之热烈,构成了当时中国自然辩证法界的基本语境。在此背景下,邬焜先生自然对科学抱有极其坚定的信念,认为哲学的建构必须以科学为基础,主张“在一般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所孕育和展现出来的哲学自身的发展”②邬焜:《从信息世界看哲学的发展及其根本转向》,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哲学必须走“科学化”的道路。虽然他本科专业是哲学,但从学生时代至今,邬先生都特别注重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他广泛涉猎现代自然科学的多个领域,特别注重对信息科学、系统科学、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自组织理论、超循环理论、突变论、协同学、复杂性科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科学原著(非科普作品)的深入研读。无疑,其信息本体论的创立有着深厚的实证科学基础。
其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唯科学主义在国内学界盛行,尤其是自然辩证法界,要么套用“教科书传统”的哲学原理、范畴去解释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认为自然科学的新发展与那些原理、范畴相符合,于是,欢呼科学的新成果再次证明了它们“放之四海”的真理性;要么紧跟自然科学某些领域的新进展进行哲学解读,其中不乏一些有真知灼见的成果,但大多数研究只是轻率地把具体的科学成果直接生搬硬套地移植到哲学中来,“创造”了许多没有哲学学术价值的“新理论”、“新范畴”。邬先生可以说也是一位坚定的科学主义者,但他决不唯科学,决不亦步亦趋地唯“科”是瞻,而是强调对有哲学意蕴的科学成果必须进行“哲学化”的反思、批判、归纳、抽象、概括与提升,才能凝炼出真正的哲学成果。比如,他关于信息的哲学界定就是在申农、维纳等科学家关于信息科学定义的基础上,经过其哲学化的反思、批判,思辨地提炼出来的。
其三,新中国成立至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哲学界的统治地位毋庸置疑。与时俱进,跟随时代而发展,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活的灵魂,但由于极左思维方式的长期影响,它被教条地僵化为众所周知的哲学“教科书体系”,这个完全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体系存在两个最根本的方面:一是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版块构成的原理和范畴;二是日丹诺夫的关于整个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发展史,并把它与阶级利益联系起来的政治化准则。它们成为长期盘踞哲学及哲学史教学与研究不可逾越的“金科玉律”。20世纪80年代初,哲学界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改革需要哲学,哲学需要改革。”对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批判、争论、重构,各种观点可谓风起云涌,热闹非凡。邬先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可以说,哲学“教科书体系”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挥之不去的双重效应:一方面,他痛彻地不满意它的教条、封闭与僵化,极力主张利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来改造它;另一方面,它却在其意识甚至潜意识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在哲学改革的浪潮中,一种主流性的观点认为“教科书体系”没有体现出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作为“世界观”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的革命性意义,仅把实践观点限制在认识论的狭小领域,所以,“传统教科书体系不是在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往前走,甚而可以说是反向逆行,甚至退回到本体论哲学和朴素实在论”①高清海:《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反本体论成为当时哲学改革的一个显著特征。邬焜断然不同意这种“去本体论”的做法,主张在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来改造和发展本体论,但他所具有的本体论观念却与“教科书体系”是一致的:本体论就是探究世界存在的本原——或用邬焜的说法——“世界存在图景”的学问。不同的是,他要在信息科学“哲学化”提升的基础上,以及应用黑格尔关于事物相互作用通过“中介环节”辩证转化的思想,来改造“世界存在图景”,原创性地把“自在信息”引入传统本体论层次的存在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虽然不赞同“教科书体系”的物质本体论,但并未抛弃本体论这一概念,往往在广义上采用各种各样的本体论提法:比如,实践本体论、社会本体论、人类本体论、结构本体论、语言本体论,等等,莫衷一是。然而,可以说包括邬先生在内的众多学者并没有对“本体论”(ontology)这一来自西方,并贯穿西方哲学史两千多年的核心哲学形态进行过学理上的深究。
其四,由于接受了“教科书体系”的本体论观念,并以它为其哲学改造的前提与对象,邬先生自然也接受了“整个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发展史”的断言——当然,剔除了政治化的因素,力图与这种框架下的西方哲学史乃至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全面对话,从而在本体论的最高层次显现出信息本体论的产生在哲学史上的价值。于是,邬先生断言,西方哲学无论是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到中世纪的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还是从近代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认识论转向,到康德的物自体不可知论、黑格尔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乃至于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和现象学转向,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由于它们始终没有突破本体论上物质和精神的二元结构关系,所以都不可能造成哲学上的根本转向!而“自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兴起的信息哲学的相关研究,也许能够为人类哲学的发展提供第一次具有根本性变革意义的理论转换。因为,正是信息世界的发现为人类提供了对存在领域的构成和人的认识方式的复杂性的新看法,从而打破了传统的物质和精神、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并由此为哲学本体论、哲学认识论、哲学进化论、哲学方法论、语言哲学论、实践哲学论、人的本质与人的生存论、人类生产与人类社会论、价值哲学论等领域带来全新意义的根本性变革。”因而,邬先生满怀信心地认为“信息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①邬焜:《哲学基本问题与哲学的根本转向》,载《河北学刊》,2011年第4期。。
显然,邬先生的断言与信心来自哲学“教科书体系”中存在严重误解的本体论观念及其在唯物与唯心僵死框架内对西方哲学史简单化、标签化、公式化的描写。如果要与西方哲学展开真正有学术价值的严肃对话,深入地理解它的思想精髓是对话的必要前提。
二、西方本体论的传统观念及其对它的误解
本体论这个词,因沃尔夫(1679—1754)的使用,才在西方哲学界流行起来。沃尔夫对其给出了至今仍获得普遍认同②《不列颠百科全书》、《美国大百科全书》等工具书对“本体论”词条的解释大都以沃尔夫的定义为基础。的定义:“本体论,论述各种关于‘ου(即on——笔者加)’的抽象的、完全普遍的哲学范畴,认为‘ου’是唯一的、善的,其中出现了唯一者、偶性、实体、因果、现象等范畴,这就是抽象的形而上学。”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89页。他认为形而上学属于理论哲学,它包括:本体论、宇宙论、理性灵魂学、自然神学。其中,本体论居于核心、首要地位,次一级的是宇宙论,是探讨关于形体、关于世界的抽象形而上学命题的普遍学说。按照这个定义,本体论是形而上学的核心,但决不是整个形而上学。反过来,也不能把形而上学或它的其他组成部分等同于本体论。本体论既不是关于世界抽象本质原理的宇宙论,也不是关于世界存在本原的自然哲学。那么,本体论①传统上,除了“本体论”这个来自日本的译名,还有“万有论”(陈康)、“有论”(贺麟)等译名。新近研究主张的汉译主要有“存在论”和“是论”两种。鉴于“本体论”已在学界广泛流行,约定俗成,本文仍采用此译名。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逻辑上讲,把“on”首先从语言上作为系动词“是”(to be)去加以理解是打开本体论之门的关键钥匙。从词源学上说,古希腊有两个表示“存在”的实义动词:和前者强调从动态的角度来表示“存在”,它来源于动词φυω,表示无常、无驻、流变、涌现等变化不定的过程,汉译为“自然”。因此,最早的希腊哲学被称为“自然哲学”(physics),其重要特征之一正是可感世界乃至其本原都具有不确定性。后者强调从静态的角度来表示“存在”,本来作为其来源的实义动词es,指的是生命、活着、存在着(existence),也强调动态,然而,随着εστι(即on)演变为系动词“是”(to be)及其确定性的名词“存在”(Being)之后,其源始的动词意义就被遮蔽了。巴门尼德认为可感世界变动不居,根本不可能抓住事物的真相,而不同的自然哲学家往往把不同的某种特殊可感的东西当作世界的本原,由此又带来无休止的争议、混乱与怀疑。于是,他就用“εστι”(on)这个同样表示“存在”的词取代“”(自然),以便在确定性中把握住真实的存在。这样,哲学才得以摆脱依赖可感经验的“意见之路”,走上“真理之路”,实现从早期自然哲学到本体论的转变,从此开启形而上学(meta-physics)对自然哲学的超越。
巴门尼德这样做实际上有着深厚的语言与文化背景。美国学者卡恩(Kahn)曾对古希腊以荷马史诗为首的古典文献中使用了“on”的句子进行了大量统计分析,发现其中作为系动词(to be)的用法占80%—85%,其他如表示“存在”、表示“真”等各种用法加起来不足20%,而且这些语义、用法来源于系动词。②参见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57-61页。这充分说明:在古希腊的日常语言中,系动词“是”构成的主谓结构陈述句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主要用这种句型来进行思考与表达。哲学家的理性思辨,反过来又推动了日常语言向哲学语言的转化。巴门尼德采用的“存在”(on,to be)一词,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单词句”,实际上它隐藏着构成命题的主谓结构(S是P),可分为两种句型:(1)无补语的主谓结构(S是),此时该词作存在动词用,意为“某存在者存在着”,即“存在本身”;(2)有补语的主谓结构(S是P),此时该词作系动词用,意为“某存在者是如此”。这两种结构合起来,既表示了事物保持自身同一性的确定性存在,又表达了事物是如此这般或是其所是的存在。①参见杨适:《古希腊哲学探本》,第222-226页由于只有通过系动词“是”才能构成命题,而唯有命题才能展开真或假的判断,哲学要辨识真假,要追求真理,就必须从“是”何以构成范畴、命题的“先验构造”为思想的起点,这正是西方本体论源起的关键。
柏拉图的本体论从根本上讲正是来源于对有补语的主谓结构命题(S是P)的思考,举例来说,当面对具体事物时可这样下判断:花是美的,人是美的,衣服是美的……,等等。在这些命题中,主词是个别的、具体可感的,但谓词“美”却是共同的、普遍的。然而,这个普遍的“美本身”是什么?何以存在呢?柏拉图此时已把谓词“美”置于主词的位置来考虑,已进入“是者”无补语主谓结构命题(S是),即进入追问“存在者”本身的思考。柏拉图认为“存在者”本身只能是与一切具体可感的事物相分离的。没有时空的、不生不灭的、永恒的、完善的存在者。这样,他把“存在者本身”(Being)规定为普遍的、超验的、确定的、永恒的“相”的世界。在相论的基础上,柏拉图力图通过辩证法,以“存在者”为核心,建立起“相”之间具有逻辑必然联系的“通种论”,形成了西方本体论传统的第一个思想体系。
亚里士多德早、中期反对柏拉图的本体论,重视经验研究,但他仍然按“是者”这一“单词句”有补语的主谓结构命题(S是P)进行逻辑思考,首先把作为主语S范畴化为“实体”(ousia),并称之为“第一实体”,指现实可感的“这一个”。再将表示本质(essence)、属性(beingness)的谓语规定为实体(第二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10个范畴。这些范畴形成了把握世界的工具。在《物理学》中,他进一步把现实可感的“这一个”(实体)归结为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并把质料当作第一实体。但他后来发现质料是无规定的,达不到“存在者”本身,于是开始向柏拉图的本体论回归。②参见G.E.L.Owen,“Logic and Metaphysics in Some EarlierWorks Aristotle”,in Logic,Science and Dialectic, Collected papers in Greek philosophy,edited by Martha Nussbau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关于“作为存在的存在”思考,侧重于从“存在者”隐含的无补语的第一个句型(S是)来思考“存在者本身”,来追问“第一实体”,发现它不仅是最普遍的范畴,而且还必须是唯一的、永恒的、不动的、作为终极原因的最高实体范畴,其他范畴来自它并依附于它才能存在,它就是“纯形式”。任何一门特殊学科都要使用以这样的“第一实体”为核心的范畴及其推理体系,以它为前提和基础。这个意义上的“第一哲学”,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在此本体论的基础上,“第一哲学”还包括他的宇宙论,宇宙就是从潜在质料向现实形式的连续转化生成过程,这个“永恒过程”本身作为整体,必然是不动的,是所谓的“不动的动者”,也就是“神”,它并非宗教意义的“神”,而是包含生成演化于一身的“纯形式”。
中世纪的神学家将本体论应用于神学,但对其基本观念并没有太多的发展。近代认识论的兴起给本体论带来了冲击,但认识论在相当程度上仍然是以本体论为基础或参照的。康德把本体论范畴改造为整理可感世界经验的先天综合的认识形式,认为传统本体论对超验本质世界的把握是独断的、矛盾的,“物自体”作为实体是不可知的。面对经验主义者,特别是康德对本体论的批判,黑格尔创造性地提出了“实体即主体”的本体论原则,把近代认识论带来的“主观性”原则与以亚里士多德为主的古代本体论的“客观性”原则融为一体,实现了“实体”的能动性,认为主观精神不过是绝对精神(实体)能动地自我发展的一个环节,人的认识实际上就是绝对精神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其逻辑学研究绝对观念作为纯粹思想的范畴、概念的自我规定与辩证展开,它显然就是黑格尔的本体论。
总而言之,西方传统本体论的基本观念可概括为:作为第一哲学,本体论是以思想本身的范畴及其逻辑展开的先验原理为对象的学问。
在理解西方本体论传统观念的原意之后,我们再来谈一谈“本体论”这个译名以及我们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对ontology的误解。陈康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指出这个译名不准确。俞宣孟教授更是认为该译名不但不准确而且十分有害:“‘本体论’这个译名最大的危害是,用它译ontology牛头不对马嘴,但却容易使我们的同胞望文生义,由它而想起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体用’、‘本根’的论述,于是在中国哲学中勾勒出一种‘本体论’,当作是与ontology相应的东西,其实是南辕北辙。”①俞宣孟:《本体论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中国人总是强调“言之有物”的思维方式,把“ontology”望文生义地视为某种“言外之物”的“本体”之学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而这种思维习惯与“教科书体系”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核心原则结合在一起,导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心目中,本体论就是关于世界存在的本原论:“世界上纷繁复杂的事物现象,有没有一个统一的本体或本原,作为它们存在的共同根据?这个本体是物质性的东西还是精神性的东西?本体和事物现象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是历来哲学家们所要回答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哲学理论就叫本体论。”②冯契等:《中国哲学范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0页。
邬先生显然持有上述意义的本体论观念:“广义的‘存在’即‘有’,它是世界上所有事物和现象的统称。所有形式的哲学对世界本原、本性的追问,无不是从对存在领域的构成范围的思考开端的。”③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第35页。他只是不满意这种本体论将存在领域分割为物质和精神二元的教条,以及把客观实在等同于客观存在的推论,认为它们“只是未经科学考察或逻辑论证的两个先验的观念”而已。邬先生或许会认为,我们中国人完全可以创造自己的本体论观念,根本不必跟着西方人的本体论观念走!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自创一套自圆其说的本体论观念及体系。但是,当邬先生要与西方哲学史及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对话时,就不能不对作为西方哲学传统核心的“本体论”之本意弃之不顾。
三、关于邬焜信息本体论的探讨
按照上述西方本体论的传统观念的基本精神,我们现在来讨论邬焜先生的“信息本体论”究竟意味着什么?究竟何以可能?是否确实带了哲学的“革命性”转向?
(一)关于本体论的对象问题
西方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是以思想本身的范畴及其逻辑展开的先验原理为对象的学问,它并不直接以现实可感的世界为对象,因而它还不是世界观、宇宙论,更不是自然哲学,只为各种世界观、宇宙论得以思想提供范畴、原理等逻辑前提和思维范式。邬先生明确地认为他的“信息本体论”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把信息首先看作是一种存在,而不是仅仅把它看作是一种方法,这其实就等于确立了一种新的本体论的观念。由这种新的本体论的观念引出的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即是一种新的世界存在图景。”①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第34页。把信息看作是一种存在,这里的“存在”指的是现实世界中的某种存在,即他所说的与物质同在的“信息体”。显然,邬先生的“信息本体论”是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
(二)关于信息本体论的思想起点问题
邬先生如是说:“广义的‘存在’即‘有’,它是世界上所有事物和现象的统称。所有形式的哲学对世界本原、本性的追问,无不是从对存在领域的构成范围的思考开端的。这便产生了种种关于存在领域分割的相关理论。”②同上书,第35页。不用说,他的信息本体论也必须从存在领域的分割开始。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存在者”,一切事物的总和就是“存在”领域,也即世界整体,这是自明的,无须论证。以此为前提,追问世界的本原,必须从世界整体的构成分类开始。然而,西方本体论却是从反对追问世界本原的早期自然哲学登上舞台的,它以思想本身为对象,必然以对思想本身的追问为起点,更具体地说,追问从隐含真理性“命题”的“存在者/是者”范畴开始。
(三)关于本体论的最高范式问题
邬先生可能会这样反驳:所谓西方本体论不就是强调从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的逻辑规定与推演开始进行思考的吗?他的信息本体论就是从“存在”范畴开始的啊!前面我们说过,“存在”范畴是隐合着两个句型的“单词句”:“某存在者存在着”(S是)即“存在者本身”和“某存在者是如此”(S是P)。或许,在邬先生看来,第一个句型没有补语,也就没有任何规定,只是同语反复,它是自明的,无须讨论。而后者事关“存在者”的本质类别,牵涉到邬先生所说的“存在领域分割”,他一定赞同关于“存在”的研究就应该从第二个句型开始。在抛弃了“存在者本身”这个本体论最普遍的、最高的、最为基础的范畴起点的追问之后,在邬先生看来,“存在领域的分割”就成为本体论的最高起点。然而,从西方本体论的观念看,本体论之为本体论的关键却在于第一个句型,即对“存在者本身”的追问。它才是西方本体论传统的最高范式,它按同一律规定了一切思想的起点,同时,按“思想与存在同一”的原则,它也意味着规定了全部存在的起点。
(四)关于按逻辑重新分割存在领域的问题
邬先生力主首先从逻辑上对存在领域进行新的分割:“如果我们假设:客观的= P;实在的=Q,那么,客观的反题‘主观的’就是劭P(读‘非P’);实在的反题‘不实在的’就是劭Q(读‘非Q’)。现在我们在这四个命题中建立两两组合的合取式,我们便可以得到如下六个逻辑公式:P∧Q;P∧劭Q;劭P∧Q;劭P∧劭Q;P∧劭P;Q∧劭Q。除去后面两个违反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的‘永假公式’,我们将其余四个公式所对应的字面含义分列如下:P∧Q=客观实在;P∧劭Q=客观不实在;劭P∧Q=主观实在;劭P∧劭Q=主观不实在。”①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第36页。这些推理从纯逻辑形式看,似乎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1)为什么存在领域的分割要从“客观的”和“实在的”这两个概念开始?它们是什么样的种或属?能否进行两两组合?这是否意味着它们其实只是“客观实在”的人为分裂?(2)客观的反题为什么不是“不客观的”,而是“主观的”?这是否已经预先暗含着主观—客观、精神—物质二元对立的假设?(3)更进一步,仅从形式逻辑就能对存在领域进行合理周全的划分吗?实际上,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特别是黑格尔,他们的本体论思辨推理在形式逻辑的基础上大都采用辩证推理。
(五)关于四个“逻辑公式”与世界中存在者的对应问题
邬先生认为他按照形式逻辑重新分割存在领域所得到的上述四个“逻辑公式”,在现实世界中是有其对应所指内容的:(1)关于“客观实在”,按照列宁的定义就是指物质,邬先生把它规定为“直接存在”这一“哲学范畴”,作为“各种物料的总和”,该范畴可根据现代科学理论将各种物料归类为实体和场这两种具体存在形式,同时,该范畴还包含着对直接存在物的存在方式和种种相互作用关系的规定;(2)关于“客观不实在”,邬先生用“水中月,镜中花”等日常现象和自然科学所揭示的种种现象为例子,并借助列宁认为事物间具有类似于反映的特性等思想,认为找到了一个“客观不实在”的存在领域,即信息世界,并把它规定为“客观间接存在”,也即“客观信息”;(3)关于“主观实在”,邬先生按照唯物反映论,认为它是没有指谓的;(4)关于“主观不实在”,邬先生认为它“显然指的就是意识、精神之类的现象。它们是主体对客体的主观反映和虚拟性建构,是主观的,不实在的”①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第37页。。他相应地把它规定为“主观间接存在”,也即“主观信息”,并进一步分为“自为信息”与“再生信息”。因此,在邬先生看来,“整个宇宙(世界、自然)中的一切‘存在’都可以划归客观实在(对应物质)、客观不实在(对应客观信息)、主观不实在(对应精神,即主观信息)这三大领域”②同上书,第37页。。
问题在于:首先,逻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确实是本体论的重大问题,巴门尼德、亚里士多德依靠“思想与存在同一”的原则来解决,柏拉图靠现实世界“分有”本质的“相”来解释,黑格尔靠绝对精神将逻辑“外化”来实现,早期维特根斯坦直觉到语言与世界共有相同的逻辑结构,但为什么会有这种对应关系却不可言说?那么,邬先生又是依靠什么来解决这一大问题呢?在我看来,他从逻辑上得到的概念形式,与从解释上赋予它的内容仍然是彼此外在的。其次,本体论对概念的规定,始终坚持范畴、概念从“存在者本身”这个最普遍、最基本、最高的范畴开始,并有自上而下的、纯逻辑的、非经验的演绎推理或辩证论证,在这样的推理中,概念的形式与内容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我们来分析一下邬先生的概念规定:
(1)把客观存在等同于物质,邬先生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列宁的物质定义,但认为它是在把存在领域无逻辑证明地划分为物质与精神两大领域的前提下,通过物质和精神的相对关系得出的结果,这样的物质定义还是抽象的。他进而按恩格斯的定义,把物质具体界定为“各种物料的总和”。这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质料,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曾赋予质料第一实体的地位,但在形而上学本体论中质料却是无任何规定的、潜在的范畴。邬先生显然避开了本体论的思辨推理,从经验性的现代科学成果概括出实体和场来规定直接存在物,并连同它们的存在状态和运动方式一起,构成了“直接存在”这一哲学范畴。这样做倒正好符合邬先生的科学主义立场,却远离了本体论。
(2)从“客观实在”范畴推出“客观不实在”范畴,从“直接存在”范畴推出“间接存在”范畴,这些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把“客观不实在”等同于“间接存在”,更进一步等同于信息,并不具有逻辑必然性。对此,邬先生借助日常经验和科学事例来进行说明,比如:天上的月亮是客观的、实在的直接存在,而水中的月亮是客观的但不实在的间接存在,“这样,我们便把实在和直接存在看成是同等程度的概念,把不实在和间接存在看成是同等程度的概念。从间接存在的角度看,间接存在是直接存在的反映(广义的),从直接存在的角度看,间接存在是直接存在的显示。”①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第38页。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而间接存在作为直接存在的显示又被邬先生规定为客观信息,于是,“客观不实在”=“客观间接存在”=“客观信息”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不用多说,这同样的论证与西方本体论非经验推理的理性主义传统不一致。
(3)关于精神或思想的领域,邬先生坚持从认识论的唯物反映论出发,他认为:“意识是一种反映,在意识之外有一个直接存在的对象,在意识中有一种关于这个对象的摹写、知识。因此,主观存在归根到底是反映直接存在的一种间接存在。”②同上书,第38页。进而,“意识作为一种主观呈现着的现象,它本身就是显现着的,所以,它本身就是信息活动的一种形式(高级形式)”③同上书,第46页。。由此,邬先生为认识论规定了信息本体论的基础。西方形而上学就是通过本体论范畴和原则来从思想上规定“世界”的。“世界”在思想中,在思想中的“世界”里,“思想”又如何规定?在“世界”中占据什么位置?也就是说,从“实体”如何推理出“思想”的规定?按柏拉图的“相”论,整个“相”的世界实际上就是“思想”的世界,“思想”本身的规定也就是“存在者/是者”的规定,人的灵魂或心智通过对“相”的回忆,通向“思想”。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整个世界由充满整个宇宙的宇宙灵魂“努斯”推动,它就是由纯粹的“思想”构成的最普遍最高的实体(纯形式),“努斯”在人之中的神圣功能就是让人进入哲学沉思。在黑格尔那里,人的思想不过是绝对精神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一个环节,人的意识不是外在地反映了世界,而是绝对精神自己认识自己的过程。
在近代认识论产生之前,古代人还没有明确的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精神—物质的二分概念,意识作为“主观不实在”反映客体这个“客观实在”当然根本就无从谈起。如果借用这些近代概念,那么可以说,古希腊人的“思想”领域恰恰反过来是超验的“客观实在”的领域(“实在”即真实的、实体的、本质的),可感的物质世界作为流变的现象却是“客观不实在”的,人的主观沉思通过逻辑或辩证法上升到客观思想的领域就达到了“主观实在”(也即从主观思想上回到客观实在)这一邬先生认为无所指的领域,而人的思想如果仅停留于经验的、现象的可感世界,充其量它只能达到“意见”这一“主观不实在”的领域。由此可见,从不同的哲学立场出发,对“实在”这“第一实体”就会有不同规定,也将赋予四个“逻辑公式”不同的意义,它们只有形式上的必然性,而没有思想内容上的必然性。
(六)关于信息作为本体论范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问题
邬先生对已有的关于信息本质的种种哲学解释进行了分析,认为它们绝大多数“还只是停留在与已有的实用信息科学的解释或哲学的已有范畴间的简单比附上”。但是,其中有两种思想对邬先生还是有重要影响的,一个是维纳的观点:“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①维纳:《控制论》,郝季仁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3页。,以及“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②维纳:《维纳著作选》,钟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4页。。另一个是民主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克劳斯(Georg Klaus)的观点:“在意识和物质之间存在着一个‘客观而不实在’的信息领域。”③格奥尔格·克劳斯:《从哲学看控制论》,梁志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这两种观点促使邬先生意识到必须把信息作为某种相对独立的“存在领域”来进行思考。更深入一步说,对信息本质的探索要具有真正的哲学品位,就必须把它纳入本体论的范畴体系,并在这个以“存在”为核心的“存在范畴之网”中得到内在的逻辑规定,成为这个网上不可缺少的环节。最终,他给出了一个本体论的信息定义:“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况的自身显示。”④邬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第46页。
下面我们按照西方本体论传统的基本观念来进一步讨论“信息”作为本体论范畴的可能性与必要性:(1)坚持唯物主义本体论,就必须以“物质”范畴作为最普遍、最基础、最高的“第一实体”,即按本体论的第一个句型(S是)来规定“物质本身”。前面我们说过,邬先生按列宁的定义把它规定为“客观实在”后,就没有进行深究了。(2)在“物质本身”即客观实在规定的基础上,按照本体论的第二个句型(S是P),应该进一步来规定“第一实体”的“种属”(第二实体)和“偶性”。邬先生用自然科学的分类(实体和场)来规定“种属”,那么,信息作为物质存在方式和状况的自身显示,作为物质的属性,作为与物同在的“信息体”,应该被置于什么位置呢?也就是说,信息显示着作为“第二实体”的“种属”及种种“偶性”,那它与实体和场这些作为种属的“第二实体”是相并列的吗?它与其他范畴规定的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状态等偶性相等同吗?或者,它与它们既不相同也不并列,而是相对独立的、新的“第三实体”?如此关键的问题邬先生并没有给予解释与论证,以至于让我质疑在本体论中增加“信息体”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由此想到奥卡姆的经济原则“若非必须,请勿增加实体”。(3)西方本体论传统还有一种说法,本体论是从思想探讨事物本质的先验范畴和原理的研究,信息作为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况的自身显示,作为“客观不实在”的间接存在,它涉及的只是显现出来的现象,而不是本质实体,因此,它在本体论中没有位置,而在现象学这一研究事物“显现”的学科中大显身手。邬先生或许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现象学是从主体的表象来讨论“事物”的“显现”的,他的信息本体论的关键在于讨论事物自身的显现。(4)本体论传统始终强调超越经验的、纯逻辑的规定与推理,从经验科学提升而来的“信息”概念,如何与之相融?邬先生的“双重批判和双重超越”能否真正解决此问题?这些仍然是悬而未决的,比如,申农、维纳关于“信息”的科学定义与邬焜的哲学定义之间究竟在思想上有什么样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
综合以上六个方面问题的讨论,我的结论是:邬焜先生关于“信息本体论”的论证是不彻底的、不够严密的,甚至是可疑的。他为了给“信息”奠定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就将它置入本体论的“存在范畴之网”,力图将“信息”实体化为“信息体”,以确立它相对独立自在的地位。邬先生之所以坚持这么做,认为“信息本体论”不仅可能,而且符合信息时代精神的对本体论的全新改造与发展,它甚至可能给哲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转向,实际上源于他把本体论当作“本原论”的误解,源于他在这种误解的本体论基础上,把西方哲学史当成唯物—唯心二元结构演变史这种哲学“教科书体系”式的曲解。这势必影响他对西方近代认识论转向以及现代西方哲学语言转向和现象学转向“革命性”的评判,反过来,则放大了他自己的信息本体论的学术价值。
本文对邬先生信息本体论的质疑与批评,并不是要用西方传统本体论来强制他的信息本体论,更不是对他整个信息哲学的否定。相反,在我看来古老的本体论在当代已经面临被抛弃的巨大危机,将“信息”本体论化不但不可能,而且没有必要,无须用本体论这个“旧瓶”去装信息哲学这一“新酒”。实际上,从内容的实质看,他的“信息本体论”应该是一种宇宙论或自然哲学。众所周知,西方严格的传统自然哲学是以本体论为基础的,以本体论提供的概念、范畴和原则去观察自然,与经验结合进而解释自然。有的甚至认为,在本体论基础上先构造某种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框架和原理,然后才能进一步开展自然哲学和具体自然科学的研究。这样,自然科学往往就会被禁锢在这些宇宙论或自然哲学的“理性牢笼”之中,这就限制了它生机勃勃的发展,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就是典型,难怪它后来痛遭科学界和哲学界的严厉批判。
去除了本体论的自然哲学依然是可能性的,它可以建立在“自然主义”哲学的基础上。“自然主义”可表述为这样一种立场:不存在高于自然科学自身的真理仲裁者。没有比科学方法更好的办法来研究科学命题,不需要也不存在如形而上学本体论或科学哲学之类的基础哲学来规范科学或科学方法。因此,哲学可以自由地应用科学发现,同时自由地批评无根据、令人迷惑的命题。这样一来,哲学便与科学贯通了。当然,自然主义也不是那种认为现代科学观点就是完全正确的教条。程炼将其总结为:“自然主义者的两个口号,拒绝第一哲学和强调哲学与科学的连续性。”①程炼:《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载《科学文化评论》,2012年第1期。近几十年来,“自然主义”哲学被广泛应用在自然哲学、心灵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认识论、伦理学等领域,产生了大量学术成果。不要忘了,它们从前也曾经是以本体论第一哲学为基础的。
邬先生作为坚定的科学主义者,在我看来,其思想深处本来就是自然主义的,他说:“哲学和科学的统一不能仅仅看成是一种外在的衔接,而应该看作是一种内在的融合;普遍理性和具体感性在人类认识活动中的不可截然分离乃是哲学与科学内在统一的最终根据。”②邬焜:《试论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第1期。去除“信息本体论”的信息自然哲学不仅足以支撑邬先生的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信息社会论、信息思维论等整个信息哲学的体系,而且能够更好地跟随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与科学的张力之间,充满活力地不断发展自身,继续为信息时代的哲学贡献思想,而不至于受到“信息本体论”的羁绊,蜕变成僵化的体系。
(责任编辑:韦海波)
B94
A
2095-0047(2015)02-0028-14
邓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工程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