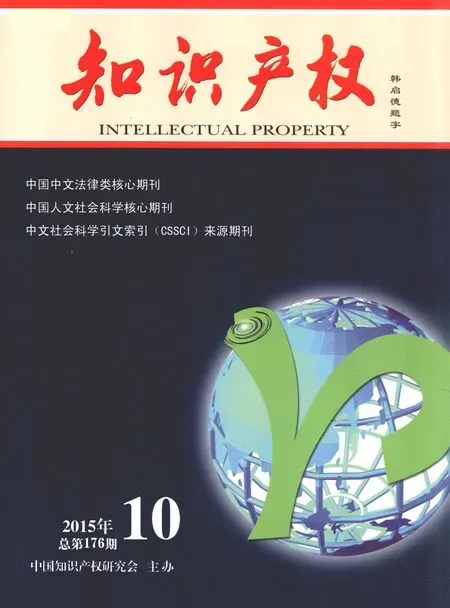从新百伦案看我国商标侵权赔偿原则的司法适用
刘小鹏
从新百伦案看我国商标侵权赔偿原则的司法适用
刘小鹏
内容提要: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因为权利人举证困难等原因,全面赔偿这一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基本原则在实践中难以适用,而作为补充性原则的法定赔偿被滥用。人民法院应当充分运用证据规则,坚持全面赔偿原则,查明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获利,考虑商标的无形财产属性以及权利人难以举证对计算损害赔偿的影响,建立法定赔偿的量化标准体系,使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达到加强保护商标权的效果。
商标侵权 损害赔偿 全面赔偿原则 法定赔偿 证据规则
2013年7月,美国知名运动鞋品牌“New Balance”因在中国市场销售中使用“新百伦”字样,被广州市自然人周某提起商标侵权诉讼。广州中院经审理认为,原告周某享有鞋、服装等商品上的“新百伦”注册商标专用权,被告“New Balance”在中国的关联公司新百伦贸易(中国)有限公司构成侵权,于2015年4月21日判决该公司赔偿周某经济损失9800万元。①参见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知民初字第547号民事判决书。尽管还在二审过程中,但该案是目前我国法院判赔数额最高的商标侵权案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也涉及到商标侵权诉讼中最关键的赔偿数额问题。
一、商标侵权赔偿原则适用的困境
在侵权诉讼中,当侵权责任确定后,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就成了诉讼的核心内容。确定侵权损害赔偿的范围及金额以全部赔偿为原则,“在因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失时,要完全地赔偿,使受害人恢复到如同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受害人应处的状态。”②王利 明著:《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09页。即以实际财产利益损失为标准确定赔偿数额。目前,这一原则在各国侵权法中已经得到普遍确认。③王军 著:《侵权损害赔偿制度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在知识产权侵权领域,我国法律对此也有规定。如原《商标法》第56条规定如何确定商标侵权的赔偿额。④2001年修订的《商标法》第56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为侵权人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或者被侵权人在被侵权期间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包括被侵权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新《商标法》第63条对确定商标侵权赔偿额有更明确的规定。①2014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商标法》第63条规定:侵犯商标专用权的赔偿数额,按照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确定;实际损失难以确定的,可以按照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定;权利人的损失或者侵权人获得的利益难以确定的,参照该商标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对恶意侵犯商标专用权,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确定赔偿数额。赔偿数额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人民法院为确定赔偿数额,在权利人已经尽力举证,而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的情况下,可以责令侵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侵权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的账簿、资料的,人民法院可以参考权利人的主张和提供的证据判定赔偿数额。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注册商标许可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300万元以下的赔偿。依据上述法律规定,我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以全面赔偿为基本原则,人民法院在确定损害赔偿时,首先应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为依据;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所获利益认定;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难以确定的,参照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上述计算方法均不能确定的,适用法定赔偿。
在立法与学理上,我国对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与适用方法均无争议,但在司法实践中,全面赔偿原则的适用存在障碍,如何确定赔偿数额成了商标侵权诉讼的难题。
(一)法院判赔数额普遍较低,全面赔偿难以实现
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发布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实证研究报告》,自2008年6月我国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以来,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的4768件知识产权侵权有效司法判例为统计对象的商标侵权案件共488件,商标权人损害赔偿诉求平均金额为32.6万元,法院判赔的平均金额为6.2万元。②参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实证研究报告》,2012年8月,第15页。有学者对全国抽样的商标侵权案件的判决赔偿率进行实证分析也得到类似的数据结论。③参见 王正泽:《商标侵权损害赔偿制度的运作及完善》,载《商品与质量》2011年第3期,第10页。
(二)法定赔偿被滥用
法定赔偿是立法考虑到权利人对其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获利难以举证以及维权困难,对损害赔偿的司法救济所作的补充性设计,是确定赔偿额的最后方法。但在实践中,法定赔偿成了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主要方式。根据上述《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实证研究报告》,在商标侵权案件的判赔中,采用法定赔偿标准的案件占全部商标侵权案件的97.63%。④参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案例实证研究报告》,2012年8月,第18页。有人以中国知识产权裁判文书网为信息源,随机选取京、沪、苏、粤等15个省区市涉及商标侵权赔偿的判决书共1073份作为研究样本,发现其中适用法定赔偿的判决书共1049份,占比约98%。⑤参见 徐聪颖:《我国商标权法定赔偿的现状及反思》,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77页。2008年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审结的109件商标侵权二审案中,有90件案判决赔偿,其中89件适用法定赔偿。⑥参见 沈志先著:《知识产权审判精要》,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44页。有人统计了2011年至2014年广东省580件商标侵权案,其中559件适用法定赔偿,占96%。⑦参见 夏芬、叶薛之:《以完善司法证据制度为视角谈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载《中华商标》2015年第6期,第6-7页。自2008年至2013年广州市两级法院审结的商标侵权案中,广州各基层法院所有商标侵权案均适用法定赔偿,广州中院仅有10件案通过证据保全查明了侵权人获利或已有证据足以证明侵权人获利远超法定赔偿额上限判赔,其他案件都适用法定赔偿。⑧参见 广州中院课题组:《知识产权赔偿问题的实务困境与对策》,载《广州审判》2014年3期,第21页。
(三)法院确定赔偿数额的酌定情节简单,同案不同判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等因素。但由于法律对确定赔偿数额的酌定因素规定得较为原则,法官在阐述确定赔偿数额的依据时,往往缺乏严谨的逻辑论证和推导程序,只是对应当考虑的因素进行简单罗列,在判决书中一般表述“根据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影响,侵权时间,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等因素,结合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酌情确定……”,几乎是照抄司法解释的规定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6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侵权行为的性质、期间、后果,商标的声誉,商标使用许可费的数额,商标使用许可的种类、时间、范围及制止侵权行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综合确定。,没有体现个案中确定赔偿额的各个具体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与赔偿额之间的量化关系;且酌定情节的简单导致法官在个案裁判中对确定赔偿额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与随意性,对于案情相同或相似的案件各地人民法院、甚至同一法院判赔数额不同,致使当事人质疑法院裁判不公。
二、商标侵权赔偿原则适用产生困境的原因
在商标侵权诉讼中,全面赔偿原则适用受限而法定赔偿被滥用的原因,主要是人民法院难以解决损害赔偿的计算标准和损害赔偿数额的证明这两个问题。
(一)商标权的无形性导致权利价值与损失难以确定
首先,商标权本身的价值不像普通有形物有一个普遍认可的评估标准。在经济生活中,商标侵权损失主要表现为市场份额的侵占、许可费收益的减少、商誉的损害和淡化等,但这些无形财产损害难以确定。完全赔偿原则要求赔偿受害人的所有可赔偿的损害(或称为法律上的损害),而并非所有“自然”意义上的损害。①周友 军:《我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的证立与实现》,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第103页。因此,适用该原则不能赔偿商标权人的全部损失。其次,商标侵权损害的证据隐蔽性高、专业性强、容易毁损,当事人举证困难。
1.对因侵权受到的损失权利人难以证明
权利人的损失主要表现为产品销售量减少或价格下跌等,本来可以由其掌控的证据来证明,但经济活动中有多种非商标权因素可能共同导致这些情形出现,如权利人经营不善、产品质量变化、市场波动等。因此,权利人的产品在相关市场中的确切份额;损失与侵权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各种非商标权因素多大程度造成权利人的损失;权利人减少的收入是否等同于因侵权所受的损失,权利人对上述事实难以证明。在实践中,侵权人常通过以上思路举证反驳权利人的损失主张。
2.对因侵权获利权利人难以举证,侵权人抗拒举证
侵权人获利主要表现为侵权产品的销售量、售价或利润等。权利人为证明侵权人获利向法院提交侵权人在税务部门纳税登记中记载的销售量或获利情况、向工商部门年检提交的报表资料,以及广告、宣传册所述的销售量等,但这些证据因关联性与真实性不够而难以被法院采信。另外,权利人通过公证购买或投诉工商部门由其行政处罚等方式取得的证据,一般只能作为定性(是否构成侵权行为)而非定量(侵权行为的情节)的证据。而侵权人掌握能直接证明其获利情况的账簿、资料等,但基于种种原因不愿提供。如在“新百伦”案中,原告要求按被告的获利计算损失,而被告不愿提供相关证据,原告只能申请广州中院对被告新百伦公司的财务资料进行证据保全。很多侵权人是小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没有完备的财务制度,向法院提交的账簿资料不完整。即使侵权人有完整的账簿资料,也有可能将账簿资料篡改后再提交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几乎不可能取得完整真实的账簿。
因此,如果机械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权利人维权成本高,败诉风险大,“按照实际侵权损失赔偿,是给商标权利人分配了较重的举证责任,还有可能阻却权利人通过诉讼维权的脚步。”②夏芬 、叶薛之:《以完善司法证据制度为视角谈商标侵权损害赔偿问题》,载《中华商标》2015年第6期,第8页。不利于商标权的保护。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中,法院依权利人申请进行证据保全或依职权调查取证,又会被被告质疑司法不公。因此,要解决权利人举证困难的问题,商标侵权的证据规则有必要进行相应的调整:适当减轻权利人损害赔偿的举证责任;适当放宽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等证据的证明标准;适用证据披露与举证妨碍规则支持权利人的赔偿请求。
(二)现行商标法律制度对确定损害赔偿存在诸多制约
1.损害赔偿法定的计算方式有瑕疵
《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规定:《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的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可以根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商品销售减少量或者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规定了两种计算商标侵权损害赔偿的方法,但“侵权人因为既没有付出开发知识产权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也没有支付知识产权许可费用,因此,侵权人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成本一般明显低于权利人的产品成本。但侵权人常常采取低价取胜的策略,其侵权产品的价格和利润也往往明显低于权利人产品的价格和利润。”①罗莉 :《论惩罚性赔偿在知识产权法中的引进及实施》,载《法学》2014年第4期,第26页。因此,采用不同的方法得出的侵权损失相距甚远。同样,对于侵权人的获利,根据该《司法解释》第14条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条规定:《商标法》第56条第1款规定的侵权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根据侵权商品销售量与该商品单位利润乘积计算;该商品单位利润无法查明的,按照注册商标商品的单位利润计算。规定的两种计算方式分别得出的结果也大不一样。并且,如同侵权人的损失难免受各种非商标权因素的影响,侵权人的获利也不是完全由商标权决定的。在“新百伦”案中,原告要求按被告财务报表显示的利润计算其获利,但被告认为该公司的服务、商品设计、商标、品牌均具有价值,这些利润不是使用“新百伦”标识获得的。
另外,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计算方法均涉及利润这个基准,而企业利润可分为主营业务利润、利润总额和净利润三种,法律没有明确以哪一种利润作为计算基准,实务中也莫衷一是。仍以“新百伦”案为例,原告要求按被告的利润计算其获利,但对被告的利润没有主张一个确定的标准,而是罗列所有能体现被告利润的依据:被告从2011年7月至2014年2月共获利20亿元,根据同行业的利润率计算利润为3.89亿元;按实际营业利润计算,被告财务报表显示达2.8亿元,被告2011年至2014年实际净利润达2.61亿元;根据其在网络收集的数据计算出“安踏”等企业2011至2013年的平均毛利率为35.72%、经营利润率为19.13%计算被告的利润。
2.法定赔偿欠缺量化标准体系,不便操作
商标法对法定赔偿数额规定的幅度较大,即赋予法官足够的裁量权,但对确定赔偿数额应考虑的因素又规定得较为宽泛,没有强调法官须受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和经验法则的约束;同时法官依职权确定事实所需行使的证据认证与证据调查等辅助手段也不足。各地人民法院尽管进行了一些探索,但对于影响法定赔偿数额的各种因素与具体赔偿数额的对应关系及各种因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并没有成功解决;各地区以及各级人民法院法官的理论素养、办案经验、认识感受等也不尽相同,因此,实务中对法定赔偿的理解与适用五花八门,也就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
(三)法官倾向于适用法定赔偿
当前,知识产权案件越来越多,法院行政化非常严重。适用法定赔偿非常简便,可以省去相应的举证、质证和认证环节,大大节约人力和时间,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且法定赔偿是综合各种情节酌情判断,没有严密的计算方法和推导过程,二审法官对一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一般比较尊重,仅因赔偿数额被改判的可能性较小,因此,适用法定赔偿有利于法官应付“发改率”等多项指标的考核。
三、商标侵权赔偿原则适用困境的解决路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确定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困难主要表现在对侵权损害事实如何通过诉讼手段进行客观再现,即人民法院要解决“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损害赔偿的计算即损害赔偿数额的客观确定标准问题,实质上是确定静态化的裁判规范标准;其二是损害赔偿数额的主观证明问题,实际上是其对应动态化的诉讼证明过程。”③唐力 、谷佳杰:《论知识产权诉讼中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2期,第184-185页。
(一)运用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制度
在商标侵权诉讼中,由侵权人掌控而权利人难以获得的涉及侵权人获利情况的证据,权利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侵权人披露;在人民法院作出证据披露决定后,证据持有人拒绝提供或不实提供相关证据,构成证明妨害。“一方当事人通过作为或者不作为阻碍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当事人对其事实主张的证明时,行为人应为其妨碍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④占善 刚:《证明妨害论——以德国法为中心的考察》,载《中国法学》2010年第3期,第100页。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都是力图通过制度设计将举证责任分配给持有侵权证据的一方当事人,使其能够提交证据,从而查清侵权获利这一关键事实。《商标法》第63条是我国首次在实体法中引入上述制度。
1.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的适用程序
(1)当事人申请。证据披露属于法院以公权力介入民事诉讼的证据收集,需要考虑当事人的主观愿望、诉讼请求及法院的审判资源;证明妨碍是为了固定被告侵权的证据,并不是免除原告的举证责任,仍属于原告举证义务的范畴。因此,上述程序必须依当事人申请启动,法院不宜依职权启动。当事人可以在一审或二审法定期间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9条①《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调查收集证据,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对方披露证据,期限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书面申请内容应包括:当事人基本情况、申请对方披露或提供证据的具体内容、该证据的拟证对象、申请原因及主张索赔金额及相关依据等。另外,申请人还应提交:权利证书等证明权属来源和法律状态的证据、对方侵权的初步证据以及法院认为应提交的其他材料。
(2)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权利人应有初步证据证明侵权行为成立以及损害赔偿可能产生;如果侵权明显不成立,不具有请求证据披露的基础,法院不应同意其申请。
(3)双方当事人辩论。如果权利人已提供初步证据支持其主张,同时提出侵权人控制着能证明其权利主张的证据,侵权人有权对其是否持有与应否提交该证据展开辩论。
(4)法院决定。法院应审查侵权人是否持有或持有但不愿出示的证据,该证据是否为认定案件事实的关键,是否权利人在穷尽了其他证明途径后,如缺少该证据案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状态。如果侵权人不愿出示的证据并非确定损害赔偿数额的关键证据,法官不宜机械适用上述规则。在认定权利人的申请请求成立后,法院责令侵权人披露或提供相应的证据,并释明如拒绝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在确定被告应提交相关的证据材料后,法官需向其送达书面的《提供证据通知书》,注明涉案证据的名称、类型、范围、提交的具体时间以及逾期不提交的法律后果;提交的具体时间还应考虑该涉案证据量的大小及合理的在途时间。②张广良:《举证妨碍规则在知识产权诉讼中的适用问题研究》,载《法律适用》2008年第7期,第20页。
(5)双方当事人质证。法院组织双方当事人对侵权人提供的证据进行质证。如果侵权人提供的证据虚假,参照其拒不提供证据的原则处理;如果其提供的证据真实,据此查明其侵权获利情况,必要时可以进行审计。
在“新百伦”案中,原告要求被告公开其财务账簿资料,并申请法院证据保全。广州中院对被告2011年7月后三年的《年检报告》、《审计报告》、《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等资料进行了证据保全,并据此认定被告的获利情况。
2.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的适用条件
首先,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原则上不适用原告主张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形。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是一种为了确定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的司法技术,这种司法技术之所以得以证成,是由于它符合经验法则——如果举证责任者主张的事实不真实,那么相对方不仅不会实施妨碍证明的行为,反而愿意将相关证据开示。”③张泽吾:《举证妨碍规则在赔偿确定阶段的适用及其限制——兼评新〈商标法〉第63条第2款》,载《知识产权》2013年第11期,第43页。
其次,适用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应考虑侵权人有无披露和提供证据的能力。该规则的适用前提是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主要由侵权人掌握,这就要求侵权人具有相对规范的财务制度。法官要依自由心证原则,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行业惯例与日常生活经验以及所申请披露的证据形式、名称、性质、形成时间等,综合判断侵权人是否持有或应当持有权利人申请披露的证据。如权利人申请披露侵权人一定时期的账簿,侵权人如果是一家个体工商户,法律没有强制其建立账簿,因此可以推定侵权人并未持有权利人请求披露的证据,也就不能简单适用上述规则。此外,如果侵权人有正当理由,如因不可抗力导致资料毁损、灭失,客观上无法提供也不应适用上述规则。
3.证据披露与证明妨害的后果
(1)降低权利人的举证证明标准。证明妨害仅是减轻而不是免除权利人的举证责任,在侵权人不提供或不实提供账簿、资料时,权利人仍应提供初步证据支持其诉请。如果权利人对其损失主张只能提供初步的证据,当侵权人构成证明妨害时,法院可以适当降低证明标准,从而实现对权利的救济。如权利人提供侵权人的广告宣传、媒体报道等作为证据,在一般情况下这些证据证明力较弱,法院不会采用,但当侵权人构成证明妨害,法院可以赋予上述证据较强的证明力,结合案情采用优势证据规则,综合认定实际损失或侵权获利。
(2)推定权利人的主张成立。权利人申请对侵权人的账簿、资料等进行证据披露,而侵权人拒不披露或阻扰、抗拒法院调查,或者向法院提交残缺、虚假的账簿资料,则构成证明妨害,应推定权利人主张的赔偿数额成立。证明妨害的结果实际上是一种法律推定,即根据一定的法律条件对法律事实进行拟制。“对证据妨害行为适用赔偿数额的法律推定,一方面保护了应举证而无法举证之原告的正当权利,另一方面有助于促使证据持有人提供相关证据以保证真实情况的发现,从而保障了民事实体法的有效实施。”①吴汉东:《知识产权侵权诉讼中的过错责任推定与赔偿数额认定——以举证责任规则为视角》,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第130页。
4.证据披露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冲突
在商标侵权诉讼中,权利人申请披露的证据可能涉及侵权人的商业秘密。侵权人常以商业秘密受保护为由拒绝证据披露。《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7条明确规定,商业秘密属于当事人可以申请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范围,因此,侵权人不得拒绝披露。但为了保护商业秘密,法院在审查权利人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披露申请时,首先应考虑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并需承担侵权责任的可能性;涉及商业秘密的证据不得公开出示和公开质证,并要求诉讼参与人履行必要的保密义务,防止权利人借侵权诉讼窃取商业秘密用于不正当竞争。
(二)运用优势证据规则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②《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3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对同一事实分别举出相反的证据,但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确立了优势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形势下知识产权审判服务大局若干问题的意见》要求在确定损害赔偿时要善用证据规则,全面、客观地审核计算赔偿数额的证据,充分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有关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证明力进行综合审查判断,采取优势证据标准认定损害赔偿事实。“我国法院审判中存在对于证据规则和证明程度的把握偏高偏严(如拘泥于一些刻板的举证要求、过于强调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过于拘谨,不太注重实际损害的确定等现象。”③孔祥 俊:《知识产权法律适用的基本问题——司法哲学、司法政策与裁判方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3 年版,第257页。运用优势证据规则是对商标侵权损害赔偿举证难的现实应对,既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又防止法官无休止地追求客观真实。在实践中,以下两种情形需要法官大胆运用优势证据规则确定赔偿数额:
1.运用自由裁量权的酌定赔偿
权利人不能充分证明其实际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但能证明该损失或获利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可在法定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这是法官在一定事实和数据基础上,根据具体案情与权利人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来认定赔偿数额,只是在具体数额上行使裁量权,并不是适用法定赔偿,也就不受法定赔偿最高额的限制。全国法院已有不少判决运用了这种做法,如在宝马股份公司诉广州世纪宝驰服饰实业有限公司等商标权纠纷一案④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高民终字第918号民事判决书。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酌定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200万元,超过了当时《商标法》规定的法定赔偿50万元的最高限额。
2.结合实际查明数额与酌定数额计算实际损失
对于某些难以准确计算或现有证据无法直接证明的损失,可参照一定的标准进行推算。如根据权利人的证据能够对其销售情况的变化作出大致判断,并足以让法官产生内心确信,就应当采纳相关证据并支持权利人据此提出的诉请。又如,权利人提供了据以计算其损失或侵权人获利所需的销售数量等数据,可以参考许可费、行业或类似商品一般利润率、侵权行为性质与持续时间、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等因素,酌定计算赔偿所需的其他数据,最终结合实际查明与酌定数额确定侵权损害赔偿额。
在“新百伦”案中,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将实际查明数额与酌定数额相结合,参考被告的侵权行为、销售规模、主观过错、获利明显超过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等因素确定原告的损失。根据被告新百伦公司2011年度《审计报告》、2012年度《审计报告》及《利润表》等证据,被告在原告主张的侵权期间共获利约1.958亿元;考虑到被告仅在销售过程中使用“新百伦”标识来介绍和宣传其产品,属于销售行为侵权,因此,广州中院酌定被告向原告赔偿的数额应占其获利总额的1/2,即9800万元(含合理支出)。同时,详述了酌情考虑的因素:1.被告作为一家年均营业额数亿元的大型企业,明知“百伦”商标已在1996年获准注册,仍使用与“百伦”商标这一臆造词相似度极高的“新百伦”来标识及宣传产品。2.被告在其关联公司新平衡公司对“新百伦”商标提出的异议被国家商标局裁定不成立后,仍持续使用“新百伦”字样。3.“新百伦”既非“NEW BALANCE”的中文意译“新平衡”,也非中文音译。4.被告使用的“新百伦”标识与原告“新百伦”注册商标的三个中文字完全相同,极易被混淆。5.被告将“新百伦”和“NEW BALANCE”并列使用或直接使用“新百伦”,“新百伦”对其产品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6.被告销售渠道多、销售范围广,销售渠道包括800多家专卖店与“New Balance新百伦旗舰店—京东商城”等网店以及大量销售专柜。7.被告通过官方网站、新浪微博、视频广告及宣传手册等各种媒介进行广告宣传,影响大。8.被告的侵权获利明显超出商标法规定赔偿额。9.原告涉案维权合理支出数额较大。
(三)建立法定赔偿的量化标准体系
《商标法》第63条第3款规定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300万元以下的赔偿。“该规定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法官同样应该要求维权者对请求赔偿数额的举证,杜绝裁判模板化,做到主观认定客观化。”①陈晓艳、程春华:《商标侵权民事责任承担的举证责任分配及证明要求——以新商标法的规定为考察范围》,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10期,第61页。通过对商标侵权案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以类型化的方式确定酌定因素的种类,细化法定赔偿的适用条件,将个案复杂、抽象的因素进行量化和具体化,大致确定各因素的权重及对判赔金额的影响程度,建立科学、规范的法定赔偿量化标准体系,有助于解决商标侵权法定赔偿的困境。
1.确定基准赔偿额
法定赔偿的基准数额是指法院对商标侵权各类案件所确定的法定赔偿的大致数额。基准数额是构成赔偿数额的基础部分,应是一定幅度范围内的具体数额,某类案件的基准数额对该类案件普遍适用通过对近年审理案件的统计分析,广州中院大致确定了商标侵权案件的基准赔偿额,在一般情况下,个体零售店5000—2万元;综合型零售店(如超市)3万元左右;普通商标的侵权产品单价在1000元以下的,如果侵权行为性质为制造,基准数额为5—15万元,如果侵权行为性质为零售,基准数额为1—5万元。②参见广州中院课题组:《知识产权赔偿问题的实务困境与对策》,载《广州审判》2014年3期,第23页。
2.细化影响法定赔偿金额认定的相关因素及权重
在具体案件中,不同法官在确定法定赔偿数额时,考虑的因素可能不同;而在被考虑的因素中,每一个因素对确定赔偿额所起的作用也可能不同,这导致类似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会有不同的法定赔偿额。在实践中影响法官酌情确定商标侵权赔偿额的因素主要有:(1)商标的价值,包括商标声誉、侵权产品售价及利润率等;(2)侵权人的主观过错,包括故意或过失;(3)侵权行为性质,包括制造或销售;(4)侵权人的经营规模,包括经营场所的面积与地点、雇员人数、注册资本等;(5)侵权行为发生地,如发生在广交会等国内外知名的展会上;(6)其他情节。
上述因素对酌定赔偿数额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如侵权人故意侵权,对权利人造成的损害一般比过失侵权要严重。如侵权人多次故意侵权,说明侵权人可能以侵权为业,侵权后果往往也比较严重。因此,侵权人主观过错对侵权事实和结果具有重要甚至是决定性作用,“过错程度较深的侵权对商标权人损害赔偿数额应高于过错程度轻的,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商标权。”①张先昌、张怡歌:《论过错与商标权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以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为背景》,载《知识产权》2015年第1期,第48页。其他因素如商标价值、侵权行为性质以及侵权人的经营规模等与侵权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一样,对法定赔偿数额起决定性作用,属于酌定因素中的核心因素。而诸如侵权期间、后果、许可使用费、侵权行为发生地以及其他众多因素对法定赔偿额仅起补充性作用,属于酌定因素中的情节性因素。综合两类酌定因素对法定赔偿额、举证难易程度等的影响,确定核心因素与情节性因素对法定赔偿数额所起作用比例一般约为7:3,其中核心因素确定的赔偿数额就是法定赔偿的基准数额。因此,如果用A、B、C分别表示法定赔偿数额、基准数额、情节性因素确定的赔偿数额,各类商标侵权案件的法定赔偿额可以用等式量化为:A=B+C[B÷(B+C)≥70%、C÷ (B+C)≤30%]。因此,在具体个案中,法官首先应对法定赔偿的酌定因素进行分类,确定每一类因素对赔偿数额所起的作用比例,然后确立该类案件法定赔偿的基准数额,在此基础上进行法定赔偿的量化适用。
3.法定赔偿的酌定因素作为法院审理重点
在损失或获利无法查清的情况下,法官应将法定赔偿的酌定因素纳入法庭调查和辩论环节,让双方当事人就案件中哪些因素应当纳入法院考量的范畴,以及该因素对赔偿额所起作用进行阐述并展开辩论。经过当事人列举—辩论—法庭审查—决定是否采信这样一个过程,既保证当事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也有利于形成一种制度预期,即酌定因素中的核心因素越多,赔偿金额就越高,反之则越少,这样会使双方当事人在辩论时就可对赔偿额作出大致的预估,比较容易接受法院的判决。
结 语
损害赔偿是商标侵权诉讼的难点,赔偿数额确定的标准和方法直接体现了法院的裁判水平和司法保护力度。“确定赔偿数额本质上是由司法对于知识产权进行‘定价’,这种定价经常参照现实的市场价值(如市场利益或者许可费的损失),而定价的高低反过来又会影响权利的市场价值(包括影响将来的许可费等市场定价),对于权利的市场价值具有逆向导向作用。”②孔祥俊:《积极打造我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升级版”——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的思考》,载《知识产权》2014年第2期,第13页。因此,人民法院在确定商标侵权赔偿数额时,应当认真研究商标的市场价值,坚持全面赔偿原则,将查明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获利作为赔偿数额认定的基本手段,充分考虑商标的无形财产属性及其价值的不确定性与权利人举证困难对损害赔偿计算的影响,使赔偿数额的确定能够达到加强商标权保护的效果。这样的司法“定价”才能正确引导与推动商标市场价值,保证商标权人权益的充分实现,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
In trademark infringement lawsuit, because of the diffi culties of proof, it is diffi cult to apply the basic principle of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damages, the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to pract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plementary principle of statutory compensation is abused. The people's court shall make full use the rule of evidence,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 and fi nd out the rights holders' actual lossor the infringers' profi ts.Considering that the intangible property attributes of brand name and the diffi culties to proof would impact on the calculation of damages, the quantitative standard of legal compensation system should be set up to make the cognizance of tort compensation achieve the effect of strengthening the protection of trademark rights.
trademark infringement; damages; the principle of comprehensive compensation;statutory compensation; rules of evidence
刘小鹏,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知识产权法院主审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