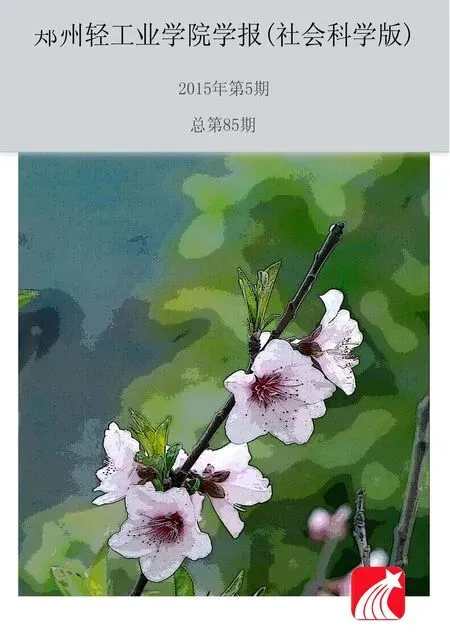《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与余秋雨的出版理念浅析
张世海(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与
余秋雨的出版理念浅析
张世海
(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摘 要]余秋雨在文学界的成名始于《文化苦旅》,这本散文集的出版一波三折,最后取得非凡的传播效果和销售业绩,其出版历程体现了出版业中创造与传播的良性互动。余秋雨对出版业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认为:出版的重心是创造与传播,出版要立足当代,传播文化,并创造新的文化;现代的出版机构要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把目光从浩若烟海的典籍转向生动的社会生活,在策划选题前走出办公楼,走进知识和文化创造者的世界,发掘其才情智慧。“创造与传播”的出版理念对当代出版业有重要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具有传播和创造的主体意识,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建设的历史经验、西方文明成果三个源头获得资源,促进了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对于古籍出版者来说,不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值得出版和传播,对历史文献的筛选、整理和出版,若缺乏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需求的深刻洞悉,就可能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同时又无益于当代文化的创造与传播。
[关键词]余秋雨;文化苦旅;出版理念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11
出版理念,简言之就是对出版业的本质和核心任务的看法,这种看法会直接影响出版活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出版业的成败。一般来说,每隔十年左右出版业的从业人员都会有一定比例的更替,新的出版从业者必须对这个问题有透彻的思考。当前,传统出版业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出版行业所面临的技术基础、社会观念、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其中数字技术的发展已先于学术界的研究和思考。
在印刷时代的黄金时期,英国出版业巨子、出版思想家斯坦利·昂温在1926年出版了《出版概论》一书,该书被喻为西方出版业的“圣经”。昂温认为,“出版工作要向准备跟随先驱人物走新路的人提供远为激动人心的奇异经历,应热心帮助人们克服麻木不仁、无知和偏见,尤其要帮助人们关怀真理的发展”[1]。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异军突起,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吴士余在谈到这批书的策划时写道:“一个民族的精神财富,除了通过长期的积累和历史沉淀,形成其稳固的民族传统文化外,从横的层面来说,每一个特定的时代,又都必须致力于建设和创造具有这个时代特色的新文化,并使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不断得到充实。”[2]关于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出版理念,我将在下文作深入分析。著名出版家聂震宁认为,“出版者在一定意义上是与作者协同进行内容创新,发现作者、发现文稿、策划选题并组织内容创新,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给读者做好服务、引导和推介,这样才能完成整个创新的过程。出版者在内容创新中应当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3]。面对数字技术给传统出版业带来的危机,四川教育出版社社长雷华认为,出版业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出版人的创造力不足,传统出版业面临的问题“不是读者变刁难,难以伺候,而是出版人智穷,缺乏创意,出版物质量下降。创意是一种创新,要求我们的理论、思想、方法、手段必须是独到的、新颖的、从没有过的;创意是一种突破,要求我们在产品内容、呈现方式、传播渠道等方面要有新的突破”[4]。
除以上来自出版界和学术界的观点值得关注外,当代文化界名噪一时的余秋雨的出版理念也值得编辑出版理论界关注,其原因有二:其一,他是当代中国罕见的畅销书作家,尽管饱受争议,但谁都不能否认,他多年来所出版的每一本书都销量不俗,深入探究这一出版现象对中国编辑出版业有现实意义;其二,余秋雨作为文化研究者,其研究对象很宽泛,其中也包括出版业,曾专门撰文探讨出版业的使命。由于余秋雨出版的著作数量较多,常需要与编辑出版界交流,因此他对出版领域的了解与认识比一般的作者更多、更深。出版界和学术界研究出版理论时,一般是针对某一具体问题和具体背景,较务实,而余秋雨的讨论多务虚,其视野较为宽广,时间跨度上百年,纵横古今,横跨中外,角度新颖,很值得深入探讨。鉴于此,本文拟对《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与余秋雨的出版理念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期为当今出版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余秋雨的散文创作与《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
文化散文是在余秋雨成名之后逐渐发展起来的、以历史为题材、语言优美华丽、有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和终极追问的散文。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散文几乎专属余秋雨,这个文体的盛与衰也系于余秋雨这个人,这种情况在当代文坛上并不多见。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经历了一个最初只是在文化圈小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到结集出版遭遇挫折,再到1990年代中期风靡一时、最终影响力才渗透到市民文化层面的过程,其实这是余秋雨个人的主观创造和出版界营销传播方式创新共同作用的结果。
1.余秋雨的散文创作特点
余秋雨的语言才华和叙述技巧在其早期学术著作里就已显露无遗,他于1983年出版的《戏剧理论史稿》(2013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时将其更名为《世界戏剧学》)语言还比较庄重质朴,但读起来一点都不觉得枯燥,已经显示出其散文的特定语言风格了。兹举一例。在分析法国古典主义戏剧学时,他写道:“这种文艺发生在贵妇人主持的客厅里,一切文艺作品若想流行于法国上流社会,先得进一进这些客厅的大门,博取坐在那里的高贵的主人和客人们的微笑。可以想见,这儿需要矫饰、缠绵、纤巧。自命风雅而又有着较高文化教养的人们毕竟也是爱挑剔的,因此这儿要求着词章的纯粹、风格的高雅、文体的整饬。”[5]余秋雨语言才华在其后来的写作中得到充分释放,其散文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语言华丽优美和叙述精巧别致。朱国华曾深刻地指出,“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已经成为余秋雨散文写作的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6]。
有人说余秋雨的散文都是华丽辞藻的堆砌,缺乏思想深度,这是有失公平的。因为余秋雨早在1980年代中期成名之前,学术上就已经有了极扎实的积累,研究领域涉及文学、史学、哲学、心理学、美学等学科,应该说,其钻研的深度和广度都高于同侪。这种丰厚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思维训练为他后来创作的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毋须讳言,他的思想缺乏系统,大多是灵光乍现,包裹在华丽的词汇中。由于他拥有极高的语言和修辞天赋,再加上他对戏剧表演及受众心理学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创作心得,能活学活用,所以,一个日常简单的道理,经余秋雨一表述,就立即显得有深度有韵味,再加一抹淡淡的感伤怀旧,使人读起来感到满口余香,回味悠长。
语言优美、叙事精巧、浅显通俗、有思想闪烁、有淡淡的感伤,这些正是余秋雨散文创作的特质。余秋雨创作才能已具备,只缺发掘他的“伯乐”了,而他又幸运地遇到了“伯乐”。
2.《文化苦旅》的出版历程
1987年中国正值散文热,但当时的散文存在很多弱点:有的偏重于政治说教而失去了文学的可读性,有的充满学术语言而晦涩难懂,还有的过于浅显以至于显得幼稚。当时,余秋雨的大学同学李小林在《收获》杂志担任副主编,借这种同窗之谊,余秋雨先向李小林提出想写散文,他试写两篇后,李小林读来感觉不错。1988年1月,《收获》杂志专为余秋雨开设了《文化苦旅》专栏。1989年,创刊不久的《鄂西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组笔谈文章,编者按认为,《文化苦旅》“表现出对人类文化整体生存命运的关注,显示出一种由传统散文的‘悟道’与现代人的开放思维交织而成的恢弘深邃的艺术境界”[7]。余秋雨感觉遇到了遥远的知音,还应邀寄去一篇文章交代写作缘由。由此可见,《文化苦旅》这个专栏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但仅限于文学圈。
余秋雨的散文要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需要遇到编辑出版界新的“知音”和新的“贵人”,而他又幸运地遇到了,虽然过程有点曲折。
南方有一家出版社跟余秋雨商量后,决定将其散文结集出版,放在旅游景点销售。当然,他们一开始可能并没有告诉余秋雨这个真实的意图,等他们开始着手编辑时,发现这些“苦旅”文章并不适合在景点销售,于是不得不大幅删减。李小林得知此事后出面干预,要求这家出版社把原稿寄回。可寄回的原稿已经面目全非,“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8]。余秋雨看到这堆稿子也不禁心灰意冷,“几次想把它投入火炉”[9]。
之后,上海文艺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这一散文集放在他们的散文丛书中出版,余秋雨嫌丛书作者太多,他的散文可能湮没无闻,并没有同意。就在这时,余秋雨遇到了他的另外一个“贵人”———与余秋雨有多年私交的上海知识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的前身)的编辑王国伟,当王国伟得知此事后,决定对余秋雨的散文重新编辑,精心策划,此决定是余秋雨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王国伟的建议也得到了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总编辑施伟达、社长朱效荣的鼎力支持”,“决定作为本社重点图书立项和运作,出版形式决定以精装本为主。在当时出精装本是出版社给作者一种高规格的出版礼遇”[9]。之后,王国伟又让余秋雨补写了几篇文章,书稿从18万字增加到23万字,《文化苦旅》最终得以出版。
《文化苦旅》出版之后的营销也做得很成功,一些举措在今天看来很平常,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创举。上海知识出版社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举行《文化苦旅》首发式,吸引了五十多家京沪媒体集中报道采访,出版方“还在全国各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签名售书、讲座报告会、见面会及读书活动等”[8]。出版社的精明与远见还体现在他们把目光投向了数量庞大的中学生群体。当时政府大力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一些革命题材的文学作品在中学生群体中没有太大吸引力,效果不彰,而《文化苦旅》中很多歌颂祖国大好河山的篇章,对传统文化虽有一些嗔怨,但总体上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恰恰暗合了这一主旋律。于是,出版方“利用多种渠道和影响力,向教育部门推荐,《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顺利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8]。学生毕业一届又有新的一届,这种稳定的读者群使《文化苦旅》保持长期畅销的势头。
经过这次精心策划、编辑出版和市场营销,余秋雨之前的知识和理论积累、丰富的游历、高效的“流水线写作模式”开始产生作用,其丰富的创造素材和技巧得到了出版界的认可。至此,散文家余秋雨正式闪亮登上中国文坛。余秋雨经过这次商业出版的洗礼之后,对出版界的作用有了深刻认识:“对我来说,我的落脚点就是出版社,因为只有出版社才能将精神产品转化为物质产品,流播于世,它是让作家与读者直接接触的前沿。”[10]
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究竟是一种文化快餐还是文化精品,它有没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是否能形成一种新的文学体裁范式并对未来的文学创造产生有益的影响,这些问题不是本文探讨的重点,它有待文学理论家进行深入研究。但不可否认的是,出版界发掘并成就了文化散文,其成功得益于对传播模式的创新。也就是说,余秋雨散文的出版过程和空前成功证明了出版界在文化成果的创造与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余秋雨的出版理念
余秋雨的研究兴趣很广泛,从最初的戏剧专业跨到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经过长时间的积累,1990年代中后期他借着《文化苦旅》的热销持续发力,创作了大量文化散文,将其语言才华和高效的写作模式发挥到了极致。笔者粗略统计一下,他的各类作品仅在中国内地就被超过20家出版社出版过,其对国内人文类出版社的运作流程较为熟悉,对文化与出版之间的关系也有自己独立的思考。
1.出版的重心是创造与传播
余秋雨的出版理念散见于他的各种作品中,最集中体现在他的一篇题为《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的文章中。在这篇文章里,他直接而清晰地阐述了他的核心观点:“出版的重心是传播与创造”,“在一个文化遭到严重破坏的境况中,出版的主要责任在于文化的积累与传承,但在如今这个时代,积累和传承却只是出版的小部分的、非重要的使命”[10]。我们认为,余秋雨提出的“传播”与“创造”是两个并列关系的词,通观原文,余秋雨在使用这两个词时并没有在它们之间建立某种逻辑关系。本文在论述的过程中,会根据论述内容的逻辑调整这两个词的顺序。余秋雨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而文化的转型却显得迟滞,这种迟滞会使人们在适应社会变化时产生各种心理问题。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殊的问题和最重要的议程,并非所有这些问题都能从历史和传统中找到答案和启示。出版要立足当代,传播文化,并创造新的文化。从这个角度说,余秋雨的观点是具有一定价值的,笔者完全赞同。
余秋雨的观点虽然比较简单,但理论的力量恰在于简单所揭示的本质,如果我们从理论上把握了编辑出版业最重要的职责,就能在我们的出版活动中建立一个根本性的原则。在中外出版史上,积累与传承和创造与传播是两个不同的原则,它们各自产生的结果也有天壤之别。
余秋雨比较了近代以来中西方出版理念的差别和它们产生的不同社会影响。他认为,向后看,创造意识淡漠是中国文化的痼疾。18世纪末19世纪初,中国和西方在文化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中国向古老和细节上深下工夫,推至极致,以段玉裁、姚鼐、翁方纲为代表的学者在古文字领域投注了巨大的精力;而此时西方却出版了黑格尔、康德和席勒等学者的原创性著作,从而揭开了启蒙运动的序幕。在自然科学领域西方也出版了一批经典著作,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西方的差距由此越来越大。1831—1832年,中国重修《康熙字典》,现在那个字典的很多文字已经死去;而法国出版了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部经典至今仍然焕发着艺术魅力。1832年6月,中国学者王念孙和英国学者边沁同时去世,前者皓首穷经,把毕生心血都耗费在古典文献上;后者着眼当下和未来,出版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英国工业革命之后的社会形态[10]。
余秋雨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版业高度繁荣,人人都爱读书,那么这个国家的整体气象和国民生存状态都将发生巨大转变。他曾经在一篇文章中用感性华丽的语言建议青年人多到书店走走,感受文化创造的前沿,享受书香氛围,接受知识熏陶:“崭新的纸页,鲜亮的封面,夸张的宣传,繁忙的销售,处处让你感受到书籍文明热气腾腾的创造状态,而创造,总是给人一种愉悦的力量。这种力量对读书人是一种莫名的滋养,使你在长久的静读深思之后舒展筋骨,浑身通畅。”[11]
2.出版者要走进文化创造者的世界
在当代国际社会,文化产业的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当前也正处于文化产业大繁荣大发展的态势之中,文化产业的发展状况将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即使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人性深处也有一种无法压抑的对新奇丰富的精神活动的追求,在物质发达的年代,这种需求更加强烈,而当前中国的文化产品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经济的信息化、知识化,以及对智力创造活动的更高依赖,对出版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出版业是文化产业所有门类中最基础的产业,它不仅直接生产文化产品,还为社会各个领域提供原创性的知识,推动社会变革,并为转型期人们迷惘躁动的心灵构建温暖的精神家园。余秋雨认为,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出版社很难以堂皇如衙门般的阵势,通过安排人事和选题而产生优秀文化成果[10]。现代出版机构应培养敏锐的问题意识,把目光从浩若烟海的典籍转向生动的社会生活,在策划选题前走出办公楼,走进知识和文化创造者的世界,发掘他们的才情智慧。“在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年代,优秀的写作者总是极少数,这样的写作者,有着独特的气质、超于凡众的高度,他们身上闪耀着可以打动读者心灵的亮光,优秀的出版人,要能够一眼发现这样的人。”[10]只有这样,出版业才能更好地承担创造与传播的社会职责。
《文化苦旅》在文化界一炮走红之后,余秋雨又陆续出版了多部畅销书,其本人的出版营销技巧也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在凤凰卫视录制的一个系列节目成书出版时,余秋雨曾写下这样一段话:“这本书的主要亮点,是我和北大学生一起创造了一种最生动的课堂方式,曾在播出时让知识界极为感动。这将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12]这段话后被印在封面折页上,上面还配了一幅余秋雨坐在椅子上派头十足地挥动双手讲话的图片。后来的事实证明,尽管他参与的节目收视率也不差,但远没有达到“让知识界极为感动”的程度,当时很多看过电视节目的观众现在只记得一些镜头中的肢体语言,记不起他在电视上到底讲了些什么;根据该档节目而结集出版的书销量确实不错,但远远没有“成为中国出版领域的一件大事”。
作为一个常与出版社打交道的畅销书作家,余秋雨有自己的独特思维方式和文化视野,他观察出版界的角度更独特,融入了个人的出书经验。他的畅销书出版的过程其实也是他对个人出版理念的诠释过程,他在与出版社的互惠互利中,完成了对自己作品的创造与传播。他的很多作品都是他用自己的方式对历史进行解读,并且其解读方式不是传承与积累,而是创造与传播。他称受黑格尔的启示,认为“历史是一堆灰烬,但灰烬深处有余温。历史学家常常不得不承担化验和清理灰烬的任务,而作家则直接用自己的体温去感知历史的余温”[13]。这种写作方式跟他的出版理念也是一致的。以余秋雨的观点推之,即使是出版经典文献,也不能仅仅把目标定为传承与积累,一定要加入创造性的元素,比如使用新的载体,加入新的阐释,进行新的编排,增加新的材料,以及创新传播方式,总之,应在经典文献与当代社会之间创造一个沟通对话的机会。
三、创造与传播在当代出版实践中的运用
尽管面临着数字技术的强烈冲击,但当代中国出版业仍然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积累与传承、创造与传播及社会认同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创造与传播的出版理念正在当代出版实践中得到运用。
1.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创造性策划
中国的现代出版理念始于商务印书馆,而商务印书馆的核心理念也可以归结为创造与传播。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得到迅速发展,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它能为剧烈转型的时代提供新的文化成果,并传播这些文化成果。正如现代出版家王云五所总结的,“政治上每经一度之变动,文化上辄伴以相当之改进。而对此改进之工作,三十年间不绝赞助且赞助最力者,其唯我商务印书馆乎”[14]。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中国社会处于经济体制大转型的前夜,那时既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僵化,“文革”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又割断了中国的文脉,知识阶层弥漫着焦躁的气氛。中国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但这种创造又不是凭空的,它需要出版者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且在分析的基础上有准确的判断,有针对性地发掘以往文化成果,以便为这种创造提供基础。
在这一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著作,其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现代的学术视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道教史》《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中国历代货币大系》《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士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等;第二类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方面所积累的历史经验,如《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和前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中国法学40年》《经济法》等;第三类是西方学术经典及当代最新学术思想和学术成果,包括近千页的大部头工具书《外国学术名著精华辞典》和系统全面的《青年译丛》等。我们可以看出,上海人民出版社有一种明确的主体意识,希望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执政与建设的历史经验与西方文明成果三个源头上获得资源,以促进中国的新文化创造。曾任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的吴士余先生在谈到策划这三类著作出版时说:“应该说,接受前人的文化遗产,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是有选择、有创造性的。这种文化传递中的主体意识,同样也是出版工作者所必须的。”[15]如果出版者失去创造和传播的主体意识,追求利润至上,一味迎合读者和市场,最后的结局可能就是经济和文化的双重损失。当代中外出版界的很多问题虽有技术方面的冲击,但主要在于创造力的丧失和对市场无原则的迎合。日本出版理论家小林一博研究了日本的出版危机后也得出结论:“对市场的时尚的亦步亦趋扭曲了原本的文化教育和文化追求,文化变成了对市场和时尚的讨好与追求;出版对阅读口味和视野的引导,变成了对读者偏好的迁就和附和。读者的口味愈下降,出版就愈迁就,长此下去,读者和出版的素质都会下降,社会文化也会日益滑落。”[16]
2.古籍出版中的创造与传播
近年来,学术界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发现,“几乎所有亚洲社会都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态度深深植根于亚洲传统之中,而且可能恰恰是亚洲传统的最基本要素。东亚的经济奇迹显然得力于集体努力追求这个优异的亚洲传统。因此,亚洲高速现代化的强大深层基础乃是它的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方式”[17]。在普通民众层面,比起政治说教或者西方的价值观,人们发现传统的处事方式和价值观念能更有效地解决当下的问题,如诚信问题、家庭教育问题、企业管理问题等。
在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剧烈转型的背景下,这种传统文化热潮的本质是一种创造当代新文化的强烈需求,人们希望用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价值观来对当代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纠偏。这种需求带动了中国相关领域的出版发展。当出版者在选择积累和传承某种类型的经典时,必须对当代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并预先设想出未来新文化的形态,从传统文化中提炼可以用来建构新文化的元素,为新文化的创造和传播奠定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丰富、庞杂的整体,每一种理论体系都有其优劣,司马迁在《史记》中对汉代以前的各学派有过精辟的论述:“阴阳之术,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墨者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强本节用,不可废也。法家严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俭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实,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18]而汉代以后到清代的漫长历史留下了更为浩瀚多元的传统文化资源,后世的很多新思想和新观念,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渊源和理论依据,这给古籍出版界提供了丰富的选择,这种选择是一门需要精心研习的艺术,也是一种创造性活动。
因此,对于中国的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岳麓书社这样的以出版古典文献为专长的文化机构来说,创造与传播这个理念也有一定的价值。不是所有的历史文献都值得出版和传播,对历史文献的筛选、整理和出版,若缺乏对当代社会问题和文化需求的深刻洞悉,可能会因出版物的滞销而蒙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又无益于当代文化的创造和传播。黑格尔曾在《美学》中写道:“历史的东西虽然存在,却是在过去存在的,如果它们和现代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关联,它们就不是属于我们的,尽管我们对它们很熟悉;我们对于过去事物之所以发生兴趣,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有一度存在过。……我们自己的民族的过去事物必须和我们现代的情况、生活和存在密切相关,它们才算是属于我们的。”[19]
[参 考 文 献]
[1] 罗紫初.出版学理论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2(增刊):5.
[2] 吴士余.出版坐标:文化的积累、建设与传播[J].编辑学刊,1992(1):38.
[3] 聂震宁.内容创新是作者、出版者和读者的有机结合[J].出版参考,2013(3):6.
[4] 雷华.回归、坚守出版的本质———创意[J].出版广角,
2014(9):1.
[5] 余秋雨.世界戏剧学[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3:165.
[6] 朱国华.另一种媚俗———《文化苦旅》论[J].当代作家评论,1995(2):60.
[7] 佚名.《文化苦旅》笔谈[J].鄂西大学学报,1989(2):1.
[8] 王国伟.我和余秋雨的交往与误解[EB/OL](2013-11-21)[2015-06-17].http://www.infzm.com/content/96105.
[9] 张弘,王梦菁.《文化苦旅》:掀起“文化大散文”热[N].新京报,2008-12-06(C10).
[10]余秋雨.文化理念与出版理念[J].编辑学刊,2005
(6):17.
[11]余秋雨.青年人的阅读[J].新湘评论,2012(8):18.
[12]余秋雨.问学·余秋雨·与北大学生谈中国文化[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封面.
[13]张国龙.2000—2010中国散文现象批判[J].南方文坛,2012(6):104.
[14]高翰卿.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C].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2:284.
[15]吴士余.出版坐标:文化的积累、建设与传播[J].编辑学刊,1992(1):40.
[16][日]小林一博.出版大崩溃[M].甄西,译.上海:三联书店,2004:151.
[17][美]罗兹·墨菲.亚洲史[M].黄磷,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574.
[18]〔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8:2556.
[19][德]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46.
[作者简介]张世海(1977—),男,河南省信阳市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传播学与编辑出版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XW072);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
[收稿日期]2015-06-18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5-0061-06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G23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