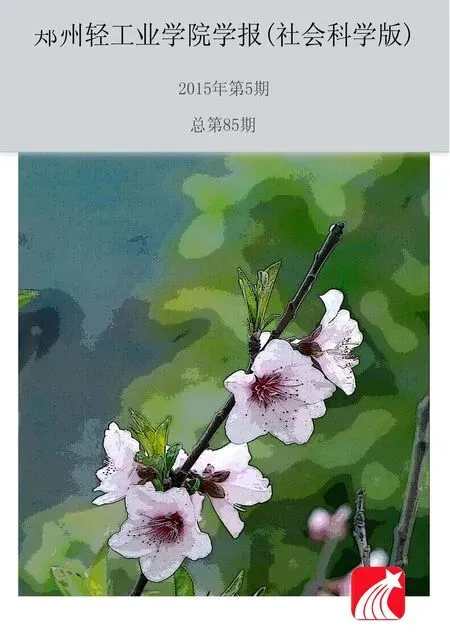马克思“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诞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深度耕读
王建锋(洛阳师范学院马列理论教研部,河南洛阳471022)
马克思“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诞生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的深度耕读
王建锋
(洛阳师范学院马列理论教研部,河南洛阳471022)
[摘 要]《〈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马克思“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诞生地。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通过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及国家哲学的三重批判,为其“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打下了深厚的哲学基础。马克思通过宗教批判,揭示了宗教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深层意识形态关联,强调只有实践地破除宗教幻象及其对现实的人的思想制约和意识禁锢,才能引导人们认清自身遭受奴役的现实根源;通过政治批判揭示了使得现实的人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获得新生的现实途径,指出:只有在无产阶级革命的作用下,才能推动旧世界向新世界转变,从而实现对旧世界的历史超越;通过哲学批判进一步揭示了颠倒的意识与颠倒的社会存在之间的本质关联,提出只有将“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人和社会的双重解放。
[关键词]现实的人;社会批判;人的解放;宗教批判;政治批判;哲学批判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2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一文中,通过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及国家哲学深刻而又彻底的批判,初步确立了其“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作为马克思社会批判和人的自由解放理论所关注的核心,“现实的人”既是马克思新人本主义哲学思想产生的逻辑起点,也是其整个社会革命学说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当代社会,对“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产生的重要文献《导言》一文重新作深度耕读,不仅有利于深化对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理论认识,而且也有利于进一步理解“现实的人”这一概念产生的历史逻辑。
一、宗教意识批判:“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的奠基
作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及宗教意识批判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奠基的基本前提。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对“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颠倒的、虚幻的反映和认识,宗教及宗教意识一方面体现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较为客观地揭示了“现实的人”的生存困境。仅靠宗教所诉求的道德理想是无法实现“现实的人”追求其幸福生活的价值目标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宗教总是与社会发展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识形态相一致。宗教及宗教意识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困境产生、存在的总体现和总依据。“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包罗万象的纲要,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1](P1-2)由此可见,作为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宗教及宗教意识既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工具,也是“现实的人”对自身无奈的现实生活与生存困境的真实反映。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要改变“现实的人”的生活状况及其生存困境,首先就必须对禁锢人们思想认识活动的宗教及宗教意识进行批判,惟其如此,才有可能重新确立“现实的人”作为历史活动者的主体地位,也才有可能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宗教及宗教意识的真正本质。正是基于这样的基本事实和理论认知,在《导言》一开始,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是其他一切社会批判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础。
对宗教及宗教意识进行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的理论关照。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现实的人”不是抽象的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真实的存在物。虽然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还没有明确提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思想,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运用新人本主义的观点,来阐述自己对“现实的人”深刻而真挚的洞见了。他认为,一个人,如果曾经在天国幻想的现实性中去寻找超人,而找到的结果只是他自身的反映,他就再也不可能在他正在寻找或应该寻找自己现实性的地方去寻找他自身的假象了。[1](P1)这就是说,作为历史活动的真正主体,“现实的人”是真实存在着的、且正从事着一定社会活动的现实个人,他们既是自身所享用的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自身所享用的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换句话说,当且仅当每个人都处在其真正现实性的地方,并展现其作为“现实的人”活动的具体特性时,才有可能重新确立自己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历史性地位。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批判宗教及宗教意识最重要的根据是“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了人”[1](P1)。在他看来,宗教及宗教意识既是“现实的人”参与社会现实活动的产物,也是生活在这一现实困境中的“现实的人”对自身生活的精神慰藉和希望。因此,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乃是重新确立“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主体地位之必要而充分的理论准备。批判宗教意识和抛弃产生宗教现实处境最根本的原因和最明显的意义就在于:一个完全不依赖宗教慰藉的新世界的真正诞生,才有可能是合理的、幸福的“现实的人”的真实生活世界。
宗教及宗教意识里所呈现的痛苦和灾难,既是“现实的人”在其现实生存困境中的重要表现,更是他们在精神活动层面上对这种现实中的苦难的苍白无力的抗议和斗争。在马克思看来,要改变“现实的人”现实生活的生存境况,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废除作为人民虚幻幸福的宗教意识。这是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宗教是统治阶级用来麻醉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鸦片,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德国落后社会制度的批判。因此,只有深入开展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才有可能使“现实的人”从此不再对宗教所宣扬的虚幻的、颠倒的社会状况存有幻想。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正是要撕碎锁链上虚幻的花朵,而不是要人们仍戴上没有幻想、没有慰藉的锁链,对宗教批判最终有可能使“现实的人”能够围绕自身和自身现实生活的太阳转动。[1](P2)换言之,马克思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深刻批判,其真实目的乃在于重新确立、重新发现“现实的人”及其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价值和地位。“现实的人”及其现实幸福生活的实现,必须诉诸“现实的人”及其具体的历史活动,而不是依赖虚幻的宗教及宗教意识本身。正是基于此,马克思进而认为,宗教及宗教意识只是人们头脑中虚幻的太阳,当人没有围绕他自身进行实践活动的时候,它总是围绕人而转动。[1](P2)概而言之,作为“现实的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产物,宗教及宗教意识一方面体现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活动主体的能动性及对理想幸福生活的期盼;另一方面也客观反映了“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真实困境。
在马克思看来,要改变这种现实的生存困境,实现“现实的人”的现实幸福,不仅要废除反映人们虚幻幸福的宗教及宗教意识,更要抛弃、改变产生这种虚幻幸福生活的实际处境,而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理论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产生这种苦难的实际处境所进行的理论批判。“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P2)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指的就是宗教及宗教意识里对“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的虚幻反映和颠倒的错误认识。这种虚幻的、颠倒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恰恰就是对尘世的、“现实的人”的存在状况及其生活状况的真实反映。因此,要改变尘世的、“现实的人”的现实困境,既要对产生这种状况的宗教及宗教意识进行批判,更要对产生这种现实状况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及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进而重新确立“现实的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是遵循这样的理论进路,马克思认为,“彼岸世界的真理”被拆穿以后,哲学的历史任务就是要重构“此岸世界的真理”。“此岸世界真理”历史任务的确立,在其必然性上,使对宗教的理论批判过渡到对产生这种苦难实际处境的实践批判。于是,在逻辑的理论维度上,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论批判就演变成了对法哲学的理论批判;在逻辑的历史维度上,马克思对宗教的理论批判就演变成了对德国现实政治制度的批判。但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无疑成了所有批判得以进行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确立的基本前提和重要的哲学基础。
二、政治制度批判:“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确立的历史依据
宗教及宗教意识批判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作了奠基。但宗教及宗教意识批判只是在认识论意义上撕碎了禁锢人们认识和活动能力锁链上的“虚构的花朵”,其在现实性上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剪断禁锢在人们身上的真正锁链。在马克思看来,要改变“现实的人”现实的生存处境,彻底剪断禁锢人们精神活动的锁链并“采摘新鲜的花朵”,就必须把批判的逻辑从宗教及神学转向社会政治制度领域。这是因为,宗教及宗教意识是人的本质在其幻想中的实现,当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现实性的时候,反对宗教的斗争及形式,就直接地表现为集中反对以宗教及宗教意识为精神
抚慰特征的世界的斗争和形式。[1](P2)正是如此,对德国落后社会状况的政治制度的批判,不但更富有现实的针对性,而且是愈加深入的批判之必然要求。
对德国政治制度进行批判以前,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德国社会的现状及当时德国社会在欧洲所处的历史地位。“如果从德国社会现状本身出发的话,即使采取唯一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是时代错乱。”[1](P3)在这里,马克思之所以用“时代错乱”这一尖锐、犀利的词语来界定当时德国的社会现状,依据的正是当时德国真实的社会现实:虽然在思想领域里有了一个历史的运动,但在整个现代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中,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相比,仍处于一个较低的历史水平。“即使对我国当代政治状况的否定,也已经是现代各国的历史废旧物品堆藏室中布满灰尘的事实了。”[1](P3)马克思这一尖锐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理论批判,充分表明了当时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真实的社会状况:与欧洲其他先进国家相比,德国在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不仅没有同欧洲其他国家一道经历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革命行动,相反,它却同欧洲其他国家一道经历了社会复辟。这恰如其分地表明了当时德国社会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社会发展水平的真实状况。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政治制度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德国的统治者害怕革命;二是先进国家的社会革命受到了各国反革命势力的迫害。与整个欧洲现代国家的社会革命状况相比,德国的社会革命仅仅在思想领域里有一定的历史变动。诚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我们的那些牧羊人带领下,总是只有一次与自由为伍,那就是在自由埋葬的那一天。”[1](P3)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肯定了德国社会革命在思想领域里变动的历史地位和积极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德国思想领域里的历史变动做出了恰如其分的批判性分析。那些具有德意志狂血统并自诩有自由思想的人,却让德国人到史前的原始森林中去寻找自由的历史。如果德国人自由的历史只能到原始森林中去寻找的话,那么德国人自由的历史和野猪自由的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1](P4)由此可见,在这里,马克思不仅充分肯定了人类在创造自己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深化了对“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命题的理解。马克思这一富有新人本主义思想的真知灼见,无疑具有深刻的、强烈的现实感和历史感。
显然,如果要实现人类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目的,就必须对产生这种落后状况的政治制度进行批判。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制度虽然低于欧洲多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水平,但它依然应当是批判的对象,正像一个低于做人水平的罪犯,依然应当是刽子手行刑的对象一样。[1](P4)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之所以把德国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社会理论批判的对象,其目的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要批判德国社会的现实及其真实的历史存在形态,所以,批判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一对象,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1](P4)在马克思看来,只有通过对德国政治制度的无情批判和深刻揭露,才能使受这种制度压迫的“现实的人”认识到压迫的存在,进而唤醒他们追求自身生存的目的、勇气和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涉及这个内容的批判是搏斗式的批判,问题不在于敌人是否高尚,是否旗鼓相当,是否有趣,问题在于让德国人不再有一时片刻地去自欺欺人和俯首听命”[1](P5)。由此观之,这一见解在更深刻的意义上,恰好表明了马克思对德国政治制度无情批判的根本旨趣,其真实目的不是为了纯粹的理论批判,而是要通过这一理论批判,让“现实的人”能够真正认识到变革自身现实生存困境的正当性、合理性。马克思认为,要彻底改变德国政治制度所带来的“时代错乱”,让受压迫的“现实的人”认识到压迫的存在,使他们彻底明白德国社会状况对其生存困境所带来的沉重性,就必须对产生这种历史状况的政治制度进行猛烈的、无情的批判。换言之,只有对德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批判,才有可能实现德国人民不可抗拒的、追求自身现实幸福生活的时代要求。
总之,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之所以要对德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当时德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它既是德国封建社会旧制度的公开完成和具体表现,更是现代国家最隐蔽的缺陷。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现实的人”追求自身现实幸福生活的目标,就必须对产生“悲剧性”现状的德国政治制度进行批判。而同当时德国的政治状况作斗争,就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过去作斗争;在欧洲各国已经历过自己悲剧的旧制度,现在又作为德国的幽灵在重复着他们自己的悲剧。[1](P5)在这里,马克思不仅肯定了批判德国政治制度对欧洲其他现代国家的现实意义,而且也指出了“现实的人”未来历史活动的可能状况。“历史是认真的,世界历史形态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它的喜剧。我们现在为德国政治力量所争取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愉快的历史结局。”[1](P6)这表明,马克思对德国政治制度无情批判的真实目的,乃是为“现实的人”的幸福生活奠基,为之提供充分而必要的现实依据和历史条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一旦现代政治社会现实本身受到批判,那么,批判本身就不仅超出了德国的社会状况,而且也真正使其提高到了时代的高度。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对德国社会的现状来说,单个人的解放和发展与整个国家的解放和发展本质上是一致的,批判德国政治制度,既是为了整个德国社会的普遍解放和发展,也是为了每一个正在从事着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的普遍解放和发展。
三、哲学思想批判:“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思想得以确立的理论武器
在马克思看来,要解决德国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改变德国政治制度所造成的时代性错误,寻找对德国社会进行批判的理论切入点,仅靠揭露德国社会不公正的历史状况是不够的。为了把批判引向深入,就必须对德国哲学思想进行彻底的清算与反思。这是因为,与欧洲多国在现实中经历了自己真实的历史过程相比,德国人仅仅在思想活动中经历了他们自己未来的历史及历史活动。“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1](P7)这就是说,要解决德国式问题,探索德国式问题解决的真正出路,就必须对反映这一问题的哲学思想进行深入的批判与清算。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继德国政治制度批判之后,马克思又把批判的重心转向了对德国国家哲学思想的批判。“当我们不批判历史未完成的著作,而批判历史的遗著———哲学的时候,批判就恰好触及到了当代社会问题的中心。”[1](P7)这意味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对与德国社会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政治制度)不相符合的国家哲学思想进行深刻的理论批判,实质上也就是对德国现实政治制度的理论批判。
德国的国家哲学之所以成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对象,其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不仅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延续,而且是唯一正式的、与当代欧洲社会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正因为如此,要使人民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社会活动成为现实,就必须对阻碍“现实的人”及其幸福生活得以实现的德国政治制度及反映这种政治制度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德国的未来既不能局限于对现实的国家、法律、制度的直接否定,也不能局限于观念上的国家、法律、制度的直接实现。观念上的制度实质上就是对现实制度的直接否定。[1](P8)马克思的这一论述,不仅如实地指出了德国社会落后于欧洲先进国家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德国社会在面对这种历史现实时的思想状况。在肯定德国实践政治派对国家哲学否定的正当性的同时,马克思也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他们理论本身的缺陷———他们没有看到“德国人民现实的生活萌芽一向都只是在他们的脑壳中萌生的”,因此,“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1](P16)。
在批判实践政治派缺陷的同时,马克思也对理论政治派的缺陷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理论政治派虽对敌手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却对自身采取了非批判的态度,他们不仅忽视了哲学思想本身就来源于现实世界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搁置了哲学思想本身也是对现实世界在观念上的反映、补充的事实。正是这样,理论政治派要么从哲学的一般前提出发,要么把从其他学科得出来的结论不加任何反思地直接作为哲学的一般要求和结论来使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理论政治派的错误就在于,他们对德国现实世界的批判,仅停留在思想领域,严重忽视了德国社会的现状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在他们看来,不把哲学反映的理论应用到现实中去,就能使哲学思想所反映的理论直接化为现实。但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此岸世界的真理”,就必须从此岸世界出发,对此岸世界的历史状况及反映此岸世界历史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因此,只有通过对此岸世界的历史状况及反映“此岸世界真理”的哲学思想进行批判,才有可能真正改变“现实的人”的生活处境,进而重新确立他们作为历史活动者的主体地位,并以此来恢复“现实的人”的真正本质。
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深刻的理论表述。[1](P9)换句话说,黑格尔哲学以思辨的言说方式,完成了德国社会在观念层面上的、未来的历史活动。但在其现实性意义上,这种哲学思想所呈现的“历史”仍然是属于“彼岸世界的真理”,这与“现实的人”的活动及其现实生活的生存处境是严重分离的。所以,马克思认为,必须对黑格尔思辨哲学展开批判性的否定和否定性的批判。这既是对欧洲现代国家以及与其相联系的社会现实的批判性否定,更是对德国政治意识、法意识的整个存在形式的批判性否定和否定性批判。马克思进一步一针见血地指出,思辨的法哲学,这种关于现代国家的理论,它现实的理想化仍然是属于“彼岸世界的真理”。德国人那种置“现实的人”于不顾的、关于现代国家思想理论的产生,只是因为这些现代国家也置“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于不顾,或者说“只凭虚构的方式满足整个的人”[1](P9)。显然,此时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方式还是黑格尔思辨哲学分析问题的方式,但毫无疑问的是,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却是“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生活处境的必要改变,而这就为其社会批判理论思想作了重要理论奠基。
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德国国家哲学对欧洲其他现代国家历史发展及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如实地指出了德国国家哲学思想本身的理论缺陷。马克思认为,德国人在政治理论上思考了其他国家已经完成了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德国是这些国家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理论良心。但德国哲学思维本身的抽象与自大也总是与它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性之间保持着同步。[1](P9)马克思这一批判性分析,充分表明了他对德国政治制度及其国家哲学的理论批判有着深厚的现实感和历史感。马克思试图通过对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理论批判,为“现实的人”的发展和解放提供某种精神性的引导力量。在他看来,要实现“彼岸世界的真理”向“此岸世界的真理”转换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对反映“彼岸世界真理”的德国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深度的理论批判,惟其如此,才有可能实现对此岸世界的变革、不合理社会现实的实践改造。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推毁。”[1](P10)但毋庸置疑的是,反映社会进步的理论和思想一旦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思想理论本身一旦与“现实的人”的实践活动相结合,它就会转变成变革世界的物质性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P10)由此观之,在这里,马克思不仅明确指出了理论变革对改善“现实的人”现实生活状况及其现实生活处境的重要性,而且也揭示了变革“现实的人”的生存处境是他们历史活动实现和发展的最终目的。在马克思看来,思想解放对德国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活动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它将彻底改变和颠覆一切奴役和压迫人民群众的社会关系。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如同德国过去的宗教改革是从僧侣的思想认识活动开始的一样,德国社会革命的变革也应当首先从哲学家的思想认识开始。“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1](P11)换言之,彻底的社会变革不仅需要被动的因素和一定的物质基础,而且也需要与变革这种现实状况相适应的哲学思想。这样,马克思对德国国家哲学的批判就实现了自身的飞跃:一方面,它使社会意识的神秘性在根本上被彻底打破;另一方面,它也使传统社会意识与实在之间的关系被彻底地颠倒过来,从而使人类一切活动的最终解释,不再被归因为某种特殊的精神性存在。[2]这就是说,马克思对德国国家哲学的深刻批判和强有力的理论解释,既阐明了精神活动对“现实的人”社会活动的意义,也阐明了物质基础变革对“现实的人”生存处境改变的优先性基础地位。
四、“现实的人”的普遍解放: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落脚点
任何形式的社会批判理论都不是为批判而批判的,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也是如此。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及国家哲学的三重批判,毫无疑问最终都指向了一个最基本的命题,那就是“现实的人”的彻底自由与普遍解放。普遍的人的解放、彻底的社会变革,对整个德国人民来说,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而是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从自身所处的历史地位出发所从事的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解放和自由的社会活动。马克思认为,在德国,整个社会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就是每一“现实的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在德国,整个人民群众的普遍解放和自由是任何部分人民群众普遍解放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在德国,整个社会的普遍解放和自由,恰恰应当是由部分人民群众逐步解放、自由的不可能性而产生。[1](P14)质言之,整个德国人的普遍解放和自由,必须依赖一个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的阶级即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这是因为,这个阶级是一个被彻底戴上锁链的阶级,对他们来说,这个社会领域自身并不会让他们享有任何特权,而只是求助于人们自身的社会权利。威胁这个社会领域的不是特殊的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求助任何历史的权利,而只是求助每一“现实个人”的权利,且最终形成一个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里解放出来的,并成为一个以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为自身神圣历史任务和责任的社会领域。[1](P14)也就是说,只有具有“完全普遍性质”的社会领域的形成,才有可能使“现实的人”最终完全恢复到自己本身。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自身普遍自由的解放者,德国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不断兴起的工业化运动才可以形成。这是因为,在德国,从本质上来说,组成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由工业化活动所造成的。这一群体不是在历史进程的重负下被机械地挤压出来的,而是因工业化所造成的社会急骤解体,尤其是因中间等级这一群体的普遍解体而产生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这一群体来说,他们要使自己能够从这种制度的解体过程中完全恢复到自己本身,必须通过对私有财产的公开否定来完成。迄今为止,无产阶级宣告世界制度的最终解体,只不过是如实地揭示了他们本身存在的秘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个世界制度最终解体的重要诱因。由此可见,德国无产阶级要改变自身生存、生活的现实处境,并最终使自己成为自己的真正主人,就必须彻底否定阻碍他们普遍解放和自由发展的私有制。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德国,无产阶级之所以敢公开、彻底地否定私有财产,那是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把已经提升为无产阶级原则的东西进一步提升为整个社会的原则。因此,整个无产阶级最终的普遍解放和自由,是任何部分人民群众普遍解放和自由的前提和基础,归根结底,他们是实现整个社会和自身彻底解放、自由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无产阶级作为人类社会整个解放和自由发展的重要力量,他们与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
由此观之,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始终都是围绕“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改变来进行的,无论是对宗教及宗教意识的批判,还是对德国国家制度及国家哲学的批判,都把“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观点,作为“现实的人”及其自由和解放理论思想奠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换言之,《导言》一文不仅赋予了无产阶级全新的历史地位,而且也赋予了无产阶级神圣的历史责任和历史任务。在马克思看来,对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对正在生成的世界所拥有的权利,就如同德国国王对已经生成的世界所拥有的权利是一样的。[1](P16)在这里,马克思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彻底的解放和自由,就必须夺取国家政权的理论和思想,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指出了,如果无产阶级不摧毁一切束缚自身发展的奴役制,那么,任何一种形式的奴役制都不可能最终被彻底摧毁。这就是说,如果无产阶级不从根本上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他们就不可能承担起自身普遍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责任。马克思由此将“武器的批判”和“批判的武器”结合起来,科学地创立了具有自身理论特质的社会批判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真相”。当然,这个“真相”还在发展,批判也必须继续下去。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揭示了无产阶级神圣的历史任务和历史责任,由此一定程度上也为“现实的人”的彻底解放和自由提供了一条社会变革的途径和方式。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对“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的理论和思想作出深刻的阐述和分析,但毫无疑问的是,马克思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建立在“现实的人”及其解放和自由这一落脚点之上了。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深刻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不仅意味着马克思已经开始对现代社会的政治进行哲学批判,而且也意味着他已经开始着手对现代国家学说及其现实的社会基础进行批判。[3]换言之,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理论进行深刻理论批判的同时,也迈出了为政治哲学奠基的重要一步。进一步说,就是把国家的形式和法的关系归结于它们的现实基础。这样以来,马克思所面对的现实,就不是被思辨哲学所神秘化了的社会现实了,而是与现实世界密切相关的、非神圣化的社会现实,即世俗化的市民社会。与此同时,马克思所面对的人,也不是抽象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了,而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现实化的个人了。
概而言之,马克思对德国宗教意识、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哲学的三重批判,都是围绕着“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存环境来进行的。“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的现实环境,既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对象,也是这一批判理论得以展开、奠基的现实依据。对“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的现实关怀,既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产生的理论旨趣,也是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现实的人”之所以构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始终处在自然和历史的交汇点上。“现实的人”及其生存环境是自然进化和人类创造自身历史的开端,因而也就成为了一切历史过程和社会关系的基本前提和核心。[4]当然,在《导言》一文中,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视野可能还是偏颇的而不是开阔的,是民族的而不是国际的,是德国的而不是整个欧洲的,更不是全世界的。甚至,《导言》通篇所用的语言、基调及所透视的问题也是德国式的,但这是马克思社会批判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理论产生、发展的必然阶段。换言之,《导言》一文虽有完整社会批判理论视野的理论缺失,但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史上,却首次完成了马克思社会批判和“现实的人”及其自由解放理论的思想奠基,在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无疑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2] 姜迎春.论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特点[J].江海学刊,2012(5):55.
[3] 吴晓明.黑格尔法哲学与马克思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奠基[J].天津社会科学,2014(1):22.
[4] 侯惠勤.马克思主义的个人观及其在理论上的创新[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2):61.
[作者简介]王建锋(1970—),男,河南省洛阳市人,洛阳师范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哲学、伦理学基本理论及应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4CZX060)
[收稿日期]2015-08-14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5-0010-07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B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