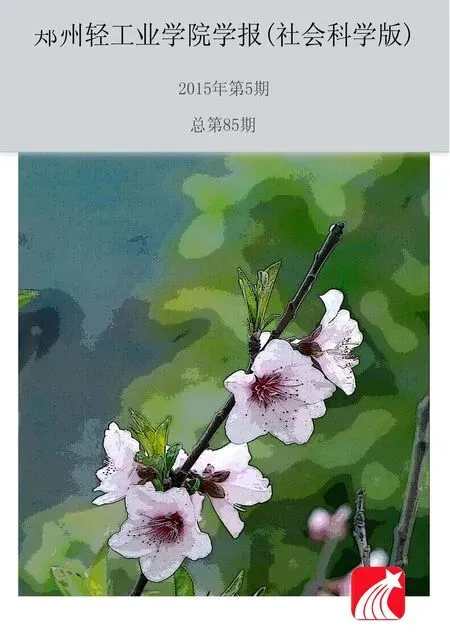科学事实的实验室建构根源探析
邱德胜(西南大学哲学系,重庆400715)
科学事实的实验室建构根源探析
邱德胜
(西南大学哲学系,重庆400715)
[摘 要]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科学事实是对事实的客观表述或直观呈现,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前提和基础,因而是与价值无涉的。然而,兴起于西方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对实验室构建的研究结论与此大异其趣,指出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实验室建构科学事实的根源在于:实验室研究对象的非自然性、实验室研究目标的非真理性、实验室研究过程的与境偶然性、实验室研究结果的可能创新性。正是SSK对科学事实与科学论文建构过程的人类学研究,才逐渐打破了正统科学哲学对科学进行合理性辩护的神话,使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一种作为日常实践活动的轨道上来。然而,实验室研究所贯穿的社会建构论主张片面否定科学客观性的叙事逻辑并不被科学共同体一致认同,因而,如何准确理解与合理把握科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建构性与实在性之间的界线和限度,还有待科学哲学和SSK的深入探究。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实验室研究;科学事实;社会建构论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5.05.003
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科学事实是对客观事实的表述,是科学理论形成的前提与基础,因而是无涉价值的。然而,随着19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SSK)的兴起,这种观念逐渐被打破。法国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家拉图尔、美国科学知识社会学家和科学人类学家卡琳·诺尔-塞蒂纳等人文学者,不仅认为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的产物,还直接深入到科学知识生产的第一现场———实验室,试图找寻科学事实实验室建构的第一手证据。他们通过对科学事实、科学论文在实验室中复杂建构过程的考察,写出了多部实验室研究的民族志作品,其宗旨不仅在于揭示科学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更在于传达SSK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以最终实现对正统科学哲学的质疑与批判。本文拟通过对SSK科学事实实验室构建根源的梳理,进一步明晰SSK社会建构论的基本立场,促进大众全面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增强科技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实验室研究对象的非自然性
从词源学的角度看,所谓“事实”(fact)就是指“已经被制作出来的东西”,与其在拉丁语中的词根facere即“制作”是一致的。然而,从科学实在论的视野看,事实就是已知的实体,尤其是科学事实,绝不会是一种社会建构的产物。在正统科学哲学看来,世界皆由事实所构成,知识的目标就在于提供一种关于世界本来面目的如实说明,这种说明往往借助科学的经验规律和理论命题得以实现。但基于SSK的实验室研究断然反对这种观点,它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充满着建构性而不是描述性,是由决定和磋商组成的链条。实验室是一个操作人工物的作坊,而不是自然物显现自身的地方,换言之,实验室研究的对象不是本真自然,其研究对象具有非自然性。
首先,实验室很少研究作为本真状态的自然物,相反,其研究对象经常是想象或视觉、听觉、电等的踪迹,研究它们的构成、提取物、纯化了的样本。实验室给予我们的印象是一个由桌子、椅子构成的工作空间,以及仪器和设备的累积。实验用的所有原材料被特地种植并被选择性地培育出来,多数的物质和化学药品被净化,并从服务于科学的工业或者从其他实验室得到,甚至实验所用的水也要经过特殊的处理。这些物质与测量仪器如同发表的论文一样,都是人类努力的成果。正如塞蒂纳所言:“实验室的现实是高度人工化的。它像一个工厂,不是被设计来模拟自然的建制。实验室中不仅不包容自然,甚至尽可能地将自然排除掉了。科学家在实验室中所面对和处理的都是高度预构好了的人造物。”[1]
其次,不仅实验的对象是非自然的或人工的,而且实验室所使用的仪器设备也是人工的。实验室研究是借助实验仪器、实验工具等人工建造物,来对实验对象进行观察、识别、筛选、控制,从而得出一些基本结论的过程。显然,实验室研究所得结论是人工物(科学仪器)与人工物(实验对象)之间互动的结果,不是对自然界本身的描述。塞蒂纳指出:“科学研究是借助工具操作的。在实验室中,科学研究的工具性不仅在科学家所操作的‘事情’的性质中表现出来,而且也体现在科学行动的专注中。这种借助工具所完成的观察,在很大程度上截断了事件的自然路线。”[1]由此看来,在实验室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很难找到一个与描述主义科学观完全相符的“自然”或“实在”———纯客观的自然必然地成为实验室的受害者。
再次,不仅实验对象非自然,而且实验现象也可能是人为建构的,而实验仪器和设备则成为实验室建构实验现象的帮手。正如拉图尔所言:“事实上,现象只取决于设备,它们完全是通过实验室所使用的仪器制造出来的。凭借记录仪,人们完全可以制造出人为的实在,但制造者却将人为的实在说成是客观的实体。”[2](P64)如何将人为的实在转化成客观的实体,这离不开科学论文的作用。科学论文一旦发表出来,人为建构的实在将被看作一种客观的实体,后人在引用相关论文时,不会再考虑实在建构过程中的人为或主观因素,于是,主观实在便转变为客观实体,并成为后续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为了使这种转变更为合理和自然,一篇篇条理清晰、逻辑严密的科学论文都可能是人为建构的产物。[3]正如塞蒂纳所言:“论文是对实验室的一种建构,完全类似于其他的实验室建构。”[4](P94)
简言之,不论是实验对象、实验工具还是实验现象,它们都可能是自然世界所不具有的、是人工的,因而,通过对非自然物或人工物所做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最多也只不过是对人工对象的基本规律的说明。由此可见,实验室研究对象的非自然性将导致实验室科学的不自然和非自然,这进一步表明了实验室科学所具有的建构本性。
二、实验室研究目标的非真理性
通过对实验室日常实践的考察,塞蒂纳等人发现,实验室科学家的科学实践并不是以探索真理为目标的,而是遵循着另外一个原则:“如果存在一种似乎可以控制实验室行动的原则的话,那么,它就是科学家对使事物‘运行’的关切,这种关切表明一种成功的原则而不是关于真理的原则。”[5]拉图尔和伍尔加提出了与之相似的看法:“观察人工事实的构成,……真实性是事实建构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这就意味着,科学家的活动是致力于有关陈述的加工,而不是致力于‘真实性’。”[2](P236-237)由此看来,实验室的日常行动是以成功为目标,而不是以真理为目标的,从这一意义上说,真理是实验室的又一个受害者。
需要说明的是,“使事物运行———产生结果———并不等同于对它们进行证伪。产生一些不顾潜在的批评的结果,也并不是实验室所关心的问题”[4](P4)。当实验室产生了实验结果之后,科学家首先要做的就是防范在实验结果公开之后所可能面对的批评。于是,在结果公开之前,科学家会通过小型会议等各种方式来反复论证一些问题,如关于事物如何运行、为何运行和为何不运行,为使它们运行应采取什么样的步骤、词汇等。在塞蒂纳看来,“这种词汇事实上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适合在被称为‘实验室’的知识作坊里对知识进行的工具性制造”[4](P4)。这种工具性制造实际上也是对事物运行取得成功的关切,而关注成功与追求真理相比,是一种更加世俗的追求,这种对事物运行的关切一旦取得成功,它将通过出版物在科学的世界里不断地演变为科学家的荣誉。
实际上,实验室的受害者远远不止“自然”和“真理”两个方面,科学理论也可能是实验室实践的受害者,这是因为,实验室的理论有时表现为一种“非理论的”特征。理论往往隐藏在对“发生了什么
情况”与“实际情况如何”的解释的背后,它们把自己伪装成对“如何理解它”这一问题的暂时答案。各种理论与实验室的工具性操作变得不可分离,这些理论也被依次编排到实施实验的过程之中。在塞蒂纳看来,实验室研究中的理论更类似于政策,而非信条。这样的政策使解释与策略性的机智、巧妙的计算融合起来。而此时政策的运用就如同实验室对“成功”的关切一样,必然会与一种利益结构相联系。于是,“纯粹的理论就可能被称为一种幻想,即科学从哲学那里保留下来的幻想”[4](P4)。简言之,
随着实验室科学实践的继续,“自然”“真理”乃至“理论”,便逐渐地消逝,而所谓的科学事实也不过是一种实验室的建构物罢了。
三、实验室研究过程的与境偶然性
在塞蒂纳等人看来,实验室的科学实践过程是一个建构性的过程,而这种建构包含着决定和商谈的链条,通过这一链条,实验的结果也被建构出来。换言之,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必须做出决定,而如何做出决定,涉及科学家的一系列选择(包括对决定标准的选择与转换),而选择本身又与科学家所处的与境*“与境”与英文中的context一词对应,也译为“上下文”或“脉络”。其含义主要包括“语义”和“生成”两方面:在语义构成上,包括理论、方法、价值等成分;在生成方面,包含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心理的等因素。塞蒂纳主要在生成层面使用“与境”一词,但这层意思是context译法中的“上下文”“语境”或“脉络”所不具有的。密切相关。由此看来,科学家对科学事实的实验室建构与多方面的因素相关。
首先,科学家的选择标准具有层次性和可转换性。实验室科学成果的做出往往与科学家的日常选择有关,而这种选择有人为的成分。换句话说,科学成果不大可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相同的方式被再生产,重复一个已有的实验过程极不可能,除非实验过程的多次选择被固定下来。这种观点与柯林斯在“复制TEA激光器”“探测引力辐射”中关于科学争论的探讨不谋而合。[4](P4)与实验室的内部建构相比,现实情况更加复杂,由于科学家之间存在着交流、合作和竞争,所以影响他们做出选择的标准将更多,而选择一旦做出,以前的选择将对后续的选择产生影响。在塞蒂纳看来,“以前工作的选择构成了能够使科学研究得以继续的一种资源,即这些选择提供了工具、方法,并提供了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可以利用的解释”[4](P96)。而在拉图尔和伍尔加看来,每当一个陈述稳固下来,它就假扮成机器、铭写工具、技巧、常规、偏见、推论、纲领等,并被重新引入实验室和研究过程。[2](P236-237)由此看来,实验室日常选择的标准会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而选择一旦完成,与实验结论相关的选择标准的产生过程都将被人为地隐藏。正如塞蒂纳所言:“当科学家把这种偶然性和与境性选择转化成‘发现成果’,并在科学论文中加以‘报道’的时候,科学家自己实际上就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非与境化了。”[4](P47)拉图尔和伍尔加也指出:“一旦一个最终产物、一个铭写被获得,导致这种产物的所有可能性的环节都将被遗忘。图表或者数据单变成了在参与者之间讨论的焦点,产生这些图表和数据的物质性过程要么被遗忘,要么被作为纯粹的专业事物被视为理所当然。”[2](P63)拉图尔还进一步指出:“事实除了是一个没有情态和……没有作者痕迹的陈述之外什么也不是。”[2](P82)
其次,科学家日常选择具有索引性。索引性本是常人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塞蒂纳借用这个概念有其特别的含义。在她看来,“‘索引性’主要是指科学活动的境况偶然性和与境定位。这就造成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这些成果是由这些活动者的特殊利益、由当地的而非普遍有效的解释来运载的;并且,科学活动者利用了对他们活动的境况定位的限制。简言之,科学活动的偶然性和与境性证实了科学成果是一种具有索引逻辑标志的混合物,这种索引逻辑表示了科学成果的特性”[4](P33)。
境况偶然性也可以理解为机会主义。在科学家的科学实践中,偶然性无处不在,科学家的日常选择事实上多半建立在机会主义的基础之上。一旦与某个实验相关的一系列操作在偶然性的选择中得以完成,实验结果便呈现出来,而此时的结果看起来是如此的合理和客观,但是它的过程充满着偶然性。正如塞蒂纳所言:“科学家是‘实践推理者’,实验室行动是在一种复杂排列的环境中进行的,科学家的行动就是设法降低环境的复杂性,从无序中制造出秩序,‘产生工作结果’”。[1]她同时指出:“在实验室呆上一天,通常就足以给观察者留下科学家在无序中操作的印象;而在实验室呆上一个月,观察者则将对下面一点深信不疑,即实验室的大部分工作都与消除和补救这种无序有关。”[4](P123)
索引性的另外一个方面是与境定位,它与实验室的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而环境因素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首先,环境因素包含实验室的物质环境,如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的使用状况、实验物质的浓度、纯度等。其次,环境因素包含实验室的地方性特质。实验室的日常实践往往会受到当地一些政策或官方倾向的影响。如有些地方的政府部门为某些实验操作制定了特定的标准,如在实验室中应该选择哪种物质,物质的数量多少,做实验的时间应该是多长等,这些都会导致不同地方的实验室所做的实验在结论上存在着差异。第三,环境因素包含实验室的规则与权力等。例如,某实验室有一台极其昂贵的大型设备,但关于这台设备如何使用则由实验室领导来决定,领导可能制定实验室的相关规则,而这些规则往往会随着权力的改变而改变。
正是由于实验室科学家的日常选择会受到工序的机会主义、当地的特质,以及社会与境等的影响,因此其科研成果也就表现为一种与选择相关的复杂合成物。换言之,随着实验室的境况偶然性和与境定位的变化,实验室选择的索引性也将发生改变。同样清晰的是,实验室的选择一旦演变为最终的成果,这种成果将与其选择的偶然性和与境性不可分离,从而导致科学知识反映出地方性和特异性的特点。
四、实验室研究结果的可能创新性
实验室与境的偶然性或不确定性,导致了科学家选择的随机性和多样性,这也是科学事实是由实验室建构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塞蒂纳等人看来,实验室与境的偶然性对科学发展而言并没有什么坏处,反而有时候还会导致科学的创新。换言之,不确定性的影响不再被看作纯粹破坏性的,它不单单是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噪音”,也不再像遗传密码中妨碍正常的生物复制的“错误”,或者像热力学系统中的“紊乱”,相反,不确定性对日益复杂的系统的进步性组织而言是必要的条件,尽管存在着局部的信息错误或信息丢失。[4](P10)
塞蒂纳借助遗传密码的复制来解释上述观点,在她看来,“人们认为遗传密码复制中出现的错误是导致突变的原因。然而,这种发生在(严格复制中)遗传层次上的随机事件,可能借助某种变异而使物种受益,这种变异相比原来的种群而言能更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这些物种通过结合一种有序的突变……而‘重新建构’自身”[4](P10)。与生物的某些突变可能会走向好的结果一样,科学知识也是一种被渐进地复杂化建构或重构起来的知识。在塞蒂纳看来,这里的复杂过程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科学具有建构‘新的’信息的能力,即产生创新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对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对问题的挑战做出回应,科学明显地越来越能够建构和重新建构它自身。”[4](P11)
然而,在科学家的日常科学实践中,虽然他们经常面临诸多选择,但他们在做出选择时也不是完全随机的,而是朝着某个目标迈进的。换言之,科学成果本身虽是实验室复杂建构的结果,但这种建构方向很明确,其目标就是得到创新性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是有意图的定向研究的结果。虽然实验室存在着诸多的偶然性,但是科学家会想方设法将这种偶然性整合到生产创新性成果的过程中来,而如何整合这些偶然性则与科学家既有的知识和经验有关,如哪些研究该做,哪些研究不该做,哪些地方该忽视,哪些地方可以进行大胆的猜测等。为了得到创新性的成果,科学家还会对具有高度选择性的材料加以修补,以实现预期的目标。简言之,科学家可能为了追求创新性的成果而会对实验室的各种偶然性加以取舍和整合,即对这种偶然出现的新信息进行建构或重构,在科学家个人努力创新的过程中,不存在非定向的或纯粹随机的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室的选择不是与个体做决定相关联,而应被看作是社会互动和磋商的结果。同时实验室的成果与实验室的“思想”是这样一种社会事件,即这些事件是在与其他人的相互影响和相互磋商中产生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实验室成果或是科学事实的产生都有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不过这种建构有时因为对偶然性的把握得当而孕育了科学的创新与进步。
五、结语
综上所述,实验室的科学实践并不在于追求关于自然世界的真理,而只是一种使事物成功运行而采取的权宜性的选择。这种选择还经常渗透着决定,而这种看似偶然的选择或决定将可能导致科学的创新。此外,科学事实的建构只是实验室实践的一个方面,科学家要想将实验室建构的科学事实固定下来,往往还得借助相关论文的发表才能得以实现。
值得指出的是,科学事实的出现是一种与社会因素密切相关的实验室建构过程,在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中,与实验室相关的一些与境因素会渗透进去,正是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科学家的活动才具有了复杂的动机。而科学家的动机之所以复杂,除了受实验室内部因素的影响外,实验室外部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忽略,正如拉图尔所言:“如果我们想在科学家和工程师工作的时候跟随他们,所有这些研究(主要指文本与话语分析),无论它们多么有趣和必要,都是远远不够的。不管怎么说,科学家和工程师们不是一天24小时都在制定计划草案、阅读和写作论文。他们总是争辩说,在技术文本的背后存在着某种比他们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更重要的东西。”[6]也就是说,不管我们对科学文本或话语作了如何详细的分析,科学家的研究动机还是很难发掘出来,而这种研究动机无疑会影响科学知识生产的全过程。
应该说,正是SSK对科学事实与科学论文建构过程的人类学研究,才逐渐打破了正统科学哲学对科学进行合理性辩护的神话,使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一种作为日常实践活动的轨道上来。然而,实验室研究所贯穿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俯拾皆是,这种片面否定科学客观性的叙事逻辑并不被科学共同体一致认同,因而,如何准确理解与合理把握科学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建构性与实在性之间的界线和限度,还有待科学哲学和SSK的深入探究。
[参 考 文 献]
[1] 肖显静.实验科学的非自然性与科学的自然回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1):107.
[2] Bruno Latour,Steve Woolgar.Laboratory Lif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
[3] 邱德胜,任丑.科学家如何建构科学论文———兼议实验室研究视域下的科学论文观[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146.
[4] Karin Knorr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M].New York:Pergamon Press,1981.
[5] Harry Collins.Changing Order: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M].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LTD,1985:41.
[6] Bruno Latour.Science in Action: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M].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63.
[作者简介]邱德胜(1975—),男,湖北省武汉市人,西南大学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规划项目(2013QNZX1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3M542250);重庆市博士后科学基金特别资助项目(Xm201358);西南大学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重点项目(SWU1409111)
[收稿日期]2015-07-12
[文章编号]1009-3729(2015)05-0017-05
[文献标志码]A
[中图分类号]N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