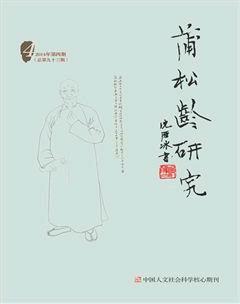蒲松龄《抱病》《病足》《念奴娇》等诗词编年推断
王光福
摘要:路编《蒲松龄年谱》谓蒲氏《抱病》等诗写于康熙十八年,盛编《蒲松龄年谱》谓《病足》等诗写于康熙二十五年,袁世硕先生谓蒲袁酬答词全在康熙二十四年。其实,蒲氏《抱病》、《病足》、《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等作品,均有可能写于康熙十八年,“抱病”和“病足”说的实际是一回事。因此,有关聊斋诗词的编年问题,应该重新考虑。
关键词:聊斋诗词;抱病;病足;念奴娇;编年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一
路大荒先生编《蒲松龄年谱》“康熙十八年己未(一六七九),先生四十岁”下云:
先生是年四十岁,有以四十为题五律一首……是年春,《志异》书大体已成,先生有自序……同年夏秋抱病,时逾三月,感赋七律、五律各一首……而新秋月夜病中又感赋词四阕,调寄大江东去…… [1]26-28
盛伟先生编《蒲松龄年谱》“康熙二十五年丙寅(1686),四十七岁”下云:
先生自春至秋病足未愈。有《病足》及《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2]3392
在路编《蒲松龄集·聊斋诗集》中,《年谱》中所提到的三首诗系于康熙十八年己未;在盛编《蒲松龄全集·聊斋诗集》中,《年谱》中所提到的两首诗系于康熙二十五年丙寅。路编《年谱》所提到的“新秋月夜病中又感赋词四阕,调寄大江东去”,即《聊斋词集》中之《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
袁世硕先生《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蒲松龄与袁藩》云,袁藩曾先后两度住进西铺毕际有的石隐园中,第一次在康熙十二年(1673),原因是与毕际有一起编修《淄川县志》,第二次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原因是协助毕际有校刊毕自严的《石隐园集》。
蒲松龄与袁藩作词酬答,全在康熙二十四年秋袁藩病卒前数月再度寓石隐园之际。[3]181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发现其中有明显的龃龉不合和启人疑窦之处。例如,蒲松龄《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词到底作于何年?在康熙十二年到康熙二十四年之间袁藩真的没有到过石隐园吗?蒲松龄的“抱病”和“病足”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下面我们联系《聊斋诗集》和《聊斋词集》中的具体作品,对此试做剖析。
二
蒲松龄是哪一年到西铺毕家坐馆的,现在已经有了结论,即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是这一年的什么季节呢?我们还记得《聊斋自志》篇末所署的日期是“康熙己未春日”,到毕家坐馆对蒲松龄和毕家来说,都不是小事情,不可能是突然议定的,所以蒲松龄应该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将以往所作的《聊斋志异》整理成卷做一初步结集,并撰写序言,以便下一步专心致志设帐教学,因此《聊斋自志》的写作时间应该在到西铺毕家之前的早春。因为同年春天,蒲松龄就到了西铺毕家,这有他的聊斋诗词为证。
系于此年的《病中》诗云:
抱病经三月,莺花日日辜。
惟知亲药饵,无复念妻孥。
骨瘦心弥瘁,想痴梦亦愚。
若能身强健,端不羡蓬壶。
“抱病经三月”,不是说抱病经过了三个月,而是说抱病经过了三月份。因为蒲松龄接着说“莺花日日辜”,如果是经过了三个月的话,辜负的事情就不可能仅仅是“莺”和“花”了。南朝梁丘迟《与陈伯之书》云:“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蒲松龄所说的“三月”,也就是丘迟所说的“暮春三月”。既然经过了三月,那就说明,最晚二月份蒲松龄就来到了西铺毕家。蒲松龄得的是什么病呢?从诗中我们看不出来。尽管他说“骨瘦心弥瘁,想痴梦亦愚”,但“骨瘦”、“心悴”只是一种艺术性的诗意表达,说的只是一种愁,决不能算是一种病,更不至于因此而只能卧病在床,而不能到园林中观花闻莺。我们知道,就是日日忧愁并且肺病缠身的林黛玉,也没有辜负大观园中的鸟鸣花放。
同年的《四十》诗云:
忽然四十岁,人间半世人。
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
坐爱青山好,忽看白发新。
不堪复对镜,顾影欲沾巾!
这首诗写于此年的几月份呢?四月份。我们知道,蒲松龄的生日是明崇祯十三年(1640)的四月十六日,那他写诗志念自己的四十岁,一定是在其生日前后或者就在当天,绝不会离四月十六日太远,何况像这样的诗蒲松龄能够提笔立就,是用不着构思多长时间的。康熙二十年(1681),蒲松龄四十二岁时写有一首《四十二岁初度》诗,其中有句云:“今日我初度,四十二岁人。”这就写在生日当天,可证《四十》诗写在四月中旬是肯定无疑的。诗中说“愁与病相循”,看来此时其病尚未痊愈。
同年的《抱病》诗云:
瘦骨支离似沈郎,高斋兀坐转悲凉。
怀中多绪愁愈病,漏下无眠月满床。
近市颇能知药价,检书聊复试疑方。
朝朝问讯唯良友,搔首踟蹰意暗伤。
“瘦骨支离似沈郎”,用历史上沈约多病的典故说自己多病体瘦。“高斋兀坐转悲凉”,是说自己独自端坐书斋不禁悲从中来。联系上文所说,蒲松龄抱病,不能到园中听鸟观花,但是却能“兀坐”。虽然“兀坐”也是一种形象化的说法,但形象必须以具体的生活为基础,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整天躺着,绝不可能写出“兀坐”的形象。并且此诗还说“朝朝问讯唯良友,搔首踟蹰意暗伤”,虽然在高斋“兀坐”着,但却不能自由行动;对良友的问讯,只能报以搔首踟蹰,却不能去探望良友。
这是一种什么病呢?来看望他的良友是谁呢?
三
我们再来看系于康熙二十五年的几首诗。先看《病足》诗:
花雨朝朝落,鸟声日日繁。
三春常抱病,一月不窥园。
服没怀妻子,回旋劳梦魂。
高斋愁不寐,冷月自黄昏。
首联“花雨朝朝落,鸟声日日繁”,可与《病中》诗的“莺花日日辜”相参,“花雨朝朝落”说的就是“花”,“鸟声日日繁”说的就是“莺”。颔联的“三春常抱病,一月不窥园”,可与《病中》诗的“抱病经三月”相参,“三春”和“三月”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暮春三月。颈联的“服没怀妻子,回旋劳梦魂”,可以和《病中》诗的“无复念妻孥”、“想痴梦亦愚”相参,尽管一说“怀”,一说“无复念”,但相反而相成,说“无复念”正是因为“怀念”。尾联“高斋愁不寐,冷月自黄昏”,可以和《抱病》诗的“高斋兀坐转悲凉”、“漏下无眠月满床”相参,一个“愁”字正好解释“悲凉”,“满床”的也正是“昏黄”的“冷月”。endprint
再看《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诗:
一庭竹树搅西风,冷入荻帘短烛红。
沈约何时非病里?少陵常是在愁中。
年年弃垒如秋燕,策策惊心见早鸿。
自分穷愁惟我甚,何期憔悴与君同!
此诗颔联“沈约何时非病里?少陵常是在愁中”,可以和《抱病》诗的“瘦骨支离似沈郎”、“怀中多绪愁愈病”相参,“沈约”就是沈郎,如果说在古代文人中沈约是“病”的代表,那杜甫也可以算作是“愁”的化身。此诗首联说“西风”,说“冷”,颈联说“秋燕”,说“早鸿”,可见都是秋天。聊斋诗词中还有没有证明蒲松龄秋天病足的材料呢?有,在聊斋词中。
在看聊斋词之前,我们再看一首系于康熙二十五年的聊斋诗《重游青云寺》,诗云:
深山春日客重来,尘世衣冠动鸟猜。
过岭尚愁僧舍远,入林方见寺门开。
花无觅处香盈谷,树不知名翠作堆。
景物依然人半异,一回登眺一徘徊。
此时写“过岭”、“入林”、“登眺”等,可见是需要一定的体力和正常的身体才能完成的。而诗中所写的景色虽说是“春日”,却又是“花香”,又是“树翠”,这不可能是春天的一月二月,只能是暮春三月的景色。如果此年蒲松龄真是“三春常抱病,一月不窥园”,并且一病就过了秋天,那他无论如何是不能在此年有青云寺之游的,如果不是《病足》诗和《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诗编年有误,就是《重游青云寺》诗编年有误,我的意见是前者编年有误,前两首诗都应该写于康熙十八年。
其根据是什么呢?
四
我们再来看聊斋词。路大荒先生《蒲松龄年谱》康熙十八年条下系有《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词四阕。此词太长,不俱引,只结合相关问题,征引相关语句。
首先,我认为这组词作于康熙十八年己未(1679)。
在此词中,蒲松龄说“四十衰同七十者,病骨秋来先觉”,蒲松龄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至康熙十八年(1679),正好四十岁,所以“四十衰同七十者”这一句,是路大荒先生定此词写于此年的重要依据。袁世硕先生之所以不同意路大荒先生的看法而将此词系于康熙二十四年,是根据毕际有《编次袁孝廉〈敦好堂集〉题词》中的这几句话:“忆当乙丑夏,余方有校刻先集之役,松篱力疾来践宿诺,时来时往,茶铛药鼎,声相杂也。逾中秋甫一日,而病不可复支,遂以肩舆送归。” [3]181-182可以说,路先生的证据是内证,是蒲松龄自己说的话;袁先生的证据是外证,是毕际有说的话。两位先生的证据,哪一条更有说服力呢?我认为还是路先生的更有说服力,其理由如下。
第一,古人在诗词中运用数字,尽管有虚数实数、举其成数之说,但这里蒲松龄所说的“四十衰同七十者”,却应该看作实际数字而不是举其成数。因为一,《礼记·曲礼上》云:“七十曰老。”杜甫《曲江》诗也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这两说当中,“七十”都是实指而非虚数。所以我们说,既然“七十”是实际数字,那“四十”也应该是实际数字。二,假如如袁先生所云,此词写于康熙二十四年,那从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已经过了六年,蒲松龄已经四十六岁了,如果举其成数,他也应该说离得近的“五十”而不是离得远的“四十”。由此看来,毕际有说得没错,袁藩是在康熙二十四年乙丑住进过石隐园,但在此之前的康熙十八年袁藩进没进过毕府,毕际有只是没说,并不能因为没说就证明没有。袁先生据此认为蒲松龄与袁藩的酬唱只能在康熙二十四年秋天一段时间,而不认为康熙十八年二人就有交往,是因为证据不足,显得过于谨慎了。
第二,此词还说“梦鸟惊笼,吟虫吊砌,多是眠难着”、“前身何似?想半生贫贱,不偿业果”,这些句子,与《聊斋自志》中的“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每搔头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盖有漏根因,未结人天之果;而随风荡堕,竟成藩溷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谓无其理哉”何其相似乃尔!《聊斋自志》写在春天,此词写在秋天,虽然隔了几个月,但心情还保持着同样的感觉,在表述上也不自觉地运用了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及意境,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过了六年之后,还保持和《聊斋自志》中同样的情绪,就让人难以理解了。
第三,此词还说“春去秋来常是病,辜负柳丝花朵。未听新莺,早惊客雁,瘦影愁千裹”、“烂漫花朝,团回月夕,具向床头尽。揽衾长叹,韶光空掷虚牝”,这可和《病足》诗中的“花雨朝朝落,鸟声日日繁。三春常抱病,一月不窥园”、《病中》诗中的“抱病经三月,莺花日日辜”及《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诗中的“一庭竹树搅西风,冷入荻帘短烛红”、“年年弃垒如秋燕,策策惊心见早鸿”相参。此词还说“试看良夜沉沉,碧天无际,风促行云躲,玉露暗漙银汉洁,河畔星星细琐。枕上支颐,床头抱膝,甚处犹差可?仰呼明月:卿卿愿汝怜我”,这可和《病足》诗中的“高斋愁不寐,冷月自黄昏”、《抱病》诗中的“怀中多绪愁愈病,漏下无眠月满床”相参。此词还说“堪怜多病沈郎,频移带孔,未觉腰围紧”,这可和《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诗中的“沈约何时非病里?少陵常是在愁中”、《抱病》诗中的“瘦骨支离似沈郎,高斋兀坐转悲凉”相参。此词还说“禾稼不询,妻孥总置,真似无肠蚓”,这可和《病足》诗中的“服没怀妻子,回旋劳梦魂”、《病中》诗中的“惟知亲药饵,无复念妻孥”相参。
总之,这几首诗词之间存在着如此之多的相似相参之处,我们说写于同一年,是应该具有较大说服力的。
其次,我认为蒲松龄“抱病”、“病中”所说之病,也就是“病足”之病,说白了,就是康熙十八年蒲松龄的脚得了病,不能行走了,只能卧病在床。其理由上文已经联系聊斋诗词的作期做了一些阐述,下面再单独挑出来做一下说明。
第一,蒲松龄的病从春天一直长到秋后,绵连好几个月,并且不能行走。按照常理,这样的病是非常严重的病,好几个月躺在床上,是有生命危险的。可是,西铺毕家却并没有因病而把蒲松龄送回蒲家庄,而是一直让他留在西铺。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蒲松龄的病虽然病情较重并且时间较长,但却不危及生命。正如他在《行乡子忧病》中所说,他的病是“有三分痛,七分痒,万分忧”,疼痛并不是最重要的。这是什么病呢?就是脚病,虽然对行走有碍,却并不太影响吃饭和教学,所以可以放心让他待在毕家。endprint
第二,《抱病》诗说“高斋兀坐转悲凉”。《念奴娇》词说“枕上支颐,床头抱膝,甚处犹差可”,就是说自己的病躺着也不是,坐着也不是,什么姿势也不舒服;此词还说“揽衾长叹,韶光空掷虚牝”,就是说病虽然厉害,但作者并不担心生命,忧愁的只是虚度光阴。此词还说“数武门庭,两重院落,似隔云山者”、“麈尾风清,石纹秋绿,翻乃游踪寡”,说的是距离近而不能至、风景好而不能游。这些也可证明,蒲松龄能卧、能坐,只是不能走,他得的就是脚病而不是别的。
第三,《聊斋词集》中还有一组《贺新凉·喜宣四兄扶病能至,挑灯伏枕,吟成四阕,用秋水轩唱和韵》。光从题目中我们就知道蒲松龄得的是脚病,因为袁藩同样是病人能来看他,而他却不能去看袁藩,他不能去看袁藩,却能在枕头上熬夜作词,并且一作一百余字的长调就是四首,这就是才高如蒲松龄,恐怕也得费大半宿的功夫,可见其精神状态和体力并不太差,这也就证明他只是脚不能走而已,其他都无大碍。此词还说“桃李开时人抱病,不觉露华秋泫”,这和上引诗词中屡屡道及的“从春病到秋”在时间上也正相合。更重要的是,此词还说“驴背装书卷。将出门,男耕女织,尽情分遣。吾辈要除儿女态,宁屑楚囚对泫”,这分明是刚离家不久的回忆和对自己的安慰,这也证明,此词是作于康熙十八年的秋天,所得之病就是脚病。
第四,蒲松龄写了《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之后,袁藩以同调词相和,题目是《再至石隐园,步蒲留仙韵》,其中有句云:“君足蹒跚,予形困惫,辜负良宵者。” [3]183假如蒲松龄的《病足》诗和《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诗真如盛伟先生《蒲松龄年谱》所云,是写于康熙二十五年,也就是说,蒲松龄的脚病是在康熙二十五年得的,我们知道袁藩在康熙二十四年中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死后一年怎么还能写词与蒲松龄唱和呢?相反,袁藩的《再至石隐园,步蒲留仙韵》词,只能写在蒲松龄得脚病之后而不是之前,因此我们说,他这首词也是写在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四十岁的时候。也就是说,蒲松龄的确得脚病,只能是在“四十衰同七十者”的四十岁上。
五
如果上文的推测不错,那蒲松龄的《病足》和《病足经秋不愈,毕振叔时亦抱恙初起,赋以寄之》两首诗的编年就要重新考虑。除此之外,在聊斋词的编年上,我们也可以有所收获。
无疑,《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写于康熙十八年。路大荒先生的说法是对的,赵蔚芝先生在《聊斋词集笺注》中,也持此说:“此词写于至西铺毕家坐馆之初。从第一首‘四十衰同七十者看,时间当在康熙十八年己未作者四十岁时。《聊斋诗集》卷二‘己未年有《四十》、《抱病》、《病中》诸篇,与此词所言情景相符,可以为证。” [4]106赵蔚芝先生在《蒲松龄志·聊斋词》中也说:
康熙十八年己未,蒲松龄40岁,到西铺毕家坐馆。……与袁藩酬唱自此年始,先后有《念奴娇·新秋月夜,病中感赋,呈袁宣四孝廉》四阕、《贺新凉·喜宣四兄扶病能至,挑灯伏枕,吟成四阕,用秋水轩唱和韵》四阕、《贺新凉·读宣四兄见和之作,复叠前韵》、《贺新凉·喜雨一阕,并寄之》诸阕。此外尚有《满庭芳·中元病足不能归》四阕,《浣溪沙·秋柳》、《乌夜啼》、《钗头凤》、《金人捧玉露·雨夜》、《行乡(香)子·忧病》各一阙,亦应作于是年。[5]226
这段话说得极为有理。除了赵先生在《聊斋词集笺注》中举出的理由,我上文的分析论证,也可证明这一观点。赵先生接着说: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袁藩应毕际有之请,复至石隐园,校刊毕自严的《石隐园集》。……是年,蒲松龄因足疾卧病,自《庆清朝慢·卧病》至《应天长·贫家乐》,中间不涉及袁氏的其他作品,亦应作于是年。[5]226-227
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到康熙二十四年之间到底得过几次脚病?如果是一次,那大概是在康熙十八年,《庆清朝慢·卧病》等词的编年就不应该在康熙二十四年;如果蒲松龄在康熙二十四年真的不幸又得过一次脚病,那关于“抱病”与“病足”之问题就真是说不清道不明,只能等待新的材料出现才能说个清楚了。
唐人白居易有一首《足疾》诗。诗云:“足疾无加亦不瘳,绵春历夏复经秋。开颜且酌樽中酒,代步多乘池上舟。幸有眼前衣食在,兼无身后子孙忧。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 [6]2667这和蒲松龄的病情是一样的。可是蒲松龄不能像白居易那样“衣食”“子孙”无忧,他想学取陶彭泽,过无忧无虑的“贫家乐”生活,可拮据的家庭经济状况却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因此,不管是“抱病”还是“病足”,都只是肉体的痛苦,更深层的心灵的痛苦才是折磨他的更严重的“病”。
参考文献:
[1]路大荒.蒲松龄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6.
[2]蒲松龄.蒲松龄全集[M].盛伟,编校.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3]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4]赵蔚芝.聊斋词集笺注[M].济南:黄河出版社,1999.
[5]袁世硕.蒲松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6]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责任编辑:陈丽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