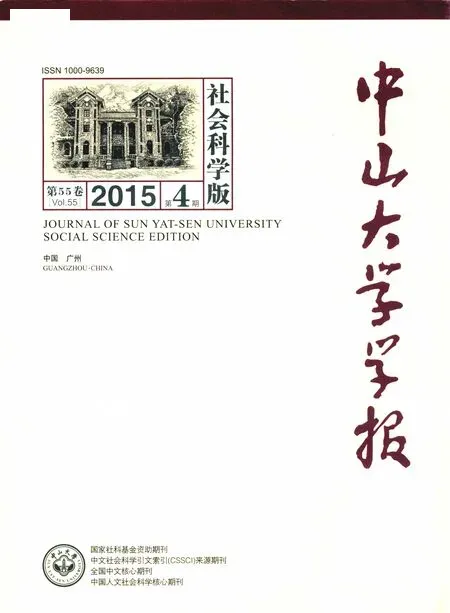说部入集的文体学考察*
何 诗 海

说部入集的文体学考察*
何 诗 海
摘要:自《弇州四部稿》立赋、文、诗、说四部后,“说部”遂成为“小说”的代名词,并在明清时期广泛流行。在目录学传统中,小说长期依违于子、史之间,缺乏稳定的归属,是一种边缘化的著述门类。而在文集与文学批评传统中,小说则长期被排斥于文苑之外,无缘于古代文体谱系。王世贞以一代文宗之尊,创造性地在自编文集中设立说部,与赋、文、诗并驾齐驱,极大提高了小说的文体地位,为小说进入文苑、跻身古代文体之林开辟了通道,具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文体学意义。
关键词:说部; 小说; 目录学; 文集; 文体
一、明清“说部”的内涵
“说部”一词,肇始于明代中叶以后,较早使用此词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是王世贞。万历初,世贞手自编定《弇州四部稿》一百七十余卷,将平生所撰之文分赋部、诗部、文部、说部四大类编次,故称“四部稿”,不同于传统目录学上的经、史、子、集四部。其中“说部”收录《札记内编》、《札记外编》、《左逸》、《短长》、《艺苑卮言》、《艺苑卮言附录》、《宛委余编》七种著作。这些著作内容庞杂,没有明确、集中的主题,体制灵活自由,行文采用随笔札记的形式,难以独立成篇。如果比照目录学史上对相似作品的著录,不难发现,此书“说部”的内涵,与传统目录学上的“小说家”关系密切。如《札记内编》、《札记外编》、《宛委余编》主要记载读书心得,类似读书笔记或学术札记。这类著作宋代以来颇为盛行,著名的如陆游《老学庵笔记》、曾慥《类说》、郞瑛《七修类稿》、王世贞《史乘考误》等,焦竑《国史经籍志》皆著录为“小说家”。《左逸》、《短长》为野史逸闻类,相似著作,如王嘉《拾遗记》,《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杂史类,而《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皆入子部小说类;《汉武故事》,《隋书·经籍志》入史部旧事类,《宋史·艺文志》入别史类,《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小说类。《艺苑卮言》、《艺苑卮言附录》为谈诗论文之作,虽然这类作品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入集部诗文评类,但因其“体近说部”,故多有归入小说家者,如《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录苏轼《东坡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谢伋《四六谈麈》等。尽管古代“小说”内涵驳杂,文体界限模糊,同一著作,可能入子部小说家,也可能入杂家;如果叙事、记人成分较多,还有可能入史部杂史、杂传、别史等类目,但《弇州四部稿》“说部”七种,依作品体性而言,在目录学史上都有著录为“小说”的先例。因此,其“说部”内涵,大致相当于目录学家心目中的“小说”概念,这一点当无疑义。
王世贞之后,“说部”一词逐渐流行,其基本内涵也大体不出传统“小说”范围。如明陈继儒《藏说小萃序》:“书之难,难在说部。余犹记吾乡陆学士俨山、何待诏柘湖、徐明府长谷、张宪幕王屋,皆富于著述,而又好藏稗官小说,与吴门文、沈、都、祝数先生往来。每相见,首问近得何书,各岀笥秘,互相传写,丹铅涂乙,矻矻不去手。其架上芸裹缃袭,几及万籖,率类是,而经史子集不与焉。经史子集,譬诸粱肉,读者习为故常,而天厨禁脔,异方杂俎,咀之使人有旁岀之味,则说部是也。第小说所载,其中多触而少讳,子孙之贤者扃锢不敢行,而不肖者,愕然如坐云雾中,不解祖父撰述为何语。间有诣门而求之,彼且狡狯掩匿,诧以十袭之藏,邀以千金之享,转展一二传,而皆已化为鼠壤蠧夹中物。”*陈继儒:《陈眉公集》卷5,万历四十三年刻本。序文或称说部,或称稗官小说,所指皆无二致。清汪师韩《说部四种题词》之“韩门缀学”条:“诸子十家,终于小说。小说十五家,终于《虞初》、《周说》。班氏谓可观者九家,固以小说为不足观也。刘向采群言为《说苑》,列于儒家,为后世说部书所自始。后人说部,盖兼十家而有之。”*汪师韩:《上湖诗文编》分类文编卷4,光绪十二年汪氏刻丛睦汪氏遗书本。其中的“说部”,亦指小说类著作。又如《四库全书总目》批明沈越《嘉隆两朝闻见纪》“体杂说部”*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434页。;评王士性《广志绎》“其体全类说部,未可尽据为考证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78,第676页。;又指清汪为熹《鄢署杂钞》“大扺多采稗官说部一切神怪之言”,“是特说部之流,非图经之体也,今存目于小说家中,庶从其类”*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44,第1232页。等,都流露出对学术著作采用小说笔法的不满。而从这些批评中不难看出,四库馆臣笔下的“说部”等同于小说家著述。这种观念,不仅贯穿于明代中后期和整个清代,甚至一直延续到晚清民国时期。如王韬《镜花缘序》:“《镜花缘》一书,虽为小说家流,而兼才人、学人之能事者也……阅者勿以说部观,作异书观亦无不可。”*李汝珍:《镜花缘》卷首,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吴曾祺编《旧小说》“例言”:“蒐罗说部诸书,自汉魏六朝,以迄近代,都为六集。其中多世所罕见本,佚文秘典,往往而在,蔚为小说之大观。”*吴曾祺:《旧小说》卷首,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既称“说部”,又称“小说”,实为同义互指。又,民国初年,上海国学扶轮社出版《古今说部丛书》十集六十册,其中所录大部分作品,都曾被目录学家归入小说类,足见明清以来,以“说部”指称小说,已深入人心。
需要注意的是,明清时期,以“说部”指称小说,仅是大体而言;在一些具体语境中,也可能别有所指,不可绝对化。如清金堡《遍行堂续集》分体编次,各体以“部”冠名,计有说部、序部、疏部、记部、传部、赞部、题部、跋部、书义部等。其中“说部”录《善覆无为说示黄碧生太守》、《天下无不可为之事说》、《圣学说为刘子安赠别》、《以德报怨说》、《宗门不必开戒说》等,皆独立成篇的论说文体,既不同于《弇州四部稿》中的“说部”,也与目录学上的“小说”没有直接关系。当然,这种涵义,属于个别现象,不影响对明清“说部”基本内涵的整体判断。另外,从语言系统看,传统目录学上的小说,主要是文言小说,许多作品学术性重于文学性。明清以后,随着白话小说的兴起,传统小说的内涵得到丰富和拓展,以写人叙事、追求文学性为主的白话小说也随之纳入说部范畴。如王蕴章《然脂余韵》称:“《红楼梦》为说部名著,形诸题咏,无虑百十。”*王蕴章:《然脂余韵》卷3,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第29页。《红楼梦》以及此前的《水浒传》、《西游记》等白话章回小说,在传统目录学,尤其是官方目录学中,很少得到著录,但在清代乾嘉之后,特别是晚清民国时期,不但跻身说部之林,且走上了与日俱增的经典化之旅。
二、传统文集中小说作为文体的缺失
明清“说部”的概念,大致相当于目录学上的“小说”,已如前论。而目录学上小说的内涵及地位,则早在汉代即奠定了基本格局。《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序云:
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然亦弗灭也。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缀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当刍尧狂夫之议也。*班固:《汉书》卷30,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1746页。
这段为后世学者反复称引的小序,所论“小说”虽然只是一个被归入“诸子略”类的学术概念,并非文体范畴,却成为研究小说早期发展状态和观念的重要史料,而“稗官”也成为后世小说的代名词。在传统儒家看来,小说只是“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小道,难以臻于大道,故“君子不为”;“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班固:《汉书》卷30,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5,1746页。,小说不在“可观者之列”。但因其可广见闻、补史阙、昭劝诫,有一定的社会意义,故也不必刻意抹灭。这种以社会功用为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决定了小说在传统学术体系中的边缘地位和卑下品级。又因表现“小道”的方式灵活多样,没有稳定的形态特征,再加上内容驳杂,遂使小说在目录学上常处于忽此忽彼、摇摆不定的尴尬境地。就《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十五家小说看,“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3页。。托古人者主于记言,如《伊尹说》、《黄帝说》等;记古事近乎野史,如《周考》、《青史子》等。这种或似子,或近史的性质,是小说在后世目录学著作中经常依违于子、史之间,缺乏稳定归属的重要原因。
从目录学看,《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是四部分类法中集部的前身,而“诗赋略”对诗赋作品的著录和分类,则被视为文集编纂的雏形,诚如章学诚《汉志诗赋》所论:“三种之赋,人自为篇,后世别集之体也;杂赋一种,不列专名,而类叙为篇,后世总集之体也。”*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附,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1065页。因此,若追溯目录学渊源,小说在《汉书·艺文志》中属诸子略,与诗赋略没有任何关系;后世小说尽管常常出入子、史之间,但绝少阑入文集。这种目录学传统,直接影响到文集的编纂。如现存第一部文章总集《文选》分体编次,收录了先秦直至萧梁时代的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策、文、表等三十九种文体。这些类目,代表着时人心目中最重要、最常用的文体,大致划定了六朝时期的文体疆域,而小说没有进入域内。其原因首先在于,在《汉书·艺文志》开创的目录学传统中,“小说”是一种学术著作门类,而非“诗赋略”那样的文体范畴,故尽管其可入子部甚至史部,但不能入文集。萧统《文选序》即明确表示,其收录范围是单篇辞章,不录经、史、子著作。在六朝人看来,辞章写作“以能文为本”,追求辞藻华美、声韵和谐。经、史、子著作尽管也有不少富有文学性的作品,但读者主要不是从文章欣赏和写作角度看待这类著作的,其性质、宗旨迥异于辞章,如经部“姬公之籍,孔父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乃“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故“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至于“记事之史,系年之书,所以褒贬是非,纪别异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子书如“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萧统:《文选序》,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因此原则上不予选录*《文选》收录了史书中的一些论赞、序述。一方面是因为这些作品“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符合辞章的审美标准;另一方面,这些文体并非史书独有,也不是史书的代表性文体,而是广泛存在各类著述中,早已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究其实质,是辞章文体在史书中的运用而已,因此酌情收录,不算自乱体例。。这种取舍标准,意在划清辞章与学术著作的界限,体现了文学创作开始摆脱对学术的依附,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历史趋势。而小说则因长期以来隶属于学术范畴,遂被摒弃于六朝文体谱系之外。
除了目录学传统,小说作为一种著述形式,不像诗、赋、骚、诏、策、令等那样具有稳定的文体形态特征,也是其未能进入文体谱系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六朝时期,小说创作已蔚为大观。在萧统《文选》之前,甚至产生了第一部以“小说”命名的小说总集,即殷芸《小说》。此书《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皆入小说类。从现存一百六十多条佚文看,其取材范围极为广泛,计引《三齐略记》、《风俗通》、《西京杂记》、《说苑》、《幽明录》、《典论》、《六韬》、《荆州记》、《俳谐文》等五十余种文献,而所涉文体也极丰富,有诏、令、上书、启、书、对问等。这些文体,多为《文选》收录。换言之,殷芸《小说》虽在公私目录学著作中普遍被视为小说,但体制驳杂,形态模糊,没有明确、稳定、可以区别于其他文体的显著特征,因此,无法像赋、诗、诏、令、策等那样在《文选》中立为文之一体。
不仅总集如此,汉魏六朝的别集也只收单篇辞章,不录经、史、子著作,自然也造成小说的缺失。《后汉书》著录传主的撰述情况,往往详载辞章文体类目和篇数。如有著作,则多与辞章分开著录,如《后汉书》卷60上《马融传》载融“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烈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所著赋、颂、碑、诔、书、记、表、奏、七言、琴歌、对策、遗令,凡二十一篇”*范晔:《后汉书》,第7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972页。,卷8《文苑传》载杜笃“所著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凡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范晔:《后汉书》,第9册,第2609页。等,这种体例,足见严格区分辞章和学术著作之意。又,任昉《王文宪集序》云:“昉尝以笔札见知,思以薄技效德,是用缀缉遗文,永贻世范。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记》、《今书七志》,为一家言,不列于集。”*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46,第2084页。序文显然是介绍自编别集的情况。结合《后汉书》的文体著录体例,可以看出,“为一家言”的著述不入文集,在六朝时期是普遍风气,并形成文集编纂传统。在这个传统下,出入子、史的小说不能作为一种独立文体跻身别集和总集之中。不唯六朝如此,整个唐代也不例外,甚至到了明清时期,大多数文集仍严守这种编纂体例。
三、宋以后文集中的小说
文集不录学术著作和小说的传统,从汉魏六朝开始,唐人因袭不改,直到宋代才开始出现变化。周必大编《欧阳文忠公集》,除录诗赋辞章外,学术著作也搜罗殆尽,涵盖经、史、子各部。如《易童子问》三卷为经学著作; 《崇文总目叙释》一卷为史部目录类著作;《于役志》一卷、《归田录》二卷为史料笔记性质,多入子部小说家或史部杂史类;《诗话》一卷,或入子部小说家类,或入集部“文史”类、“诗文评”类,与别集、总集并列,而绝少入别集、总集者。周必大卒后,其子纶手订《文忠集》二百卷,既录诗赋辞章,又录《辛巳亲征录》、《归庐陵日记》、《泛舟游山录》、《玉堂杂记》、《二老堂诗话》、《二老堂杂志》等著作。这些例子表明,别集到了宋代,除表现辞章藻彩外,又增加了表彰学术的功能,打破了文集不录著作和小说的传统惯例。然而,这种现象,并不意味着宋人已把小说视为文之一体收入文集。事实上,他们收录包括小说在内的学术著作,主要是出于保存文献的动机。如周必大称其编纂《欧阳文忠公集》,旨在“补乡邦之阙”*周必大:《欧阳文忠公集后序》,《文忠集》卷52,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第550页。,即保存乡邦文献。又陆游编《渭南文集》,录《入蜀记》、《牡丹谱》等著作,并向子遹解释说:“如《入蜀记》、《牡丹谱》、乐府词,本当别行,而异时或至散失,宜用庐陵所刊《欧阳公集》例,附于集后。”*陆子遹:《渭南文集跋》,陆游:《渭南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这一解释恰恰表明,在宋人观念中,学术著作本当别本刊行;收入别集,只是防止文献散佚的权宜之计,这在一些求多求全、有作必录的“大全”类别集中尤其明显。此端既肇,遂成风气,辞章而兼收著作的别集越来越多。如宋刘克庄《刘后村集》录《诗话》二卷;金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录《著述辨惑》一卷、《诗话》三卷;明舒芬《舒梓溪先生全集》收《东观录》一卷,韩邦奇《苑洛集》收《见闻考随录》五卷等。这些自成卷帙的作品进入别集,与《欧阳文忠公集》、《渭南文集》所录性质一样,皆非以辞章之体跻身文苑,而仅是以学术著身份附缀于文集之中。
至于总集,历来只录单篇辞章,不收成部著作。值得注意的是,宋代以后的一些文章总集,如《文苑英华》、《唐文粹》等,收录了韩愈《毛颖传》、柳宗元《童区寄传》、陈鸿《长恨歌传》、沈亚之《冯燕传》等屡屡入选后世小说选本的作品。这些作品都有浓厚的小说意味或传奇色彩,但它们进入《文苑英华》等总集,是凭藉传统辞章中的“传”体文身份,而非小说身份。换言之,宋代文集中,无论总集还是别集,尽管收录了一些被后世视为小说的作品,但小说仍然没有在文章谱系中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这种坚冰,一直到明代王世贞编《弇州四部稿》才开始被打破。
如前所述,《弇州四部稿》将平生所撰之文分为赋、诗、文、说四部。其中“赋部”两卷,分赋、骚两类。“诗部”五十二卷,下立风雅类、拟古乐府、三言古、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五言排律、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杂体、杂言、回文、词等二级类目。“文部”八十四卷,有序、记、纪、传、墓志铭、墓表、神道碑、墓碑、碑、行状、颂、赞、铭、祭文、奏疏、史论、杂记、读、策、书牍、杂文跋、墨迹跋、画跋等子目。“说部”三十六卷,没有二级类目,收录《札记内篇》、《札记外篇》等通常被目录学家归入“小说”类的作品。综观全书体例,不管一级类目还是二级类目,都是按文体类聚区分的。其中二级类目所列是各种具体文体,而一级类目则是依据文体共性对这些具体文体的合并归类。因此,无论一级类目或二级类目,都具有显著的文体学意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一级类目中,收录小说的“说部”与赋部、诗部、文部并列,使其成为文体的一大门类,从而使小说获得了明确、独立的文体地位。这在文集编纂史上是一大创举。那么,王世贞这一创举,是偶尔为之的率意之举,还是深思熟虑的体例设计呢?《又与徐子与》云:“比间寂寂,公署若深山中道院。了得全稿,诗、赋、文、说凡四部,百五十卷,可百余万言。”*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第22 页。《又与张助甫》云:“弟校集,凡赋、诗、文、说部,将百三十万言,得百七十余卷。异时更得玄晏一序,便足忘死矣。”*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1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1册,第65页。所谓“了得全稿”,指王世贞五十岁时,初步编成《弇州四部稿》一百五十余卷;后经不断增补校订,得定稿一百七十余卷,即 “弟校集”之谓。可见,《弇州四部稿》在编纂过程中,尽管内容、篇目时有增补,但按赋部、诗部、文部、说部四大门类编次的体例,始终保持稳定。稍有变化的是,在初稿与定稿之间,赋和诗的位置有所调整,但不影响整体格局。换言之,说部获得与诗、赋、文并列的文体地位,这是一以贯之的。不仅如此,王世贞还在书信中屡屡提及《弇州四部稿》中的说部。《与陈玉叔》:“今年梓拙稿成,得百八十卷……聊上说部一种之半,或足佐握麈耳。”《又与陈玉叔》:“鄙集于说部大有损益,先上一部,有续刻者亦俟此期致之。”*王世贞:《弇州续稿》卷18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第694页。对自刊文稿的其他内容不置一词,却于说部再三致意,足见其自得、自重之意。这也从另一侧面表明,说部与赋、文、诗并列,并非率意为之,而是精心设计的体例,自有深意寓焉*王世贞何以在自编文集中设赋、诗、文、说四部,笔者已另撰专文讨论,兹不赘述。详参笔者未刊稿《〈弇州四部稿〉“说部”发微》。。
王世贞是后七子领袖,影响文坛至为深远。明末艾南英曾批评七子派之流害曰:“后生小子不必读书,不必作文,但架上有前、后《四部稿》,每遇应酬,顷刻裁割,便可成篇。骤读之,无不浓丽鲜华,绚烂夺目,细案之,一腐套耳。”*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172,第1508页。这种尖锐的指责,恰恰透露了《弇州四部稿》对后学读书、作文的巨大影响。明刘城《李善承元胤罢太仓司训归里》诗云:“忆得之官正乱初,干戈弦诵竟何如?饱看娄子江涛色,多读王家说部书。”*刘城:《峄桐诗集》卷9,清光绪十九年养云山庄刻本。太仓为王世贞故里,即使身处战乱,里中士子依然弦诵弇州说部而不辍。比照艾南英的批评,可知诗中所写王氏著作的影响力并非虚夸。这种影响,除了具体作品外,也包括文集立“说部”这种编纂体例。如明吴沛《西墅草堂遗集》按诗、文、说、论四部编次。其中“说部”仅收《题神六密》一篇,分竖、翻、寻、抉、描、疏、逆、离、原、松、高、入诸题,专谈八股做法,其性质与弇州说部中的《艺苑卮言》、《卮言别录》相似,属诗文评著作。而全书立说部,与诗、文、论三部并列的编次体例,显然也受了王氏影响。又,清王士禄《燃脂集例》“部署”条曰:“仆之此书,颇杂采《文选》、《文粹》及《弇州四部稿》诸书体例,而间参以己意,总为四部,曰赋,曰诗,曰文,曰说,析为六十四类。”*王士禄:《燃脂集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0册,第731,731页。《燃脂集》是王士禄辑录的先秦至清初女作家诗文总集,全书两百三十余卷,卷帙浩繁,体例精严,对于研究女性文学有重要意义。可惜原书已佚,而介绍其编纂体例的《燃脂集例》一卷保存完好,为后人了解此书原貌提供了宝贵文献。例文明确表示此书编纂杂采《文选》、《唐文粹》及《弇州四部稿》诸书分体编次的体例。事实上,《文选》、《唐文粹》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二级类目即各种具体文体的名目上。至于全书整体框架结构,即一级类目上立赋、诗、文、说四部,则完全沿袭王世贞的体例。其中“说部”录“杂著之自为一书者”*王士禄:《燃脂集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20册,第731,731页。,如班昭《补列女传》、《女诫》,方维仪《宫闺诗评》,李清照《打马例》等。与《弇州四部稿》“说部”七种一样,这些作品不再以史部或子部著作的身份附缀于文集之末,而是以文体门类的身份与赋、文、诗并列于文集之中。
如果说《弇州四部稿》等文集中的说部,主要还是传统目录学家心目中的小说,学术性重于文学性的话,那么,晚明宋懋澄《九籥集》所录小说,则更具文学价值。此书虽也分体编次,但不像《弇州四部稿》那样有两个层级,而是直接切入具体文体,计有记、传、序、论、铭、诔、诗、书、表、说、祭文、赤牍、稗等文体。在这些文体中,最有新意也最引人注目的是“稗”体,即稗官小说,收在此书《前集》卷1和《后集》卷2、3、4,共有四十多篇作品。其中《掷索》、《齿跳板》等篇是传统笔记体小说,仅以短短数十字的篇幅,记载趣闻异物,基本没有情节。而更多的作品,如《刘东山》、《葛道人传》、《珠衫》、《耿三郎》、《李福达》、《负情侬传》、《顾思之传》等,以记人叙事为主,篇幅较长,情节曲折,叙事生动,艺术水平较高,与弇州说部相较,显然更符合今人的文学小说文体观。
四、明清说部入集的文体学意义
《汉书·艺文志》确立的目录学传统对小说的学术定位、汉魏六朝别集编纂传统以及《文选》作为现存第一部文章总集在文体收录和编次体例上的经典示范意义,都使得小说长期被排斥在辞章之外,不能成为古代文体谱系中的一员。这种观念,也反映在文学批评著作中。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范畴远比同时代的《文选》宽泛,不但诗赋、乐府、铭箴、碑诔等有韵之文皆有专篇探讨,还特立《史传》、《诸子》篇,论述明确被《文选》排斥在篇翰之外的史部和子部文体。《文心雕龙》按照一定程式系统论述的文体有三十多种,再加上附于《书记》、《杂文》两篇之后略作说明或仅列其目的四十余种,包括谱籍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契符券疏、关剌解牒等应用文,几乎穷尽了当时一切文字体式。然而,即使在这样庞杂、宽泛的文体家族中,依然没有小说的一席之地。虽然《诸子》篇有“青史曲缀以街谈”*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08,272页。,《谐隐》篇有“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308,272页。等语,似乎论及小说。然而,这些只言片语,只是刘勰在评价作品或探讨文学技巧时,涉及一些符合小说特征的因素而已,而非明确把小说作为一种文体来探讨*详参郝敬:《刘勰〈文心雕龙〉不论“小说”辨》,《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尽管《文心雕龙》中的“文”所指如此庞杂,但刘勰并未突破汉魏六朝人的普遍观念,将小说纳入文体之林。对此,钱锺书先生曾深表遗憾:
然《雕龙·论说》篇推“般若之绝境”,《谐隐》篇譬“九流之小说”,而当时小说已成流别,译经早具文体,刘氏皆付诸不论不议之列,却于符、簿之属,尽加以文翰之目,当是薄小说之品卑而病译经之为异域风格欤?是虽决藩篱于彼,而未化町畦于此,又纪氏之所未识。小说渐以附庸蔚为大国,译艺亦复傍户而自有专门,刘氏默尔二者,遂使后生无述,殊可惜也。*钱锺书:《管锥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157—1158页。
钱先生推测,在“小说已成流别”、“渐以附庸蔚为大国”的背景下,“刘氏皆付诸不论不议之列,却于符、簿之属,尽加以文翰之目”的原因,“当是薄小说之品卑”。这一判断自然不错。然而,簿录、符契、券疏等日用文体,历来不为文论家所重视,亦可谓“品卑”。刘勰称这些文体为“艺文之末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57页。,即有看轻之意,但毕竟能居“艺文”之列。可见,“品卑”并非刘勰不论小说的全部或唯一原因。目录学传统以及小说作为一种著述门类,形态特征模糊,也是重要因素。总之,《文心雕龙》作为六朝文学批评的高峰,与《文选》作为六朝选集和总集的典范,不约而同地摒弃小说,恰恰体现了一个时代共同的文学思想和文体观念,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小说长期游离于文苑之外。
唐宋以后,随着小说创作的发展,尤其是传奇、话本等富有文学色彩和艺术感染力的体裁的兴盛,从文学创作或辞章欣赏、写作角度论小说者越来越多。如唐沈既济《任氏传》:“嗟乎,异物之情也,有人道焉。遇暴不失节,狥人以至死,虽今妇人有不如者矣。惜郑生非精人,徒悦其色而不征其情性。向使渊识之士,必能揉变化之理,察神人之际,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不止于赏玩风态而已。惜哉!”*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452,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697页。《任氏传》是讲述狐仙故事的传奇名篇,在唐代文士中广为流传。沈既济在这段交代创作缘起的文字中,流露出他心目中的传奇小说观,即当“著文章之美,传要妙之情”。这种文学性追求,迥异于一般的史著或子书。宋洪迈《容斋随笔》卷15曰:“大率唐人多工诗,虽小说戏剧,鬼物假托,莫不宛转有思致。”*洪迈:《容斋随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92页。肯定唐人小说虚构设幻的创作方法,欣赏其思致婉转的叙事水平和艺术感染力。在此基础上,洪迈进一步称赞唐人小说:“小小情事,凄惋欲绝,洵有神遇而不自知者,与诗律可称一代之奇。”*莲塘居士辑:《唐人说荟》卷首凡例,上海:扫叶山房,1922年石印本。这种摆脱社会功用的束缚,完全从艺术标准出发对小说的推崇,在小说观念史上是重大突破。此外,刘辰翁《世说新语评点》不仅开创了一种小说批评新体式,并在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故事情节刻画等艺术特点和创作规律的探讨上,作出了超越前人的贡献。这些批评,都在理论层面推动了小说的文学化进程。然究其本质,主要还是站在文章学立场来考察文苑之外的小说,并没有把小说视为文苑成员。与此相应,宋代别集中尽管收录了一些小说,但并未赋予小说明确的文体地位。
明代以后,小说的文学化批评进一步发展,并且出现了新的趋向,即不仅站在文章学立场看文章之外的小说,甚至直接把小说视为文章之一种。如桃源居士《唐人小说序》:“唐三百年,文章鼎盛,独律诗与小说,称绝代之奇。何也?盖诗多赋事,唐人于歌律,以兴以情,在有意无意之间。文多征实,唐人于小说摛词布景,有翻空造微之趣。至纤若锦机,怪同鬼斧,即李杜之跌宕,韩柳之尔雅,有时不得与孟东野、陆鲁望、沈亚之、段成式辈争奇竞爽。”*桃源居士辑:《唐人小说》卷首,上海:上海艺文出版社,1992年。以律诗与小说并称“绝代之奇”,是唐代文章鼎盛的标志,而小说的艺术成就,有李杜诗、韩柳文所不能及者。这在小说观念史上可谓又一次飞跃。至李贽将不登大雅之堂的章回小说《水浒传》与《史记》、《杜子美集》、《苏子瞻集》、《李献吉集》并称为“五部大文章”,更是振聋发聩之论。这些观点,并非个别思想家的孤明先发,而是明代文学思潮的反映。明中叶以后,文学批评界出现了一种“泛文章”倾向。许多评点家,把一切著述都视为文章,从文学角度广泛评点包括小说在内的经、史、子、集等各类著作。这种风气,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四部分科的藩篱,为小说以文之部类甚至文之一体的身份进入文集克服了障碍。正是在这种时代氛围中,才能出现《弇州四部稿》这样于别集中设立说部,与传统赋、诗、文并列的文集编纂新体例。
当然,弇州四部中的说部,多为学术笔记,主要是传统目录学家心目中的小说,而非文学家心目中的小说。王世贞编《弇州四部稿》时,早已完成《世说新语补》、《剑侠传》的编纂工作。但这两部以写人叙事见长、更具文学性的著作,却未能入选《弇州四部稿》,可见其小说观念偏于保守。尽管如此,王世贞以一代文宗之尊,将历来被逐于文苑之外、依违于子史之间的小说,破天荒地收入自编文集中,与传统赋、诗、文并驾齐驱,这对于提高小说的文体地位,仍有重要意义。由于“小说”或“说部”内涵的丰富、驳杂,既包括学术性的笔记丛谈,又包括文学性的志怪、传奇,《弇州四部稿》立“说部”的创举,打破了千余年来层层冻结的坚冰,为文学性小说进入文集、跻身文体谱系开辟了尽管狭窄但极其珍贵的通道。宋懋澄《九籥集》正是经此通道,在文集中立“稗”体,收录大量情节曲折、叙事生动、描写细腻的传奇小说的。需要指出的是,《弇州四部稿》中的“说部”尽管获得了与赋、诗、文并列的文体地位,却是以文体部类的身份出现,其文体形态并不清晰。而《九籥集》中之小说,不是以文体部类,而是以一种具体文体的身份,与诗、书、铭、诔、论、传、记等传统文体并列于文集中的。因此,此书所录稗体文,都是独立成篇的辞章,而非弇州说部那样成部的著述。小说至此才真正成为文章家族中的一员,其文体地位远比面目笼统、模糊的“说部”更为具体、明确和清晰。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利器先生对《九籥集》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明代末年小说“登上大雅之堂的破天荒之举”,“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一件大事,应该加以大书特书的”*王利器:《〈九籥集〉——最早收入小说作品的文集》,《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如从文学小说观念看,这一评价无可非议,但不能因此忽略了《弇州四部稿》“说部”在发凡起例上的开辟之功。
由于文集编纂传统及其所蕴含的文学思想、文体观念的强大惯性力,小说明确以文之一体的身份进入文集,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不常见,更未成为普遍风气。明末张燮编《七十二家集》,其凡例第二则曰:“集中所载,皆诗赋文章。若经翼史裁,子书稗说,听其别为单行,不敢混收。盖四部元自分途,不宜以经、史、子而入集也。”*张燮:《七十二家集》卷首,《续修四库全书》第1583册,第1页。可见,文集不收经、史、子著作,小说不入文集,不在文章之列,是何等根深蒂固的编纂传统和文体观念。这种传统和观念,即使到了古代文学的最后阶段即明清时期,依然占据主流和正统地位。这一点,在目录学中更为显著。明清时期的图书著录,不管是正史艺文志,官修目录如《内阁藏书目录》、《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还是私家目录如明高儒《百川书志》、晁瑮《宝文堂书目》、徐《徐氏红雨楼书目》,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祁理孙《奕庆藏书楼书目》、张之洞《书目答问》等,均未见有小说录入集部的特例,小说依然徘徊于子、史之间,诚如姚名达先生所论:“凡非写实之小说故事, 旧目录学家皆归之子部小说家;鬼神传记则有归之史部传记类者……要之皆不承认为文学, 故未尝侧入集部焉。”*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47页。目录学著作在对图书的整理、分类和著录中,体现的主要是对传统和当代知识界限、范畴、谱系及谱系成员之间的关系、地位等的一般性认识。而明确将小说视为文之一体,则只是明清文学领域个别先行者燃起的星星之火,没有成为知识界一般的知识、思想而被广泛接受。正因如此,尽管文学批评界和文集编纂者已出现可贵、大胆的创新,但在目录学中,小说入子、入史而不入集的基本格局,没有任何突破。事实证明,依靠传统文化内部的自我调适和更新,无法完成这一突破。小说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圣殿,并成为一种普遍观念,一直要到社会形态已发生天翻地覆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这种巨变的动力,主要是外来的,而非文学内部产生的。当然,在强调这种外来动力的同时,也不能无视传统文学内部早已潜滋暗长的流脉。
【责任编辑:张繤华;责任校对:张繤华,李青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4-0010-08
作者简介:何诗海,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州 510275)。
*收稿日期:2014—12—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书凡例与文学批评——以明清集部著作为考察中心”(12BZW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