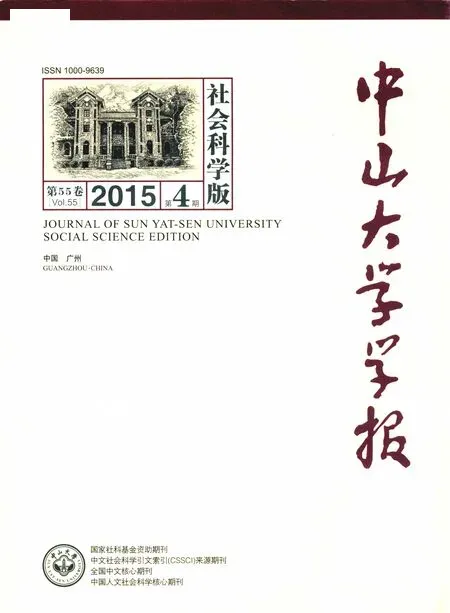“以浅持博”:陈澧“小学”理念之演进及旨趣*
於 梅 舫

“以浅持博”:陈澧“小学”理念之演进及旨趣*
於 梅 舫
摘要:陈澧之学渊源于以江浙学术为本的学海堂,循“训诂明而义理明”的路径,特重“小学”一道。其《说文声表》、《切韵考》及《外篇》,对“小学”一道大有推进,他也因此获得极大的学术声誉。有意思的是,陈澧在深入“乾嘉考据”之小学后,便开始对这一“皓首穷经”式的治学理念能否承受“治经门径”的初意产生怀疑,且以为此是晚清学术衰弊的一大要因。因此,便开始对六书小学作深入浅出的诠释,以期恢复小学“古”意——亦即幼学之意,进而将此“真小学”突破六书之学,发挥至群书入门的门径,真正变成“以浅持博”的门径书。这一过程,既反映其小学理念的变化,也承载其改变乾嘉大儒在治学实践中形成的治经门径的抱负,蕴含陈澧与学海堂所本的江浙学术立异、争胜的运思,体现确立新的学海堂治经门径的意趣,也凸显其构筑沟通汉宋之学的基调。
关键词:陈澧; 小学; 音训; 以浅持博; 汉宋兼采
陈寅恪在上世纪30年代曾综论有清一代学术,称史学“远不逮宋人”,经学虽号称极盛,也“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故“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而不能讨论问题。其夸诞者,又流于奇诡悠谬,而不可究诘”*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69—270页。。概而论之,清代学术真正能超迈前代,独具特色而自成一格者,倒是“附庸蔚为大国”的“小学”。之所以有清小学能自居格调、极乎大成,其要因在于能将声音、文字、训诂融贯一体,而犹以声韵贯穿训诂为根基。其中,陈澧声韵训诂之学,集顾炎武、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以来之大成,据切语确定声类、韵类,汇通古韵、今韵,复厘清等韵之纠纷,居于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可称一时名家。有意思的是,陈澧虽深于“乾嘉考据”之小学,且将此推进一大步,他本人却明显具有对“乾嘉考据”之“皓首穷经”式小学的自觉反思,甚至认为这是晚清学风衰弊的要因,有意“专明小学一段工夫”,且加以实践。近人对于陈澧多有研究,从文献整理到史事考订,皆进展明显,然从考辨学术的角度,重心多落于陈氏汉宋兼采之学,鲜有专门论及其声韵小学者,对于后一层次的“小学”,更是语焉不详*目前的陈澧文献整理与史事考订,以黄国声主编的《陈澧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及黄国声、李福标著《陈澧先生年谱》(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进展最为明显。於:有关于僮与初学童子,首为原文如此,可教学僮,但不太抬僮子。。事实上,此事不仅关乎陈澧“小学”理念本身的嬗变,亦与其早期学术转向关系密切,同时牵涉其结撰汉宋兼采之学的学术路径。考察陈氏“小学”观念嬗变的渊源、本事,不仅可以理解陈澧“小学”的丰富层次,同时可兼及其学术理路的逐渐演进,进而把握陈澧精心结撰汉宋兼采之学的起点与底蕴。
一、学海堂与小学入门
梳理陈澧“小学”观嬗变的脉络,首先需确定陈氏“小学”观念的发端。陈澧治学多变,早年治学由务科考,喜诗文,转为攻经史之学。内中核心,是预流学海堂经解之学,循音韵训诂这一治经门径。陈氏“小学”观植根于此。
陈澧幼年即为其父称道“此子能读书”*陈澧:《默记》,《东塾遗稿》第47合订本,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无页码,下同。,然因循于当地学风及家庭背景,其早年读书及论学兴趣多偏于科考时文及诗赋一类。陈氏先世本居于江浙一带,自陈澧祖父因家贫依人,始迁入广东。岭南学风,自明叶兴起陈献章、湛若水诸大师,可与王守仁抗衡并名,之后遂湮灭不彰。明清之交,虽多有明季遗民遁迹于此,而多“以诗文显,而学者无闻也”。康熙末,虽经学政惠半农提倡,涌现“惠门四子”,而“仍皆文士,于学无足述者”*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1期,第35页。。陈澧生当之时,岭南仍诗文之风远胜于治学之气。陈澧之祖、父,虽“好读书”,“喜读《资治通鉴》”,却绝非所谓“读书人”、“学术名家”。陈氏祖、父赖以谋生的,主要还是幕业,或是担任低级官僚*黄国声、李福标:《陈澧先生年谱》,第1—3,16页。。陈澧生长于斯,故幼年所受教育,基本与家庭出身及生长环境相匹配。其父延请的塾师,如徐达夫、尉继莲、郑光宗、王和钧、胡征麟,皆非经师,更多为时文师。讲授的内容,虽有关经史、古诗文,亦多出于科考时文、试帖诗之准备*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辑之763,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第4—9页。。
受此影响,陈澧早年酷好作诗。陈澧曾与人说:“澧十五六岁时,笃好为诗,立志欲为诗人。稍长,知有经史之学,虽好之,不如好诗也。”*陈澧:《与陈懿叔书》,《东塾集》卷4,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68页。黄国声主编《陈澧集》,收录《陈东塾先生遗诗》,据编者按语,《素馨斜》一诗“今存抄件于中山大学图书馆”,“诗前有东塾亲笔题云:‘此余少时诗社之作,此首诗社取第一’”。经编者辨证,此诗当作于乙酉年,陈氏时年十六岁,与其自述相符*陈澧自记此诗作于己酉,时年四十,与少作之语不符。已经黄国声考辨,当是将“乙酉”误题为“己酉”。详见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550页。。而此类吟诗作赋的诗社,大体应是切磋科考中的试帖诗。如倪鸿专门记述试帖的诗话之作——《试律新话》便记载了陈澧与同人结诗社之举。其言:“陈兰甫先生幼时偶与同人结诗社,题为《流莺比邻》,邻字颇难贴切自然。先生诗中有一联云:‘低闻当户织,高被隔墙偷。’关合邻字,极有作意,而炼句押韵,亦复警峭,同人为之搁笔,不减崔颢题诗也。”*黄国声、李福标:《陈澧先生年谱》,第1—3,16页。可见陈澧颇善于此道。

真正促使陈澧由喜好诗文一变为用心经史之学,当是受学海堂及江浙学术的影响。
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三岁的陈澧获得与学海堂名家接触的机会。此年,浙江嘉善学人陈鸿墀掌教越华书院,时与学海堂学长曾钊、吴兰修等宴游、雅集,论辩书史,高谈乾隆、嘉庆时江浙名贤硕儒的言行掌故*参见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14页。。陈澧受业陈鸿墀,亦得与焉。陈澧初次与学海堂学长有了直接的联系,也渐从言传身教中体会到学海堂学术的三味。
曾钊、吴兰修皆为当时广东学界名宿,代表一时粤学高度。曾钊治经名家,盛名遍于广东,甚至远被京师。江苏名儒刘逢禄得见曾钊论著,极口称:“笃学若勉士,吾道东矣。”*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48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80页。颇为钱大昕、王鸣盛推重的任兆麟,阅曾钊所校《字林》,极见功力,遂告知阮元。阮元阅后,极具同感。曾钊后遂受业于阮元,“由是学识愈进”*陈在谦评辑:《国朝岭南文钞》卷17,清道光十二年,七十二峰堂刻本。。缪荃孙记曾钊生平,说:“笃学好古……研求经义,文字则考之《说文》《玉篇》,训诂则稽之《方言》《尔雅》。虽奥晦难通,而因文得义,因义得音,类能以经解经,确有依据。”阮元故而惊艳其学,延请课子,开学海堂,请其为学长*缪荃孙:《曾钊传》,闵尔昌录:《碑传集补》卷41,周骏富辑:《清代传记丛刊·综录类》5,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第507—512页。。陈璞因而称曾钊:“湛深经术,博稽古籍,吾粤治汉学者为最先。”*陈璞:《面城楼集钞序》,《尺岗草堂遗文》卷1,清光绪十五年,《尺岗草堂遗集》刻本。岭南后起学人侯康,在评价友人孟鸿光的学问时,称若使其“不废学,谁能及之?曾勉士不如也”*陈澧:《书孟蒲生》,《东塾集》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204页。。可反观当时学人认同曾钊学问,视其为粤学高度。吴兰修同样深得阮元赏识,善作词,然而自题其门为“经学博士”,“自云唤作词人,死不瞑目”。吴兰修经史之学颇能入流,其在学海堂八学长中名列首位,并非虚荣*伍崇曜跋吴兰修著《南汉纪》语,录自容肇祖:《学海堂考》,《岭南学报》第3卷第4期,第26页。。曾、吴皆受阮元影响,以江浙学术为正宗。

当然,最直接的要因,当是道光十四年(1834),二十四岁的陈澧被选为学海堂专课生,得以直接浸润于学海堂及其所本之江浙学术中。
学海堂由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所创,仿浙江杭州诂经精舍,只课经解诗赋,不课时文,欲引入江浙学术,旨在张大阮氏经解之学*详见於梅舫:《科考与经解——诂经精舍、学海堂的设置与运思》,《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阮元虽左迁云贵总督,却在离粤前定下数目众多、条理清楚的院规,涉及书院发展诸多方面。其旨趣分明,施行严格,使得学海堂的整体规制得以延续。通过将教化约束为制度的方法,保证创办原意可以保留持续,不致因人事变动而发生根本变化*林伯桐初编,陈澧续编,周康燮补编:《学海堂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伍),第615页。。
阮元主要通过编辑接近其治学理念的应课文,且配以自己或学长的程作,集成《学海堂集》,作为具体示范。阮元称:“多士或习《经》、《传》,寻疏义于宋、齐,或解文字,考故训于《仓》、《雅》,或析道理,守晦庵之正传,或讨史志,求深宁之家法,或且规矩汉晋,熟精萧《选》,师法唐宋,各得诗笔。”*阮元:《学海堂集序》,《揅经室续四集》卷4,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77页。其重心显然还在经史之学,尤其在经解之学,不仅在院规中规定“此课之设,首劝经史而诗赋备具”,而且在《学海堂集》的编排顺序、内容安排上,也明确以经解之学为主,卷首便是阮元解经的程作《易之彖解》,而《学海堂文集》中经解之学整体以此为规矩。卷1除《易之彖解》外,另题为《尚书之训解》、《诗之雅解》、《春秋之传解》、《仪礼之记之传解》,大致都以字解经,颇合阮元倡导的治经规矩。卷2分别为《问仪礼释宫何人为精确》、《问虞夏书商颂易卦辞何以不言性亦皆无性字》、《问性始于何书、周人汉人言性其义与孔孟合否》、《释广》,本身便是阮元极其关注,意在与宋儒较高下的“性命”论。卷3、4,为曾钊《诗毛郑异同辨》。虽然诸人高下有别,入门深浅不同,总体可见阮元引导诸生趋向经解之学的努力。《学海堂集》所示范的治经门径,大致就是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所概括的那样:“公识字之法,以经为验,解经之法,以字为程。是公训故之学。”*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王佩诤校:《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年,第226页。以训诂解经,秉承戴震一系“训诂明则义理明”的治经路径,对理学重要概念作考镜源流的梳理。
上以导之,下以受之。学海堂诸生受阮元及江浙学术影响,出现明显的以江浙学术、诂经精舍为圭臬的自觉,不仅主观上能与诂经精舍并列而觉荣耀,亦有在此基础上超越之意。《学海堂集》中文字极能体现此意。如,有人说:“诸生诚能奋其稽古之志,笃其修身之力,取汉唐经疏诸史,精研博考之而无浮慕乎外,如《汉书》所谓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者,岂非今日之学海,足以比美于西湖哉。”*樊封:《新建粤秀山学海堂题名记》,《学海堂集》卷16,清道光五年,启秀山房刻本。也有人说:“即谓此堂与西湖诂经精舍相并,亦无不可。”*崔弼:《新建粤秀山学海堂记》,《学海堂集》卷16。更有人说:“以视西湖之诂经精舍,不更壮远乎?”*谢念功:《新建粤秀山学海堂序》,《学海堂集》卷16。虽亦存堂舍壮美之比较,实亦寓学术争高下之意。
陈澧入学海堂后,大体沐浴于类似氛围中。本已见诗文转为经史之意,自此更是根据学海堂示范的经解之学摹拟学习,自觉地深入学海堂经解之学中去。第二年,陈澧赴京会试,留京时与友人书信内道及:
足下弃苏季揣摩之术,笃江都下帷之志,究洞许书,熟精萧选,甚善,甚善。近所述造,知益斐然。昔相如、子云,赋颂之首,而《凡将》训纂,甄极小学。刘彦和云:文字乃言语之体貌,文章之宅宇,鸿笔之徒,莫不洞晓。岂不然乎?*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2页。
此书中所言,与阮元在《西湖诂经精舍记》中所述基本观点相近,可见渊源。阮元称:“诗人之志,登高能赋。汉之相如、子云,文雄百代者,亦由《凡将》、《方言》贯通经诂,然则舍经而文,其文无质,舍诂求经,其经不实。”*阮元:《西湖诂经精舍记》,《揅经室二集》卷7,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548页。更为明显的是,陈澧在书信内更对友朋夹辅、共同研治经解之学的乐境非常怀念,称:“每念曩昔斗酒相乐,命俦啸侣,辨析经传,竞说字解,高谈未终,谑浪间作。”*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2—443页。“竞说字解”,可证陈澧深受阮元所引导之“经非诂不明”治学主张的影响。此是陈澧入学海堂后,极为明确的表达。
这一层意思,从陈澧所撰入选《学海堂二集》的文字可得实证。又一年,时在道光十六年(1836),吴兰修编刊《学海堂集》第二集,陈澧所撰有三篇共四首治经解小学的季课文入选,分别为《騋牝三千解》一首,《春秋刘光伯规杜辨》二首,《书江艮庭征君六书说后》一首*分别见《学海堂二集》卷3、7、9。并可参看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21页。。其一解经,其一辨家法,其一论小学,显示陈澧此时治学,大致依循阮元引导经解之学门径进行,且娴熟沉稳,获评定者好评。陈澧不仅擅长此道,亦乐在其中。此为陈氏浸润以江浙学术为圭臬的小学之起始。
二、声韵贯穿训诂
入门之后,陈澧很快便完成了两部重要的小学论著,其一为《说文声表》,另一为《切韵考》*此二书撰述之时间,可参见黄国声、李福标:《陈澧先生年谱》,第46—58页。《说文声表》之名,撰写过程中屡有更易,据陈澧《自记》及《与杨黼香书》等,其先欲撰《篆说》,后改作《说文声类谱》,又改名《说文声统》,准备付梓之际名《说文声表》。参见黄国声《说文声表》整理说明,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肆),第3页。,尤以后者知名于世。此两部著作,皆始作于道光十八年(1838)陈澧二十九岁时,二年后《说文声表》成稿,再二年后《切韵考》成稿,而修订补充则陆续进行,“十年来所学在此”*陈澧:《与硕卿侄书》:“三场策题问小学、音韵及《禹贡》水道,我十年来所学在此。”《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9页。。两书皆循学海堂所导之江浙门径,又于此道承前启后,大有创获,在清代“小学”演进过程中居于重要位置。
咸丰三年(1853),四十四岁的陈澧欲将久已成稿的《说文声表》刻板行世,并撰序交代旨趣。序称:
上古之世,未有文字,人之言语,以声达意。声者,肖乎意而出者也。文字既作,意与声皆附丽焉。象形、指事、会意之字,由意而作者也。形声之字,由声而作者也,声肖乎意,故形声之字,其意即在所谐之声。数字同谐一声,则数字同出一意,孳乳而生,至再至三,而不离其宗焉。澧少时读《说文》,窃见此意,以为《说文》九千余字,形声为多,许君既据形分部,创前古所未有。若更以声分部,因声明意,可以羽翼许书……其后读戴东原书,知其尝劝段氏为此书,谓以声统字,千古奇作。窃自幸所见,不谬于前人……尝欲为笺附于许君解说之下,以畅谐声同意之旨,其后更涉他学,不暇为此,姑俟异日。古人有自悔其少作者,澧编此书,年未三十,然本昔人之意,非自出臆见,虽未必为奇作,世之治小学者,或有取焉,不必悔也。*陈澧:《说文声表序》,《东塾集》卷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24—125页。
这一段语言,大体交代了陈澧撰写《说文声表》的根据、方法及凭借。其中最为重要的特质,便是发挥以声韵贯穿训诂的取向,也即“谐声同意”之理念。这一理念,建立在一个基本推想之上:“天下事物之象,人目见之,则心有意。意欲达之,则口有声。意者,象乎事物而构之者也。声者,象乎意而宣之者也。声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于是乎书之为文字。文字者,所以为意与声之迹也。未有文字,以声为事物之名;既有文字,以文字为事物之名。”*陈澧:《小学》,《东塾读书记》卷11,朱维铮、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228页。后之刘师培,称陈澧此意“其蕴至精”,并对此有一自然的推论,谓:“盖人声,精者为言,既为斯意,即象斯意制斯音。”而“古人名物,以一意一象为纲。若意象相符,则寄以同一之音。虽审音造字,形不必同,然字形虽殊,声类同者义必近”。刘氏未见《说文声表》,故叹:“后儒有作,若于古韵各部建一字,以为众声之纲,以音近之字为纬,立为一表,即音审义,凡字音彼此互同者,其义亦可递推矣。”*刘师培:《原字音篇》、《古韵同部之字义多相近说》,《左庵集》卷4,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9),第3829—3832页。这显然即是陈澧所阐释“以声统字”之意及其实践*此说与右文说义近而有不同。黄侃有辨之:“声音、训诂相通,古人未尝不知。王子韶右文说,本于王荆公《字说》。如言波是水皮,恐仓颉造字时已如此解。东坡以‘滑岂水骨乎’拒之,此则有相当之理由。凡緐变之物,不可以一理解,此因执形以求,故有是误。荆公但知文字、训诂之合而为一而遗其声,若以声音通假之说补之,则疑难不烦而解矣。以声音贯串训诂,而不拘于形体,可以补二王之说。然此至清儒始得明之。黄承吉为曲直通知说,少病粗略。若王念孙则不谓之哲人不可也。”然凡同音便可同意,仍需区别而论。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87页。亦可参见:《文始序例》,第179—180页。。已与以“形”分部,以形为主的小学理念大为不同。这便是后世黄侃所概括:“小学分形、音、义三部……三者之中,又以声为最先,义次之,形为最后。凡声之起,非以表情感,即以写物音,由是而义傅焉。声、义具而造形以表之,然后文字萌生……因此以谈,小学徒识字形,不足以究言语文字之根本,明已。”*黄侃:《声韵略说》,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陈澧对于这一“发现”不无自负,称“少时读《说文》,窃见此意”,“可以羽翼许书”。当然,陈澧稍知读书之后,便知此意绝非孤往独发,而是清人治小学的先行凭借与基本理念(亦有可能是深入其中,潜移默化而不知或不说)。“不谬于前人”,说明陈澧治小学之取径,实是相因前人而续成。
陈澧在序中,早已指出戴震尝劝段玉裁“为此书”,“以声统字”。这也是陈澧一度将此书命名为《说文声统》的要因*可参看陈澧:《小学》,《东塾读书记》卷11,朱维铮、杨志刚编校:《东塾读书记(外一种)》,第227页。。戴震此说背后之学理,反映近代小学发达的渊源。
深于小学,集清人小学成就的民国大家黄侃尝述小学治法之迁变,认为:“唐、宋以降,治小学者率散漫而无统系。有清一代,治学之法大进,其于小学,俱能分析条理而极乎大成。”*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40,40—42,42—43页。其要因之一,在于治法门径的不同,犹以声韵贯穿训诂为关键。具体则谓:
唐、宋以来,治小学者率以己意推求。古人言语文字既随方俗时代而变易,则以今之心度古之迹,其不合也必矣。唐陆德明作《经典释文》,以为古人韵缓,不烦改字,已不明古音之异于今音矣。宋吴棫首主叶音,《韵补》一书,就《唐韵》二百六部注以某字古通某转某,则强以今之范围以绳古人,皆不知音声之学者。虽然,音学之发生探讨,则始于陆吴诸家。由古韵之发生,以至今日之合形声义以求真确之文字语言系统条例,则自明陈第始。陈氏作《毛诗古音考》,首驳叶音之说,而吴氏遂不攻而自破矣。此则言小学之开山一人也。继陈氏而起者则为顾炎武。顾氏承陈氏之后,已知古有本音,乃就古人文章韵脚以求古人韵部,虽其所言不免纰陋,而其法则有统系矣。次则为毛奇龄。毛氏主五部、三声、两界、两合之说。又音之分言声韵,亦自毛氏始,其考古之功亦甚伟。次为江永。江氏《四声切韵表》、《古韵标准》以研究古韵所得,而以之研究古声,而字母等韵遂为入门必经之路,其所成虽未臻闳美,而其法实有条贯。次为戴震。戴氏之于小学,可谓能集其成。其《转语序》一书,实可攀古括今,后戴氏之学人无能出其范围者……惟陈、顾、毛、江诸家虽于古声音之学究之綦详,而于义之一途则多不之及。至东原戴氏,小学一事遂确立楷模。段氏王氏为戴氏弟子,段氏则以声音之道施之文字,而知假借、引申与本字之分别。王氏则以声音贯穿训诂,而后知声音训诂之为一物。*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40,40—42,42—43页。
清代小学的发展,诚如黄侃所揭示,根基在于声韵之学的重大进展,进而以声韵贯穿训诂,达到声、形、义之贯通,“由音而义,由义而形,始则分而析之,终则综而合之,于是小学发明已无余蕴,而其途径已广乎其为康庄矣”*黄侃讲,黄焯记:《文字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40,40—42,42—43页。。
试看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谓:“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戴震:《转语二十章序》,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91页。何尝不是交代“以声统字”的原则,揭示贯穿的办法。段玉裁承此意,《说文解字注》称:“许君以为,音生于义,义著于形。圣人之造字,有义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学者之识字,必审形以知音,审音以知义。”*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卷1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64页。此即揭示义、声、形发生的先后顺序,由此发生的顺序,一定程度决定小学家的理路中“说文解字”的顺序,其中声韵实为枢纽,蕴涵声韵贯穿训诂之理。此意即段氏为《广雅疏证》作序所称“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的旨趣*段玉裁:《王怀祖广雅注序》,钟敬华校点:《经韵楼集》卷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7页。。且看章太炎《国故论衡》称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超胜之要因,便在于“凡治小学,非专辨章形体,要于推寻故言,得其经脉,不明音韵,不知一字数义所由生。此段氏独以为桀”*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页。。可见,“以声统字”仍为一大原则。王念孙以为“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故《广雅疏证》的主旨,以音通义,“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王念孙:《广雅疏证序》,钟宇讯点校:《广雅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页。。声韵的地位,更见关键。王引之述父意,《经义述闻》称“古字通用,存乎声音”。进而批评“今之学者,不求诸声,而但求诸形,固宜其说之多谬也”*王引之:《经义述闻》卷3,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8页。。显示声韵于小学一道之枢纽地位。
乾嘉江浙学人的这一小学治法理念,反映近代小学的进步与发达,同时也是当时学人治小学的基本规矩与学理原则。引江浙学术入粤的学海堂,当然承袭此风。学海堂的创办者阮元,便是这一理念的秉持者与推广者。
阮元尝自定文集,名为《揅经室集》,其中最为用心之作即如其集名,为说经之文。自谓:“幼学以经为近也。余之说经,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阮元:《揅经室集自序》,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1页。而说经之文,以推明古训为本,推明古训,则采音训兼合之意。这一理念,尤以最具显要地位的卷1体现得淋漓尽致。
卷1首篇《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综论古人创造文字之本义,显以声韵为枢纽,主以意象、语言合一。其言谓:
庖牺氏未有文字,始画八卦,然非画其卦而已,必有意立乎卦之始,必有言传乎画之继……至黄帝时始有文字,后人始指八卦之字而读之以寄其音,合之以成其书,而庖牺八卦命名之意传乎其中矣。故六书出于八卦,而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皆出于《易》。舍《易》卦无以生六书,非六书无以传庖牺之意与言。故《传》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此也。书乃六书之书,《传》曰“易之为书也”,亦谓籀篆之著简策,非如今纸印之书也。《易传》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此即许叔重所谓“庖牺氏作《易》八卦,以垂宪象,神农结绳,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初造书契,以乂以察也。”书契取于夬,是必先有夬卦而后有夬意,先有夬意而后有夬言,先有夬言而后有夬书,先有夬书而后有夬辞也。*阮元:《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1—2页。
此即刘师培所概括:“古人析字,既立意象以为标,复观察事物之意象,凡某事、某物之意象相类者,即寄以同一之音,以表其意象。”也就是说,“惟有字义,乃有字音;惟有字音,乃有字形”。从此意出发,许慎《说文解字》,“以左旁字形立部首,乃后儒析字之例,非古人造字之本义也”*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第1239—1243页。。隐见阮元突破前人之抱负。陈澧《说文声表》“以声统字”,别于字形部首而言声部,以解字义,以统字形,与此意极为相通。
阮元训诂文义之作,多具此眼光。《揅经室集》说经之文《释易彖音》与《释易彖意》,即是对此理念的实践。此二文由厘正古音而阐古字本义,音、训连贯配合,一体而成,最具典型。《释易彖音》首先纠正“彖”字今读之误,以复古音:“《周易》‘彖’之为音,今俗皆读‘团’之去声,与古音有异。古音当读若‘弛’,音近于‘才’,亦与‘蠡’字音近。故《系辞传》曰:‘彖者,材也。’此乃古音训相兼。是‘彖’音必与‘才’音同部……若读今音‘通贯切’……与‘材’字迥不同部,孔子何以‘材’字训之哉?”*阮元:《释易彖音》,《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4—5页。可见具备极强的音训(或声韵贯穿训诂)之眼光,由声类以推本字,进而求其本义。《释易彖意》道:“‘彖’之为音,既据《系辞》、《大雅》定之矣,然则其意究如何?孔子‘材也’之训究如何?曰:此但当以‘彖’字为最先之字,但言其音,而意即在其中,即如‘蠡’字,加‘’与不加‘’无异也。《方言》曰:‘蠡’,分也。‘蠡’尚训为‘分’,则彖字本训为‘分’可知也。‘豕捝’即分也,此即孔子之所以训‘彖’为‘材’也。‘材’即‘财成天地之道’之‘财’,亦即‘三才’之‘才’,以天、地、人三分分之也。今人但知写‘化而裁之’之‘裁’,方谓用刀裁物,而不知古人音意相同,字多假借,‘材’即‘裁’也,‘财’亦‘裁’也。否则‘货财’之‘财’,安可曰‘财成天地’邪?孔子所训之‘材’,言用此彖辞说卦象而分之也。且‘说’从‘兑’,‘兑’与‘彖’同意,‘兑’者最先之字,‘说’者后造之字,即谓‘彖’为‘说’之假借,亦可明乎。此则‘爻者效也’之意于此更明矣。是故学者以‘彖者材也’求孔子之意不能明,以‘蠡者裁也’求之则明矣。若执迂守浅,古音古意终不明矣。”*阮元:《释易彖音》,《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4—5页。
阮元撰《释矢》,更是直揭此意。此文开章明义便谓:“义从音生也,字从音义造也。”并证曰:“试开口直发其声曰‘施’,重读之曰‘矢’。‘施’、‘矢’之音皆有自此直施而去之彼之义,古人造从‘’从‘也’之‘施’字,即从音义而生者也。”故凡与“施”、“矢”音相近者,诸如“尸”、“旗”、“夷”、“易”、“雉”、“止”、“水”、“屎”,皆含有“平陈”、“自此而施去之彼”之义*阮元:《释矢》,《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22—25,25页。。《释门》一文,则称:“凡事物有间可进,进而靡已者,其音皆读若‘门’,或转若‘免’、若‘每’、若‘敏’、若‘孟’,而其义皆同,其字则展转相假,或假之于同部之叠韵,或假之于同纽之双声。”而“斖”、“没”、“懋”、“迈”、“勖”、“莫”、“卯”、“”,皆音近而义通*阮元:《释门》,《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31—33页。。阮元且强调:“明乎此,可知古人造字,字出乎音义,而义皆本乎音也。”*阮元:《释矢》,《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22—25,25页。“观乎此,更见古人声音文字之精义矣。”*阮元:《释门》,《揅经室一集》卷1,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第33页。另可参见刘师培:《小学发微补》,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3,第1238—1243页。
显然,阮元并非就一字解一义而已,乃是欲就此发凡起例,阐明古音古意相贯通之意。而这一治经首基、小学要例,也是阮元有意在学海堂确立、推广的规矩与原则。集合学长程作、诸生优秀习作的《学海堂集》,卷首赫然便是阮元说经论小学的示范性程作:集合《释易彖音》与《释易彖意》的《易之彖解》。
故欲明训诂,首通古音,欲知字义演变,亦需兼通古音、今音的迁转。所以,音韵之学的进展,便是训诂之学进展的前提。陈澧治小学之理念,与此不无关系。陈氏述《切韵考》撰写旨趣,谓:“治小学,必识字音;识字音,必习切语。”*陈澧:《序录》,《切韵考》卷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叁),第1页。其中理念,显然渊源于江浙前人及阮元学海堂的示范。而其具体研究结果,则可为先因后创的案例,是在继承前人成果基础上的重要前进。
承此理念,识音,为通小学的根本,而明声韵、通切语,则为贯通音训的枢纽。陈澧小学的进展,便落实于此。
清人小学虽盛,然皆知识音之难。其中要因,在于声音不如文字凝固,流质易变,无所凭借,又加之时、空殊隔,故最难把握。对此,黄侃解释道:“字体之变改有形,故虽篆隶草书纷纭更易,而脉络条贯尚为易寻。惟字音变改,圆神无方;以时而言,则古今遞殊;以地而言,则楚、夏歧出。若使是非无定,人用己私,则音学竟难成立;所谓立朝夕于圆钧之上,终古不定也。”*黄侃:《声韵略说》,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78页。
考音分声、韵,考韵犹难于考声。《切韵考》及《外篇》对此多有发明。
若论集清人小学之大成者,当推黄侃。黄侃自述其声韵成就,颇不晦与陈澧之学的关系。故欲明陈澧音学成绩,颇可参考黄侃之说。黄侃主张小学合声、义、形而合一,而以声韵为根本,所谓:“《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八九,而义训不过二三。故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然则声训者,训诂之真源也。”*殷孟伦:《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40页。而其《音略》直言:“今声据字母三十六,不合《广韵》;今依陈澧说,附以己意,定为四十一。古声……定为十九,侃之说也。前无所因,然基于陈澧之所考,始得有此。”*黄侃:《音略》,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49页。称陈澧所定,“兼备古今,不可增减”*黄侃:《与人论治小学书》,滕志贤编:《新辑黄侃学术文集》,第49页。。
当然,音分声、韵。其中“声理简单,韵理繁赜。声无变动,韵则有洪细、清浊、开合、轻重之分。故解韵难而考声易。就清一代而言,论声者十之六七,论韵者仅十之一二。盖因声易求而韵难明也”*黄侃讲,黄焯记:《声韵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146,144页。。考韵显然难于考声。陈澧《切韵考》及《外篇》于此道颇有贡献。黄氏对于考韵之难处,颇多体会,谓:“考韵者莫急于考韵部之由来。古韵家但据成迹以为分合,虽于理未明,而于事不缪。谈今韵者,徒执《广韵》附会之以等韵之学,纷纭膠葛,方凿圆枘,其于反切成立之历史,韵部分合之所以然,盖有未能明说者也。愚谓此二事不憭,其人韵学必不可信。”针对其本人,“往者妄谈音学,亦徒据前人古韵、等韵之学得其大略,中间汉魏六朝一截殊未尝用意。近则专以时代先后为次,始觉音学盘根错节,乃独在此一期”*黄侃讲,黄焯记:《声韵学笔记》,黄延祖重辑:《黄侃国学讲义录》,第146,144页。。刺激黄氏一变之人,即是陈澧。
陈澧《切韵考》指出:“音随时变,隋以前之音至唐季而渐混,字母等子以当时之音为断,不尽合于古法。其后切语之学渐荒,儒者昧其源流。” 甚至如辨声韵极精的钱大昕、戴震,对于“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未及详也”。陈澧之治法,在于“切语旧法,当求之陆氏《切韵》。《切韵》虽亡,而存于《广韵》。乃取《广韵》切语上字系联之为双声四十类;又取切语下字系联之,每韵或一类或二类或三类四类。是为陆氏旧法……于是分列声韵,编排为表,循其轨迹,顺其条理,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陈澧:《序录》,《切韵考》卷1,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叁),第1页。。这一做法,实即“以时代先后为次”,见“音学盘根错节”处,对于《说文》以下唐以前,“汉魏六朝一截”,洞明其理。黄侃综而论之,谓:“顾、江、段、王虽能由《诗》、《骚》、《说文》以考古音,然舍《广韵》,亦无以为浣准……番禺陈君《切韵考》,据切语上字以定声类,据切语下字以定韵类,于字母等子之说有所辨明,足以补阙失,解拘挛,信乎今音之管钥,古音之津梁也。”*黄侃:《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9,94页。而一变“往者,古韵、今韵、等韵之学,各有专家,而苦无条贯” 。自陈氏《切韵考》及《外篇》出,“而后《广韵》之理明,《广韵》明,而后古韵明,今古之音尽明,而后等韵之纠纷始解。此音学之进步也”*黄侃:《黄侃论学杂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49,94页。。
由此可知,陈澧小学不仅渊源于江浙一派,以声韵贯穿训诂为原则,而其具体进展,则在此基础上,更能贯通声韵之古、今,使音学贯穿联通。
三、小学与初学
陈澧虽根本于学海堂,循着江浙治经门径,层层深入所谓“乾嘉考据”之小学,然尚在其发愤治声韵之学的同时,便开始对“皓首穷经”式的小学理念于学风的正向推进产生一定怀疑。这显现他对于阮元所定学海堂治经规矩的自觉反思。
陈澧对于“皓首穷经”式小学之反思,与真正深入小学之道几乎同时。道光十八年(1838),陈澧致信好友杨荣绪,既告知《说文声表》粗已成编,又坦言对于此前深信不疑的治经路径发生怀疑。其言道:
澧今年亦教授乡里,假馆僧舍,既讲举业,还读我书。所述《说文声表》,粗已成编,复以训诂之余,辨析名物,述经传群书之言,依《尔雅》、《释名》之体,已成数篇,但未卒业耳。澧尝以为班孟坚有言云:“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此古今之同患也。夫治经者将以通其大义,得其时用也。若乃小学一道,经术首基,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然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窥堂陟奥,俟之何年?又诸儒之书,多宏通之篇,寡易简之作,可资语上,难喻中人。故童蒙之子,次困之材,虽有学山之情,半为望洋之叹。后学未振,或此之由。澧所为书,事繁文省,旨晦词明,思欲视而可识,说而皆解,庶几稽古之初桄,研经之先路。若乃方闻硕学之彦,沈博澹雅之才,见而陋之,亦无懵焉。*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3—444页。编者有按语:此文“有眉批云:‘道光十八,在粤寄京。’盖识作书时日也。”
显然,陈澧对于小学这一“近世儒者,咸知考索”的学问之道,能否体现本应担当的“经术首基”、振兴学风、便于童蒙的责任深表怀疑,甚至推测“后学未振,或此之由”。这一怀疑与其本人深入其中既是一矛盾,也很可能是深入之后的切身体会。
欲真切体会陈澧之意,需先置身于清人“小学”观念本身的发展史中去考究。仅就“小学”理念本身而言,清代“小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两大宗。其一为秉承朱子《小学》之意,注重“幼仪”之学。其一偏重于六书之学。
清廷以程朱一脉的理学为学问正宗,故朱子“小学”,当然是一大支。顺、康、雍期间,不少官场与士林中人对此有所集解、分类。如《四库全书总目》中便列具高熊徵《小学分节》、张伯行《小学集解》、黄澄《小学集解》、蒋永修《小学集解》、高愈《小学纂注》、玉建常《小学句读记》。另李塨编辑有《小学稽业》,甚至叶鉁还编撰了《续小学》。此类书皆是根本于朱子《小学》。其中,张伯行、蒋永修皆带有官方性质,加以推行。根据《四库全书总目》,张伯行撰是编,缘于“坊刻小学数十种,纂注标题,止为试论剽窃之具,无当于朱子亲切指点、引人身体力行之意,因集诸家注释,融会其说,以成是编”*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95,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804页。。一方面反映当时朱子《小学》的流行,一方面反映此书正本清源的指向。
当然,诸多研求朱子《小学》的著作中,亦以张伯行所撰《小学集解》影响最大。其序发明朱子《小学》之意,称:“朱子集圣经贤传及三代以来之嘉言善行,作小学书,合内外二篇,三百八十五章,以立教、明伦、敬身、稽古为纲,以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使夫入大学者,必先由是而学焉,所谓做人底样子是也。”*张伯行:《小学集解序》,《正谊堂续集》卷4,清乾隆年间刻本。反映当时士人对于小学的认识,重在幼仪,养德性,为大学培基,不仅断不止教以六书而已,主要也不是六书之学。
同时,清人治学,承明末学风,渐趋朴实,解经多重训诂之学。如对清人学风影响甚大的顾炎武,便主张:“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顾炎武:《答李子德书》,华忱之点校:《顾亭林诗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73页。启发后世学风。乾嘉大师惠栋,承前人之言,称:“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惠栋:《九经古义述首》,《松崖文钞》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1427册,第269页。戴震有所推进,主张:“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戴震:《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赵玉新点校:《戴震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68页。钱大昕也如是说:“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钱大昕:《经籍籑诂序》,《经籍籑诂》卷首,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大体反映清儒治学独重声、形、义,以此为解经根基。这一治学理念,以声韵训诂为根基,必然刺激六书之学盛行。当然,此道亦是循序渐进。晚清名儒俞樾便注意到:“以亭林先生之博洽,而始一终亥之《说文》,未一寓目。栋下老人周亮工,并误以为始子终亥,可发大噱。直至乾嘉以来,乃始家有其书,人习其学,今则三尺童子皆读《说文》。”*俞樾:《与章一山》,《文献》2006年第1期。总体而论,“说文解字”之小学,由治经的基础与路径,渐而演为独立之学,附庸蔚为大国,成为学人终身研求而不可竟的事业,也是乾嘉以降的事了。
而此一类小学,因缘于《四库全书》的修撰,确立了其正统地位。成书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皇朝文献通考》,由张廷玉奉敕编撰,后嵇璜、刘墉等奉敕再撰,最终由纪昀等校订。在此书《经籍考》内,列举上述蒋永修《小学集解》,编撰者按语道:“古所称小学,皆《尔雅》、《方言》及六书训诂而已,至朱子以《小学》对《大学》,勒成一书,多切于身心日用之言,义类当属儒家。”*清高宗敕撰:《清朝文献通考》卷225《经籍》15,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考6879。已显现此时小学观念的变化。这一理念,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意如出一辙,其称:“经部之小学类……流派至为繁夥,端绪易至茫如。谨约分小学为三子目……今惟以论六书者入小学,其论八法者,不过笔札之工,则改隶艺术。”直接明确,以讲六书者列入小学*永瑢等撰:《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四库全书总目》卷首,第17页。。提要小学类的叙说,讲述详细,针对明确,称:“古小学所教,不过六书之类,故《汉志》以《弟子职》附《孝经》,而《史籀》等十家四十五篇列为小学。《隋志》增以金石刻文,《唐志》增以书法书品,已非初旨。自朱子作《小学》以配《大学》,赵希弁《读书附志》遂以《弟子职》之类并入小学,又以蒙求之类,相参并列,而小学益多歧矣。考订源流,惟《汉志》根据经义,要为近古。今以论幼仪者,别入儒家;以论笔法者,别入杂艺;以蒙求之属,隶故事;以便记诵者,别入类书。惟以《尔雅》以下,编为训诂;《说文》以下,编为字书;《广韵》以下,编为韵书。庶体例谨严,不失古义。”*永瑢等撰:《小学类叙》,《四库全书总目》卷40,第338页。
如此,明确小学类书,只应包含训诂文字之书,幼仪一类应在小学之外。小学便与蒙学、幼仪等没有关系了。消减幼蒙之意后,小学训诂也便与其他经学书籍一样,成为儒者终身研习的门类之一,以至白首不能穷。至于解说朱子《小学》、续撰朱子《小学》的书籍,都归入子学类,评价也不高。更加突出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对于蒋永修《小学集解》的处理,因其原为《孝经小学集解》之合作,不仅拆分,更称:“以宋儒杂纂之本,与圣经并为一编,拟不于伦。”*永瑢等撰:《孝经集解》提要,《四库全书总目》卷32,第267页。“圣经”与“杂纂”的论定,极见意思。
《四序提要》对于小学作正本清源式的诠释,未必完全符合所谓“古小学”的真意。余嘉锡辨证《四库提要》,指出《四库全书总目》“所据者,仅仅由《汉书·艺文志》以上溯刘歆之《七略》而已,未尝征之于他书也,究之歆以前,亦并不如此” 。遂据《礼记·内则》、《大戴礼·保傅篇》、《尚书·大传》、《白虎通·辟雍章》、《汉书·食货志》、后汉崔寔《四民月令》等先秦两汉书籍,证明:“要之,幼童之入小学,其所学皆幼仪也,所谓学小艺而履小节也。此为人生之始基,养正之功,有多少事在,故使之读《论语》、《孝经》,以培养其根底,断不止教六书而已。”且断言:“有康成《礼记注》所言小学之制,与宋儒何尝有几微之不同乎?”*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73页。
只是,《四库全书总目》深入人心,学人以此为学问门径,此“小学”自然风行。“小学”也与“幼学”之意相距越来越远。这也必然引起学人的反思。
深入其中的汪喜孙,有鉴于此,指出:“古人六岁入小学,即通训诂,识九千字始为吏。”进而述戴震“今人或皓首不能明”之说,强调“小学乃为学之门户,非终身之业也”。事实则是,虽然“近来六书、九数,家有其书,人为其业”。而大体为终身之业,如戴震一门,号称汇聚清代学人菁英,也是“传小学者多于《三礼》,传《三礼》者胜于义理。(《孟子字义疏证》,东原先生自谓平生第一书;段以为是书,所以正人心也。)于《尔雅》、《说文》、《方言》、《释名》、《广雅》、古音、等均之学,实过汉儒;而《三礼》之学只任子田,亦不甚深;义理之学只洪初堂,亦未成书”*汪喜孙:《与刘孟瞻书》,《汪孟慈集》卷5,《汪喜孙著作集》,台北:中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第164—165页。。话语虽曲折,意思却很明白,即小学本应为治经初基,进学之阶。“小学”盛行下,本应该如戴震等所提倡,最终是由训诂进而知义理,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当然,这既体现“皓首穷经”式的以“六书之学”为本的小学盛行于学界,同时汪氏之言,本身也体现着对此的反思。
汪氏之论,绝非孤往独发。嘉庆年间,学人钱馥旗帜鲜明地进行汇合两种小学的实践,其结果即是《小学盦遗稿》。阮元序其书,称:“《汉志》载史籀、苍颉等十家为小学,宋人又辑《小学》书,专言明伦立教之旨。处士谓必兼汉儒、宋儒之说,而小学之义乃备。尝自题其居曰:‘小学盦’,其学与行概可知矣。”*阮元:《小学盦遗稿·序》,钱馥:《小学盦遗稿》卷首,《丛书集成续编》第92册,第691页。吕荣作跋语,道:“海宁钱处士广伯读书稽古,不为举子业。尝以小学名其盦。程子有言:自洒扫应对,便可到圣人事,是小学即大学之根柢也。至于研求音韵,参考异同,据三十六字母以通古音,从二百六部以寻古韵,皆抉汉唐诸儒之奥。盖音声所以定训诂,训诂所以明义理,苟文字之不解,而谓有得于心者,妄也。”*吕荣:《小学盦遗稿·跋》,钱馥:《小学盦遗稿》卷末,第735页。钱氏汇通六书小学与洒扫应对诸幼仪之意甚明显。然而有意思的是,就其本人实践看,以穷一生之力从事于小学,本身即与天然便有“幼”这一意思的小学有着隔阂。
稍后的曾国藩,虽极重王氏父子的训诂学,却显然将小学更归于蒙养之意。曾氏认为:“班固《艺文志》所载小学类,皆训诂文字之书。后代史氏,率仍其义。幼仪之繁,阙焉不讲。三代以下,舍占毕之外,乃别无所谓学,则训诂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则训诂文字者,亦犹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绘事后素。’不其然哉?”而强调:“先王之治人,尤重于品节。其自能言以后,凡夫洒扫、应对、饮食、衣服,无不示以仪则。因其本而利道,节其性而不使纵,规矩方圆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剂其血气,则礼乐之器盖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学,乃进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习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扩焉,故达也。”故曾国藩实际认同朱子《小学》“古圣立教之意,蒙养之规,差具于是”,“故录此编于进德门之首,使昆弟子姓知幼仪之为重。而所谓训诂文字,别录之居业门中”*曾国藩:《钞朱子小学书后》,《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47—148页。。这一处理非常有意思,实际是保留朱子小学为幼学进德之学,而承认六书之学为可终身治之之业。
无论如何,这些反应,都与清代两种“小学”共存并立导致的争议有关,处理的是究竟何为古之小学,或何谓真小学,如何各见其长的问题。陈澧的自觉反思大体与此有关,而其指向,则另见意思。
前已述及,陈澧早年问学于张维屏,张告之以《四库提要》。这不仅成为陈澧进学之阶,也是教弟子门生的一大功课*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11—12页。。陈氏小学观念不免受《四库提要》影响。从上引《答杨黼香书》可见一斑。此文既认同“小学一道,经术首基,近世儒者,咸知考索”,又质疑近儒“或《苍》、《雅》甫明,华颠已至” 。故曰:“窥堂陟奥,俟之何年?”显然,大致以《仓颉》、《尔雅》等为小学,符合《四库提要》阐发之意。陈氏之质疑,与上引汪喜孙的反思相近,落脚于:小学究竟应为终身研求、白首不能穷的事业,或是以此传授初学,便于幼童治经的门径。陈氏对于当时亦流行的后儒发挥的朱子《小学》实际并不喜好,其读张伯行《小学集解》道:“道学先生不甚读书,慎勿著书,议论迂陋,不足以感发人而徒使有学能文之士鄙薄之。”*陈澧:《北宋》(五),《陈澧遗稿》第53合订本。
当时的陈澧正循学海堂所导引的江浙小学门径治文字声韵,其反思当应出于深入其中的切身体会。陈澧此文所引古典,出自《汉书·艺文志》,重心在于《艺文志》称:“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30,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23页。而学海堂实际上是强调白首穷经之艰苦卓绝的治经精神。阮元序《汉学师承记》,即称:“我朝儒学笃实,务为其难,务求其是,是以通儒硕学,有束发研经,白首而不能究者,岂如朝立一旨,暮即成宗者哉!”*阮元:《汉学师承记序》,朱维铮、徐洪兴编校:《汉学师承记(外二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页。不仅不以“束发研经,白首不能究”为不存大体,而以此为治经笃实表现。故学海堂经解之文,如《艺文志》所批评,说一字多至数千言者毫不稀奇。《学海堂集》中《易之彖解》、《尚书之训解》、《诗之雅解》、《春秋之传解》、《仪礼之记之传解》,何尝不如是*参见《学海堂集》卷1,清道光五年,启秀山房刻本。。陈澧读《汉书·艺文志》,案语:“古之治经者,存大体,玩经文,非如今日之治经也。”*陈澧:《东塾杂俎》卷12,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698页。其中两种治经方式之高下暂不论,其意思则颇具现实针对。
此文反映陈澧一时的治经理念,这一理念中,诸如视六书之学为小学核心以及“由考据而明理,余之学也。讲义理必由考据,否则臆说耳,空谈耳”*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83,385页。,与学海堂秉承的训诂明后义理明的治经理念并无大异。差异处,在于“皓首穷经”式的小学,本身既已穷尽人力,如何再能在此基础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呢?这本身便是小学脱离治经之基,附庸蔚为大国后,与其本来寓有“幼学”之意间的必然矛盾。值得关注的是,此信对此矛盾似已找到解决方案,所谓:“澧所为书,事繁文省,旨晦词明,思欲视而可识,说而皆解,庶几稽古之初桄,研经之先路。”*陈澧:《答杨黼香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44页。此处虽不明确,还是可看出具有浅化“小学”,尽力恢复幼意,导向真正治经先路的意思。
四、小学与以浅持博
陈澧这一治学眼光转向较早,而在此理念指导下的实践,因各种原因而落实较晚。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后续发展,反映陈氏精心结撰汉宋兼采之学的动因,及化“小学”为“浅学”以筑汉宋学始基的深远运思。

此计划,大概酝酿于道光十八年陈澧对“皓首穷经”式的小学弊端作出反思至道光二十四年(1844)侯度“大挑一等,试用知县,分发广西,署河池州知州”间。后直至咸丰五年(1855),侯度方归家,惜不久便离世*陈澧:《二侯传》,《东塾集》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97页。。因为现实原因,此事遂作罢。
在此期间,道光二十年(1840),三十一岁的陈澧被补为学海堂学长。在此后的十年间,陈澧循着学海堂所导引的江浙门径,治声韵训诂之学而有成,《说文声表》、《切韵考》、《声律通考》相继面世。道光二十九年(1849),又集“考证经史子集、天文、舆地、算法、音韵、金石之文共若干篇”,陆续刻成《东塾类稿》*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第25—42页。桂文灿著,王晓骊、柳向春点校:《经学博采录》卷4,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0页。。这些循江浙门径的论著,为陈澧赢得极高的学术声誉。
这十年是陈澧深入近儒小学的十年,也是极思突破的十年。深入此道的成功,并未打消其恢复“小学”便于初学的初衷。之所以没有延续此前编撰“真小学”书的原因,或在编撰此类书籍一人不可为功,不能仅凭自己之力;而启蒙之书,又“非老师宿儒不能为,盖必其途至正,其说至明,约而不漏,详而不支”*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方可,故人才可遇不可求。
大概在道光三十年(1850)稍前,陈澧找到了合适的编撰人选,此人便是精于《说文》之学的徐灏。陈澧对他循循善诱,道:“今当著一书,略如君家楚金《通释》之意,发凡起例,开通门径,使许书义例,易知易从,则于此学为功大矣。所谓理而董之也,任此事者,非君而谁?”*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此书即为《象形文释》。陈澧对全书编撰方向,有明确意见:“尊著《象形文释》,必须分类如旧,断不宜改为编韵……澧教小儿,即用吾弟之法……录许书元文,须加疏解,故不如概括之简明。”*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简明”与“教小儿”显现此书简化六书之学,为初学入门的旨趣。而当听闻徐灏欲将此书改为《说文笺》,陈澧虽称“亦甚是”,更强调“原书可为学僮讲授之本,真古人所谓小学……其实古人所谓小学,正是如此,能成此等书,其功正不小耳。容稍暇再详具条例奉商,同力合作,乃易就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65页。此信称:“澧暂停河源之行,已到县递呈告病假,欲俟明春方赴考验。”又称:“近来因敝门人虞子馨一病不起……何期夭折如此。”根据陈澧《自记》,虞必芳卒于道光三十年,赴河源县训导任在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日,故可定此信作于此年。。稍后又函告:“急欲读《象形文释》,乞早日寄示。近日实甫弟七令弟怡庭颇似有志,常来问小学,欲以此书授之,将来能诱掖一二人,知小学门径,亦未可知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短期内连番函告催促,温和的陈澧难得地显示出急迫、强硬与必得之意。
徐、陈二人有关小学观念的矛盾,恰反映陈澧小学观念与学界通行小学观念的冲突。徐灏有心笺释《说文》,但不能接受的是,他有心做的是接近段玉裁式的学术发挥,而非陈澧强调的启蒙幼学。陈澧序《新刻说文解字附通检》,称:“《说文》,小学书也。《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汉尉律学童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今人以识篆书习《说文》者为古学,岂能八岁教之,十七岁试之哉。”*陈澧:《新刻说文解字附通检序》,《东塾集》卷3,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25—126页。可参证此意。陈澧对徐灏之意当然了然于心,以为“吾弟之意,似轻视启蒙者,与澧所见不同”*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7,460,464,458页。。
陈澧强调启蒙之功,以为:“学问之事,莫难于入门,既入其门,则稍有智慧者,必知其有味……入门者多,则此道日昌,其能深造者为通儒,不能深造者亦知其大略,而不至于茫昧,而文学彬彬矣。”故“精深浩博之书,反不如启蒙之书之为功较大” 。古之小学,“十五岁以前之学也。十五岁以前,既明乎此,故十五而入大学,三年通一艺,三十而六艺皆通也”。实即启蒙入门之意。“书虽曰启蒙,而实入门,则学者多;学者多,则通人出;门径端正,则初学不误;初学不误,则谬说不作。夫通人出而谬说不作,天下有阴受其益者矣。”于维护世道与学风皆有益。而“百年来儒者之治小学,为唐宋诸儒所不及,然所著书,往往精深浩博,但可为知者道,中人之资不能领解,读不终卷而置之矣……真白首而不能穷者,非古人所谓小学也” 。虽“稍稍有志者,读此等书,又苦不得其门而入,此学术所以不振”。所以,陈澧“独恨百年以来,未有著此等书者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又称:“小学之功所以大者,为天下教初学童子,凡人无不自童子来者也。”*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95,395,366页。
咸丰元年(1851),陈澧撰成数年来颇耗心力、符合其理念的“小学”书籍,名为《音学》。陈氏随即函告徐灏:“近著音韵书一种,甚有法,以授小儿女,四声,清浊,双声,叠韵,累累然脱口而出。”并谓:“此正可与《象形文释》并传。”虽然《象形文释》已散入《说文笺》,他还是指出:“所引群书,并不必录许书元文,而本许氏及群书之旨,隐括其词,自为之释,义取简明,俾家家塾师皆能为学僮传授为佳。”*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导其入启蒙初学之意。
这一实践,反映陈氏理念。而这一理念,与前引道光十八年时其所作反思同条共贯。虽然陈澧对于乾嘉小学颇多反思,欲将其化为启蒙初学之意,却也显然仍以《四库提要》所约束的六书之学为小学核心,并非有心走向宋儒“洒扫应对”之小学。陈澧读朱竹垞《重刊玉篇序》,对其中 “宋儒持论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由是《说文》、《玉篇》皆置不问。今之兔园册子专考稽于梅氏《字汇》、张氏《正字通》,所立部属分其所不当分,合其所必不可合,而小学放绝焉。是岂形声文字之末与?推而至于天地人之故,或窒碍而不能通,是学者之深忧也”颇有感,谓:“此等议论开一代风气,此真中宋儒之病。然今仍不以《说文》、《玉篇》为小时之学,而以为皓首研穷之学,而大学又于绝矣。论学甚难,稍偏即有流弊。”*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95,395,366页。
咸丰二年(1852)张维屏作《古诗赠陈兰甫学博即送北上》,称陈澧“小学尤专门,嘉惠到童稚” 。自注谓:“君以近儒小学书皆奥博,著《初学编》,于六书、训诂、音韵,皆浅言之,使初学易晓。”*张维屏:《松心诗录》卷10,清咸丰四年,赵惟濂羊城刻本。极能揭示陈澧之意。而陈澧对此有所计划,定有专人。他与桂文灿通信,说道:“至《初学编》之作,明年看来又不能专功,且未必人人皆勤奋,各人各自勉成之可也。”*陈澧:《与桂皓庭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29页。
“六书之学”作为乾嘉儒者治经之道,影响深远,学海堂实亦承此而来。陈澧如此处理,颇具纠正乾嘉考据学入学门径之意。陈澧认为此时学风衰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尝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盖浅尝者有之,深造者未必有耳”,“以百年来诸儒提倡之力,而衰歇之易如此”。强调:“推原其故,非尽时文之为害,此朱子所云欠小学一段功夫耳。”故认为“我辈既无势力以振之,又不尚声华标榜,惟有著书专明小学一段工夫,以教学者,使其易入……近儒号为明小学,然其书岂学僮所能读,则虽谓之欠小学工夫可也。初学欠小学工夫,岂能读近儒奥博之书,此其所以易衰歇也”。揭出:“如能补小学工夫,则汉学、宋学皆有基址,然后可以义理、考证合为一矣。”*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揭示“补小学工夫”于沟通汉、宋学之效力。
所谓义理、考证合为一道,实即由小学进于大学之道。陈澧读《学记》“此大学之道也”之正义“是大学圣贤之道理,非小学技艺耳”,叹息“近百年来之学,皆小学技艺耳”*陈澧:《东塾读书论学札记》,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395,395,366页。。将终身为之、皓首穷经式的“小学”,深入浅出,化为真正的“小学”,在此根基上,进于大学,融汇汉、宋学,是陈澧的抱负。
更具用意的是,陈澧“小学”的观念,仍有扩张,实不限于“六书之学”。
陈澧对徐灏称:“小学工夫,须有两层,此等是下一层,尚有一层工夫,教人初读古书者,其书不易作,然竟欲夕为之也。”*陈澧:《与徐子远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58—459,454,455,457页。陈澧读《南齐书陆澄传》之“时国学置郑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榖梁》,郑玄《孝经》。澄谓尚书令王俭曰:《孝经》,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便注意到:“尔时不专以字训诂为小学,而谓孝经为小学之类。深得古小学之意。”*陈澧:《晋至隋诸史·学思稿·孝经·孟子》,《东塾遗稿》第12合订本。
此上一层之小学,反映陈澧彻底跳出乾嘉考据的六书小学。陈澧与其最得意的弟子桂文灿道:“前日携来朱墨字《春秋地图》,仆一见以为甚善。夜间复思之,喜而不寐,此庶几可当荀卿所谓以浅持博者,有益于读《春秋左传》者不小。仆尝谓无人能著浅书,盖书虽浅,用功实深,否则粗浅而已,浅陋而已,何能持博哉!所谓浅者,能使人从此得门而入,及其学问大进,而仍不能出其范围,故足贵也。近者,震伯为《说文检字》,与足下之为此图,皆可当‘浅’之一字。更望于此用功,精益求精。所谓精者,心精、力精、体例精,及其成书,而人仍不见其精,乃可谓以浅持博也。见震伯时,并以此告之。若礼乐、天算等事,皆有此一种书,则后学之幸矣。”*陈澧:《与桂皓庭书》,《东塾集外文》卷5,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439—440页。其中“复思之”、“喜而不寐”,可见其得“以浅持博”之书的欣喜。
此意更可见咸丰五年(1855)陈澧《复王倬甫书》中,道:“尚有未成之书二种:一则以荀子云:‘以浅持博’‘是大儒者也’,本朝儒学奥博,而无以浅持博之书,初学之士,难得其门而入,故其道易衰。因欲取礼、乐、书、数、天文、地理之类,以其浅者粗辟门径,启导初学。”*陈澧:《复王倬甫书》,《东塾集》卷4,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第162页。晚年自述著书的主要用意,称:“余之著书,一则标举大纲,一则整理繁乱,一则抄撰群书。维正学,救流弊,晓初学,有益有用。”*陈澧:《学思录序目》,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第768页。
陈澧著书大纲中“晓初学”占据重要位置,对于他来说,这是维持学风,救正学弊的重要一环,牵涉治学门径的正误。陈澧晚年论及此事,仍强调:“四五十年前,诸儒以博学矫前明之陋甚有功,但不当并讥刺朱子也。宋学既衰,而又不能维持汉学,故今日汉宋之学俱衰也。如使我《初学编》成,则能以浅持博,而汉学不衰矣。”*陈澧:《东塾杂俎·通论》,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稿本。显然,《初学编》已突破原本简化六书之学之意,而成以浅持博的群书入门。这一举动,蕴含着陈澧修正乾嘉以来学人治学门径的抱负。
综上所论,陈澧逐渐深入“乾嘉考据”之小学后,便开始对这一“皓首穷经”式的治学理念能否承受“治经门径”的初意产生怀疑。“训诂明而义理明”的“训诂”既已变成终身之事,那么“义理”及其所承载的“大学”能否达到,便顺理成章成一大疑问。故陈澧“小学”理念与实践的展开,经历以下过程:一开始对于六书小学作深入浅出的诠释,以期恢复小学“古”意——亦即幼学之意,进而将此“真小学”发挥至群书入门的门径,真正变成“以浅持博”的门径书。这一过程,既反映其小学理念的变化,也承载其改变乾嘉大儒在治学实践中形成的治经门径之抱负。这一理念,当然也蕴含陈澧与学海堂所本的江浙学术立异、争胜的运思,体现确立新的学海堂治经门径的意趣,也凸显其构筑沟通汉宋之学的基调。
【责任编辑:赵洪艳;责任校对:赵洪艳,张慕华】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5)04-0074-16
*收稿日期:2015—02—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学海堂与近代汉宋关系”(13YJC77006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13FZS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中山大学青年培育项目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