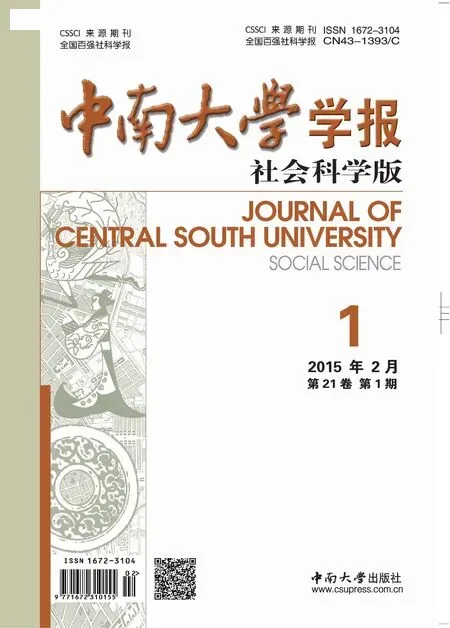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失乐园》对《圣经·创世记》的传承与超越
李滟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失乐园》对《圣经·创世记》的传承与超越
李滟波
(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失乐园》对《圣经》的传承与超越表现在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这两个方面。就经典互文而言,《失乐园》第7、9、10卷在情节、题材和主题上与《创世记》第1-3章构成尤为显性而密集的互文指涉,主要显现于弥尔顿对《创世记》文本大量且大胆的引用和转述;就文学想象而论,史诗对上帝所造之物的拟人化和具体化描写丰富了创世造人情节;对亚当夏娃尝食禁果前后内心活动的细致刻画和对人类堕落带给大自然伤害的艺术化呈现拓展了人类堕落题材;关于亚当夏娃对待惩罚之态度与认识的诗性描写深化了罪与罚主题。通过经典互文,史诗传承了《圣经》原有的宗教文本内涵;通过文学想象,诗人赋予《失乐园》独特的宗教审美意蕴。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共同成就了《失乐园》永恒的经典地位。
弥尔顿;《失乐园》;《创世记》;经典;互文指涉;文学想象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经典》中指出,文学经典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让读者初次阅读时“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1]被布鲁姆誉为“圣经般的史诗”的《失乐园》,其“神奇的力量”主要源自对西方文化源头经典《圣经》的传承与超越,分别表现在经典互文和文学想象这两个方面。整体而论,史诗《失乐园》与《圣经》有着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①但就情节、题材和主题而言,讲述上帝创世造人、人类堕落及罪与罚故事的第7、9、10卷更是“严格依循《圣经》的叙事”[2],与《圣经·创世记》第1-3章形成高度对应的互文关系,构成互文指涉的诗文多达587行,占这三卷诗行总数的20%,呈现出显著的互文特质。
一
讲述上帝创世造人故事的第1章由31节经文构成,英文含词量(“钦定本”)不足八百,但具备完整的情节元素: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尾。其间,作者逐一描述上帝六日创世造人全过程,叙事呈推进式展开,天地万物逐一呈现,创世场面宏大雄伟且井然有序,叙事风格“庄严却不失崇高的简洁”。[3]
《失乐园》第7卷是史诗下半部分的开端,从先前对撒旦堕落的叙事闪回到对上帝六日创世的讲述。在述说上帝六日创世造人故事时,弥尔顿完全依循《创世记》第1章的情节结构,辅之以第2章中的造人情节,与《创世记》构成显性而密切的互文指涉关系,其中最显著的互文特质是对《创世记》第1章文本的引用、转述和拼接。②
据《 创世记》1:3,“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③史诗对该经文的直接引用(PL VII.243)表明,弥尔顿在两个方面完全认同《圣经》文化内核。首先,诗人认同上帝言语创世说,八次借用“上帝说……”这一句式,将上帝的话语置于存在之上。这虽有悖于希腊哲学关于存在先于话语的认知,但一如斐洛所言,当上帝在“说”时就是在创造,其话语与存在同步;其次,诗人认同《圣经》中“光”的文化内涵及其象征意义。在弥尔顿看来,作为“万物的始初”和“纯粹的第五元素”的光实为“上帝的最初显现”[4],与原初的“黑暗”形成鲜明对照,代表至善的上帝战胜代表邪恶的“黑暗”。在基督教文化中,“光”与“暗”是“善”与“恶”的隐喻之说,如《新约》中耶稣自喻“世界的光”(《新约·约翰福音》8:12)。弥尔顿对“光”有着独特的领悟,认为人类必须接受“上帝播种于我们心中的理性之光”的指引[5]。这“理性之光”对当时身处双重黑暗中的诗人来说是“精神力量”的象征[6],是激励他完成史诗的精神灯塔和力量源泉。
以《创世记》为互文对象,史诗第7卷中,上帝第二日造出天空,所用诗文“众水之间/当有穹苍,众水和众水要分开!/于是就造成了穹苍”。④(PL VII.261-64)是对《创世记》1:6-7的直接引用。据《创世记》,上帝第三日造了大海,并使露出水面的大地长出青草、“结种子”的菜蔬和“包着核”的果子。“种子”和“核”均为英文seed的汉译,seed一词在《圣经》文化中被赋予传宗接代的社会学意义。史诗讲述上帝造地并使之长出菜蔬的4行诗文完全依据《创世记》而来,同样强调菜蔬和果子“结子传种”的功能。但和《创世记》作者简约的叙事风格不同,弥尔顿运用丰富的想象力用15行诗文详细描述各种花草树木的生发过程:未经耕种的荒芜之地“立刻生出嫩草”,嫩叶给大地“披上青绿”,各种花草“使大地的胸怀鲜艳芬芳”,还有乔木“站立起来”(PL VII.315-29),呈现给读者一幅大地生机盎然的景象。《失乐园》讲述上帝第四日所造太阳、月亮和星辰之功能的47行诗文中有14行直接引自《创世记》,其中“划分昼夜……管理昼夜”(PL VII.339-52)与《创世记》措辞几乎丝毫不差,其互文指涉清晰可辨。弥尔顿继而用61行诗文描述上帝第五日所造海里和空中的活物,其中14行诗文(PL VII.387-98;446-47)直接出自《创世记》,就连上帝赐福所造之物的话语“生养众多”(Be fruitful and multiply)也被弥尔顿原封不动地搬进史诗中。但与用词精简的《创世记》不同,诗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水里“成群结队”的鱼群、“贪玩”的海豹、“摆腰”的海豚,还有空中“翱翔”的小鸟、“凌空飘舞”的天鹅。诗人对上帝之造物的描写栩栩如生,彰显绝境中的诗人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自由的渴望。
《创世记》中,上帝的创世在第六日达到高潮。继海里和空中的活物之后,上帝造了地上的生物且使之“各从其类”。以此为互文前提,在转述上帝所造之物的同时,弥尔顿凭借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以50行诗文的篇幅将大地拟人化并将上帝所造生物具体化:“大地立即从命,敞开丰润的肚子,/产生一群群的生物。”(PL VII.453-55)大如狮子、老虎和大象,小若鼹鼠、昆虫和蚂蚁。诗人笔下的十几种动物形态习性各异,但和谐相处,宛若一幅动物总动员的欢乐图景:“水、陆、空中满是虫鱼鸟兽,/成群结队地泅泳、飞翔、行走。”(PL VII.502-03)至此,诗人依据《创世记》第1章中的创世情节逐一描述了上帝对宇宙万物的创造,在传承《圣经》宗教文本内涵的同时赋予了史诗中创世故事独特的宗教审美意蕴。
创造人类是《创世记》中上帝六日创世的最高峰。《失乐园》第7卷中,弥尔顿巧妙地将上帝所言(《创世记》1:26)和上帝所为(《创世记》2:7)完美地“拼接”在一起,完成对上帝造人故事的完整叙述:“现在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他说了这话就造了你,亚当/一个尘土的人;他把生命的/气息吹进你的鼻孔/于是你成了一个活的人。”(PL VII.519-28)诗人的高妙之处在于借天使拉斐尔向亚当转述的方式将《创世记》中的两个造人故事缝合得天衣无缝。⑤《创世记》中,上帝创世造人后创世高潮结束,“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1:31)然而,这并非《圣经》创世故事的结束。《创世记》第2章前三节是第1章的自然延伸:上帝将第七日定为圣日后便歇息了。这不仅解释了犹太教和基督教文化中安息日的由来,而且给上帝创世造人故事一个完满的结局。弥尔顿以此为互文对象完成对上帝六日创世造人情节的描写:上帝眺望他的“一切创造物,看一切都好”(PL VII.548-49)。但不同于《创世记》简洁的叙事风格,诗人的想象力跃出《创世记》之外,用40行诗文渲染天使们在天庭里欢庆这圣日的和美景象:各种乐器“和鸣协奏”,歌颂上帝的“六日工程”,迎接上帝的“凯旋”(PL VII.594-634),充分体现了诗人对上帝创造之伟绩的颂赞。
由是观之,《失乐园》第7卷关于上帝创世造人的情节走向和文本内涵与《创世记》第1章保持高度一致,致使有学者认为“整个第7卷不过是《创世记》某些章节的诗译而已”。[7]更为重要的是,弥尔顿凭借其超凡的文学想象力将敬畏生命和渴望自由的情愫倾注于对上帝所造万物的诗性书写中,从而使史诗中的创世造人故事更加生动和丰满。
二
就题材的互文指涉而言,《失乐园》开篇即开启了与《创世记》的互文之旅:“关于人类最初违反上帝命令/偷尝禁树的果子,把死亡和其他/各种各色的灾祸带来人间,并失去/伊甸乐园……”(PL I.1-4)史诗首句论及《创世记》伊甸园里的禁树、禁果⑥、禁令和破禁,是对《圣经》中人类因堕落而失去乐园这一重要题材的直接转述。关于《圣经》中人类的堕落,一直是令神学界和宗教界困惑的问题,也是文学创作中经久不衰的题材,作为清教徒诗人的弥尔顿对此更是情有独钟。⑦弥尔顿对该题材最全面且最深刻的诠释集中在史诗第9卷。
《圣经》中人类最初的堕落记载于《创世记》第3章,直接源自蛇对女人的诱骗。加之禁果本身好作食物,悦人眼目,能使人有智慧,于是在多重诱因的驱使下,女人“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3:6)。《创世记》作者仅用6节经文(“钦定本”共计179个英文单词)勾勒出人类堕落这一重大事件,夏娃悲剧性的抉择使《圣经》中的人类堕落故事成为“整个西方文学的一个原型悲剧”。[8]
《圣经》中关于人类堕落故事的记载极为简短,为后世留下众多阐释余地和想象空间。史诗中,蛇将夏娃引到禁树前并挑衅道:上帝“不许(你们)吃园中一切树木的果子?”(PL IX.656-57)对此,和《创世记》中的女人一样,夏娃回答蛇说只有园子中央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否则必死无疑。为了达到引诱人类堕落的目的,蛇进一步诱骗女人说,吃禁果会使眼睛明亮,能和上帝一样辨善恶。于是女人采果而食,人类由此堕落。实质上,关于《圣经》中“勿食禁果”的禁令,弥尔顿在史诗中多次重申,且反复强调尝食禁果与死亡的必然联系(PL VII.542-44;PL VIII.323-30),足以表明诗人对上帝的敬畏和对生命的热爱。
除引用和转述《创世记》第3章相关文本外,《失乐园》第9卷主要是通过运用文学想象填补叙事空白的方式诠释了《圣经》中的人类堕落题材。
弥尔顿关于《圣经》堕落故事的文学想象力最突出地体现在对夏娃和亚当尝食禁果前后心理活动的刻画上。《创世记》对女人吃禁果前的内心活动没有任何描述,但史诗第9卷中随着蛇狡智的言辞进入女人脆弱的心,夏娃定睛看着果子出神,且时值中午,果子的香气激起她难抑的食欲。与《创世记》里女人屈从于蛇的引诱摘果而食不同,弥尔顿笔下的夏娃“踌躇”片刻,关于知识、自由、死亡和公义等问题使她陷入“沉思”。对此,史诗用35行诗文详细描写夏娃内心的各种疑惑,终于“她那急性的手,/就在这不幸的时刻伸出采果而食”(PL IX.780-81)。尽管诗人对夏娃摘食禁果这一举动本身的描写如同《创世记》一样简短,但“急性”(rash)一词生动形象地描述了夏娃对禁果的贪欲和对禁令的漠视,无视禁令必然导致“不幸”。史诗继而用39行诗文将女人尝食禁果后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先是对“万能之树”的赞美,转而犹豫是否该与亚当共享“全部快乐”,进而担忧独享禁果会遭致死亡从而失去亚当,最后决定“和亚当祸福与共”(PL IX.795-833)。弥尔顿将自己对女性的敏锐观察和对人性的深刻思考融入史诗中,将《创世记》中原本扁平的夏娃形象刻画得血肉丰满,无疑增强了夏娃犯禁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史诗中的亚当得知夏娃触犯天条时顿时“茫然若失”,一阵寒栗之后先是斥责夏娃违犯禁令“冒渎神圣的禁果”,继而誓死与妻子患难与共:“但我和你是/注定同命运的,和你一同受罚;/和你相伴而死,虽死犹生。”(PL IX.952-94)亚当生死与共的坚定态度让夏娃喜极而泣,于是她“慷慨地从枝上把那诱人的美果/摘下来给他。他不迟疑地吃了,/违反自己的识见,溺爱地被/女性的魅力所胜”(PL IX.995-99)。与《创世记》中被动地尝食禁果的男人不同,弥尔顿笔下亚当的堕落主要源自女人外表的魅力和对女人的怜爱。《失乐园》中,彻底堕落后的人类始祖意识到已经失去“廉耻”“天真”“忠信”和“纯洁”,于是二人泪如雨下,内心满是怨恨和猜疑,第9卷在始祖二人没完没了的“相互斥责”和“无益的争论”中落下帷幕。
史诗第9卷中诗人的文学想象还表现在对女人堕落场景和蛇狡诈性诱惑的描写上。弥尔顿为女人的堕落铺陈出一个极易被诱惑的场景:因为亚当的不在场,身处伊甸园幽栖处的夏娃“如此孤独”,她“单独站着,包围在云香中/半隐半现……”(IX.425-26)。此情此景中的夏娃曾一度使蛇的恶意退缩,但它马上陷入“憎恨”和“忌妒”,一番思索之后决定实施“毁灭她”(IX.493)的计划。诗人5次用“诱惑者”(the Tempter)指代《创世记》第3章中“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的蛇,用116行诗文详尽描述蛇“诱惑”女人的计策和诈术(IX.532-48;568-612;679-732)。深知女性虚荣心和好奇心的蛇将夏娃比作“美丽世界的女王”“万物的主宰”“宇宙的女王”,用浮夸的言辞赞美女人的容颜和使人智慧的禁果,并以自己吃禁果后获得神力的谎言成功诱骗夏娃尝食禁果,由此导致人类的堕落。
此外,史诗对人类堕落带给大自然无限伤害的拟人化描写也充分体现了诗人无穷的文学想象力。弥尔顿笔下,因为女人的犯禁,“大地因而觉得伤心,‘自然’从座位上/发出叹息,通过万物表示/灾祸临头,一切都完蛋的悲哀。”(PL IX.782-84)如同夏娃的堕落,亚当的犯罪立刻震怒“自然”:“大地再次/从内部震战,‘自然’再度呻吟,/空中乱云飞渡,闷雷沉吟,/为人间原罪的成立痛哭而洒雷雨。”(PL IX.1000-04)史诗对男女堕落后自然景象的这种描写表明,人类始祖的“原罪”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异化。将自然拟人化是文学创作的常用手法,弥尔顿通过夸张的文学想象和艺术化描写凸显人类堕落导致的严重后果。诗人对超自然现象的这种想象性描写让读者联想到“福音书”中耶稣献身十字架时的自然景象:当时“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新约·马太福音》27:51),虽然时值中午,但“日头变黑了”(《新约·路加福音》23:45)。弥尔顿富于想象地将《圣经》中人类堕落事件与耶稣受难事件相对接,以此体现对堕落与拯救这一宗教命题的关注和思考。
通过引用和转述《创世记》第3章文本,《失乐园》第9卷生动地再现了《圣经》中的人类堕落故事,弥尔顿对亚当夏娃尝食禁果前后内心活动的细致刻画和对人类堕落带给大自然无限伤害的艺术化呈现无疑拓展了《圣经》中的人类堕落题材。虽然对该题材的讲述中没有古希腊史诗般轰轰烈烈的行动,而如迪克霍夫所说其“核心事件只不过是吃了一个苹果”,但对弥尔顿及其熟悉《圣经》的同时代人而言,该题材确实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题材,其内涵和结果具有压倒一切之势……事件本身很小,但它决定了人类的命运”[9],人类从此失去伊甸乐园,从无邪与幸福的状态坠入罪恶与悲惨的境地。弥尔顿对《圣经》中人类堕落题材的援引和再创作使《失乐园》成为英语文学中“以《圣经》为题材的最著名的基督教诗歌”。[2]尽管西方有学者批评《失乐园》将《圣经》中人类堕落的故事用作史诗题材,但弥尔顿钟情于此,因为通过该题材诗人能“最大限度地将自己对人类和历史的哲学思考写进史诗中”。[10]
三
整体而论,《失乐园》与《圣经》在罪与罚主题方面的互文指涉最直接地显现于史诗标题“失乐园”所揭示的中心题旨:人类因堕落之罪而被罚出伊甸乐园。为了准确地诠释这一主题,弥尔顿将《创世记》第3章中的相关经文直接移植到史诗中,在精心设置的互文框架内运用丰富的文学想象力对罪与罚主题进行诗性书写。如上所示,《创世记》第3章精简地讲述了人类堕落题材,但同时也最为集中地阐释了基督教文化的核心主题之一,即贯穿整部《圣经》的罪与罚问题。在由简短的24节经文构成的《创世记》第3章,前13节聚焦于人类始祖的堕落(犯罪)及缘由,后11节逐一描述上帝实施的惩罚。罪与罚主题同样贯穿《失乐园》之始终,其中第10卷对该主题的诠释最为集中和深刻。
史诗第10卷与《创世记》第3章之间显性而密集的互文指涉首先表现于诗人对上帝与人类始祖两轮对话的引用和转述。《创世记》中,上帝与人类始祖的第一轮对话关涉人犯罪之后的心理变化和行为反应。当听到上帝呼唤“你在哪里?”(3:9)时,尝吃了禁果的亚当和夏娃满怀恐惧地躲进树丛中。对此,弥尔顿在史诗中直接引用《创世记》中亚当的回答:“我听见您在园中,害怕/您的声音,因为赤身裸体,躲起来了。”(PL X.116-17)伊甸园里曾经和谐的人神关系由此破裂,“害怕”成为人犯罪后的第一个心理变化,“躲起来”便是第一个行为反应,人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而有了自我意识和羞耻感。第二轮对话论及人类犯罪的缘由。史诗中上帝与亚当夏娃之间的问与答和《创世记》第3章几乎一模一样。当被问及尝食禁果的原因时,亚当和《创世记》中的男人一样将罪责推卸给了女人,而女人则怪罪于蛇。无论是《创世记》还是《失乐园》中,男女二人的回答说明一个事实:犯罪后的人类始祖毫无悔改之心和担当之举,由此导致男人与女人、人类与动物之关系的疏远与异化,违抗上帝至高命令“勿尝禁果”且不知悔改的人类始祖必然受到上帝严厉的惩罚。
两相比对,史诗第10卷中上帝对夏娃和亚当的惩罚与《创世记》第3章构成更为显著的互文关系。《创世记》中上帝对女人的惩罚意义重大,关涉人类的繁衍和女人的地位。史诗直接援引《创世记》经文:“我将把你的痛苦在怀孕时/大大增加。你要在痛苦中生小孩,/你还得服从你丈夫的意志,/他必将君临于你,管制你。”(PL X.193-96)可见弥尔顿完全认同基督教文化对女人的角色定位。首先,女人必须诞育后代,忍受怀胎生子的痛苦。这既暗含了人类因犯罪而被逐出伊甸乐园的必然性,也是对《创世记》第1章中上帝要人类“生养众多”这一赐福的合理解释;其次,女人必须服从男人的管制,只能做男人的“帮手”,这是对《创世记》第2章中上帝所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2:18)的逻辑延伸。史诗对《创世记》经文的直接引用体现了弥尔顿对《圣经》中男尊女卑观念的认同和传承。正因为认可《圣经》中女人先于男人堕落且该受制于男人的观点,弥尔顿被女权主义批评家吉尔伯特等人视为“所谓‘父权诗歌’厌恨女人的核心”。[11]
为了深刻诠释《圣经》中罪与罚的主题,弥尔顿采用几乎同样的措辞记述上帝对亚当的惩罚:“连土地也因为你而受到诅咒/……你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最后回归土地,因你原本出自泥土,/你既生自尘土,将来也归回尘土。”(PL X.201-08)较之夏娃,上帝对亚当的惩罚是致命的,直接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命运。首先,对土地的诅咒究其实质是对人类的惩罚,人必须辛勤劳作才得为生。更为重要的是,死亡进入人的世界。诗文对“尘土”一词的重复使用表明,上帝最初用泥土捏成的人最终要归于泥土,人成为必朽。
综上所述,弥尔顿采用引用和转述的方式使史诗中的上帝和人类始祖与《创世记》发生身份认同,在两部经典之间建立起密切的互文性关联。通过互文,《失乐园》第10卷完好无损地传承了《创世记》第3章的宗教文本内涵。
但必须指出的是,诠释罪与罚主题时,诗人弥尔顿的想象力再次跃出《创世记》之外,对亚当夏娃对待惩罚的认识和态度做了详细的描述,填补了《圣经》作者留下的众多叙事空白。例如弥尔顿对亚当犯罪后求死不得的内心独白做了长达117行诗文的想象性描写:从对上帝的抱怨到自责,再到对死亡的渴求,其中“为什么不给我快死,给我/所渴望的一击,结果了我呢?”(PL X.854-56)言辞绝望悲愤,与《旧约·约伯记》第3章中约伯的言辞如出一辙。相反,被亚当怒斥为“蛇”和“祸水”的夏娃却谦卑地俯伏在亚当脚前祈求宽恕,愿意承担所有的罪名。亚当被夏娃对待罪与罚的果敢态度折服,转而希望上帝“将全部罪罚落在自己头上”。于是始祖二人重归于好,用“相互怜爱”取代“相互责备”。更为重要的是,弥尔顿笔下的亚当最终认识到靠劳动养活自己的价值。“劳苦过日子”和“汗流满面”虽然是一种惩罚,但在史诗中的亚当看来,“其他动物都整日游荡,/……/人却每天有体力或脑力的工作,/这就宣布了人的尊严。”(PL IV.616-19)可见犯罪后的亚当经历了绝望→责备→宽恕→觉醒的心路历程,最终从有如“被豢养的宠物”成长为真正的有“尊严”的人,这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但这进步“必须依靠知识和劳动”。⑧弥尔顿基于互文的文学想象赋予《圣经》中罪与罚主题以新的文化内涵:和伊甸园里无忧无虑的生活相比,伊甸园外靠知识和劳动“养活”自己对于人类更具价值和意义。
如《创世记》第3章所示,被上帝“赶出”伊甸乐园的亚当夏娃默默地步入尘世,开始艰辛的人生旅途。与此不同,史诗第10和12卷对始祖二人因犯罪被迫离开伊甸园之情形的描写则略显凄美,犹如一曲挽歌:他们恭恭敬敬地俯伏在神座面前,“一同忏悔,祈求宽恕,泪洒/大地,叹息声充满空中”。(PL X.1099-1101)但他们很快拭干眼泪,“手携手,慢移流浪的脚步,/告别伊甸,踏上他们孤寂的路途”。(PL XII.668-69)诗人对人类始祖“手携手”但却感“孤寂”这两相悖论的描写呼应了史诗的标题“失乐园”,同时也将读者从时间的终点拉回到起点,让人再次回望始祖二人最初被安置在《圣经》伊甸园的情景。被赋予浓厚宗教色彩和人文关怀的史诗结局足以彰显弥尔顿本人对人类前途及其未来命运的深切关怀。
综观之,就对互文本的直接引用和转述而论,史诗第10卷几乎是《创世记》第3章的翻版。《失乐园》如此大量引用和转述《创世记》内容,与诗人对《圣经》的喜爱程度有密切关联。弥尔顿一生研读《圣经》,创作《失乐园》时虽已双目失明,但每天请人给他朗读《旧约》,史诗中有如此“众多的《圣经》引语和对《圣经》的释义”也就不足为奇了。[13]然而,弥尔顿并非简单地抄袭《创世记》文本,而是以其中简短的罪与罚故事为互文材料,用史诗的形式和诗化的语言将其谱写成“新的基督教悲剧”[14],其间对人性的刻画和对人类始祖对待惩罚的态度和认识的诗性描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圣经》中罪与罚的主题。
乔纳森·卡勒在《符号的追寻》中指出,互文性是指“一部作品在一种文化的话语空间中的参与”,能“唤起我们注意先前文本的重要性”。[15]《失乐园》通过引用、转述和拼接等互文策略成功参与基督教文化话语空间,引领读者回归《圣经》这一西方文化源头经典。史诗第7、9、10卷在描写上帝创世造人情节、人类堕落题材和罪与罚主题方面与《创世记》第1-3章之间的互文指涉如此显性和密集,致使“历代读者混淆了弥尔顿的叙事与《圣经》本身的叙事”。[16]尽管史诗大量且大胆援引《创世记》文本,但诗人弥尔顿凭借其非凡的文学想象力对《圣经》进行了最为成功的改写,因此,《失乐园》“仍然是一部最具原创性的诗歌”。[17]如上所析,通过经典互文,《失乐园》传承了《圣经》原有的宗教文本内涵;通过文学想象,诗人赋予史诗独特的宗教审美意蕴。经典互文与文学想象共同成就了《失乐园》永恒的经典地位。可以说,弥尔顿最终完成了书写一部类似于但丁之《神曲》或继《旧约》和《新约》之后“第三约”(a third Testament)⑨的夙愿,并因此深刻地影响了后世文人对《圣经·创世记》中人类堕落故事的想象与书写。
注释:
① 关于《失乐园》与《圣经》多层面的互文指涉,从著名圣经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的《失乐园》汉译本可见一斑。朱译《失乐园》共做注释666个,其中50%与《圣经》相关。据统计,《失乐园》引用《圣经·旧约》930处,《圣经·新约》490处。
② 根据西方学者对互文性理论的阐释和相关文学作品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引用、转述和拼接是文学创作中最常用的互文策略,其他互文方式包括模仿、套用、戏拟、重写、改编等。
③ 文中所引《圣经》汉译引文均出自《圣经》“启导本”(香港:海天书楼,1996年),后文出自《圣经》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注章节数,不再一一做注。
④ 文中所引《失乐园》诗文均出自弥尔顿《失乐园》,朱维之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后文出自《失乐园》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明卷码及行码,文中卷码及行码按英文原著注出。
⑤ 关于《创世记》第1-2章为何记载两个不同的创世造人故事,学界一直存在争议,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达成一致意见,出现“四底本”说,即亚卫本(J本)、埃洛兴本(E本)、申命记本(D本)和祭司本(P本)。此说认为,前者出自祭司本,后者出自亚卫本。上帝用尘土造亚当的故事虽被安置在《创世记》第2章,但学界普遍认为其形成时间早于前者。据考,两个创世神话均非古代希伯来人独创,而是受到巴比伦创世神话的影响。
⑥ 关于禁果具体指什么,《创世记》作者没有明示,但后人大多推测是苹果。在古代希伯来文化中,苹果是催情果,隐喻爱情,《旧约·雅歌》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失乐园》中的禁果指苹果(PL X.487),取《雅歌》中苹果的隐喻之意。对此,弥尔顿对二人尝食禁果后顿生爱恋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述(PL IX.1008-45)。
⑦ 1640年弥尔顿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时就曾酝酿过与圣经题材相关的悲剧。《失乐园》的前身曾以“亚当与蛇”“被逐出乐园的亚当”和“夏娃”为题,均以堕落为题材,《失乐园》最初是关于堕落的五幕剧。See William Poole, Milton and the Idea of the Fall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130.
⑧ 参见朱维之:《失乐园》“译本序”,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 年,第8页。
⑨ 据布鲁姆《西方经典》,弥尔顿希望能和但丁一样创作一部神曲,或是继《旧约》和《新约》之后的“ 第三约”(a third Testament)。See Harlot Bloom,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171.
[1] Bloom, Harlot.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3.
[2] Guiborry, Achsah. The Bible, religion, and spirituality in paradise lost [C]// Angelica Duran. A Concise Companion to John Milt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7: 128−129.
[3] Sarna, Nahum M. Understanding Genesis: The Heritage of Biblical Israel [M]. New York: Schocken, 1970: 10.
[4] Lewalski, Barbara Kiefer. The Life of John Milton: A Critical Biography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3: 461.
[5] 肖明翰.《失乐园》中的自由意志与人的堕落和再生[J]. 外国文学评论, 1999(3): 69−76.
[6] Frye, Northrop.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82: 124.
[7] 马克·帕蒂森. 弥尔顿传略[M]. 金发燊, 颜俊华, 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1.
[8] Ryken, Leland. Words of Delight: A Literary Introduction to the Bible [M].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Company, 1987: 98.
[9] John S. Diekhoff. Milton’s Paradise Lost: A Commentary on the Argument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58: 49.
[10] Masson, David. The Critical Response to John Milton’s Paradise Lost [M]. London: Greenwood Press, 1997: 183.
[11] Gilbert, Sandra M. & Gubar, Susan.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M]. New Haven: Yale UP, 1984: 188.
[12] Potter, Lois. A Preface to Milton [M]. Beijing: Peking UP, 2005: 73.
[13] Lewalski, Barbara Kiefer. The Genres of Paradise Lost [C]// Dennis Danielso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ilt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121.
[14] Culler, Jonathan. The Pursuit of Signs: Semiotics, Literature, Deconstruction [M]. Cornell UP, 1991: 103.
[15] Corns, Thomas N. A Companion to Milton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2003: 44.
[16] 沈弘. 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Classics’ intertextuality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Milton’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Genesis of the Bible in Paradise Lost
LI Yanb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Milton’s inheritance and transcendence of Genesis of the Bible in Paradise Lost is revealed in the classics’intertextuality and his literary imagination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classics’ intertextuality, Books 7, 9 and 10 in Paradise Lost share the most evident and concentrated intertextual referentiality concerning plot, subject and theme to Chapters 1-3 in Genesis, which is primarily realized by his audacious quoting directly or indirectly of the relevant texts from Genesis. As far as literary imagination is concerned, Milton’s personified and specified depiction of the living creatures created by God enriches the plots of God’s creation of the universe and mankind in Genesis. The meticulous characterization of human ancestors’ inner activities before and after eating the Forbidden Fruit and the artistic presentation of the Fall’s harm on Nature expands the subject of the Fall. And the poetic portrayal of human ancestors’attitude to and understanding of God’s punishment deepens the theme of Sin and Punishment. Through classics’intertextuality, Paradise Lost inherits the original religious connotations of the texts in the Bible, while through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the epic is endowed with unique religious aesthetic implication. Both the Classics’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literary imagination make Paradise Lost an everlasting classic.
John Milton; Paradise Lost; Genesis; classics; intertextual referentiality; literary imagination
I059.9
A
1672-3104(2015)01−0184−06
[编辑: 胡兴华]
2014−09−28;
2014−12−01
李滟波(1964−),女,湖南常德人,文学博士,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圣经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