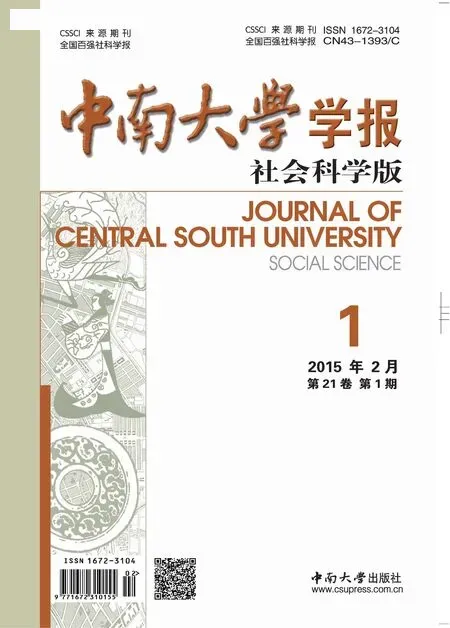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
——以湘社为例
郑学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
——以湘社为例
郑学
(南开大学文学院,天津,300071)
以易顺鼎、程颂万为代表的湘社作家群,集中体现了乡邦世族在晚清诗学传承中的作用。世传家学是诗学传承的重要途径,并造就家族文学的思想底色;对本家族文学造诣的自豪感维系了传习文学技巧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家庭独特的文化氛围,还会浸染进作家的创作个性。家族在文化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掌握传播领域话语权,并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批评。女性文学的传承附庸于家族文学。
家族文学;晚清湖南;诗学传承;湘社
家族当然是以血脉和财产关系相维系的生活共同体,但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它还承担着文化传承的职能。作家要成长起来,并且建立文学声誉,必然需要一定的外部条件,例如可供汲取营养的文化资源,又如沟通文本与接受者的传播媒介。对作家来说,如果能够借助家族在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在传播领域掌握话语权,并且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评价,显然是非常有利的。此外,对女作家而言,出身于一个文化家庭就更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检视那些别具特色的女性诗歌,不难发现其基本的传承之道,就是附庸于家族文学,因为在当时女学不兴的社会环境下,如果没有家庭的培养和翼护,女性文学几乎不可能拥有生存之地。
湘社雅集的十二位作家及其亲友都是很好的例证。这是一个乡缘色彩浓厚的文学团体。光绪十七年(1891)二月至四月,龙阳易顺鼎、易顺豫兄弟,宁乡程颂万、程颂芳堂兄弟和道州何维棣,宁乡周家濂,江夏郑襄,善化姚肇椿,长沙袁绪钦,保山吴式钊,益阳王景峩、王景崧兄弟,在长沙周氏蜕园结集酬唱。两个月间,诸人文酒欢会,往来频繁。社团解散后,易顺鼎、程颂万同编《湘社集》,辑录湘社文学作品,并作为程氏《十发庵丛书》中的一种刊刻出版。
稍作关注就会发现,家族性创作是这个文学群体最基本的特征。湘社作家群里,有易、程、王三对(堂)兄弟,何维棣则与著名诗人何维朴是兄弟……不仅如此,易、程、王、何、郑几家都是父子有集、祖孙能诗,甚至一家四五代人作家辈出,彬彬不绝。
在最直观的层次上,即可感受到文学与血缘的纠葛:《湘社集》中凡属易顺鼎发起的唱和,乃弟易顺豫往往首先庚和,甚至有些唱和只有兄弟二人参加;程氏兄弟情况也与之相近。深究其底里,家族性特征是与湖湘地域性特征相融,而后综合作用于文学创作。兹就其大者,分述于下。
一、文献与师资:网状人际、学统结构的意义
“宗族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乃是士绅生活的一大特征。”[1](41)湖湘宗族凭藉联姻等手段,构建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人际网络。学术资源和学统脉络都依靠这个网络发挥作用。治学与为文两方面不可分割,凡学养不同,则“嗜趣自异,假使创作文学也便不能一样”。[2](23−24)反之,学养相近,其文学创作也会表现出一定相通性。换言之,世家出身的作家会因家学而被赋予一定的思想背景。
湘社内部不乏世家间的姻娅联系,如程、易两家“姻笃逾三世”[3](1439),易顺鼎次女仲瑾就嫁与程颂万四子君谋(著名演员程之之父,京剧名票)。一个典型的个案可以说明姻娅关系的文化意义:王闿运高足,杨度、杨淑姬之弟杨钧是道州何氏的姻亲,与何维棣同辈,而周家濂一家与杨钧也有交情。杨钧《草堂之灵》“记唐碑”条谈到:“宁乡周氏以蝯叟(何绍基)藏小字《麻姑仙坛记》三种,质于余斋。”[4](204)这样,文化资源在几个家庭中互相流转。按照杨钧的记载,类似事件频频发生。通过网状的人际关系,湖南世族之间建立起一个互相取资、交流频繁的体系。凭藉这一体系,这些文化家族的成员就有条件充分利用整个文化圈子中的图书资料、法书碑帖等等来扩大视野,增进学识。
网状人际关系中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世代之间的交叉性人际活动。例如,易顺鼎与郑襄曾在湘社中唱和,又曾与郑襄之子郑叔献同游,互赠诗篇。甚至《郑叔献遗集》中还有《叠韵呈函楼先生》这样投赠易顺鼎之父易佩绅的作品。很显然,郑叔献这样的子侄辈是因父兄的关系而得以结识、接近文学前辈。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写给诸弟的信也可作为一例。他在信中写道:“何子敬近来待我甚好,常彼此作诗唱和。盖因其兄钦佩我诗,且谈字最相合。”[5](400)
人际网络中的前辈会热情地为“通家世好”的后辈标榜称誉,以助其延取声誉。典型代表如易顺鼎《程十七郎歌为穆庵作》,旗帜鲜明地赞颂程颂万的侄子程康:“吾友十发犹子康,美哉程氏十七郎。性情风义文章媵,竟与先哲争芬芳。”[3](1360)程康的“性情”“风义”与“文章”固有可称,但易顺鼎作诗比之“先哲”的首要原因,还是在“吾友十发犹子”的一面。
后辈文人在与长辈的唱和往还中受到提携,既受到长辈的褒奖揄扬、依附前辈而建立起名望,又通过与长辈论诗切实提高了诗艺。每次同题、同韵唱和,前辈的作品都像是提供给后辈揣摩借鉴的范本。所以,人际网就是一个师资库,当一个家庭通过姻娅戚里年谊等等关系并入了这张网络,该家族的子弟就得到了接受诸多“乡前辈”指导的机会。湘军老将、当时湖湘地区的文化名宿吴大澂对此深有感触:“为己择交,即为子弟择师。父兄无良友,子弟从何而取法?”[7](187)一语足证人际网络对新一代士人成长的重要性。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曰:“文非一趣,道有多门。其间如天资之禀赋、学术之陶镕、师友之熏习、时境之影响,亦有较然相异者。”[8](4)刘氏所列举影响文学风格的四个要素中,天资、时境暂不讨论,则除开学术陶镕之外,“师友之熏习”也是重要一环。
晚清湖南,恰有一位前辈大师经常扮演这一“父兄之友、子弟之师”的角色,他就是是王闿运。这位湘绮老人与湘社作家的父辈易佩绅、程霖寿等人交谊深厚,从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可以看出一二,如云:“同治之末,龙阳易佩绅者,易顺鼎之父也,以郭嵩焘之介谒闿运,谈学论政极欢。”[9](65−66)
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论王闿运:“刘诒慎《读湘绮楼诗集》云:‘白首支离将相中,酒杯袖手看成功。草堂花木存孤喻,芒屐山川送老穷。拟古稍嫌多气力,一时从学在牢笼。苍茫自写平生意,唐宋沟分未敢同。’褒贬差得其平。”[10](142)引文中“一时从学在牢笼”一句点出一件事实:王闿运半生致力于教育,传授诗学,金针度人,诲人不倦。青年一代湖湘作家基本都曾向他学习,从王氏诗学中得到滋养。他的霑溉,泽及几代学人。湘社作家一般尊他为师,晚湘社作家半辈的郑襄之子郑叔献,同样称王氏为“湘绮师”。对于这些湖湘作家,王闿运就像一座高山矗立在面前,无论向哪个方向去,都要在他脚下走过。《草堂之灵·记夸》记载曾广均说过:“中兴以来,诗家皆以湘绮为宗,余亦不能出其范围者也。非人人学王,以其才大,不许他人自立,而诗有习矣。”[4](32)像易顺鼎这样的一流诗人,不甘于傍人门户,难免故意追求与王闿运不同的风格,但即便如此,得自王闿运的成分也不可能完全掩盖。
类似的前辈师长还有郭嵩焘、郭崑焘、王先谦、熊鹤村等。易顺鼎的首部诗集曾呈请郭嵩焘评点指正,刊本保留了部分评语。如《客行》诗“日暮鸡犬聚”句下自注:“筠仙丈评云‘五字似齐梁人语’。”[3](10)又如《四鼓发顺德,月中行三十里作》注云:“此十字,筠丈皆加圈。”[3](15)等等。可见青年时代的易顺鼎颇以此为荣,并借以自高声价。像熊鹤村这样的人物,早年曾亲炙龚自珍、魏源诸家,晚年又经常与湘社作家为代表的新生一辈往还,在湖湘文化传承中扮演承上启下的纽带。龚魏佚事旧闻往往藉之而传,如瞿兑之《杶庐所闻录》记龚自珍“名士气”[11](7),即引叶德辉转述熊氏语。湘社作家中,年龄最长的郑襄受熊鹤村提携最多,事见郑襄《久芬室诗集》。
湘社这样的社团和雅集,网罗集中了大量的活跃文人,是最大规模的人际交流形式。从另一角度看来,士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也十分依赖于这样一个平台。所以类似雅集活动颇受欢迎和重视。湘社雅集并不是依靠文学主张的号召而形成,而是在互相熟识的小圈子内构建。比如袁绪钦、易顺鼎、易顺豫三人自幼相熟。袁绪钦《蜕园饮集,赠易五易六》描绘说:“我年十九君(指顺鼎)十七,叔由最小初垂髫。”[12](23)与社者通过在雅集内部的频繁交流、密切影响,逐渐形成比较一致的文风。也就是说,先有社团,再有流派。
以世学相授受,以雅集相召集,在明清两代相当普遍。胡朴安《中国文社的性质》区分中国文社为“治世(盛世)的文社、乱世(衰世)的文社、亡国遗民的文社”[13]。光绪前中期,社会比较稳定,若有“中兴”气象,文人处在比较宽松裕如的风气里,忭舞盛世、歌咏流连。自嘉庆结束结盟立社之禁以后,江南地区的世家大族呼朋携侣地在园林中宴集酬唱,早已蔚然成风。因此,就湘社唱和而论,这是它传统性的一面;就湖湘文化而言,这则是努力向文化中心——江南靠拢的表现。但是,湘社群体还有自己独特的一面:它在原有的顶尖文化家族之外,吸收了湘军子弟进来。湖南军功绅士集团庞大,这一阶层以湘军为维系,组成政治集团,并将影响力扩展到文化领域。蜕园主人周家便是典型一例:周家濂的父亲周达武出身武官,但精于史学,有名著《武军纪略》,记载作者参与的种种战事,包括与少数民族的交战。该书自比“赵瓯北《皇朝武功纪盛》、魏默深《圣武纪》、王壬父《湘军志》”[14](1),深具学术自信。周家濂研究《通鉴》成就斐然,当由乃父启发。郭嵩焘《周渭臣赠裘》描绘周达武,说“将军书法兼颜柳,诗笔长河汇百川”[15](786),高度评价了周达武的文事。《大中华》1916年第2期《文苑》栏目发表了蔡燕生一篇《寄周渭臣尚书乞马》诗,似乎周氏还扮演过文坛资助者的角色。又因为湘军创办时以士人为将领,文化家族和军功绅士间并无绝对界限——易佩绅曾追随骆秉章与石达开部交战,程霖寿曾入胡林翼幕府。
二、榜样与交流:诗词文创作经验的直接传承
父兄会将创作经验传授给子弟,子弟也会将父兄作为模拟的对象。因此,同家族的几代作家间,不难发现创作经验、创作理论的直接继承关系。要特别强调的是,湘社作家对本家族前辈的文学造诣往往怀有深深的自豪感,故而自觉地传承创作经验。程颂万的堂兄程颂藩写信教诲他:“二伯父(指程颂万之父程霖寿)虽不多作诗古文,然一动手则不懈,而及于古,非我辈心思笔力所能及。望弟时引庭训相告。兄常欲弟奉教于老父,实胜外人纷纷之谈。……兄早年有以词掩意之病,实由二伯父时时谆谆戒之,始痛改也。”[16](491)正是这种自豪感,维系了文学技巧传习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
父兄子弟间的传承关系在湘社最活跃、最杰出的诗人易顺鼎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甚至只要略一翻检,就能在诗文集的标题中发现某种继承关系。易顺鼎的诗集取名《琴志楼诗集》,而其父易佩绅室名琴心楼[17];其弟易顺豫有《琴思楼词》;1939年,重庆诚达印书馆又铅印了其子易君左的《琴意楼丛书》。其他湘社作家也有类似的父子相承情况,比如社友王景峩、王景崧的父亲王德基曾与王闿运、皮锡瑞同学,著作等身,世称“玉屏先生”,父子三人一样擅长古体诗和骈文[18];社友何维棣与祖父何绍基同宗宋诗,等等。
词为专门之学,较诗更依赖父子家学的传承。因此,早在宋代,就是“一门能词者亦众”。[19](676−678)据唐圭璋《词学论丛》统计,今传宋代父子词人22家,兄弟词人21家。易氏兄弟在词学方面也颇受乃父影响,影响途径为互相唱和,如易顺豫光绪十三年(1887)初夏作《凤凰台上忆吹箫·丁亥初夏,和大人遣怀之作,即次原韵》。同样的,湘社社友中程颂万兄弟以词知名,也得益于家学。九江吕传元编钞过一种《三程词钞》,系程颂万与其父程霖寿、兄程颂芬词作的合集。
在词学传承方面,湘社作家群取法桑梓先辈、父子兄弟一门能词这两个特点,恰是典型的清代模式——严迪昌《清词史·绪论》曾提示读者“提起注意”,“清代词派和群体非常突出地具有地域性和家族血缘关系的特点”。[20](7)类似的团体,自云间以降,历有清一代而不磨,直至清末的大规模复苏。
家学传承给作家带来的还有家族特色的题材喜好与创作个性。最典型的代表为易顺鼎。易顺鼎自称明正德年间才子张灵后身,照其《题张梦晋画折枝长卷,寄宗室伯义祭酒》诗前长序的说法,黄九烟为张灵转世后身,易顺鼎又是黄九烟转世后身。他们几人以及晋代贤才王昙首,都是擅长吹笙的仙人王子晋转生托世。关于他的“五个前生”,各种传记材料中都有涉及,王森然在《中国公报》连载的《易顺鼎先生传》记载尤其详尽。[3](1456)
后来易顺鼎还为此刻了一块图章。王森然《评传》说:“哭庵晚年书札中常钤一朱文大印,文曰:‘五岁神童,六生慧业,四魂诗集,十顶游踪。’”此事亦为友朋所津津乐道,《湘社集》中,程颂万的组诗《题中实所藏张梦晋〈岁寒三友〉卷子八首》前有小序:“ 中实自记为张梦晋后身,同人多传其事。”[12](31−32)此外其他湘中友人如王先谦有《实甫自言前生为张梦晋,其友藏张船山书画册中有张灵后身小印,以归实甫,携之至台湾索题》组诗四首[21](586)、寄禅有《题哭庵观察所藏张梦晋画轴》组诗三首等。[17](178)
意味深长的是,这种畸人放诞之行居然还有家族渊源。始作俑者为其父易佩绅。王先谦《林寺饯送易佩绅笏山归龙阳,次前韵》首联“再世支公合爱鹰,朅来香积快同登”句自注:“君自言支遁后身。”[21](593)寄禅和尚《寿壶天遁叟》“久惜支公堕,何堪更转轮”自注介绍更为详细:“叟自云前身为支道林。叟有‘来生愿作转轮王’之愿,故云。”[17](153)同年寄禅先有《赠哭庵观察》之二曰:“三生圆慧业,莲萼共标名。”[17](152)影指易顺鼎自言“张梦晋”后身之事。当时易氏父子正同在庐山扶乩,同“乩仙”唱和,大说其鬼话——这种情形,在今人想来是十分吊诡的。
易氏父子扶乩所请大抵为白玉蟾、吕岩一流道家仙人。《郑孝廉遗集》《感事四首,和白、吕二仙》题下自注:“时在实甫丈处扶鸾。”[22](7)一家人捣鬼弄怪,颇乐此不疲。易顺鼎寡姐也参与进来,自称“谢道韫后身”。郑襄挽易顺鼎亡母云:“夫前身道林,女前身道韫,儿前身王子晋,一门神仙眷属,升天成佛总团圆。”[23](33)戴展成亦云:“儿仙才女亦仙才。”[23](13)指的都是此事。易佩绅尤其热衷于此,汲汲倡导。易顺鼎乩诗集《倚霞宫笔録》记载,其母“生平尤不喜道仙佛怪迂之迹,以姊孀居奉佛,父始为言佛理”。[24](1)盖佩绅侫佛,曾欲弃官出家,又好治《老子》,其《老子解自序》曰:“老子孔子一道也。”实际上是要援老入孔,用老子的通脱态度来处理传统上以儒学思想来处理的社会生活问题。总之,一家人有此奇行,难怪能留下诸多奇诡瑰丽之诗。
三、传播与接受:世家声誉、地位的优势
易顺鼎与程颂万都是少年才子,他们刊出首部诗集时,都仅有十六岁:一则天分高明,再则得益于家庭良好的声誉与地位。
总结这些家族的情况,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特点:这些家族都有一个政治地位较高的“始祖”,从这个始祖开始进入人们的文化视野,而晚辈事功虽然不及父祖,却在文学方面成名较早,颇有发展。可以确信,存在一个这样的模式——长辈仕宦较显达,而晚辈往往文学较优长。之所以这些家族在文学上“有跨灶之兴”,原因不外清朝人所总结:“父兄之衣钵,乡里之标榜,事甫半而功必倍,实未至而名先归。”[25](164)相反,杨钧《草堂之灵·哭陈》记载过一个事件:沈醉白(沈瀚,字咏荪,号醉白山人)与何维棣胞兄,出身名门道州何氏的何维朴书画水平“不过伯仲”,甚至沈氏比何维朴更“能出新”。但是沈“郁居湖南,其名不显”,而何维朴则“名满天下”。杨钧的结论是:“门第不及,亦不遇之因。”[4](33)
父辈的显达,首先为这个家族在文学上的发展准备了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还是他们为家族取得了社会地位、文化身份。对于作家来说,非此不足以进入批评家的视野。柳亚子在《胡寄尘诗序》中愤怒地描绘:“就而视之,外吏则道府,京秩则部曹,多材多艺,炳炳麟麟;而韦布之士,独阒然无闻焉。呜呼!此与职官表、缙绅录何异,而诗话云乎哉?”[26](455)基于这样的批评环境,“名父之子”显然更容易跻身作者之林。要言之,亲世代的科第、名位可以为子世代提供更高的起点,至少在子世代立足文坛之初,这非常关键。
家族的文化地位一经奠定,又会很快促使“学而优则仕”的家族传统形成。然后,每一个家族成员都能从家族地位中获益,同时,每一个家族成员也都承担起维护家族声望的责任。据传,何维棣之祖何绍基青年时随父入京,半途中其父发现他学问空疏,居然怒而“笞掌二十,推之上岸,曰‘不可使京中人知我有此子,以为吾羞’”[4](32)。无独有偶,《草堂之灵·记何》一节曾借王闿运之口指出:“何蝯叟(何绍基)待后辈极严,尤恶吃烟。”[4](21)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三十二咏何绍基、绍业兄弟曰:“大郎尤贵二郎清。”[27](112)从何绍基、绍业这两个名字可以看出何氏对绍传家业的重视,的确,既“贵”且“清”,兄弟二人诠释了这些湖湘世族的立身之道。
另外,作家的家族地位并不一定绝对地表现于行政领域。科名是敲门砖和过墙梯,一个家族通过它取得相应资格之后,会将影响力向上层建筑的各个层面渗透,其中最显赫的家族将牢牢掌控文教层面的权力。比如湘社作家与书院的关系应当受到格外重视。作为湖湘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深入地联系着两湖各重要书院。在湘社立社期间,除了何维棣等年辈稍长者外,大部分社友尚为书院生徒,正在接受书院文化塑造;而他们的父兄辈则占据教谕、训导、山长位置。若干年后,这些职位被移交给资历渐深的湘社作家们,文化影响力就开始通过书院向下一代湖湘士人辐射。若干联系紧密的书院还共同构成一个文化圈子。在易顺鼎、顺豫兄弟之母逝世开吊时,竟有来自九所书院的十四位山长赴吊,几可谓“门上往来半山长”。如表1所示,这些山长所掌教的书院或为两湖教育重镇,或为张之洞之前在广东巡抚任上兴办。
从这十四个高垂史册的姓名可以想见,在晚清文化界,那是一股何其重要的力量。这种影响力甚至绵延至现代:程颂万家族自程霖寿传至程君硕、程康,再到南京大学的著名教授程千帆;何维棣家族从何凌汉、何绍基父子到何维朴,相沿几代学人都比较知名。部分获益于家庭带来的学术地位,程、何二人都成为近代重要的学者和教育家。程颂万1897年在湖北创办中西通艺学堂,后来又历任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之一)总稽察、提调,岳麓高等学堂监督。何维棣1896年受四川总督鹿传霖委任创办四川中西学堂,该校是西南地区最早的近代高等学校,后来发展为四川大学,今天的川大追奉他为首任校长。

表1 《易母挽词》所载赴唁书院山长统计名单表
四、一门风雅:女性作家涌现的可能
湘社作家的家庭中,多有才女涌现。易顺鼎、顺豫之姐易莹有《湘真馆集》;其五妹易瑜曾执教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南京复正女学堂、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民益女子职业学校,在教育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并著有《湘影楼诗》百首和小说《髫龄梦影》《西园忆语》。易顺鼎二女孟美、仲瑾,程颂万二妹程琼、程珏也有才名。才女在这些家庭中集中地出现,其创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名声播于人口。吴虞《重印曾季硕〈桐凤集〉序》把她们视为湘女多才的典型:“王壬秋先生之女师芳、易笏山之女瑜,俱擅才艺。”[28]
这绝非偶然。一代才女冼玉清讨论女性作家的成长,指出:“其一名父之子,少禀庭训,有父兄为之提倡,则成就自易;其二才士之妻,闺房唱和,有夫婿为之点缀,则声气相通;其三令子之母,侪辈所尊,有后嗣为之表扬,则流誉自广。”[29](2)与此同时,女性对其他家庭成员也起着同样的作用。她们与父兄、夫婿唱和,参与营造家庭的文化氛围;课子读书,指导下一代的文学创作。易顺鼎《庐山诗录自记》追忆,“余年始五岁,已从先君行万里路,从先妣受五七字诗。”[3](1482)母亲是他文学上的启蒙者。无独有偶,何维棣《先母事略》追忆,他的母亲李楣为著名诗人李星沅之女,著有《浣月楼诗集》,且对兄弟二人指导颇多:“维棣兄弟初解言语,即以立身行己为熏。既入塾,督之尤严……诸子得以稍稍知书,恭人之教也。”[30](60)
易顺鼎晚年为施淑仪女士《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作序时,曾阐发过他对女性家庭教育的看法:“昔吾孔子,采风十五国,选诗三百篇,以‘诗无邪’为旨归、‘乐不淫’为准则。家庭教育,尤注意于诸侯大夫;闾巷歌谣,多数者妇人女子。盖治莫先于门内,化必起于闺中。”[31](2)可见在易顺鼎看来,文化家族应该重视对妇女的教育,而妇女教育要特别重视诗歌。教化大事,由此着手。
湖南文化家族秉承这种观念,注意“家庭教育”,从“闺中”“门内”起步,营造文学氛围和文学传统,进而保持整个家庭的文学水准。易顺鼎、易瑜兄妹曾为亡母征辑过一部《易母挽词》,其中王景峩、王景崧兄弟赠送的挽联充分地描绘了这种家庭氛围:“女、妇、姪一门文学,待大家集出,合教海内尽师承;父、夫、子三世名人,惜太史书成,未伏阁中先受读。”[23](13)易顺鼎集中今存《游晋祠和仙姐真一子韵》《将返京师和仙姐真一子赠行韵》等易氏家庭内部唱和之作——女性创作反过来促进了男性作家的文学活动。从诗学承传角度着眼,其意义是不可小觑的。如果超出湘社的范围看,曾国藩家族的情况更为典型。孙海洋《湖南近代文学史》为此特设专章《湘乡曾氏闺秀诗人》。
五、结语
以上所论种种,属于当时湖南士林的普遍性现象,有典型性价值。湖湘大族往往能够世传其家学,见诸载籍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王闿运之子代功博闻强识,能背诵《史记》《汉书》,其父犹讥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32](65),事颇出名;曾国藩家族成员曾广均与湘社的两位主将易顺鼎、程颂万齐名,时称“湖南三诗人”,被视为一代湖南文士的代表,等等。
湘社活动及其人际结构反映着一代作家的成长与成熟。而代际演替问题,无论着眼于学术史还是知识分子史研究,都很值得关注。如果将王闿运、何绍基、易佩绅、郭嵩焘等人视为湖湘士人的第一个世代,湘社作家就属于第二个世代,而湘社作家的弟子门生则当属于第三世代。不妨为第三世代寻找一个例子:袁绪钦在长沙求实书院任教时培养的一位学生,后来很有名,他就是《猛回头》《警世钟》的作者、革命志士陈天华。袁绪钦对陈天华极其赏识,姜泣群《陈杨两志土投海史》记述,“绪钦尝语余:‘吾院有一生曰陈天华者,真人杰也。’”[33](14)三个世代间的嬗递关系非常明显,总体上可以简括为“接触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认同西方文明”的演进谱系。思想近代化的任务,大概要交付第三世代的新一辈“人杰”来彻底完成,而文学思想、题材、语言和体裁的变化,也在这一过程中与之俱进。
湖南是晚清文学重镇,湖湘文学是地域文化和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相磨砺的产物,是近代化风潮冲击下传统文学演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这个背景下直击今古之变的肯綮,探讨诗学传承问题,就是将目光投向飙风突变前夕,一片平静下孕育的胎息,倾听静夜里的微声。
此外,文中所论几个家族的子弟,如易氏之易君左、程氏之程千帆,在现当代文化界仍有巨大影响。因此本文所论,意义又不限于近代文学范围。
[1] 艾尔曼. 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今文学派研究[M]. 赵刚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2] 罗根泽. 我怎样研究文学史[C]// 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3] 王飚校点. 琴志楼诗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4] 杨钧. 草堂之灵[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5] 曾国藩. 曾文正公手书日记: 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M].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10.
[6] 吴大澂手批, 全国公共图书馆古籍文献编委会编著.吴大澂手批本《弟子箴言》: 卷六[M]. 北京: 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96.
[7] 刘永济. 十四朝文学要略[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8] 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9] 钱仲联. 近百年诗坛点将录[C]// 梦苕庵清代文学论集. 济南:齐鲁书社, 1983.
[10] 瞿兑之. 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
[11] 易顺鼎, 程颂万辑. 湘社集: 卷一[M]. 刻本. 长沙: 蜕园, 光绪十七年.
[12] 胡朴安. 中国文社的性质[J]. 越风半月刊, 1936(23/24): 7−8.
[13] 周达武. 武军纪略[M]. 刻本, 光绪十八年(1892).
[14] 郭嵩焘著, 杨坚点校. 郭嵩焘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15] 王勇, 唐俐. 湖南历代文化世家·四十家卷[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6] 寄禅. 梅季校注. 八指头陀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7: 187.
[17] 王德基. 玉屏集[C]//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 三十一册.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8] 唐圭璋. 词学论丛[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9] 严迪昌. 清词史[M].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1.
[20] 王先谦. 梅季校点. 王先谦诗文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8.
[21] 郑襄, 郑叔献. 久芬室诗集: 郑孝廉遗集[M]. 刻本, 石门, 光绪二十一年.
[22] 易顺鼎, 易瑜辑. 易母挽词[M]. 琴志楼丛书. 刻本, 京师, 光绪十年.
[23] 易顺鼎. 倚霞宫笔録[M]. 琴志楼丛书. 刻本, 京师, 光绪十年.
[24] 陈夔龙. 梦蕉亭杂记: 卷二[M].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25] 舒芜, 陈迩冬, 周绍良. 中国近代文论选[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6] 刘逸生注. 龚自珍己亥杂诗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7] 钱基博. 现代中国文学史[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56.
[28] 冼玉清. 广东女子艺文考[M]. 长沙: 商务印书馆, 1941.
[29] 何维棣. 潜颖文[M]. 刻本, 成都, 宣统二年(1910).
[30] 施淑仪. 清代闺阁诗人征略[M]. 影崇明女子师范讲习所1923年铅印本,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78.
[31] 杨钧. 草堂之灵[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5.
[32] 姜泣群. 陈杨两志土投海史[C]// 朝野新谈: 上海: 光华编辑社, 1914.
The role of the native fellows and the aristocracy in poetics inheritance: a case study of the Xiangshe Writer Group in late Qing Dynasty
ZHENG Xue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The Xiang-she Writer Group represented by Yi Shun-ding and Cheng Song-wan, had embodied a concentrated reflection of the role that the native fellows and the aristocracy played in poetics inheritance of late Qing Dynasty. Family learning, including learning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history, philosophy, and achievements, is an important way of promoting the poetic tradition and cultivating the ideological basis for family literature. The pride of one family’s literary achievements could maintain the enthusiasm to study literary techniques and the stability of literary style in the alternation of generations. Family’s unique cultural atmosphere would affect those writers’ personality. The influence of the family on the local and the writer circles could help a writer access cultural resources and obtain the discourse right in the communication field. It could also prompt their first readers to give positive and authoritative reviews on their works. Besides, the inheritance of female literature is attached to family literature.
family learning; Hunan province; late Qing Dynasty; poetics inheritance; the Xiang-she Writer Group
I207.22
A
1672-3104(2015)01−0217−06
[编辑: 胡兴华]
2014−10−08;
2014−12−01
郑学(1986−),男,河北秦皇岛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近代文学,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