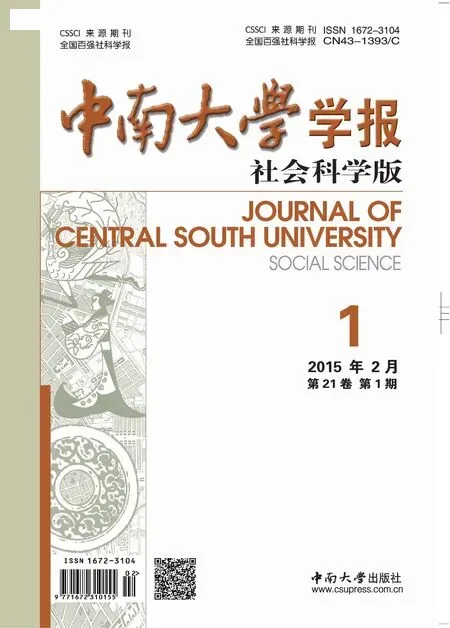交互记忆系统视角下成员经验与团队绩效关系研究
张谦,刘人境,刘林林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交互记忆系统视角下成员经验与团队绩效关系研究
张谦,刘人境,刘林林
(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对团队成员的不同类型经验及其分布与团队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团队成员通过交互记忆系统来吸收、转化已有经验,成员共享经验及其平均分布水平能够促进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与发展。而趋于平均分布的成员自身经验对交互记忆系统有阻碍作用。交互记忆系统水平与团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并受到团队信任的调节作用。
成员经验;交互记忆系统;团队信任;团队绩效
一、引言
在复杂快变的市场环境中,越来越多的企业依赖于不同类型的工作团队,以快速有效地获取、整合和创造知识资源,完成创新性强、灵活度高的各种工作任务。团队,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成员组成,通过彼此相互协作,追求共同价值目标的群体。[1]一个团队往往由来自不同领域、拥有不同专长的成员组成,在完成工作任务时,成员间需要彼此协作,进行充分的信息与知识分享,才可能取得好的绩效。然而,在实际生产活动中,由于团队成员在任务完成过程中缺乏有效的协作,无法充分利用完成任务所需要的相关知识,许多拥有相似的经验水平的团队,其绩效水平却相差甚远。[2]因此,虽然团队成员的经验和知识水平是判定其是否能够完成任务的基础条件,但是成员间如何在特定情境下通过沟通与协作,达到知识共享目的,决定了团队能力是否能够真正发挥。
作为团队成员之间形成的一种彼此依赖的, 用以编码、储存和提取不同领域知识的合作性分工系统,交互记忆系统(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理论对团队信息处理过程与知识协调机制做出了解释。[3,4]团队的交互记忆系统水平高,有利于成员间进行有效的信息分配,合理安排任务,提高协作水平,使团队能够高效地完成任务。团队成员通过交互记忆系统来吸收、转化已有经验,进而提高其绩效。因此,交互记忆系统能够有效解释成员经验如何影响团队绩效。本研究基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采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不同类型的经验对于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影响。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 交互记忆系统
交互记忆系统是一种关于学习、存储和交流知识的合作性分工系统,由团队中每个成员所拥有的知识的总和,以及对于他人的差异化专长的认识所构成[3]。现有研究中还存在着其他描述团队认知的概念,如团队心智模型(team mental models)、共享任务理解(shared-task understanding)等。虽然这些概念都关注团队成员间的认知表征,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是,交互记忆系统与这些概念存在显著的区别。首先,在认知的内容上。交互记忆系统仅包括关于谁知道什么的认知,而团队心智模型与共享任务理解还包括了成员对于团队目标、团队策略等内容的认知。其次,已往团队认知概念关注团队成员共享的知识,而交互记忆系统则强调团队成员间差异化的知识分布和信息处理特点,即不同的成员专注于学习、共享与传播各自擅长领域的知识,以实现个人与组织目标。[5]再次,交互记忆系统包含成员间进行信息编码、存储和检索的交互过程,有助于理解工作过程中团队成员互动时的差异性。因此,相比其他概念,交互记忆系统体现了分工与协作的思想,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团队成员进行知识共享、转移和创造行为。
根据交互记忆理论,可以将一个工作团队或组织视为通过相互交流进行编码、存储、检索、应用知识的交互记忆系统。[6]当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水平高时,成员间能够产生内隐的信息协调机制,提高团队整体的信息处理能力。[7,8]从团队行为视角看,交互记忆系统的运作机制包括目录更新、信息分配和检索协调三类行为。通过目录更新行为,团队中的成员能够准确知晓团队中其他成员擅长的知识领域,通过信息分配行为,成员间可以产生合理的分工机制,将不同类型的工作分配给最适合的成员,通过检索协调行为,成员向团队中擅长特定领域的专家进行学习,获得完成工作必要的知识,从而有效地共享、整合和利用团队中不同成员所具有的知识,提高团队绩效。[9]
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和种族特征对于交互记忆系统的专长认知有重要影响[10],团队成员专长异质性与交互记忆系统呈正相关关系。[11]由具有自信型性格的团队成员组成的团队更容易产生良好的交互记忆系统[12],人格异质性与交互记忆系统强度呈正相关关系。[13]此外,变革型领导对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专长、可信和协调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4]可见,现有研究主要从成员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人格特点、领导行为等角度对成员个人特点对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进行考查,而对于团队成员经验如何影响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进而影响团队绩效关注不足。
(二) 团队成员经验与交互记忆系统
本研究将团队成员经验分为两类,一是团队成员自身经验,即成员自身积累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这种经验是员工能够有效进行工作的基础。二是团队成员共享经验,指成员过往共有的工作经历。[15]此外,经验的分布结构,即相应的经验资源是集中在少数团队成员中,还是平均分布于每一个团队成员中也是交互记忆系统的重要影响因素。[16]因此,本研究还关注团队内成员自身经验与共享经验的分布结构情况。
团队成员自身经验水平对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有重要影响。首先,成员自身更多的工作经验会增加其在相关领域的知识积累,能够提高成员个人知识与团队任务所需知识间的相关性与准确性,有效加快团队的信息处理速度。[17]其次,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有利于团队成员正确评估自己和他人的专长,更踊跃地进行知识共享活动。[18]再次,团队成员个人拥有更多的工作经验时,成员间拥有相似工作经验的可能性更大,相似的工作经验有助于团队成员对于团队任务、客户需求、任务进展等情况达成一致的期望。[19]由经验产生的共同知识基础能够提升成员间的相互协作性,促进交互记忆系统的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1:团队成员自身经验水平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
团队成员共享经验的水平也会对交互记忆系统产生影响。团队成员间越熟悉,对于他人了解什么和不了解什么会有明确的认识,在完成任务时,就可以对其他成员的需求判断得更准确,熟悉的团队成员间能够有选择性地传递需要的信息,使得团队沟通更加有效、相关和清晰。在一起工作过的团队成员更有可能开发出一套共享的术语[20],这能够有效提高信息交换速度与信息理解能力,产生内隐的协调机制。随着一起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团队成员会明确地知晓谁拥有特定的工作专长[21],以及面对特定任务环境时,自己应该检索多少信息。此外,团队成员共享经验水平越高,会产生直接影响互相信任的共同信念。共享经验水平高的团队成员更愿意冒一定的风险来完成团队任务。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2:团队成员共享经验水平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
团队经验的分布结构也是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成员自身经验趋于平均,即团队成员的经验水平相当时,有可能削弱团队交流的有效性。在团队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需要明确的指示来进行协调与整合个人的知识。在协作过程中,人们更愿意接受工作经验更丰富的成员的指示[22],因此,当工作经验集中于较少的团队成员时,能够为团队提供更简单的工作指示,提高沟通的有效性。并且,广泛分布的自身经验还会削弱团队的协作性。成员经验不存在相互差异时,彼此可能会对团队运行过程和团队运行结果控制权进行直接争夺。[23]当参与团队影响力与控制权争夺的成员人数增多时,成员便不会相信团队交流是客观公正的,会影响对于他人专长的正确认知。因此,团队中成员自身经验分布越平均,由此带来的竞争性行为会削弱团队交流的协作性与有效性,破坏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3:团队内成员自身经验的分布对交互记忆系统有负向影响,自身经验分布越平均,会阻碍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团队共享经验水平能够促进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提高成员在团队中搜索知识的有效性、鼓励知识共享行为。[24]因此,当更多的团队成员间拥有共同工作经验时,成员的协作性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收益会更大。相反,当团队中只有少数几个成员间拥有共同工作经验时,相互熟悉的成员更愿意彼此交流,而不愿意与那些不熟悉的团队成员交流[25],从而降低了成员间信息共享与协作水平,影响团队绩效。因此,趋于平均分布的团队成员共享经验会提高团队信息交换水平[26],对于一个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价值。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4:团队内成员共享经验的分布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正向影响,共享经验分布越平均,会促进团队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
(三) 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
交互记忆系统的提出者Wegner认为,拥有良好运行的交互记忆系统的团队会更有效地完成其团队目标,并使团队成员感到满意。这个观点受到了随后进行的相关实验研究、实地研究和仿真研究的广泛支持。良好的团队交互记忆系统能够使得团队成员快速检索到团队内的现有知识,改善团队信息处理与整合能力。其他研究发现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工作质量、新产品开发成功、新产品推向市场的速度、团队决策质量、消费者服务质量等形式的团队绩效有正向关系。[27,28]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H5:团队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有正向影响。
(四) 团队信任对交互记忆系统和团队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团队信任,即团队成员间关于信任的共同观念,在交互记忆系统和团队绩效间起重要的调节作用。团队成员关于专长的认知,会受到成员间社会关系、尤其是成员间信任的影响。团队的信任水平高时,成员会愿意交换更私人的信息,这使得成员间能够更好识别他人专长,增加成员专长可信性,在完成任务时将任务信息分配给更擅长的成员。此外,团队信任能够促使团队成员对执行任务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与总结,从而提高交互记忆系统的作用。[29]由于团队信任是成员间通过工作交流产生的,团队信任能够降低成员间情感冲突的可能,提升成员间的协作水平。[30]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H6:团队信任在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之间起调节作用,团队信任水平越高,交互记忆系统对团队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本研究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概念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 样本及数据收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3年6~9月对西部某大型国有企业的问卷调查,调查对象为企业中的持续性工作团队。采用现场发放问卷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发放问卷523份,共120个团队。在对回收的问题进行编码、筛选后,最终得到有效的团队样本88个,共376份,团队层面有效回收率73.3%。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表明,男性占62.2%,女性占37.8%;员工年龄以35~45岁最多,占42.0%,其次是45岁以上,占41.2%;员工学历以本、专科为主,占91.7%;团队规模最少为3人,最多为8人,平均规模为4.27人。
(二) 变量测量
团队成员自身经验水平由成员在企业中的工龄、所在岗位工作时间以及技术职称三项进行测量,被调查员工在问卷的人口统计学部分进行填写。在收集数据后,先分别对题项进行标准化处理,再取均值得到每个员工的自身经验水平,最后将所得每位员工经验水平进行平均化处理,得到团队层面的成员自身经验得分。[31]
为了测量团队成员共享经验水平,在调研时,每团队成员会拿到其所在团队成员的列表,要求调研对象报告与其他每一位成员共同的工作经验,使用5点量表进行测度,包括:1一起工作小于1年;2一起工作1~3年;3一起工作3~5年;4一起工作5~10年;5一起工作超过10年。对团队成员的每一对关系进行平均后得到团队层面的成员共享经验得分。
本研究使用Blau系数计算团队成员自身经验的分布情况[32],计算公式为:其中ip表示员工i的自身经验得分占团队整体得分的比例。团队成员自身经验越平均,Blau系数越大,反之就越小。同样地,团队成员共享经验分布情况的计算方法与变量解释与自身经验分布相同。
交互记忆系统、团队信任、团队绩效的测量使用已有成熟量表。为了使其更符合中文的阅读习惯,在不改变问题原意的前提下,本研究在翻译时对问题的陈述方式进行了本土化处理。其中,交互记忆系统采用Lewis开发的量表[33],对专长性、可信性、协调性三个维度的交互记忆系统强度进行测量,专长性测量成员掌握差异化专业知识的程度,可信性测量成员信任并依赖他人知识的程度,协调性测量成员协调任务进程、有效利用分布知识的程度,共包括15个测量题项。团队信任的测量采用De Jong等的量表[29],包括5个测量题项。团队绩效的测量采用Jehn等的量表[22,34],包括4个测量题项。为了有效降低共同方法偏差(Common Method Bias)的影响,团队绩效水平的量表由团队主管领导进行填写。
已有研究表明,团队规模、性别异质性会对交互记忆系统及团队绩效产生影响,本研究选取团队规模、性别异质性作为控制变量。
(三) 数据分析与结果
1. 团队层面数据聚合检验
由于本研究假设模型的提出是基于团队层面,因此,需要将个体层面数据聚合至团队层面,并对数据聚合的一致性进行检验。当测量变量的内部一致性系数Rwg不小于0.7时,则该项目的一致性程度可以接受。[35]经计算得到各变量的Rwg值和Rwg≥0.7所占的比例为:交互记忆系统0.859,87.7%;团队信任:0.818,90.9%。组内一致性的判断标准要求测量变量满足ICC(1)大于0.12、ICC(2)大于0.60[36],经计算得到交互记忆系统的组内一致性系数ICC(1)、ICC(2)值分别为0.290,0.860;团队信任的ICC(1)、ICC(2)值分别为0.360,0.738,检验结果说明数据符合进行团队层面整合的判定标准。
2. 信度、效度分析
本文采用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变量的信度,采用累积解释量检验变量的效度。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均大于0.7,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累积解释量均大于5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效度,适合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1 信度和效度检验结果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理论模型涉及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系数
四、假设检验
本研究使用OLS模型对假设进行检验。在进行回归分析前,首先考察了数据的多重共线性以及残差分布情况,整体结果通过检验。多组回归模型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OLS回归结果
(一) 团队成员经验对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影响
为了检验假设H1—H4,以交互记忆系统为因变量,将成员自身经验、成员共享经验、自身经验分布与共享经验分布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方程(模型1)。回归结果显示:成员自身经验(P>0.05)对交互记忆系统没有显著影响,H1没有得到支持。
成员共享经验(β=0.454,P<0.01)对交互记忆系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2得到验证。在经验分布方面,自身经验分布(β=−0.329,P<0.01)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共享经验分布(β=0.273,P<0.01)对交互记忆系统有显著正向影响,H3、H4得到验证。
(二) 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的影响
在模型2中,以团队绩效为因变量,将交互记忆系统放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回归结果表明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565,p<0.01),H5得到验证。
(三) 团队信任的调节作用
使用调节回归分析对H6进行检验。先将团队信任作为自变量放入回归模型(模型3),再将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信任的乘积项放入回归模型(模型4),回归结果显示: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信任的乘积项系数显著(β=0.272,p<0.05)。说明团队信任在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图2显示了调节作用的模式。按照团队信任的中位数,将样本数据分为高团队信任、低团队信任两组,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回归并画图。从图2中可以看出,团队信任水平高时,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要强于低团队信任水平。因此,H6得到验证。

图2 团队信任对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基于88个持续工作团队数据,本文从交互记忆系统视角对团队经验与团队绩效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首先,团队中不同类型的成员经验及其分布结构对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不同。成员共享经验及其平均分布水平对交互记忆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有促进作用(H2, H4)。而趋于平均分布的成员自身经验会阻碍交互记忆系统的发展(H3)。成员自身经验水平对于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不显著(H1)。影响不显著的原因可能与本研究调研团队面临的任务类型有关,当团队面临不确定性高的任务时,成员自身经验对于完成任务帮助不大,一味使用已有知识会导致团队过程僵化,影响团队成员沟通的有效性和整体协作能力。反之,在执行程序性任务的团队中,完成任务所需知识技能明确,高水平的成员自身经验对交互记忆系统的正向影响会更加明显。
其次,团队信任在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在信任的氛围下,团队成员不但能够正确识别他人专长,合理分配信息,在对团队任务进行深入交流与反思时,也能够不刻意隐瞒,畅所欲言,更好发挥交互记忆系统的作用。而在低信任的环境中,团队成员并不十分信任他人提供的信息,会对信息内容的真实意图产生怀疑,甚至过度解读,这种不必要的行为会影响团队协作的效率。团队信任水平高时,交互记忆系统对于团队绩效的影响更大。
(二) 管理启示
本研究结果对于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本研究结论支持了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绩效间的正向关系。高水平交互记忆系统,取决于团队能否产生一种可信且有效的沟通形式,以充分利用团队成员拥有的专长和知识。其次,由于不同类型的团队经验对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不同,当经理在组建团队时,需要同时考虑团队成员个人经验和共享经验,合理进行人员选择与搭配,提高团队的有效性。最后,在团队运作过程中,团队信任起重要作用,团队领导应努力培养信任的氛围。通过恰当方式增进成员之间的了解,建立共同目标,提升团队凝聚力和彼此信任。
(三) 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存在如下不足。第一,本研究的调查样本来源于一家企业,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其他环境下团队成员经验水平对交互记忆系统的影响,来验证研究结论的普遍适用性。第二,本研究仅收集了截面数据,无法对交互记忆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的动态过程进行考察。未来的研究可针对不同类型经验对于交互记忆系统产生与发展的影响进行纵向追踪研究。最后,本文只关注了团队信任这一个调节变量,其他调节变量如任务特点、时间压力等情境因素对团队也有重要影响,未来可以对其他调节变量的影响进行研究。
[1] MATHIEU J, MAYNARD M T, RAPP T, et al. Team effectiveness 1997—2007: A review of recent advancements and a glimpse into the futur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8, 34(3): 410−76.
[2] PENTLAND A. The new science of building great teams [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2, 90(4): 6−9.
[3] WEGNER D M. Transactive memory: A contemporary analysis of the group mind [J]. B Mullen, G R Goethals, eds Theories of Group Behavior,.Springer-Verlag, New York, 1986:185−208.
[4] 张志学, S.HEMPEL P, 韩玉兰, 等. 高技术工作团队的交互记忆系统及其效果[J]. 心理学报, 2006(2): 271−80.
[5] EDMONDSON A C, DILLON J R, ROLOFF K S. Three perspectives on team learning outcome improvement, task mastery, and group proces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07(1): 269−314.
[6] REN Y Q, CARLEY K M, ARGOTE L. The contingent effects of transactive memory: When is it more beneficial to know what others know?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6, 52(5): 671−82.
[7] LIANG D W, MORELAND R, ARGOTE L. Group versus individual training and group-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transactive memory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5, 21(4): 384−93.
[8] 薛会娟. 共享心智模型和交互记忆系统: 对立或协同?——基于知识管理视角[J]. 心理科学进展, 2010(10): 1559−66.
[9] 王端旭, 薛会娟. 交互记忆系统与团队创造力关系的实证研究[J]. 科研管理, 2011(1): 122−8.
[10] BUNDERSON J S. Recognizing and utilizing expertise in work groups: A status characteristics perspective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3, 48(4): 557−91.
[11] 张钢, 熊立. 成员异质性与团队绩效: 以交互记忆系统为中介变量[J]. 科研管理, 2009, (1): 71−80.
[12] PEARSALL M J, ELLIS A P J. The effects of critical team member assertiveness on team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06, 32(4): 575−94.
[13] 黄海艳, 李乾文. 研发团队成员人格异质性与创新绩效: 以交互记忆系统为中介变量[J]. 情报杂志, 2011, (4): 186−91.
[14] 王端旭, 武朝艳. 变革型领导与团队交互记忆系统: 团队信任和团队反思的中介作用[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预印本, 2010, (10): 4−9.
[15] HUCKMAN R S, STAATS B R, UPTON D M. Team familiarity, role experience, and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indian software service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9, 55(1): 85−100.
[16] TEECE D J, PISANO G, SHUEN A. 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7, 18(7): 509−33.
[17] REAGANS R, ARGOTE L, BROOKS D.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experience working together: Predicting learning rates from knowing who knows what and knowing how to work together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5, 51(6): 869−81.
[18] BUNDERSON J S, SUTCLIFFE K M. Comparingalternative conceptualizations of functional diversity in management teams: Process and performance effect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5): 875−93.
[19] CRONIN M A, WEINGART L R. Representational gap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conflict in functionally diverse team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7, 32(3): 761−73.
[20] CRAMTON C D. The mutual knowledge problem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dispersed collaboration [J]. Organ Sci, 2001, 12(3): 346−71.
[21] HOLLINGSHEAD A B. Communication, learning, and retrieval in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8, 34(5): 423−42.
[22] LEWIS K. Knowledge and performance in knowledge-worker team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4, 50(11): 1519−33.
[23] BENDERSKY C, HAYS N A. Status Conflict in Groups [J]. Organ Sci, 2012, 23(2): 323−40.
[24] LEWIS K, LANGE D, GILLIS L.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learning, and learning transfer [J]. Organ Sci, 2005, 16(6): 581−98.
[25] HOFMANN D A, LEI Z, GRANT A M. Seeking help in the shadow of doubt: The sensemaking processes underlying how nurses decide whom to ask for advice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5): 1261−74.
[26] COLEMAN J S.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88, 94(S95−S120.
[27] FARAJ S, SPROULL L. Coordinating expertise in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ms [J]. Management Science, 2000, 46(12): 1554−68.
[28] AKGUN A E, BYRNE J, KESKIN H, et al. Knowledge networks in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projects: A transactive memory perspective [J].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2005, 42(8): 1105−20.
[29] DE JONG B A, ELFRING T. How does trust affect the performance of ongoing team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flexivity, monitoring, and effor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10, 53(3): 535−49.
[30] EDMONDSON A. Psychological safety and learning behavior in work teams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9, 44(2): 350−83.
[31] HITT M A, BIERMAN L, UHLENBRUCK K, et al.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6, 49(6): 1137−57.
[32] BLAU P M. Inequality and heterogeneity: A Primitive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M]. Free Press New York, 1977.
[33] LEWIS K. Measuring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s in the field: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4): 587−604.
[34] JEHN K A, SHAH P P.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nd task performance: An examination of mediation processes in friendship and acquaintance group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7, 72(4): 775.
[35] JAMES L R, DEMAREE R G, WOLF G. Estimating within-group interrater reliability with and without response bias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84, 69(1): 85−98.
[36] BLIESE P D. Group Size, ICC values, and group-level correlations: A simulation [J].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998, 1(4): 355−73.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experience and team performance from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perspective
ZHANG Qian, LIU Renjing, LIU Linlin
(School of Management,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Based on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 (TMS) theory,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team members’ experiences, their distributions and team performances. Results show that team members absorb and integrate each other’s experiences by utilizing TMS, and that shared experiences and distribution among team member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TMS, whereas decentralized distribution of individual experience in team may impede the development of TMS. The impact of TMS and team performance a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and moderated by intra-team trust.
team member experience;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TMS); intra-team trust; team performance
C939
A
1672-3104(2015)01−0127−07
[编辑: 苏慧]
2014−06−17;
2014−11−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多主体仿真的互联网集体智能的形成机制和应用研究”(71271166);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互联网群体智能的形成机制及其应用研究”(20120201110068)
张谦(1985−),男,陕西咸阳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团队学习;刘人境(1966−),男,新疆乌鲁木齐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管理及知识管理;刘林林(1991−),女,山东嘉祥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组织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