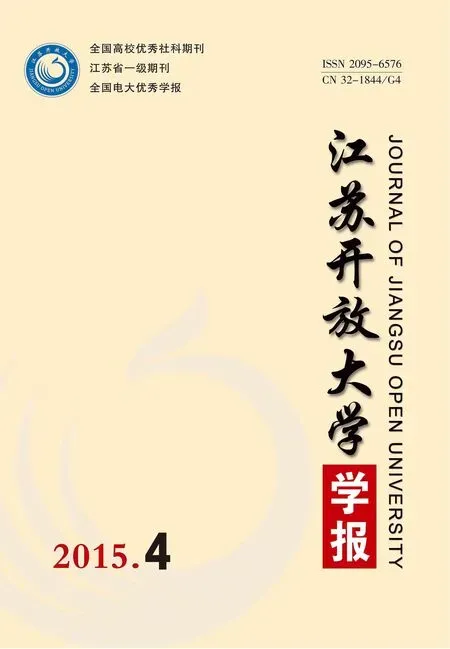身体经验与文学行旅
——试论余秀华诗歌的关键词
尤呈呈
身体经验与文学行旅
——试论余秀华诗歌的关键词
尤呈呈
余秀华以身体隐喻作为观察核心,在诗歌中消融肉体和心录的界线,抒写出饱含情境的诗心景观。除了取材于情动于中的身体经验,她的诗歌亦根植于女性经验和乡土经验两个层面,这三者互为感应,形成独特的诗歌语言张力网。雷可夫和詹森的概念性隐喻视点和茱莉亚·克里斯蒂娃的诗性语言革命观为解读余秀华诗歌所流露出的身心景观之美、女性情感之美和自然之美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并进一步论证了诗人通过身体隐喻、女性主体意识和自然场景的构建,扩大生命意识的感知,运用诗歌语言完成了对男权和主流文化所暗指的强权秩序的亲密反叛。
余秀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身体隐喻;女性意识; 自然场景
2015年初的“余秀华现象”仿佛给中国诗坛注入些许生命力。但是不到半年,余秀华和她的诗歌被贴上了各种标签,“中国的狄金森”“身体写作”“脑瘫诗人”“自白体诗人”等,有人说是“娱乐至死”的年代里大众对诗人上演的一出“文化滑稽戏”,有人称是草根诗歌在社交媒体上掀起的集体阅读狂欢。这其中不乏女权主义者的声音,认为余秀华大胆突破作为边缘群体或弱势者的身份局限;亦有学院派诗人表达对她诗歌走红的揶揄和不屑,称之有媚俗、鸡汤之嫌。当舆论的喧嚣褪去,我们真正能从余秀华的诗中收获什么?是浮躁的追捧和遗忘,转瞬即逝的灵光,或是意义弥久的馨香?本文对余秀华的诗歌进行研读,通过解析其中的母题、意象、结构阐释她的诗歌所迸发的文学想象和美学感受。
一、以身体隐喻为观察核心
因物色而情感共振,因情动而辞发可以说是古今诗人的写作共性。台湾学者郑毓瑜追溯中国诗的修辞传统时指出,“所有存在的意义其实都离不开身体的观点和姿态。”[1]余秀华的诗歌常以身体为想象主轴,体悟现实和理想夹层中的人生场景:“那些花终于不再开了:如虚构的潮水退去/土地呈现本色:荒凉啊/荒凉的爱,荒凉的表达和身体里的次序”[2]187。诗人由身体的感受力张开想象,探究并重绘她的心灵版图。她把身体比作“隐藏着夜色,毒蛇,盗窃犯和一个经年的案件”的矿场、晚风中摇晃的花朵,想象着身体里住着种种可能:溺水的狼,不会错轨的列车或黄昏时的乌鸦,腹腔的花朵,鸟鸣,一条蛇皮。这些不可思议的生机譬喻把读者带进身体隐喻和自然场景交织起来的异域空间,产生一种介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魔幻现实感。
《我的身体是一座矿场》[3]一诗所营造出的亦真亦幻、主客体颠倒所致的模糊界限感尤为明显。诗以身体/矿场的类比开篇,分为三节,每节六行,以洗练简明的意象表达出另类的身体经验。在当代的新闻语境中,矿场无疑是事故频发的边缘化社会地带。诗人在第一节用“经年的案件”和“一个个可以上版面的好消息”等文字间接指向见诸报端的矿难悲剧,弥漫矿场上空的恐怖气氛通过吊诡的意象扩散,夹杂着讽喻社会不公的哀叹,而“盗窃犯”“绑架者”的出现加强了戏剧感,或与个人处境有关。对矿场资源的肆意掠夺与身体所经历的私密感受相互投射,诗人意在从痛苦的经验中淬炼出依然不可浇熄的生命意识。试看第二节第一行的喃喃:“这是一座设备陈旧煤矿,黑在无限延伸”,将身体比作生产工艺和开采技术落后的矿场,取其阴森、晦暗、隐秘的特点,刻画出一具饱含沧桑的疲惫身躯。即便如此,“我”的身体并不轻易示弱,它潜藏着强烈的对抗意识。“我会在某个塌方前发出尖锐的警告,摇晃着蛇信子”,给读者呈现了一幅严酷的视觉画面,流露出绝不臣服于任何强势入侵者的心态。第三节继续深化感官意象的运用 (虫鸣、月光、狐狸的哀嚎、火焰、爱情),使之盘绕整体的身体意识,以矿场内部的美好景象再次呼应身体内部的感情线索,亦刚亦柔。诗以无名者扔进的石头十年后听到的回声作结,于黑暗中敞开光明的愿景,余音袅袅。整首诗亦如身体的戏剧性独白,展露了身体的心声和经受创伤的直觉记忆。面对如矿场般满目疮痍的身体,诗人并不因此自怨自艾,而是融入直觉、素朴、魔幻的力量来赞颂爱与痛的经验世界里流逸出的美感。
语言学家雷可夫和詹森曾提出,“无论如何,理性不是宇宙或去肉身化的心智(disembodied mind)所具备的超验特征。相反,它是由人类身体的特殊性、脑部神经结构的显著细节,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常生活运转特性而塑造的。”[4]他们认为,人的身体经验是许多隐喻及抽象推理构建的基础,这一论断成为当代哲学和认知科学的重要辩题。这其中涉及身体写作的基本概念“embodied mind”,该词常被译作肉身化、实体化、具身化、体塑的心智等,却由于本身蕴含了哲学史上关于身体/灵魂、感性/理性二元对立的深刻思辨,至今没有达成翻译的共识。[5]虽然该关键词缘起西方语境,而中西语言体系截然不同,可是以身体作为情绪震颤核心的书写却能在中国诗的抒情传统中寻得共鸣。《文心雕龙·物色篇》曰:“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6]刘勰认为诗与物互为感应,不仅带来物我气息的相融,更与宇宙万象形成妙不可言的互通应和。而诗人置身于引譬连类的感知体系,其身体所引发的觉动觉知则是发情采为辞章的重要源泉。雷可夫和詹森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中以空间隐喻“UP IS GOOD(向上就是好的)”为例,阐释每一个空间隐喻都有一个内部系统。[7]在英语中,“I feel upbeat(我情绪高昂)”,“things are looking up(事情渐有起色)”用来表达欢快的情绪。在他们看来,这些肉身化的概念性譬喻蕴藏着人类对孩童乃至万物向上生长(“growing up”)的初始愿望,并逐渐演化成人类文化群体共享的隐喻。他们进一步指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们擅长透过自己熟悉的类别去诠释相对难以理解的类别,如通过身体的动静、上下、前后所牵引的空间方位感融入描绘季节更迭及情绪起伏的语言,这在感通层面上,与刘勰所说的“诗心”与物色共徘徊的论述不谋而合。
除了前文略加爬梳的身体譬喻,余秀华诗中常用的词汇如“摇摆”“摇曳”“摇晃”等亦暗指她的隐疾,同时叙写她对世事风物的幽微念想和盎然情感。如她所云:“我的身体全是声音,而雨没有到来”[2]18,“你无法不承认我身体里的一轮落日/和眉梢秋意/它们在风里依然有/动人之色”[2]34,“被一只乌鸦居住过的身体是不是一只乌鸦的假象”[2]38。她在诗中常把身体试想成容纳百千景象的巨大容器,映射出万物在肉身情境里的创意衍伸。通过表现受知觉与肌动控制的起坐、俯仰、摇晃、进出等身姿,余秀华笔下的身体隐喻也构建了诗与外界互动契合的情绪张力网。在她的诗作中,肉体不再是与精神升华成对立面的克己存在,也不附属于传统伦理道德的框囿。那么贯串余秀华诸多诗作的肉体是什么?年轻时欲望的凝视,中年时的臃肿、庸俗、衰老,老来百病残身,乃至死亡时不可逆为的腐朽?在《在我们腐朽的肉体上》诗中,她说,“我一直无法压抑/以腐朽亲吻你肉体的冲动”[8]72,对于肉身如梦幻泡影般的表象,余秀华选择以一种几近悲悯的方式拥抱它的存在。
于是,我们看到余秀华在诗中构建起超越现实时空的身体美学:月光下她忍受孤独的受难日,等待着命运女神的放逐,万物“如一副棺材横在她的身体里”[2]76;正值大好韶光,她思索“如何把身体里的闪电抽出,让黑夜落进来”[2]94……阅读余秀华对身体这座矿场的挖掘,看到“血肉模糊却依然发出光芒的情意”[9]。正如诗人刘年所言,“她的诗,放在中国女诗人的诗歌中,就像把杀人犯放在一群大家闺秀里一样醒目——别人都穿戴整齐、涂着脂粉、喷着香水,白纸黑字,闻不出一点汗味,唯独她烟熏火燎,泥沙俱下,字与字之间,还有明显的血污。”[9]59而这种脱离传统胭脂味的诗歌,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残疾者所经历的身体艰难,一如《唯独我,不是》诗中远非华丽虚饰的文字所言,“唯有这一种渺小能把我摧毁,唯有这样的疼/不能叫喊……我怀疑我先天的缺陷:这摧毁的本性”。[2]68谦卑而疼痛,是余秀华的诗所赋予肉身存在的感觉。不仅如此,潜伏于肉身的视点交织着诗意自觉,悠然跃于纸面,传达了漫游于女性生理和多样化精神特质之间的审美体验。
二、女性经验的呐喊式言说
肉身体验或病体经验所赋予的女性意识是微妙而强烈的,正好映写了余秀华内在的情感挣扎和渴望。她的诗歌常使用第一人称的称谓。在西方,诗名“我”不仅具有自传体性质,还展演出面具人格/假面(persona)。故在叙事抒情层面,既能表露出诗人的参与感,又隐含她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探寻。若从荣格的精神分析角度出发,面具之下的潜意识人格则是影子(shadow),寓意着被压抑而无法充分在意识上表露的另一层面。这两者正反协调后所综合的整体则是均衡的自我(self),犹如阴阳两极在人体内的配合和调和。[10]在这个层面上,“我”应该是没有任何性别预设的人,是脱离了男性凝视、阶级差异的个体。而在余秀华的诗中,作为女性诗名的“我”却是易被察觉的,从自身疾病的隐喻、衣着、生活习惯的描述(“裙摆掀起的风”“端一杯花茶去一棵树下迷恋这烟草年华”)、自然意象的使用(美人蕉、黑蝴蝶、水里的倒影、云朵、树影的玻璃、低垂的向日葵)和第三人称“他”的频繁指涉,可以看出,诗歌中的“我”掺杂了余秀华个人的精神历程,并延伸出女性的自我认同和丰富的自觉意识。由此,我们听到两种声音,一者是自白式的苍凉呐喊:“我的深夜只有两种声音/冤鬼的嘶吼/余秀华的悲鸣”[2]142;另一者是大男人主义者趾高气扬的鄙夷:“在这人世间你有什么,你说话不清楚,走路不稳/你这个狗屁不是的女人凭什么/凭什么不在我面前低声下气”[2]157。在这两股声音之间浮现出的“我”,带着几分虚构几分真实,如那生长在缝隙里却依然得以绽放的野百合,在惨然的宿命前自有一份矜持和操守。
余秀华在诗歌中喜以花草的意象为象征进行自我形象的雕绘。她从不满足于“低于一棵狗尾巴草的宿命”,转而幻想一朵花倔强的姿态。《一只野百合只信任它的倒影打开的部分》[2]107一诗就借着野百合沉寂的姿影呐喊出丰富的女性生命情感。全诗共五段十二行,以五月山野上的野百合为凝视焦点。“一朵野百合就是一个秘密通道,谁摸到,谁消失/一朵野百合也是一个喷涌的山泉,谁到来,谁溺亡”。诗的开头令人联想起美国画家乔治亚˙欧姬芙的花朵内部微观图。欧姬芙画笔下的花总是色彩饱满、肌理分明,既蕴含情色爱欲的想象,又体现花的精神维度,带给读者十足的视觉冲击力和联想。余秀华再现的花亦是半抽象半写实的隐秘力量。野百合本是繁茂的具象,却被比作含蓄隐晦的“通道”和热情贲张的“山泉”。物与物之间的类比代表着逐渐消逝的自然野性?象征着母体生殖的花阴?抑或是消融一切的情欲之泉?诗人写道: “但是它打开的部分是关闭的另一个途径/没有一种信任能让它停止在风里的飘摇”。在修辞层面,拟人巧妙地转换了主客体的关系,拟人化的野百合是有自主选择权的,并不是全然静默的存在。作者或寄寓于野百合的怀疑主义,不受控于任何支配力量,无论如何也不会停止摇曳之姿。“打开”亦是“关闭”,生命历程的流转在此没有泾渭分明的界线。
可是莫名的危险步步紧逼。野百合始终颤动着,隐含无法平息的不安。这种不安是什么? “缴械的危险”又源自何处?作者紧接着用“故意让自己丢失的羊”与牧羊人的类比指涉女性追寻身份时的自我流放历程。在疼痛中或绽放或呐喊无疑是余式的流放美学,显露出她诗歌中感性与理性声音的冲突及和解,就如只有摆脱牧羊人理所当然的管理和宰制,性情温顺的羊才能走向自我认同和独立思考的自由邦国。因此,野百合的信任止于“它的倒影打开的部分”,这一切出离常规的叛逆,与异化的旁观者无关,与轻浮的示爱者无关,纯粹是自我主体的情感诉求。“五月凌乱,一朵花发出喊声就升到了天空/河流湍急,不过是有声的静止”。诗以大自然生命体的召唤作为结尾,激起物我相融的情绪跳跃。画面戛然一止,花的无声呐喊与苍穹下河流的辽阔动态形成鲜明对照。法国思想家西蒙娜·韦伊曾写道:“宝贵事物的脆弱性 (vulnerability) 是美丽的,因为脆弱性便是存在的标志。”[11]而在这首诗里,野生的不羁与柔和温婉的意象,瞬息荣枯的生命气息与五月的蓬勃相互衬托产生的力与美一览无余。
以上所举的诗例,容有不同解读方式,但余秀华借由感官意象和身体的开展显现出生命脆弱无常及万物有情视野下的自我观照,是极为突出的。她偶尔运用佛家的参悟之词如“虚空”“慈悲”“修行”,但并不刻意以佛理入诗。在《屋顶上跳跃着几只麻雀》《荒原》《一种缓慢的过程》等诗作中,我们看到生态美好的情境:春天飞来的水鸟、站在平庸的词语上鸣叫的麻雀、把蓝都举在篱笆上的牵牛花、水里清洗暮年的孩子,诚然是万物与我并存的和谐写照。类似这些彰显脆弱性美学的诗意描述,均可归类为女性经验视野下流露出悲悯情怀的意境。这种笃定且悲悯的女性意识反映了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推崇的集多重社会属性及自然意识为一身的女性主体。在伍尔夫看来,女性意识从不止于对母性的深情言说,更应拥抱与生俱来的情欲性和灵性,而后两者却往往受到男权社会的禁锢。伍尔夫曾写道,“剑影投射在女人广阔的生命版图上”[12]。这把剑是父权社会下男性宰制女性生活所圈定的世俗界限,剑的一端是符合社会期许的女性规范与秩序,而另一端则是背离常轨的乱象。以巫婆、疯女人甚至是写作的女人为例,因为她们挑衅了男权秩序长久以来巩固的社会文化界线,常被认为是游离于既定边界上的危险力量。
在女性主义诗学的视域下,余秀华的诗歌同样焕发出女性书写的意义和能量:一方面,她强调用女性的身体接触世界,以敏锐的感通式语言铺陈女性的生存处境。《浮尘》一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她试图从身体里掏出光亮/……/可是,原谅她吧/把远方拉近身体,依然有无法穿过的恐惧”[2]77。我们不禁要问,恐惧源于何处?这和“缴械的危险”是否同属于平静表面下对女性处境的深切担忧?是日常生活与诗歌语言之间的古老敌意?主流文化和边缘身份的博弈?受困于中年婚姻的爱情理想所面临的窘境(“这辈子做不到的事情,我要写在墓志铭上/ ——让我离开,给我自由”[2]157)?诗人在《每一个时辰都是孤独的》中,“我还是怀抱危险行走的女子”[2]165,隐约道出才华横溢却身历艰辛的女性在世俗生活中的万般无奈。另一方面,她以脆弱或戏剧性的意象营造文本的张力,演绎出诗歌包容万千柔情的心灵状态。香港诗人廖伟棠在阅读余秀华诗歌时注意到她频繁使用“白色意象”,认为这“借以完成自己的强,恰恰是美学上的弱”[13]。的确,我们无法忽视她诗歌里的那团白。月光的白,白春衫的白,野百合的白,失眠的白,梦见八千里雪虚张声势的白,父亲银发的白,鱼池浪花的白,荆棘上白丝巾的白,白鸟斜水而去的白,黄昏光线窄窄的素白……诗人仿佛手持灯盏,试以白光照亮她所目睹的充满疼痛与孤独的晦暗世界:“白,不是一种色彩。而是一种姿态”[2]126。在笔者看来,白是悲悯情怀的象征,是意象和概念的邂逅,既体现个体生命的脆弱性,又彰显诗人不甘受制于宿命的创作意志。除了白的意象,我们也读到余秀华偏向女性美感经验的自然意象的使用,如花草树木鸟虫鱼蔬,均直指微渺的生命,恰恰唤起安静的力量,使人意识到要以谦逊的姿态参与到微观生命史,才能实现诗意栖息、身/心—言/意良性互动的双向平衡。这令笔者想起叶嘉莹先生所勘悟的“弱德之美”,即“在强大之外势压力下,所表现的不得不采取约束和收敛的属于隐曲之姿态的一种美”[14]。余秀华诗歌所奏响的命运回旋曲仿佛也回荡着身为弱势群体在张扬强者至上的社会中依然秉持的一份精神持守,一种逆境中不争的胸怀。
三、返身自然场景的身体─心灵─思想连续体
如果说身体经验和女性的自主意识成就了余秀华的文学行旅,那么深耕于横店村的乡土经验则是她玩味女性姿影、体恤万物风华的重要基石。如同莫言笔下的文学世界深深烙上高密东北土地的印记,横店村流淌的自然生活气息,也以质朴本色的状态进入她的文本。诗中交织的自然意象浸染着她对故乡难以名状的爱恨情仇。生于斯,长于斯,却仿佛也困于斯,诗人因肉身疾患、婚姻状态等个人原因无法远离故乡,字里行间常有这样的感慨,“这不清不白的一生,让我如何确定和横店村的/关系”[2]19,“多年来,我想逃离故乡,背叛这个名叫横店的村庄/但是命运一次次将我留下”[2]182。纵然身运不济,诗人却并不耽溺于消极喟叹,她守望着家园的一草一木,借助诗歌的治愈作用,逐步构筑起与故乡的良性关系模式。“横店!一直躺在我词语的低凹处,以水,以月光,以土”[2]18在她的身体落地生根。在《一个人的横店村》《关系》《晚安,横店》等诗中,我们读到更多的是她对这片土地深厚的爱:“一根稻子就能打开关于田野所有的想象,它的沉默和高傲,忧伤和孤独/它们的隐藏里,有怀孕的老鼠,刚出壳的麻雀和野鸡,这都是田野富饶的部分。”[8]75横店村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村落就这样被带进诗歌的具体化场景,成为余秀华缘情而绮靡的地域坐标。她以诗歌为归依,在身体和感性的双重联结的基础上,见微知著,开拓出女性在天地间的位置。
综上所述,余秀华一再回归身体语言、女性意识和自然场景,发掘并书写女性主体的反叛意义,如她于《在黄昏》诗中的体认:“我看见每一个我在晚风里摇曳/此刻,我的飘逸之态是一种形式主义的对抗。”[2]84语言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指出,人作为言说的主体,乃是持续不间断的创造意义的过程。我们的主体性并非纹丝不动,而是永恒的动态过程。她认为人们不仅是“过程中的主体”, 还是“受审的主体”(subject-in-process/on trial)。[15]女性的身体可以借助语言体系,通过自省和自我审视,构建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克里斯蒂娃的经典论著《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她提出“符号”和“象征”两种永远交缠的语言倾向。在她看来,身体是符号层面的,但并不与心灵形成对立关系,两者并非是完全割裂而独立存在的,反过来它与男权、理性思维主导的象征界相互依附。[16]这有力地衔接了雷可夫和詹森的理论所检视的认知概念“embodied mind(肉身化的心智)”。综合两者而言,身体是文本生成的发端,既是能量场,也是意义场。参照这些与身体经验及女性意识有关的视角,我们从余秀华的诗歌中获得更多的讯息。她不仅以女性身体为据点,使诗文韵律、节奏、意象紧跟身体脉动,还发展出铭刻女性特质的诗心语言。与此同时,我们得以理解她笔下的身体并不等于男性凝视的欲望对象,可以被肆无忌惮地围观、展示乃至剥削,而是自我观照和心灵剖白的载体,甚至是消弭一切对立界线的关键媒介。
作为草根诗人,余秀华或许不了解学院派诗歌理论的脉络和思辨,但这并不影响她的诗歌价值。如她在诗集《摇摇晃晃的人间》所说,诗歌并不是“一种武器”,而是一种近乎本能的情感流泻。[8]2她的诗作也正因为挣脱了条条框框的理论束缚和传统伦理枷锁,才能在广泛的读者群里收获热烈的反响。而她也并非打着女性主义的旗号与所有的男性进行高压对峙,诗中的“他”时而是象征暴力符号的绑架者,以夜色、刀锋、烟草为伍,时而是知音,熟谙“我灵魂迁徙的方向”,均来自真实生活的形色人群。偶尔我们能读到她所宣示的身体内和平共处的理想世界,“我身体里的火车,油漆已经斑驳/它不慌不忙,允许醉鬼、乞丐、卖艺的,或什么领袖/上上下下”[2]12。如此种种,她的诗还原了真实的肉身化心灵状态,进而呈现出内外奇幻的诗心景观。
借用克里斯蒂娃的话语分析,在特定的社会政治语境里,个人反叛的完成有赖于语言及其情感驱力,以身体—心灵—思想的联结体,对抗男权和主流文化所暗指的强权秩序,并作为独立主体与他者、外界建立联系。不管是伤痕再现还是边界书写,诗终究是润泽并守护心灵状态的一方净土。鸟兽微虫、花草树木随着时节变化而呈现的不同物色,借助身体经验所感知的律动、距离、方位与宽窄限制等因素,伴随着情绪、凝视、守望在余秀华的诗心上空回旋。她的诗歌立足于身体经验、女性意识和乡土情结,既结合具象特征,又不抽离现实,传导她对女性身份和大千世界时而温柔时而暴戾的审美和敬意,凸显出身体—主体—文本三位一体的文学景观。这亦是展现了克里斯蒂娃所期许的女性之姿,即,主体必先治愈内伤,重构破碎的自我,关注体验和感知,才能走进与世界审美、同情的关系模式。[17]余秀华在诗歌中检视人生伤痕,尝试自我疗愈,并从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她的诗歌颠覆了身心二元论,调和情欲性、母性和灵性的多重欲望,并完成了对强权秩序的反叛,可以说是极具美学意义的文学行旅。
[1] 郑毓瑜.引譬连类:文学研究的关键词 [M].台北:联经出版社,2012:65.
[2] 余秀华.月光落在左手上[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3] 余秀华.余秀华的诗[J].新诗,2014(1):43.
[4] Lakoff,George & Johnson,Mark.Philosophy in the Flesh—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New York: Basic Books,1999:4.
[5] 冯晓虎.论莱柯夫术语 “Embodiment” 译名[J].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 (1):86-89.
[6] 刘勰.文心雕龙[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94.
[7] Lakoff,George & Johnson,Mark.Metaphors We Live By [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50.
[8] 余秀华.摇摇晃晃的人间[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
[9] 刘年.诗歌,是人间的药[J].诗刊,2014(9):59.
[10] Joseph Donceel.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M].New York: Sheed & Ward,1967:262-265.
[11] Weil,Simone.Gravity and Grace[M].London: Routledge,1963:108.
[12] Woolf,Virginia.“Harriette Wilson”.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M].Vol.4.New York: Mariner Books,1994:254.
[13] 廖伟棠.大众喜欢的诗人也能是好诗人——也谈诗人余秀华[EB/OL].[2015-01-21].http:∥dajia.qq.com/blog/455544026421332.
[14] 叶嘉莹.从文学体式与性别文化谈词体的弱德之美[J].人文杂志,2007(5):100.
[15] Kristeva,Julia.Polylogue[M].Paris: Seuil,1977:55-106.
[16] Kristeva,Julia.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M].New York: Columbia UP,1984:21-25.
[17] 郭军.克里斯蒂娃:诗歌语言与革命 [J].外国文学研究,2003(1):56.
责任编辑 虞晓骏
Bodily Experience and Literary Construction——On Keywords in Yu Xiuhua's Poetry
YOUCheng-cheng/UniversityofMacau
Taking body metaphors as the point of departure, Yu Xiuhua dissolves the boundary between body and mind in her poetry and creates an embodied mindscape. Apart from deriving from body experience of moving, her poetry is rooted in feminine and regional experience, the above three of which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o form a unique net of poetic language. Lakoff and Johnson's relevant notions of conceptual metaphors and Julia Kristeva's concept of poetical language as a revolution offer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rpreting the beauties of scenes woven with mind and body, female subjectivity and nature in her poems. Moreover, the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s demonstrate that the poet expands the life consciousness in ways of constructing body metaphor, feminine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natural scene, and invokes an intimate revolt against the power order implied by male authority and mainstream culture.
Yu Xiuhua; Julia Kristeva; body metaphor; feminine consciousness; natural scene
I207.25
A
2095-6576(2015)04-0068-06
2015-04-15
尤呈呈,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英文系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英语文学研究。(ccyou1984@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