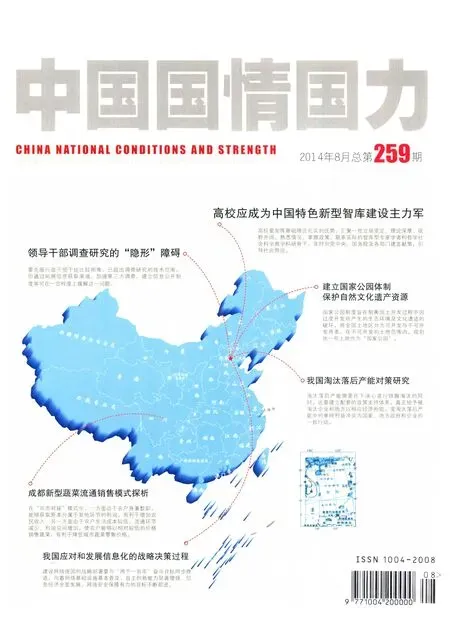瑞典社会公共服务地方化和民营化的启示
◎ 文/张汝立 刘伟明
瑞典社会公共服务地方化和民营化的启示
◎ 文/张汝立 刘伟明
在现代社会,人们对政府高效、优质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已达成共识。但在有限财力的现实约束下,政府应当采取何种方式、优先提供哪些社会公共服务,则充满了无穷的论争。我国政府正尝试转变政府职能,积极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服务,将适合市场化方式提供的公共服务事项,交由具备条件、信誉良好的社会组织、机构和企业等承担。
笔者认为,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通过研究瑞典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实践,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诸多改革措施,有助于增进我们对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理解,进而将这些认识建设性或批判性地运用于我国未来的政策设计和政策安排之中。
瑞典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实践
瑞典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的具体路径为地方化、民营化,共同点在于以政府购买的形式破除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一元化,消解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中的垄断地位,通过引入竞争机制来增加民众自由选择权,进而降低服务成本、提高服务质量。
1.地方化改革
在地方化改革中,瑞典中央政府以财政资助的形式承担着提供大部分医疗服务的责任,具体的服务选择权则由各地方政府乃至民众个体行使。这样的制度安排,既体现了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责任、实现了社会公平,又激励各地方政府和医疗机构为获得更多财政资助而相互竞争,努力为民众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
为了进一步消解中央政府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瑞典政府对财政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1993年以后,社会公共服务的财政资助不再由中央政府按照项目分类原则拨发,而是实行综合性原则,即中央政府根据各郡人口结构、税收等情况提供不同数量的财政资助,具体使用则由地方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自行决定。此外,在老人服务、医疗服务方面也强化了地方政府的职权。
在职权下放、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后,瑞典又进一步推进了地方政府在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中的竞争,体现在增加民众的自由选择权。以医疗服务为例,各郡政府不再为民众指定医院,而是着力于培育内部市场,组织有管理的竞争。可以根据各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来选择医院和医生,甚至可以到本辖区之外的医院就诊,各医院则必须通过竞争来争取患者。
2.民营化改革
瑞典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地方化改革使地方政府有更大的自主权,打破了妨碍社会服务资源有效利用的地区界限,引导各服务提供方为了获得更多中央政府的财政资助而展开良性竞争。此外,还鼓励社会服务领域的民营化,在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与由私营企业或社会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之间引入竞争,继续扩大民众的选择范围。在民营化改革中,瑞典政府仍然承担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财政责任,而引入私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来具体运营部分社会公共服务,方便民众选择。民营化改革在老人服务、医疗服务和教育服务方面表现明显。
(1)在老年服务方面,瑞典政府认为,公共与私人老年服务机构之间的合理竞争是实现社会优质服务提高个人选择自由度目标的主要手段。各种私人老年服务机构的引入,为老人提供了更大的选择范围,更多老人选择了居家养老,居住在各种公共老年机构的老人数量明显下降,这也冲击了既有的公共老年机构。
1992年,瑞典政府颁布法令,系统提出老年服务的民营化改革方向,要求有效合理利用各种老年社会服务资源,提高老年社会服务实际效果,强调为老年人提供更多的个人选择机会。当年瑞典即建立270个私营老年护理机构,占瑞典全国老年护理机构的1/3,71个地方政府和6个郡政府已经就老年和儿童照顾与私营社会福利机构签订了协议 。自开展政府购买养老服务以来,政府购买在瑞典地方政府整个支出中所占的平均比例有了显著提高,将社区照顾老年人的任务外包出去的平均比例从1990年的1%增加到1997年的8%(在一些大型的、主要由保守党执政的城市中,这一比例甚至高达30-40%)。1995-2005年间,老人服务领域的私营公司增加了5倍。经过快速发展,截止2011年有18.6% 的老年人上门服务由私人护理提供 。
(2)为解决公费医疗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民营化改革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化改革重视私营医疗机构和私人开业医师的作用。通过对公共医疗机构的服务项目进行公开承包招标,政府鼓励各公共医疗机构之间、公共医疗机构和私营医院之间进行良性竞争,以提高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医疗服务价格。
随着私人开业医师的增多,一些地方政府在专科医院不提供或提供不足的医疗领域增加了公立医院内私人开业医师提供服务的比例。目前瑞典全国约有800名私人开业医师,主要从事初级卫生保健服务,大多数都与国家保险机构签订合同。政府根据他们为患者提供的服务量和服务类型提供补偿和资助。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私人提供的部分医疗服务纳入了国家医疗保险体系。此外,有大约18%-27%的公立医院医师工作之余受聘在私营医院工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
为促进公共医疗机构和私人医疗机构之间的竞争,还需要破除政府对医疗服务的某些管制,加强医疗服务在不同服务提供主体之间的流动性。2007年5月,瑞典国会通过了关于解除政府对门诊医疗服务限制的修订方案,这使得各省政务委员会可以更容易地将医疗服务转移给私人医疗机构。2009年2月,瑞典国会通过法案引入基础医疗的初选制度,允许病人在私立和公立医疗中心之间进行选择 。这些举措有力促进了医疗服务领域的竞争和医疗服务的多样化,提高了医疗机构的工作效率和质量。可见,民营化改革已经使私人医疗服务机构成为瑞典医疗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在教育服务改革中,瑞典政府引入独立学校与公立学校竞争,学生可以在不同性质的学校间自由选择。政府以“教育券”的形式为独立学校提供资助,间接地为选择学校的学生购买教育服务。“教育券”既保持了政府提供教育服务的责任,又充分体现了民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促使各学校为获得补助而相互竞争,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
瑞典政府综合运用财政资助与严格监管等制度安排,只有经批准设立且运营符合管理要求的私立机构才能够获得由市政当局给予与同类公立机构学生人均费用相当的财政资助,因此政府有效地掌控着私立机构的办学方向、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保证了教育领域中的良性竞争。
3.瑞典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成效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瑞典福利国家改革已经收到明显成效,改革目标已基本实现。表现在:
(1)社会福利支出得到控制。瑞典社会福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3年的38.6%下降为1999年的32.7%,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由63%下降为54%。
(2)政府财政状况开始好转。1998年消除了财政赤字,国债数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93年的77.9%下降为2000年的55.6%。
(3)瑞典经济重新稳定增长。1995-2007年瑞典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平均增长3.2%,大大超过改革前1981-1994年平均1.5%的增速。
(4)有效控制了社会公共服务支出。瑞典用于社会服务的公共支出在1990-1997年间下降了4%。在地方政府中,从事社会服务的工作人员同期下降率超过9%(如果限制到具体部门,从事老人服务的医生和护士人数有所增加)。
在医疗服务领域,1985-1997年瑞典病床的数量减少了近40%,医疗从业人员也从1990年的45.1万下降到1996年的32.6万。2003年瑞典药品补贴支出的增长率为2%,明显低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10%的增长幅度。虽然支出总量保持稳定甚至有所下降,但由于政府购买引入了竞争机制,使社会公共服务提供机构有了更大的外在约束和激励,社会公共服务水平并没有降低,反而与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工作方法的改进并行不悖。
瑞典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实践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在竞争风险加大、流动性增加等因素作用下,传统的家庭服务、自我服务已不适应时代要求。这就要求由政府以税收为后盾,为全社会提供一定水平的社会公共服务,保障每个公民最基本的生存权,促进个人发展,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但由政府直接提供社会公共服务面临着机构臃肿、花费昂贵、效率低下、反应迟缓等挑战。瑞典政府直面困境,采取了地方化、民营化等改革措施,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大力推行政府购买,积极引入地方政府、社会组织、私营企业等多元服务提供主体,取得了良好成效。这对我国建立健全社会公共服务体系有着重要启示。
1.中央政府应积极调动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的积极性,将更多资源整合到社会公共服务领域中来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增加了中央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难度。社会公共服务地方化和民营化改革,在继续维持政府财政责任的前提下,打破了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主体的一元化格局。随着竞争机制的引入,服务提供者必须为了获得政府资助而努力发现民众的不同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外部竞争的激励与约束,有利于服务提供者努力改进工作方法,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此外,因地制宜地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更能够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避免资源浪费。
对中央政府而言,地方化和民营化改革要求其强化筹资和监管职能,体现在政府提供社会公共服务中的财政责任和行政责任。通过优化政府职能,将中央政府从繁杂的具体事务中解放出来,更多关注战略性问题,有利于实现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共同提高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2.政府应大力推动制度变革,公平对待社会组织,培育多元的服务提供主体
目前,我国政府对各类社会组织控制还比较严格,社会组织的成长壮大还受到双重管理、禁止同业竞争和跨地域等多方面的制度性掣肘,在与公立服务机构和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这不利于拓宽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选择空间。因此,在依法管理、依法监督的前提下,政府应考虑在社会公共服务重点领域中解除对社会组织的限制,以便吸引更多社会资源,共同解决社会问题。
3.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时,还应当重视中外社会组织发展程度不同带来的影响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的兴起较晚、发展尚不成熟,在人力资源、资金、管理水平、社会地位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存在较大差距。我国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除了与发达国家政府类似的政府自我限权、授权给社会组织,政府还必须首先“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培育有竞争力的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地方政府已进行了一些富有成效的探索,如以税费减免等方式扶持社会组织发展,并试行社会组织星级评估机制,从社会组织结构保障条件、活动能力、社会实效、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评选出等级,分别给予不同奖励,从物质、声望等方面激励社会组织发展。如何既促进政府积极发挥并强化正当职能,又严格限制政府权力、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地位平等和功能互补,尚需要进一步探讨。
综上所述,社会公共服务地方化和民营化改革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形成了多元服务提供主体,多元主体的相互竞争有利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全局性目标实现,即保障民众的生存与发展、使民众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益处、促进社会繁荣和谐。
*本文系中央高校专项资金项目《中国城市改革中弱势群体的保护与支持政策研究》(编号:201010556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管理研究院)
编辑:武振协
——以十堰公交公司民营化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