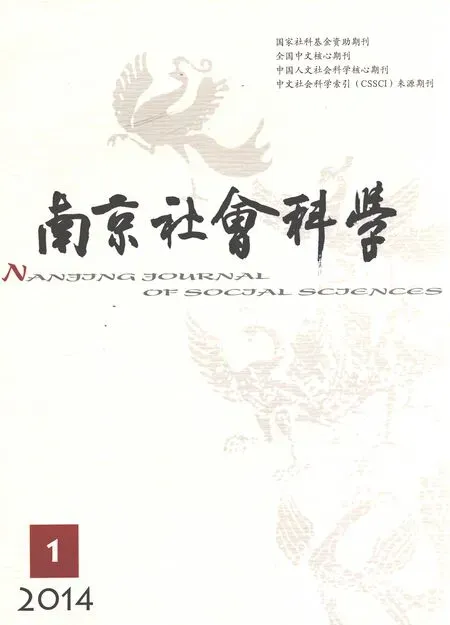国民性改造的社会支持与教育使命*
冯建军
国民即一国之民,是一个群位概念。国民性就是一国之民的共同特性,这种特性指向国民的群体人格。因此,“国民性”又称“国民性格”或“民族性格”,指一个国家的国民或一个民族的成员之群体人格,是特定历史阶段一国国民或一民族成员所普遍具有的思想观念、社会心理与行为方式的共同特征。它赋予民族心理以质的规定性,因此,从本质上说,它是那个民族国家中的社会心理。①在这个意义上,国民性是一个中性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19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Arthur.H.Smith)所写的《中国人的性格》(Chinese Characteristics)就全面列举了中国人的特点: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其中,既有节约、勤劳、刻苦、坚忍、忍耐等积极的一面,也有好面子、漠视时间、猜疑、缺乏同情心等消极的一面。②但20世纪初,随着对国民性消极一面的放大,尤其伴随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批判,不仅使国民性成为一个流行的词汇,而且也使其从一个中性词蜕变为一个意义消极的贬义词,与“国民劣根性”同义。这就有了20世纪初声势浩大的国民性批判运动与国民性改造思潮。笔者虽不认同国民性就是国民的劣根性,但也深知,即便是今天,国民性改造的任务仍很重要,如同英格尔斯所指出的:“如果在国民之中没有我们确认为现代的那种素质的普遍存在,无论是快速的经济成长还是有效的管理,都不可能发展;如果已经开始发展,也不会维持太久”③
本文从20世纪初国民性改造运动入手,分析国民性改造没有能够完成的社会条件,指出当前社会转型为国民性改造提供了可能性,进而提出国民性改造的当代路向和教育的使命。
一、20世纪初的国民性改造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华民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这样一个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维新派从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戊戌维新的破产中惊醒,开始把目光从原先重视器物、制度层面改革,转向思想文化层面,反思国民性的弱点,试图通过改造国民性,实现救亡图存的目的。20世纪初期的中国迎来了颇有声势的国民性批判和改造思潮。
最早检视国民性的中国人当属严复。严复发表于1895年3月4-9日天津《直报》上的著名论文《原强》,正式开启了中国国民性改造的近代征程。在这篇论文中,严复借助进化论的思想,对中西方的文化和人性进行了对比,指出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在《原强》修订稿中,他提出了“新民”的标准:“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虑之强,三曰德行仁义之强”。拯救民族危亡,“收大权、练军实”只能“治标”,“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则能治本。“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原强》)因此,对中国的变革而言,则应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中国如果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便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制度,也难有成效。从国民性变革着手,或许有望。“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国民性成于教化、教育。他批判旧教育为了猎取“富贵功名”而造成“民智“之低下,倡导西学,主张在学校中教授理论科学和科学方法论。在民德方面,他提倡用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启蒙思想代替中国传统的宗法等级制度,进而达到重塑国民人格的目的。严复国民性改造的思想,将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变器物的表层引向思想文化启蒙和人性的改造,将变法维新推向更深的层次。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对国民性反思较多的思想家之一。他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时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中开始把国家的衰弱归因于国民。他说:“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在1899年的《独立论》中又声言:“不禁太息痛恨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提出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的内在根性。梁启超痛恨的国民性是奴隶性,是一种臣民思想和意识,因此,根治国民的奴隶性,“自除心中之奴隶”,必须用独立自由之思想启蒙国民,培养新型的理想人格。他在1902年之后《新民丛报》上连载了他的10万余字的《新民说》,提出了“新民”的形象:国家意识、权责意识、政治意识、政治能力、冒险精神,以及社会公德、自由理念、自治、自尊,等等。梁启超在《新民说》中非常强调改造国民的旧道德,重建现代伦理价值。他把道德区分为公德与私德:“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④中国旧伦理偏于讲私德,忽视了私人对群体(社会、国家)的伦理关系,缺少社会公德。然公德是“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⑤它比私德更重要。因此,梁启超强调国民的社会公德,尤其强调树立国家意识和群体观念。国家意识、群体的观念,并非否定个人的私德和利益,相反,“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⑥也就是说,只有每个人的独立、自由,才有群体的独立、自由。所以,梁启超也强调新民“自由”“独立”“利己”的人格品质,但不忽视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依然注重利国利群。这是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公民思想的根本差别,使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严复、梁启超等维新派是在一个幕落的封建制度下批判国民性的,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⑦所以,建设新的共和制度,首先需要批判的是与共和制度不相适应的国民性,确立新的国民性。陈独秀在《青年杂志》(1916年改为《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呐喊“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新鲜活泼之青年”的出现。新青年具有六种人格: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⑧。为了培养这样的“新青年”,陈独秀提出了“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并特别强调以兽性主义教育来改造国民性。兽性主义的特征是“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他要改变中国人过于文弱的状况,使之既“尚文”又“尚武”,成为文武双全的“新青年”。
对国民性批判最深刻的,非鲁迅莫属。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是因为他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壮,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⑨。鲁迅塑造的“阿Q”形象,集中表现了国民的劣根性,这就是在皇权统治下形成的堕落、奴性、麻木,加以卑怯和贪婪与自私。鲁迅接受进化论和启蒙主义思想,通过文艺的手段,唤醒人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记念刘和珍君》)“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是“中国的脊梁”(《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写小说、杂文,不是单纯为了文艺,而是带着一种人生启蒙,是为了人生,而且改变人生。所以,毛泽东高度评价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孔夫子只能是封建社会的圣人”。⑩鲁迅一生始终求得人的真正解放,实现在“立人”的基础上建立“人国”。
总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代思想家,超越了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学习和模仿,试图通过对国民性的改造摆脱民族危机,从根本上治理国家的落后,是一种巨大的认识进步。但我们应该看到,国民性的改造,尤其是通过教育塑造或培养国民性,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是否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决定了教育对国民性改造的可能与否。
二、国民性改造的社会条件
任何时期的国民性都是当时社会条件在人性上的反映。这就意味着,国民性的改造,不是想当然的事情,需要国民性形成的社会条件。20世纪初,近代启蒙思想家所批判的国民性的保守、狭隘、闭塞、缺乏理性、奴性、自私自利,缺乏国家的观念、民族意识和社会的公德等等,从本质上说,是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自然经济以及封建礼教相互作用的产物。
就政治体制而言,传统的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与封建宗法相互整合的共同体。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力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成为整合分散的自然经济社会的重要力量;在另一方面,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组织形式,全面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和领域之中,二者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上的封闭、凝滞和专制。这种状况在辛亥革命后才渐渐出现变化,中国的封建皇权被成长起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推翻,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共和制。这种体制相对于传统的封建专制无疑是进步的,但是新生的革命政权并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内有封建专制的“复辟”闹剧以及革命政府自身并不完善的政治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殖民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依然强大,造成革命往往只停留在外部的变革,与共和政体相匹配的国民性没有形成。从严复到鲁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正是封建统治者和封建专制制度扭曲了国民的人格,造成了严重的依赖性和可怕的消极性等种种国民性弱点。
就经济而言,小农自然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它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生产、生活模式下,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活需要,生活比较稳定,所以小农经济下的农民安土重迁、生活封闭,与外界的交流很少。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往往通过设立名目繁多的户籍制度将人们固着在土地上,不允许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如此,封建生产关系中的人在丧失了人身自由的同时也丧失了自由独立的人格。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以及帝国主义寻求市场和生产原料的需要,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逐渐被打破。但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殖民势力的夹缝中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都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的自然经济的框架。
就文化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上表现为臣民文化。“在自然经济和封建宗法条件下,弥漫于传统中国的必然是个体消融于整体的封建臣民文化。在传统中国,以往数千年的社会伦理体系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个人对家庭、国家、社会的绝对认同,是对人的独立性的剥夺、理性的削弱和自信的压抑,这就造成中国数千年来的臣民文化和伦理文化强调的是个人对君主、对家族长者、对宗族制度的隶属和依附关系,是礼制、官本位、伦理观等价值理念。”⑪封建社会的臣民文化以及由此决定的封建礼教是塑造中国人奴性的最重要手段,也是统治者强加在国民身上的精神枷锁。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家族本位。对此,孙中山指出:“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⑫中国人以家族为圆心,难以扩展至国族,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没有扩张到国族,致使国人缺乏民族、国家观念。
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的国民性改造理想没有实现,一方面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语),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新国民性成长的社会土壤。在一个封建专制的社会,不可能培养出自由、民主、独立的国民。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从根本上解除了压迫与被压迫的奴役关系,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和国民之间人人平等的关系。但由于人民民主专政刚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尚不健全,更由于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加之思想文化领域高度的一元化,致使只有国家的意志,没有社会的空间和个人的意志,个人再次成为国家的工具,失去了自我。还由于封建礼教文化和习俗的惯性使然,国民的奴性意识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触动。
1978年的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新历程,中国社会逐步出现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由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促动社会转型的根本因素是市场经济体制。
计划与市场,不仅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还反映了人的不同生存方式。计划经济体制遵循的是“一切行动听指挥”,采取僵硬的、划一的管理方式,养成上级的主子意识和下级的奴才意识。市场经济是人与人之间等量的劳动交换关系,每一个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在市场中遵循着公共交换规则,确立了平等的交换关系。计划经济只承认国家的利益,市场经济承认利益主体的多元化;计划经济崇尚权力和指令,市场经济强调平等和协商;计划经济压制人,养成了被动的奴性;市场经济解放人,激发了人的主体性。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是一个“总体性社会”,只有国家,没有公民社会和个人;市场经济使“总体性社会”向国家(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的三元结构转变,越来越多的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被释放出来,国民有机会参与社会的管理,担负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的公民。
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政治体制也朝着更加民主的方向发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继续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尊严、权威,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政治制度的民主化,需要公民摒弃奴性,以一种主人翁的姿态积极参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公共生活。
市场经济是一种个体经济,它打破了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人治和等级文化,赋予一种民主的、理性的、法治的、平等竞争的关系,这成为市场经济所要求的以现代性为核心的新文化。当然,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建设,新的文化正在形成中,这种形成既有自发的历史沉淀,更有自觉的文化改造。这就需要能够创造新文化的新国民。
总的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这场静悄悄的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生存方式,使人的发展由从“依附性人格”走向“独立性人格”。但国民性形成的历史惯性,尤其是传统文化的惰性,使深入骨髓的国民劣根性在当代社会还不时地显露。因此,在社会发展具备良好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就更需要自觉地改造国民性。
三、以公民性改造国民性
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批判的国民性主要指向两个方面: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所谓臣民意识是对个体而言的奴性意识,梁启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奴隶云者,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依赖之外无思想,服从之外无性质,馅媚之外无笑语,奔走之外无事业,伺候之外无情神。呼之不敢不来,麾之不敢不去,命之生不敢不生,命之死亦不敢不死。”⑬所谓私民意识,即缺乏公共意识。国民作为国家的成员,理应具有国家的意识、公共的意识,但国民性中以家族为本位,使国民失去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的关注,“于国家之盛衰兴败,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少动于心”。⑭国民以自我为中心,对国家民族、社会群体、公共事务一概冷漠,无政治热情,无责任感,无义务观念,无群体意识、公德观念,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私民”。
20世纪初期,严复、梁启超提出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就是一种早期的公民教育启蒙。梁启超提出的“新民”具有国家思想、权利思想、义务思想、政治能力、进取冒险精神,还包括公德、私德、自由、自尊、尚武、合群、生利、民气、毅力等品质,⑮这就是一种公民形象。公民的形象和公民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地看,古代的公民秉承共和主义思想,强调公民的公共性、公共生活和公共参与。现代的公民以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为开端,坚持自由主义,强调个体的人格独立和个人的权利、自由。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构成了公民性两个极端。公民性的当代发展,无论是新共和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都走出了自由主义个体性和共和主义公共性的单一向度,寻求公民个体性和公共性的弥合,既强调个体的独立性、权利和自由,又强调对他人的责任、对国家的忠诚和对社会的义务。⑯所以,改造国民性中的臣民意识和私民意识,我们需要从个体性和公共性两个方面建构公民性。据此,我们提出当代公民性的几个方面:
第一,交互主体与主体间性。公民与臣民相对,没有独立人格,称不上公民,只能是臣民。所以,独立人格是公民性的第一要素。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公民,首先要看他有没有从臣民意识中摆脱出来,确立个人的主体意识,成为共同体中独立的个体。
独立是相对于依附而言的。公民首先要走出对他人的依附,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我。但独立不是“孤立”,依附不等于“依赖”。人不依附别人,不等于不依赖别人。人处于社会关系之中,客观上,对国家、社会和他人必然具有一定的依赖性。这也是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关系中,同时又要在社会关系中保持一个独立的自我,即不屈服于别人的自我。
国家是公民之间按照契约和法律组建的协作共同体,国家中每个公民既独立,又休戚相关。因此,现代公民不是个人主体,而是交互主体。个人主体确立了我的地位,但有我无你;交互主体,不仅有我,而且有你,你我作为主体平等共在。个人主体在自我独立的情况下,把他人作为客体,成为我所占有的“臣民”。主体间性的人格,既保持了个人的独立,又使每个人作为平等的主体,和谐共存,实现了公民个体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统一。所以,公民的独立人格,不是个体的单子式主体人格,而是主体间的共生性人格。公民身份必须建立在主体间性的基础上,只有这样的人格特征,才能实现个体性与公共性、权利与责任的统一。
第二,自由与平等。公民是交互主体,这意味着公民首先是个人主体,其次作为主体有交互性。公民作为个人主体,则意味着免予他人的支配和控制,这就是公民的自由。公民自由是公民主体性的要求,也是公民身份获得的前提。古希腊城邦只有自由人,才能够成为公民。但有了自由,也不一定是公民。因为自由,尤其是积极自由的过分张扬,就会蜕变为新的专断和控制。正如柏林所意识到的:“在‘消极’自由观念的拥护者眼中,正是这种‘积极’自由的概念——不是‘免于……’的自由,而是‘去做……’的自由——导致一种规定好了的生活,并常常成为残酷暴政的华丽伪装。”⑰自由是公民身份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其充分条件。
共同体中每个公民都有自由,自由必须是平等的。公民的主体间性,要求公民必须是共同体中具有自由身份的平等成员,“任何有关公民身份本质的探讨都不能忽视平等的原则”。⑱现代公民身份是不断扩大的平等主义。从希腊城邦到罗马共和国,公民范围逐步扩展,意味着公民平等性的递进。现代公民身份以卢梭的“人人生而平等”为依据,赋予每个人平等的公民身份和平等的权利。法国革命的《人权宣言》、美国革命的《独立宣言》都把平等作为立论的最终依据。《独立宣言》指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权宣言》也指出“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
第三,公共性与公共责任。主体间性一是表达主体间的平等性,二是表达主体间的公共性。权利是公民主体性的反映,代表了公民的价值和尊严;公民主体的平等性,决定着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但公民主体间的公共性或者共在性,决定了公民不能是自私自利的人,他必须具有公共意识和社会公德,参与公共生活,承担公共责任。公共责任的本质特征是维护公共性。维护有消极和积极两个层面:消极的层面是不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积极层面是主动参与公共生活,为国家、为人类做出自己的贡献。梁启超当年批判国民性中“爱国心之薄弱”、“公共心之缺乏”、“团结力之差”、“公德之缺乏”,指的就是公民公共性的缺失。孙中山也怒斥国民只有家族的观念,缺少国族的观念。所以,他试图以国家的意识、民族精神来改造国民性。公民作为共同体成员,必须具有公共性。正是公民的公共性制约着个体性,才能使公民的个体性健康发展。
第四,民主与协商。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政体,还是作为一种集体决策的方式,都与公民直接相关。作为一种政体,民主的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或“人民做主”。作为一种集体决策的方式,民主就是凡涉及到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务,都需要集体共同决策。民主政体、民主决策和公民是统一的,公民是生活在民主政体中参与民主决策的人,是行使民主参与权利的人。
作为一种共同的决策方式,民主的决策需要的是协商。协商是因为差异的存在,为了避免差异冲突,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为了寻求共识,就需要一种公正、合理及和平解决利益冲突的方式,这就是协商。协商是要每个公民都参与公共决策,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倾听别人的意见,最后通过一种民主的方式,达成一致的结果。
民主与协商不只是一种制度,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或公民意识。或者说,即便是有一种民主与协商的制度,若没有民主与协商的意识,也不会有制度的自觉力量。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公民意识,民主、协商,与专制、独裁相反,意味着“开放”、“平等”、“公平”、“尊重”、“包容”、“妥协”“宽容”等公民美德与品质。
四、公民教育:培育时代的公民性
公民性具有个体性和公共性两个维度,两个维度是相左的,但公民教育必须寻求二者的平衡,最终培养健全的公民性。据此,公民教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培育个人主体性
公民区别于臣民,就在于公民是个人主体,具有主体性和独立的人格。所谓主体性,是公民作为独立的人,不受别人的奴役和支配,具有自主性、能动性和自我选择、自我判断的能力。康德对启蒙精神做过这样的概括:“大胆运用自己的理智,敢于批评,善于怀疑,不崇拜权威,不轻信教条,独立自主地做出抉择并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⑲这就是公民独立人格的表现。
培养主体人格的公民教育,应该首先是主体性教育。主体性教育就是以一种主体教育的方式,培养学生的主体人格。所谓主体教育的方式,是把学生当作教育过程中的主体,这种教育过程不仅包括课堂教学中学生的自主参与和质疑问难,而且包括学校管理中学生的自主参与,后者对培养公民所需要的独立人格,意义更为重大。公民教育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教化或政治灌输,政治乃至道德的驯化和灌输都是一种奴性的教育,只能培养安分守己、听话、顺从的奴才,而不是具有自我意识、自主判断能力的公民。
权利是人格独立的象征与体现。公民的独立人格,是公民获得自由和权利的前提条件。没有人格的独立,受他人的奴役和支配,就不会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也就不可能成为公民。现代公民以权利为核心,从18世纪的公民权利,到19世纪的政治权利,再到20世纪的社会权利以及当代社会提出的性权利、环境权利等等,权利的范围不断地扩大。权利是主体地位的一种逻辑延伸和价值确认,是主体人格的外在化,也是主体性人格的外在保证。所以,培养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也是公民权利的教育。传统中国社会,国民的奴性就表现在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虽然公民需要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但与义务相比,权利是本源性的。没有权利,谈不上义务。权利是政体和法律赋予的,但公民需要具有权利意识。一方面要争取公民应有的权利,另一方面要保护个人的权利,谨防个人权利被侵犯。公民教育作为主体教育,内在地培养公民主体性和独立人格;同时,作为一种权利教育,外在地培养公民的权利意识,使之成为主张和合理运用权利的“权利公民”。
公民的独立人格,不仅表现为拥有权利,而且表现为一种自由的状态。自由也是一种权利,并且在洛克看来,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权利意味着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不合理干涉或奴役的消极自由,也意味着一种按照自己意愿支配自己行为的积极自由。在这个意义上,培养公民独立人格的教育,必然是一种自由教育。自由有多种指向,既可以指向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也可以指向对社会的创造;既可以指向私人领域,也可以指向公共领域。公民教育中的自由,是个体面向公共领域的社会自由,而不是面向私人领域的个体自由。
2.培育主体间性
培养独立人格的公民教育,是个体公民的教育,它捍卫了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这是公民对自我身份的要求。但公民教育不能只停留于此。止于此的公民教育,培养的虽不是奴才,但却是主子,他们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公民不是“唯我的主子”,不能成为“单子式的、孤立的自我”,而必须成为“社会中的我”、“共同体中的我”,尽一份社会的责任与义务;人与人之间也不是霍布斯所说的“豺狼关系”,而是马丁·布伯所说的“我与你”的关系。
在德国社会学家贝迪南·滕尼斯看来,“共同体”与“社会”是人类结合的两种不同方式。“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而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⑳之所以如此,因为共同体成员之间“默契一致”,他们有一种“相互之间的—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共同体自己的意志”21;而社会是基于一种“契约”,它是“两个不同的单独意志相交在一点上的合量。”22共同体基于血缘、情感和道德而联结,社会是基于契约和法律而联结。共同体是人类结合的原始形式,城邦是典型的共同体。城邦只有共同体的利益,而没有个体的利益,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城邦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原始和谐”阶段。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独立意识的觉醒,尤其是现代公民的出现,人与人之间不再以共同体的形式结合,而是以社会的形式结合。
现代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分离式结合。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是为了个人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迫不得已。在社会里,“人人为己,人人都处于同一切其他人的紧张状态之中”,“没有人会为别的人做点儿什么,贡献点什么,没有人会给别人赏赐什么,给予什么,除非是为了报偿和回赠”,而且“报偿和回赠与他给予的东西相比,至少要同等”。23这就意味着,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保持着自我权利和利益的最大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对他人的义务,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且要求一种平等回报,这就是一种平等互利的交换关系。现代国家是“社会”,而不是“共同体”。按照霍布斯的解释,国家是保护人人平等的权利而成立的一个协议体。个人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或者好处而放弃某些权利,这些让渡出来的权利需要掌管的人,掌管者被称为国家,个人与国家订立契约,国家通过其管理机构——政府来保护个人的权利。国家因为个人存在而存在,其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认识到社会和国家的本质,就可以分析公民作为社会或国家的成员与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公民首先是作为主体的个人,但同时又要超越个人主义,是一种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公民必须是一个相互的主体”。24主体性是公民的首要条件,但公民的主体性,不是单子式的个人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
公民要保持自我的独立,保持自己的权利和自由不受侵犯,但这种自由和权利不是某个公民的特权,而是所有公民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这就孕育了公民主体之间平等的关系。公民教育是一种平等的教育。只有确立社会关系中的平等意识、平等地位,才能使每个人都能成为社会的主体,成为社会的公民。
公民要有权利,权利是公民的第一要素。但正如滕尼斯所说,没有人会主动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为你做点什么,个人权利的获得只能以对他人的回赠、奉献来换取,而且换取的比例要相等。所以,责任或义务是权利的伴生物。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公民享有权利,就必须对他人、对社会承担责任,而且权责一致。所以,公民教育不只是权利教育,也是一种责任教育,是权利优先基础上权责统一的教育。
社会不同于共同体,就在于社会是由利益各异的主体构成。个人要成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必然面临着各种矛盾与冲突。专制社会使用专制或奴役的办法解决冲突,民主社会只能通过公民间的协商解决。所以,公民教育是一种民主教育,它不仅要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民主生活方式,而且要教会学生解决冲突的技能,培养其协商、对话的能力。
3.培育公民的公共性
“主体间性连接了公民的两个方面:公民的主体性和公民的公共性。”25主体间性,既意味着公民个体之间的平等,又意味着公民个体间利益的共在与统一。公民身份不是个人的范畴,而是一种关系范畴。按照滕尼斯的认识,社会是公民个体间的利益联合体。虽然公民在社会联合中是“分离”的,但他们毕竟还具有共同的利益之联合,具有共在的现实基础。但现代公民的问题是,把个体性凌驾于公共性之上,无视公共性的存在,造成公共生活的缺失和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公共参与的积极性降低。所以,当代公民教育,不能只强调公民主体人格的培育,还必须强化公民的公共意识、公共精神。当代公民身份的发展,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社群主义,都在谋求个体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平衡。“新自由主义调和了个人性和社会性,它否认个人的原子式的图景,但又把个人权利当作个人自我实现的最根本的因素;它把个人视为互相促进和自我发展的,把社会生活视为合作而非竞争的。”26社群主义也“从一开始就关心社会力量和个人之间、社群和自主性之间、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27在一个自由主义主导的公民教育时代,更需要强调公民公共性的培养。
主体间性教育,超越了单子式的个人主体,它关照公民他人,培养公民间的平等意识、责任意识,但缺少对社会公共性的关照。培养公民的公共性,从教育的角度说,就是要使学生意识到我们生活中正在出现并扩大着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并且正在形成着共同规则、共同伦理,这些都是一个现代公民所必须承认和遵守的;28使他们了解当代人类发展中所具有的世界化、全球化、一体化的大趋势,不断地扩大公共生活的空间,扩大公共利益范围,从家庭、社区、族群到国家、地区联盟和全球。公民身份也从个体公民扩大到城市公民、国家公民、区域公民(如欧盟公民)乃至世界公民。
在民族国家主导的时代,公民的核心身份是国家公民。世界公民,不是“世界国家、世界政府”的公民,而是具有世界意识、国际视野的国家公民。但国家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人类社会发展将会经过这样一个“国家社会”之后走向一个“无国家社会”的更高级发展阶段,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类社会”,也是可以预见的最高阶段。类社会不同于人类原初的城邦共同体,也不同于现代的“社会”,恰是滕尼斯所说的现代“共同体”,费孝通将其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类社会的公民,将成为完全的世界公民。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公共性与个性并不矛盾。世界的大同,不是压制个性,而是充分发展个性,正如李大钊所说:“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个性解放,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29在人类可以预见的最高发展形态中,世界公民身份取代国家公民,成为类主体,公民的形态也实现了与人之发展最高形态的统一,不仅实现了公民个体性和公共性的统一,也实现了公民性与人性的统一。公民发展的方向,就是不断地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公民教育的最终发展则要超越了公民某种身份的局限,走向成“人”的教育。
注:
①周晓红:《理解国民性: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角》,《天津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袁洪亮:《“国民性”概念的辨析与界定》,《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年第1期。
②伍国:《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书屋》2006年第7期。
③英克尔斯、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54—455页。
④⑤梁启超:《新民说·论公德》,《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⑥梁启超:《新民说·论自由》,《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⑦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297页。
⑧陈独秀:《陈独秀文章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73—74页。
⑨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页。
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⑪赵晖:《社会转型与公民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1页。
⑫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5页。
⑬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⑭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五》,中华书局1989年版。
⑮黄仁贤:《梁启超的新民说与近代公民教育理念的形成》,《教育评论》2003年第1期。
⑯冯建军:《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论证与弥合》,《教育科学研究》2013年第9期。
⑰以赛亚·柏林:《自由论》,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200页。
⑱德里克·希特:《何谓公民身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84页。
⑲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2页。
⑳21 22 23 贝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52—54、71、102、95页。
24 尼尔·史蒂文森:《文化与公民身份》,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53页。
25 冯建军:《多元公民身份与公民教育》,《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26 27 徐友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的若干新问题和新动向(上)》,《国外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28 鲁洁:《当代德育基本理论探讨》,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页。
29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7—5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