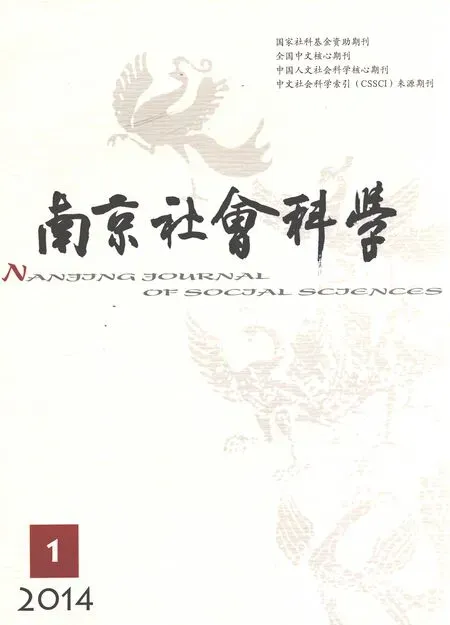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周晓虹
人类社会的变迁自古有之,但是变迁成为人类关注的社会事实或者成为人类自觉思考的主题,却和社会学甚至社会科学本身一样,是因传统社会的断裂而生的所谓“现代性”(modernity)的产儿。①熟知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内在的主要成就和基本规则主要都来自近代以来欧洲社会那场所谓从传统到现代的大变迁。说简单一些,变革的路径及其动因分析,就是西方或现代社会科学的全部知识遗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提出,应该努力将改革开放30年多来中国发生的巨大的社会变迁转化为学术,②否则就会像黄万盛所言,“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巨大的损失”。③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不但迅疾,而且因其特殊性而蕴含了巨大的理论价值和学术意义,研究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理应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
一、社会科学是社会变迁或现代性的产儿
尽管人类社会始终处在变动之中,但真正具有质的意义的大变动只有两次:一次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发生的“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④(亨廷顿,2010:47);另一次即18世纪自欧洲开始延续至今的波及全球的所谓“现代化”,作为从传统到现代或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⑤它“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⑥如果说在公元前5000年,无论是人类本身的心智还是社会的复杂程度都还不允许我们的祖先分析和讨论文明出现的意义,那么作为现代性或变迁之子,自18世纪开始孕育的包括社会学在内的整个社会科学面对愈益频繁而复杂的社会变迁,凭借因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获得的各种实证手段,开始了对人类社会变迁的自觉思考。如此,从现代社会科学出现的时间顺序来看,先是经济学和社会学,接着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再接着是政治学和心理学,最后是传播学,无一不是这场大变迁或转型的产儿。⑦正是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在改变了人类的组织和行为方式的同时,也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结构和行为的观察前所未有的必要并且第一次成为可能。
就观察现代社会科学的孕育和形成来说,社会学因为与社会生活律动的感性关联,以及与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以及传播学的复杂纠葛,成为我们绝佳的切入视角。在谈及社会学的诞生时,美国社会学家D.P.约翰逊提出,社会学的产生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是“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社会变迁”;其二是这种变迁获得了来自知识界的有意关注,因为正是“急剧的社会变迁……有可能提高人们自觉地反复思考社会形式的程度”。⑧进一步,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认为,社会学是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现代性出现的直接后果之一,而“这些变迁的核心就是18和19世纪欧洲发生的‘两次大革命’”,⑨即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产生于欧洲的现代社会学不过是对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而导致的传统社会或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种种反应而已。
尽管法国的政治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对社会学的出现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但从当时的直接效果来看,两者的作用大不相同。具体说来,虽然从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制度并成为现代资本主义诞生的助产婆这一根本意义上说,它对西方社会学的出现无疑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直接而浅表的层面看,社会学的出现最初乃是对法国大革命及革命造成的旧社会秩序崩溃后果的消极回应。对社会学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社会学中自孔德起到现在为止始终占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倾向。⑩
同法国的政治革命相比,社会学从源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中汲取的力量则更多是正面的。工业革命尽管始自18世纪60年代以纺纱机取代传统纺车的变革,但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西方世界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各种相互关联的因素的一次大推进。这次大推进造成了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工业体系、进入城市;造成了工厂在一系列技术的不断改进下的转变;而伴随着大工业的要求,现代分工体系和科层制度也随之出现;以市场为中心的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开始确立……。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工业化不仅是促成西方社会学产生的重要因素,甚至就是现代社会赖以存在的前提条件。⑪
如果我们将围绕上述两次革命性事件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迁视为社会学诞生的动力的话,那么就可以将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提出的各种理论和他们所作的不同努力,视为对人类尤其是西方世界在18-20世纪的转折时期所遭遇的社会危机或文明断裂做出的种种回应。具体说来,马克思和迪尔凯姆意识到他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但他们又都对未来抱以乐观主义的态度。马克思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无序和崩溃的必然性,但他设想将有一种更为人道的社会体系的诞生,并解决在资本主义社会无处不见的物化和异化现象;迪尔凯姆则相信,“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将建立一种和谐而完美的社会生活,并且,这种社会生活将通过劳动分工与道德个人主义的结合而被整合”。⑫和马克思、迪尔凯姆不同,滕尼斯、齐美尔、帕雷托特别是韦伯,则以一种悲观主义甚至绝望的心情来对待上述断裂或危机。比如,在韦伯眼中,现代西方世纪正在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在这里,人类社会要想取得任何物质方面的进步和扩张,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与个人的创造性和自主性天然不容的作为“理性化”象征的科层制“铁笼”的不断扩张。
进而言之,既然欧美社会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直接孕育了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的一般叙事逻辑中,从一开始建立在单线进化论基础上的有关传统与现代的讨论就会成为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idea type)。如此,在经典社会学的文献中,几乎随处可见“传统-现代”这对二元模式变项的各种变式。比如曼恩的身份社会-契约社会、斯宾塞的尚武社会-工业社会、马克思的封建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腾尼斯的共同体-社会、托克维尔的贵族制-民主制、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以及韦伯的宗法传统经济-理性资本主义经济,等等。⑬事实上,经典时代有关“社会”的所有“乌托邦”想象,说到底都不过是站在“传统”的此岸向“现代”的彼岸所作的理论眺望。导源于西方文明转型而带有的这块天生的“胎记”,使得“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是欧洲中心主义的”,⑭由此西方的理论家们无论从认识论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角度,都会自然地站在西方主位的立场上,用西方中心论的观点和西方的经验来看待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世界的变迁,即形成了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或东方学视角。⑮
在这里,我们这样论证起码想说明这样两个问题:其一,以西方为叙事主轴的社会科学理论,最初也是一种建立在特殊性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的话语体系,它只是随着从西方开始的现代化进程向全球推进而开始获得某种普适意义的;⑯其二,正因为西方社会科学家精心研究了在自己的特殊场景下发生的历史事件的必然性,最终不仅使得他们的研究在揭示人类社会结构与行为时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普适意义,而且最重要的是,这种理论或学术的转换使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最终获得了精神意义或文化价值,即我们所说的避免了将西方世界的发展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
二、社会转型: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
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18-19世纪这一朝向现代性的力量对一门后来影响越来越大的知识体系的破土或催生作用,也同样表现在对其后继形态、分支学科乃至具体理论的不断革新和塑造。鉴于西方的社会转型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一直持续绵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并未有任何停滞的迹象;加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1960年代以来,随着拉美、非洲以及东亚国家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下也步入了社会转型或现代化的进程(当然,我们一会也会说到,共产主义文明及其实践是现代发展的另一主轴),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新趋势和新经验一刻也没有停止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充实、修正和再造。最近一百多年来,现代社会科学分支越来越庞杂、理论越来越繁芜、方法越来越精当,庶几正是变迁或社会转型的普遍性、多样性和复杂性所造就的。
还是以社会学为例。继马克思、迪尔凯姆、韦伯和齐美尔这些经典大师之后,继续凭借变迁或社会转型之主题锻造自己的理论之矛的社会学家不胜枚举。以直接诉诸变迁或广义的社会转型为主题的发展社会学为例,它的两种主要形态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就分别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变迁和拉丁美洲、非洲及东亚模式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和分析对象的。事实上,虽然现代化理论和发展理论都是在社会学及经济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但在战后“这两种理论几乎在全世界占据了社会科学的主导地位”。⑰
现代化理论作为发展社会学的最初形态,形成于冷战时代开始的1950年代。从理论脉络上说,构成现代化理论的基础是此时如日中天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而更为深远的渊薮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理性资本主义”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演问题。而从现实挑战上说,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显然是为了与此时如火如荼的共产主义相竞争,在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之外,为欠发达国家确立一条以美国为标准的发展之路。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它是一部标标准准的“非共产党宣言”。⑱虽然现代化理论涉猎广泛,但其基本的理论主张不外这样几条:(1)从传统与现代的两分法出发,现代化就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进化过程;(2)现代社会的发展是单线的,现代化只有一种模式,即西方或美国的模式,由此进一步推导出现代化的趋同论;⑲(3)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所以未能实现现代化,在于这些国家的内在制度结构或文化传统不利于现代化;因此,与西方的接触或西方文明的传播是不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唯一路径。⑳
自1960年代末开始,经典现代化理论及其上述主要信条因多种原因受到广泛的批评并陷入困境。借用美国社会学家赵文词(Richard Madsen)的观点,学术范式的更替,是流行理论、可获得的经验性数据和社会舆论三者互动的结果。21就现代化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而言,此时,在理论上,伴随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的失势,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大行其道;就经验数据而言,拉美、非洲和东亚的发展为新的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资料;而就社会舆论而言,美国卷入越战及其对这样一个弱小民族的狂轰滥炸,不但导致了战后“美国梦“的破灭,也使得其所推行的现代化在全球范围内广受质疑,一如韦伯斯特所说,对“现代化理论最激烈的批判,是指责它完全无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影响”。22
在这样的背景下,自1960年代中期开始,现代化理论开始受到包括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在内的发展理论的强有力的挑战。依附理论主要导源于拉丁美洲的学者对自己国家现代化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现今的世界系统中,存在着由发达国家组成的“中心国家”和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边陲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困境,就是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的经济贸易关系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技术依附。如此,正是西方国家的发达导致了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而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西化”过程,自然也就是不发达国家不断被纳入“中心-边陲”的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过程。23
同依附论者大多为拉美国家的学者不同,世界体系论的首创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来自世界体系的中心美国。虽然和依附论一样,世界体系论也是对现代化理论的回应,但与依附论不一样的是:(1)它的分析单位不是国家,而是作为一个单一整体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中心”、“半边陲”和“边陲”三个等级构成;(2)现代世界体系分为三个维度: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体、多民族国家体系和多元文化体,其中世界经济体是现代世界体系的经济功能体,是政治体和文化体存在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3)世界体系的三级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边缘国家可以通过结构位置的流动而上升到半边陲甚至中心的位置,因此“发展的意义主要就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结构位置”。24
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发生在中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继续为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灵感和想象空间。不仅像伊利亚(Gil Eyal)和赛勒尼(Ivan Szelenyi)等人尝试着通过对匈牙利和前苏联等国的社会转型的研究,25建构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而且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有关中国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学术文献数量(也)大幅度增加”,26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当代中国研究进入欧美社会科学的主流学术圈,从一个单纯的学术“消费领域”开始逐渐成长为一个“生产领域”。27鉴于无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都既是人口众多的世界性大国,又都在20世纪大规模的共产主义实验中做出过令人惊讶的尝试,同时还构建并逐渐固化了与其意识形态相一致的庞大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与前述拉丁美洲诸国相比,其所经历的变迁或社会转型过程不可能不更为复杂、更为触目惊心。正是如此,自然使人们深信,“我们有理由认为,共产主义文明及其转型,对社会学的发展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对这个文明的特点、运作逻辑及其转型的研究应当成为当代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的灵感来源和动力”。28
尽管中国与前苏联、东欧的社会变迁或转型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根本性的差异。除了政治体系在前苏联发生断裂而在中国依旧延续以外,“在俄罗斯,这一过程是自发的……在中国,这一调整则直接来自上层,因此更为稳健并富有连续性”。29虽然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转型吸引了包括伊利亚和赛勒尼在内的社会学家的高度关注,也产生了诸如《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这样的名篇巨制,但从某种程度上说,19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尤其是经济独一无二的高速增长,更是成为推动社会科学进步的强劲动力。认真分析我们能够看到,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上述历史上每一次巨大的社会变迁一样,具备着普遍的理论蕴含和独特的学术意义。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之所以会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与我们一再论述的变迁与社会科学的天然联系决定的。我们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理解这种普遍性或普适性:首先,中国社会的当代转型,虽然有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背景和运作逻辑,但与人类社会近代以来的种种大变迁一样,依旧是一种朝向现代性的运动,一如其转型的起点高度计划和集权的苏式社会主义也同样也是对现代性的反应一样。30换言之,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就是与整个世界文明进程背道而驰的“对向车”,中国也并不是整个世界文明的“他者”。考虑到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间里,中国可能就是这么一个转型社会”,31我们更有理由同时也有必要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对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人类文明进程的某种普遍价值。如果这种普遍价值不能获得有力的证实,中国的转型及其经验就只能是人类文明的一种“例外”,从根本上说我们也就无法真正消解西方文明所鼓吹的绝对普世性。其次,对那些和中国一样具有相似的文化传统和历史遭遇的东方世界的各个民族和国家来说,13亿中国人民当下所经历的复杂而剧烈的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或许可以为他们未来所经历的嬗变提供一种借鉴或参照。当然,我们申明当今中国所经历的这场大变迁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变迁可能具有某种普遍意义,并不意味着要用中国人的转型实践代替其他国家的发展实践,也不意味着要在其他国家推广中国转型的经验(就像西方新老殖民者曾经以及还在做的那样)。鉴于发展和转型的多样性,每一个国家哪怕与中国文化和历史传统相似的国家,在与中国转型或变迁的相似性之外,也一定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因此我们申明中国转型的普遍意义是以承认这种特殊性为前提的。但显而易见的是,申明中国社会的转型具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普适性,才能确立这种转型的正当性,并真正破除绝对意义上的普世价值。
进一步,中国社会转型所具有的普遍的理论价值,是以这场大转型对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独特的学术意义为前提的。我们曾经论述过,今天盛行于世的西方文化所以能够成为一种多少具有普适价值的流行话语,正是由其所率先经历的那场绵延数百年的独具特色的现代化进程所决定的。问题只是在,形形色色的西方中心主义或东方主义,在过度彰显自己的普遍性或普世意义的同时,都有意无意地遮蔽了自己所走道路的特殊性。32由此,我们不但不回避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性,而且意识到,如果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没有自己的独特性,它只是西方世界或其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过的转型实践的一种变式或重演,那么这种转型也就不会有自己的独特意义,所谓“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也就成了一个伪命题。事实也是这样,在这个世界上不乏人口众多的国家(如印度),也不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型的国家(如前苏联和东欧),同样不乏拥有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如印度和埃及),当然它们也都无一例外处在全球化的影响之中。但是,既历史悠久,又人口众多,在面对共时态的全球化冲击之时,也在经受历史态的社会转型,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国家,大概只有一个中国。“这种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广泛而深入的变迁,不仅对中国人民来说是独特的,是他们先前五千年的历史中不曾有过的,而且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独特的,是其他民族或国家未曾经历的”。33能够想象,以中国社会转型为朝向的社会科学,自然能够从这种转型的独特性中获得同样独特的学术意义。
三、理解变迁: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在论述了现代社会科学与社会变迁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社会目今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理论蕴含和学术意义之后,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去说明,如何理解当下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如何通过对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独特解释,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推进社会科学的中国化?
近年以来,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深远意义,34并且力图通过对“中国经验”的研究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价值和实践品质。35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也进一步提出,总结所谓“中国经验”只是这种学术“转换”的可能路径之一,“转换”的另一路径是关照“中国体验”——即在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13亿中国人民的精神世界所经历的巨大的震荡,他们在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模式上的变化。36在我们看来,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应该成为社会科学家理解中国社会变迁或社会转型的双重视角,或者说,中国体验起码在精神层面赋予了中国经验以完整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乔舒亚·库珀·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37虽然中国学者广受雷默之启发,意识到这有可能是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之外的另一种发展模式,但鉴于中国的一切远未定型,因此他们最初相对谨慎地选择了“中国模式”来表述与雷默同样的发展内涵。38接着,在进一步的疑虑和批评之下,39最终产生了更为中性和谨慎的“中国经验”这一替代性概念。
在“中国经验”的概念形成和内涵讨论中,人们逐渐将其视为与西方现代化道路不同的新的发展经验的一部分,而其基本的内涵包括:(1)它不仅仅指“成就”,也包括“教训”,包括走过的发展路程的一切特殊经历;(2)它特别指一些因为中国的特定人口规模、社会结构、文化积淀特点而产生的新的发展规则;(3)它是开放的、包容的、实践中的、没有定型并在不断变化和发展中的经验,他尊重其他经验的选择,它不是作为“西方经验”的对立面而建构的,它也不强调自己的普世性,它的存在只是说明统一律与多样性完美结合的可能性。40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中国经验”视为,在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中国社会近十几年来在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方面的发展与教训。如果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尤其是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社会转型相比,中国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所积累的所谓“经验”起码有这样一些特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因此许多重要的转型或制度变迁是通过变通的方式实现的;(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也就是说,在市场发生巨大转型的同时,居于主导地位的却仍然是先前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41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42
比较而言,“中国体验”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我们说“中国体验”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要用这一概念代替先前的“中国经验”或其他相似概念。“中国体验”的概念之所以具有新颖性,一方面是指它和“中国经验”一样,也是中国社会这30年的急速变迁或社会转型的结果,因此先前的社会科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关注到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另一方面则是指虽然它和“中国经验”一样都是变迁或转型的结果,但和“中国经验”相比,“中国体验”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关注,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中国社会宏观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的同时,中国人的微观价值观和社会心态同样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嬗变。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作为1978年开始的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赋予我们这个独特的时代以完整的历史意义和文化价值。如果单单总结“中国经验”而忽视“中国体验”,我们就不可能发现在这场涉及13亿人口的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现代化之主体的中国人的精神起了何种作用,他们的欲求、愿望和人格在改变中国的同时又发生了何种改变,表现他们喜怒哀乐的社会心态是如何随着社会的变迁而潮起潮落,最后,他们的精神世界遭遇过现在又在面临何种困窘和茫然?
在近年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43我们多次陈述了“中国体验”起码应该具备的基本内涵:(1)“中国体验”不同于中国经验,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它不是中国社会在最近30年中发生的那些结构性或制度性的宏观变迁,而是中国人民在宏观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方面的微观变化;(2)“中国体验”既包括积极的心理体验,也包括消极的心理体验,前者诸如开放、流动、竞争、进取、平和、包容……,后者诸如物欲、拜金、浮躁、冷漠、缺乏诚信、仇富炫富……,人格的边际化或社会心态的两极化恰是中国体验的最重要特点,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国体验本身就是变迁的一种精神景观;(3)“中国体验”虽然是一般经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社会都可能出现的人格和社会心理嬗变,但却因为中国特定的人口规模、转型前后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差异、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全球化的推动以及变迁的速度之快而带有一般的精神嬗变所不具备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得社会心理学家对人类精神世界嬗变的研究具有了全新的意义;(4)虽然中国体验具有独特性,但并非就不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普世意义,也就是说,这一“体验”对其他民族或国家尤其是剧变中的发展中国家可能具有借鉴意义,一部分甚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以复制,而反映到社会科学中,即能够像石之瑜所说将中国研究之成果与“人类普遍性的行为律则相衔接”。44
如果确实可以将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视为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目前正在经历的这场大变迁或社会转型的一体两面,而对变迁的理解又与社会科学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就是关注变迁的路径及动因分析的社会科学本身,那么通过对中国经验和中国体验的研究就不但能够促进中国社会科学的健康发展,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实现社会科学中国化的一次天赐良机。
众所周知,有关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努力并非始于当代。早在上个世纪20-40年代,中国第一代社会科学家尤其是社会学家,如孙本文、吴文藻、潘光旦、陈达和费孝通等人,在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时,就产生了使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适用于中国社会即使之中国化的具体设想,他们并且为实现这一设想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45可以说,当时提出中国化的设想,既是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且不断接受西方文化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又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满足于被动地接受包括社会科学知识在内的西方文化、作西方文化传声筒的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这种设想的提出前提是,对西方社会科学的两面性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既不但了解了作为西方现代性产儿的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普适性的一面,同样也了解了它的非科学性和特殊性的一面。此后,在1970年代因反对美国学术霸权而兴起的“本土化”浪潮中,46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做出了回应,并因此影响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走向。47
尽管我们承认今日中国大陆社会科学的中国化运动与上述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有着某种前后一致的学术继承关系,今天讨论的诸多主题如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化的必要性及基本路径在1930年代和1970年代也都已有所涉及,但我们还是需要说,由于1980年代以来席卷整个世界的全球化运动和中国社会独特的转型实践,既加深了社会科学中国化的紧迫性,也为最终实现社会科学的中国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先来看全球化浪潮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尽管100多年以来,中国知识界在接受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西方文化的时候,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研究的主体性问题,但显然1980年代后当人们面对以中国为客体或知识构成的海外中国研究时,这种主体性或对主位立场的欲求会前所未有地高涨起来。如果说30年前台湾的叶启政教授就直言不讳:“中国社会学所具有的‘移植’和‘加工’性格,就是令人难以忍受的”;48那么,今天像刘东所说的“读着‘洋书’去认识中国的场景”49自然更令人难堪。而就可能性一方而言,由于全球性的生产和市场体系的形成,促进了不同国籍的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的“跨界”流动,这不仅“动摇了原本欧美学者观察中国时为自己所预设的客观基础”,50而且也有可能使中国学者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研究,了解社会科学知识的非普适性的一面,这都有利于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中国化。
再来看社会转型对社会科学中国化的影响。就紧迫性一方而言,中国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由于中国社会的转型涉及面广,原有体制的刚性十足,现行改革的均衡性不够,中国的改革或社会转型已经进入矛盾多发期或“深水区”。我们曾经论述过,因为人口众多和素质不高、基础设施落后、资源有限以及政府管理能力欠缺和执政理念落后,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所遭遇的经济与社会问题(比如人口膨胀、贫困失业、贫富差距、环境污染以及越轨与犯罪)与西方世界曾经遭遇的问题相比,在性质上是相似的,在程度上可能更为严峻。51现在,无论是巨大的成功还是严峻的现实,都向社会科学提出了挑战,要求这样一种现代知识体系能够解释中国经验的利弊两面。同样,就可能性一方而言,也正是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某种程度上对与我们相似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适意义,第一次赋予社会科学的中国化以现实的可能性。我们以为,无论在1930年代的大陆,还是在1970年代的港台,两度社会科学中国化或本土化运动所以最终都未能成功,并不是倡导者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社会的传统与西方世界现实的巨大差异,而是受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研究者们根本上都以为中国的发展进程就是不断克服这种差异、最终实现西方已经实现的现代化的过程。如此,几乎所有的讨论者都着眼于如何用西方的“普适”理论去说明中国的特定“异例”,52而很少有人去思考如何用中国的“异例”去修改西方的理论,或者从中国的“异例”中挖掘带有某种普适意义的新的理论。正是从中国社会的转型及其对人类社会所可能具有的独特意义而言,对转型的学术关照不仅为锻造中国社会科学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而且或许也能够使这场转型避免沦为单纯的财富增长或GDP堆积,从而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这场巨变的精神意义。
注:
①Westwood,Sallie,2000,“Re - Branding Britain:Sociology,Futures and Futurology”,Sociology,34(1):185 -202.
②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③黄万盛、刘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价值》,《开放时代》2009年第7期。
④⑥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7页。
⑤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沈宗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⑦尽管这种思考标志着社会科学的萌生,但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学科的诞生,并不存在统一的标志。一般人们公认:经济学出现在1800年前后,其标志包括1805年托马斯·马尔萨斯出任东印度公司学院历史、商业和财政教授,1825年和1828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分别设立经济学教席;社会学出现于1839年,这一年法国哲学家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创用了“社会学”一词;历史学在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手中成为一门强调“回到原始的第一手资料”的社会科学,大致在19世纪的中叶;人类学成为一门学科,也大致在19世纪中叶稍后,其中1860年德国历史学家巴斯典的《历史中的人》一书的出版和1863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成立都是标志性事件;1880年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研究院是政治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而早前一年即1879年,冯特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建立心理学实验室则是心理学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的重要标志。如果说社会科学的大部分学科都是在19世纪建立的,那么迟迟到20世纪面世的传播学应该是个例外。尽管在20世纪初的30年中,众多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都为这一学科的孕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但一直到1940年代,施拉姆才为这一学科面世揭开了最后的面纱。如此,“到1945年,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峰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3页)。
⑧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
⑨Giddens,Anthony,1982,Sociology:A Brief but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 Pr.Ltd.p.46.
⑩Zeitlin,I.,1968,Ideolog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ological Theory,Englewood,Cliffs,New Jews:Prentice - Hall.
⑪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⑫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⑬一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还是有许多社会学家仍在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将社会作类似的类型学划分:比如,库利的“首属群体-次属群体”,索罗金的“亲密关系-契约关系”,雷德菲尔德的“乡民社会-市民社会”,贝克尔的“神圣社会-世俗社会”,以及费孝通的“礼俗社会-法理社会”(参见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第一卷·经典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3、139页)。
⑭沃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刘峰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5页。
⑮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5—9页。
⑯ 36 周晓虹:《中国经验与中国体验:理解社会变迁的双重视野》,《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⑰沃勒斯坦:《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刘琦岩、叶萌芽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09页。
⑱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队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辑出版社2003年版,第IV页。
⑲虽然马克思也同样表达过所有社会都将通过共同的演进过程变得越来越相似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但冷战时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鼓吹趋同论,却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就是为什么在麦卡锡主义的社会氛围下,现代化理论顺利成章地成了美国应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国策(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或者说成了一种为美国战后国际政策辩解的意识形态(Peck,James,1969,“The Roots of Rhetoric: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2:1)。在这点上,艾森斯塔德讲得最为直白:“就历史而言,现代化就是一个朝向欧美型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的演变过程”(Eisenstadt,ShmualNoah, 1966, Modernization: Protestand Change,Englewood Cliffs:Prentice-Hall)。
⑳Alexander,Jeffrey C.,1994,“Modern,Anti,Post,and Neo:How Social Theories Have Tried to Understand the‘New Problem of our Time’”,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23(June).
21 赵文词:《五代美国学者对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载涂肇庆、林益民主编《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页。
22 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
23 参见普罗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苏振兴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毛金里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Amin,Samir,1976,Unequal Development,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s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
24 27 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25 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吕鹏、吕佳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26 在这篇文献中,林益民和涂肇庆两位主编做了这样的统计:在1978-1987年的10年间,美国两份顶尖的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学刊》所登载的文章中没有任何一篇是有关中国的,但从1988-1992年的5年间,则刊载了5篇这类文章;1993-1997年的5年间,有关中国的论文更是增加至15篇。进一步,“同一趋势也可见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如政治学和经济学”(林益民、涂肇庆主编:《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28 Perry,Elizabeth,1999,“Partners at Fifty:American China Studies and the PRC”,Washington:Paper for Conference on Trends in China Watching.
29 Tucker,Aviezer,2010,“Restoration and Convergence:Russia and China since 1989”,in lawson,George,Chris Armbruster&Michael Cox(ed.),The Global 1989,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0 如孙立平在上面提到的文章中所述,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与现代性毫不相干的,恰恰相反,社会主义运动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独特反应,作为文明的一种形态,它用新的框架组合了诸多现代性的因素。比如,如哈耶克所言,即使集权主义也来源于人们过度信任自身的理性能力——而这也正是现代性的核心内涵之一。
31 金耀基:《现代性转型与转型社会》,载秦晓《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32 33 51 周晓虹:《社会建设: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学术月刊》2012年第8期。
34 参见孙立平《实践社会学与市场转型过程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可能立场与范式重构》,《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周晓虹:《中国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意义》,《学术月刊》2010年第9期。
35 樊纲:《学习中国经验,加速中国改革》,《中国改革》2005年第6期;李培林:《现代性与中国经验》,《社会》2008年第3期;温铁军:《“中国经验”与“比较优势”》,《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37 雷默:《北京共识》,《参考资料》1月29日。
38 42 俞可平:《“中国模式”:经验与鉴戒》,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4页。
39 李克钦、史伟:《“中国模式”还是“中国经验”》,《中共南宁市委党校学报》2006年第2期。
40 李培林:《东方现代化与中国经验》,《社会理论》2007年第1期。
41 参见邹东涛《“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载俞可平等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0页;以及注34中孙立平的两篇文献。
43 同注⑯,另见周晓虹《再论中国体验:内涵、特征与研究意义》,《社会学评论》2013年第1期。
44 50 石之渝:《中国研究文献中的知识伦理问题:拼凑、累读与开展》,载王荣华主编《多元视野下的中国》,学林出版社2006年版。
45 参见周晓虹《全球化与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周晓虹:《孙本文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
46 Moghaddam,Fathali M.,1987,“Psychology in the Three Worlds:As Reflected by the Crisis in 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Move toward Indigenous Third-World Psychology”,American Psychologist,Vol 42(10).
47 杨国枢、文崇一主编:《行为与社会科学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
48 叶启政:《从中国社会学的既有性格论社会学研究中国化的方向与问题》,同注47。
49 刘东:《熬成传统——写给〈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十五周年》,《开放时代》2004年第6期。
52 比如,我们曾经撰文论述,包括最早提倡社会学中国化的孙本文,其人生宏愿也不过是“彻底研究社会理论”,并在中国文献中“搜集足为印证之实例”(周晓虹:《孙本文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社会学》,《社会学研究》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