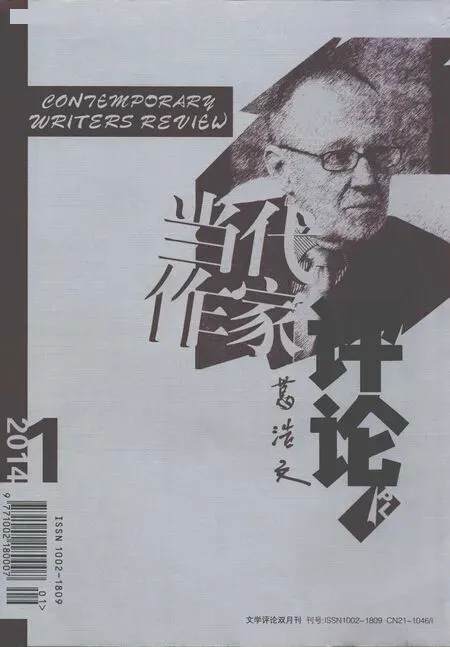张承志对红卫兵的反省和书写
李有智
张承志是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但他不是红卫兵运动中任何一派的领袖,也没有过多地纠缠到当时的一些政治是非里面去,当“八·一八”红卫兵运动达到狂潮阶段,张承志与同学到外地去“串联”了;约一年后,又与同学一道前往内蒙古,在乌珠穆沁汗乌拉插队,当了一名知青。大体说来,在整个红卫兵运动中,张承志的经历是简单的,借用他本人后来评论歌王冈林信康时说过的一句话,“正牌红卫兵比仿造红卫兵更脱离政治”,虽为戏语,亦属实情。当红卫兵运动大潮退去、社会舆论普遍一致地予以谴责时,张承志则以文学的方式探析了此现象,总结其中的教训,这也是他创作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早期的小说如《北方的河》、《金牧场》等,借描写几个年轻人形象,来反省红卫兵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尤其对红卫兵打人现象,有过大量的、细节丰富的描写,其中有反省,有辩解,同时也有着一种并非表面化的忏悔。在一般社会舆论中,红卫兵就是暴力、邪恶的化身,形象极为可怕,他的小说也可看作是对此类舆论的一种答复。一九九四年,张承志在日本出版了《红卫兵的时代》一书,他自认这是第一部认真探讨红卫兵运动的著作,因为使用了日语,国内学术界虽也纷传此书观点,毕竟难睹全貌,无法了解作者的全部观点。进入新世纪以来,张承志试图从理论的角度,表达他对红卫兵的认识,二○○六年发表《卢沟桥的四十年》一文,他对红卫兵运动的全部看法,基本上包含在其中了。
虽然不能读到日文《红卫兵的时代》一书,但他的几个小说文本以及大量散文作品中关于红卫兵的描写和议论,同样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将这些散见于各处的材料连缀、归纳起来,也可以显示出张承志的基本观点,大致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红卫兵运动中,“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也即张承志肯定的是红卫兵中“这一部分”,而非全部。这一点对理解他的思想极为重要,不可忽视。第二,红卫兵运动最大的特点或遗产,是它的青春和叛逆性,是反体制和反官僚精神。张承志至今坚持了这种精神,并将其延伸或发展,试图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层面。第三,红卫兵运动中最大的恶行,是曾经提倡“血统论”,虽然仅仅流行过一段时间,但这一理论中包含着的对人的歧视,是张承志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这一理论将人性中的恶表现到了极致。
一、小说中的红卫兵形象及反省精神
张承志对红卫兵形象的描写和反省,始于中篇小说《北方的河》,小说主要刻画一个以考研来改变命运的知青形象,其中有两处地方公开亮明了主人公前红卫兵的身份,并表示愿意为红卫兵运动中个人以及他人的行为,负起一份责任,这一主题似乎在迄今为止的张承志研究中,是被忽略掉的。
新时期文学中,红卫兵的形象有一个逐渐模式化的过程,打人则是其暴力形象的一个基本标志。实际上红卫兵并非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组织,也即不是所有的红卫兵都是打人者、加害者,如《北方的河》中主人公声明从未打过人,而且他确实也没有打过人,但是作为一个反映知青和红卫兵经历的文本,在当时必须面对社会的质疑,并尽可能地予以回应。
小说在第一章即设置了一个情节,来正面回答这种质疑:当主人公对女记者抱怨说,几十年前他就被父亲抛弃了,成了一个没有父亲关怀的孩子,女记者突然情绪激动地也讲起了自己的不幸遭遇:正是在一九六六年狂暴风潮中,她的父亲,一个中学传达室的打钟工友、前国民党军队士兵,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这个故事在整个结构中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即它终止了主人公对父亲的无限怨恨,在这个终止的地方,开始了“修正”自己过去及现在的一些想法,从而直面红卫兵的历史责任。
张承志曾说过,《北方的河》中的主人公,多半有着自己的影子,那么,主人公的反省不妨也看作是作家本人的反省。张承志还说过,他早年对革命的向往,其实也是青年人的一种“浪漫的情绪”,是一种按捺不住的青春激情,小说主人公身上也反映出了这一点,第二章开首部分有一节文字,既是对女记者的回答,也是对社会的一个正面回应:
那时你崇拜勇敢自由的生活,渴望获得击水三千里的经历。你深信着自己正在脱胎换骨,茁壮成长,你热切地期望着将由你担承的革命大任。那时你偏执而且自信,你用你的标准划分人类并强烈地对他们或爱或憎。你完全没有想到另一种可能,你完全没有想到会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为你修正。
主人公在这里谈到了一个青年对革命的理解,以为革命是非常简单的事,简单到将人一分为二,要么是被爱的一类,要么是被恨的一类,革命就是青春、激情甚至美好;然而,主人公从来没有想到过革命其实还有着“另一种可能”,也即非常血污、残酷的一面。正是这个小姑娘,修正了他那种对革命过于简单的认识,为他提供了一种反省的实例:当整个社会狂热地高呼“万岁”的时候,他根本无从知道,此时有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在一间黑屋子里,正在“用毛巾擦着父亲尸体上的血污”,对他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修正,从此认识到革命的残虐、人性的黑暗。作为一个前红卫兵,主人公愿意承担一份责任:
我感激你,小姑娘,你使我得到了宝贵的修正……那时我是个地道的红卫兵,但是我没有打过人,更没有打过你那当工友的爸爸。不过,我愿意也承担我的一份责任,我要永远记住你的故事。
王爱松曾指出:“作为红卫兵运动最早的发起人之一和红卫兵这一名词的命名者,张承志一直设想存在过一种完全纯粹的、没有血污的红卫兵运动,并试图将青春、理想、革命、正义等等命题从一场民族的泥潭中剥离出来”。从《北方的河》中主人公的反省可证,张承志其实已经察觉到了,革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激情,他从那个十二岁小姑娘擦拭父亲身上血污的故事中,了解到了革命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无可避免的血污。这是一件令他极感沉重的事,“他也觉得自己的心变得丰富了”,对世界、对革命的认识更为丰富。或许一种比较接近事实的说法是,张承志在认识到了革命或红卫兵运动中的血污的同时,并不因此否定一种理想、正义等;也可以说,在反省那种灾难、血污的同时,更应肯定理想、青春等本身的价值。
对《北方的河》中的反省精神,对主人公甘于承担的勇气,批评界未能予以足够的重视。薛毅就曾说过,他细读了《北方的河》,“这是一个为红卫兵辩护的文本,辩护的方式是:我是个地道的红卫兵,但我没打过人。而打人杀人的恶棍、狗东西当然不是‘地道的红卫兵’了。他把红卫兵呈现出的可怕一面从红卫兵中分离出来,转移到他人身上。这样,红卫兵的理想主义可以坚持、发展下去了。张承志的有关革命历史、红卫兵生涯都构不成完整的故事,他把它们放在现在的有关他和大众追求宗教精神的故事的边缘。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把过去的残酷的东西剔除掉,把过去的理想主义实践提纯、过滤、净化,把它们统一在现在的宗教精神中,照亮它们,并使它们神圣化”。薛毅预设了所有的红卫兵都是打人者这一前提,因而抹杀了肯定还有不打人的红卫兵这个事实,这样的逻辑是非常成问题的。其结果是,在面对张承志复杂的文本以及更为复杂的红卫兵运动时,以简单对复杂,以成见代分析,终而归结于模式化的社会舆论。
把红卫兵与打人现象捆绑在一起,这是一种本质化、狭窄化的思维模式,无助于对这一历史问题的解决。
丁东对红卫兵现象有一个非常中肯的评价,他认为这代人经历了一个由驯服工具到逐渐怀疑的过程,严格地说,“对自己当初的历史也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但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主角:
这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二十岁的青年,他们既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并不错,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
如此洞彻历史的观点,在红卫兵研究中确不多见,体现了一个学者真正清明的理性和开阔的视野。
在长篇小说《金牧场》中,张承志以甘于承担的勇气和责任感,继续探讨红卫兵的打人行为。张承志其实并不愿纠缠在这个现象上,问题在于,当整个社会舆论乃至学术界似乎仅仅止步于这个关于红卫兵的固化模式上时,他是不能回避的,要迎面那种质疑。
如果说在《北方的河》中,主人公从打人事件知悉了革命也有极其血污的一面,那么,从《金牧场》的三次打人事件中,则洞悉了人性的恶。此为张承志对红卫兵运动中一个方面的深度反省,尤为值得注意。主人公三次打人事件分别为:第一次打了一个前国民党士兵,此人曾将红军的一个落伍副连长打得吐了血;第二次打了自己的小学同学;最后一次是一路人撞了自己的妻子,上前给了对方一耳光。
以第一次打人事件为例,小说在叙述过程中伴以深度的心理分析,一层层地将一个红卫兵,更是将一个年轻人释放恶的心理,呈现了出来。这段文字里,出现了相当重要的一句“逾越了人鬼不知的关隘”,其意为越过了人的底线:主人公和同学打的不是一个武装的士兵,却是一个和他们一样有着血肉之躯的人。这里就有了一个分界:一个真正属于恶的化身的人,一个真正残暴至极的人,于虐待他人时只会产生出兽性的快感,兽性大于人性,这种人是不会反省的;在此段描写中,主人公于体验虐人快感的同时,已经于朦胧中觉察出此种快感是非人的,正是人的意识、未泯灭的人性使主人公觉出此种行为的罪感。
主人公进一步审问自己:人是能够轻易越过一个“关隘”的,恶也是人自身的一个本质,且在于瞬间控制了人,令其为恶;做了恶的人,就是罪人。可是,“我说我是罪人并不是说我已经犯过罪孽,也并不是人们在道貌岸然之上再加上那一份廉价的自责”,那么,什么条件下人才是真正的“罪人”?自己愿不愿意“为历史充当负罪人”呢?这种逼问最后指向了内心深处:
我的罪就是我自己……如果算一算已经十多年过去了,不知在哪一天我突然震醒了,我看清了历史的真实。可是也是那么一天我懂了:历史的一切罪恶也都潜伏在我的肉体上。
这样一种深度的反省,在张承志的作品中以极度渲染的笔墨写出,却并未引起批评界的注意,反而认为他是在自我辩护,则殊不可解。在对张承志的认识上,存在着一种同样固化的误解,因着对红卫兵的反感,连带反感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此亦人之常情,却非学术、学理的态度。
比如,许子东在批评《金牧场》的一篇文章里,即认为张承志是拒绝忏悔的:
张承志虽然没有像梁晓声这样直接宣告“我不忏悔”,但实际上,《金牧场》要比《一个红卫兵的自白》更能体现“我不忏悔”的“红卫兵精神”……张承志“我不忏悔”的理由只有一条:即“造反有理”错在革命潮流,红卫兵本身的反叛精神是可爱的……《金牧场》中虽然也描写了红卫兵长征途中用皮鞭打人以及在武斗中用自行车链条报复的细节,并将这些少年狂热联系到“人性之恶”来检讨,但作品中的绝大部分篇幅表现的是红卫兵理想可爱的一面:步行几千里,真诚追随红军足迹,而且至死不悔。同梁晓声的自白相比,《金牧场》主人公的红卫兵立场更痴迷更浪漫,其道德标准也能够一以贯之至少自圆其说。所以拒绝忏悔的反思立场更加坚定。
很奇怪,许子东不仅远远低估了张承志对人本身之恶所做的深度探掘,而且将模仿长征的红卫兵与打人的红卫兵等同为一,忽视了一个明显的、重要的分野:当城市里那些被人操纵起来的红卫兵们疯狂打人的时候,一小批红卫兵沿着曾经的长征路途,走向了穷乡僻壤,接触真正的底层中国;即便他们在路上偶然打了一个前国民党士兵,当打人之际,作家也将他们置于严厉的拷问之境,直至自觉意识到自身的恶。打人之际即为反省之时,而更多时间则是走在路上,与那些在城市里四处行凶的红卫兵相比,这些白日黑夜里走在荒野之路上的少年们,就算作家刻意表现他们可爱的一面,又有什么不妥当的呢?
再如张志忠对主人公的这句深度反省的话语,作了另外一种解释,并不认可那是一种忏悔或“领罪”,反而认为是主人公男性惯有的一种“自炫”,他的理由如下:
《金牧场》的主人公,在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时,说自己是罪人,“历史的一切罪恶也都潜伏在我的肉体上。而且,而且我还——别以为我温和善良我是嗜血的!”他甚至还回顾了自己几次动手殴打他人的往事。但他所言的罪恶却不是指这种残忍的打人,而是话锋一转,朗声宣告,“我的血里深深藏着一种罪,它会害我的亲人尤其是害我的女人我总把我的女人当成解罪的蓝草”;而这样的充满男权主义和自我欣赏的话正是面对一位倾心于他的日本女子夏目真弓所言,无怪乎后者再一次惊叹:太美了。主啊……
只要是真诚的反省或忏悔,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也不管其程度强弱与否,皆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精神;可是,如果预设一种前提,或心存一种否定意念,再深刻的反省,都会被认为是无意义的。
还是丁东说得好,仅仅盯着红卫兵的打人行为,并且只要求红卫兵忏悔,就是回避了真正的问题。王年一也持同样的看法,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他如此评说:“红卫兵的如此造反只是一种现象。对这种现象斥之为‘荒唐’、‘疯狂’是肤浅的,归咎于红卫兵是不公道的。这时的红卫兵,绝大多数无非按照上面的提倡去行事,上面的提倡并非出于盲目。表现在某些红卫兵,根子却在上面,更值得研究的是上面何以肯定和提倡。轻视知识,鄙视文化,歧视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简言之是文化平均主义的产物,是阶级斗争‘左’倾错误的恶果。”李泽厚亦曾说过,对“文革”时期的红卫兵不应完全否定,“需要作仔细分析,不能一概骂倒”,他又补充说,这并不意味着要肯定“文革”。
二、红卫兵遗产:青春叛逆及反官僚反体制精神
张承志将红卫兵运动及其精神遗产归结为两个正反对立的方面:好的一面是红卫兵的青春、叛逆特点,尤其是反官僚、反体制的精神,坏的一面是血统论。一九九一年在接受梁丽芳的访谈中,张承志就谈到了这两个方面:“红卫兵最可贵的是反叛精神。红卫兵有很多好的地方,也有很多坏的地方。好的方面是反一切体制,坏的方面是‘血统论’。批判坏的地方和保存好的地方都很难。把所有的红卫兵都否定,或者光说他们好,像四人帮那时候,很容易。最难是当人都说他好,你批判他坏的地方,人家说他都坏,你看到他的好的地方。”
在一九九三年发表的散文《三封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张承志首次从一个高度上赞扬了红卫兵运动,突出了其“反体制形象”:
……应该说,不是法国五月革命的参加者,不是美国反战运动的嬉皮士,是我们——我们这一部分坚决地与官僚体制决裂了的、在穷乡僻壤、在底层民众中一直寻找真理的中国红卫兵——才是伟大的六十年代的象征。
此后,张承志一直坚持红卫兵反官僚、反体制精神一说,然而,他的这一观点却并没得到多少人赞同,持不同意见或反对者倒不在少数,比如许子东就直截了当地说:“张承志后来说红卫兵‘好的方面是反一切体制’。但他小说里的红卫兵其实是不会反对一切体制的,至少无意反叛红军的体制。”
另外,陈思和也不认可“红卫兵现象”中有什么“批判精神”,谁如此认为,那便是轻看了红卫兵在历史上造成的教训:“红卫兵的要害在于权力者利用青少年的幼稚,用革命魔术煽起了青年心中骚动反抗的激情;反过来,青年人又利用权力,企图实现内心对功名的渴望和发泄蛰伏于本能的兽性欲望,而不在于(或者说,主要不是表现在)青年人对既定世界秩序的批判功能。”
许子东和陈思和的批评,相当尖锐,不假迂回,直指张承志论说中存在的矛盾或要害之处。张承志的观点确实存在着一种悖论,看上去很难自圆其说,显出种种纰漏、破绽。比如,关于法国五月革命和美国反战运动,张承志以为这些国外同龄人发动的运动,难以与红卫兵运动相媲美,但马克·科兰斯基《一九六八:撞击世界的年代》一书在高度评价了法、美学生运动的同时,对中国红卫兵评价则很低,他也视红卫兵为中国的“一九六八年一代”,特别指出“他们是毛主席的保卫者”,但在实践中,“文革”十分残忍,是一场灾难,红卫兵就是破坏者。再如,徐友渔在他的一本研究红卫兵运动的专著中,认为“造反”亦即反体制是一个具有讽刺意义的词语,根本上难以自圆其说,“在文革中,不论是老红卫兵还是后来的造反派红卫兵,都是在中国最高统治者——毛泽东的支持和赞许下造反的……所谓造反,几乎是挟着最高领袖毛泽东的威势,欺辱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当权派’……严格地说,中国文革中不论哪一时期的造反派,都是货真价实的保皇派”。
那么,张承志为什么仍然坚持着一种看起来不无漏洞的观点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他并没有执著于此观点的具体历史情境,而是将其抽象出来,上升到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层面:反体制即反对一切对人和人性的束缚、压制等等。他举了一个关于当今教育现状的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也显示了在现今讨论反体制并不是无意义的事:
……是逼着学生受教育,变成社会体制的奴隶。比如今天的北京,家里没有人对音乐有兴趣,却逼着孩子练钢琴、画画。我从小喜欢画画,到最近我才有钱买颜料。可是,现在北京有些孩子,五六岁就已经有全套的油画用具,孩子像个机器。这个风气,把学生又逼成类似红卫兵的境况。
这个例子颇能证明,张承志所说的红卫兵反体制精神,是抽象的、引申意义上的,并不拘泥于过往的历史情境,那么,在分析、研究这个问题时也就不可以仅仅盯着字面意思。张承志本人对所谓反体制的说法,也尽可能地作了简洁明了的解说:当年清华附中过于重视成绩,以致束缚了学生创造性精神的传统,终于造成一种逆反心理,这是红卫兵发生的原因之一;而今天,学生承受的压力,与当年学生并无二致,甚至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种观察或分析,不单是张承志一个人才有,非常有意味的是,阎阳生在《清华附中红卫兵一百天》一文末尾数语,涉及当今大学教育现状,与张承志所观察到的何其相似:“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虽然阎文没有作进一步的解释,其中所含有的意思,其实非常明显,那就是对当今教育的忧虑:一种过于严苛的束缚机制中,会产生、聚积反抗它的巨大能量。
张承志的反体制说,还被他赋予了另外一层反抗的意义,也即将此概念引入了对“世界体制”的反抗中去。所谓世界体制,就是张承志所说的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十字军等等,不一而足,主要是指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张承志对世界局势的一个基本看法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继续着对第三世界的控制,在试图消灭了中东穆斯林国家之后,会将下一目标锁定为中国,面对此形势,他提出了一个判断红卫兵的新标准:
……评价红卫兵孰优孰劣的、新的判断标准,已经来到了。对美国的帝国主义和新十字军主义是采取反对与对抗的立场,抑或是协力、取媚、并把帝国主义的立场和十字军主义作为自己的观点——虽然失之简单,但我认为:此乃判断红卫兵、革命、共产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最重要的标准。
这段文字里出现了相当犯忌的用语和说法。如果理性、冷静地审视,这些概念中所包含的大约仍然是作家强烈的批判精神。姚新勇较早地观察到了这一点,他曾说在张承志的一些文本中,看似有着某种红卫兵情结或造反有理的影子,但张承志与以前的红卫兵造反“有着本质的区别”,在红卫兵那里,只是以“破”字当头,只破不立,在张承志这里是“以‘立’为主,以破辅之”,所以他对西方文化、体制的批判就不是空洞的,而是有着坚实的基础。张宏认为,红卫兵的理想在张承志这里“已经脱离了当时具体的政治和社会语境,变成了实现主体认同和解放的纯粹精神活动,或者说,成为一种革命意识”,这是对张承志“寻求解放的意识形态”的比较准确的解读。
三、红卫兵的“原罪”:血统论
张承志对红卫兵“血统论”的批判,严厉到了令人难以理解的程度。在《墨浓时惊无语》一文中,他说自己十几年来一直在思索红卫兵时代的“原罪”即血统论问题,这已渐渐成了他无法摆脱的“痛苦的内心折磨”。二○○六年恰逢红卫兵成立四十周年,就在这一年,张承志发表了纪念遇罗克并批判血统论的散文《卢沟桥的四十年》。这篇文章开篇即说道,因批判血统论而死的遇罗克,几十年来成了他内心“蛮横的压力”,所以,他必须要写出来,对他而言,这是一笔“不能逃避的孽债”,写了就是“一次赎罪”,如果不写出来,他将不得安宁。旷新年后来对这篇散文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是一篇深刻反省“文革”罪恶的文章,“达到了一种无人企及的深度”。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张承志并不认识遇罗克,他们之间也没有什么交往,因此,即便是纪念遇罗克,也不至于如此刻骨铭心,到了还债、赎罪的地步;二是张承志并未参与血统论的争论中去,何况,现在这一理论已经被证明是极为错误、荒谬的,如果要检讨、反省,首先是当时提出这个理论的人,或与此相关的人,而不应当首先是张承志。
然而,张承志却写出了还债、赎罪一般的《卢沟桥的四十年》一文,从这里反映出,作为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作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对历史抱有严肃负责的态度,借用《金牧场》中的一个句子,他是甘当了历史的负罪者。确切地说,他之所以以此文来赎罪,有一个基本的原因,那就是当遇罗克被害时,自己无意中充当了一个“看杀”的角色:
在举意写这篇文字以后,我多次企图读到遇罗克的判决书,但至今也没有如愿。后来听说出版了一本悼念他的书,但我已经无所谓了;因为我更强烈地意识着的,不是枝节的解释而是立场的追究——毕竟我的双脚曾经站在那一边;在那一边,我们看杀或者加害,心情轻松,不假思索。
张承志说,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派别是阶级的一翼”,这个话语的意思是指,其时活跃着的每个派别都有着“依附权势”的一面,没有多少人会发现,这实际上是“沿袭着一种漫长的历史和阶级的腐朽,它隐藏着人的对他者歧视的恶秉,它是一种卑劣的传统,一种丑恶的遗传”;而依附体制、跻身一翼,即便是在讲求精神的六十年代,同样包含着一种“实惠”在里面。另外还有一种对恐怖的规避,使得人们尽可能地远离危险、谨慎自保,因而像遇罗克那样以一人之身独自直面潮流,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张承志在这里已追问到人的软弱本性了,他说,这是比浅薄的自责或洗得干净的忏悔更令人心动的:
哪怕到了此时此刻,哪怕思想的认识已然足够,我也不敢说:若是那时头脑清晰,我就能一迈脚踏入泥潭。还有一个更大的主角叫做恐怖。众多的、被视为反体制的思想和行为,事先已决定规避那种遇罗克遭逢的恐怖。当年,就算意识到了这一边的不义,谁能说,他肯定会蹈火赴海,站到受辱的那一翼去!
这是张承志公开的、深度的反省,他比任何一个曾经的参与者或亲历者,都毫无避忌地直面了那似乎已被忘却的历史。因此,那种认为张承志拒绝忏悔,或者认为张承志是“原红旨”、“死不悔改的红卫兵”等等说法,都是一些不实之词,是缺乏了解、不负责任的说法,实在不足为训。对此,张承志有时显得颇为愤激,他多次说到自己对红卫兵运动的反省,为今日的“话语霸权”所不能容:
我选择了使用外国语,最低限度地表达思索的方式。但即便如此也不被人放过,那些智识阶级虽然不读外语,却处处著文污蔑他们道听途说的、我对红卫兵的自省。他们竭力把我漫画成一个残余的“四人帮”分子,企图挑起人们的误解,把我引向人们对往日悲剧的巨大仇恨。
因此,纪念遇罗克,也是张承志借此对自己的一个深度反思,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深刻的“自省”。
张承志毫不留情地批判血统论,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这个理论中包含着的人对人的歧视因素,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造成了无数的受害者,它同样会脱离具体的历史语境,继续沿袭下来,进入当代社会,以各种形式来侵害人的尊严。据江沛《红卫兵狂飙》一书的研究,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出现血统论的倾向,而“文革”期间,徐友渔在《蓦然回首》一书中回忆到,当时学生之间已经划分为三六九等,很不平等了,一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现,“不平等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主仆关系或主奴关系,受害者的人格尊严从对联上就可以看出是荡然无存。”在如此恐怖的社会气氛中,遇罗克以一篇《出身论》,独自抗击了血统论,张承志说,“他留下的遗产,是拒绝对人歧视的立场”。
血统论中所包含的歧视因素,并没有随着特定历史情境的消失而消失,却是如一股潜流延续下来,以变异的因素影响当前的社会。张承志剖析了血统论中“对人的歧视”恶劣影响,以为这是中国六十年代最大教训之一,是一项“严重的罪恶”。甚至张承志把遇罗克遗产中的反歧视思想,再一次上升到反对强权、反对世界体制的高度,而对他来说,反歧视也就意味着反帝国主义、反霸权主义:
作为他的承继者,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变本加厉的各样歧视。对人的歧视并没有随着上个世纪的结束而收敛,反而从新世纪降临伊始,就大肆地全球蔓延:对弱者、对少数、对他者的权利、对贫瘠的第三世界、对不同的文明。从民主渴望开始举步维艰的启蒙,又悲剧般迎对着侵犯和抹煞他者文明的神圣十字军同盟,正如迎对着当年神圣的“阶级路线”。
这种严厉有加的批评,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全面或不正确的,但就张承志本人而言,首先是他个人立场分明的体现,其次这种批评是建立在现实判断基础之上的。
总之,张承志对红卫兵及红卫兵运动的反省和探析是真诚、严肃的,亦不乏深度。但是,就像王彬彬所说的,“仅仅因为张承志当过‘红卫兵’,是‘红卫兵’这个称号的发明者,便把他的一切都与‘红卫兵’绑在一起,便把他的整个精神风貌都用‘原红旨主义’和‘红卫兵情结’来解释”,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张承志的反思和描写构成了一种干扰、一种压力。尽管如此,张承志并未放弃进一步的反省,他那种直面严酷历史的姿态,本身就是可贵的。
——从《黑骏马》到《心灵史》看张承志文化身份认同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