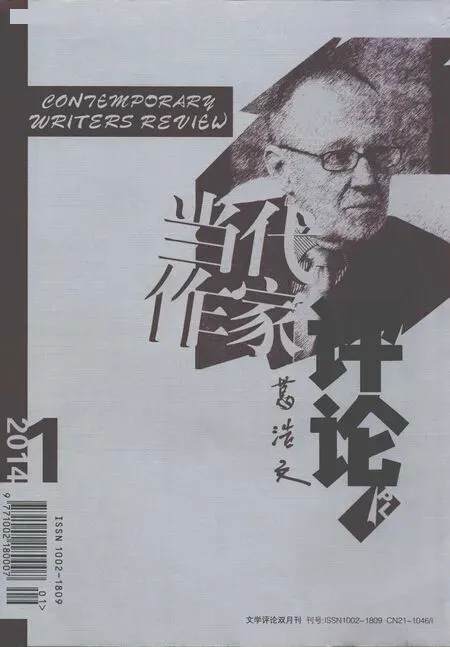当代新诗教育中艾青“经典”身份的丧失与重构
黄晓东
一、艾青在革命与审美之间的平衡及其“经典”身份的确立
艾青由诗人到著名诗人,及至最终成为经典诗人,这个过程是从他的成名作、代表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发表以及被接受开始的。这首艾青写于国民党监狱中的诗,据说写成之后,“狱中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用上海话念了起来,念着念着便哭了”。艾青托人(李又然)将该诗稿带出监狱,最初投稿于《现代》杂志,但被编辑杜衡以“待编”为名压下,暂时未能发表。后再转投《春光》杂志,被编辑交口称赞,于该杂志一九三四年第一卷第三期刊出。这首诗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纷纷写信给《春光》杂志称赞这篇好作品”。不久之后,这首诗流传到了日本。据说“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东京分盟的刊物《诗歌》杂志举办的朗诵会上,一个留学生边读边哭,使听众大为动情。该诗后被译成日文”。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艾青从自己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年创作的新诗中挑选了九首,由上海群众杂志公司结集出版,名为《大堰河》。由此,艾青的诗歌创作进一步引起了评论界的关注。
从一九三七年开始,最早对艾青诗歌作出专业评论的是茅盾和胡风。茅盾在《论初期的白话诗》一文中认为初期的白话诗大多为“印象的,旁观的,同情的,所以缺乏深入的表现与热烈的情绪”,但在将刘半农的《学徒苦》与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进行比较之后,茅盾认为自己更喜欢艾青的诗:
新近我读了青年诗人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是一首长诗,用沉郁的笔调细写了乳娘兼女佣(大堰河)的生活痛苦,这在体制上使我联想到《学徒苦》。可是两诗比较,我不能不喜欢《大堰河》。这问题当然不在两诗人才力之高下,而在两人不同的生活经验等等。
茅盾在文章中认为该诗的风格是“沉郁”的。“沉郁”此后也成为对艾青诗歌风格的总括之一,获得广泛认同,并延续至今。胡风一九三七年二月在《文学》杂志第八卷第二期发表的《吹芦笛的诗人》一文中,对诗集《大堰河》中的文本逐一作出分析评论,并对艾青诗歌作出较高的评价:
我想写一点介绍,不仅因为他唱出了他自己所交往的,但依然是我们所能够感受的一角人生,也因为他底歌唱总是通过他自己底脉脉流动的情愫,他底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底情愫,唱出了被他底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底几幅面影。
此后直至一九四九年,相继对《大堰河》以及艾青诗歌整体的创作做出评论、阐释的,主要还有杜衡的《读〈大堰河〉》、雪苇的《关于艾青的诗》、端木蕻良的《诗的战斗历程》、冯雪峰的《论两个诗人及诗的精神与形式》、吕荧的《人的花朵——艾青与田间合论》、闻一多的《艾青和田间》,以及劳辛的《歌唱光明的诗篇》、《评艾青的〈反法西斯〉》、《艾青论》。从一九三七年及至整个一九四○年代,艾青诗歌的影响逐渐扩大,其诗歌典范的作用也逐渐显现。例如,“七月诗派”的形成和发展,不仅受到胡风及其文艺理论的影响,艾青的诗歌创作对其影响也非常显著。绿原在为诗集《白色花》所作的序言中就曾说,“本集的作者们……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这样,艾青的诗歌经过普通读者的接受以及专业评论家、诗人们不断的阐释,其经典诗人的身份开始逐步确立起来。当然,“作家的经典地位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在‘大多数人长久不断的赞赏中’逐渐形成的”。而要想获得“大多数人长久不断的赞赏”,如本文开头所述,其文本必须具有原创性,另外还要具备艺术上的独特性,并且对新诗史的发展要做出贡献。而这些艾青都不缺少。因为其诗歌艺术的独特性与原创性,主要体现在富有修饰词的繁复的句式的使用,对具体形象进行绘画美特征的细节性刻画,以及饱含忧郁的诗歌情绪。而他对新诗史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其使自由体新诗的发展,在当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从而使白话新诗真正实现了散文化,并向现代彻底转型。其次,其新诗写作的创造性,使胡适提倡的白话诗在由徐志摩等人为其奠基并获取了合法性之后,在新诗的又一个嬗变期,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从而成为连接五四新诗与“新时期”的“新诗潮”的重要诗人、关键性诗人。他对新诗的发展、延续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在中国新诗史的发展中,又必须考虑到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艾青从走上诗坛,到创作的影响逐渐扩大,其走向经典化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现代中国的意识形态系统话语体系转换的过程。在救亡暂时压倒了启蒙之后,如何处理革命与审美、大众化与精英化之间的对立?艾青一九四○年代的写作,在毛泽东《讲话》发表前后,也在进行由审美向革命、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调整与转换。在这种调整过程中,艾青在革命与审美之间竭力保持一种平衡,而不至于一边倒。另外,再加上其诗歌艺术方面创造性的天才,在受到政治的压抑时,也并未完全隐失。这一切决定了艾青的诗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主流所接受,从而未被现当代文学史和现当代文学教育驱逐,或者遮蔽。对此种文学史现象,黄曼君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中有系统的学理化的分析:
审美在不断膨胀的“革命话语”制约下,越来越成为一种“潜话语”,但在这样的“潜话语”下,三十年代前后有沈从文,四十年代有张爱玲、钱钟书这样的经典作家,坚持文学的独立审美品格,超越现实人生,深入到生命的审美形态中。但是这一类经典在政治意识形态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长期得不到承认。……艾青的作品,则属于在革命与审美的张力下比较执中的一类经典:一方面有着倾向革命的进步倾向,因而被冠以“民主主义”的称号;另一方面又不是为某一特定政治团体和思想主义而创作,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艺术的独立性,表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因此其命运要风顺得多。
正是由于这种“审美”与“革命”之间的某种平衡,使艾青似乎尚未经历“光荣的周期”的循环,就成了新诗史上持续的“典范”。当然一九四九年之后大中小学的新诗(史)教育,对其经典诗人地位的建构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大学的新诗教育者、研究者对其文本的艺术特征与审美价值,及其对于新诗史的意义,不断地进行阐释、修正;大学这种研究、阐释以及对其诗歌典范性的肯定与否,自然又会影响到下游的中小学的新诗教育。一九五七年之前,无论从“审美”还是“政治”的角度考量,艾青的诗歌文本被转换成中小学生学习的“知识”都没有问题。这样,再加上教师的讲解、学生的阅读以及考试和书写等现代教育手段的介入,艾青经典诗人的地位也就日益稳固。但是一九五七年九月艾青被划为“右派”之后,在当代的新诗教育中艾青的经典身份经历了由丧失到重构这一过程。
二、“十七年”新诗教材中艾青“经典”地位逐步丧失
王瑶编写的文学史教材《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一九五一年就交由开明书店出版,后一九五四年由新生活出版社重印。史稿的下册,一九五三年八月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教材中对艾青新诗的阐释应该算“十七年”新诗教材中最早的。艾青在教材中被纳入“左联十年”的文学“前夜的歌”中,作为新诗“新的开始”而出场。编者重点介绍了诗集《大堰河》中的《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认为其刻画了旧中国一个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的形象,描画了穷困悲惨的旧中国的农村,同时也表明诗人对地主家庭的叛逆以及回到农民中去的愿望。这个主题上的阐释应该算是中性和平正的。另外,也承认艾青对新诗的形式有所创造,并且指出西方象征主义对其产生了影响,但是其创作并没有染上不健康的因素。王瑶的教材在“抗战时期的新诗写作”的叙述中,认为艾青在为祖国而歌的众多诗人中,他是主流,此时“艾青的芦笛变成了号角”。教材对艾青此时的艺术总括是“散文化”、忧郁的诗绪。但是,“这种忧郁与一些作家颓废性的忧郁又有所不同”。在教材的第十七章“人民翻身的歌唱”中,介绍了诗集《雪里钻》中的叙事诗,主要为“叙述敌后抗日根据地英勇故事”的《雪里钻》,还包括歌颂苏联卫国战争的女英雄的《索亚》。另外,还简述了艾青政治抒情诗集《欢呼集》中的《人民的狂欢节》、《人民的城》、《欢呼》、《献给斯大林》等。其阐释基本是学理性的。
一九五五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则开始从“阶级出身论”来阐释艾青诗歌的主题与艺术,认为地主阶级出身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对其诗歌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因此,“反抗气息不够壮健”,忧郁伤感的诗情也与此有关:
作者的出身经历和他的诗篇是多少有些关系的。由于他在农村里长大,受了农民的抚养,所以他虽然是地主阶级出身,但对于受着苦难的农民却有着真挚的热的。不过他究竟是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又在资本主义国家受过几年教育,多少受了一些象征派印象派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因而,他面对他所热爱的人受着的苦难,虽然威到愤怒,但却浓厚地染上了一层忧郁和伤感,而缺乏一股壮健的粗犷的反抗气息,他只是“用迟滞的眼睛看着这国土的没有边际的凄惨的生命”,“用呆钝的耳朵听着这国土的没有止息的痛苦的呻吟”。
接下来,丁易还认为艾青没有学会用阶级分析来看待问题是一个缺陷,“虽然他还没有明确地从阶级关系上去观察分析一切问题,但这一热爱祖国的崇高意念,却成为他的作品的生命源泉”。另外,他认为艾青诗情的忧郁,作为“个人的忧郁的感情阴影,潜伏在作者心灵的深处,不知不觉就会流露出来”。结果导致“《北方》描绘的只是无力的、悲哀的、北方与人民”。丁易还认为作者叙事诗中塑造的人物经常带有小知识分子的气质,而不是农民的。最后,教材的编者认为诗人到了延安之后,“在政治抒情诗的写作中,一种比较健康的人民的情感逐渐成长起来,过去的那种个人的忧郁伤感的情调是被清洗干净了。作者的诗篇的艺术造诣及其所已达到的成绩,对于中国青年诗人是曾经起过较大的积极影响和作用的,因而他的诗篇在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史上也就有其一定的意义”。
在经典作家、文本的形成和阐释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变化,包括诗人经典地位的变动,我们称之为“经典序列的形成史”。就王瑶与丁易在教材中对艾青的阐释而言,二者就有较大的不同。证明意识形态话语在诗人“经典化”过程中的影响在不断地变动。
再来看一九五七年出版的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刘绶松在教材中对艾青的阐释反而没有丁易的“左倾”,基本没有采用政治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而且尚能看出王瑶的“史稿”对其影响比较显著。刘氏在在教材的上卷中,对艾青的诗歌主题和艺术作出分析之后,认为“艾青的诗集《大堰河》的出现,是这一时期值得珍视的新的收获”。教材在下卷中认为艾青政治抒情诗风格更为明朗健康:
艾青本时期的诗歌,同上一时期比较,其进展是非常显著的:第一,在本时期(特别是来到解放区以后),作者的生活幅员扩大了,与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了,因此,他所歌唱的东方是更为深广而丰富了;在诗集《大堰河》某些诗中出现的“流浪者”的感情已经消褪,代替它的是诗人在现实生活中所感受到的人民的苦难、战斗和胜利的信心,是工人阶级的更坚实更壮阔的胸怀。第二,诗的风格是更为明朗而健康了。如果说,艾青的上一时期的诗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晦涩和过度欧化的毛病,那么,这种缺点在本时期就逐渐地得到克服,而一种明朗的平易近人的艺术风格是在慢慢地形成了。这里,我们可以很明白地看出一个作家的生活锻炼与思想情感的改变对于他的创作风格有着怎样重大的影响。
从这三部教材对艾青诗歌的阐释可以看出王瑶的文学史与后两部不同,它基本未过多地采用阶级出身和政治分析来作为阐释的视角。而后两部还透露出它们的一种未完全言明的观点,即艾青到延安之后的政治抒情诗在艺术上洗去了忧郁的色彩、诗歌更为简洁、明快,是艺术上的一种进步,这也是阐释上的一种变化。在“十七年”时期中的一九五七年,艾青被划为“右派”,而且被认为是“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的成员之一。一九五七年九月四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批判艾青的文章,标题很长:《丁玲的伙伴 李又然的老友江丰的手足吴祖光的知心艾青长期奔走于反动集团之间》。这样,此后直至“文革”编写的新文学史教材中,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艾青及其新诗写作开始大批判,上纲上线;还有一种就是让艾青从教材中彻底消失——在抗战时期的“代表诗人”的叙述中,只剩下了臧克家和田间。我们来看一九六二年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文学史教研室编的教材,标注有“校内使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义(初稿)》。对艾青的阐释在教材的下册,是在“艾青的民主主义诗歌及其个人主义意识”这一标题和框架之下展开的。其内容其实是对艾青的大批判,其“论点”及语言风格完全带有时代性特征。所用的观点为“阶级出身论”、“思想转变不彻底”等,摘录要点如下:
艾青在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阶段,主要是抗战爆发前后的期间里,曾经是一个有影响的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大堰河》出版于一九三六年,显示了他的诗歌的特色,也潜伏着创作的暗流。……在他早期的诗歌中,诅咒黑暗,追求光明的思想感情还是与时代脉搏相呼应的。
但是,艾青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诗人。他的阶级出身和生活教养,造成了他的狂妄自负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西欧世纪末的颓废诗风也给他很大的影响。艾青虽然对当时中国的黑暗现实怀有不满,但是他没有背叛自己的阶级,而是带着一种个人主义要求来追求革命和光明,他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观察、衡量一切。因此他是不可能其正了解和同情劳动人民的。
再看教材中,对艾青未脱离自己的阶级、革命不彻底,以及写作受资产阶级影响等作批判时,所采用的论据和进行的“论证”,这在当时的文学史写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一诗中,尽管用了大量的词藻来赞美、同情那个劳动妇女,但是感情却不坚实。这首诗没有写出处于奴隶地位的劳动妇女和地主之间阶级的对立,反而抹杀了她的阶级意识。她对地主家庭驯服、感戴,甚至“在梦里”天真的幻想:“她吃着她的乳儿的婚酒,坐在辉煌的结彩的堂上,而她的娇美的媳妇亲切的叫她‘婆婆’”。
在“马赛”、“巴黎”等诗里,工业无产阶级旧形象映在他的眼里成了酒徒、流浪汉,他们“摇摇摆摆地”走着,“不止的狂笑”,拿着“红葡萄酒的空了的瓶子”。在这雨首诗里,他也写出了一些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淫嚣、糜烂,但他的诅咒却苍白无力,倒是不时流露出依恋的情调。
教材还举了闻一多评论艾青的话,来论述“艾青在诗中,他的自我形象一直凌驾在自我之上,在人民之上”,以及“艾青到延安后感情上格格不入,创作质量、数量大不如前”:
在“太阳”一诗中,他描写“太阳滚向我们”;在“向太阳”中,艾青又以一个自命不凡的人自视,他听到:太阳对我说,“向我来/从今天/你应该快乐些呵……”闻一多对艾青的批评很对:“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滚向太阳呢?”……艾青到延安后,在革命阵营里感到格格不入。此后他的创作,无论质量数量,比起以前来都大大跌落。
在这个大批判的最后,教材的编者要求艾青“要彻底改造思想、彻底革命,才能创作出适应时代的作品”:
艾青的创作道路,再一次地印证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文艺工作者要到工农兵的火热斗争中进行彻底思想改造的英明指示的无比正确性。一个作家只有彻底革命,作一个共产主义者,才能够在迅速发展的时代中,唱出最强音来。
新文学史对艾青创作的阐释,以及意识形态发生的变化,也影响到“十七年”中学新诗教育中对艾青新诗的教学。在人教版一九五○、一九五一年版的《初中语文课本》选入了艾青的《给我以火》,人教社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版的《初级中学课本文学》中选入了《黎明的通知》,人教社一九五七年版的《高级中学课本文学》中选入了《黎明的通知》和《春》。在一九五七年版《高级中学课本文学》的“教学大纲”中,还规定了《黎明的通知》、《春》的具体教学、阐释的要求,引录如下:
黎明的通知 艾青
黎明象征光明幸福的新社会。作者号召人民以欢快心情迎接新社会。诗人对光明幸福的新社会的热爱和对新社会就要到来的信念。准备欢迎黎明的种种景象的描写。
而在当时初中三年级课外阅读参考书目中,则推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艾青诗选》。当时的“教学大纲”对《春》的具体教学、阐释要求如下:
春 艾青
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和有关的历史年代的简单介绍。
作品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青年的罪恶,指出革命烈士的伟大先驱作用和革命的胜利前途。
“春”的象征意义。
“十七年”中学语文教材中选入艾青的《给我以火》、《黎明的通知》、《春》三首,还是表现出编者的选择意图以及对“经典”确认的标准——这三首诗注重抒写的是“革命”以及对“革命”胜利的憧憬和信念。
但是,自被划为“右派”之后,他的文本就从“下游”的中学的新诗教材中消失了,一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再次入选。
三、“新时期”新诗教材对艾青“经典”身份的重构
在新时期之初的新文学史教材中,还存在着用阶级、政治分析的方法来阐释艾青创作的情况。但是有些文学史家已开始竭力修正极左思潮的负面影响,恢复艾青经典诗人的地位。从唐弢、严家炎主编,一九八○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三册中对艾青的评价,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对此前有些文学史中批评艾青在“巴黎”、“马赛”等诗中表现出“对资本主义都市生活的依恋”,该教材认为“《马赛》、《巴黎》等诗,虽也略带依恋,更主要的却是充满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揭露和诅咒”。同时,对以往教材中对艾青“革命”不够彻底,阶级身份暧昧不明,诗歌留存有浓厚的忧郁情绪,到延安后“诗歌数量质量跌落”的指责,甚至包括闻一多对艾青的“为什么不滚向太阳”的诘问(闻一多所言的“太阳”后来被用来指革命领袖,或者就是毛泽东),也一一地进行修复和“正名”:
1.证明艾青与地主阶级“发自内心的决裂”:
《大堰河》诗集中所表现的对于农村劳动人民的热爱,发自内心的亲近他们的要求,以及对于剥削阶级的憎恶和决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怀疑和批判,等等,正可以说是作者过往生活和感情的总结,也是诗人新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道路的起点。
2.证明艾青抗战后,诗歌中对以往忧郁情绪的克服:
……抗战爆发了。作者“拂去往日的忧郁”,迎着“明朗的天空”,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作者抗战开始后写的诗歌,更富现实意义,更多抒写人民群众,诗歌的形象更鲜明,丰富,语言也更朴素、健康和清新。过去流露的忧郁的情绪,已日益带上愤恨甚或悲壮的色彩,而对于光明和革命的追求,则愈趋明确,坚定。
3.对抗战及到延安后,“感情上格格不入,诗歌数量质量大大跌落”的辩护:
正如不少从国统区来到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那样,他们虽然努力地反映新的生活,却由于一段时间内思想感情上的距离,甚至格格不入,他的作品往往在艺术上比较薄弱;艾青这时的诗作,也曾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是随着作者在延安生活的深入和思想的提高,这种情况才有了变化。爱的热烈如果反映出观察的深刻和理解的透彻,它们就能使政治信念化为高昂的形象的诗情。
4.为闻一多的“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辩护,并以对《向太阳》的具体分析,证明艾青“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并且,“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
闻一多在谈到诗人们的“知识分子气”时,曾说:“艾青说‘太阳滚向我们’,为什么不是我们滚向太阳呢?”应该说,《向太阳》中是已经出现了这种思想感情的良好转化的。特别是作者在向往一些民主革命的领袖和理想的同时,更歌颂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导师列宁和《国际歌》等,这里标志着作者思想感情的趋向。
……最后的两段转向作者自己的内心感受,太阳驱散了他的寂寞,彷徨和哀愁,召回了他的童年,在“热力的鼓舞”下,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宽怀与热爱”,他奔驰着,向着太阳。长诗诗情联绵,却又层次分明地反映了作者心情的发展,越到最后,作者越渴慕和靠近太阳。
最后,教材对艾青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典范性”的意义做出了总结与高度评价:
艾青的诗,标志着‘五四’以后自由体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又给以后的新诗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
新时期以来,“上游”的文学史教材中对艾青的“平反”,也影响到了中学语文教材对艾青的“选择”,对“经典”的重新确认。按照一九八○年、一九八八年、一九九二年陆续修订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的规定,中学教材一直选入了艾青的新诗,依次为:《黎明的通知》、《给乌兰诺娃》、《大堰河——我的保姆》、《礁石》等。其中,《大堰河——我的保姆》入选频率最高。对艾青的新诗创作的阐释和研究,在当下的新文学史教材中,已经“拨乱反正”,重回正常的轨道,并且更加侧重于其语言、文体等艺术的层面。例如,对其诗歌繁复句式、色彩感与画面感等特征及其渊源的揭示。在此基础上,学界对艾青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甚至“走向了世界”。而对其诗歌意义的阐发,更是发掘出“体现了东西方文化道德观念”,“基督教义中的某种精华”,如“博爱、人道、献身”,以及东方的“匡世救民”、“圣经意象”和“希腊神话意象”等。而对艾青与文艺思潮的关系,也揭示出艾青确实与戴望舒一样,曾受到象征主义影响,但是“归国后,在严峻的现实中又都先后走向现实主义。这与创造社成员们的艺术道路十分相似,但艾青们仍然或多或少地保持着象征艺术的影响,不像创造社的转变那样彻底”。学界对艾青研究的重视,以及因此所产生的研究成果再次影响到了大中小学的新诗教育。这些成果一般会被写入文学史、新诗史教材,并且继续横向地影响到“大学语文”的教学,在纵向上也影响到了中小学的新诗教学。在新世纪以来的新诗史以及与文学史所配套的“作品选”中,在“大学语文”教材中,艾青诗歌入选的频率很高。据粗略统计,“大学语文”中入选的经典篇目基本固定为:《大堰河——我的保姆》、《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我爱这土地》等。而新世纪以来的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艾青则更是必选的经典作家,其文本除了上述的三首外,还加入了《绿》、《我的思念是圆的》、《北方》等。这也说明,艾青具有代表性的经典文本——或者说经典文本序列和谱系——在新的价值体系、知识体系以及意识形态体系之下,被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确定。
从一九四九年到新时期,及至新世纪,艾青经典诗人的身份与意义日趋受到重视。因为这涉及到“新诗向何处去?”这个严肃问题。而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当前世界上一个普遍关心、尚待讨论的问题。随着这一问题的逐渐解决和明了,艾青诗歌的地位、意义和价值,才会越来越深刻清楚的显示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