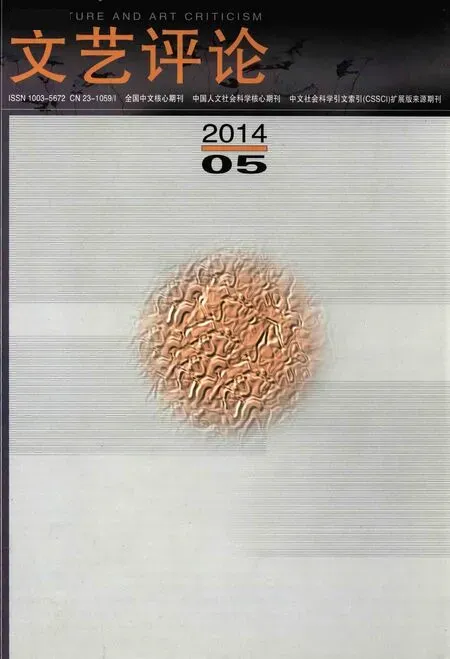影视与文学:百年论争的再审视
○薛晋文
当前,关于影视与文学关系的讨论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有的学者认为影视的基础是文学,文学对影视的母体作用不可动摇,将影视看作文学的衍生体和小兄弟而津津乐道。有的学者认为影视的基础未必是文学,影视若无法扔掉文学的拐杖就不会独立行走,寄人篱下的影视永远不会建构独立的艺术体系。其实,两种非此即彼的极端论断均不可取,爬在文学树梢上俯瞰影视的惯性思维有些不合时宜,早在1905年中国电影诞生之初,文学曾带着异样的口吻将电影唤作“西洋镜”或“影戏”,时过百年,谈及影视言必称文学的论断依旧铺天盖地,这多少有些“欺负”影视的味道。同样,站在影视屋顶上嘲弄文学寒酸的贵族心态要不得,毕竟文学作品曾为影视的繁荣立下过“汗马功劳”,电子媒介崛起并不意味着印刷媒介退场,兼容吸纳并为我所用是新媒介高效传播的明智之举。严格意义上讲,影视属于典型的电子媒介范畴,文学属于典型的印刷媒介范畴,倘若将两种不同范畴的媒介彼此混同而争论不休,本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倒显出了几分蛮不讲理。坦率而言,应将两者置于平等的位置去探究各自存在的优劣,方可对“百年论争”仍悬而未决的话题得出客观公允且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
一、两种媒介各有传播优势
文学作品本质上是一种时间艺术,是在时间绵延中按特定思维逻辑并借助文字符号建构的时间艺术。文学作品中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将人类的抽象思维进行了物化表达,连贯性的文字记录、浑整性的信息聚合与移植性的信息裂变使得文本内容远远大于媒介形式,对于信息的完整保存和思想的精深表达拥有极大的优势,而且阅读的主动性体验和个体性视角,让独立思想与自由阐释获得了较为充分的尊重,让精深思想的寻觅与深度共鸣的追索获得了充分满足。一位西方学者曾精辟地指出“书面文献将字词从它们的言者和它们最初的上下文中分离出来,削弱了记忆的重要性,允许对信息内容进行更加独立和更加从容的审视”。①由此可见,平面的时间叙事带来了线性阅读的文学传播特征,读者主要是以文字为载体想象复原故事情节并拓展延伸人物形象,需要经过想象的努力和感悟的专注,需要维持感觉平衡且投入丰富的想象力,方可实现从文字符号向现实生活的有形过渡和图景还原,思考置于感觉之上的阅读体验通常是理性化和深层性的,读者因自身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的差异,往往能在静观凝思和独立审视中,让文本内容更加丰富开放,让文本意义不断获得累积增值。例如,位列四大名著之首的《红楼梦》,其厚重深邃的文化内涵让无数文人驻足沉思,历代名家在解读中各显神通且各展其妙,至今无人能穷尽其博大精深的艺术气象,以至发出了“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林黛玉”的慨叹,但每一次阐释都是对艺术世界和实在世界之间各种可能性的挖掘与补足,都是在努力缩小文字符号创作中能指与所指碰撞后的疏离与间隔,也是对文本真实内涵的无限逼近与深度传播,而且这种传播活动是一种远距性或不在场的虚拟传播,在时空穿越与意义再生中引发了历代读者的极大阅读兴趣和阐释冲动。与此同时,文学作品的媒介属性注定了其传播的私密性与人际性,致使其传播范围、传播效果与影视媒介相比难以望其项背。
影视作品本质上是时空艺术,是按蒙太奇逻辑并借助视听符号延续的时空综合艺术。倘若说线性的印刷文字需要努力维持感觉的平衡方可有效传播,那么影视作品中声画直通感知神经的特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想象力的努力程度,感觉的不平衡削弱了文学阅读中经验的抽象性和想象的虚拟性。也就是说,立体的空间叙事特征和画面预设的生产特点,让文学作品中读者习以为常的线性阅读、从容审视和深度审美的接受习惯变得无所适从,扑面而来的是空间阅读、浏览瞥视和印象审美的欣赏习惯,直观逼真、生动具体的视听形象代替了想象虚幻、若隐若现的内心视像,观众主要以镜头为载体直观画面内容和注目事件变化,快速剪辑的运动画面很难让观众静默沉思视听内容的意义与价值,既定内容的单向高速传输,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交互对话的空间和余地。影视文本的开放程度和意义增值程度较之文学难以深度爆发和细腻呈现,特定的生产特征注定了影视传播中感觉和直觉的比重大于阅读中思考与凝视的比重,视听形象的大众性和普适性削平了文学传播中精英化和阶层化的接受门槛,影视艺术的大众化传播程度和化大众传播成效远非文学作品能及,将私密性的文学接受推进到大众性的新阶段,让人际性的专享获得了全民性的共享,视听的孪生、不在场传输特性突破了文学传播中的时空局限性,可以将传播效果无限放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大众传播媒介则不然,它们有巨大的能力使单方向的传播增大无数倍并且使它在许多地方都能收到。它们能克服距离和时间引起的问题。视听媒介还能超越发展中地区由于文盲而造成的障碍”。②譬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和《茶馆》在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不仅以乘数叠加效应拥有了几个亿的观赏群体,让遥远的观众都能欣赏到名著的视听盛宴,即使目不识丁的观众也能对视听内容略知一二。再如,四大名著经过改编影视剧和几轮翻拍之后,观众基数翻倍增加,恐怕一般的世界名著都难以企及,上述效应正是由于活动的画面和动作表情成为了主导性的传播符号,实现了文字向影像的飞跃转换,降低了文字符号的比重并弱化了抽象的传播效果,视听媒介具体化和形象化的优势在四大名著传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又如,许多躲在书店角落中默默无闻的文学作品,或许因为内容抽象而无人问津,或许因为故事平庸而被人遗忘,但它们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一夜间家喻户晓,恰是视听媒介生活化的表达、活灵活现的身体动作语言激活了那些孤独的文学作品,成为所谓的畅销读物而名噪天下,传播渠道的变化对此类文学作品而言扮演了救赎者的角色,传送媒介的置换让它们收到了意外的惊喜。
不难看出,影视与文学两种媒介既有竞争关系,同时也有合作关系。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影视制作中内容的预定特征和可操控性为文学作品的当代阐释注入了新的活力,人类进入读图时代之后,中华文化的传承显得尤为重要,如何实现传统经典文化的当代转换和当代阐释?是攸关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命题,对此影视与文学的合作共生至关重要,作为重要的时代媒介,它们有义务在合力共进中让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影视生产中的可控性让两者的合作共赢变成了可能。比如,新版电视剧《三国》中对曹操形象的公允评价和重新审视让人印象深刻,对千百年类型化的扁平历史人物进行了立体还原和深度修复,值得充分肯定。再如,新版《水浒传》中当阎惜娇(原名阎婆惜)的奸情被宋江发现后,宋江以豁达的胸襟写了休书并同意“成人之美”,这种巧妙的当代阐释,不仅无伤宋江英雄的整体风范,而且给人物形象增色不少,因为“宋江杀妾”固然正义凛然,但选择理性放手何尝不是成大事者的另一种坦荡胸怀?时代空气中弥漫的“以人为本”意识和“人性关怀”意味在这里隐约可见,而原著中的杀戮气息和尚武情结在新版《水浒传》中几乎不复存在。此类名著改编剧,借助影视生产的内容预设特征,将时代的价值观点和精神诉求熔铸其中并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获得观众广泛认同,让当代人的价值理想依托两种媒介的互补实现了相得益彰的有效传播,堪称影视与文学成功合作的典型范例。就此而言,作为时间艺术的文学作品与作为时空艺术的影视作品各有优长,在媒介发展的长河中正是有了各具特色的传播媒介形态,我们的艺术殿堂才更加五彩斑斓和丰富多彩。
二、叙事功能优劣清晰可辨
文学作品的叙事主要是借助文字描述故事情节、人物行动和环境背景,通过语言符号间接传达人物的情感波澜与内心体验,并依托读者的“抽象阐释”获得文本与受众之间的共鸣和通感。文学叙事有许多优势,它善于在文字内浓缩厚重深邃的思想,像孔孟经典中经常言及的“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仁者爱人”、“德不孤、必有邻”,虽然寥寥几语,其思想密度却博大精深;它善于将感情和思想蕴藉在叙事符号之中,让读者行走在“感目”、“会心”和“畅神”③的审美体验中如痴如醉,受众在主动欣赏和自觉认同中各得其所,阅读视角和阐释结论很难轻易被“他物”所操控和左右;它善于在叙事中采用完整的起止、递进的情节、间或的小高潮、立体多元的人物变化以及封闭的结构去讲述故事内容,因而戏剧化的叙事手法往往是文学作品制胜的重要法宝。当然,读者也可以控制文字信息传送的速度,在其需要反复咀嚼和重点思索之处自主“叫停”,可以“囫囵吞枣”、也可以“细嚼慢咽”,信息传输的速度和信息的流量尽在读者的掌控之中。
影视作品的叙事主要是依靠镜头的联接组合去表情达意,视听兼备的“具象感知”叙事替代了文学作品的“抽象阐释”叙事,蒙太奇就像语言文字中的“主谓宾”等语法那样,本质上是一种影视叙事的语法规则,某种意义上具有反文学叙事的特性,它将蛰伏在文字背后的深层联系,变成直观形象和通俗易懂的连续性画面内容,以往在文学中需要想象才能完成的“虚幻”形象变成了可视可听的“仿真”形象,需要思维再加工的万物声响变成了轻松悦耳的直感声响,需要冥思苦想去体悟的内心情感变成了逼真生动的动作表情。影视叙事的具体特征比较明显,其一、它具有较大的时空跳跃性和动作展示性,在叙事的缜密性和深邃性方面与文学叙事相比稍逊风骚,对此费瑟斯通有过精辟论述,“观众们如此紧紧地跟随着变化迅速的电视图像,以至于难以把那些形象的所指,联接成一个有意义的叙述,他(或她)仅仅陶醉于那些有众多画面叠连闪现的屏幕图像所造成的紧张与感官刺激”。④譬如,作为电视剧的《红楼梦》与文学作品的《红楼梦》相比,前者在叙事的集中性、视觉性和造型性方面优势明显,但在叙事连贯性、丰富性和深化性方面和小说相比还有不小差距。其二、叙事主体具有较大的主观性和渗透性,他们会根据自身的喜好和市场的口味更换和渗透叙事内容,如电视剧新版《红楼梦》结尾处“林黛玉裸死”的叙事情节,新版《水浒传》企图说服观众对“怜香惜玉”的西门庆和“风情万种”的潘金莲予以同情和谅解,这些都是叙事主体将自己的价值理想强加给观众的典型体现。其三、叙事的非理性倾向比较鲜明,影视作品往往将文学叙事中的完整起止束之高阁,甚至弱化故事背景、故事情节和人物复杂性,将新奇的构思、人物的动作表情和刺激的声画效果作为叙事的主要着力点,比如,根据莫言小说改编成的电影《红高粱》就是如此,它在当时不论对传统文学叙事,而是对经典电影叙事而言都是陌生化的“他者”形象。此外,观众对影视叙事的信息传输速度难以支配,特别是面对某些意味深长的镜头进行思索时无法驻足凝思,观众支配权的弱化对于影视叙事内容的深度传播是一种莫大的遗憾,同时观众对信息传送的内容难以形成有效回应,影视叙事的“中转站”特性和群体化传播特征,使得审美体验中的思索时空与交互反馈质量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然而,新媒介的出现并非意味着对老媒介的放逐,而是在相互渗透中实现了媒介功能的叠加与整合,在借鉴吸收中造出了一种新的媒介文化生命,因为“各种门类的艺术家总是首先发现,如何使一种媒介去利用或释放出另一种媒介的威力”。⑤蒙太奇叙事既承接了文学的叙说功能,又延伸了文学的表现功能。首先,影视媒介的出现解放了接受者的听觉功能,将印刷媒介时期只靠眼睛“单渠道”接受的视觉艺术,推进到主要依靠眼睛和耳朵“双渠道”视听接受的新阶段,“因此,视听媒介在传达一定题材、一定数量的信息上,要比单纯的听觉或视觉媒介要更为有利一些”,⑥它降低了参与者文化储备与思想积累的门槛,让大众文化的普及和意识形态的直接传播成为了可能,例如,电视剧《解放》、《辛亥革命》、《一九四二》,让无数基层观众因此而加深了对中国革命与社会演进的基本了解和常规认识。其次,影视叙事突破了传统文学叙事中严肃审美的范式,使得娱乐、刺激、宣泄、狂欢、感性等世俗叙事由边缘向中心跃进,当代社会的公共场域逐渐浮出地表,叙事价值取向更加多样和自由,叙事的自由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的自由。比如,以部分好莱坞歌舞片、警匪片、卓别林喜剧电影以及肥皂剧为代表的影视作品,它们依托世俗叙事将大众的娱乐诉求,以及宣泄欲望做了妥帖表达和积极回应,使得个体生命的灵魂栖息在世俗叙事中获得了安慰和寄托。再如,热播电视剧《幸福来敲门》,该剧在世俗叙事中叙说着有关幸福的家常琐事,但顷刻间引起了全民对幸福缺失现状的思索和追问,幸福话题成为了大众交往与互相倾诉的焦点媒介,幸福看似一个小话题,实际上属于一个时代大主题,由电视叙事引发的公共场域效应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再次,影视叙事的集体制作特性,让文学生产抵达了由个体创作向集体批量生产的新天地,以往充满私人性和神秘性的昂贵精神生产成为了普罗大众的共有物,在人人手握DV机的时代,全民精神生产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因为一个时代精神自由的程度往往是社会文明程度高下的晴雨表。譬如,一年一度的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各种中外DV作品大赛的热闹场景即是精神生产从“天上”回归“人间”的最好说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和生活褶皱进入了影像艺术世界,影像媒介给他们带来了许多温暖和救赎,由于叙事媒介的变革,以往需要仰视和跪拜的精神生产逐渐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也许一种感官的解放会伴随着另一种感官的萎缩,影视叙事在延伸视听感官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弱化了文学叙事的某些优秀功能。例如,面对像李清照诗词中“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样复杂的内心表达,当下的影视叙事显得捉襟见肘,有时能借助独白和音乐去实现直接表达和间接烘托,但思想意蕴和精神内涵多少有些打折。再如,遇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样充满哲理意味的诗句,影视作品多使用理性蒙太奇去予以表现,倘要深刻阐释诗人内心孤独迷惘的博大情怀,对于蒙太奇叙事而言有些犯难。又如,像《阿Q正传》那样意蕴深邃的名著,用镜头组合演绎的视像与语言文字建构的小说相比还是让人意犹未尽。事实上,视听艺术完全有能力进行深度表达和理性叙事,同样可以承担为生活提供意义的重要功能,⑦如电影《公民凯恩》中“玫瑰花蕾”的隐喻蒙太奇,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姿态各异的石狮组成的隐喻蒙太奇至今让人拍案叫绝,只是这种深度叙说能力有时被资本逻辑和娱乐至上掏空了,有时被传统文学话语所误解了,让世人误以为视听艺术就是浅表文化的代名词,以至有人发出这样的感慨“小报里没有任何东西称得上是《李尔王》这样的悲剧,但它可能是电视时代合适的文学”。⑧总之,文学叙事不等于影视叙事,文学叙事功能的蜕变是媒介发展的必然趋势,影视在接续并延伸文学叙事的同时,也应该正视叙事中平庸化、低俗化和拜金化的误区,只有这样才能在媒介整合中实现自身的高效传播与深度表达,这抑或就是媒介更迭的辩证法。
三、剧作与文学不应简单混同
文学作品是影视剧作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外许多优秀的影视作品改编自文学作品的不在少数,文学确实给了影视艺术许多滋养,尤其是故事性、动作性和表现性较强的文学作品更容易获得制作者的青睐和光顾。在我看来,少部分还保留着文学语言,具有情感丰富性和思想深邃性的剧作依旧是文学,比如,像英格玛·伯格曼、佛朗索瓦·特吕弗的剧作就是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他们不仅用文学的语言进行创作,而且内蕴着浓郁的文学情感和思想精神。然而,许多源自文学改编的剧作已不再是文学作品本身,尽管他们都富含“文学性”,但“文学性”不等于“文学”,“文学性”的阐释各有千秋,本文认为其主要是指特定社会历史文化的思想内涵与价值意义的总和。而“文学”是指以语言文字为媒介符号、依托特定语法规则以及叙事手法反映人生的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包括小说、散文、戏剧和诗词等诸多表现形式,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文学性”等同于“文学”,它们正确的关系当是,文学需要剧作去拓展其普及空间,剧作需要文学性去提升其艺术品质,剧作未必是文学,但剧作不能没有文学性,没有文学性的剧作必将滑向粗鄙和浅俗的另一端。一句话,文学性不只是优秀剧作的灵魂,更是一切优秀艺术的灵魂,文学性的覆盖范畴远远大于文学作品本身,将文学性视同文学是典型的常识错误。鉴于此,将文学的头衔强行赐予剧作显得有些牵强和霸道,对此学界早有不满,“在戏剧、电影、电视剧这种主要以空间和身体的技术诉诸视听并通过所有观众进行选择观看的艺术领域,剧作可以是文学,但不必是文学”。⑨
事实上,依据影视生产规律和传播规律编织而成的剧作,使得原先连贯缜密的故事变成了跳跃性的片段情节、原先抽象性的阐释变成了形象性的描述、原先立体多元的人物变成了直观可见的人物、原先细腻的心理变成了可直接读解的表情,影视画面对动作性、造型性和展示性的视听拍摄需要,将人生与人性的复杂性、丰富性做了简单化和浅俗化的处理,文学作品中富含的语言美和思想美遭到了放逐与稀释,作为文学重要本质属性之一的语言美被直白浅陋的说明性文字所取代,没有了文学语言的媒介载体,其文学本体属性多半是空心的躯壳。上述变化,不是一种机械简单的删繁就简,而是视听符号对语言符号的粉碎与再造,这种变化不是形式和表层的变化,而是本质和深层的涅槃,是一种基于解构基础上的艺术重构活动,其中必定若隐若显地存在着“文学性”,但媒介符号和媒介载体的双重转变通常会带来媒介形态与艺术审美标准的本质变化,媒介结构的转变最终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与文化形态的巨大变化,所以,此时的影视剧作距离真正的文学作品越来越远。比如,电影《红高粱》的剧本主要是以地点场景的变化统领故事情节,不仅将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进行了简化,将主要人物的命运轨迹做了大尺度的改动,而且只选取小说的部分精神内涵进行放大和表现,经过“伤筋动骨”后的小说只剩下粗线条的轮廓,以及“颠轿”、“野合”、“抗日”等动人心魄的场景,即便如此,这样的剧作依然蕴藉着文学性和思想性,但文学的媒介结构与本体符号早已被肢解和置换,造型性和视觉性占据主要地位,运动性和节奏感十分强烈,视听思维和影像意识主导了一切,再将其等同于小说本身实在难以让人信服。
再往深处说,部分影视作品倘若被还原成剧本,再以文学的审美眼光去看,会让文学爱好者乘兴而来失望而归。比如,像《阿凡达》、《第五元素》、《2012》这样的经典好莱坞影片如果被还原成影视剧本,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叙说很少,大多是简单的说明性对白话语,然而,大量惊险刺激的超现实体验、视听奇观的震撼性场面和精妙绝伦的视像创意,让观众在现实与未来的穿越张力中流连忘返。再如,像《速度与激情5》这样的惊险动作大片,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主要靠极速飙车、警匪追逐、硬汉对决和惊悚枪战编织而成,其中没有多少“文学”的精华元素,引人思索和想象的文字少之又少,假如还原成剧本恐怕连三流小说的水准都够不着。上述两类影片横扫全球票房与口碑的确凿事实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其说此类电影剧作的基础是文学,不如说是天才般的艺术创意更为准确深刻,这是形式设计和内容表达之间的独创组合与相得益彰。影视创意简而言之就是拿什么样的形式去创造性地表现什么样的内容,好的影视创意不是模仿克隆,也不是天马行空般的乌托邦,而是基于现实和理想的视听化与艺术化表达,背后潜藏着艺术家的深远想象和新颖追求。具有独创精神的上述影视作品并非仅仅靠感官刺激取悦观众,剪辑流畅的画面同样指向哲学和美学,它们同样具有主题思想,而主题思想正蕴藏于艺术创意的审美观念中,也就是说,潜伏在影像之下的人生与社会真谛正是它们穿越时空的永恒支撑。在全球影视竞争格局中,得创意者得天下,好的创意根本上讲是艺术形式(节奏、风格、技巧等)与生活内容(个体、环境、政经等)之间的科学配方与绝妙隐喻,这是欧美影视多年来笑傲江湖的重要秘籍所在,正如罗伯特·麦基所言,“他们之所以出类拔萃是因为他们选择了别人没有选择的内容,设计了别人没有设计的形式,并将二者融合为一种不会被误认的、只能属于自己的风格”。⑩我们倘不能尽快走出重故事内容、轻艺术创意的审美误区,难以割舍重“语言文字”、轻“视听符号”的价值偏好,无法赋予影视媒介合法体面的身份与名分,甚至无视“鸠占鹊巢”的霸道做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中国影视在国际舞台上恐怕难有大作为和大出息。
落笔至此,影视的崛起势不可挡,“电视在所有先进的工业化国家里已成为主要的公共机构,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也迅速如此”,(11)与此同时,文学的转换提升也迫在眉睫。我们不必再纠缠于非此即彼的无休止争论而内耗不已,跳出影视看影视或者跳出文学看文学,得出的结论可能更加心平气和与客观公正。其实,文学天生未必是博大精深艺术的永恒代表,随着网络文学和集体写作的强势崛起,文学的大众化和世俗化再所难免,文学不应在自暴自弃中跟着感觉漫无目的地随意滑行,应在借力影视媒介和网络媒介中重新找回昔日的自信与威力,媒介的更替越快,越需要文学乃至文学性健步跟进为新媒介提供内容与材质。影视天生未必是浅薄浮泛艺术的特定代表,影视同样有能力去承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担当与文化使命,同样可以表达深刻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内容,影视的社会属性注定了它必须以艺术性的画面去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不应在过度商业化的操控中放弃了自我的无限潜能和种种可能,任何鄙弃思想性去单纯迎合人们快感需求的影视作品在风靡一时之后,很快会被人无情地扔进历史的垃圾堆而长久遗忘。综上所述,影视与文学各展其长、有效互补并共存共荣是当代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发展的希望所在。
①参见罗杰·菲德勒《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明安香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②⑥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陈亮等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126页,第123页。
③参见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④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⑤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89页。
⑦参见周宪《审美现代性批判》,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⑧理查德·凯勒·西蒙《垃圾文化》,关山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⑨李道新《剧作不必是文学》,载《文艺报》,2010年6月2日。
⑩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周铁东译,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版,第10页。
(11)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张永喜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