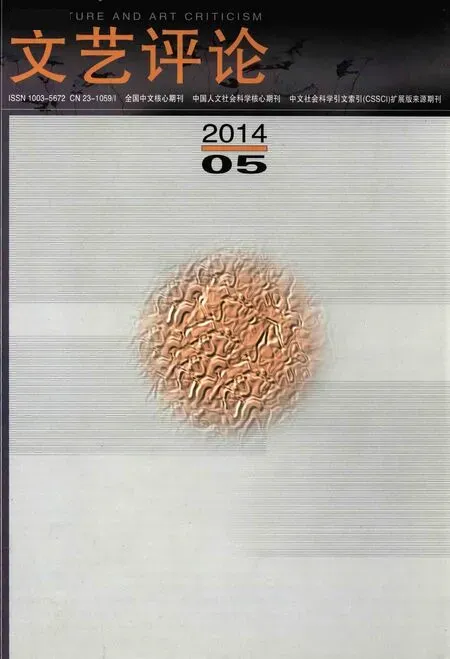寻找汉语诗歌的独立品质
○张曙光 吕智博
把新诗的精神和建设放在它的源头来考察,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新诗的发展脉络。还有一个更大的背景应该提到:一百年前的1913年,被认为是欧美现代主义运动的开端。在一本《1913:现代主义的摇篮》的书中,作者让-米歇尔·拉巴泰向我们描述了当年的场景,他说,“每当一个旧的规则被打破时,新的道德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便随之兴起。这种创新常常是作品表现出来的一种模糊不清的求新欲”。很难说新诗的诞生是受到了这场现代主义运动的影响,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影响确实显露出来,并且在不断加大。
因此新诗的成长,有着来自自身新文化运动和西方现代主义运动两个方面的推力。同样可以从中看到两条较为清晰的轨迹,一条是外部的,即逐步建立起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新的诗歌形式,另一条是内在的,就是现代性的实现。
关于现代性,学者们有过诸多的解释。文学的现代性,简单说,无非是要站在时代精神和审美的制高点来观照当下的生活,并用相应的方法来加以表现。现代性不仅体现在艺术的形式和手法上,同样渗透在词语体现出的意味中。在我看来,现代性除了使文学更加切合这个时代,也是为了达到文学最原初的目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表现真实。真实无论是否被作家们在写作中所强调,但确实构成了他们作品的共同点,甚至可以说是他们写作的终极目标。当然巴尔扎克有巴尔扎克的真实,卡夫卡有卡夫卡的真实,普鲁斯特有普鲁斯特的真实。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作品中努力体现所处时代的风貌和本质,以及人类的生存境遇。新诗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在求新求变,处在对传统的反叛和不断地自我否定中,恰好是为了适应这种真实,实现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
因此,谈到新诗的精神和建设,似乎应该围绕着现代性而展开。新诗的精神内涵在我看来,应该是自由、开放、反叛和人性的。对现代性的强调使诗歌与时代的联系更加紧密了,也使我们具有了一种世界的眼光,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的诗歌处在相同的起跑线上。这样说多少显得有些乐观,新诗还有很多问题,也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去做。在形成了一个基本格局之后,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实现汉语诗歌的独立品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诗的形式和手法主要是从外国诗歌那里学来的,也包括诗学理论和观念。这是求同,是要融入世界文学潮流并掌握共同的游戏规则,但作为个体存在所必不可少的独立品质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古典诗歌倒是有自己的独立品质,但不适于表达现代经验,变成了僵死的东西,因此被抛弃。当然新诗由于其中固有的本土经验和文化而多少具有了自己的一些差异性,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美学上的建树。因此,新诗走到今天,建设的难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大。
汉语诗歌的独立品质,应该就是在写作中体现出的独特精神气质和艺术个性。这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非常重要,对于一种语言的写作来说这也同样重要。有人说艺术个性是自然形成的,当然是对的,但清醒的、有意识的艺术追求也同样重要。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一个较为完整的现代诗学体系,一种既有现代意识又有自己独特文化气质的诗学体系。就写作的个体而言,当然是越独特越好,千人一面总是令人厌倦。每个诗人都应该充分表现出自己的个性,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建立诗学体系,并不意味着要取消诗人的独特性,而恰好是建立在这些独特性之上,也将使独特性变得更加突出。现代社会使人丧失个性,无论是全球化的影响还是其它,对抗全球性弊端的最好方式就是寻求和保持差异性。在今天,仅仅凭着感觉写作是远远不够的,诗人们在个性的形成和诗艺的探索上应该更具自觉性,同时要有理论上的支持和跟进,明确自己的写作观念,深入理解写作与时代的关系,审美与真实的关系,个体写作与整体写作的关系,以及主流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我想今天的思考应该回到原点,就像现象学所提出的那样,把既有的成见搁置起来,对一些与写作相关的问题重新做一下梳理。首要的一点是要深入理解我们这个时代,处理好写作与时代的关系。不仅要清楚这个时代的本质,存在的问题,它的真实的幻象及带给我们的焦虑与影响(这将是写作的原始材料),也要了解它的思想文化和审美风气,在这个大的语境下深化对诗的认识。在这个媒体时代,诗歌有自身的约定性,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诗中找到某些共同点,但在不同的时代诗确实会发生变化或偏移,或者说,针对不同问题和审美风气诗歌会做出不同的反应。比如华兹华斯说诗是情感,里尔克则说诗是经验。两人都没有错,诗还是诗,但却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诗学观。这不同是时代造成的,也是形成不同流派的基础。正如巴雷特所说,“任何一个信徒,不管他多么虔诚,即使他具有堪与但丁媲美的才华,今天也写不出一部《神曲》来。幻象与象征对我们不再具有它们对这位中世纪诗人所有的那种直接而有力的现实性了”。一首好诗是创造力加上对诗的深入理解而产生的。创造力要建立在对诗的深入理解上才有效。不幸的是年轻时有创造力却缺少对诗的理解,到了能够理解时创造力又开始减弱。因此一个有效的诗歌观很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发挥创造力。但我们应该建立起一种怎样的诗歌观,既符合这个时代的审美,又适应我们文化自身的特质?这不仅是批评者也应该是写作者首要思考的问题。
诗与时代的关系很容易被片面或机械地理解。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诗歌是时代的产物,另一方面也要清楚并不是所有诗歌都必须介入现实。诗歌既有介入的一面,也有超越的一面。缺少了后面的特质,诗歌就不完整。正如马尔库塞所说,“艺术的政治潜能在艺术本身之中,在作为艺术的美学形式之中”。甚至“仅存在于它的美学方面”。李白和杜甫同样伟大,少了他们中的一个,唐诗就不再是我们心目中的唐诗。当然还有一个更好的例子,那就是陶渊明。
其次是写作与传统的关系。现在有些人经常提到原创性,如果就某种写作倾向来说并无不可,但严格意义上的原创性是否存在就有些可疑了。脱离传统或共同语境创造出诗歌的例子即使有,有多大意义也很难说。说现代诗是在两大传统的影响下写作,也显得多少有些笼统。两个传统是客观的存在,但在不同时期的影响或强或弱,或隐或显,不能等同起来。相比之下,传统诗歌在很长时间内对新诗的影响应该是处于弱势或隐性。直到近些年来,一些诗人开始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中国古典诗歌,并试着从里面发掘出写作的原素。如果说最初对古典诗駣用极端手段是为了保证新诗的方向即现代性的实现不受干扰,那么今天把目光转向传统诗歌说明新诗已变得成熟而自信,有能力从异质或相反的东西中吸取有益的成分而不必担心受到消极的影响——尽管后者仍然存在。新诗应该有更开阔的视野和胸怀,这样才有助于形成自身的独特性。尤其是这种独立品质的形成并不完全是外在的,更多依赖于内在的精神和气质,而中国古典诗在这方面恰恰可以提供参照。
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人们喜爱的更多是在写作中融汇两种文化中的诗人,如米沃什、布罗茨基、沃尔克科、扎加耶夫斯基、阿多尼斯和达维什等。喜爱他们的原因可以找出很多,但最突出的是他们的作品中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和焦虑表现得更当强烈,也包括他们诗歌技艺中本国传统与域外手法的交融。融会不同传统并不是优秀诗人的先决条件,却无疑是一条值得重视的成功之路。但无论学习和借鉴国外诗歌还是中国古典诗,都应该是内在的和深入的,取其精义,而不应该停留在浅层次的照搬和模仿中。尤其是对中国古典诗歌,更需要用现代性来观照,找出另适合于今天的元素。借鉴中国古典诗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无论是陶渊明、杜甫还是其他诗人,和新诗都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语言方式中,很难直接拿来。处理不好,就会或变得半文不白,或由于文化上的亲和力而迷失在陈旧的意识和趣味中。食古不化和食洋不化同样有问题,或更糟。钱钟书曾讽刺某位宋代诗人用陶渊明的眼光观看自然而没有了自我,王国维在评纳兰容若时也曾说,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也,说的问题约略接近。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后来,因袭太多,意识和语言都变得陈腐,既使不遭遇新文化运动也是要陷入困境的。胡适对旧体诗的批评虽然过激,但不无道理。这些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如果说今天的中国诗人用国外同代诗人的眼光看待世界固然有问题,但用古人的眼光和思想来观照则更糟。继承和借鉴与复古如果混为一谈,效果就会适得其反。
因此,这里提到的所谓精义,不是简单照搬,不是皮相的摹仿,而是从艺术和审美上把握其精神实质。我们了解一种写作风格和流派,不仅要知道它的思想观念,以及它是如何产生、如何发展的,也要放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这样也许可以更加清楚它的独特性,看出哪些适合我们哪些不适合我们,可以避免盲目照搬。我想这点无论对国外诗歌还是中国古典诗歌都适用,否则我们的诗歌就会真的变成了一场摹仿秀——西方的或古典的。西方诗歌在与时代和现实的关系上,在形式和手法的不断创新和实验上仍然值得学习。而中国古典诗中有很多的杰作,在理论和方法上也相当丰富,如讲求格调,注重意蕴,简洁含蓄,意在言外,这些可能正是需要我们继承的而又正好被我们所忽略。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古诗十九首》中的直接质朴和体现出的风骨和生命意识,以及陶渊明诗中的豁达和蕴藉。《诗经》的清新活泼也是我所欣赏的。关键是这些属于风格和内在气质的东西如何纳入我们的诗中?尤其是古典诗歌中的“意”及有别于西方诗歌的表意方式也是近期我所关注的。
再就是对语言问题的重新认识。我们对诗的语言的理解多少有些狭窄,一谈到语言,无非就是文言还是白话、书面语还是口语。但诗的语言所包涵的内容应该更为宽泛,句法、音韵、语感、修辞及与表现力相关的技巧都在其中。在这些方面我们有过一些探索却没有很好的总结,严苛地讲,在这些方面的探索也仍然不够。现代汉语用于诗歌只有不到百年的历史,显然还不够成熟。就说句式,现代汉语大多的句式过于简单,固然容易做到简洁,但要表达更严密幽曲的意思就力不从心了。恰当的句式可以使语义变得更加突出,也有助于风格的鲜明。弥尔顿的一首十四行诗全诗下来只是一个完整句子,给人一种浑然一体的感觉。金斯伯格在人们眼中是一个不太注重诗歌技巧的诗人,他的《嚎叫》的第一部分上百行在中译中被译成了一连串的排比句,而原诗只是一个大的定语从句,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一堆散乱的菜叶,一个是叶子紧紧抱在一起的白菜。这些在汉语里面就很难做到。我读到一篇文章,谈及国外诗歌,说汉语诗中最强烈的作品也很难与外国的比肩。这当然是由民族性格和气质造成的,但我想也应该与语言不无关系。了解国外的文化,不是要寻找到本国也有的或不如自己之处来增加自信心或满足虚荣心,而是要学到不同的东西来丰富自己。常有人批评现在的句子欧化,反驳者成功地指出他们批评欧化的语言同样欧化。这里并不存在知识版权问题,关键要看是否有助于汉语表现力的增强。还有音韵、语感以及最新的流行语和网络语言,这些都应成为当代诗歌的资源然而却缺少深入的研究。诗人依赖语言,也对语言负有责任,除了净化语言,也要丰富语言。海德格尔说过,日常语言是死了的诗的语言,这是因为日常语言把其中包含的涵义损耗到了最低值。在诗人那里,一切语言资源都可以用在诗里,并使之在其中发挥作用。诗人能够最大限度地丰富语义,把日常语言变成诗的语言。诗歌创造性使用语言。正如艾略特所说,诗歌的每次变革,都是日常语言的回归。当代诗在语言方式上的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我们从歌唱转为了说话,从夸饰的描写转为了日常细节的叙说。或者说,诗歌从摹拟音乐转为摹拟日常说话,这种转变的深层动机是什么,值得思考。语言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创作,另外的问题是——至少对于我来说——是使用一种自然明晰的语言,还是使用模糊、繁衍的以及持续和自我重构的语言更为适合今天的写作?
创新也仍然值得关注,它的对立项是守旧或因袭。目前的诗坛显得有些沉寂,不是写诗的人太少,而是真正锐意求新、大胆探索的作品并不多见。先锋在今天只是一个标签,可以随意贴在任何一个诗人身上,哪怕他的写作既无反叛性也无实验性。这种局面与一百年前生气勃勃的新文化运动不能相比,与当时西方轰轰烈烈的现代主义运动更是无法相比。无论我们怎样评价先锋派和学院派,但中国并没有真正意义的先锋派和学院派。激进的文学态度和对形式技巧的均衡控制在今天显得稀缺。缺少创新注定会缺少活力,无论社会还是艺术。今天仍然需要大胆的实验,但要思考什么是新,怎样的创新是必要的,又该怎样去创?路有很多条,关键要看你想去哪里,没有相应的方向创新就会变得盲目。还有另一些非常重要的写作元素应该进入我们的视野,如格调,境界和风格等。
上面是对新诗的一些思考,涉及到一些常识性的问题。在中国,很多问题的讨论都绕不开常识打转转,或纠结在一般常识上,比如你一谈到诗歌的建设,他就说诗是个人的东西。诗歌的个人化当然重要,但这个人化不是封闭产生的,而来自更多的交流和对诗歌发展的整体把握。离开了这一点,个人化就无从说起。这种连基本常识都搞不清楚的状况并不利于诗歌的发展。上面提到了两种传统,还有一点容易被人忽略,那就是除了这两种传统外还有另外一种传统,那就是新诗自身的传统。无论我们怎样对待这个传统,都要很好地对它进行思考和总结。我们也同样应该意识到,诗人受惠于诗歌,也同样对诗歌负有责任,除了严肃写作外,也应该经常问问自己为诗歌做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