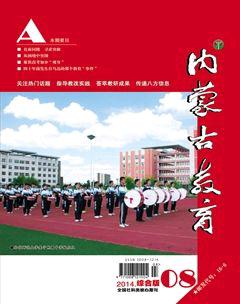教书与种地的类比
李世开
对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兵”来说,就“备课”而言,不但耳熟能详,而且是有感而发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教小学低年级语文。一天,校长和我说下周有外地的领导及骨干教师要来听一节课,学校暂定你来承担。我战战兢兢地应允下来。先是组长召集本组人员商定讲哪一课,后是教导主任提原则要求,再后来是全体语文老师拿初稿,作比较,讨论出一个初步的方案。我把那节课的方案拿复写纸写了十来份发给有资历的老师,让众人找毛病、“挑刺”,定下了讲课的“坯子”,用现在的时髦说法就是“集体备课”。
两三天的工夫,我脑子里全是这些程序内容,校长又把县教育局教研室的两位五旬老人请来作最后的定夺。隆冬时节的办公室,学生放学后炉子也就“下班”了。两位老人看完教案后先让我对着他们试讲一遍,一位做记录,一位看时间,完毕每人又提了N个意见。于是我再按老专家的意见修改,并仔细推敲每一个细节:怎么出现生字,象形字与形声字该说到什么分寸,哪个时候组词造句,学生可能怎样呼应,等等。
“不行,小李,咱们还得来一次!”听到这严肃且不容置疑的话语,肚子饿脚板冻的我满脸不高兴地嘟囔了一句,“不就是学几个生字吗,吃点饭再说吧!”一位刘姓长者笑嘻嘻地顶了我一句,“我们吃饭了吗?”
哎,没办法,该咋呢,再来吧。又一遍“课”下来,已是九点多了。——隆冬的九点是什么时候,读者都明白。这时两位教研员才面露喜色地说:“暂时就这样吧!”
讲课那天,一进教室,面对黑压压一群听课者的确有点紧张,但程序娴熟、胸有成竹的我顺利地按“教案”完成了教学任务。一节获得赞誉之声的公开课,让我内心感到:成功来自精心的自我准备、同事的合作,还有行家的帮助、指点……
时代在进步,备课这点营生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上世纪末,市场上有了多种版本的“教案”,为了方便我也买过几本,课前粗略地看一看,课上照本宣科,结果大相径庭:看是很好的方法,一拿到课堂上就不灵验了,不是这个环节不紧凑就是那个过程脱离学生的认知水平……于是我还是回到现实中,静下心来仔细研读课本,结合班上学生的实际,写出恰到好处的教案,课堂上用起来得心应手。
如今我也早不登讲台了。年轻教师们的“命真好”, 碰上网络时代,常见不少老师备课时上网查一查,哪一章哪一节哪一课,山南的、海北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然后一连打印机,“自己”的教案就“写”好了——下载现成货,省时省劲。
一位种地把式告诉我亩产比别人多的真谛——头年秋天就翻一遍地,春耕时施足底肥,然后选籽下种,及时查苗、间作、锄草、浇水、灭虫、收割、拉运、碾打、晾晒、收储,一个程序挨着一个程序的忙碌,一点儿也不能马虎偷懒。
完了,这位老农又极认真地补上一句:“要是人哄地一季,地就哄人一年!”
我不禁联想到备课讲课,教书育人,不也是这个“理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