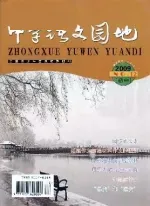《登高》的诗境形态解读
滕 越
[作者通联: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我们已经习惯了在一个平视的世界里生活。而杜甫的《登高》这首诗,却给我们换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视点,在山边、在水涯,才会真正体察到,天高地迥,顿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的诗境形态之美。
杜甫在他生命将尽前的第三年(唐大历二年,公元767年)登上了夔州长江之畔的一处高地。此时正值重阳时节,满目秋景触发了诗人的悲情,于是一首冠绝千古的七言律诗便横空出世:“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这是一首拔山扛鼎式的悲歌。全诗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前四句写景,景中有情,重在勾画悲秋的景致形态。后四句抒情,情景相生,尽吐苦恨的情致形态。我们从文学形态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作的意境形态。
一、景致形态:悲壮之气冲天起
这首诗作是以特定的视角来叙事化描述诗境形态的。诗的前四句先写景境形态,诗人一俯一仰,一近一远,运用视角转换的方式为我们叙述勾勒出一幅萧瑟秋景图。风、天、猿、渚、沙、鸟、落木、长江,八种景物形态交替呈现,构成了一组别具景致形态的意象群。
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这是何等靡丽的意象形态!风是急风,天是高天,哀哀的猿啸之声在耳边回荡,清朗白净的沙洲之上有宿鸟在飞旋。作者不是孤立地为写景而写景,而是远近对举、高下相称,把动静声色等形态融注于字里行间,在景境里倾注进自己内心深处的情感体验。“风急”二字,首领全篇,极为紧要。一个“急”字,赋予了原本无形的风以动感、声感和触感。秋天本来就是个容易起风的季节,更何况这风呼啸在江边、怒号在高处,吹打在万里飘泊、年老多病的诗人身上。身体的冷和心里冷叠加在一起,凉入骨髓。急风似乎要裹挟着诗人的命运,一起走向穷尽。“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抬头问天,却发现视线尽头那片深邃的蓝色是那样遥远而冰冷,秋日的天高得不近人情,高得难以企及。天地之间,唯余一人而已。空间上的孤独,心灵里的寂寞,便在这“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中愈加凸显。此时,一声声猿啸划过诗人耳边。夔州一带多玄猿,曾经有过这样一首渔歌:“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跳跃的黑色身影在因风战栗的树丛里若隐若现,猿猴凄切的叫声在峡谷间被风扭曲、拉长,愈显凄厉。“啸”和“哀”,不仅写出了猿鸣的声感形态,也传达出了诗人心中抒不出的悲愤和散不尽的哀愁。第二句诗人视线下移,落到了江面上。沙洲很清朗,细白的沙子扑在岸上。风动波起,粼粼的水光里,小洲仿佛能随波摇动,白色的沙粒卷出一个个漩涡,迷离在风里。凄清的色调融着朦胧的感觉,浸染出一种苍凉的视感形态。然后,诗人又抬起目光,看到了在江上飞动的鸟。由于风急,鸟很难挥动翅膀、控制方向,“回”有“飞回盘旋”之意,准确而生动。这让诗人不由得想到了自己——“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他又何尝不是急风中高天下吃力盘旋的孤鸟!不,他还不如这“飞回”的鸟,鸟飞倦了还可以归林,他在外漂泊了8年早已无家可归。
如果说首联14个字描摹的多种景致形态,联缀起来如同一幅细密的工笔画,纤毫毕现,那么颔联点画的落木和长江的景致形态,便渲染出了一幅秋意十足的写意图。诗人从大处落墨,把俯视所得之二景如特写镜头般摄入笔下:上句写山景,承“风急”而来,自上而下、承天接地。“无边”延展了空间,放大了思绪。用“落木”而非“落叶”,从重量、质感和颜色上便有所差别。“落木”重而粗糙,带着象征着衰老的棕褐色;而“落叶”轻而平整,或许还杂着几许未尽的绿意。叠词“萧萧”,借窸窸窣窣之声,状落叶纷飞之形,尽秋意正浓之态。人活一世,草木一秋,萧萧而下的落叶背后,是同样无奈着生命之短暂的诗人。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70年,终年58岁,此时已是767年,离他生命终结只有三年了。这随风急转直下、飘忽不定的落叶又何尝不是在为诗人奏着一曲生命的挽歌!下句写江景,接首联次句,自左而右、横贯东西。“不尽”应和“无边”,不仅指空间上的长江水流一眼难尽,更反映出时间维度里,历史长河的浩浩汤汤。“滚”字相叠,叠出了江水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动态和声感,叠出了浑厚恢弘的景致形态。人类生命的永恒和个人生命的短暂在这景境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生百年,有生有死,诗人已经了然。“无边落木萧萧下”,老去的是年华,凋敝的是历史;“不尽长江滚滚来”,载着千古多少事,扑面而来的是未来,是一代一代不可阻止的更迭。千百年后,我们再读这一句诗时,心胸也随着滚滚而来的长江水为之一开,应和着萧萧而下的无边落木,一叠又一叠的气势相合,悲壮之气冲天而起。
二、情致形态:艰难苦恨悲难诉
景与情是诗境生成的基本要素,在景致形态构成的境域中自然生发出特定的情致形态。我们面对着诗人苦恨难诉的情态不禁发问,为什么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天,在杜甫《登高》的诗境里是这么悲壮,让我们直想流泪?答案就在诗的苦恨情致之境中。“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宋代的罗大经从这一联里勾出了八层悲情形态:“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凄惨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杜甫的老家在河南巩县,而他现在却在离家万里的重庆夔州,相隔万里之远,怎能不悲!此时他已经在外漂泊了八年,接下来的三年,他还将继续漂泊下去,最后贫病交加,死在漂泊的船上。他的“作客”,是真的“常作客”,怎能不悲!时至秋天,秋风萧瑟,草木摇落,秋江滚滚,天高水远,猿啸鸟回,怎能不悲!人生百年,匆匆而逝,烈士暮年,行将就木,怎能不悲!眼瞎耳聋,手臂僵硬,贫病交加下的身体早已连一杯酒都无法承受,怎能不悲!重阳佳节,本该一家团聚,登高饮酒,可自己漂泊在外,无亲无友,只能独上高台,怎能不悲!战乱阻隔了亲情,时光催老了年华。此时的杜甫,已不是当年那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意气青年;此时的大唐,也已不是当年那个“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的盛世大唐。“安史之乱”虽然已经结束四年了,可朝廷元气大伤,边境动乱频仍,百姓还在水深火热中挣扎。诗人更是“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离家万里,又值悲秋,异乡异客,时间久远;百年将尽,年老多病,无亲无友,重阳登台,怎一个“悲”字了得!这层层重重的悲情形态之境,叠生成难以消恨之愁,令我们为之深深地悲叹。
漂泊之悲愁,老病之悲伤,家国之悲哀,构成了特定的悲情诗境形态之美,也凝结出了这首诗尾联的起首四字——“艰难苦恨”。这四个字是一种内心撕裂的情致形态,也是一字一顿的倾心发泄,含了多少血泪!国家和个人的命运太过“艰难”,种种的悲意只能“苦恨”以对。“苦”是“极其”的意思,这“艰难”招致的“苦恨”之情当有多么折磨人,生生地让诗人两鬓如霜的白发与日俱繁!叹一声“潦倒”,叹一声“潦倒”,重阳节高台上,“独酌无相亲”的,有他一人就够了,万千的愁绪,就都付与这一杯菊花酒吧!诗人抬起手,斟满杯,却在即将饮下的那一刹那,僵住了。常年的漂泊摧残了他的身体,老病之躯早已无法承受哪怕一杯浊酒。轻轻地放下杯里唯以解忧的杜康,原来他连“举杯销愁愁更愁”的机会都没有啊!诗人手中的“杯”,又何尝不是心里的“悲”,那快要溢出来的悲愁随着一个“停”字,又被诗人尽数咽下——诗已尽,而悲却郁结在他的心中,郁结在悠长的历史里。显然可见,诗境中的这种细腻而又跃然生动的情致形态,是一种极致刻画的诗情之美。
三、心灵形态:人间高处悲中爱
杜甫的律诗具有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这根源于杜甫丰富复杂、磨难辛酸的生活阅历和他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深重情怀。当这种情感与壮阔的景境相遇,就取得“异质同构”的审美对应关系,构成了深邃的心灵形态与境界。诗人溶身于境,以系统的观点看待事物:既看到意象的彼时彼境“共时态”形态,也不自觉的看到诗人自己情感经历的“历时态”形态发展变化,凝聚成诗,不仅仅是物化,更是升华。情由景生,景为情设,天然混成、错综交织。给人的感受不是悲哀而是悲壮;不是消沉而是激励;不是眼光狭小而是心胸阔大。这是一种景境和情境融注构成的特有的心灵形态。
为什么同样是登高,同样是大唐诗人,杜甫不能像李白那样叹一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然后潇洒地一转身,去寻天上的神仙?为什么不能像王维那样,建一座终南别业,过那种“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自由生活?除了际遇不同,他们的视点也不同,而视点正是心灵形态的反映。李白的视点在现实之外,他的诗境里追求的不是人间的规则,而是生命永恒的超越。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王维的视点在画里,纵然官至宰相,他心里记挂的仍是他的终南别业。因而他的诗境形态同他的画一般,美丽而平和,充满了禅意。和他们相比,杜甫的视点更为现实。他称自己为腐儒,纵然境遇上穷困潦倒,但满脑子都是儒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被这种忧患意识驱赶得时刻都处于内心紧张状态。在这种心灵形态的观照下,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成了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登高,不仅是身体状态上的登高,更是作者心灵形态上的登高。我们无法评判李白、王维、杜甫三人的视点孰高孰低,因为他们每个人都代表了一种生活方式,都对这个世界上不合理的东西做出了抗争。可在笔者看来,杜甫,让我们尤为感动。所以,李白是天上的诗仙,王维是山里的诗佛,杜甫是人间的诗圣。圣人的眼里,常含悲悯,圣人的爱,在阔大的心灵形态中内含着大爱无声!或许,后人称《登高》一诗为“古今七言律诗之冠”(胡应麟《诗薮》),不只是因为此诗“句句皆律,字字皆律”,用句用字“皆古今人必不敢道,决不能道者”,更因为它的作者,有着人间最高处的视点,有着最真挚的感情,有着最阔大的心灵形态之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