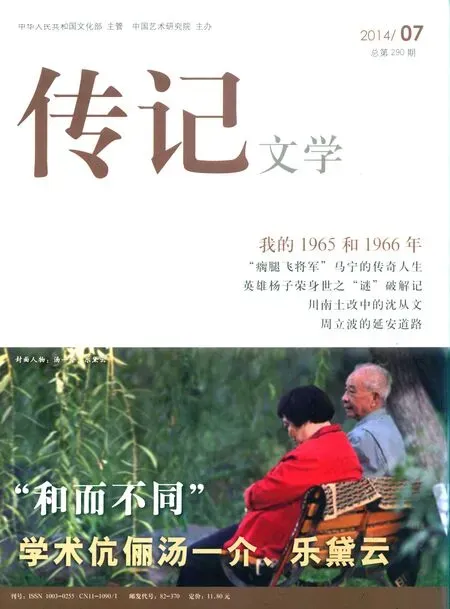用苦难铸成文字
——冯积岐评传(七)
郑金侠
用苦难铸成文字——冯积岐评传(七)
郑金侠

第七章 银元,以及那些艰难的日子
1
在冯积岐的短篇小说《银元》中,冯积岐讲述了一个地主出身的少年的成长故事,这个与两块银元相关的故事始终关系着人的尊严。故事中的一些情节取材于冯积岐历经过的事情,是他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那些刻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给冯积岐的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使年少的他稚嫩的情感备受折磨与摧残。
1
964年的农村社教以后,冯积岐家里和所有农村家庭一样的是,日子一年比一年更加困难了。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天的工分只有二三毛钱的报酬,全家人所挣的工分勉强够分口粮。每年分红时,他的家庭从生产队得不到一分钱。1
966年,冯积岐又添了一个小妹妹,一家九口人要吃盐要点灯,生了病要诊治,每年所有的经济来源是喂养的那头黑猪到年底卖掉所得的钱。幸运的是,家里还有几十块银元。那是爷爷当家时省吃俭用抠下来偷偷藏起来的仅有的家底了。银元兑换成纸币才能拿出去用,而要把这些银元兑换成纸币就要去县城的银行,父亲不愿去做这件事:他怕的是在县城街道上碰见自己当年的“革命同志”。父亲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当年的父亲,在岐山县政府工作的时候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十八九岁去农村搞“土改”,不论老少,村里人都尊称父亲为“老冯”。而如今,父亲落魄了,觉得自己无颜面对昔日的同事。父亲还怕被银行里的工作人员盘问,他毕竟曾经是党的干部,如果银行里的工作人员不给面子,父亲也许会难堪,会尴尬,会无地自容。而母亲不识一个字,连县城银行的位置都找不到,让母亲去兑换银元,会不安全,也不能让一家人安心。因此,就是再难,也只能由冯积岐去完成这样一件使命。他是第一次去银行兑换银元,一路上,冯积岐将手伸进衣服的口袋里,手捏住两块银元,不敢放开,生怕银元从衣服口袋里掉出来。直走到县城西关的时候,他还是忐忑不安。找到银行的门,脚虽然踏进去了,但他心里一阵发慌。他一步一步地挪到窗口。因为柜台比他的个子还高,他踮起脚,看到了柜台里面的工作人员,那是一个长着一对三角眼、嘴唇很薄、下巴很短的中年人。冯积岐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两块银元递进去,说,给我换成钱。三角眼把银元拿过去,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抠住银元的边,左手在银元上很老练地弹了一下,银元发出发露汁一样晶莹的响声。三角眼将银元收了起来。冯积岐等着那人付钱给他。半晌,三角眼不吭声,冯积岐也不敢问,只是眼巴巴地看着柜台里面,等待三角眼给自己兑换银元。又过了一会儿,三角眼抬了一下眼皮,问他:银元从哪里来的?冯积岐一时无法回答,他心想,当然是家里的,这还用问吗?三角眼又问:家里是啥成分?冯积岐嗫嗫嚅嚅地说,地,地主。三角眼说,我就知道贫下中农没这东西。你回去,银元没收了。冯积岐一听,头“轰”地响了一下,立时傻眼了。他争辩着:这是我家的,你咋能没收?三角眼看也不看他,只顾干自己的事。站在柜台外面的冯积岐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不停地求着三角眼,叔,你把钱给我吧;叔,你把钱给我。我婆病了,等着用钱看病哩。他的话等于树叶落在地上,没有一丝回响,他没有办法,只有一声声地恳求着。他声泪俱下,哭着说,叔,你把钱给我吧。三角眼吼道:喊啥喊?碎崽娃!冯积岐看到三角眼拉下的那张脸如同木匠的刨子刨过一般,那人双目圆瞪,目光像弹弓上的石子儿一样直直地射向了他。三角眼的喝喊吓住了冯积岐,他不由得止住了哭声。又过了一会儿,还是没有等到回音,他双手趴在柜台上,茫然而又绝望地看着柜台内的那个人,一声不吭地在等待,等了好长时间,三角眼把四张一元钱的纸币从柜台里面扔了出来,纸币飘到了地上。冯积岐一张一张地拾起如此艰难才兑换到的钱,噙着眼泪走出了银行。
回到家,冯积岐把钱交到父亲手上。父亲问他,人家没问啥吗?冯积岐说,没有。他将自己受到的屈辱悄悄地吞咽了下去。
当父亲再一次要冯积岐去银行兑换人民币时,冯积岐不去。父亲一听就躁了,他责备冯积岐:十几岁的人了,啥事都干不了。在父亲的眼里,他认为兑换银元就是个跑跑腿的小事。没办法,父亲见拗不过和他一样有些倔强的儿子,便叫母亲去,母亲不能不去。母亲虽然不知道儿子不愿去的原因,但她看得出,儿子肯定不会平白无故地违逆父亲的意愿。她叹了口气说,算了,我去吧。母亲已走出了院门,冯积岐又撵出去,把母亲叫住,从母亲手里接过银元,他要自己去。小小年纪的冯积岐已目睹过母亲多次受辱的情景,他不愿意母亲去银行受人欺侮。
揣着两块银元,冯积岐从村口的白皮松下的那条乡村土路上走过去,走上了去县城的乡村土路。走了大约一半路程。冯积岐不想再往前继续走了。他把两块银元从衣服口袋里掏出来撂进了路旁的谷子地里。他憎恨银元!他觉得他的屈辱是这可憎的银元带来的。就像冯积岐后来读到的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中的情节一样,契诃夫在小说里写道:年幼的小保姆长夜不眠,瞌睡得实在不行。在小保姆看来,她不能睡眠,是因为摇篮里的婴儿造成的,于是,她就掐死了那个婴儿。这样,她终于可以睡个安然觉了。这是多么可悲又愚蠢的想法啊!冯积岐憎恨银元,就像小保姆憎恨婴儿一样。成年后,他明白过来,他憎恨的不应该是银元。恰恰是这些曾令他受尽屈辱的银元在生活及其艰难的年月里使他们摆脱了困境,救了他们一家人的命。试想,如果没有这些银元补贴家用,他们一家的日子真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他准备回去给父亲说银元丢失了。于是他便向回走,走了几步,他又返回去。他突然感觉到,这四块钱,对这个家庭来说有多么重要。他走进了谷子地,找到了那两块银元,又开始往县城里赶。他已做好了受欺负的心理准备,即使银行里的人向他脸上吐口水,对他拳打脚踢,他也要忍受这一切。在那一天的煎熬中,他似乎成熟了许多。

1983年,冯积岐摄于西安钟楼
跟第一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冯积岐面对的是一个脸圆得跟金瓜一样的年轻女人。她照例问了冯积岐家里是什么成分之类的话。冯积岐脱口而出:地主。年轻女人说,回生产大队开一个证明拿来再取钱。冯积岐愣住了,他怎么敢去生产大队开证明?!他家里私藏银元的事一旦让大队干部知道,肯定又要来抄家的啊。他只能闷声说,证明我开不来。那女人说,开不来证明就别想要钱了。冯积岐无奈,只好左一声右一声地叫着,姨,把钱给我,姨,把钱给我。只见那女人站了起来,冲着柜台外面的他吼道,胡喊啥哩?谁是你姨?!走开!冯积岐不知所措了。他心里明白,自己是不能就这样走开的。他只能等待,等待那女人什么时候开恩再把钱还给他。柜台里面坐在年轻女人对面的一个小伙子说,瓜娃,你把人家叫姐才合适,你再叫姨就别想要到钱了!原来,女人认为自己被这个小屁孩叫老了,他无意间惹怒了年轻女人。冯积岐不能叫姨又不敢叫姐,只好在柜台外面怔怔地站着,无论何种结果他都得等。他心里如同猫抓一样,无奈、焦灼、担心、不安、渴望、失望等各种情绪一齐涌向他,捉弄着他。大概到了吃中午饭时分,那个小伙子似有不忍,对那女人说,把钱给娃吧,娃等了一晌午了。女人瞅了小伙子一眼,转向冯积岐对着他眼皮一翻,迅速地瞅了一眼,取出钱,却故意放在柜台的最里边,冯积岐人小,胳膊伸进去也够不着,他向上跳了一下,还没够着。他再一跳,用粗布做的布条子裤带被挣断了,裤子霎那间掉在了脚踝处,里面没穿内裤,屁股和私处一下子就全部亮了出来。冯积岐听到身后的笑声,他脸红心跳,委屈至极,滑稽至极。他一只手撩着裤子,用尽力气跳起来去抓钱,终于抓到了钱,他将钱装进了贴身的衣服口袋,拾起断了的裤带,绑续在一起,勒上裤子,几乎是小跑着出了银行。回到家,他把钱交给父亲,再也憋不住,他放声大哭。不知缘故的父亲却责备他,你看你,十几岁的人了,叫你去换个钱,还哭啥呢?我像你一样大的时候,犁地,扬场,啥活都干哩。面对父亲不明就里的责备,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只能把心里的委屈咽下去。他知道,即使父亲破口大骂,他也不会倒出自己所受的屈辱的,因为父亲替代不了他。那样的生活环境锻造了他既懦弱又倔强的双重性格。
冯积岐两次兑换银元受辱,感情上很难接受那样的现实,但是他很快平复了自己的一腔愤恨,因为他想到了曾经被大队干部叫去和村里的地主、富农一起训话,上批斗会陪斗的情景。当他第一次和地主、富农分子站在一起被当作牲口一样喝斥时,年少的他心里在滴血,他顺着墙跟站着,连头也不敢抬。他记得,那天午后,大队干部把他们几十个人召集到一家拆了房的空地上,这几十个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儿女都低垂着头,听大队干部训话。这些人都像木头一样,石头一样,没人敢吭一声。站在角落里的冯积岐看着西斜的太阳,胸口像被谁踩上了一只大脚,堵得慌。那时候,有谁会拿他当人看?!
在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里,他写到了他对“银元”的记忆:“我再一次上路了。我从村子前边的那棵大松树下走过去走上了通向县城的土路。我走得很慢。我一触摸到衣服口袋里的银元憎恶之感油然而生,我极其憎恨它。县城离我越来越近了,我一看见灰黄而孤单的城墙,心跳得更厉害。我走过了商店走过了食堂走过了贴满标语的砖墙和唱着语录歌的高音喇叭,终于走到了银行门口。我朝里张望了一下,一眼就看见了被我蹬翻的那张凳子,看见了银行里的男人和女人。我害怕银行、害怕凳子、害怕男人和女人、害怕我存在的空间,我没有胆量再向前跨出半步,拧身就向回走。
走上了田间土路,我长长地出了口气,田地里的小麦很旺盛。我的手指刚一触到银元,害怕就从手指头上传遍了全身的每一根神经。我还是憎恨它,憎恨银元!……”
冯积岐通过主人公周雨言的口讲述了自己当时深刻的体验:那就是害怕,对一个时代的真实而庞大的恐惧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给一代人造成的心理上的伤害和扭曲。因为有自身兑换银元的切身体验,他才能如此透彻而准确地写出周雨言内心的痛苦与无奈。周雨言羸弱的性格的形成是和对那个时代深切的恐惧分不开的。
关于“银元”的故事,冯积岐没有仅仅写到此为止。改革开放后,周雨言的哥哥周雨人因为祖辈留下的一部分银元奠定的家业,创办了针织厂,而后发了家,成了企业家,也成为县里数一数二的新闻人物。有了钱以后的周雨人没有摆脱掉“文化大革命”带给他扭曲的创伤印记,他始终怀有强烈的报复心理。由于特殊环境造成他缺失了健康的心理,缺失了完美的道德标杆,最终使他回过头来报复社会,以致于最后走上了歧途。
也许,这是冯积岐憎恨银元的深层意识,那就是,银元这一象征财富的东西带给人们的又是什么?在《沉默的季节》中,由“银元”而生发矛盾的故事情节带着作家对人生深邃的思考与严谨的拷问。憎恨银元,不是简单意义上对金钱的诅咒。金钱本身没有罪恶。憎恨银元,是因为兑换银元让本就无自尊可言的日子更增添了心灵上无以复加的痛楚。1974年冯积岐结婚,日子依旧像破旧的衣服一样,四处是洞。他没有一双像样的鞋穿,想买一双胶鞋也苦于没钱。当他为没钱的日子惆怅煎熬的时候,祖母从她的小柜子里拿出了包裹了数层的两块银元,那是祖母积攒了大半辈子的私房钱,她平时舍不得花钱,给了困难中的长孙。冯积岐一旦提起银元,就怀念曾经给了他无限疼爱的祖母。遗憾的是,1975年,在那依然艰难的日子里,祖母去世了,没有享受到儿孙带给她的宽裕和幸福的生活。现在,每当提到银元,就会勾起冯积岐对祖母深深的怀念。

《冯积岐短篇小说自选集》书影
2
为了活下去,确切地说,是为了苟活着。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冯积岐的自尊心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冯积岐刚从学校回来的那两年,由于身体羸弱,根本吃不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家族中的一个爷爷当了生产队长,为了让这个孙子能自食其力,他想叫冯积岐去生产队里当记工员。结果,支部书记知道后决然地阻止了这件事,而且还当着爷爷的面说,地主的娃当记工员,贫下中农不答应。一个小小的记工员也不能当,冯积岐很失望。
1970年,冯积岐被派往太白修战备公路,刚去的时候,生产队带队的负责人指定冯积岐当管理员,管理2
0多人的伙食,负责买菜、记账。在外的日子里,虽然条件艰苦,冯积岐还是很认真地做事,将伙食管理得井井有条。过了一个月,一个刘姓干部不答应了,他说,这么多人的伙食咋能让地主的娃管理,地主的娃当管理员贫下中农不放心。一句话,冯积岐就被打发到工地上干活去了。他的委屈只能憋在心里,他又能对谁去说?!他也看清了——自己只能像劳改犯一样干最累最苦的活儿。1984年,冯积岐已经是北郭公社广播站的一名通讯员了。他的勤奋好学与聪明的天资,让他很快脱颖而出,写广播稿,当通讯员。一天中午在单位灶上吃饭,大家蹲在院子里边吃边聊,一位干事随意开了冯积岐一个很私密的玩笑,也许那个干事无意间触痛了冯积岐那根敏感的神经,当即,冯积岐将端在手上还未吃一口的一碗滚烫的面条朝那个干事的脸摔过去,那个干事被烫得哇哇大叫。冯积岐后来跟别人说起时曾为自己动粗而后悔,但他又说,“八大员”(八大员: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在乡镇工作,但没有编制也不领国家工资的半脱产干部)难道就低人一等?就可以让人随便欺负?自己虽不领公家工资,但人格并不低贱,宁可不干这份工作,也不能被人下眼看。他把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在别人眼里,他就是一团不能随意碰触的地火,带伤的是自己的内心深处。
1964年社教时,冯积岐家的好多树木被分走了,只留下了一棵老柿树。深秋时节,柿子成熟了,冯积岐爬到树上去摘下柿子,等到了冬天,他担上柿子去县城里卖。第一次去卖柿子,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星期天,他担着两小笼子柿子进了县城,那一担柿子全部卖掉,也只能卖两三块钱。他在县城西关的街道上蹲了半天,只卖得了一毛钱。后来,来了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要冯积岐交三毛钱,说是税款。冯积岐把身上所有的兜翻出来只有那一毛钱。那两个干部不相信,又在冯积岐身上搜了一遍,确实只有一毛钱。他们拿走那一毛钱后,还厉声喝喊冯积岐,没有钱,就把棉裤脱下!冯积岐以为是他们在开玩笑。他红着脸,站在那儿,没吭声。一个长着马型脸的中年人再次喊叫,脱!冯积岐这才觉得,他们不是在开玩笑。他下意识地用双手提住了裤子,马型脸走到他跟前,一双大手拽住他的裤腿猛一拽,裤子就掉到了脚踝上,冯积岐哭了。他露出了光腿,冷风吹来如鞭子在他的赤裸的腿上抽打。马型脸又一脚把一只笼子踢翻在地,与另一个人扬长而去。柿子没卖完还受人欺侮,而且还糟蹋了一笼子柿子。冯积岐担上空担子,十分沮丧而又百般难过地回到了家。父亲问他是咋回事,他没有吭声,父亲就开始抱怨,十多岁的娃娃了,啥事都弄不成!我十几岁的时候,你爷爷在县城开了一个店铺,我就成天守在店里帮忙卖东西。父亲总是用自己小时候怎样怎样来训示儿子,好像他的苦难他的冤屈比儿子多很多。冯积岐听了,无法言说的委屈积压在他的胸口,他哭了。
柿子卖不掉,可以担回来再卖。而山柴卖不了,就没办法了。
那时候,冯积岐的父亲给生产里放羊。每天回来时,父亲要割一捆子山柴。为了换几个钱,冯积岐把父亲割回来的山柴拉到县城东关的柴集上去卖。去的时候,是下坡路,回来就成上坡了。如果卖不掉,回路是上坡,一架子车很难从县城拉回陵头村。卖柴的是农民,买柴的都是县城里的居民。冯积岐在柴集上苦守大半天,又饥又冷,他抱住膀子,在架子车旁转圈圈。到了半下午,眼看没人来买,他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假如柴卖不掉,他真不知道该咋办。等到天擦黑的时候,终于来了一个买主,价钱压得极低,还要求冯积岐把柴拉到县城南关去的家里去,一架子车山柴仅仅卖了三块钱。回到家里的时候,家人都已经吃过晚饭,冯积岐又饿又累,一句话也不想说。
为了生存,他打过席盖,卖过席盖;他编过笼子,卖过笼子。如果让生产队长知道,就要以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为名断送他们一家为生存而谋划的出路。那样的年代,是不允许任何人私自外出给自己挣钱的,哪怕是靠吃力流汗多挣的那几个钱,也要偷偷摸摸进行,做贼一般。
打席不是一件轻松活,而且只能在晚上加班干。买来芦苇,用工具把芦苇一根一根的一分为三破开,然后,拿到打麦场上去,一双手推动着碾压麦子的碌碡把芦苇碾压柔顺了,才能开始打席子,打蒸馍笼上面盖的席盖。碌碡在芦苇上碾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最后,他已是浑身汗水淋淋。处理好芦苇以后,晚上借着月光蹲在院子里打席子或打席盖。稀薄的月光水一样洒在院子里,他一干就是两个多小时,站起来时,人发昏,腿抽筋。打好席之后,串乡走村地去卖,在村子里转上半天,才能卖掉二三个席盖。而且,还要背着生产队长偷偷地去卖。

1985年,冯积岐摄于陕西临潼华清池
笼子不是用做扫帚的竹子编的,而是用在北山里割回来的荆条编。一般都是在晚上,坐在昏黄的油灯下整夜不睡觉编笼子,一个笼子也只能卖二三毛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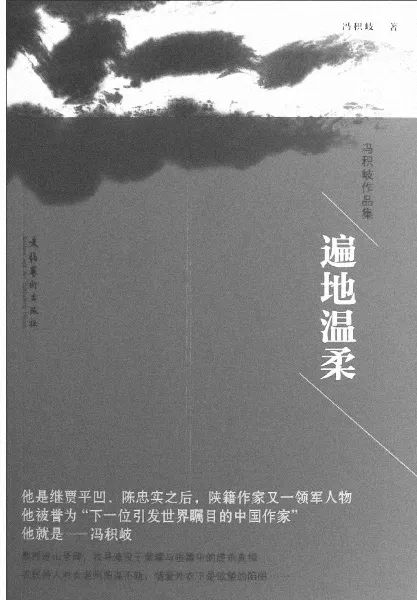
冯积岐著《遍地温柔》书影
1980年春天,冯积岐的一个远房表弟在国营523厂揽下一个拉土方的活儿。这是个军工企业,厂子要在周公庙旁边的一条山沟里建几个存放弹药的库房,这就要求必须将山头削下来,建成一处平坦的空地,拉土方这些活儿要人工才能完成。表弟是工头,他担心冯积岐身体瘦弱拿不下来这么重的力气活,吃不了这么大的苦,可冯积岐满口答应自己能行。他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只要有活干,能挣钱就行,苦和累他根本就不在乎。
当时,他在生产大队担任出纳、广播员和村里的兽医。他给大队请了两个月假,去了523工地上干活儿。
每天,天未大亮,冯积岐就在家匆匆吃过早饭,带上两个馍作为午饭,拉上架子车去四里开外的周公庙旁边的山沟里拉土。一天至少要拉六方土,将近60架子车。山沟里的土质很硬,用力太小,镢头轮下去就会被弹回来。一到工地上,他就脱成单衣单衫,不停歇地用尽全力抡着手里的镢头。太阳还在山那边徘徊,冯积岐已经挖好了几十土方,撂下镢头,就拉起车子运土。土要拉到两里开外的土坝上去。下去的时候,是一道慢坡,回来时一路上坡,拉上两回,就已是汗流浃背了,身上的衣服被汗水浸得湿透,头上汗珠滚滚,头发也粘到一块了。那时候,工地上的人都想多拉几回土,都想着多挣些钱,因此,架子车不是在路上走,而是在跑着,一路小跑,听不见车子在路上碾压的声音,只有人的喘气声像尘土一样铺满了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不停歇地从早晨7点多拉到中午1点多,这才坐下来,啃两块冷馍,在工地的简易楼房边的水龙头上喝几口凉水,一顿饭就这样搞定了。然后,抽两支家里带来的劣质烟,接着又开始挖土、拉土的工作。每天干到太阳落山才拉上架子车往回走。等回到家里的时候,早已是饥肠辘辘了,不论啥饭,端起碗来囫囵吞下,先填饱肚子要紧。冯积岐的妻子一旦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不止一次地说,在那两个月里,冯积岐每天要吃二斤四两面,早上走时吃一斤二两,下午回来,再吃一斤二两。能吃那么多,可见干的活儿有多重。吃完了饭,他就累地站不起来了。去工地开始拉土那两天,冯积岐确实感觉有些撑不住这种强度的体力劳动,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一分钟也不停,从早到晚,身上的汗水从没有干过。他给妻子说,自己流下的汗如果每天滴下来,至少有一桶。他硬是咬着牙在工地上坚持了两个月,同时,他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汗水中捞出来的500元工钱,那是他有生以来见到最多的钱了。他万分高兴,当即买了一辆自行车,这是他和父亲分家后置办的第一份家业。
干了两月,冯积岐还想继续干,他找大队长去请假,大队长说,你要去拉土方就不要在大队里干了,让你到大队里来,是经过支部会研究过的,怎么说你也算一个干部,你好好掂量一下。冯积岐也想在大队里干下去,他明白虽然当时只挣工分不挣钱,他也不能丢了这来之不易的工作。一个地主的娃,能在陵头大队人模人样地工作,实在太不容易了。冯积岐知道大队长是好意,他静下心来考虑了一番生产队长的告诫以后,放弃了继续拉土挣钱的打算。
到了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贫穷的生活状况还是没有完全得到改善。冯积岐打算给自己家里盖上几间房,可是,盖房的钱要一分一分地攒才行啊。1982年,农村分田到户,冯积岐收了第一料自己耕种的麦子,也收获了几千斤麦草。那年初秋,冯积岐把自家的麦草在打麦场上捆成捆子,当天晚上,装在架子车上,第二天再拉到了蔡家坡纸厂去卖,为了积累那十几块钱。
蔡家坡纸厂距离陵头村35里路,也就是说,一个来回有70里的路程。要命的是,去的时候,要上河家道和杨柳村两面坡。这两面坡既陡又长。蔡家坡在南塬下,回来的时候,空架子车要拉上走过八里多的蔡家坡的坡。整个陵头村1000多口人,除过冯积岐和同村同姓的一个农民拉架子车去蔡家坡卖过麦草,再也没有第二个人。那两面坡,真是挣死人的坡!清早起来,冯积岐和同村那个农民分别拉上一架子车麦草从自家的打麦场旁边上路了。
冯积岐拉着一架子车麦草,仿佛背负着一座高山,艰难地行走在长长的杨柳村坡上。他的腰弯成了一张弓,鼻子尖几乎触到地上,喘气声如牛一般,汗水像雨淋似地往下滴。架子车在长长的坡上扭来扭去,呈s型一寸半寸地向前蹭。每向前拉进一步,不仅要付出巨大的力气,也要付出巨大的毅力。等把一架子车麦草拉上长坡,心跳得要从胸腔里窜出来的感觉,汗水顾不上擦,双眼也被糊住了。坐在车旁,冯积岐觉得自己快要断气了。中途只歇息一会儿,又开始赶路。
中午一点多,两个人才到达纸厂。卖麦草的人排着长队,冯积岐一边向前一步半步地挪着架子车,一边啃着随身带来的蒸馍。终于轮到了冯积岐。验麦草的人将手伸进麦草捆子中间,摸一摸,在本子上写上等级,开始过秤。麦草过了秤,冯积岐抬头一看,麦草垛子像山一样高。冯积岐已是十分疲倦了,但是,无论如何也要把麦草背到“山上”去。他勒紧裤带,把麦草一捆又一捆地背上麦草垛子时,双腿酥软得如同抽了筋。把麦草垛好以后,才去领卖麦草的款。600多斤麦草卖了15块零6毛钱。当架子车拉上八里长的蔡家坡时,太阳快落山了。回到家,已是庄稼人吃毕晚饭的时节。冯积岐吃毕饭躺在土炕上,累得一点也不想动弹了。
日子在艰难中前行,生活似乎也没有多少起色。为了活着,冯积岐付出了太多,精神的屈辱也罢,身体的透支也好,都在一天天地增加着他生命的厚度,也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