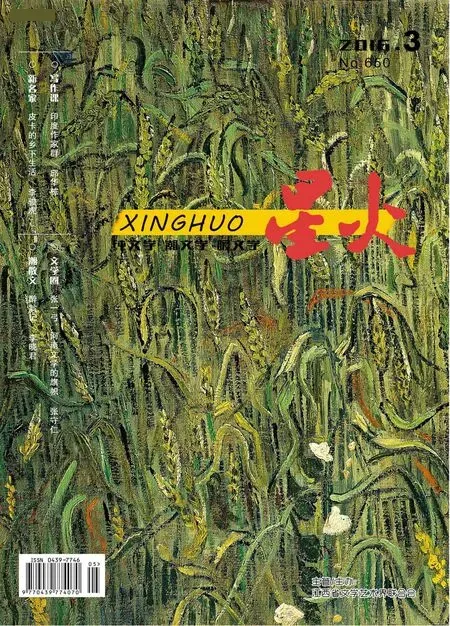隐秘的爱(创作谈)
□文 非
我的姑姑终身未嫁。在乡村,谁会看上一个失聪而弱智的女人。
在我们这个枝繁叶茂的家族,姑姑一直是个被忽略的人。爷爷奶奶共育有五子一女,其中两子夭折,唯一的女儿姑姑也只能算个半成品。但在众多子女中,爷爷最看重的还是这个有些痴傻的姑姑。这种偏爱在奶奶去世后表现得尤为突出。
姑姑曾有过两次说亲的经历。第一次是二十八岁那年,在叔叔们草率的撮合下见了几次面,姑姑也答应了这门亲事,但爷爷站出来反对了。爷爷担心嫁过去了遭人欺侮,大家也就罢手;第二次是时隔多年后的春节,幡然醒悟的爷爷竟然主动提出要为姑姑说亲,态度很坚定。大家都很高兴,认为老爷子终于想通了,这回可以将姑姑名正言顺地“嫁”出去,没了“包袱”老爷子也就自然会随他们进城颐养天年。在叔叔们的努力下,安排了几个鳏夫与姑姑见面,但都因遭到了当事人姑姑的强烈反对而收场。
两次说亲,间隔二十多年,我的姑姑也在乡村粗粝的日子中人老花黄。这二十多年,一直是姑姑在“照料”爷爷,一个没受过教育且脑子有问题的女人照料一个老人,生活质量可想而知。乡村伦理的巨大压力,“失爱”的现实生活,让叔叔们下决心要把老爷子和姑姑分开。每年的春节,孝子们从天南海北聚集到老家,商量最多的是如何安排姑姑的去处。他们甚至迁怒于姑姑,暗地里谋划将姑姑送往养老院。但叔叔们的计划又一次破产——养老院的车在门外候着,爷爷和姑姑却抱成一团抵死不从。爷爷姑姑的执拗,让叔叔们在乡亲们眼前感到颜面无光,就此愤而不提进城一事。
其实,叔叔们关于爷爷“失爱”的判断未免有些武断。爷爷已经很知足,在负疚和疼爱交织的复杂的情感下,已经习惯于每天早晨睁开眼就看见傻傻笑的姑姑,习惯于围着灶台笨手笨脚忙碌的姑姑,习惯于经常变戏法似的从身后掏出零嘴给他吃的姑姑,习惯于为他缝补衣裤而将手一次次扎破还挂泪傻笑的姑姑,习惯于被他训斥时还搞怪的姑姑……谁说这之间没有爱呢,只是我们未看见罢了。
在广袤的乡村和城市,有太多的智障和生理残缺的人在自生自灭地活着。他们有的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残缺,他们卑微但也有尊严。我曾目睹过许多家庭在分崩离析之际,因为智障或残缺儿女的抚养问题而反目。他们总让我想起失聪的姑姑,想起姑姑和爷爷之间那种没有语言的爱,这种爱也让我动念写这样一个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