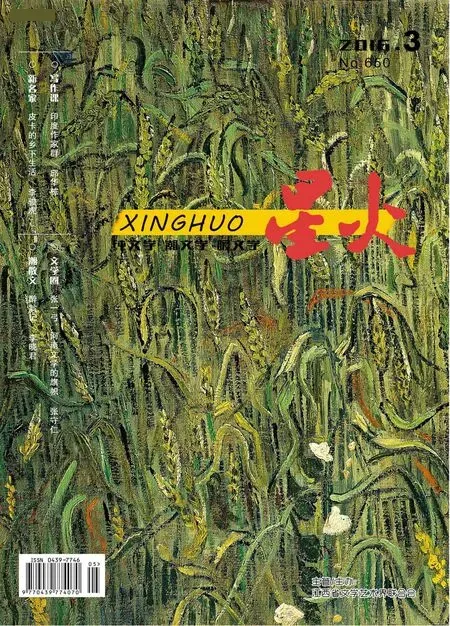滕王阁文学院第四届特聘作家作品选(三)一个人的屠宰场
□樊专砚
滕王阁文学院第四届特聘作家作品选(三)一个人的屠宰场
□樊专砚

县城近郊莲花村的夜晚不再是寂寞的夜晚了,自从两年前村子作为县城新区开发建设以来,整个村子就是一个大工地了,工程车、升降机彻夜轰鸣。
村民们都住进了集中安置小区,村民变市民。诸多不习惯中,最先适应的还是环境。喧嚣的夜晚他们已经能够安然入睡了。只有一个人的夜晚是失眠的夜晚,是与一头头猪纠缠的夜晚。每天太阳下山的时候到第二天天亮,他的耳朵里一直有猪嚎的声音,仿佛有一粒耳屎变成了一只播放这个声音的微型耳塞,但怎么掏也掏不出来。他总叫醒女人听听,只惹得女人骂骂咧咧,鬼都没叫,翻了个身子又睡去了。他就只好和猪们继续纠缠不休了。
这个人就是启富。他六十一岁了,是个杀了大半辈子猪的老屠户。十多年前,儿子在南昌生儿子了,要他老夫妻去那里带孙子,再说那时村里养猪的人也不多了,屠户的收入大不如前,就毅然离开了村子。后来孙子上学了,与儿媳也难以处好关系,老两口只好灰灰地回来。
对他耳朵里老是有猪叫,女人虽然骂他,但还是很在意的。她多次打电话向儿子咨询。儿子的回答也简单,杀了一辈子的猪了,出现这种幻听是很正常的——这就是职业对人的影响。老爹不是常常做杀猪的梦吗,老娘你就不会做杀猪的梦吧。儿子还半开玩笑地说,恐怕老爹在最后时刻听到的都只能是猪的嚎叫哦,他对自己的杀生罪孽太敏感,越老越迷信了。女人心中的石头,被儿子的几句话融化了。儿子说得的确有道理,她从来没有做过杀猪的梦,虽然几十年天天和杀猪的人在一起,天天说与杀猪有关的事。
启富不承认他是幻听,坚持说他听到的,就是金吾那个屠宰场的猪叫声。金吾的屠宰场在山的那面,虽离得不远,但大山的隔音效果很好,即使那些机械屏住呼吸,耳尖的人也听不到。
对金吾一个人一夜杀十几头猪的杀法,启富十分好奇。作为杀猪的行家里手,作为十村八寨杀猪后辈的师傅甚至祖师爷,他觉得自己被抛弃和嘲笑了。他没有脸向别人打听,他更不会向金吾打听。他偷偷去屠宰场看了,那里什么也没有,两个空房子,其中一间六面都贴有瓷板砖,有两个锅灶以及一些特干燥的松木劈柴。他很想找个机会去现场看看金吾的操作,但那里是人迹罕至的荒滩,启富一去,谁都知道是去干什么。
一天晚上,他对女人说:
“金吾一夜杀十多头猪,只有一个人,真不知他怎么做到的!”
“你不是他师傅吗,你没教他,他怎么会呢?”
女人的讽刺让启富很久都没有话说。金吾是他最后一个徒弟,是他唯一一个本村的徒弟。回想起来,的确是招收得草率,传授得简单。因为要急着去南昌带孙子,启富不能让本村的村民到外村去请杀猪的,就决定在自己放下刀之前,培养一个本村的屠夫。最后他找到最穷的老光棍金吾,终于有了接班人。肉是家家户户要吃的,但做屠夫,不是穷不择路的人,是不会选择的。金吾对杀猪无师自通,只要给他一把刀、一头猪和一句“今后你可以杀猪”的话,他就行。启富按门道要求,备好了很多课程,例如怎么调节心理、怎么请神、怎么捂猪眼……。一课都还没有开始,金吾就已经在村里杀死了三头猪。那时正值儿子催得紧,他干脆高调宣布与金吾的师徒关系,正式宣布退出日益衰落的传统杀猪行业。自古以来杀猪手艺的师徒关系一般都很深的,因为在心路上同病相怜,但这对师徒间的情深义重只是表面。启富打心底瞧不起金吾,觉得他太心狠手辣,目无祖法,虽然金吾一口一声师傅,过年过节也来送点小礼。
见他心思沉沉,女人补充说:
“不远,你过去看看不就知道了。”
“那,哪叫杀猪呀,不遵守行规祖训,没一点体统。你去山头听听,只听到猪一头接着一头叫。要是阎王管猪的话,划生死簿都忙不过来。”
“都是杀猪的,你以为你杀猪就高贵些呀。你那个杀猪慢,照现在的吃肉,你屠户都要被吃了。他才高贵哩,一天十多头。你算算吧,多少工钱,那才叫贵。这样紧巴巴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我懒得与你嚼舌头。”
女人翻身就起了齁声。启富对身边的齁声听而不闻,耳畔又是那遥远而真切的猪叫声。他觉得,自己杀猪的猪叫声是平缓从容的,声音里还含着猪的体温、神的安抚、还有魂的超度,十分温润和祥和。哪有这么凄厉悲惨的。挣再多的钱也不愿意这样杀猪,一天十多头,一个人杀,真不可思议。他觉得猪都一头头在求他,纷纷不愿被金吾杀,都想请他启富去杀。他就只好一头头去安慰,去解释,去用他的门道仪式送猪走最后一程。
在启富看来,一天顶多杀两头猪,还要东家准备三四个壮汉做帮手。杀猪的藏刀、捂眼、祭纸、鸣炮等几个关键程序,一个都不能少。那时他帮人家杀猪,进门第一件事就是问人家,社神请到了没有,直到亲眼看到社神坐在堂前享受着香火才罢休。接着就要亲眼看到火纸和鞭炮。这样之后他才示意把猪放出来。先让圈养了一辈子的猪,在野地里欢腾十几分钟,然后他对着社神作个长时间的揖,接着防贼似的把长刀藏在用来盛猪血的盆子下面,铺几张火纸在盆子旁边,才示意壮汉们捉猪。几个壮汉牢牢把猪架在凳子上了,他左腿膝盖顶在猪的下面那只眼附近,左肘抵在上面这只眼附近,猪的世界就黑暗了,看不到刀光和杀手。他右腿后退一步弓好身子聚集力量,右手握刀,把刀迅速从最接近猪心脏的地方捅进去,旋转一下抽出来。盆子里立即冒起了热气。他洒一些猪血到火纸上,示意东家派人去烧,猪快断气的时候,示意放鞭炮送魂。启富每一次杀猪都这样,十年前最后一次杀猪也是这样。启富杀猪的时候,养猪多是自给自足,人们吃肉很少。他只是在过年的时候忙些,平时十来天也难得杀一头。他有的是时间和从容,总把生命和神灵都放在心上。
但启富这种传统杀猪法,已经完全被时代淘汰了。
启富不懂得从时代变迁上分析,只知道怨恨金吾不遵祖法行规。给他这个职业没两年,还不顾村里的猪有没有人杀,跑去外面打工,几年都不回来。闹得村人都到远处请屠户来,或把活的猪卖到远处去。启富甚至把村里养猪的人越来越少都归罪于金吾的不敬业。有几年,村里年头到年尾都听不到一声猪叫,过年的肉都从肉店里买。然而去年金吾回来了,家家养猪的习俗仍不愿回来,反倒发生了夜夜猪叫的情况——金吾在山后的荒滩建立了一个屠宰场,猪一车一车从外地运来,肉一篓一篓批发给各个肉店。从猪叫可以听出来,那是流水式的,一头紧接着一头,几乎没有任何中间环节,更别说烧纸钱和鸣炮了。
金吾与启富住在一栋楼。搬进楼房以来,启富无事可做,杀猪刀早就给了金吾,锄头、镰刀、犁、耙等也都脱去木质部分,藏在储藏间已经锈迹斑斑——永远都没有使用的机会了。启富很少到房外去,人们一见他还是叫他富十万。杀猪是个低贱的行业,但收入很高。他曾是村里的富裕户,自吹过家产十万。现在,他有屠夫的名号,没有屠夫的实惠。他在家里就笼中的老虎一样,张望着铁栅栏外的世界。每天金吾去上班的时候,启富总是知道的,并在窗下偷偷目送他一程。金吾骑的摩托车很旧,浑身是猪油味,发动机的声音也很特别,有猪叫的意味,一听就知道是金吾。他的摩托车装上了特制的木箱子,很多刀具插在里面。金吾上班很准时,都是下午五点去。他摩托车一发动,仿佛猪就叫了,启富就起身到窗口,远处的十几头猪就开始烦躁不安。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已经一年多了。金吾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富裕,启富的日子却在无聊中贫穷,贫穷中无聊。
女人买菜特地等到中午才去,捡别人挑剩下的便宜货,有时有些变质了的也要。每次上厕所出来,启富都不冲水的。女人不冲吧要骂女人;女人冲吧,又骂女人冲多了水。因为没钱装窗玻璃,工地的灰尘经常落得满屋子都是。女人经常哀叹,这日子无法过了。
启富的老房子拆迁置换了这套近两百平米的超大住房——他喜欢比其他人活得气魄一些,开始没有想到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田地补偿款及此前的大部分积蓄都给儿子在南昌付了房子的首付款。在南昌住的那三年,启富也挤怕了。现在儿子的工资每一分钱都有着儿子的用途。
征地拆迁后,一身筋骨劲儿没地方用的村民,很多人都到长虹立交桥下去站街。他们等着被雇去干苦力,例如卸车装车、搬家、运建筑材料等。如果运气好,两天三天被人雇上一回,也有上百块。启富也去站过,但村民都讥笑他排挤他,批评他金吾那么好的地方不去,浪费了自己的手艺。他们还自嘲说,男人站街待雇与女人站街揽客没有什么两样,又说他的儿子在大城市里都有工作了,老父亲站街丢了身价。
夜晚的猪叫,越来越刺耳;金吾上班去的背影,把他的视线拉得越来越长:他的脾气越来越大了。他经常拿女人发火,不是说买多了菜,就是骂她买贵了米。女人又去向儿子讨办法,这次儿子态度认真了很多。儿子说,那就让他继续杀猪吧,田地不种了,总要给他一个事情做做。儿子还说多做做事情,高血压的情况也会好些的。
“你爹杀猪与现在杀猪不一样的?”女人还是有疑问。
“那就师傅做一回徒弟,徒弟做一回师傅吧。活人不能让尿憋死。都要跟着时代前进嘛!”
当女人把儿子的意思告诉启富。启富久久没有说话,最后叹息道:
“落到这个田地,师傅徒弟的名分倒是其次的。就是我那样杀猪,有天地良心,这样杀猪的,听着就不是滋味,别说看了,更别说自己去做了。”
坚冰有了突破口,化解就容易了。恰在这个时候,金吾又一次来请启富去他那里帮忙。因为肉的销量大,一天杀十来头猪满足不了需求。
金吾的身材比启富的要小很多,但一进来,就让人感觉有一股血腥味。
“师傅,你就出山帮帮徒儿吧。你能杀几头算几头的钱,一头五十块,计件付现钱。人家运砖上楼,一天也不足一百块。师傅你这样的身子骨,出山了一天至少能有四五百块……”
金吾还没说完,话被师傅的干咳打断了。女人接着话题一味地说好好好,说去去去。
“师傅,你考虑考虑,去的话给个信。我就天天下午带你去。”
女人帮着问道:
“你师傅的老杀法,在你那里没用吧,总不能再请几个人帮忙捉猪嘛。”
“师娘多心了,老杀法师傅那么溜,新杀法师傅看一眼就会了。很简单的,猪会帮着我们杀猪的,就像傻逼被人贩子卖了还会帮着数钱一样。嘿嘿……”
金吾知道自己对着师娘说逼字不好,吐了一下舌头就知趣地急着告辞了。杀猪的人的确难寻,不是实在找不到人,他也不会来找启富。
“很简单的,猪会帮着我们杀猪”,这天晚上启富听着一头接一头的猪叫,被这句玩笑话弄得几次冲动要起床去看个究竟。
第二天下午,金吾的摩托车发动的时候,女人在楼上喊:
“金吾,金吾,你师傅想去你那里看看。”
启富就坐在了金吾那猪叫似的摩托车后面,虽然离得不远,但因为大山隔着,只能走弯弯曲曲的沿河小道。一路上,金吾几次没话找话,启富还是爱理不理。
到那里后,两个房子还是空的。
金吾一边从摩托车工具箱里拿出几把刀放在门口的磨刀石旁边,一边叫师傅进去坐。屋内有几个油腻很厚的松木矮凳子。金吾把墙上的开关一摁,水管就开始给锅里灌水,然后他拖一个凳子到锅灶前面,坐下开始了生火。火旺起来了,就开始磨刀。启富没坐,也没问什么,但看得十分仔细。
为避免尴尬,启富很快就自觉地去照顾火了——其实劈好的干燥的松木,基本上不要照顾的。他本能地觉得这就是泡死猪的开水,用两个锅是为了加快烧水速度,可以轮流烧。按照他的行业老规矩,需跪下烧三把柴的。这次他没有下跪。正在他看着火苗想传统老规矩的时候,汽车的喇叭响了,接着就是一群猪的唧唧哼哼声。金吾继续磨他的刀,后来进来一个人,拿个单子给金吾签了字。
“师傅,去看看吧,是不是十五头?那就是我今晚的任务。”
另一间房叫储猪间,一下子就挤满了猪,十五头。原来房间设计很机巧的,车厢与后门一相连,猪就能轻易被赶进储猪间。屠宰场一下子热闹了。
刀磨好了,金吾就冲洗地板,也是开关一摁,水管把瓷板砖冲得干干净净。
“这操作间的六面墙都要冲湿,只有保持湿度,猪血喷上去了冲洗起来才容易些。”
金吾开始传授真经了。
“师傅,我马上开始杀猪了,先让你看看一个工具。小物件大用途。”
金吾从摩托车工具箱里拿出一个一尺来长的铁钩子。钩子很锋利,另一头有一根横杆,整个如一个“丁”字,只是上面的一横旋转了九十度,便于使用。金吾向启富示范怎么握钩。只见他左手掌心紧握横木,拇指食指一头,另外三只一头,铁钩子从中间伸出来,钩锋正好向上。
“我们要用这个钩子钩住猪嘴巴下面的肉。说没有用,我先杀一头你看看。”
金吾的钩子钩着一头猪的下巴,牵牛一样把它牵到操作间来了。猪和金吾沿一条直线的两头用力,拔河一样,但人的力量很大且精于控制,猪被乖乖地牵引着。当猪被牵到水泥地的中央时,金吾右手捡起备好的尖刀。金吾喊了句师傅注意看哟,就左手抬起,把猪的头拉仰,用尖刀对准脖子的抵心脏处,左右手同时协调用力,刀就进去了。在抽出尖刀,回出钩子时,金吾身子一闪,喷射的猪血没有洒到他。
拔河的一头一松手,猪往后一退,倒下了。然后,这头喷血的猪就在地上自由地挣扎着,嚎叫声,还爬起来跑几圈,血染一身。对此,金吾看都没看,加柴烧火去了。
“关键是猪就是猪,死到临头了,都拼命往后退。让它翻滚吧,挣扎几分钟就安静了。猪死后,用开水一淋,之后的事就都在水泥地上操作,关键是现在的刀好,特好的钢材,还配了什么什么金属材料,剃毛、开肉特爽快。……”
金吾声音很大,盖住了猪的叫声。但启富早已目瞪口呆,耳朵里轰鸣着,没有听到金吾的指导。金吾还没说完,猪还在挣扎,启富就出门了。
“师傅你慢走,过不了多久就有车子来拉肉的,我实在不能送你回去啊!决定来的话,一头猪五十块,五十哦。”其实金吾也不是真的尊重这个师傅,他把后面一句说得很重,想发挥钱的吸引力。
启富心中翻酱倒醋,有对猪的怜悯,有对金吾的愤怒,也有对自己的嘲笑,有对自己那个手艺的绝望。这样简单、这样下得了手、一进一出就是他金吾日进六七百元的工作……猪和屠户面对着面,刀就在中间比划,这杀猪还叫杀猪吗……金吾杀进去,没有旋转一下,猪走的路程就远很多,那头猪现在死了没有……他一路走得很快,翻山路回家,到了山上才喘一口气。
县城新区的全境在启富的眼下了。无比熟悉的那民房顶上的炊烟、菜园子碧绿的叶子、羊舍猪圈的气味、田埂小道的野菊花、池塘里打滚的水牛,变魔术一样,竟然没了。弥漫的尘土被夕阳的霞光染上了红色,暮霭一样。他首先看到了一丛楼房,那是所有莲花村人聚居的莲花小区。那是已经长成的钢筋水泥林,它的四周的楼房,雨后春笋一样,在冒出、在拔高。街道纵横交错,工程车穿梭其间,扬起更多的灰尘。对这个环境他十分陌生,他感到了恐惧。他在南昌儿子那里住了三年,也始终没有适应城市。如果没有银行存折,他想不到其他的生存办法。他往更远处看了看,那里是繁华的老城区,他突然想到了站街。他摇了摇头以极快的速度下山来了。
回到家里,女人见了他大气都不敢出,更不敢问他——加倍悉心地服侍好他的晚餐和洗脚洗脸。女人平时骂骂咧咧表面上凌驾在启富之上,其实启富是家里的绝对权威。
这天晚上,启富的耳朵里依然是猪叫声不断,但他的感觉截然不同。他不再是站在高处的怜悯者和安抚者,不再是声音的倾听者。他觉得是自己发出声音,是猪发出了他启富自己的心声。被一个钩子钩着,自己拼命地往后退着,只有痛着,只有挣扎着,只有任人宰割。启富拉开被子,扯了棉絮堵住耳朵,但没有用,声音还是能听到。他突然明白,声音不是从外部进去的,而是里面内生的。他感到一阵恐慌。他对自己的处境进一步清醒了,他觉得要抗争要摆脱了。他突然吆喝了一声,女人吓得坐了起来,启富觉得舒服一些了。
他一吆喝,猪叫的声音就消失了;但安静不了多久,又会响起。这夜启富发神经一样,吆喝了很多次。女人不敢问,不敢打电话给儿子,心惊肉跳地熬到天亮。晨声喧嚣,耳朵里却安静了。吃早餐的时候,启富很轻松,对女人说:
“今天跟金吾去杀猪。”
两军对垒,倒戈的戈更具杀伤力。启富在猪群和金吾的两个阵营间,由猪群倒向了金吾。第一个晚上,试杀几头,技艺一次比一次有大进步。第二天他就有了一套自己的工具,全新的。第三个晚上,他杀得比金吾还多,金吾说了很多“宝刀不老”之类的好话。启富手法的关键是杀进去旋转了一下,喷血快了,缩短了猪的生死路程。他的操作注意力集中,从不对视猪的眼睛,用力精准、直接。只见他手起钩准,刀出猪毙,金吾心悦诚服地再次拜他为师了,也高兴招来了一个技艺精湛的员工。
大把大把的钞票压在枕头下,改在白天睡觉的启富再也没有听到过猪叫的声音。他心里平静,只是浑身筋骨有些累。睡到下午四点后,总能恢复元气,轻松愉快地坐到金吾的摩托后座,奔赴屠宰场。
一个人的屠宰场变为两个人操作了,他俩合作得心情愉快,工序流畅。他们一起说说话,笑话、荤话,也议论国家大事,夜晚就不那么显得漫长了。听猪的叫声,就像开拖拉机的听马达声一样;开猪的胸膛,就像木匠砍开木块一样。不过有一件事,他俩都十分小心,那就是当一个人去钩猪的时候,另一个人不钩。如果两个人都钩猪的话,猪群乱窜,猪挤动着猪,容易造成钩子钩不准的情况。劳动中的很多禁忌总是自然而然的。
启富的生活立即得到了改善,女人买菜不再等待中午的剩货了,窗户的玻璃装上了,女人冲厕所也不骂了。还有一个变化就是给南昌打长途电话的机会更多了,一说就几十分钟甚至超一个小时,做爷爷奶奶的总有与孙子说不完的话——孙子十岁了,因为朝夕抚育了三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家乡方言。虽然一家人不能住到一起来,但这种富足、其乐融融的日子让启富的脸色越来越红润了。不知不觉,启富开始教导儿子、孙子要向前,不要退缩,老是拿杀猪说事——看得出来,启富对自己的工作很有干劲,很心安了。不久,孙子一接电话,先自我喊几句口号:“向前,不要退缩!”于是一家人笑开了。
然而,生活总在戏剧中。儿子从内部得到机密消息,屠宰场的土地纳入了城市规划,要建一条隧道和一座桥,山那边的荒滩就变成金银了。那地面上的建筑就只有金吾这个屠宰场。金吾即将成为百万富翁了,至少三百万,可金吾还不知道。“就是想趁他还不知道,设法转让过来,这就是商机。我那个同学在那个部门工作,他说这个事就靠我们做通金吾的工作。他出转让费,一百万都行,他全部出。转让到手,到时一人一半。至少一百五十万。”儿子说得很激动。
如果转让到手,大富大贵的日子即将到来。这天启富坐在破旧的摩托车上,看着金吾疲惫的背景,内心怎么也无法平静。他知道金吾这个场开起来,投资不足十万,证照手续办下来,不超过十五万块。这晚杀猪,启富一下子有劲,一下子没劲。金吾说玩笑话,他也笑起来皮笑肉不笑。他恨不得直接提出转让,但他最终还是理智冷静的。这天晚上没有让金吾感觉到任何异样。
第二个晚上,启富先是叹杀猪的辛苦,“哪是人做的活呀,晚出早归,人不人,鬼不鬼的”,又说要是他是金吾,就不干这个了,本钱够了可以做别的干净舒服的生意去。金吾对这项生意坚定不移。启富感叹起自己一辈子做屠夫,被人看不起,还说不知到最后,会不会因为杀生太多要被阎王刁难。金吾说:“别说地位不地位的事,没有什么了。有钱了,妓女都很多人愿意认作娘,嘿嘿。阎王嘛,师傅,我们要做唯物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启富不懂,但他理解金吾,他根本不信阎王。也许是金吾想给启富打气,也许是金吾想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改行,他用安慰的、又有些炫耀的口气说:“师傅,说了你别不行。我会点天文地理的。我这个地方杀猪能挣钱,长草也生金呀。我们莲花村建成城市之后,城市再向哪里发展,瞧瞧吧,四面是山。我这个地方是唯一的地儿。多则五年,少则三年,我这里至少值五百万。我还想扩大面积,可惜已经批不下来了哦。师傅,不是批不下来了,我还谁都不会说的。今晚我第一个在你面前夸夸,我女人都不知道,她嘴多人傻。我们还是好好安心干吧,好日子在后头。到时我不会亏待你的。谁敢瞧不起我们杀猪的呢,嘿,杀——”
启富从脚底到头顶都冰冷了。金吾以为他是被这个秘密怔住了,其实启富是彻底绝望了。
“走,我们钩猪去。杀不了多久就要发大财了,就可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哦。”
金吾邀请道,吹着口哨去储猪间钩猪了。
启富觉得自己的处境退到了有生以来的最低谷,一种绝地反击的冲动占据了他、控制了他。“向前,不要退缩”,他耳畔响起了自己经常教导儿孙的这句活。他应邀也钩猪去,紧随着金吾进了储猪间。
钩子的出现,猪群潮水一样涌动。金吾这时特兴奋,为自己的富贵未来得意忘形。他瞄准着猪,保持猎豹发起突击前的那种状态。猪好像清醒了自己的处境,乱成了一团糟,金吾几次要出手时,都在毫秒间取消了行动——没有精准地钩住猪,就容易钩到自己头上。越是失手了几次,越是注意力集中,金吾没有注意启富就在他的身侧。正是启富的掺合,致使猪群过度惊慌,致使金吾无法确定目标和精准出手。
启富同样无法出钩,当确定了一个静止的目标时,另一个屠夫一挥钩,静止的又移动了。他们两个人都只有目标,只有兴奋,各自鼓着一股杀劲。启富终于钩住了一头……
事故发生了。
金吾的钩子钩猪时落空,钩到自己头上去了,因为他钩向的那头猪,被启富钩住的猪挤开了——恰在此时,启富与猪之间的“拔河”发生了力量逆转,猪后跌了一步。
流血、昏迷、送医院……
所有的亲人来了,朋友来了:急救室外挤满了人。突然医生开门允许人们进去,一下子在手术台旁围了一大圈。金吾清醒了,他的目光转了一圈,最后停在了启富的脸上,很久。他嘴唇动动,但已经没有了声音,只好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丧事办完之后,有人找到金吾老婆谈屠宰场尽快开业的事——猪肉生产关乎民生大计,不能停产太久,否则会引起本地猪肉价格的波动。金吾老婆说,让启富师傅一个人先做起来,师傅要的话转给他;这应该也是金吾的意思。
启富的儿子特地请假回来了,笑声朗朗地进门,一看见启富,就过来拥抱了一下老父亲——这是儿子成年十多年来第一次这样。但事故发生以后,启富总是呆头呆脑,注意力不能集中。转让的事情都是他儿子帮着办理的。成本核算后,另加一些转让费,一共二十五万块——他儿子的同学答应全出。因为仍在丧期,转让的正式手续没有办,议定付了一万元定金后,可以先开工。
重新开工的那个下午,启富是走路去的。很想要女人去作伴——但他终究没有,因为他觉得女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去了可能会叫他更内疚。他在去开业的路上,仿佛金吾在钩着自己往前拉,是向前呢,还是拔河一样后退。启富还是不愿做个后退者。他害怕归害怕,向前归向前,两项同时控制着他。
有一辆小车停在门口,下来一个人,带着金边眼镜,面相斯斯文文的,个子也很小号。他一见启富就喊大伯,就热情地握手。那人自我介绍,他就是启富儿子的同学。他没有多说什么,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这个屠宰场必须和以前一样,一切正常;二是安慰安慰他的大伯,“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就是要把日子过好;听说你精神不是很好,这就不对嘛,生死有命,富贵就靠自己把握啊。”
那人走后,启富照例开始了烧开水、磨刀、冲洗房间。猪送来的时候,那个人习惯了还是喊“金吾,签字”,启富签字的时候,手有些发抖。屠宰场因为猪的到来一下子热闹了,猪的唧唧哼哼却使启富更加感到孤单和压抑。
随着最后一缕霞光的收起,黑暗笼罩了大地。屠宰场的灯光异常明亮,但启富的心离开光明游离到屠宰场之外了。由于猪血猪零碎都排泄在外面,围绕着屠宰场,杂草茂盛,野物云集。长期以来,食物链在这里异常活跃,这里的厮杀与死亡一到夜间就大规模上演。老鼠、蛇、蝙蝠、野狗、夜鹰……尖利的怪叫、诡异的魅影、凄惨的呻吟……以前启富没有感觉到这些,这晚他才身临其境。
一头猪都还没有杀,他有些想逃离了。他又想起刚才那个人说的,要保持一切正常。这是什么意思,怀疑我故意谋杀了金吾?绝不是故意的。绝不是故意的,是他邀的去钩猪,他说“走,我们钩猪去”——谁也没有规定不能同时去钩啊。……不是故意的,怎么就那么巧?不是故意的,怎么就在那个时刻松了手。如果不松一下手,被钩住了的猪不后退,就不会撞动金吾要钩的猪。……
启富的头很痛。他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自己到底有意还是无意?他极力去回忆那个时刻,那几分钟,那几秒,甚至那几毫秒的细节,但一切一会儿梦境一样,飘渺无迹;一会儿就在眼前,真真切切。
为摆脱这种折磨,他横下心来,提着钩子来到储猪间。他的出现引起了猪群的骚动,可启富把这种骚动看成了猪群的狂欢,在表达对自己的鄙视和厌恶。他恼羞成怒,一下就钩住了一头,就往操作间里拉。然而,他与猪的力量势均力敌,拔河一样僵住了。
“你没有资格杀我!”
被钩住的猪说。接着,所有的猪帮腔。
“你没有资格杀猪。”
“你用过去的那种杀猪法杀,我们才服。你老都老了,还来染上一身杀气。难得善终啊!”
启富无言以对。他用力拔了一下,毫无动静——他的力量已经无法超过对方了。
这时,他的目光与所钩那头猪的目光对视了一下。启富做了一辈子的屠夫,这还是第一次与猪眼对视——看到了一双闪亮的眼睛,充满着思想和感情。说仇恨也不是,说宽容也不是,说痛苦也不是,说求饶也不是,说猪眼也不是,说金吾眼睛的也不是……
启富突然触电一样,身子一麻,弃钩而逃。
县城新区在莲花村新成立的警务室里,启富纠缠着,要求自己被拘留。
“金吾的死我有责任、有罪。金吾是我害死的。”
“是你钩了他?不是吧。是你推了他?不是吧。不是你的错,老人家。”
“我钩着的猪推了一下他要钩的猪。”
警察们哭笑不得。
“这不犯法。没什么,没有规定哪个时候能出钩,哪个时候不能出钩。你想太多了,你回去吧。劳动中,难免会出意外的哦,你们师徒这么多年的往来,村里人都知道,情谊太深了啊。”
“我的猪推了他的猪。是我害了他。……”
警察们不耐烦了。
“上了年纪,手劲是要差些的,是不稳定的。只要不是故意松劲就没有问题。是故意的,你就不会来说哦。”
“……”
……
其实,这个事情到哪里都无法确证。启富被送回了家,警察还交代,要好好安抚他的情绪:
“老一辈的屠夫,因为迷信思想,到了晚年总是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做家属的要理解啊!……”
女人拿怪怪的眼光瞧他,儿子更是不去正眼看他。这晚家里的气氛是僵死的,启富只好提前上床了。这晚的世界出奇地安静,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启富自首和启富疯了两个版本的传言连夜传开。第二天一早,金吾的女人到启富的家里,退回转让的一万元定金,要求废除转让。启富的儿子与他那个同学经过几次电话密谈,最后决定放弃。屠宰场的转让不得而终,屠宰场的屠宰完全停止了。
菜市场依然有肉买,没有人去追问是哪里屠宰的。启富偶尔出来走走。看到他的人,都远远地回避他。
两个月后的一个早上,启富来到了长虹立交桥下站街——他老得很快,腰、背都弯了好多,步履也有些蹒跚了,左手还不停地抖动。人们聚到他的身边来,开始是好奇地围着看。后来有一个人说开了,就都七嘴八舌地调笑着:
“启富,你到底是不是故意松了一下手?我看是故意的,现在报应了吧。怎么你这只手抖个不停呢!”
“启富,不是你故意的,是猪故意的!”
“启富,派出所不审你,杀了一辈子的猪,阎王可要审的哦。金吾的事,他要顺便问问的哟。别找派出所了,到时到那里去说吧!”
“如果我是你呀启富,不是故意的不说,是故意的更不说。转让到手三百多万,儿孙都花不完。”
“现在金吾女人可牛了,三百万到手。追求者们都打起架来了哟,你知道吗启富?”
……
这天从早到晚,打趣启富的人很多,雇佣启富的人却没有一个。
责编:朱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