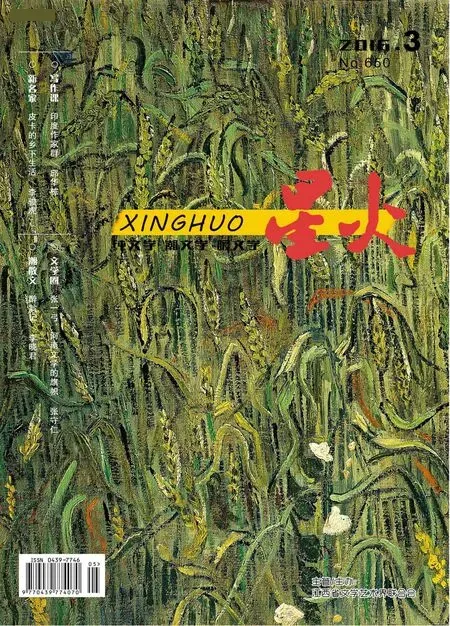潘婆
□张品成
潘婆
□张品成
一
潘婆五十多岁,成天绷着张脸,什么事稍不顺意都能让她骂骂咧咧。
但她从不骂万小坎,也从不骂凌照照。
万小坎那天给伤员剃头,借的是潘婆的铜盆,王坪没几个人用铜盆,大家用的都是木盆。但潘婆用铜盆,据说那只铜盆一直跟了潘婆。
万小坎给那个伤兵剃头,刀才举了,那个伤兵说:“我要用铜盆。”
万小坎说:“铜盆木盆不都是盆吗?难道铜盆洗头你就成皇上了?”
那伤兵说:“我知道我伤在头上,也活不了多久了,我就想用铜盆洗个头。”
万小坎没办法了,他去找潘婆,麻着头皮跟潘婆说:“我要借你的铜盆用下。”
潘婆说:“没事没事,小坎娃儿你拿去用就是。”
那天,竟然出了点事情,铜盆放在条凳上,那伤员一蹬脚,踢倒了条凳,铜盆掉在地上,磕出一个凹斑来。
要死噢,你把潘婆的宝贝弄坏了,潘婆放得过你吗?万小坎也觉得事情严重,他脸上阴云密布,怯怯地去了潘婆那,他手端着那铜盆。喊一声潘婆,却不敢进那门坎。
潘婆说:“是小坎呀,你进屋来呀。”
还是不敢进。呆呆地站在那。潘婆拉开门,看见万小坎捧着只铜盆傻傻地站在那。
万小坎说:“潘婆,我把你铜盆摔了。”
潘婆接过铜盆看了看,“没有哇,好好的。”
万小坎说:“你看这有个凹地方呢。”
潘婆说:“漏水不?”
万小坎说:“那倒不漏。”
潘婆说:“那就不算个事。”
万小坎说:“这不妥,你借我时好好的,现在弄成这样,我会帮你弄好的。”
他真的去找张乐生,张乐生说:“这事好办,敲回去的就。”可他一个铁匠使锤用惯了大力气,才一锤,就敲出了麻烦。先前才是一个凹斑,现在好了,敲出一个裂缝来。
万小坎脸上阴云密布再加了一道霜,怯怯地去了潘婆那,他手端着那铜盆。喊一声潘婆,依然不敢进那门坎。
潘婆说:“是小坎呀,你进屋来呀。”
还是不敢进。呆呆地站在那。潘婆拉开门,看见万小坎捧着只铜盆傻傻地站在那。
万小坎说:“潘婆,我把你铜盆敲裂了。”
潘婆接过铜盆看了看,“没有哇,好好的。”
万小坎说:“你看这有条缝了哩。”
潘婆说:“漏水不?”
万小坎说:“漏。”
潘婆还是说:“那也就算了……等外面太平了,我去苦草坝交做铜的师傅补下就是。”
潘婆五十多了,但没嫁过人,没嫁人的原因谁也不知道,她的身世从来也是个谜,有人说她是从巴山深处走来的,传说充满了臆想和夸张,几乎要把她说成仙人。但这话也没错,潘婆确实是从陕西那边过来的,从陕西过来就要爬过巴山。她早年说话夹一点陕南口音,后来才逐渐改了。她不嫁人,有人说她可能本身就是尼姑出身,犯了什么戒被逐出山门。可是,没听说尼姑织一手好布的。有人说,这也难说,尼姑闲了没事,捻棉花织布也是修身养性。有人说是因为潘婆的性格,你看那怪怪的一个女人,谁敢要?她整天脸绷了,你和个泥人过活也比跟这么个女人过要好呀。
反正说法很多,没有一个被印证,所以都是谜。
二
潘婆织得一手好布,是方圆百里内最好的织匠。大户人家要嫁娶,点名要的是潘婆的手艺,有人就直接用轿子接了潘婆去家里织布,高墙深宅豪门大户,潘婆是常客。
磨儿垭神匪匪首李茂春过生日,想着气派排场,说要穿潘婆的新布。有人挖空心思弄了来,李茂春掂起好布看了又看,说看不出这布好在哪哟,这是潘婆织的布吗?你们把潘婆请来我要亲眼看她织。喽罗们愣了,真就出山拎着厚礼抬了轿子去潘婆那。潘婆说这种活我能接吗?唾沫会淹死我。她说我不去,你李茂春能绑了我去吗?那时候红军还没来,这一带匪患严重,谁要拉了支队伍上山都能称霸一方,山高林密,官府拿他没办法。神匪真还有那横行霸道随心所欲能耐,李茂春说我倒要看看什么人请不来非得硬请。
那天夜里,是个月黑风高的夜。月黑风高杀人夜,但李茂春的手下没杀人,你不说要绑了你去吗?那就绑了。喽罗们把潘婆绑了塞进轿里抬到寨子里。李茂春说:“我倒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妇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匪首李茂春见了潘婆,他说:“松绑松绑。你们怎么能对我们客人这样?”
潘婆说:“是我自己要这样的,我说要不李茂春绑了我去。你们就真把我绑了来了。”
李茂春说:“我请不动你嘛。”
潘婆说:“我不给匪盗出力流汗,你绑我来也没用。”
匪首李茂春说:“你来这里,你就是我的客,你先住些日子再说。”
潘婆就被困在磨儿垭了。潘婆想,你就是打死我也不会给你织布的。
他们没打她,他们把她关在小屋子里端饭送水。他们给她笑脸,更没打没骂。但不让潘婆出那小屋子。一天两天的潘婆没事,关了有十天八天的潘婆就受不了啦,她骂人,但没用,没人理她。关了一月两月的潘婆就有些受不了了,她绝食,但饿了两天受不了又狼吞虎咽了。
要是红军不来,这种日子潘婆还不知道能坚持多久。要么就挺下去,要么就真绝食或者撞墙,不然会让李茂春逼疯。但红军来了,红军突袭了磨儿垭,把土匪打得落花流水狼奔豕突,把潘婆给救了。潘婆当时已瘦得走了形,她走出牢房时眼睛眯了很久才睁开,一万根针样的光芒一下子拥进她的眼眶。
她长叹了一口气。
红军问她:“我们救了你,你还叹气呀?”
潘婆眉头跳了几下,心想,我晓得你们的来路哟,才从这个盗匪手里到另一个匪盗手里。但潘婆没说出来,她想说也没用。
红军说:“你得救了,你走吧。”
潘婆不信。但红军确实给了她大洋作路费。她信了,但潘婆怎么走?她没力气了,这么个山路她走不了多久就倒在地上作了狼的美食。
潘婆说:“我抬脚的力气都没了,怎么走哟?”
红军说:“也不是让你自己走呀,让你家里人来接。”
潘婆说:“我没家里人,孤老太婆一个。”
红军说:“哈,那样吧,你先在我们队伍待待养养身体,养好了身体再走。”
潘婆鬼使神差竟然跟这些被人说成匪的一群待了些日子,待着待着,潘婆想,不对呀,怎么就匪了?红军“劫富济贫”,你说是匪怎么这么多的人争相入队伍跟了共产党走?处着处着,就觉得红军是开明之师是穷人的队伍。
潘婆在毛浴养身体,养养就养得不自在起来。我不能白吃白喝白让人家养了。她跟红军说,我给你们织布吧。李茂春六十大寿没做成,那些准备做新衣的棉花却让红军缴了,送到织布厂,那还有从别处弄来的棉花。红军说你要闲着觉着无聊你去织布厂看看散散心。他们没把潘婆的话当回事。
但潘婆却真上了织机,她一上织机那架势就让那些妹娃儿婆娘就都鼓眼睛了,再接下来是织出的布,妹娃儿婆娘们捏布在手。
“天!只有潘婆能织出这样的上等好布。”
潘婆说:“我就是潘婆。”她说得很平静,让人觉得这话不真实,但她确确实实就是传闻中的潘婆。不是潘婆能有这等织布手艺?
从此,潘婆的名声在红军里不胫而走。
三
潘婆是徐敬乾特意从毛浴请到王坪来的。红军攻下平梁城,意外缴获劣绅的一批棉花,首长决定把这批棉花给医院。棉花对于医院来说也是重要物品,医院把一部分做药棉,但绝大部分要用来做纱布绷带。
潘婆来了,医院也成立了织布队,潘婆在那做师傅,有事没事,潘婆教那帮妹娃儿织布。她成天拉着脸,不苟言笑,但在织机前却一丝不苟。手艺的事,是东西说话,织出的布剃出的头做出的木器篾器……纱布绷带看去没什么讲究,但要织得软绵,要织得经用,这还真比普通的布要讲究。潘婆在织机上织出的东西就是不一样,让人不得不服。
徐敬乾说:“潘婆织的纱布绷带那哪是纱布绷带哟……”
人家问:“不是纱布绷带那是什么?”
徐敬乾说:“是些妹娃儿柔软的巴掌抚在伤口上……”
徐敬乾这么说,许多伤兵就都凝神感觉,“是哦是哦,软软的是像巴掌抚在伤口地方,怪了,先前觉得这纱布绷带好,但没往妹娃儿柔软的巴掌方面想,你徐参谋一说,还真是的哟……”
徐敬乾笑笑。
一个伤兵突然较起真来:“徐参谋你又没受伤,你怎么知道潘婆织的纱布绷带像妹娃儿柔软的巴掌?”
徐敬乾说:“我问潘婆要了一块正经地贴在手臂上,我就知道了呀!”
伤兵说:“呀!那不吉利的哟,明天天亮时就近找一棵树,把你名字和生辰八字贴上面哟,拍树三下。”
徐敬乾说:“你看你都是队伍上的人了,你还信这些?”
那个伤兵咧嘴笑了下。
四
潘婆不苟言笑,对谁都眯了眼睛看。有外来的人,看了觉得怪怪的,说:“这个老女人怎么这么看人?看谁都好像借了她的米还的是糠哟。”
有人就作答:“这也不算什么,你知道吗?潘婆五十多岁的人了,一直孤寡了过日子,那性格难免有点怪怪。”
外来的人就说:“原来如此噢。”
“但她人是好人。所以,那怪怪性格不算什么,你别惹着她就是。”
说得外来的人毛骨悚然,远远地躲了潘婆那身影,潘婆也不在乎,她不想和陌生人来往。
潘婆不爱和人交往,我行我素,但她却很喜欢凌照照。
是凌照照长得乖巧?看护队织布队洗衣队……清一色都是妹娃儿,许多妹娃儿都长得乖巧呀,可好像都挨过潘婆的骂。
是凌照照布织得好?那就更说不上了,凌照照在招呼队,还兼了洗衣队的活。伤员一多,就忙得陀螺似的,坐在织机前的机会少,都说业精于勤,你没多少时间坐织机前那学织布能学出名堂?
那是两个人沾亲带故?更是不可能的事。
找不出个什么原因,反正好像就是凌照照没被潘婆骂过甚至连脸色也没给过。找不出原因人们背后的说法就多了,当然只能是背后,没人敢把那些话当了潘婆的面说,甚至不敢把话传给潘婆听。王坪伤兵多,重伤的轻伤的不重不轻的伤员都得待在那养伤,你想就是,人躺在那甚至动都不能大动,就是能动也走不出王坪这片个山窝窝,人能不烦不闷吗?人能不无聊吗?就想有些新鲜的猎奇的让人遐想联翩的什么事情说说,也想有什么让舌根嚼嚼,尤其是爱嚼舌根的几个。人偏生就有生来舌头痒的,爱嚼嚼舌根,嚼出的话也无伤大雅,为什么不嚼嚼呢?
“是不是她先前有过个女儿长得和凌照照像。”有人说。
“我看有可能。”听的人说。
“要不就是有个妹妹小时和凌照照一个样……”
“难说难说……”
他们作了无数猜想,就有无数想象,觉得潘婆先前有过个女儿长得和凌照照像这个更靠谱。然后就都兴味盎然地绕了这个“话题”添油加醋,他们把两个人的经历编了一套又一套,编出无数故事来,煞有其事。
有人有意无意传了一句两句到潘婆耳边,他们想试探这些故事的真伪。潘婆不可能不听到些零星的东西,但她没动静,依然先前那样。
潘婆没有风吹草动,那些好事者就觉得那一切是真的。
万小坎来王坪后,也在潘婆那得到青睐。
那天新来的几个娃儿去织布厂帮了搬东西,几个人完事后喝水,潘婆走了过来,潘婆不摸别人头,单摸万小坎的头。万小坎以为那个老女人是欣赏他的头发。他跟潘婆说:“是我师傅帮我剃的,我师傅的手艺。”
潘婆说:“你师傅是谁哟?”
万小坎说:“我是胡泊万的徒弟。”
潘婆说:“蝴师傅呀我晓得哟。”然后又补了一句“蝴蝶的蝴……”她没有笑,她只补了这么一句。
人们也大眼小眼地互相看看,大惑不解一脸的疑云密布。
难道潘婆还有个儿子长得像万小坎?难道……
他们又有了许多想象,但想来想去,越来越不清晰,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还是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想。
有人突然一拍膝盖说:“哦哦!我明白了!”
旁人说:“你明白个什么?”
那人说:“潘婆怕是想给凌照照物色个人,给自己找个好郎婿哟。”
这么一说,竟然有人应和了,“就是就是……”他们说。
然后,说说话题就移到了万小坎和凌照照身上。
“天般地设的一对哟……”有人说。
“是哟是哟。”有人说。
议论就多了,就像大雨天山里的水,粗粗细细在大壑小沟里流了淌了,有一些就流入万小坎他们的耳朵,也流入凌照照的耳朵。但就是好像没有点滴流入潘婆的耳朵。对这点,王坪的这些爱嚼舌根爱听闲言碎语和传闻的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不相信,他们觉得是潘婆装出来的。于是察颜观色,可看不出什么。他们要的就是当事人有点反应,尤其是过激反应,可潘婆万小坎凌照照相安无事。
当然,那些耳根痒的舌根痒的都没什么恶意,睁大了眼睛掏净了耳朵没看见什么没听见什么也就安分了。
五
潘婆有把桃木的梳子,看去有些年头了,木梳深黑油亮,木梳的两头分别雕有龙和凤。这种木梳一般是大户人家嫁妆里的一种,始用于洞房,新婚日子里梳头,龙凤呈祥。潘婆没结过婚,谁也弄不清楚她怎么会有这么一把木梳。有人由这把梳子猜想潘婆出身名门大户。但一把木梳不足以说明什么。也许人家从别处得到这么一把木梳,也许人家潘婆喜欢这种木梳花大价钱买来的也不一定。反正奇怪是一回事,木梳的存在是另一回事。
大家对潘婆本来就感觉神秘,猜想颇多,多一把木梳的想象并没有什么。
潘婆不管那些,只要是晴好天气,每天早上或者黄昏收工之后,潘婆端一把竹椅坐在墙跟下梳头,她表情安祥,旁若无人,梳得细致而从容,好像那不是梳头,好像是进行着某种仪式。她似乎想把这种仪式做得很别致很灿烂。选择那么个时候还有那么个位置,肯定是潘婆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刻意所为。早上,红红的日头从东面跃起,往那面老墙和潘婆的脸和身子抹上微红,尤其是那头乌黑头发,在晨曦更加显眼,散乱中有一种神秘,梳理间有一种优雅。而黄昏时正好相反,坐姿虽然依旧,但情景却不一样。昏黄的光照映着另外半边身子和脸,那把木梳和头发也似乎一成不变,但意境却不一样。散乱中有一种灰暗,梳理间有一种忧郁。
没人能劝她放弃清晨和傍晚对那束头发的摆弄,那种从容的梳理细致的收拾。只有风雨霜雪恶劣天气,潘婆才无奈地在屋里草草梳理,阴雨风雪的日子里,坐在织机前的潘婆谁都觉得少去几分容光。
潘婆很讲究梳头,潘婆当然把那把梳子视作至宝。很少有人能从潘婆那拿到那把梳子,更不要说在手里把玩了。
那把木梳和潘婆一样神秘。
六
红军医院做手术麻醉药一直是个烦恼的事,白军封锁,尤其军火药品相关的物资,红军更是难弄到。伤兵做手术,一般都用的自己熬制的中药。但中药用在麻醉上有个量的问题,用多了一睡不醒也是常有的事。有的伤员说我用我用,有的知道那种可能出现的后果,坚决不用,说拿那根木棍给我吧。医院备有筷子长短拇指粗细的几根棍棍,手术时就横穿在伤员的口里,用绳从后脑地方牢牢绑住。就那么动刀手术,伤兵疼痛难当,却叫不出声。一场手术下来,棍棍上满是牙印,也有直接就把棍棍咬断了的,当然,也有不愿意绑棍棍的,那就必定会有惨叫,那声音瘆人。
然后,就传染似的引发一些哭声。
潘婆总是在号哭暴漾的当机出现在那些棚寮里。伤兵们还是哭,此起彼伏,他们并不在意一个绷了脸的婆娘出现在视线里。他们对于潘婆的到来视而不见。
潘婆依然不笑,但她说话心平气和。她问的是绷带的事,阿红要给伤兵诊伤,叫看护小心地解开那伤兵的绷带。潘婆就问:“这布好用吗?”
伤兵是个四十多岁男人,伤看去并不重,笑笑着说:“好用不好用谁都不愿意用呀。”
看护说:“潘婆,这布用作纱布可惜了。”
潘婆说:“起秀看你说的,救人命哩,哪地方用了有这种用场功德高?”
然后潘婆就给人端茶递水。看护说:“潘婆,这是我做的活,你去忙你的。”
潘婆说:“我忙过了,我想跟他们说说话。”
人家说:“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潘婆回了一句:“不是说话的地方是哭的地方?”
医官马洪说:“想哭就让他们哭哭……他们身上伤痛,心上不好过……”
潘婆嘴唇抿了一下,说:“他们身上伤痛,心上不好过就是要跟他们说话,尤其心上不好过那是被东西堵了塞了。话是流水,说说就大水冲了那些东西……”
医官马洪不知道潘婆抿嘴实际上是对人笑,潘婆对医官马洪笑了一下,她很少对人笑。但医官马洪不知道。他只知道,有些时候说说话,确实能让人解除痛苦忘却忧烦,这对治病确有好处,但要看话题哟但要看说些什么哟。
潘婆平时话不多,说话也硬声硬气,初初接触,听她的话总是不舒服,想说什么也没法说,如鲠在喉。医官马洪就不喜欢听潘婆说话。其实潘婆的话一次两次是有点硬有点说不上什么中听。但听得多了,不知道是习惯了还是什么,大家都能容忍。有的不仅容忍,还很愿意听潘婆说话。当然,医官马洪很忙,他忙得几乎没说话的时间,他当然没法“习惯”。
潘婆跟伤兵们聊天,心平气和,和蔼可亲,与平常迥然不同。她的聊天还真缓解了棚寮里那些沉郁。伤兵们爱跟潘婆说话,其实不要说养伤的人,你个健康的人躺在床上整天呆在那试试?有人跟你吵架你都愿意。整天呆在床上守着头顶的一片茅草屋顶多无聊?
所以,伤兵爱跟潘婆说话。
有一天潘婆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几天我听到你们哭……”
伤兵说:“整天看着阎王在门口招手,整天有人活了抬进来横了抬出去抬去了大城寨,人心上就塞满了乱草,就想哭……”
潘婆说:“就是怕死嘛……我知道你们不是怕痛,是怕死。”
“你看潘婆你说的,世上谁不怕死?”
潘婆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从这个山头到那个山头,从这个岸边到另一处岸边……”
对方说:“看你潘婆说的……”
“怎么?我说错了?”
对方哑了。他没话反驳,他知道自己一说,潘婆就说你没去过那地方你怎么知道?谁也没去过。如果人家说潘婆你难道去过?潘婆就似是而非的说一句,那是个好地方。人家不说了。
潘婆就滔滔不绝,她描绘“那地方”,说黄泉路,说路上开着的彼岸花。潘婆说:“那花只见花不见叶,一朵一个颜色,悬着飘着……”
伤兵听着听着就听入了迷,他们没听人说过这些。屋里果然安静许多,没了哭叫,伤痛的士兵也只轻轻那么哼了。
“花像流水,河里流的不是水是花,你们谁看过?”潘婆说,大家往她脸上看,那表情好像她真的亲临其境过。
流着流着就汇到一处了,不是河了,是一片大湖,湖面上满是五颜六色的花,花会漾上来,成了彩云……那些彩云簇拥了那条路,人就在彩云里游走……”
“啧啧……”有人啧着。
有人急于想听下去,但潘婆说:“明天说明天说,我得织布去了,我出来歇歇的,时间到了……”
七
王坪的人发现这几天潘婆老往病房里跑。万小坎问潘婆:“潘婆,我看你老去那棚寮了……”
潘婆说:“我去那有事。”
“去那地方有什么事哟?”
“重要事!”
万小坎就被勾起了好奇,不仅他,王坪的人多少都勾起了好奇。没事的时候也往棚寮里去。
伤兵们有了许多猜侧,也就有了许多话题。他们说难道潘婆真的去过那地方?说得有鼻子有眼……有人说,那肯定去过,有人说,她胡编哩,也有人说潘婆是仙姑转世吧?
“就是就是!我看是何仙姑转世!”有人嚷嚷了。
潘婆再来时,有人就问:“潘婆,你是仙姑转世吧?”
潘婆抿一下嘴,潘婆不说。潘婆接着说“那地方”。
“谁说那地方黑哩,谁说那地方处身一桶漆里?”潘婆朝坐着躺着的那些伤兵说。伤兵们互相看着,谁也没说过这话呀,谁说过?
潘婆说:“那地方也不黑,那地方放五彩的光,山很安静,水很安静……”
潘婆描绘死亡,把死说成去个地方,轻松得好像一次可意的旅行。她说往黄泉路上走,走走你就看见一树。那棵很大的树,一棵树就罩住了整个村子。那有间屋子是你的去处,是你另一个家哟。那个家可能很简陋,你别看简陋哟,可是一定整洁……屋是石头垒的。四面墙上都开有小窗,窗是木窗,窗台上放着红红的红苕和南瓜,金黄的是柿子哟,也有红,红得耀眼睛,那是干椒,一串串挂着石头墙上,紫的当然是茄子,有不大不小的院子,用松板做的篱笆。院里有石凳石椅,你随时可以坐在那喝茶……花绕蜂飞,鲜艳包围着小屋,有风掠过,吹得树叶沙沙作响……那地方没有白天和黑夜,所以,天没有黑也没有白。人呢,凡间人叫那是鬼,可阴间人还是自己当作人……在那人只是一个随心所遇的影子,见风变成风,见水变成水,见花变成花,见树变成树……没有烦恼,没有忧愁,也没有痛,也没有苦……你想就是,那是个什么地方?……
伤兵听得入了迷,万小坎他们听得也入了迷。
有人反映到徐敬乾那,徐敬乾觉得有点那个,他去听了一回,几次想打断潘婆的话,但看看当时大家投入的表情,忍住了。
八
“你看她跟伤兵说这个……”徐敬乾是总医院的党代表,他留过苏,是彻底的惟物主义者。他把潘婆在棚寮里说的做的点滴不漏地告诉首长。
首长说:“潘婆为什么跟伤兵们说这些?”
徐敬乾说:“我问过她,她说他听到棚寮里老有哭声,她说她不想听那些哭声她跟他们说这些……”
“那后来效果怎么样?”
“哭声真就少了……”
“那就是了……”
“可这是封建迷信那一套,红军不信这些……”
首长当时没说什么,徐敬乾老看首长的表情,但看不出什么。潘婆的言行让他困惑有些日子,他想从首长那得到点拨,但首长好像还想让他困惑下去。对此徐敬乾也很疑惑,摸不透首长此刻心里是怎么样的。
他们进了屋,首长来王坪总要召集大家开个会,不是通报外面的军情,就是调研医院的问题。徐敬乾说了很多,医官马洪也说了很多。首长说:“你们的工作很努力,一切都很好。医院在短时期和条件有限的情况下,能把工作做到这种程度,你们付出了很多。后方有所保障,前方的将士就更有信心了……”
然后,首长说到潘婆,他问大家:“潘婆为什么要这么做?”
有人说:“潘婆想要少些哭声……”
首长继续问:“为什么会有哭声,为什么潘婆那么做会让那地方少了许多哭声?”
没人接话,他们都在想,是呀,为什么呢?
首长说:“是我们工作上的欠缺,我们一直以为医院就是救治伤病,只是注重伤兵的身体,没有注意到伤病员的心理。一个女人,却敏感到了这一点,也用她的方式在帮着伤兵,也帮着医院……虽然那种方式有点古老,所涉及的内容有迷信色彩,但实际的作用在其它方面,是种心理救治……”
徐敬乾想,首长是这么想的,首长到底是首长,比我们看得透,想得深。
首长说:“为什么会有哭声,为什么不是笑声?我们要想一想……王坪是个特殊的地方,应该有笑声……”
九
笑在王坪很重要,这事甚至惊动了首长。
首长隔一些日子会来王坪看看,医院对于一支军队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部门。他惦着,怕出个什么问题。对这的工作,他得常关注。医院若出问题是大问题,有时决定了战争的胜败。
首长又来了王坪,他到处走了走,去了医院的每个角落,觉得一切都还挺好。可想想,总觉得有不对劲的地方。什么地方不对劲呢?想了很久,终想出来了,是周边的氛围。一切都很好,可是怎么氛围不对?那些阳光少年,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年华里,怎么一个个脸上蒙了米口袋?一层厚厚的灰。这样子,对他们的成长不利的哟。还有那些伤员,身体受了伤,心情不能阴郁哟,不能整天呆在这种没笑的灰灰气氛中呀,对身体康复有百害无一利。
“要有笑脸。”首长对徐敬乾说。
“可脸长在人家身上,他们不笑怎么办?”徐敬乾说。
“要想办法呀。”
“我想过了,我动员大家唱歌,他们不唱。”
“总会有办法的。”首长说。
是因为要引来笑,首长专门给徐敬乾有过交代,一定要成立剧社,一定要排出节目,一定要好好给伤员们演出,这也是医院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首长说,潘婆这么个女人都注意到的事,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注意呢?医院不仅治疗肉体的伤,更应该注重伤员的心理上的伤。首长说。
首长说:“医院要有自己的剧社,唱歌跳舞演文明戏,既可以活跃气氛,也可以教育大家,尤其是那些俘虏伤兵。”
徐敬乾做党代表,也管了后勤,一直也是夜校的校长兼先生,现在却成天琢磨建剧社的事。他想,要建剧社,首先要挑选能歌善舞的人才。他想了想,医院这里有上千号人,唱歌跳舞的人才肯定是不缺的。就是平常不唱不跳也难说有潜在的才能,只是没被挖掘出来。尤其是那些娃儿妹娃儿,他们正是能唱会跳的年纪,应该找得出“人才”。
可大家都不肯开这个口,这里开口是指唱歌。也许平常也唱歌的,但气氛使然,歌只在肚子里唱不在口上唱,歌不出口,那怎么辩得出好坏高低?
徐敬乾想来想去想出个主意,再上课时,他说上堂音乐课。
“什么叫音乐课?”
“就是教大家唱歌子。”
“哦?!哦?!”大家觉得这事有些意外。
徐敬乾也挑了一晚上歌子,先是选了《拉把胡琴唱给白军听》,觉得这歌说唱味浓,政治味也浓。又选了《消灭刘湘作战歌》,也觉得不妥,这是战斗进行曲,豪迈是豪迈,但属于直了噪子吼的那种,听不出唱歌技巧。想想,就选了《八月桂花遍地香》中的主调。
《八月桂花遍地香》是红军剧社一直演的一出歌剧,从鄂豫皖就一直演着,深受军民喜欢。且这歌是民歌,曲调好,也是抒情歌子,能唱出情绪听了也不乏味。
那天夜里,伤员们听得卫校的大教室里歌声响起,他们觉得很诧异,他们互相看了看,轻伤的说看看去。重伤员起不了身,但可以听,他们支了耳朵听。
支了耳朵听的还有潘婆,潘婆在黑暗中织着绷带,全王坪也许全通江只有她不用亮灯黑灯瞎火能织布。这是功夫,不是三天两天能学到的技艺。潘婆晚上闲了没事,就会坐在织机边从容地织一会儿布。突然那夜有人唱起了歌。王坪的夜很静,没了白天的喧嚣。白天打铁的声音凿木的声音捣药碾药的声音尤其是伤兵手术时的号叫声音此起彼伏,难得有个清静时刻。只有到夜里,王坪除了蛙虫喋噪和猫头鹰的号啼及远处的狼嚎,就没有别的声音了。所以,卫校那边传来的歌声,清新悦耳。
潘婆想,你们唱你们唱去,她依然摸黑织着她的布。
责编:朱传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