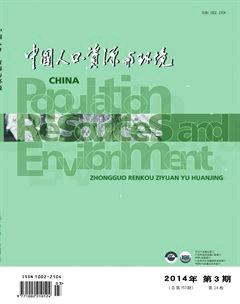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陈伟 王喆
摘要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关键词农地转用;农地制度;软约束;土地征收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4)03-0061-08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403010
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形成“土地城市化”现象。人口城市化相对滞后于土地城市化,是各国的普遍特征,但在中国,这一特征表现得尤为突出,并导致了土地资源浪费、财富分配失衡、社会矛盾激化等一系列问题。若想理解为何在中国存在农村土地向城市土地的过度转用,就必须分析地方政府的行为,因为地方政府是农地向市地转用的决策主体。认识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除了要分析其内在利益权衡之外,还要分析它所面对的外部制度约束。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前者,本文将主要针对后者展开分析。
1问题的提出:农地转用模型中的外部制度约束建立高效的农村土地向城市转用制度,是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的话题。农村土地向城市转用,实际上是土地资源在不同用途的配置问题,而政府和市场是两种主要的配置手段。当然,还有一种治理机制是社会自治,但究其根本,仍是基于平等协商,体现的同样是市场逻辑。两种手段都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因此,理论上讲,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乃至更深层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大化,需要综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以避免出现严重的“市场失灵”或“政府失灵”,或者说是在二者之间进行权衡,两害相权取其轻。当然,农村土地城市转用不仅仅是资源配置过程,同时也是利益调整过程。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难实现纯粹技术意义上的最优配置,最终的配置方式往往取决于利益博弈。
由于资源禀赋、发展阶段、经济模式和利益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不同国家农地转用制度的基础、功能、目标与结构不同。但相当一部分在农地转用方面较为成功的国家都高度重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注重清晰界定产权、限制政府权力、合理规划引导和允许自由流转。当然,个别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小国/地区(如荷兰、新加坡、香港)建立了计划主导的土地资源配置方式,但它们同时确立了规范的宪政框架,以确保行政过程运行受到有效监控。也就是说,总体而言,在市场化国家,土地征收(征用)只是市场失灵的少数情况下采用的一种农地转用方式,并且要经过严格的公益限制、补偿限制和程序限制。
在农地转用市场化国家,农地转用主体是多元化的,因此,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的市地地价与农地地价趋于一致,而农地转用后市地的溢出效应,是由社会主体分散享有的,而城市化扩张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增长由政府享有,与其转用决策主体无直接关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虽不是利益中立地位,但直接干预程度受限,并且很多时候更侧重扮演着管理者角色。
陈伟等: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年第3期中国在农村土地城市转用领域采用的是一种政府垄断、高度行政化制度模式。政府(主要是地方政府)几乎是农地转用的唯一合法主体,农地转用的利益享有是高度集中化的。农地转用为市地后,除了能促进增长、改善就业从而获得更好的政绩评价外,地方政府还可以获取大量财政收入。并且,由于是双头垄断,地方政府还能通过“低入高出”获得丰厚的土地出让收益。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再只是管理者,也不再相对被动地分析农地转用的利益,而是通过“经营城市”和独家垄断来获得经济收入。除此之外,土地批租制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追求短期土地收益,以GDP为核心的考核机制助长地方政府过度转用。这些都会使得地方政府倾向于高估城市土地的综合价值。
另一方面,在土地资源量既定的条件下,农地转用为市地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对农地价值做出合理评估,可能会影响到其决策,将农地转用控制在一定限度内。但现实情况是,在高估市地价值的同时,地方政府在农地转用决策时,往往又会忽视(没意识到或意识到了不愿做)农地的多重价值。除了经济价值外,农地的外部性价值还包括粮食安全价值、生态保护价值、社会保障价值等(农村宅基地还有住房保障价值等)。
此外,现行的政绩考核和官员任免体系导致了政府行为的短期化,使得地方政府在农地转用过程中往往会轻视“不可逆风险”。
本文并不打算对这一模型展开全面分析,而是聚焦于农地转用的外部制度约束(模型中的RE),重点分析制度内涵及其实效,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方向和初步思路。这种来自外部的制度约束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见图1):一是土地产权人的自主维权,这可以视为一种来自基层、自下而上的机制;二是中央政府的垂直管控,这可以视为来自高层、自上而下的机制;三是本级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监督,这可以视为一种基于权力制衡的平行机制。
所有制和产权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所有制清晰条件下的产权模糊,是我国公有制的基本特征,在土地领域,这点表现的尤为突出。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在不到十年的短时间内进行了数次土地制度改革,逐步确立了二元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改革开放后,我国虽未改变土地所有制,但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对土地产权体系进行了调整。但是,为了建立和维持高度行政化的农村土地向城市转用制度,国家对国有和集体两种所有制框架下的产权采取了不同的改革思路。对于国有土地,国家以确立可市场化的土地产权目标,赋予独立而清晰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及担保权等。对于集体土地,国家则以有限市场化为目标,仅在农业用途范围内赋予较为清晰的土地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流转权),为了阻止农地(包括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替代性地进入农地转用市场,维护行政力量在土地转用过程中的唯一性,国家基本剥夺了农民自主的农地转用权,并刻意维持了集体土地产权的内在模糊性。
2.1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法律禁限
除了国家为公共利益而征收农民土地而发生的农村土地城市转用外,在符合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的前提下,如果国家允许农民将自己的土地转用为城市建设用地,那么这种流转的发生可能出于两种动因:一种是主动流转,即农民作为土地的所有者或实际权益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将非农用途土地的使用权出售给土地需求方,这可能是主要方式;另一种是被动流转,也就是农村土地作为抵押物,因为相关权利的实施而被转移或拍卖。
在现实中,国家通过直接的法律规定构建起了产权壁垒,有意地禁止或限制了农民将农地转用为城市土地,即农民自主的土地非农化。按照我国法律规定,集体土地使用权(承包经营权)是一种基于成员权的派生产权,因此,它只能在一定期限内“流转”,而不能一次性买卖,因为国家必须保护集体成员的基本生存权。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就意味着在“城市”范围内的土地必须转为国有,必然不存在集体所有性质的土地,即使有,早晚也要被消除,否则就违宪。我国《物权法》第128条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依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有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转包、互换、转让等方式流转,但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并且,未经依法批准,不得将承包地用于非农建设。在《土地管理法》中,使用国有土地规定的范围从“城市”进一步扩大至全部“建设”用地。但有关法律做了一些例外规定,以确保农民集体的“自用权”。在一些省的实践中,集体建设用地以工业用地形式转让和进入市场却被网开一面,最典型的就是以土地股份合作制形式招商引资(如广东南海模式)。这种土地开发性质其实已经超出了“自用权”的范围。但对利用集体土地建设住宅,国家一直是严格禁止的态度。
对于作为集体建设用地主体的宅基地及农房的流转,由于实行了“房地分离”政策,农房的私有产权属性得到了承认。因此,从法理上讲,即使宅基地使用权禁止转让,宅基地上的房屋(农房)仍可以转让。此外,对于宅基地转让,尽管有些地方出台了禁止性措施,但多数地方都默许(但不鼓励)宅基地在本集体内部成员之间的流转,与此同时,《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但对于城镇居民购买农房、宅基地使用权和建在集体土地上的“小产权房”,国家则严令禁止。
此外,与农地转用权直接联系的另一种土地权属,就是集体土地的抵押权。在这方面,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也存在着显著差别。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企业和居民可以去银行申请抵押贷款。但是,集体土地则被明令禁止用作担保抵押物。1995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下列财产不得抵押:(一)土地所有权;(二)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即使有些地方进行了一些探索,最终也难以形成一般经验而在更大范围内推广。有些地方(如浙江温州乐清)虽然尝试了“农房抵押贷款”,取得了初步成效,但遇到了一系列制度瓶颈。
2.2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
在限制农民自主的土地非农化转让权的同时,为保障政府主导的农村土地城市转用体制,现行制度还利用集体所有自身的缺陷,有意地维护了其产权模糊。
虽然在国有土地产权关系链条中也存在公有制内生的委托代理问题,但国有土地制度的产权关系相对清晰。集体土地制度的产权关系有些含混,它既不同于共有制度,也不同于公司制度。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人可以对财产进行直接管理和分配;在后一种制度下,股东可以通过公司治理机制影响管理层的决策结果。在集体所有制下,农民虽然获得集体成员的名分,往往缺乏参与管理、影响决策的手段和机制。此外,在现行集体所有制下,每位集体成员的“退出权”被剥夺[1],也就是说,农民缺乏“用脚投票”的制约机制和退出利益兑现机制,即使农民个体对所谓集体的决策不满意,往往也只能选择被迫接受或 “净身出户”,现实中缺乏来自外部的制衡和监督机制。
上述治理机制造成的后果就是,除了农用地的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的使用权等相对清晰外,其他一系列集体土地产权(如处置权、收益权)则在非土地所有者的政府(特别是乡镇)、作为所有者的集体组织和作为使用者的农民个人之间模糊地配置。当然,不同的地区差异性也比较突出,中国各地农地制度呈现出高度多样化特征[2]。
集体土地产权模糊性,还可以从农民对土地归属的认识中得到验证。在作者组织的征地制度问卷调查(2013)结果显示:认为农村土地属于农民个人所有的占39%;其次为国家所有,占32.75%,村集体所有只占25%。
这种集体土地的产权模糊恐怕并不是自发的,而是政府主导下的自觉行为,也就是说是一种“有意的制度模糊”,其用意是为政府在经济发展中随意支配土地资源留下空间[3]。集体所有制是由国家控制但由集体来承担受其控制结果的一种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安排[4]。
2.3产权缺陷下的集体决策问题与维权限制失灵
由于国家基本剥夺了农民通过市场自主转用农地的权限,更重要的,有意维持了集体土地的产权模糊性,在面对不合理的征地行为时,农民就不能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并通过多种方式对征地进行抵制。这就为政府通过征地等手段主导农地转用,最大限度地获取土地增值收益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集体所有制下的产权模糊性还导致了搭便车心理和机会主义行为,再加上基层政治与农民权益保护方面的缺陷,农民个体往往不愿意出头“惹事”。这在我们的征地问卷调查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我们设想了农民对征地做法不满可能所采取的方式(可多选):①忍气吞声,听从村集体和政府安排;②出面与本地乡镇政府进行反映、协商;③去上级政府部门上访、举报;④去法院起诉,用法律保护自己;⑤通过网络或媒体曝光,争取社会支持;⑥与政府对抗,充当钉子户;⑦不知道如何去做。从调查结果来看,有超过一半的村民选择忍气吞声,听从村集体和政府安排,只有少数村民选择上访、去法院起诉、媒体曝光和充当钉子户等带有对抗性的方式。
在农民个体不愿意出头的情况下,作为集体土地的产权代表的村民委员会(或者说村干部)能否出面伸张农民的正当利益呢?遗憾的是,村委会和村干部往往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并不完全能够代表村民的利益。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虽然大多数被调查农民表示村干部都经过村民选举产生,但是,仅有27.3%的村民表示,村干部是村民民主选举产生;23.5%的村民表示,村干部选举过程中存在贿选或者贿赂选民的情况;另有29.5%的村民表示选举只是形式,村干部实际是由乡镇政府领导安排任命。
在我国的乡村治理中,村干部实际扮演着“双重代理人”决策,接受农民和上级政府的双向委托。但由于其个人利益主要受制于基层政府,因此,他们更可能采取“向上看”的立场,不能代表。这点也反映在了问卷调查回答中,对于村集体和村干部能否“代表全体村民诉求,为大家争取合理利益”,回答者给出了偏负面的评价,分值为3.35/7(1-7分,4分为中间评价)。
综上,由于农民个体不愿出头,农民集体又无法充当维权主体,这就为地方政府征地和转用农地奠定底层基础。
3中央政府的多目标性与纵向控制弱化
土地资源的用途管制和国有建设用地指标计划管理,是国家对土地资源在不同用途、不同区域、不同时间进行配置的基本手段,是中央约束地方转用农地的两个主要工具。
3.1通过用途管制划定了一定空间的农地转用
土地用途管制(Land use regulation)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为了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通过编制土地利用及其他控制性规划确定不同区域土地的用途和使用限制条件,并要求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严格按照规划用途利用土地的一种制度。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土地用途管制的名称不尽相同,如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称之为“土地使用分区管制”(Land use zoning)、瑞典称之为“土地利用管控”(Land use control)、英国称之为“土地规划许可制”、法国和韩国等则称作“建设开发许可制”[5]。
土地用途管制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制度。从性质上讲,用途管制是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目标是减轻土地资源使用中出现市场失灵所带来的损害,促进土地资源的节约、集约利用和可持续开发。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的目标存在一些差异,概括起来,主要分为两类:环境保护和农地保护。在一些农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如美国、加拿大,土地用途管制的主要目标是环境保护;在一些人多地少、耕地短缺的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用途管制强化的初衷是农地保护[6]。
我国从1990年开始就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9年修订后的《土地管理法》(第四条)正式写入了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在我国,实行用途管制制度的总体目标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可持续开发,其中,首要目标是保护耕地。《土地管理法》第三条规定: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形成以用途管制为基础,基本农田保护、占补平衡、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制度相互配合的耕地保护制度。《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了规划期土地利用目标: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规划2020年耕地保有量12 033.33万hm2( 18.05亿亩),确保10 400万hm2(15.6亿亩)基本农田不减少、质量有提高。
18亿亩耕地保护特别对农村土地向城市转用构成了有力制约。特别是对于占耕地80%以上的基本农田,国家还以国务院法规的形式出台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并规定占用基本农田的审批权限在国务院。
3.2通过指标计划控制一定时期的农地转用
我国对农地城市转用指标实行了层层分解的计划管理,其依据就是土地利用规划。中国的农地转用指标体现为三个配额,即建设用地总量配额、耕地保有量配额、土地利用年度配额。按照时间长短,计划指标分为长期指标、中期(五年)指标和年度指标三类。在我国,土地指标控制权掌握在不同层级政府手中。
首先由国家编制《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该规划纲要会对未来15年左右的全国土地利用做出统一部署,并对各省(市、自治区)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建设用地等指标做出了具体规定。《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提出,到2020年,全国新增建建设用地585万hm2 (8 775万亩),通过引导开发未利用地形成新增建设用地125万hm2 (1 875万亩)以上。
在国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基础上,各省级政府对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分解,并最终形成土地利用年度计划,通过年度计划对各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和耕地保有量计划指标做出限定。在省级土地利用规划会逐次分解至各地(市),然后由各地根据本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具体指标的使用方式和项目。
此外,考虑到地方发展和建设的实际需要,国家施行了地方耕地总量占补平衡政策,试图通过这种“动态平衡”的管理方式,在确保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前提下,赋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但是,占补平衡的范围一般被限定在县域之内,国家严格禁止地方擅自开展跨县、跨地区、跨省的异地占补平衡、异地代保。除非被列入改革试点地区,如成都是全市范围、重庆是全“省”范围,其他地方被禁止异地的土地发展权交易,浙江、安徽等地在这方面曾进行了大范围试点,但2008年被《国土资源部关于严格耕地占补平衡管理的紧急通知(国土资电发[2008]85号)》叫停。
3.3增长目标优先条件下的纵向控制失灵
以上对以用途管制基础、指标管理为手段的垂直控制体系进行了介绍,那么,这种制度能否真的抑制地方的土地转用冲动呢?是否真的完成了保护耕地、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目标呢?实际上,效果似乎离制度设计者的初衷差距甚大。
理论上讲,面对地方政府的农地过度转用,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应该代表国家的长远利益进行管制。现实中,中央政府也是努力这么做的。但遗憾的是,中央政府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包括经济增长、耕地保护、农民利益维护、环境保护、政治稳定等方方面面,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增长成为全国的优先考量。中央政府在政策目标上的波动与摇摆,再加上财税等体制方面不顺,使得中央对地方农地转用的监督明显弱化,对违法行为也缺乏必要的惩罚手段。
有学者对我国的城市空间增长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土地资源条件的限制(如耕地保护等)对城市空间增长约束并不明显[7]。不少地方甚至将各种规划作为推动城市空间扩张所谓依据,从而使其失去了客观性和科学性。
以第二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6-2010)为例,1997-2010年全国非农业建设占用耕地控制指标2 950万亩,实际到2002年就有2/3以上省份的耕地占用突破了2010年的控制指标,到2005年就已用完全部耕地占用指标。
4现行政治架构的局限与横向监督缺失
理论上讲,在一些地方自治的民主国家,对于农地转用中涉及的规划调整和土地征收,还需要经过地方代议机构(议会)或独立第三方的审查和司法机构的裁决和监督。其中,前者侧重审查农地转用和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后者侧重审查征地补偿是否合理、被征收人权益是否得到了有效维护。下文主要通过对比分析的方式说明,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架构上,这种横向的制衡机制基本上是缺失的。下文将以法治国家的做法为标杆,通过中外比较说明上述观点。
4.1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
对于何种征地符合公共利益,前文已经有所论及,在此再简单分析一下。在美国,美国的每一项具体的征地行为必须得到立法机关的授权。政府在征地之前,要公布其发展规划与征地规划,而被征地人及利益相关者可以就此向政府提出看法,政府应根据这些看法调整征地规划。此后,政府要举办若干次公众听证会(何时及如何举行听证会,各州规定不尽相同),以便让公众当面表达自己的看法。即使所有规定的听证会都举办过,土地权益人如果政府有违反法律规定或程序的话,仍可以提出抗辩。在美国,即使是像全国性高速公路这样的国家性公益项目,也会在项目动工之前保障公众参与权,使其了解该项目并表达意见。如果双方不能在此阶段就征收方案达成一致,不动产所有者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查会就征地的性质是否是符合公共目的、符合环境评估要求或联邦或州的其他要求做出判决。如果法院驳回政府征地请求,若想继续征地,市政府都必须回到整个流程起点,开展新一轮的公众听证会。
在德国,依据就是土地利用是否符合规划,而这些规划是经过议会批准的,是在公众广泛参与下制定的,并且是这些规划是标明每块土地界限的详尽规划,而不是粗略的城市总体规划。
尽管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立法机构缺乏独立性,其决定能否代表民意,值得商榷,但是否征地符合公共利益,并不需要立法机构的授权与确认,而是行政机关直接决定。
行政机关实施征地权的范围由规划来界定,并且主要是土地利用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的约束力相对较弱。这些规划都是粗线条的,并没有具体到每个微观地块。市、县级政府都可以对具体的微观地块向省级政府提出征地申请,只要不违反国家用途管制及其他政策规定(如产业管制)并且没有超出用地计划指标,省级政府就认为该征地项目可以通过。因此,省级政府的审查只是合规性审查,而不是也不可能做到公益性审查。这么看来,尽管要通过省级政府的审批程序,但每个征地项目的实际决定权基本掌握在了市、县政府手中。
在上述过程中,公众无权参与,甚至连知情权也被剥夺,因为这些规划在政府正式公布前,往往都是涉密的。当然,规划制定过程会邀请专家参与,但他们都是技术专家,在多数情况下,其行为目标是服从和服务于地方领导和规划部门。
4.2农地征收补偿和强制执行缺少独立司法(第三方)介入在美、德等国,地方议会做出了土地征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农地转用决策后,法院或者独立的第三方(德国为地区专员)将会充分介入,由其对征收补偿数额及程序进行有效监控。具体而言,从流程上看,第三方介入分为四个阶段:自主协商补偿;申请土地征收;征收方案确认;征地强制执行。
4.2.1政府(或开发商)与土地权益人先要平等协商
征地虽然带有一定强制性,但它的动用是以补偿合理为前提的,而不是反过来,因为可以强制,所以否定市场价值。因此,在法治国家,开发商在申请征地之前,要向土地权益人协商购买,这种协商是平等自愿的,它并不以“必然征地”为前提。
在德国,这种自主协商是必须的,体现了宪法保护私人土地所有权保护的基本原则以及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并使得土地所有者可以通过协商过程了解更多信息,降低开发商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8]。
在美国,在进入征收程序前,不动产所有者也可以和市政府进行谈判,由市政府以购买的方式获得土地,在政府相关部门批准后生效(这一过程也被称为“行政调解”)。在美国,实际上非常强调行政调解,避免案件走上法庭,各州都制定了申诉程序,建立了申诉委员会。
在中国,并不存在这样的平等协商机制。在城市规划范围内(“圈内”),有的情况下,开发商会与村集体代表(村领导)、村民在实施征地前进行补偿协商,但这种协商是在“必然征地”的前提下进行的,并且有时也只是与村领导之间的利益“勾兑”,其他村民则没有知情权和参与权。
4.2.2土地征收应是必要乃至唯一可用手段
这一阶段的中心目标是共同论证征地的必要性。因为,即使符合公共利益,也未必非得通过征地手段,政府(或开发企业)必须证明进行征收是出于无奈。
在德国,自主协商失败后,开发商要向拟开发项目所在区域的上一级(而不是本级)行政机构(地区专员)提出土地征收申请。地区专员除了进行公共利益审查和符合规划审查外,还要考虑,开发商在自主协商阶段是否尽力。如果地区专员评估后认为,非征地不可,就会通过征地审查。如果土地权益人不同意征地决定,可向地区专员提出不同意见或向高级行政法院对地区专员提起诉讼,并可以一直上诉至联邦行政法院。
在美国,行政部门实施征地的必要性还要经受司法审查。政府首先向法院提出征收申请,并将征收通知所有的利益相关方。随后,法庭会对征收申请进行判决,同样,政府也必须在法庭上说明征收的必要性。如果被征收人不同意地方法院的征收判决,可以逐级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在我国,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第一,征地审批主体是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第二,农用地转用审批与土地征收审批是同一过程,只要获得了前者或者说建设用地指标的权利,后者是自动实施的。
4.2.3即使必须征地也需制定稳妥的实施方案
在征地决定成为事实、无法再改变的情况下,政府便开始协商制定征地方案。但这不意味着政府可以为所欲为,而是要与被征地者认真协商。在德国,在征地开始时,双方要就征地的具体方案继续进行口头协商,并由地区专员做出决定。如果被征地者不同意地区专员关于征地方案的决定,可以依照前述程序一直上诉至联邦行政法院做出终审判决。在美国,在多数征地纠纷案件中,被征收者并不质疑“公共使用”,更多的争议都是围绕补偿金额问题。[9]征地补偿的确定是以法庭为中心开展的。双方都要向法院告知自己的评估价值,法院会首先让双方协商,尽量达成和解(也被称为“司法和解”)。事实上,美国超过95%征地案件是以司法和解的方式结束的。如果不能达成和解,就要进入司法诉讼程序,这使得政府无法控制征收的时间和方式。
在中国,征收土地方案是申请农地转用方案时一并上报的,与征收权批准是同一概念。因此,在征地审批获得通过后,方案也就同时确定了。在征地方案批准后,便进入了“两公告一登记”程序。《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对此做出了规定。对补偿标准有争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协调;协调不成的,由批准征收土地的人民政府裁决,也就是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实际执行中以后者为主)。
4.2.4法院应是强制征地的唯一合法主体
在征地决定获得批准后,就进入到了征地执行阶段。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先补偿后征地”问题。在法治国家,一般都是要求先补偿后征地。其次,在征地执行过程中,被征地者的知情权和其他相关权利仍受到保护。在德国,被征收人仍可以对地区专员的征收决定依次向各级行政法院提起诉讼。在美国,被征收人在收到的搬迁通知中,应该说明搬迁的期限、被征收人在接下来的程序中享有哪些权利,其中就包括申诉和接受政府援助的权利。此外,在居民和企业被搬迁时,都可以获得搬迁费用的补偿。对于居民搬迁补偿,政府往往还被要求提供“体面、安全、卫生、足够大的”替代住所。最后,关于强制拆迁的实施,法治国家都是通过公权实现的。在美国和德国,如果出现拒不搬迁的“钉子户”(所有者或租户),政府应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我们就以上三个方面看中国的情况,就会发现差距所在:第一,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中对“先补偿、后征地”做出明确规定,反而规定:“征地补偿、安置争议不影响征收土地方案的实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第二,在执行阶段,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和合理安置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征地过程中,农民流离失所的情况并不少见;第三,对于征地拆迁的批准与执行主体,“中国特色”也十分明显。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6条:征地申请批准后,由县级以上政府予以公告并组织实施。实际做法往往是党、政、公、检、法各个部门齐上阵,这在提升“强制力”和加快征地速度的同时,也引发了严重社会矛盾。
5总结与启示
讨论的主题是:在以地方政府为决策主体的中国农地转用模型中,外部的制度性约束包含哪些要件,各自的实效如何。
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中国,对于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无论是源自集体土地名义所有者即农民的自我维权,还是来自中央(或省级)政府的垂直控制,抑或是地方立法和司法机构对同级地方政府的权力制衡,都不能有效抑制地方政府转用和征收农地的冲动。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
上述农地转用模型及制度分析框架,也为农地转用制度改革提供了方向指导。除了从内因上弱化地方政府过度转用农地的冲动外(如改革绩效考核机制,完善财税制度和土地财政体系,改革土地出让模式),从制度约束这一外因出发,应该从三个方向理顺农地转用制度体系:
第1,从农民维权的角度看,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是基础,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
第2,从中央政府控制的角度看,应该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加强统筹协调,适当弱化GDP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关键是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
第3,从地方横向的监督制衡角度看,应该建立平行的公益审查与科学决策机制,增强政府决策和行政过程的透明度,特别是强化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功能,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逐步弥补对农地转用和征收的制衡缺失问题。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俊.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三题[J].管理世界,1999,(3):184-195.[Han Jun. Three Topics on China Rural Land System Construction[J]. Management World,1999,(3):184-195.]
[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 2000(2):54-65.[Yao Yang. The System of Farmland in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000(2):54-65.]
[3]何·皮特.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10. [Peter Ho.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Land Ownership,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8:1-10.]
[4]周其仁.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J]. 管理世界,1995,(3):178-220.[Zhou Qiren. Reform in Chinas Countryside: Chang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Ownership (First Part) [J]. Management World, 1995,(3):178-220.]
[5]张全景,欧名豪. 中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9-51.[Zhang Quanjing,Ou Minghao. On Land Use Regulation Effect on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2008:49-51.]
[6]李茂. 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国土资源情报, 2003,(10):1-6.[Li Mao. Land Use Regul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Canada[J]. 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2003,(10):1-6.]
[7]杨东峰,熊国平.我国大城市空间增长机制的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J].城市规划学刊,2008,(1): 51-56. [Yang Dongfeng,Xiong Guoping. Mechanism of Urban Spatial Growth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J]. Urban Planning Forum,2008,(1): 51-56.]
[8]王维洛. 德国、中国征地拆迁的程序与赔偿之比较[M]//洪范评论第7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71-88.[Wang Weiluo. A SinoGerman Comparison on Land Acquisition Procedure and Compensation[M]//Journal of Legal and Economic Studies(7).Beijing: China Law Press, 2007:71-78.]
[9]托马斯·米勒. 美国土地征收及纠纷解决机制[C]//中美土地征收和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研讨会文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2008:327-328. [Thomas Merrill. Land Acquisition in USA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C]//Proceedings of SinoUS Land Acquisition in USA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orkshop. Beij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Law, China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2008:327-328.]Abstract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sof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to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process in China and gives some proposal for further reform.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which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policymakers taking four factors into account including rural land value, urban land value, irreversibility risk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st variable.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limit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y farmers selfadvocacy because of the legal defect on farmer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and inherent land right ambiguity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there is a longlasting vertical control failure because of the multiobjective issue which give more weight to economic growth, 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limit local land conversion by use regulations and planning measures. Additionally, in view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could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use without horizontal counterweights because there is no democratic mechanism to check the land conversion and Land acquisition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and the courts have not intervened the compensation and enforcement process effectively eith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ree failures”, including weak selfadvocacy of farmers, hesitant vertical control and powerless horizontal check, have resulted in serious soft institutional restraint to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omina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leads to excessive conversion of rural land, inefficient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outofbalance of land value increment during us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above analysis, thre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1) Improving the farmers capability of maintain their own benefits, which requiring to construct a clear rural land property system, especially empowering farmers with the right to convert their rural land independently, and introducing market mechanism; 2) 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ominance to land conversion at local levels, conform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mproving and enforcing main part functional district planning,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l politic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ystem,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equalizing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nationally; 3) enhancing balance and check of legislature and judiciary to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rural land institutions; soft constraints; land acquisition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俊.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三题[J].管理世界,1999,(3):184-195.[Han Jun. Three Topics on China Rural Land System Construction[J]. Management World,1999,(3):184-195.]
[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 2000(2):54-65.[Yao Yang. The System of Farmland in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000(2):54-65.]
[3]何·皮特.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10. [Peter Ho.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Land Ownership,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8:1-10.]
[4]周其仁.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J]. 管理世界,1995,(3):178-220.[Zhou Qiren. Reform in Chinas Countryside: Chang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Ownership (First Part) [J]. Management World, 1995,(3):178-220.]
[5]张全景,欧名豪. 中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9-51.[Zhang Quanjing,Ou Minghao. On Land Use Regulation Effect on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2008:49-51.]
[6]李茂. 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国土资源情报, 2003,(10):1-6.[Li Mao. Land Use Regul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Canada[J]. 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2003,(10):1-6.]
[7]杨东峰,熊国平.我国大城市空间增长机制的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J].城市规划学刊,2008,(1): 51-56. [Yang Dongfeng,Xiong Guoping. Mechanism of Urban Spatial Growth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J]. Urban Planning Forum,2008,(1): 51-56.]
[8]王维洛. 德国、中国征地拆迁的程序与赔偿之比较[M]//洪范评论第7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71-88.[Wang Weiluo. A SinoGerman Comparison on Land Acquisition Procedure and Compensation[M]//Journal of Legal and Economic Studies(7).Beijing: China Law Press, 2007:71-78.]
[9]托马斯·米勒. 美国土地征收及纠纷解决机制[C]//中美土地征收和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研讨会文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2008:327-328. [Thomas Merrill. Land Acquisition in USA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C]//Proceedings of SinoUS Land Acquisition in USA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orkshop. Beij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Law, China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2008:327-328.]Abstract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sof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to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process in China and gives some proposal for further reform.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which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policymakers taking four factors into account including rural land value, urban land value, irreversibility risk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st variable.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limit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y farmers selfadvocacy because of the legal defect on farmer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and inherent land right ambiguity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there is a longlasting vertical control failure because of the multiobjective issue which give more weight to economic growth, 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limit local land conversion by use regulations and planning measures. Additionally, in view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could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use without horizontal counterweights because there is no democratic mechanism to check the land conversion and Land acquisition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and the courts have not intervened the compensation and enforcement process effectively eith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ree failures”, including weak selfadvocacy of farmers, hesitant vertical control and powerless horizontal check, have resulted in serious soft institutional restraint to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omina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leads to excessive conversion of rural land, inefficient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outofbalance of land value increment during us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above analysis, thre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1) Improving the farmers capability of maintain their own benefits, which requiring to construct a clear rural land property system, especially empowering farmers with the right to convert their rural land independently, and introducing market mechanism; 2) 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ominance to land conversion at local levels, conform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mproving and enforcing main part functional district planning,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l politic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ystem,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equalizing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nationally; 3) enhancing balance and check of legislature and judiciary to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rural land institutions; soft constraints; land acquisition
(编辑:李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韩俊.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三题[J].管理世界,1999,(3):184-195.[Han Jun. Three Topics on China Rural Land System Construction[J]. Management World,1999,(3):184-195.]
[2]姚洋.中国农地制度: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 2000(2):54-65.[Yao Yang. The System of Farmland in China: An Analytical Framework[J]. Social Science in China, 2000(2):54-65.]
[3]何·皮特. 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10. [Peter Ho. Institutions in Transition: Land Ownership, Property Rights and Social Conflict in China[M].Beijing: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8:1-10.]
[4]周其仁. 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J]. 管理世界,1995,(3):178-220.[Zhou Qiren. Reform in Chinas Countryside: Chang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Ownership (First Part) [J]. Management World, 1995,(3):178-220.]
[5]张全景,欧名豪. 中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耕地保护绩效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49-51.[Zhang Quanjing,Ou Minghao. On Land Use Regulation Effect on Arable Land Protection in China[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2008:49-51.]
[6]李茂. 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国土资源情报, 2003,(10):1-6.[Li Mao. Land Use Regulat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such as US and Canada[J]. Land and Resources Information, 2003,(10):1-6.]
[7]杨东峰,熊国平.我国大城市空间增长机制的实证研究及政策建议[J].城市规划学刊,2008,(1): 51-56. [Yang Dongfeng,Xiong Guoping. Mechanism of Urban Spatial Growth in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 [J]. Urban Planning Forum,2008,(1): 51-56.]
[8]王维洛. 德国、中国征地拆迁的程序与赔偿之比较[M]//洪范评论第7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 71-88.[Wang Weiluo. A SinoGerman Comparison on Land Acquisition Procedure and Compensation[M]//Journal of Legal and Economic Studies(7).Beijing: China Law Press, 2007:71-78.]
[9]托马斯·米勒. 美国土地征收及纠纷解决机制[C]//中美土地征收和土地纠纷解决机制研讨会文集.北京: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研究中心,2008:327-328. [Thomas Merrill. Land Acquisition in USA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C]//Proceedings of SinoUS Land Acquisition in USA and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Workshop. Beijing: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ve Law, China National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2008:327-328.]Abstract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analyze the soft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 to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process in China and gives some proposal for further reform. The author constructs a decisionmaking model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which the local governments are policymakers taking four factors into account including rural land value, urban land value, irreversibility risk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e article focuses on the last variable. It points out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limit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by farmers selfadvocacy because of the legal defect on farmer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rural land, and inherent land right ambiguity of collective land ownership. And there is a longlasting vertical control failure because of the multiobjective issue which give more weight to economic growth, th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limit local land conversion by use regulations and planning measures. Additionally, in view of contemporary political framework and administrative system, local governments could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use without horizontal counterweights because there is no democratic mechanism to check the land conversion and Land acquisition is in the public interest,and the courts have not intervened the compensation and enforcement process effectively eith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aper is that “three failures”, including weak selfadvocacy of farmers, hesitant vertical control and powerless horizontal check, have resulted in serious soft institutional restraint to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omina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which leads to excessive conversion of rural land, inefficient use of land resources and outofbalance of land value increment during use change. On the basis of above analysis, three recommendations are proposed at the end of the paper: 1) Improving the farmers capability of maintain their own benefits, which requiring to construct a clear rural land property system, especially empowering farmers with the right to convert their rural land independently, and introducing market mechanism; 2) strengthen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dominance to land conversion at local levels, conforming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erspective, improving and enforcing main part functional district planning, implementing differential political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ystem, the last but not the least, equalizing of land development rights nationally; 3) enhancing balance and check of legislature and judiciary to administration.
Key words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rural land institutions; soft constraints; land acqui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