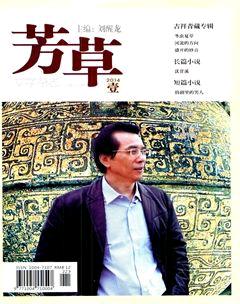无仪式的葬礼(短篇小说)
觉乃·云才让
地里的庄稼已经收割了,按理说,道杰扎西村长可以好好歇息一阵子,但是他失眠了。连续几天过去,还没有恢复的迹象。于是他称病,把村庄里那些可有可无的事情,托付给协助村务的额啦,自己在家里养病。
其实失眠的原因是:他已故几年的老阿爸,总是出现在梦中,老阿爸没有责备他,也没有向他索要什么,只是生动而清晰地出现在眼前。如果,换一个人,他可能立刻感动得泣不成声,但是对于老阿爸,村长实在没有什么可难受的感觉。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老阿爸在世的时候,父子俩之间发生了矛盾,用村长的话说,当时轻轻地“碰了”一下,不料老阿爸栽倒在了地上。然而,无论轻重,有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就是从此以后,老阿爸的左腿瘸了,他也背上了打阿爸的骂名。直到现在,说本村村长,不一定认识,一提村里打阿爸的人,那肯定十有八九的人都知道说的是谁。
他晚上失眠,白天像个死人一样,躺在炕上萎靡不振,偶尔长吁短叹,村长爱人看着日渐憔悴的丈夫说:“外面都在说……”
“胡说八道,不要给我提这件事。”
“那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懂什么,给我滚得远远的。”
偶尔有人来探病,村长一概不见。但是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于是某天晚上,村长像个自首的小偷一样,穿过窄窄的小巷,来到村东老藏医家。老藏医是个还俗的喇嘛,虽然有家室,但是仍然如同出家人那样保持清欲寡欢、深居简出的生活习惯。他看见村长的模样,笑说:“哈哈哈,平日里身体像拴狗的木桩一样结实的村长,怎么变成一头受凉的黄牛了呀?”
“这些天……我……”平日腰杆直直的村长,像换了一个人,蹑手蹑脚地坐在炕沿上,道来这些天他所遭受的折磨。但是他在描述的过程当中,有关阿爸的那段,有意地省略,或者淡化了。这就像给出一个小麦的种子,然后索要青稞一样,非常不得要领。蒙在鼓里的老藏医皱眉,把了很长时间的脉,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说:“脉象很乱,看来情况比你说的要糟糕一些,我先给你开几天的药吧!”
“寺院里的喇嘛,都到你这儿来取经,可见你的医术很高啊!”村长先奉承了几句,然后,若有所思地说:“小时候,我阿爸经常派我到你这里抓药,他老人家总说你没有治不好的病, 这次我这点小病不会难倒你的。”
“你的阿爸……”老藏医准备说什么,突然话锋一转说:“哎,我老了,俗话说得好啊,办事的手虽长,但是跟随的袖子太短了。”
炎炎烈日下,村庄都快要烧焦了,一片寂静中弥漫着焦躁不安的空气,村长躺在堂屋的炕上,汗臭味和浓浓的药味,溢满了整个屋子。正在窗外的院子里晒青稞穗子的村长爱人闻到刺鼻的臭气忙说:“吃了几天的药,仍然不见好转,照这样下去,没有治好你之前,准会把我们先熏死。”
村长什么都没有说,突然猛地关上开了一半的窗户,发出重重的“砰——”的一声,以示抗议和不耐烦。村长爱人似乎习惯了丈夫的脾气,喃喃地说:“你还是到阿拉仓(活佛)面前去打个卦吧,总该有个说法!”
突然几只蜂子不知从哪儿窜出来,嘤嘤嗡嗡地飞到村长爱人的头上,她时不时地用空手驱赶它们。不久,静悄悄的堂屋里传来了微微的声音,但那显然不是蜂子的鸣叫,而是村长的祈祷声。
第二天,村长早早起来,在佛龛前点了一盏酥油灯,然后磕了三个响头。从里屋走出来,家里被他砍伤的花母猪正好横在眼前,伤口虽然有些愈合了,但是腐烂之处已经生虫,看起来恶心。
村长懊恼地说:“这个该死的畜生,怎么还没有死啊!”说完,准备绕着走。花母猪好像要跟村长过不去,村长绕到哪儿,它就爬到哪儿挡路,村长狠狠踢它一脚,一阵刺耳的猪叫声,搅乱了早晨的宁静。街上的行人纷纷停下来,朝他们家院子里张望。
村长爱人看见了骂说:“你踢什么踢,这还不是你自己干的好事,你知道这个花母猪给我们家下了多少猪仔吗?”
村长气愤地说:“你自己没有看好母猪,让它糟踏庄稼地,现在后悔有什么用?”
村长拖着疲软的身子,已经消失在门口了,村长爱人还在嘀咕说:“只有没有用的人,才这样对待畜生,反正庄稼地里有的是牲口,你干吗没有去砍一个别人家的,让老娘也解解气呀!”
今天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是阿拉仓寝宫门前,前来朝拜的人排成一队。村长在队伍里晃晃悠悠地站了一会儿,正好一个小喇嘛看见他,热情地跟他打了招呼,笑言:“村长,你怎么不直接进去?”村长嬉皮笑脸地回说:“今天是辦私事来了,所以不好意思闯进去!”小喇嘛说:“村长大人哪能有什么私事,走,跟我一块儿进去!”村长看了看前后排队的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还是等一会儿吧,不着急!”小喇嘛说:“没有关系,跟我进来吧!”村长也只好跟着小喇嘛进去了。
阿拉仓坐在长廊里的椅子上,一对年过七旬的老人,跪在地上接受阿拉仓的摩顶,泣不成声的老奶奶怎么也爬不起来,恼羞成怒的老大爷搀扶无果,用拳脚伺候,惹得阿拉仓像个大男孩咯咯笑个不停。
小喇嘛和村长出现在眼前,阿拉仓这才恢复一本正经的样子,说:“村长,近来安然无恙?”这让村长感到非常惊讶,他想莫非阿拉仓知道了我此来的目的,于是跪在阿拉仓面前,不敢吱声。阿拉仓倒是谈起另外一桩事情。
阿拉仓说:“俗话说,不要杀生是阿拉仓说的,要吃肉也是阿拉仓说的,但是重修大经堂迫在眉睫,免不了增加你们的负担呀!”
“啦索(是)!”村长跪拜在阿拉仓面前,心脏如同小绵羊一样跳个不停。
阿拉仓说:“你们村的森林最茂密,希望大经堂所用的木材都由你们村来捐献,至于县农林局那边我来沟通,你觉得如何?”
“啦索!”村长的额头上流下浑浊的汗水,从脸颊上直抵下巴,滴在石板上。
谈完正事后,阿拉仓兴致勃勃地跟村长拉起家常,说:“不要总说啦索,谈谈最近村里有什么新鲜事儿。”小喇嘛提醒阿拉仓,说外面还有信徒在等待,阿拉仓这才说:“那算了,你先下去吧!”
“阿拉仓,我有个事……”如同接受某种惩罚,村长把额头几乎贴在地板上,把自己的遭遇全部禀告阿拉仓。阿拉仓虽然是今生的依靠、来世的救主,但是这样的问题头一次遇到,先愣了一阵,然后手指掐算了一会儿,脸上露出某种神秘的表情。
站在一边的小喇嘛,似乎明白了什么,避开了,但那只是象征性的,并没有走远。阿拉仓伸过脖子在村长的耳畔嘀咕了几句,说不清是惊讶还是恐惧,村长脸色大变,嘴里喊出一声“啊”。
阿拉仓马上说:“没有关系,只要善于积功德,罪果可变善因!”
村长忙说:“啦索!”然后连磕三个头后,从阿拉仓面前退下。
傍晚,村长回来的时候,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暗黑中,家家户户门窗上亮着零星的灯光,一片寂静中,偶尔传来犬叫声,可那声音断断续续,极其微弱。倒是村庄上面的丘陵,为了已故的人立起的一排排经幡哗啦啦地响起来,似乎向人们提醒不要忘记那些逝去的人。
村长心事重重地往家里赶,经过位于村中央的篮球场的时候,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乐此不疲地耍手机,他们是暑假归来的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平日里,村长会使点坏,比如突然从某个人的背后抱一下,或者喊一声“哇——”来吓唬他们。今天他没有这样的闲心,只是远远地朝他们看了看,然后急忙忙地赶回家去了。
里屋的灯光,透过玻璃窗口,照在大门外的马路上,村长进了大门后,哐当一声,随手关上了门。出来迎接的爱人一见丈夫,抱怨说:“你怎么回事,打电话也不接,我都担心死了!”说完,怀里取出一个破旧的三星牌手机,似乎要证明给他看。村长说:“我能有什么事,干吗要浪费那几毛钱的话费?”
他边说边走过院子的石板路向里屋去。一脚踏进门槛的时候,回头问爱人:“花母猪呢?”爱人忙回说:“它除了猪圈,还能在哪儿!”
村长和爱人前后进入内屋,内屋里的灯光很惹眼,本地有个习惯,面粉和装酥油的皮袋,高高叠放在大堂上,以显示家里的殷实。但村长家内屋里除了一台老式的电视机,和几袋喂猪的饲料,没有那么多摆设。
大堂中央的墙壁上,装了雕刻精美、富丽堂皇的佛龛,佛龛右侧的木板上,贴了两张乡人民政府颁发的荣誉证,荣誉证上的汉字虽东倒西歪,村长的名字却特别显眼。佛龛前面的地板上有一道痕迹,显然是磕长头留下的手印。佛龛左侧的木柱上,架着一个破旧的转经筒,据说这是村長家老阿爸去拉萨朝圣的时候,一路上背回来的。
村长的老阿妈双眼紧闭,坐在炕上,口中念念有词,手拉转经筒的绳索。不知道是过于专注了还是眼力不好,村长回来许久,一直蹲在火塘边,但是她老人家不吱一声。转经筒微弱的吱吱声和火塘里噼噼啪啪的火声,交织在一起形成某种独特的旋律,给这个家里增添了不少的温馨。
过了一会儿,一次蓄谋已久的咳嗽把老阿妈的身体都咳趴下了,如同经历了一场恶战,好不容易才呼吸平缓。老阿妈六十多岁,老伴的去世对她的打击很大,好端端的五官都不听她的使唤而扭曲了。
老阿妈眯缝的眼睛看见火塘里的光照在儿子的脸上,儿子的脸虽然依旧那么憔悴,但是变得红彤彤的,她老人家心里略微好受一点。老人家苍老的脸上露出一丝渴望,从炕上伸出脖子问:“道杰扎西,见到阿拉仓了吗?”
村长说:“见到了!”
老阿妈没有听见,问:“你说什么?”
正在一旁给碗里斟茶的村长爱人,把嘴贴近婆婆耳边说:“说见到了!”
老阿妈激动地说:“阿拉仓说什么呢?”
村长说:“阿拉仓说,没有大碍!”
老阿妈担忧地说:“阿拉仓说有大碍,那怎么办呀?”村长有点不耐烦,回到堂屋,把门哐一声关上了。
夜里,夫妻俩睡在炕上,各怀心事。不过,凌晨的时候,村长入眠了,嘴里喃喃地响起久违的呼噜声,曾经备受折磨的讨厌的噪音,今晚在村长爱人的耳畔变成悠扬的妙曲,然而这妙曲并没有成为把她带入梦乡的安眠曲,各种往事和悲喜交加的思绪荡漾在她的脑海中……
第二天,中午时分,村长如同一个贪睡的动物,在被窝里抬头的时候,听见隐约的霍霍磨刀声,但是他还没有完全睡醒,把头钻到被窝里,继续眯了一会儿。突然一阵刺耳的猪叫声,把他彻底叫醒了,于是他穿着便装,匆匆跑出来一看,院子里熊熊燃烧的柴火堆上,架着一个大铁锅,弥漫的烟雾中,匕首、麻绳和大小盆子胡乱摆放在一边,几个牦牛一样强壮的年轻人,正在摩拳擦掌,追捕花母猪。
花母猪虽然拖着残疾的下身,但为了活着,它使出了浑身的劲,在院子里爬来爬去。此时,圈在猪圈里的一群小猪,从门缝里窜出来,悲悲戚戚围在花母猪边上,似乎在保护它。
村长看见此情景,发了疯似的,冲到几个年轻人面前展开手臂,加以阻止,弄得几个年轻人不知所措。村长爱人忙解围说:“你不是说把它给宰了吗,现在不宰,再过几天恐怕就死了!”村长站在原地,没有说什么,但他那长长的马脸比三月的天气还阴沉。
村长爱人对丈夫的这一反常行为有些不满,但她忙跑回内屋,拿来几包上等的烟,塞到几个年轻人的手里,把他们打发走了。
翌日,女人们头上戴着五颜六色的围巾,三三两两,站在自家屋顶或者院落里打青稞和麦子,整个村庄沉醉在一片忙碌的秋后的收获中。每个女人脸上绽放着笑容,随着手中连枷的起降,那些爱说笑的少女舞动的身姿更加妖娆了。
而村庄下面,通向乡政府的马路上,村长推着一辆架子车晃晃悠悠地行走,劣质的白色衬衣,两边的袖子挽到胳臂上,露出坚硬的膀子。偶尔一辆疾驰而过的摩托车或者汽车从他身边滑过,风掀起他的衣襟,别在腰带上的黑色手机套,暴露在外。
村长推着架子车,大约走了一个小时,到了乡兽医站门口,可是兽医站的铁门关得死死的,他敲了半天,没有任何动静。连续三天遭到闭门羹,再次徒劳回去不是个办法,无奈的他把架子车推到旁边的乡人民医院门口。
乡人民医院是个四面围墙的建筑,院子里格外安静,他探头探脑看了半天没有看见人影,于是喊道:“阿古曼巴!阿古曼巴!”喊了十几声后,突然“咯吱”一声,某个房门打开了,但并没有人出来。
他轻手轻脚地到门口,往里面一探,有个卷发医生气冲冲地说:“有什么事?”
“看病!”村长说。
“病人呢?”医生漫不经心地问。
“就是这个……”村长把医生带到门口,打开架子车上盖的塑料袋子,手指里面的花母猪。
“我们是给人看病,不是为畜生看病,你这不是挑衅我吗?”医生气得发抖。
“不好意思,我是推来让兽医看的,但是他们不在,反正来了,想问一下,有没有办法治疗?”村长诚恳地说。
“头一次遇见给畜生看病,实在有些荒唐!”医生的话里带有些许讽刺。
“那也跟我们普通人差不多,看一下,总比我空手而归好些!”村长忙解释说。
“没有希望,还是早点宰了,不然在这个季节里死了,容易发生瘟疫!”医生很嫌弃地看了看花母猪的伤口,然后,如同一只猫一样,不知钻进了哪个房间里。
村长很少抽烟,但是办事的时候,给对方递一支烟,有时比寒暄一百句还顶用,所以他随身带着一包烟。今天有些悲伤和无奈的他,坐在架子车的手把上,抽起了烟。烟影如同他的内心一样,胡乱地飘散在他的眼前。村长连续抽了几支烟后,推着架子车,返回乡上唯一的一条街道。
焦躁不安的花母猪,按捺不住村长的折腾叫唤起来,村长从路边的小卖部买了一些零食,喂给花母猪吃,果然有效果,花母猪乖得像个小老头。
几天以后,村长推着他的架子车又出发了,但是此次他的目的地不是医院,而是寺院的转经路。本地寺院紧挨在乡政府一侧,寺院的转经路相比起来虽然并不宽敞,两个不同的世界,划分得恰到好处。转经路上,村长推着架子车缓缓转经的时候,有些转经的人从他身边匆匆而过,似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有些人好奇地频频回首,驻足观望。
有个戴鸭舌帽的老大爷问:“你这架子车里乘的是什么?怎么看上去,有点……”
村长脸上露出某种神秘的表情。
有个大妈,伸出脖子一听,里面的叫声有一点不对,问:“这是?”
村长一言不发继续上路。
有个穿马夹的中年人说:“难道是个行动不便的老人?”
村长背后跟着一堆七嘴八舌的围观人,但是村长并没有回应,他一心只是上路。突然一阵风刮来,掀开塑料袋子,里面装的是一头花母猪,顿时转经的人都吓了一跳,有的叫喊着逃走了。
“第一次看见带畜生转经的!”
“这是一条幸运的母猪。”
“臭死了,转经路上怎么可以带母猪!”
“又不是你老阿爸,怎么带一条母猪来转经呢!”
后来村长经常拉着花母猪到寺院的转经路上转经,身后总是有人交头接耳地议论。余日不多的花母猪,似乎不担心自己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它那炯炯的眼神、美美的睡姿和贪婪的吃相,引起转经人的好感,有人把自己带来的干粮喂给它吃。从而,在转经路上,村长和它家花母猪的境遇,变得“风调雨顺”了……
几个月过去了,某天晚上,突然刮起妖风,天降暴雨,位于村中央的经堂屋顶掀开了。对于这个不太吉利的天气,村人都避而不谈,生怕预言般的不幸发生在自己身上。正好,第二天,村长家院子里散发出某種不安的气氛。
村人们感觉到村长家摊上了什么事情。为此,他们有种渴望,但又觉得不能幸灾乐祸,处在一种不可名状的矛盾心态中。然而,村长家并没有摊上太坏的事,只是他们家花母猪死了。花母猪死后,村长把花母猪的死尸裹在白布里,“供奉”在佛龛前,他的爱人看不下去了,说:“你这是怎么了?花母猪有恩于我们家,但也不至于如此吧!”
“不要瞎说,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知道什么!”
“你把它带到寺院里转经,都成了笑话了,你还不消停呀!”
“我自有考虑……”
“老阿妈到小姑子家去几天了,还没有回来,你这样折腾下去,恐怕她再也不回来了!”
“哎……她这是何苦呢!”
花母猪的死,当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情,毕竟那也是一条性命,老阿妈看见儿子的反常行为后,不由想起从前老伴去世时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事。
当时,老伴刚刚去世,尸骨未寒,儿子不满她阿爸把家里仅有的家传送给女儿,也就是村长的妹妹,于是赌气,不来料理丧葬。如果说儿子打了阿爸还可以原谅的话,儿子不来参加阿爸的丧葬,那是黑头藏人视为最大逆不道的行为。
老阿妈在女儿家里闭门不出,爬满皱纹的脸一天比一天衰老,女儿心有不忍,愤慨地说:“阿妈,你知道外面都传什么吗?都说在我哥眼里阿爸连一条母猪都不如呢!”
“你再不要去乱嚼舌头,人家说的都能信吗?都是你惹的祸,当时你阿爸临终的时候,要不是你死活要那个家传的话,也不至于你哥闹到如此的田地!”
“阿妈,你怎么抱怨我,打阿爸的又不是我呀!”
“打阿爸?这个是你该说的话吗?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哥呀!”
“那好,我哥是自己离家搬出去讨的媳妇,我的丈夫,可是上门女婿呀,在这个家里我是名正言顺的继承者,给谁还不就是明摆着的事吗?”
“你怎么能这样说呀,你哥小时候不懂事,惹了不少事,但他现在已是一村之长,你应该为他高兴才对呀?”
“阿妈,你放心吧,我哥现在当了村长,风光得很!”
“你说你哥容易吗?表面上风光,但是都四十几岁的小老头了,膝下无子女,他的内心能愉快吗!”
……
自从遭到暴雨的袭击之后,村人们都忙于修缮经堂,没有人关心村长家花母猪的后事,然而死猪供奉在佛龛的消息,不胫而走传开,村人难以理解,议论纷纷。
村长不但没有反省,他下了一个更加匪夷所思的决定,准备“厚葬”花母猪,把花母猪的死尸送到天葬场,像人一样天葬。这好比火上浇油,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于是有人提出罢免村长,有人主张阻拦……
村里几个老年人为了制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自发来到村长家里,一个满脸白胡须的老人说:“村长啊,我们虽不是百岁老人,但耳闻过千年老话,俗话说,有枝干的树易攀爬,有智慧的人好沟通,听说你要天葬花母猪,确有其事?”
村长说:“是的,希望你们理解我!”
白须老人说:“前任几个村长的遭遇,你又不是不知道,如今若你真的执意行事的话……”
村长说:“我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不怕!”
白须老人说:“村长,你仙去的阿爸我们虽不是故交,但是同一代人,所以我有责任和义务再次警告你,天葬场里可不是什么都能天葬的,不要说猪等畜生,连福分不好的人都不行!”
村长说:“不管遭到什么天谴,我将承担后果。”
白须老人说:“俗话说,蚂蚁走过头,则粘在松脂里,青蛙跳过头,则撞在石头上,你可要慎重啊,这不是儿戏,即使你要天葬,那也有一系列的仪式,你这样匆匆地送葬,会亵渎神灵的。”
村长说:“仪式是给活着的人看的,没有也罢。”
几个老人劝说无果,灰溜溜地散去了。村长在几个老人面前嘴硬,但是临近送葬的那天,他私下请了寺院里的喇嘛和几个亲朋好友,为的是象征性地念点经和搞点仪式什么的。但“出殡”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通向天葬场的小路,如同坎坷的人生,弯弯曲曲,被各种横七竖八的植物包围了,村长孤零零地背着花母猪的尸体上了天葬场。当村长把花母猪的尸体放在天葬场中央捣尸台的一刹那,不知是在欢迎,还是在谢绝,一阵呼啸而来的狂风中,凋零的树枝狂舞起来,满地的枯叶在飞扬……
天葬场离村庄不远,平时天葬的时候,村人们都屏住呼吸,遥望着天葬场的上空,看着从天而降的秃鹫,不管认不认识死者,总为人生的无常感叹,也为亡者念颂几道六字真言。今天,没有人相信村长的一意孤行能招来神圣的秃鹫,即使偶尔有人遥望天葬场的上空,那纯粹是耻笑他的闹剧。
然而,不到半个时辰,奇迹出现了,天葬场的上空,出现了第一只秃鹫,然后第二,第三……最后黑压压一群秃鹫落到了天葬场。不久,村庄上面一排五颜六色的经幡堆里,一顶崭新的经幡高高飘扬,非常瞩目。
村里有了新的传说,说花母猪是村长阿爸的转世……
(责任编辑:张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