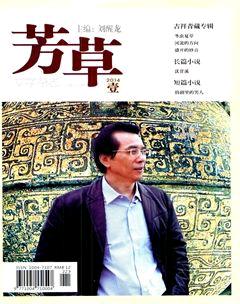欲(短篇小说)
班丹
山头和草滩被云雾涂抹得灰蒙蒙,轻风夹着雨滴自由飘荡的黄昏时分,玉措一瘸一拐、神情沮丧地赶着羊群回到家里。
一进家门,她就将母亲康珍拉到帐篷外面的羊圈里,抱住她,带着哭腔说:“阿热欺负我了。”
“怎么欺负的?”康珍关切地问。
“他把我摁倒在地上,亲我,还用手摸我。”玉措学了一下摁倒人的动作。
“那他动过你的身子?”康珍紧张得脸色一变,声音也有些走样了。
“没有。可是……吓死我了。”玉措把眼睛瞪得像泉眼似的看着母亲,抽抽搭搭地哭了又哭。
康珍不希望玉措像自己当年被孩子们的父亲别若(别若:阿里雄巴语,老酒鬼之意。其实他并不是见酒迈不开步子的酒鬼,只是他一旦喝起来,没有个一两瓶,是打不住的)拉松野蛮占有那样,不明不白地失身,“真的没有发生别的事情?”
玉措做个深呼吸,“真的没有,我向神发誓。”
康珍提到嗓子眼儿的心,这才回到原来的位置。
玉措的父亲别若拉松得知这件事儿,心头一乐,拍掌说要告发阿热。
康珍往炉膛里添着羊粪蛋,嗔怒道:“你告发人家小孩干什么?玉措都跟我说了,那事没成。”
“没成也不行。不教训一下那小子,他还会打玉措的主意。”他嘴上是这么说,可心里在打着什么算盘,康珍多少能猜得到。她心想,别人我不敢说什么,可是自己男人的那点心思我还是心知肚明的。拉松最大的毛病就是喜欢占别人便宜,讹人的事情他以前干过不少。
“当年你打狗(意即找女人得先制伏看家狗)打到牧场,把我弄到手,谁跟你计较了?”康珍的语气变得有些尖酸刻薄。
别若拉松把脑袋侧向一边,点燃一根烟,快速吸着,由片刻的沉吟变成无奈的语塞。
“哼,这个糟老头,哪像个草原汉子。” 康珍提起铁桶,倒炉灰去了。
那天,别若拉松喝过半斤白干,背着妻子,向洛德村长告发女儿玉措被阿热欺负的事儿。可是这话从别若拉松嘴里说出来就变味儿了,成了被人视作可耻可恶可怕的“强奸”。洛德听了,像是一小块骨头卡在喉头,感觉很不舒服。他没法接受这个词。他虽然知道什么叫做强奸,但打记事起,生养他的那片草原上还没有出现过这类事儿。因此,他一再向别若拉松确认这件事情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强奸罪。
别若拉松忙发誓,他所说的句句是实话。
于是,洛德很快把一个副乡长、综治干部、村官和一个副村长、两个不同作业组的组长请到他家里,叫上玉措和她父亲别若拉松、阿热和他父亲布果,像法官开庭审案似的拉开了调解的序幕。
洛德看着玉措,“你先讲讲被阿热欺负的过程。”
“不是欺负,是强奸。”别若拉松挥挥手,大声纠正。
“你先不要激动。”洛德冷静地看着别若拉松。
玉措用头巾把脸重新捂好,埋下了头。
一天中午,阿热沿着牲畜踩出的小路,循着羊们发出的咩咩声,到山上找寻早已扫入眼中的玉措。没多大工夫,他便爬到了山头那块盆状草地。
阿热的突然出现,弄得玉措一下子傻眼了。她本能地站起来,瞪大一双黑亮如宝石的眼睛,盯起眼前大汗淋淋的阿热。那样子活像一只受惊的兔子。
阿热将两只手放在大腿上,弯腰屈膝,吃力地仰起头,呼哧呼哧地大口喘气。等到稍稍缓过气来,就快步逼向玉措。
玉措头一回见有人像饥饿的狼扑向羊群一般闯入她的领地,便毫不迟疑地从腰带上解下抛石绳,挥动着,迈起牧羊女特有的幅度很大的步子,走到一面斜坡上。
哒,哒,哒。玉措的抛石绳把阿热请下了山。
一阵嗷嗷呃呃的哀叫声告诉玉措这是她第一次被人骚扰。可她陶醉于自己的“胜利”,并没有把这事当一回事告诉自己的家人或旁的什么人。
玉措停顿下来,“不讲了。没意思。”
“没意思?你得讲清楚呀!”
玉措抬眼看一下在场的人,然后把头埋得更低,用发颤的声音说:“过了十来天,阿热又像鬼影似的出现在我面前。”
沉默。玉措不再往下讲了。
大大小小的官员和双方当事人亲属个个都焦急地等待她把事情讲完。
这次阿热悄悄向伴着轻风吟唱着牧歌,在离羊群不远处溪流边走动的玉措摸了过来。一靠近她,就像一只雪豹将身子往前一蹿,不等人家反应过来,用抛石绳反击,就把她摁倒在地,身子稳稳地压了上去。等到他把嘴唇向她贴过去,手像一只虫子在她身上蠕动、摩挲。她猛然推开他,连着打几个滚儿,站起身,用颤抖的声音哭叫着,迅捷逃过了他并不友好的亲近。
玉措把头埋进了两腿间。她父亲别若拉松觉得很不好意思,便佯装去解手,小声给洛德村长打了个招呼,离开了帐篷。
洛德瞅瞅在場的人,问玉措:“你跑掉了啊?”
玉措摸摸腿,“可我一着急,重重地跌了一跤,腿撞惨了,肿块到现在都还没有消。”
与第一次受到不太友好的骚扰不同,这第二次使得玉措既感到害怕、羞赧,又觉得好笑,她心头一热一凉,眼里涌满了泪水样的液体。她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这液体里到底害羞、害怕的成分多一些呢,还是伤心、恼怒的成分多一些。
这个比阿热小一岁的玉措,一直低埋着头,手指头在地上擦来擦去。看那情形,好像是她骚扰了阿热,而不是阿热骚扰了她。
综治干部的眼睛变形了、发绿了。他的目光犹似多情的子弹,从副乡长和洛德村长之间的夹缝里准确地射向玉措,希望她抬起头,把蒙头盖脸的头巾揭开,让自己美美地欣赏她白里透红的脸蛋和勾人魂魄的眼睛。
接下来,阿热交代欺负玉措的过程。
阿热看看在场的人,“啊,事情就像玉措讲的那样,就那么发生了。”他顿了顿,“没错,我很早就看上了玉措。还经常梦见她。” 他微闭双眼,死盯着玉措,“你可能没有感觉到。”
玉措抬眼的瞬间,双眸与他相擦。她意识到自己的失态,立马把头埋了下来。
“其实你们也都渴望着得到玉措。谁要是能得到她,就是被枪毙九十九次也值。是吧?”
“不要脸的。说什么呢?”洛德骂了一声阿热。
“你们说句实话。见了玉措,这天底下的所有女人是不是都变得和老母狗没什么两样?”
在座的除那位综治干部外,都哧哧地笑起来。洛德笑着笑着,忽然意识到处理这么严肃的事情,不应该这么随随便便,就赶忙收住笑,“你还这么小,怎么很早就看上她了呢?”
阿热盯着帐篷的天窗,大声地说:“我阿爸说了,男儿要在年轻时闯荡世界,鸟儿要在幼小时翱翔天空。我趁年轻时找漂亮女孩总没错吧?”
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俊不禁,又一次噗噗嗤嗤地笑出了声。
阿热的父亲布果瞪了他一眼。
“玉措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姑娘。所以我就找她了。”阿热笑微微地瞥了玉措一眼,还随口唱了起来:
在那翠绿的草原上,盛开着娇艳的邦锦花。
我心中的玉措姑娘,比那邦锦花还娇艳。
在那高高的雪山上,盛开着吉祥的雪莲花,
我可爱的玉措姑娘,比那雪莲花还要吉祥。
大伙的目光犹如同时射出的箭镞,一下子聚集到阿热身上。
村长洛德严厉地问:“看上一个女孩,就要像畜生一样对待人家吗?”
阿热摇头辩解:“我是真心在向玉措求爱。我爸说了,他睡过一百多个女人,扔掉了一条“百裤”(旧俗。男人睡满一百个女人,就扔掉一条裤子,以示其能力),也没有一个人说他这是欺负女人。”
“你胡说什么呀!”阿热的父亲布果听不下去了。
阿热像个喝醉酒的人,对着父亲说:“呀,阿爸你说句实话,你没有教过我怎么搞女人?你还给我讲过很多你找女人的故事吧?”
“你,你,你,你这个狗崽子胡说什么呀?” 他在扬起手的同时抬起屁股,准备给阿热一拳,却被副乡长挡开了。接着他把目光移向村长洛德,“呵呵,不管怎么说,能搞女人,是真正的男子汉。是吧,洛德?”
“胡说!”洛德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情。
阿热扫一眼玉措,“阿爸经常跟我们年轻人说,世上没有比搞上处女更美妙的事情。”
布果感到无地自容,便噌地从地上爬起身,朝阿热大腿狠狠踹了一脚,溜出了帐篷。
布果一到外面,就跟别若拉松争吵了起来。
“别若拉松,你这个人脸皮怎么比野牦牛皮还厚?”布果指着别若拉松的鼻子问,“当年你是怎么把康珍搞到手的?还不是强行睡成的。你还有脸告我儿子欺负你女儿。”
别若拉松也把右手食指指向布果的鼻子,“欺负?哼,是强奸。”
“不要說得那么难听好吗?”
“嫌难听,就应该好好管住你那个狗崽子。”
他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争得面红耳赤,都快要拳脚相加、短兵相接了。他们的吵闹声不时传到帐篷里。而此时帐篷里正进行着热闹而又有些滑稽的对话。
村长洛德像是要唱歌似的清清嗓子,“阿热,你说实话,你看上玉措什么了?”
阿热眯缝着眼,不住地在帐篷内扫来扫去,“眼睛、鼻子、耳朵、嘴巴、腰、腿、头发,还有……”他看看玉措,“我长这么大了,还没有见过比她漂亮的姑娘。最重要的是她走路的样子太好看了。”说着说着,他站起身,在帐篷里走个来回,学了学玉措的步态。
玉措随手从炉边拣起一块干牛粪掷了过去,正好打在阿热的嘴上。
阿热抹了一下嘴角,郑重地补充道:“还有,她笑起来像一朵花。”
村长洛德板起面孔,死死盯着阿热,“严肃点。”转而问大伙,“他像个欺负人的吗?”
大伙不解,木然地看着洛德。这反倒弄得洛德一头雾水。
阿热捋了捋乱蓬蓬的头发,“玉措那种走路姿势呀,我在县城也没有看到过。啧啧,实在是太美了。”
玉措低着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其他人都面面相觑,低声发笑。
阿热却不以为然,“笑什么?我说的都是实话。”
“正经点。你到底欺负她没有?”村长洛德朝玉措努努嘴。
“我已经说过一百遍了,这不叫欺负。我倒要问问你们是怎么把女人弄到手的?”阿热一副很不耐烦的样子。
副乡长补充一句,“你已年满十八周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一旦强奸罪成立,就要判刑。看你还有心思开玩笑。”
阿热不买副乡长的账,“强奸?哼,笑话。”
村长洛德恨不得扇他一记耳光,“不许狡辩,坦白交代。”
阿热不无遗憾地说:“太可惜啰,没有成功。不然我会把她带回家,做我的媳妇,让天下所有男人妒忌死。”
村长跟阿热一问一答式的对话在帐篷里摇荡,俨然两个贫嘴的人在磨嘴皮子。
阿热像讲故事一般在向大家描述他父亲的风流韵事,辅之以各种夸张、露骨、肉麻的动作,弄得大家哄然大笑。一阵阵脆亮的笑声从帐篷里传到吵得正起劲的布果和别若拉松的耳朵里,使他俩的吵闹受到严重干扰。
玉措感觉脸烧得滚烫滚烫的,仿佛立马要着火,便把头埋了下来。
年轻的综治干部时不时地望一眼玉措,暗忖,谁见了像玉措这样长得楚楚动人,性情又温和、腼腆,却又不乏刚毅之气的姑娘不动心,谁的脑子就进水了。别说是阿热,换了我,也会千方百计把她弄到手。
帐篷内的大小行政长官仍在审理案子。而帐篷外面的别若拉松和布果这时还在进行着激烈的舌战。
副乡长终于说话了,“玉措,你可以出去休息一会儿。”
玉措一离开,阿热把嘴一闭,什么话也不说了。他把要说的话一一写入了大脑。
阿热回想起第一次到县城的情景。
一天晚上,那个打小跟他一块长大、大学毕业后分到县城工作的朋友,把他带到自己的宿舍,给他端来酥油茶、煮羊肉和啤酒。他很不客气地吃肉喝茶,但死硬不喝酒。他说:“我一个牧民的孩子,哪有喝酒的闲钱?这个我不学。”他那个朋友笑呵呵地点点头,说:“那我给你放个影碟,你自己看吧,我出去一下,很快回来。”
《岗拉梅朵》。曾上到初一被迫辍学的阿热认得藏汉文片名。他把这部电影从头到尾看过一遍后,傻傻地盯着荧屏,回味剧情。他没太弄明白讲的是什么故事。倒是剧中人物,年轻时在拉萨开酒馆,因唱响了一首叫做《岗拉梅朵》的歌,而被人们称为岗拉梅朵的拉姆,把一个女孩塞进了他的脑子。从那一刻起,他苦思冥想,一直在意念中寻找那个女孩的影子。但怎么也没找着。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那个很像,而且在他的脑子里慢慢变得跟拉姆一模一样的女孩儿,多次跟影片里的拉姆一块出现在他的梦中。后来这两个女孩儿交叠成一个人,如同衣裳一般依附在他身上,萦绕在他的脑海,陪伴他从清晨走到夜晚,又从夜晚走到清晨。
那天,阿热到乡里买东西时,在商店门口与玉措邂逅。玉措莞尔一笑,算是跟他打了招呼。他也面带有些别扭的微笑,回敬了一下玉措。其实,在这之前阿热跟玉措并没有见过面。他们虽是一个行政村的,但两人的家离得很远,平时没有见面、接触、交往的机会。只是玉措这个孩子跟她母亲康珍一样很懂礼节,见谁都要以花朵般的微笑打个照面,哪怕路遇陌生人也如此。
岗拉梅朵!阿热突然记起电影里的岗拉梅朵,差点朝玉措喊岗拉梅朵。他为找到与电影和梦中的那个女孩相对应的玉措暗自庆幸。打那以后,玉措取代了电影中年轻时候的拉姆,进而在心头萌发了一种连他自己都感到惊讶的大胆想法,我要把她弄到手。
说来够有意思的,阿热看电影看走眼了。其实玉措比電影里的拉姆漂亮多了,就像美丽矫健的藏羚羊。
“说真的,不把她弄到手,我就不是男子汉。”阿热低声嘟哝着,要往外走。
副乡长喝住阿热,让他把布果和别若拉松叫进来。接着趁阿热出去的工夫,跟村长洛德耳语了几句。
阿热把布果和别若拉松叫进来以后,村长洛德习惯性地干咳两声,“大家说说,这起案子该怎么解决?”
阿热开口了,“这不是什么案子,而是一般的很正常的事情。”
布果和别若拉松你一言我一语地争辩着。别若拉松非要布果承认他儿子阿热强奸了自己的女儿玉措,而布果偏不承认。
“这既不叫强奸,也不叫欺负。” 阿热反驳道。
布果也争着说:“对。”
“那干嘛强行把我女儿摁倒在地,亲嘴,还把罪恶的爪子伸到袍子里面捣鼓?”别若拉松极力争辩。
“不要吵,你们一个一个说嘛。”副乡长发话了。
这下又没有人吭气,一时气氛变得十分沉闷。
副乡长觉得这么耗下去没意思透了,便说出了他对解决这件事情的意见。对此村长洛德表示同意。乡综治干部点了点头。布果和阿热也接受了。而别若拉松却死不同意副乡长的处理意见,非要布果给他拿出三万元赔偿金。
村长洛德气愤地指责别若拉松:“你的胃口也太大了,是想借机狠狠敲人家一笔吧?人家又没把你女儿怎么着,让布果家拿五百元给你,这已经是够给你面子的了。”
“诬告他人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哟!”副乡长看着别若拉松,“你女儿不是承认阿热没有欺负她吗?”然后副乡长又悄悄对综治干部说了句什么,综治干部马上拿出纸笔,密密匝匝写了两页,交给副乡长看。副乡长扫两眼,吩咐村长洛德把玉措叫进来。
玉措走进来,坐在村长旁边。
副乡长给综治干部递了个眼色,综治干部会意地点点头,宣读了裁决书。
毕了,副乡长和村长洛德分别对阿热进行了一番传统的说教。
次日,玉措的母亲康珍特地登门造访,向阿热父母谢罪,并把别若拉松带回家的五百元赔偿金如数还给了他们。她的理由是,她年轻时也和多数漂亮女孩一样,被很多男人搂抱、亲吻过,甚至袍子也被撩开过。这在牧区是很正常的,没有必要把事情做到不讲情面的份上。更何况阿热并没有伤害玉措,只不过跟有些前辈男人一样有点粗鲁。想想过去,谁还管这种事儿。这样子弄出来的孩子和成为夫妻的还少吗?
康珍被布果两口子的热情浸染,一坐就是大半天。
这时被妻子惹恼的别若拉松正在家里大口大口地往肚子里灌“沱牌”。
康珍和布果两口子说着说着,不经意间把话题转移到别的事情上了。
康珍跟主人在说笑声中喝掉了一壶酥油茶,气氛融洽得无以复加。
待康珍告辞时,阿热的母亲把那五百元钱塞回康珍手里,“这是乡领导和村干部作出的决定,我们得听他们的。再说,我这崽子也需要长长记性,不能让他跟他阿爸似的……”
布果瞪了妻子一眼。
康珍拒不接受,并说:“你们的家境虽然比我们好得多。可是我不能要这个昧心钱。”
这场官司在极少出现令人兴奋的新鲜事物的偏僻荒原产生了天翻地覆般的轰动效应——首先使玉措的知名度提高了几百倍,众多外村外乡的男人不辞辛劳、特地前去一睹玉措的姿颜。大饱眼福之余,为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增添了鲜有的乐趣。其二,人们记住了阿热这个小伙子,称赞他是个真正的草原汉子。其三,很多青春少年非常友好地充当起阿热的情敌,以各种方式努力接近玉措,让她骄傲自豪,让她烦恼懊丧。这也使得她的抛石绳变得更加忙碌、凶狠了。
约莫过了半个月,阿热又一次跟踪玉措到放牧的草滩。
这次他可不像前两次那样采取粗野的进攻手法,而是慢慢地靠近她,呆呆地坐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唱几首草原情歌和也不知是从哪儿学来的当代新情歌。接着三步一回头,离开玉措放牧的草滩,走了。
玉措目送着阿热,心里感到空落落的,像掏空了的牛皮袋,很不是个滋味。
打那以后,玉措天天希望阿热再来欺负她。可阿热偶尔出现在她眼前,也只是远远地望着她,哼两首情歌或者牧歌,一步一回头,慢悠悠地离去,却不敢靠近她。
过了一年,玉措嫁给了那位乡政府综治干部。而阿热剜去一只眼睛,离开家乡到岗仁波琪山脚下,从事起了替年迈体弱或其它条件不允许朝圣的信徒转山挣钱的行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