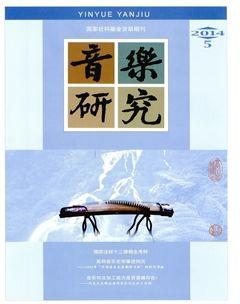朝气蓬勃的时代歌唱
蔡梦
中国近现代诸种文化艺术形态中,群众歌曲是流布最广、接受人群最多的体裁,某种意义上看又是对普通人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乃至整个社会精神结构影响最大的文化样式之一。
针对群众歌曲的阐释,在《音乐百科词典》中主要包括:(1)泛指由专业或业余作曲家针对现实社会生活创作的、适于群众演唱的歌曲。歌词浅显,曲调简单,音域不宽。常取分节歌曲形式,常用进行曲体裁,有齐唱、轮唱、合唱等。(2)群众歌曲一词由苏联音乐家于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其概念和特征在30年代确立,40年代以后受抒情歌曲的影响,风格趋于多样化。(3)中国的群众歌曲始于学堂乐歌,后迅速发展,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工农革命歌曲,三四十年代的“抗战”歌曲,共和国成立后《歌唱祖国》、《我们多么幸福》、《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文革”时期《北京颂歌》,粉碎“四人帮”后的《祝酒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等。由此可了解群众歌曲形态和风格的基本特点,同时,由于不同时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不同,群众歌曲从种类到风格都具有多样性。
历史、社会在发展,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形成一定的社会心理并对作曲家的审美心理、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产生影响,从而创作出居于主流风格的音乐作品,同时培育出特定时代听众的审美趣味。群众歌曲更是如此。某种意义上说,一定时代的群众歌曲是作曲家与听众审美心理和趣味的写照,由此折射出该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时代精神。
1949年共和国成立至“文革”前的17年,社会初定,当家做主的人民对未来充满希望,百废俱兴的各行各业焕发出勃勃生机,作曲家在新时代、新生活的激励下进发了创作热情,他们将丰富的思想和感情融会在艺术构思中,用作品表现意气风发的时代,一时呈现出“万方乐奏”和“遍地歌声”的繁荣局面。具体到群众歌曲,产生了大批气质豪迈的作品(如《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也有小部分在题材贴合时代主旋律的前提下,音乐上流露出更多抒情飘逸的特质(如《我们的田野》、《草原之夜》、《我爱这蓝色的海洋》),还有少数作品通过运用音乐对比的表现手段,展示出富于逻辑化的艺术构思(如《唱支山歌给党听》、《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此外,散发着浓郁艺术芬芳的大量儿童歌曲也自然地融人此期群众歌曲的百花园(如《快乐的节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新中国17年”的群众歌曲数量众多,本文仅从音乐审美视角,对其中八首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综合分析。
一、题材与风格
在社会文化背景和政治经济形态的统一作用下,“新中国17年”的群众歌曲就整体而言呈现出一些共性特征。
(一)“颂歌型”群众歌曲占有很大比重,其带有鲜明的政治功利目的和思想教化功能。写于1950年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劫夫词,劫夫、中艺曲),原是歌剧《星星之火》中的一首选曲。其剧情早已淡出人们的记忆,而这支歌曲却穿越时空隧道,如汩汩清泉流转在几代人的心间。歌词借挺拔的青松寓意为正义和民族解放而英勇无畏者的坚毅,他们的精神和信念如同屹立在高山之巅的松柏,无论现实环境如何严酷,始终以积极、乐观、昂首挺立的姿态展示大气磅礴的生命力,给人以向上的力量。
歌曲形式上的创意在于作曲家别出心裁地选用3/8拍这种带有个性化特点的律动来表现“英雄”的题材,用其摇曳的韵律来表现“革命”的抒情。此外,歌曲的调式与旋律融会了大调式与民族调式两类风格的音乐元素,具体表现为:(1)音高素材既可视为加变宫的六声音列,也可视为少下属音的大调音阶。(2)旋律线条多穿插分解和弦的三、四、五、六度音程语汇,间捕片段化级进音调。其中,五声化旋律中视为级进的小三度音程与和弦分解所获得的小三度音程,在歌曲的不同地方有巧妙、自然的融会。(3)乐句落音各不相同,包含了五声调式的五个正音级,构成的音程关系依次呈现为四(五)度一二度一(四)五度一三度,由此看出其与整体上的音乐陈述素材具有统一性。(4)歌曲最后作为收束的调式主音,同样带有宫调式与大调式的双重释义,这一点从其前一小节的旋律片段即可看出。一方面,其中蕴含了强拍终止四六进行至弱拍属和弦的和声内涵;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此处突出的是带有下方大二度助音的角音,之后再大三度进行到主音,这无疑又呈现出民族五声调式音乐的旋法特点。综合以上方面,这首歌曲的旋律既给人以清新、亲切的音响感受,又不失力量的蕴含和明朗乐观的阳刚气质,它如同共和国初期一个特定的历史符号,赋予那个时代以鲜明的审美特征。
(二)带有一定抒情意味的群众歌曲多以明快、昂扬的风格基调凸显特定时期的群体意识,但从中仍可感受到作曲家心迹的袒露,或对生命的体验及内心情感的抒发。写于1953年的歌曲《我们的田野》,是管桦作词、张文纲创作的儿童组歌《夏天旅行之歌》中的第三首。词作者用生花妙笔忘情地勾画着一个情景交融、天人合一的意境,以此表达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坚守不同岗位、为国家和平富强忘我工作的劳动者的由衷赞颂。
歌曲的音乐部分由三个派生发展关系的乐句组成,每句依歌词字数及内部的字词组合特征而长短不同。2/4拍框架中的节奏组合形态多为基本音型(一音一拍,八分均分单位拍,二分时值附点音型等),韵律鲜明、节奏规整,明晰、严整的乐句划分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来,其中的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每乐句可划分出两个具有关联语气的乐节,两乐节间的句法组织多为鱼咬尾结构,跨小节延长音多为句读划分的标志;乐句或乐节都以带强位八分休止的正拍或弱拍八分均分音型起音,与起伏有致的波浪式旋律相得益彰,使音响既有规整、规则的一面,又自然带出动感与飘逸;大调性五声宫调式的旋律与明朗清新的田野气息自然贴切,令歌曲的形式与内容统一为堪称完美的整体;这首精练的小歌用中等速度、宽广的气息演唱,犹如一袭被两岸垂柳依依包围的清水缓缓地优雅地流淌,称得上一篇清新飘逸的抒情颂歌。
写于1959年的歌曲《草原之夜》,原为电影纪录片《绿色的原野》中的一首插曲。词作者张加毅与曲作者田歌随纪录片摄制组深入新疆伊犁地区的一个军垦农场体验生活。一天傍晚,他们偶遇一群维吾尔族青年正围坐在一堆燃烧的篝火旁歌唱,动人的歌声伴着晚霞和炊烟,构成一幅如诗般温馨的画面。词曲作者深受感染,回到驻地,趁绕耳的余音还未散尽,心中的感动仍在发酵,便连续工作,完成一首新歌的创作。这首触景生情的歌曲,着力点在于通过一个轻吟小唱的剪影,塑造垦荒战士的形象:战士们身处远离家乡的边疆,心中难免产生孤寂的感受,但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却是火热的、浪漫的。白天投入农垦生活,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着一场场不见硝烟的“战斗”,而当夜幕降临,他们轻抚琴弦,和着草原的清风,伴着醉人的音乐,倾吐心中的理想和憧憬。他们的理想是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大草原的崭新气象,他们的憧憬是远方相爱的人快点来到这变了样的草原,与他们共建美好家园,共享美好生活。基于以上背景,歌曲以徐缓、委婉的旋律创造了一种宁静、悠远的意境;以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格,抒发垦荒战士对远方爱人的绵绵思念。这首作品有情有景,又有高远的立意和审美的音响感受,被冠以“中国式小夜曲”的美誉。
歌曲的音乐部分有两个乐段,材料为带再现的单二部曲式。第一部分(A段)四乐句,对应两段歌词,分节歌特点。每乐句多为六或七小节,根据歌曲开始主题的音调和节奏自由展衍,句尾多以长延音停留,在此背景上叠人语气统一的间奏音调。四乐句间显现出“平铺直叙”的音乐发展特征,其中前两句为音区提升八度的同头旋律,第三句变化节奏,延续发展,第四句回归歌曲开始的节奏形式,并以由低向高的正波型旋律与前三句的反波旋律形成起一承一合的音响统一体。几个乐句绵延着一致的调式风格,引申着深情、怀念的音乐情绪。作曲家在创作中糅人了维吾尔族音乐的表现特征,五声调式,民族风格鲜明,具有民谣体的抒情意味。第二部分(B段)通过插入衬词与重复歌词的方式成为第一部分的副歌,使原本一个乐段的歌词扩大为单二部规模。此部分两个乐句各6小节。第一句,通过“来”的衬词乐句构成对比;第二句,词曲再现A段第二段第四句。衬词句的节奏形态、旋律线、音区、语气等都显现出基于前段基础上的递进式情感抒发特点。最后,运用再现手法“呼应”前段最后一句词曲,对歌曲的音乐与主题进行了有力的提炼和概括。
《草原之夜》的第一部分侧重叙事,第二部分突出抒情。全曲以开始的主题确立了整首作品的特性音调和节奏,其后以原形或变形面貌贯穿于音乐发展过程中;作曲家围绕歌词的语言声调特征,很好地斟酌出旋律起伏与声调走向的协调一致;在此基础上,再以一字多音的词曲结合方式,重在发展字少腔多的环绕旋律,创造出曲折婉转的音乐线条,加之前后倚音的使用,最终获得了如切切私语般的语气,渲染出形象塑造的细腻表情。
(三)儿童歌曲在思想内容和音乐表现上独具特色、风格不一,其中的每一首优秀作品无不散发出馥郁的艺术芬芳。《快乐的节日》写于1953年。儿童节来临之际,孩子们穿上漂亮的衣裙,胸前飘着鲜红的领巾,心怀自豪和骄傲,在公园里奔跑、欢笑,快乐而幸福。著名词作家管桦与女作曲家李群有感于这令人快慰的现实图景,于1953年的六一之际创作歌曲《快乐的节日》。它是艺术家奉献给“新中国”少年儿童的一份特别礼物,同时寄寓了创作者心中美好的愿景。
歌曲三个段落,并列单三结构(ABC)。每乐段的规模和次级结构划分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乐段四乐句(3+3+3+4)13小节,第二乐段三乐句(3+3+4)10小节,第三乐段三乐句(4+3+5)12小节,显示出灵活贯穿的音乐发展方式。
歌曲围绕单一形象的主题陈述及其引申发展所获得的变化而构成一个整体结构。几个贯穿全曲的音乐表现要素主要体现为:(1)2/4拍,律动鲜明;(2)整体规整的节奏组合中内含前行的动力及宽广的抒情,契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园风貌;(3)明朗、清新的大调式旋律与朝气蓬勃的形象塑造相统一;(4)上下行的多样化音程跳进(包括了从四、五度至六、七、八度各种音程跳进的上下行旋律语汇)创造出旋律的起伏激荡,渲染了荡漾在孩子们心问的幸福甜蜜感。(5)大调性民族风格旋律平易上口,中西合璧的发展手法融会通俗易懂的形式,从而获得了极具特色的音乐语言风格。结合歌词看,前两段音乐足歌曲主歌部分,分别对应不同内容的歌词重复演唱三遍。两段的音乐材料为引申、发展关系。第二段开始,呈对称、呼应关系的两个小分句,引入跨小节的切分节奏,使旋律线条更为舒展,形象刻画上也在第一乐段基础上延伸,进入了新的表现层次,之后的第三句铿锵有力地收束了主歌部分。第三段音乐承担了歌曲的副歌部分,以相同的歌词接应主歌的三次演唱。音乐整体看与之前材料既有对比又有变化组合、概括提升基础上的“再现”。其中对比主要表现在开始的两乐节,配合连续演唱且具有衬字意义的“跳呀”,音乐呈现出新的节奏形态、演唱方式、语气,情绪更加活泼热烈。之后,三个小分句连缀,对歌曲的前两段音乐材料进行了变化后的发展,此部分作为整首歌曲的结尾发挥了明显的总结概括功能。
这首儿童歌曲的歌词提供了轻快而充满活力的群体形象,曲作者抓住了内在的节奏律动,旋律基调为“节奏明确、积极乐观、朝气蓬勃”的进行曲风格。节奏规整而不失动感,唱起来朗朗上口;旋律跌宕而不失童真童趣,散发出明朗的抒情气息。创作者对特定时代特定艺术表现对象的艺术塑造和形象刻画生动、传神,从而铸就了其传唱半个多世纪而不衰的艺术魅力。
女作曲家瞿希贤1957年写作了童声独唱《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并于创作当年荣获全国第二次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音乐作品一等奖。1987年,作曲家将之改编为同名童声合唱。歌曲音乐部分为再现单三部结构。作曲家以通谱式记谱,有机融会引申和重复两种创作手法表现歌曲内容,创造了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音乐风格。
第一段(A段):六乐句。前四句为派生发展的音乐材料,形成开放性终止。之后,重复三、四两句,收拢性完全终止,从而在两次重复之间呈现出句尾的“属一主”呼应,加强了语气,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乐段。歌曲开始,清脆、明亮的童声即时将听众带入追忆的氛围。2/4拍,速度稍慢,音乐的弱起与歌词语气保持了最密切的关联;四分、八分、大小附点及有限的十六分音型铺设出舒展的节奏脉络;旋律自高至低勾勒出反波状的线条,作曲家在平稳进行的音列间点缀不同幅度的跳进音程,于优美、细腻的音响中涌动起内在的起伏,形象地烘托出月亮在云朵中穿行的意境;以中音区为主要阵地,音域随音乐发展不断扩大,渐进式地表达了主人公难以抚慰的心潮;旋律的主体音高素材为七声清乐,do—re—mi—sol—la五“正音”发挥骨干支撑作用,fa、si两“偏音”多在音阶流动中发挥填充作用(如第12、20小节中的变宫),或配合音乐终止(半终止)的需要使用(如第16、24小节中的清角)。此外,六乐句的句尾落音分别为宫调式的Ⅱ一I一Ⅲ一V一Ⅲ一I,这个音列从和声对音乐结构划分所发挥的作用来看,表现出内在的功能关系,为融合、统一歌曲的音响整体具有独特的意义。此段描绘了一幅皓月当空的乡村夜景,音乐主题呈现为非方整结构的乐句连续展开,主题的总体基调极其贴切地渲染出歌词特定的叙事意味,使听众与歌曲中的人物一道,在散发着麦香的收获季节,置身空旷的场院、恬静的夜晚,伴着宁和的意境,随妈妈的故事陷入追忆的思绪。
第二段(B段)开始,歌曲首先以一个大六度音程的下行跳进再反向两次级进(mi—sol--la--do),进入一个富有创意的叙事语境。音乐随故事叙述表现为上、下的音响回转、起伏,尤其不同幅度的上行音程跳进常停留在跨小节的切分延音上,形成大小不等的句读,推动了层层相叠、环环相扣的音响递进,总体情绪也在这故事叙述与音乐激扬的双重作用下,呈现出节节高涨的态势。这个段落可划分出三个乐句,之间显现起一开一合的音乐发展特征。第一句7小节,2+2+3三乐节,其中前两乐节为变化重复材料,第三乐节为派生发展;第二句5小节,2+2+1三乐节,前两个乐节为下二度自由模进关系,之后接弱起的句尾语汇;第三句5小节一气呵成,以综合、提升、概括的音乐材料和语气发挥了乐段的收束功能。之后,作曲家截取B段的后两个乐句(从高音区主音开始的下行),将之变化力度反复三次,结合歌词叙述内容,抒发主人公对往昔生活的悲愤、控诉与今夕生活的欣慰、感恩相交织的心怀。其中,作曲家用两乐句的循环、贯穿,笔者认为非常恰切并有其妙处。一方面,此处的焦点应是妈妈叙述故事的内容,惊心动魄,环环相扣,无论是歌曲中的孩子们还是欣赏歌曲的听众,其注意力必然随故事的开展而跌宕起伏,作曲家在此不使用新的音乐材料,更有利于稳固这种特定的重心;另一方面,作为讲述人的妈妈,此时一定是投入地沉浸在其讲述的内容和特定的情绪中,循环反复的两个乐句正形象地刻画了讲述人“絮絮叨叨”、“若有所思”的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曲调的反复不仅没有给听众以停滞不前的静止感、单调枯燥的乏味感,反而因乐音材料的高度凝练和集中,在环环相扣的故事陈述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使听众获得了极为深刻的艺术感受。
A1段完全再现第一部分词曲,但完全再现并非等同于其初次呈示的原始陈述功能。在经历了一个音响和情感跌宕起伏的过程之后,此时的情境已从对过去的追忆回归现实生活的夜晚,月亮依然在云朵里穿行,晚风依然快乐的歌唱,而妈妈的故事却让孩子更加珍惜他们幸福的新生活。悠扬旋律回荡在夜空,是那样经得起品味,留“香”久远!
二、歌曲是音乐与诗歌构成的
矛盾统一体
歌曲作为伴随社会生活的一种主要音乐体裁,其样式看似短小,但对它的理论把握却异常繁难。音乐美学家王宁一先生在论文《从词曲关系看歌曲中的音乐形象》中,围绕歌词与音乐两个主要方面如何相互作用、塑造歌曲的整体形象,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文章认为,歌曲是音乐与诗歌的综合体,其中音乐发挥并扩展着文学形象的内涵,赋予它以听觉方面的具体性;歌词则限定并解释着音乐形象,赋予它以概念方面的确定性。两者的关系有形式和内容两个主要方面,前者是歌词的语言规律和结构规律与音乐陈述的相互关系;后者则是音乐形象和文学形象之间的关系。对于歌曲特殊本质的理解,只有在诗歌和音乐之间的全面关系中才能见出。
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中。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刊上摘记的一首诗歌,作者姚晓舟(笔名蕉萍)为山西铜川矿务局焦平煤矿的普通职工。作曲家朱践耳将这首小诗谱写为一首融亲切抒情与淳朴叙事两种风格的独唱歌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由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首唱,后经藏族青年歌唱演员才旦卓玛通过共和国第一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将之演绎为翻身做主人的藏族人民对共产党感恩之情的经典表达,流传广泛而深远。
歌曲的八句歌词包含了丰富的思想感情,平实、真切地袒露了雷锋与党亲切谈心的心境。作曲家在整体理解歌词思想和情感内涵的基础上,展开艺术想象力,创作了一首再现单三部结构的歌曲。其中,第一乐段四句歌词对应起承转合关系的四乐句旋律,词曲同构,音乐流露出民间歌谣体裁的抒情特点,以中等速度演唱,亲切地抒发了主人公“把党比母亲”的真挚情感。第二乐段在同步对应第二段歌词之后,重复后两句歌词,推进音乐发展,直至第四个乐句以富于动力的节奏和向上模进的音调,将歌曲推向高潮,终止在属音,为主题再现做好和声准备。整个第二乐段在体裁风格(叙事与进行曲两种风格)、舰模容量(从“旧社会鞭子抽我身”的诉说,至“共产党领导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的豪迈,具有宽广的题材容量)、结构方式(不等长的四个平叙乐句)、节奏形式(从开始的舒缓节奏转换为进行曲体裁的步伐式节奏)、音乐材料(使用新的音乐材料和旋律发展手法)、速度(由慢速转中等偏快速度)及音区安排(由深沉的低音区向明亮的中高音区逐渐伸展,情绪随之变化)等方面,都与其前、后两部分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乐段再现第一段词曲,之后,重复最后一句歌词写作结束句,整首歌曲在激昂、高亢的音响中收束。
依据对以上分析的理解,音乐在塑造形象时,首先遵从文学形象的本质规定。作曲家从歌词所蕴含的特定生活形象出发,结合自身深刻的情绪体验,透过歌词看清音乐的内涵,驰骋丰富的艺术想象,挖掘歌词中的合理乐意,提炼具有概括性的音乐语汇,并将之纳入音乐发展的逻辑手段之中,最终与歌词文学形象的表达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另一方面,音乐作为形象思维的一种独立形式,它具有自己所独有的特点和规律性。当旋律进入调式体系形成独立的表达形式时,反过来又借助于语言的音色、节奏等多种变化的可能性发展并丰富了语调的表情意义,使音乐的表现更加富有隽永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看,音乐创作又存在着较为自由的空间。因为,歌词中的词句作为语言,在音响上并不具有乐音体系的那种精细准确的逻辑规范,它在音的高低、节奏的长短,以及整体结构方面的表现是粗略的、相对的,故而同样的歌词可能在不同的音区,以不同的节奏形态、旋律线条和音乐结构样式都可获得不影响基本词意前提下的音乐表达,作曲家正是发挥自身能动性地运用艺术创作的自由空间,去创造尽可能理想的作品。
三、旋律是歌曲的“生命线”
音乐的各种表现要素中,旋律最接近灵感,被称为“音乐灵魂”,这一点在单声部的歌曲中更是如此,它通过旋律来结构音响的整体,表现出上下传递、辗转相承、通达连贯、蜿蜒不绝的千姿百态。某种意义上说,围绕歌曲作品的研究,把握了其主题材料——旋律,也就基本上把握了整首作品。
中外音乐文化传统是一条河流,每一位作曲者都受到它的滋养,这就使优秀歌曲常呈现出一些共性的规律和方法,如作曲家常选用内涵不同的音乐主题连缀发展,多侧面地塑造音乐形象;通过不同的音乐风格和音乐要素设计展现歌曲不同层次间的对比;通过融会民族调式使旋律展现民族特色与乐观气质于一体的艺术风格;围绕歌曲的形象、意境和思想感情表现,着重于音乐本身的构思。此外,好的歌曲都是建立在现实生活体验基础之上的,对社会现实与人生的理解愈深刻,作品的情感内涵就愈丰富、厚实,显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因此,在旋律的形式要素和意义要素的结构和对应关系中去理解旋律的深层背景,把握旋律符号承载的外显和内隐的整体文化信息,是一种可行的研究思路。
创作于1956年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芦芒词,吕其明曲),是新中国初期拍摄的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故事叙述的主题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1940)活跃于山东枣庄铁路沿线的一群游击队员身上。他们机智勇敢,与敌人周旋,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被当地百姓冠以“飞虎队”的美名。
歌曲的词曲同步对应,均为带再现的单式四部曲式结构。音乐上,同一主题的呈示、发展、再现使单一音乐形象的刻画获得了不同层次的深化,最后在新的高度上获得统一。
第一部分(A段,8小节)以写景状物为主,展现了游击队员在紧张战斗之余享受悠闲时光的画面。这个富于生活气息的剪影同时烘托出抗日战士豁达乐观的性格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本是普通农家朴实自然的生活场景,而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却成为人们难得而宝贵的瞬间享受,由此反衬出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现实灾难。音乐与歌词相应。四四拍,韵律平衡、持重;顺分与均分音型为主的节奏框架,舒展、从容。各4小节的两个对称乐句构成方整乐段;每句又可分出2小节的乐节语气(以长时值延长的羽音呈现),节奏为重复或变化重复关系。音乐材料用加变宫的六声徵调式,旋律在不同乐句问呈派生发展特征,而每乐句的两乐节间呈自由模进关系;由音程跳进获得的上扬音调贯穿于每个乐节,音乐气息悠长,婉转动听,流溢出鲁西南山东民歌的独特韵味。
第二部分(B段,11小节)歌词从第一段温馨的生活画面切换至硝烟弥漫的战斗场景。演唱形式由前段的独唱变换为男声合唱;节拍由4/4变换为2/4;节奏由舒展、从容变换为紧凑、动感;旋律由婉转、悠扬而自由变换为顿挫、整齐而有力量;音乐起句由前段的正波旋律语汇变换为以下行开始的反波音调。所有这些音乐元素的变换和运用,都是作曲家苦心经营以贴切、传神地刻画游击战士在铁道线上与鬼子周旋时那矫健的身姿、敏捷的动作和果敢的形象,唯有六声徵调式的音乐材料和上扬式音调渲染出的山东民歌韵味与第一段一脉相承。
第三部分(C段,11小节)歌词是第二段的延伸。前两句描述游击队员与鬼子斗智斗勇的具体细节。配合其中四个具体的动作,音乐节奏安排得更为紧密,并运用十六分节奏的动力性弱起,从一个个传神的动作描绘中映射游击战术所蕴藏的口大威力。之后,以“钢刀插入敌胸膛”这个生动的比喻,说明机动灵活、神出鬼没的游击战使鬼子断无招架之力,他们魂飞魄丧,惶惶不可终日。此时的音乐节奏从紧密、急促转向宽广、舒展,并以一个七度音程的上行跳进激扬起振奋和高亢的情绪,形成了全曲的高潮,刻画战士们面对胜利的欣慰和豪迈。之后,音乐在音程跳进后的反向平稳进行及音区趋于回落的过程中,平稳收束。
第四部分(A1段,9小节)的歌词与第一段相比,仅有两处变化:第一句“两边的太阳快有落山了”改为“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第二句“微山湖上静悄悄”改为“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两处改动一是说明时间次序,二是指故事叙述的内容因果关系。音乐再现第一段之后,配合末尾两个具有收束意味的衬字,从低音区主音(徵)连续两次四、五度音程上行跳进,最后停留在高音区带半音前倚音的结束主音上。
整体观察,创作者紧密围绕了电影故事的叙述和人物刻画,以真挚感人的笔触写作了朴实无华的歌词和音乐,创造了一首既具有高度写实又散发着浪漫气息的歌曲精品。歌曲以抒情主题(A)开始,在经历了中间两个段落的发展或对比之后,再现此抒情主题,从而以一个稳定的、具有一定向心力的拱形结构支架,呈现出整首歌曲“起一开一合”的音乐发展脉络。抒情主题在歌曲中具有主导地位,它在一头一尾出现,却发挥了呈示与概括的不同功能,彰显出不尽相同的题材内涵。“微山湖”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但宽阔的水面下蕴藏了无尽的力量,她滋养的英雄儿子为了让她永远安宁和富饶,正在与入侵者进行着殊死搏斗,用正义的力量迎接就要到来的“鬼子的末日”。如今,这首歌曲早已跃出纷飞的战场,也越过了新中国初期的那个时代,而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恒久激荡着的,是那熟悉的旋律、英雄的影像和朴实的人们……
结语
“音乐美是内容美与形式美的统一”。歌曲是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体,歌词主要反映内容,音乐则主要代表形式。创作过程中,作曲家首先从对歌词的斟酌中获得一定的心理体验,他们研究歌词获得的心理体验愈鲜明、愈生动、愈深刻,进行音乐转化时就会愈顺利,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就愈大。之后,作曲家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并调动构成音乐的物质材料——乐音,将研究歌词的心理体验物化为具体可感的音乐形象,最终实现内容与形式在歌曲作品中的统一。某种意义上说,一部音乐作品在它完成时即已成为“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体”,其客观存在着的美,是审美主体进行音乐体验和评价的最重要依据。歌曲既是歌词与音乐两方面的有机结合,而音乐则又是基于乐音组织的有机体,那么当研究者或欣赏者面对已经完成的作品时,就应熟悉和掌握音乐发展的规律,了解作曲家在作品中如何按照音乐美的规律组织乐音材料,体会作曲家在作品中如何综合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以塑造鲜明生动的音乐形象。基于这种认识,本文对新中国初期的部分歌曲进行了较细致文本分析,期望从对作品的感受与鉴赏中获得审美层面的认知和体验,并使之成为审美主体进行艺术体验和评价的参考依据。
另一方面,文学艺术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特定的文化表达方式不仅与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生存环境密切相关,而且生动地记录了人类情感的脉动。罗曼·罗兰曾说,“一切能够永存的艺术作品,是用它的时代的本质铸造成的”。“新中国17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代自不例外,词作家乔羽对这一时期的歌曲有过评价:“50年代的歌曲虽然比较单调,但那‘红彤彤的劲儿,却是那种岁月里必不可少的,极富战斗性。歌曲的创作与当时社会背景紧密相连,每一首歌曲中,我们都不难寻找到明显的时代烙印。”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决定了产生于其中的歌曲作品的题材特征和音响风格,这对于研究那个历史时期的歌曲作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