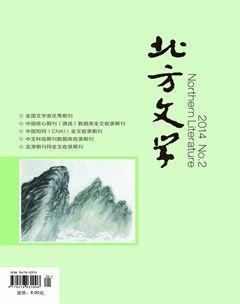辛格与余华的“苦难”追寻
张兰英
摘 要:辛格和余华都是用生命写作的伟大作家,他们关注现实的苦难并不停地思索生存的意义。在对“苦难”主题的选择,以及选择这一主题的原因和对“苦难”的处理上,两位作家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当然,由于作家不同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以及个性特点又让他们的作品打上了专属的印记。
关键词:辛格;余华;苦难
作为本民族骄傲的儿子,辛格和余华都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责任感和荣辱感,作为有良知的作家,他们时刻不忘的是用他们的笔消除世间的残忍和黑暗,化解人间的痛苦和灾难,正因如此他们的作品都是从灵魂的高度探求人类的生存状态,表达特有的人文关怀,无不充斥着浓厚的悲悯情怀。
一、“苦难”的主题
在作品主题的选择上,辛格和余华的共同点是都执着于对“苦难”的阐释。“辛格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受奖演说》中宣称自己是犹太民族的儿子,内心汹涌着拯救人类的一腔热血,终生锲而不舍地探寻着永恒的真理和生命的真谛,对苦难深重的犹太民族处在即将到来的危险中有不敢掉以轻心的强烈关怀。他袒露了对民族解放多次努力而始终找不到真正的出路的忧虑和永不放弃的决心。”[2](P104)辛格这种为苦难民族寻求救赎的决心和坚持用意第绪语写作的行动表明了他对犹太民族炽热的忠诚。犹太民族的历史可谓是一本道不尽的血难史。19世纪末反犹主义产生了;20世纪初希特勒的灭绝性大屠杀开始了;二战后,斯大林的大规模迫害爆发了。辛格经历或目睹了太多犹太民族的苦难,作为一个以拯救民族为己任的伟大作家,辛格无时无刻不在为古老而神圣的弥赛亚情结忧思,他相信上帝是存在的,是怜悯世人的,“但伟大的智慧怎么可能对无辜生命的苦难视而不见呢?”所以这种“民族忧煎情结”[3]不断困扰着辛格,正因如此他的作品中苦难意识如同血液一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开来,甚至所有的作品都逃离不了这一永恒的主题。
《傻瓜吉姆佩尔》中傻瓜的形象正是苦难犹太人的缩影,他一生谨小慎微,虔诚老实,受尽欺压,善良宽恕,但却一生都找不到出路、得不到救赎。《那里是有点儿什么》中的尼切米亚拉比开始怀疑上帝是否真的存在,他放弃宗教,放弃信仰,只身前往华沙,目睹一幕幕污浊的社会生活图景,终于失望返回贝契伏镇。在弥留之际他终于又回到了上帝的怀抱,嘴里喃喃道:“那里是有点什么。”上帝对犹太人的苦难视而不见,弥赛亚终究没有骑着白毛驴将犹太人救起,那么到底还要不要无条件相信上帝?这既是作品中吉姆佩尔和尼切米亚拉比的声音,当然也是作者百思不得其解之处。作品中人物的一生无论短暂还是漫长,都是一个不断探求生命真谛的过程。结尾处辛格用宗教的力量使主人公在弥留之际获得解脱,但这种同情的安排毕竟是逃避现实的一种短暂的慰藉,说到底还是一种苍白无力的安慰。无疑,辛格独特的宗教背景深深影响了他的上帝观,他在求解的过程中始终没有背离上帝存在的信仰,他也一直相信上帝是同情和怜爱苦难的犹太人的,所以在《傻瓜吉姆佩尔》、《那里是有点什么》和《短暂的礼拜五》等小说中才会安排人物投入上帝的怀抱,获得温暖和关爱。至于上帝究竟在哪?信仰能否拯救人类?如同作者一样,我们很难得出结论,但是背离信仰是一定得不到救赎的,这在辛格很多作品中都有体现,如《三次偶遇》。
同辛格一样,余华也是一位关心人类生存状态的作家,他的作品同样旨在表现人类生存中的苦难,无不充斥着作家特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曾说过:“文学的力量就是在于软化人的心灵,写作的过程直接助长了这样的力量。它使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和伤感的同时,也使他的心灵经常感到柔弱无援……让我们生离死别后还是互相热爱。”[4](P43)他的创作也紧紧围绕人这一永恒的对象,表现出对人类生存状态的高度关注。不过,他对苦难主题的关注尽管与辛格一样抓住了本民族弱者个体的现实苦痛,探求解脱之路,但却少了宗教信仰的关怀与质疑。
《十八岁出门远行》用一种不习见的方式表达成长过程中必须经历的苦楚,阐释了人性恶的主题。《一九八六年》用冷峻的笔调回顾了文革的灾难,历史前进的脚步虽已将其淹没,但苦难却永远刻在人们心中。《现实一种》作家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兄弟不像兄弟,母子失去该有的关爱,就连孩子也享受着由暴力带来的愉悦和痛快,这样的一幕幕让世人陷入无尽的痛苦之中,也引发了作者对于生的思考。《活着》是余华苦难意识的集中爆发,也是余华本人创作转型的重要标志。《活着》平静并残忍的叙述背后是作者排山倒海的激情,富贵的“活”有种惨烈的庄严,余华曾说过“但丁告诉我们:人是承受不幸的方柱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物体能够比方柱体更加稳定可靠?”[4](P45)从《活着》开始,余华作品中多了对苦难的温情的关注,他开始探求救赎之路,在强大的苦难面前人就像面对着无法改变的宿命,唯一的出路便是忍受。人的忍受能力是强大的,富贵正是这最稳固的忍受苦难的“方柱体”的典型代表。《许三观卖血记》同样是余华关注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许三观一次次地用卖血来解决生活给他出的难题,他发现了卖血的即效性,但这着实是为生活所迫的无奈之举。生活使他进退维谷,但同富贵近似麻木的状态不同,许三观的状态是乐观的,当他再次卖血因为年老被年轻的血头赶出来时,许三观为自己再也没有能力招架生活的困境时嚎啕大哭,最后用幽默的一句缓解了糟糕的心情:“这就叫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5](P254)苦难是无法回避的,但人可以改变自己面对苦难的态度,余华用这种下层人民特有的幽默和乐观来化解无边的苦楚,比起《活着》又前进了一步。
二、“苦难”的原因
辛格和余华选择并突出表现“苦难”这一主题的原因是同中有异的。辛格的苦难意识其一源于他曾经亲历或目睹的犹太人的悲惨遭遇。他曾说过:“我的民族承受过人间疯狂到无以复加的沉重打击,作为这个民族的儿子,我对即将到来的危险岂可掉以轻心。”犹太人经历了太多上帝“赐予”的灾难,很多灾难是辛格未曾亲历的,但他目睹了希特勒大屠杀和斯大林的迫害,血肉模糊的悲戚场景令我们的作家如何做到视而不见?当苦难成为一个民族历史的主旋律时,它自然就成为对民族有责任感的作家无法回避的主题。
余华作品中的苦难意识则更多源于对现实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思索。余华出生、成长、心性趋于成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正赶上文革时期,余华经历过文革的动乱,在那场灾难中一切价值都被摧毁,一切信仰都要重新评估。从历史的层面上讲,文革已经距离我们几十年,但在人们内心,尤其是像余华这样一个有着敏感内心的作家来说,它永远不可能褪色。《一九八六年》的创作正是对文革给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带来的身体和精神毁灭的控诉。
不同的成长经历和文化背景是造成辛格和余华选择“苦难”主题的不同原因,但作为当代伟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意蕴并没有局限于本民族人民的生存状态而是早已超出民族国家的界限,着力反映人类面临的普遍困境。
辛格说,“生我育我的是属于一种善恶兼而有之的世界。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偏不倚的,你或者奉行神明,或者违背教规。二者必居其一。”可是现在这种思维方式已经绝迹了,不仅是在伦理观上,而且在其他很多方面人们的精神层面都产生了危机。孩子们不相信善恶的存在,他们成为在道德上中立的畸形儿,中庸调和并不能使他们摆脱危机。这里作家表达了对现代社会信仰缺失的深深忧虑。宗教的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宗教毕竟给犹太人提供了精神上的信仰和依托,使他们能够清楚地辨别是非善恶。所以辛格忧虑地说过:“大屠杀没有把犹太人彻底消灭,现代性这把温柔的刀子反而有可能把犹太人连根拔除。”
对于新时期的中国,余华说:“今天的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巨大差距的中国。我们仿佛行走在这样的现实里……唯一不同的是,欧洲耗费了四百年的历史,在中国只需要三十年。”[6]余华简短的文字尖锐地指出了中国的现实,在经济急速发展的同时,带来的是文明的迷失和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德律令仿佛失去了原有的约束力。所有的这些无疑加重了人们生存的苦难。所见所闻,所感所受让余华有了挖掘表现这段历史时期苦难生活得雄厚资本,于是他的笔的指向也就自然而然凝聚在了这样的主题上。
辛格及余华作品中的人物所面临的精神危机同时也是整个人类所面临的问题。20世纪以来,现代人面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诱惑开始变得眼花缭乱,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他们往往只顾及自己的利益,道德意识日渐淡薄,加上宗教意识,信仰意识的缺失,人们在精神层面的迷失迫使作家在作品中发出强烈的呼吁,呼吁道德的回归。
三、“苦难”的处理
对主题的选择其实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对主题的把握与处理上。在对苦难的处理上,两位作家不同的是:辛格独特的犹太教背景令他时常将宗教作为人类获得拯救的途径,并且他一生都在为探求民族出路做着锲而不舍的努力和尝试。《傻瓜吉姆佩尔》、《那里是有点什么》和《掘墓人》中作者安排的宗教救赎正是这种处理方式的体现。余华则更多地关注人性,他只负责把人物搬到作品中,却并不急于指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作家通过他们揭露人性的虚伪和残忍,最终将人物隐匿在现实中。这种差异正和两位作家生活的环境有很大关系,辛格目睹了太多犹太人惨遭杀戮和驱逐,凡是关系到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都会令作家时时不得安心,时刻处在高度紧张和危急的情形中。“根据他的秘书回忆,辛格的神经极为脆弱。他在成名之后到去世以前,一直有个习惯,总是把存款、支票、现金带在身上,以防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到来的第二次“希特勒大屠杀”。”[2](P37)他随时做好可能流浪的准备,这种无所依靠的漂泊感对作家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所以探求一条使全民族获得解放的出路是辛格不能回避的问题。余华生活在和平年代,他面对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建设”问题,这是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没有血淋淋的杀戮,没有命悬一线的危机,他像是一位社会观察家,批评家,所以作品着重于对人性的剖析。辛格的作品不仅写出犹太人的苦难,同时也是对全人类苦难的关怀。犹太人的遭遇里也有很多现代人正在遭遇的。而余华的作品是对国人某个阶段人性的展示,从这一点看,辛格在对苦难关注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要胜过余华。
当然,辛格为他的人物找到宗教这一途径来消解现实的苦难,余华专注对人性的分析却并没有给他作品中的人物指出明确的出路,这的确是他们对“苦难”处理的显著区别。可是,这一表象的不同背后深藏的是我们伟大的作家共同的悲悯情怀,是他们共同的对人类的普遍关怀。表面上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实则是殊途同归——为了本民族的复兴而写作,为了让人们生活得更好。
参考文献:
[1]余华.温暖的旅程[M].北京:新世界出版,1999
[2]傅晓薇.上帝是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3]傅晓薇.辛格:民族忧煎情节探析[J].外国文学评论,1998(3)
[4]洪治纲.余华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5]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6]余华.差距[R].上海:上海中德心理治疗大会,2007